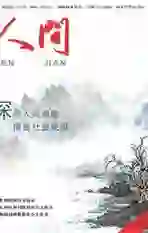孟子的“性善论”
2016-05-14闫璐璐
摘要:关于孟子性善论的问题学界一直有很大的分歧。本文主要依托徐复观先生的观点,以心善来言性善,不仅是因为人之所异于禽兽的几希,更重要的在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在现实中,由于人过度的耳目之欲和外在环境的影响,使得人丢失了自己的本心,因此,需要人对善的不断存养和扩充,以找寻人丢失的善的本心,使人成之为人。
关键词:孟子;心善;性善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127-03
《孟子》一书中,最早提出性善说是在《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将过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但孟子之所谓性善,是说一般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也只是因为他是“人”,只是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1]关于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观点,可以通过他对告子人性无善无恶的驳斥中找到根据,告子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告子认为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恶,但后天的习行却可以使之为善或为恶。孟子以水流之喻对此作了驳斥“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不善,水无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以水必然向下来推断人性本善。
一、人心为善,以言性善
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孟子在中国文化中最大的贡献,是性善说的提出。”[2]孟子是将性善论纳入哲学思想当中进行讨论的第一人。为了论证性善论,孟子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为其逻辑起点,以此推论出人生而就有的“四心”、“四德”,性由心显,以心善言性善;孟子通过与告子的辩论,论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几希”使得人和动物有了质的区别,这“几希”便是人之为人的道德本心;同时孟子通过天与心为其性做保障,用心承接性,即“尽心知性知天”。
(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性善论的逻辑起点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以下这段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性善论同时也是理解心性关系的关键。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此预设了一个情景来论证“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如果突然看见一个幼子将要掉入井中,无论是谁都会有“怵惕恻隐之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的产生是人们当下的本能的反应并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过程。那么人为何会有这种不假思索的同情心呢?孟子没有做直接的回答而是通过反面陈述来排除一切可能:人们产生“怵惕恻隐之心”,不是为了与孩子的父母结交,不是想要在乡里朋友中间求得好的名声,不是因为讨厌孩子的哭声。既然这都不是产生“怵惕恻隐之心”的原因,那么产生这种同情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里的“乍见”二字可以为我们找到产生同情心的根源。“乍见”二字表明了情况发生的突然性,是在人毫无预知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此刻人所作出的心理反应也就是最为自然,不参杂任何杂念的,发自人内心的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是天所赋予人的。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的,所以面对“孺子将入于井”,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此孟子推出人皆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若没有这“四心”,也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人,因为“四心”是“仁义礼智”这“四德”的萌芽。人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善端,与人有四肢一样是自然本能的,而“四心”是人本性的显现,人心本为善,故人性本善。
(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孟子主张人禽之辨,批评告子的“生之谓性”。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 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告子认为人生来就有的生理欲望就是性,他关注的重点在于人和动物的共同点。孟子反驳道:“生之谓性”,就如说“白之为白”吗?他指出白羽、白雪、白玉就白色本身来说是彼此相似的,而“性”也有人之性、狗之性、牛之性,说“生之谓性”难道人性就是狗性、牛性吗?孟子的驳斥是有道理的,因为告子所说的“白”只注意到白色东西的共同点,而“性”就是要注意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
这就是孟子的独特之处,告子只着重于人和动物的相同点,而孟子则认为正是因为细微的差异才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这表明了人与一般的动物,在饮食饥渴等一般的生理本能上都是相同的,人同时具有的生理欲望,是属于人的动物性并没有体现人的特性,也就没有被孟子列入人性的范畴。在孟子看来,正是这一点“几希”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孟子不是从人身的一切本能而言行善,而只是从异于禽兽的几希处言性善。几希是生而即有的,所以可称之为性;几希即是仁义之端,本来是善的,所以可称之为性善。”[3]
(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性善说是在“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体系中确立的。孟子从人皆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引出“四端”之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四德”(仁、义、礼、智)之源,然后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的心性体验,将心、性、天之间完全贯通。孟子所谓“尽心”,即存养扩充人的四端之心并在现实生活中践行善。在这里应明确区分心、性、天这三个概念。所谓“心”,对孟子而言主要指的道德心,心具有反思的功能,这是天所赋予的。所谓“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是人区别于动物最本质的内容。所谓“天”,孟子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他说:“尧、舜、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孟子以“莫之为而为者”来定义天,也就是人无法做到但却真实的出现了,这可能是天意。孟子的天是具有道德意义上的天。关于“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将心的善端完全扩充,则人潜伏的善性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显现,就可以知道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本善乃是天所赋予人的善端的显现,从而就可以知道仁义礼智是上天所赋予的,也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
二、性本为善,为何有恶
在孟子看来,人的本性是善的,是天所赋予的。那么恶又从何而来?归纳孟子的观点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是来自人的耳目之欲;二是来自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两者都可以使人将自己的“本心”放逸掉。
(一)人的耳目之欲。
就人欲而言,孟子并非否定人的生理欲望,只是主张由思考的心做主,对人的欲望要求进行合理的满足。欲望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只是因为人们过分的欲望要求超出了其本身的界限,不懂得适度原则,使得过分的欲望成为了恶。“他说‘饮食之人,则人皆贱之矣,是因‘为其养小以失大(《孟子·告子上》),即使为了欲望而淹没了心,只要不养小而失大,则‘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孟子·告子上》)。由此可知心与耳目口鼻等本为一体;口腹能得到心的主宰,则口腹的活动,也就是心的活动的一部分,所以口腹此时也理性化而不仅为尺寸之肤了。”[4]
耳目欲望虽本身不是恶,但恶却是从耳目等欲望而来。下面这段话这是表达了这个意思,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由此,孟子区分了人的耳目之官和心。他把人的耳目之官称为“小体”,把心称为“大体”,他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一个人如果能够以心支配耳目之官,就是“大人”;如果从其“小体”也就是听从耳目之欲,而不是听从思考的心,那就是“小人”。“大体”“小体”是天所赋予的,但“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感官如果不能受能思考的心的指导,在与外物接触时,就容易受蒙蔽而走入迷途。因此,耳目之官应跟随心的引领,这样才可以避恶扬善。
(二)外界环境的影响。
孟子非常重视环境对于一般人的影响。心虽本为善,但如果没有适合恰当的环境,就人而言,心的思考功能就无法完全的发挥,由此也会失掉心对于耳目之官的引领的正确能力。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跷,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这段话的是孟子来解答人的本性都是善的,但为什么每个人的成就都有所不同?孟子认为这是因为环境不同的缘故。如他所举的例子,关于种大麦,播了种并耙松土地,种的地方相同,时间也相同,麦子蓬勃的生长,到夏季的时候都成熟了。即使有所不同,也是因为土地肥瘦、雨露的滋养、人工的管理不一样的缘故。以大麦为比喻,人性也如此,虽秉同一的人性但却有不同的成就,完全是因为外界环境的原因。
而在诸多环境因素中他特别注重经济生活的影响。“当时决定经济的是政治,因此,他便要求以仁政代替当时的虐政(“民之憔悴于虐政”)”[5]孟子认为实行仁政的前提条件是让人民在生活上有保障。因此,他提出了在制民之产上改革井田。所以,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要实施仁政,就必须从改革井田开始。孟子的这种改革,使耕者有其田是解决民生问题,推行仁政的关键,是最根本的经济措施。进行土地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让农民有地可耕,这样就可以为人民的生活条件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他认为,如果能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发展生产,就可以使人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
三、如何为善
钱穆先生指出:孟子所谓本心,就是“本可以为善之心也”[6]“孟子所说的性善即是心善,而心之善,其见端甚微(四端,几希),且又易受环境的影响,易于放失。”[7]由此,孟子不但以心善论性善,把善心作为性善的本源,而且也提出了一系列为善的理论。
(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虽主张性本善,认为人生而有善端,但是人过度的耳目之欲会蒙蔽人的善性,使人的善性不能发挥而显现为恶。因此,应通过教育找回被人们所放逸掉的的本心。他指出:“人,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有,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仁是人天生就有的,但人不知其是人之本性所有,反而给它命名为人心,可以看出仁是人身体变化的主宰,因此不可以丢失它;而义之行事之宜称为人路,可以看出这是出入往来必由之道,因此也一刻不可以舍弃它。但人们放弃了这样的大道不走,丢失了本心却不知找寻。接着孟子以人们家中的鸡犬丢失尚去寻找,但人的道德本心丢失却不知寻求为对比,发出了“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感慨。
强调“求放心”,就是要求人们找回迷失的本心,把丢失的善心找回来。那么又该如何“求放心”?孟子认为最根本的在于“立大体”,即确定和扩充道德理性,以理性来排除外物的诱惑,控制感性情欲的发展,使人能够具有完善的人格,保持善性不失。
(二)善的存养与扩充。
求得放心之后便是善的存养与扩充。存心之道在于存于仁、礼:“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君子不仅仅是存心于仁礼,更重要的是要时时涵养,“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孟子在得出这个结论时举过一个例子,牛山上曾经草木丰盛,但周围的人们却不爱护,经常砍伐和放牧,使得牛山上光秃秃的。以至于后来当人们看到无任何草木的牛山,就认为牛山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没有茂密的树木。同样的,仁义之心是每个人所拥有的,但人们如同砍伐树木一样使自己所拥有的善端、本心日益减少,使得人们误以为人本身就是这样,但实则是人们自己没有存养保持它,使得善心日益丢失。
如何养心呢?孟子认为在于“寡欲”,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多欲,则耳目的官能可以压倒心的作用。寡欲,则心所受的牵累少而容易将其本体成露。但如前所说,欲并不是恶,所以只主张‘寡,而不主张‘绝,这是与宗教不同的地方。”[8]关于善的扩充,孟子认为:“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的“扩充”是基于人心的自觉性和自发性,他认为人心具有“不学而能”的“良能”,以及“不虑而知”的“良知”,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良知”与“良能”都根植于人生而就有的四端之心,皆为具有思考功能的心所引导。由此可见,存养扩充的功夫是相互依赖又不断递进的过程,从求放心、存心、养心以至于扩充即尽心。
(三)养浩然之气。
就如何扩充人心中之四端,孟子根据自己的修养体验提出了“养浩然之气”,“‘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 配义与道;无是, 馁也。是集义所生者, 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 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所谓“浩然之气”,一方面要靠把握义与道才能达到,另一方面,要靠“养”,即持久不懈的修养和锻炼,“以止养而无害”才能够巩固、持久和扩大。如何“直养”?孟子解释说:“必有事焉,而心勿正,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用正义来培养“浩然之气”这种精神力量的时候,既不能中止,也不能拔苗助长过于急躁。用持续不断的毅力来“养气”,实际上也是意志锻炼。孟子和孔子一样强调“志”在培养理想人格中的作用。孟子认为读书人应该“尚志”即使自己的执行高尚,那么何为尚志?孟子说:“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要使自己的志向高尚,无非是行仁义罢了。杀一个无罪的人,是不仁的;不是自己所有,却去取过来,我不义的。以仁为安身立命之所,以义为行动准则,“居仁由义”,大人之事便齐全了。这里的“大人”就是具备理想人格的人。
通过锻炼和培养“浩然之气”,就可以产生大丈夫人格。孟子这样描绘它:“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朱熹注曰:“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与民由之,推其所得与人也;独行其道,守其所得于己也。”[9]可见,“这种大丈夫人格是以仁义为根本,以“与民由之”为宗旨,以浩然之气屹立于天地之间,力行其道而不为外物所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上下于天地同流。”[10]这种人格正是为善的必然结果,是性善的人格化表现。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
[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
[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
[6]钱穆.《孟子研究》上海: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8年,第89页.
[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8]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
[9](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70页.
[10]赵法生.孟子性善论的多维解读【J】.孔子研究,2007(7).
作者简介:闫璐璐,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