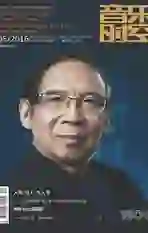中国二胡·中国料理
2016-05-14拓化贤
拓化贤
主持人:关老师,岳老师,你们好。我想就二位老师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分别做一下请教。首先,我想问一下关老师,您为何会提出“中国二胡·中国料理”这样的命题呢?这个命题又是从何而来?
关铭老师:这个事情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日本作曲家给王国潼先生写过一首二胡曲,在日本的大阪上演,大约有二十多分钟,这首作品技术难度很高,王国潼老师演奏完之后把这个录音寄给我,我听完以后我觉得这是中国二胡日本式的料理,因为他没有中国元素。所以在2008年上海之春国际二胡邀请赛的时候,作为那次大赛的评委,我在一次研讨会上我做了题目为《中国二胡必须中国料理》的发言。
主持人:《中国二胡必须中国料理》这篇文章中的中国二胡中国料理都包括哪几个方面?您觉得中国二胡应该如何料理呢?
关铭老师:料理这个词实际上是中国的文化,譬如料理家务,这就有料理这个词。料理就是如何去做,中国二胡是中国的民族乐器,中国的民族乐器如何去操作?如何去写作?这就是料理。我觉得料理就是一定要把中国二胡做成中国的,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这个国界必须明确,因此我在以往的创作中或之后的创作中是遵循“中国料理”这几个字的,中国料理就是要讲母语、讲国语、讲中国的地方语。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东西,这是中国的理念,这种理念指导下要用中国的方法。中国的方法很多,比方用中国的音阶、中国的调式、中国的音律,以满足中国人的欣赏习惯。用二胡常用的语言,也就是二胡善于表现的语言去写作品,这样会更接地气。在二胡音乐写作上第一位的就是要选择好音乐语言,中国人是中国的作曲家为中国人写东西,必须要用母语,什么是母语呢?普通话,地方话都是母语,我们用这些话与老百姓对话,老百姓就能听得懂,能记得住,能留得下。
二胡作品首先要写好旋律,旋律是二胡作品的灵魂。在写好旋律的前提下,必须有现代技术的展现。中国二胡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发展,现在的技术程度可谓炉火纯青,不管作曲家写的多难,多蹩手,演奏家都可以非常顺利的演奏下来。所以说技术在二胡作品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技术必须要融入到旋律之中,如果是为技术而写,那不是一个乐曲,那可能就是一个高难度的练习曲。
主持人:现在的二胡曲已经多达2000多首了,那么您认为这些作品中哪些是包含中国基因的?哪些又夹杂了外来基因呢?
关铭老师:在二胡曲库中大概有人统计过是2000多曲二胡曲,但是我们常见的或出版的或音乐会上的常用的曲目也就100来首,大部分都放到文库中了,没有使用。但这100多首里面,除掉传统作品以后,还有一些现代作品,包括比较时尚的作品,这里面传统作品没有什么说的,全是按中国料理走的,一部分现代作品也是用中国料理的方法加进了一定的外来因素,最后一部分时尚作品。现在有音乐学院的老师或一部分学生写了一部分的现代作品,我说这个现代是比较时尚的,它与国际接轨了,用国际上常用的创作手法去写中国的东西,这里有外来因素,所以二胡的可听性就大大的少了。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问题,因为这些作品流行圈非常小,一般就在音乐艺术院校这个圈里,老百姓基本上是很少接触的。如果拿这些作品为老百姓服务,那么麻烦就大了。
主持人:岳老师,请您跟大家说两句?
岳峰教授:各位同仁大家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首先我想说的是,张国亮老师搭建的这个平台,对胡琴同行很有吸引力,因为它把全国院团的专业同行们数百人聚集在一起,使我们有机会不受地域限制、不受时间限制,随时都可以在一起交流,能第一时间了解同行们的信息。
刚才介绍时,用了“民乐学者”这个词,我觉得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是指学问者;第二是指学习者,显然我是第二层含义,我是个民族音乐的学习者。今天设计的这个学术交流栏目也很有意思,因为可以与更多的年轻人沟通。在近些年来参加的十多次全国大型学术研讨会中,多则四五十人,少则二三十人,有更多的同行没有机会听到从各个学者、各个角度对我们这个学科的不同看法,这个蛮遗憾的。有了这个平台,就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分享。
我知道在我们这个群里,有不少富有经验的胡琴界老前辈,还有演奏高手和学术精英,我想以后都会陆陆续续在平台上和大家见面。我们今天就算是抛砖引玉吧!很高兴为这个平台交流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主持人:非常感谢岳老师。我向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怎样想到转基因这个话题的?
岳峰教授:近些年来,“转基因”这个词越来越引起老百姓们的注意,不少人都在越来越关注转基因食品对于人类的危害。那么,音乐有没有转基因这一说呢?我们现在听到的民族音乐是不是转基因的呢?准基因民乐是不是对一个民族的乐种变异产生潜在的危害呢?等等,引起了我长久的关注和思考。
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培养民乐传人的地方。当我们来到音乐学院的教室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琴房是被钢琴所包围的。也就是说,我们学生的耳朵随时随地都是用十二平均律的标准来训练,来“修理”的。我们的课程表上排满了西方乐学的理论,如视唱练耳、西方音乐史、作曲技术,曲式分析等课程。可以说在大部分音乐学院的学科里,你基本上听不到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古琴音乐,也看不到中国乐学基础的黄钟大吕,那我们不妨要问了,在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音乐教坊里,我们的音乐是否在为西方音乐传宗接代,培养后生呢?而我们本土音乐的内容,比方说中国音乐史、民间民族音乐、民族声乐和民族器乐这些基础课程几乎达不到四分之一,更谈不上国学意味上的文化传承了,比方说诗歌,乐赋等等。当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肯定是要扪心自问的,这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学院”呢?这样的音乐学院,能培养出中国人自己的乐学人才吗?
换句话说,在西方乐学体系的培育下,我们能不能产生真正的中国音乐?在西方医学体系的培育下,我们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在西式大餐体系的培育下,我们能不能真正地做好中餐?我专门请教过医学界和餐饮界的专家,他们都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明明是用西方音乐体系培养了一个世纪的中国音乐人才吗!
主持人:那么,什么是音乐中的基因呢?
岳峰教授:音乐中的基因到底是什么呢?古人说过,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乃声之宗也。如果没有人能推翻这句话,那么,也就是说,音律是音乐生成的宗法和基因,基因就是音律。当你的音律改变了的时候,音乐基因是不是已经产生变化了呢?在国人把转基因食品看成洪水猛兽的今天,我们中国音乐教育辛辛苦苦了一个世纪,是不是悄然走过了一条自我转基因之路呢?
再往深处想一想,以钢琴十二平均律为基础的西方乐学体系,是不是中国音乐自我转基因之路的起点呢?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很值得理论界来好好研究。那么,中国音乐自我转基因的代价又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看出来了,我们现在很多的音乐都千篇一律,听之无味,就好像我们吃了黄瓜西红柿和茄子,看起来表面上形式不同,五颜六色,实际吃起来都是一个味,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工业化带来的结果。所以通过这一点我们也不难看出,我们不能责怪现在的年轻民乐人,说他们演奏起来听之无味,是千人一面的“罐头乐手”;说他们不中不西的民乐创作,因为他们是我们工业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我们朝着西方 “同质化” 标准训练出来的标准件。
主持人:您认为民族音乐中为什么会出现转基因这种现象呢?
岳峰教授:为什么我们民族音乐的发展一直在做着“去民间化”“去中国化”的努力呢?这是在我们百年来现代化中国西方化进程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有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史就是西方化的历史。这个话题就比较大了,我们再缩小一点,有音乐学家说过,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史那就是西方化了的音乐史。其实,20世纪的二胡史也是西方化了的历史。所以,这不光是我们二胡的事儿,民乐的事儿。
主持人:面对您所说的这种民族音乐转基因的情况,那我们作为民乐工作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岳峰教授:这是大家都关心的话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其实,就我们音乐而言,答案非常简单。路,就在脚下,根,也就在脚下。中国的戏曲和古琴是我们学习中国音乐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音乐教育中首先应该读的“《黄帝内经》”是我们学习中国音乐的必修课。说唱与戏曲,民歌和地方乐种才是我们中国人学习中国音乐的四大件。也就是说,中国音乐的复兴之路应该从传承我们自己的华夏之声开始。
主持人:这与国家的传统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没有衔接好有很大的关系。
岳峰教授:是的,说的很对。中国音乐教育应该首先传承自己的传统音乐,而不是以传承西方的传统音乐为主。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来丰富和改进自己的不足,而不是用西方音乐来改造和代替中国音乐。正如20世纪初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我们自己的音乐是主体,西学是我们拿来用的。而现在,我们的很多民乐创作、演奏,尤其是创作表现的特别突出,几乎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地步。就是他的观念,他的旋律手法,他的曲式结构都是西方的模式,中国的音乐素材只是作为味精和调料加进去的一些元素,这完全就是本末倒置了!对于“中国元素”这个词呢,我很赞成关乃忠老师的一句话,他说,我很不赞同“中国元素”这个提法,他说,你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你用中国元素,你本来血液里流的就是中国的血,你本来就是中国人,你只能说你用了法国元素或者德国元素。说这个话那是立场完全站反了!
关铭老师:我很赞同岳老师的看法。现在我们的音乐学院他们有一个口号要与国际接轨,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接上了没有,远远没有接上,因为我们是中国的音乐学院,不是美国的或英国的音乐学院,所以培养方向要搞清,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要改变这个现状,必须从我们的教材上着手。看看我们现在音乐学院的教材,不管是作曲的,指挥的,音乐学的。这个教材不改变的话,我们培养的还是罐头产品,因为它没有中国特色。作曲系80%—90%的教材都是欧美的教材,作曲法,和声,复调,曲式等这些教材没有中国的。我现在怀念李银海先生这样的人,他们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那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再者,在我们的教材中,没有我们中国古典音乐这一课,没有戏曲这一课,没有民歌这一课,没有民族大剧乐这一课,所以我们的学生出来以后,对这些带有风格性,地域风格性的东西无从下手,他们拉东西,拉技术可以,但是如果拉到风格他们简直可以说是大学的已经退到附中这个程度了,我在几个音乐学院里面看过他们表演,完了以后我说你们这个地域,地方音乐语言没有掌握,你的风格表现不出来,你表现的全是技术,这个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原来的中国音协主席赵季平先生曾在我们省戏曲研究院呆了二十年,满脑子都是名额与戏曲,所以他出手不凡,先出的东西都有根。这就是他从小熏陶的结果。现在的很多学生享受快餐文化太多了,所以感受“大米饭”文化的时候很不习惯。我们有很多作品得到的反馈是:听不懂、记不住、留不下。这是很普遍的问题,很多专业同行都听不懂的作品,要给百姓们去听,无异于听天书。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习主席的文艺座谈会提出了两大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第二是“如何为”的问题。我认为有一些作品就在“如何为”这方面出现了些许偏差。
岳峰教授:关老师说的非常具体,这里面就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从古到今我们几千年的中国音乐是怎么教育的?是怎么传承的?我们有没有好好研究自己的音乐教育体系?我们有没有自己的乐学体系?实际上,搞史学的专家们他们是更懂得的。那么现如今,我们谁来研究和建立自己的音乐体系呢?那肯定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指望靠西方,因为我们现在应用的这套乐学体系是拿来的,现成的,那我们要想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要从自身做起。
对于刚才那位老师提到的快曲和慢曲技巧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觉得器乐演奏是分“文功”和“武功”的。“武功”强调的是竞技,“文功”着重的是涵养;“武功”的很多指标是表面的,可以量化的,比如,力度(强弱)、速度(快慢)等等,“文功”的很多指标是隐性的,不可以量化的,比如,虚实、刚柔、轻重、疾缓等等,还有更多的风韵、气韵、神韵等等,更加无法量化。因此,竞技比赛,只是演奏的一个方面,它绝不能代表器乐演奏的全部。
当然,目前处于这个相当功利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或者心情去自我修行了。其实,音乐的价值,很大一部分还在于修行,只有修行才能细细地品味,才能找到中国器乐中那种天籁之声。而只是竞争比武,更高,更快,更强,那就把乐器当体育了,就会失掉很多乐趣,失掉了品味这个非常宝贵而又具有中国文化品质的东西。当然,这个话题说来就大了,它与我们当今这个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相关,不是我们哪个人或者哪一个行当,或者仅仅就二胡演奏就能说得通的,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了再跟大家细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