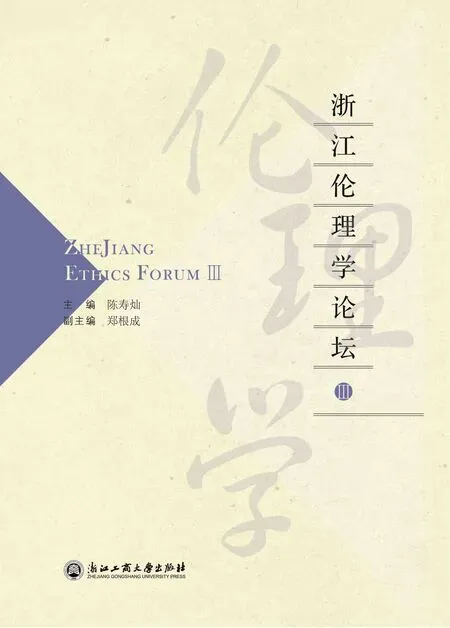欲望、普纽玛与行动①——亚里士多德心理学对身心二元论的突破
2016-05-12陈玮
陈 玮
欲望、普纽玛与行动
①——亚里士多德心理学对身心二元论的突破
陈 玮②
本文通过考察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运动》中的相关论述,试图从心理学和生物学两个层面重构他的欲望—普纽玛—行动模型,并由此指出“普纽玛”在欲望导致行动的过程中,在物理层面上起到了重要的联结作用。这种解释模型为亚里士多德突破身心二元论的传统思路、结合物理层面的因素来说明人类行动者的心理过程提供了关键支持。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戴维·查尔斯对亚里士多德的思路所做的评论并试图回应可能招致的批评,由此捍卫查尔斯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与辩护。本文认为,尽管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运动》中对普纽玛的说明仍存在含混之处,但是他所持的这种心理物理学路线在今天仍然能为我们研究人类行动者的道德心理提供重要启发。
亚里士多德;灵魂;欲望;行动;普纽玛
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运动》③De Motu Animalium,以下简称MA,本书所用英译文来自M.Nussbaum:Aristotle's De Motu Animaliu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中明确提出,动物的灵魂(尤其是欲望的部分)是导致一个有生命的物体运动的原因。根据普遍的运动原理,一切物体的运动都必须具有某个导致运动的原因。具体到动物的运动,这个原因就是与身体相对的、无形体的灵魂。④亦参见Aristotle:Aristotelis De Anim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英译本见J.Barnes: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中译参秦典华译本,[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DA。不仅如此,由于一个充分发展的、较高层级的灵魂(例如成年人的灵魂)内部具有不同层次①根据《尼各马可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以下简称EN),灵魂内部具有理性的部分和没有理性的部分(1102a30),其中无理性的部分又分为营养和生长的部分(1102a35-1102b14)与欲望的部分(1102b15-1103a5);而有理性的部分又分为知识的部分和理性计算的部分(1139a5-15)。根据《论灵魂》(DA),灵魂可划分为营养与生长、欲望和理性这三个部分,其中欲望又可分为欲求、意气和想望(DA414b-415a20)。,因此,在最具体的层面上,导致运动的原因就是灵魂中的思考和欲望的部分,即推理(dianoia/reasoning)、想象(phantasia)、决定(prohairesis/decision)、想望(boul ē sis/wish)与欲求(epithumia/appetite)。②参见MA700b15-25。Nussbaum将prohairesis译作choice,我采用decision的译法,并相应地将中文译作“决定”。但是,仅仅指出灵魂中的哪个部分构成了运动的原因是不够的,因为要说明动物如何运动、人类行动者如何被自身的欲望和思考推动着做出一个行动,我们还需要对灵魂的某个部分如何推动身体运动给出充分的说明。一旦亚里士多德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就会面对三个困难:第一,如果灵魂遵循普遍的运动原理而推动身体运动,且“接触致动”③参见DA406a-407b15。是物理世界中普遍的运动规律,那么如果灵魂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自身不动的,它又如何令一具身体发生运动?第二,如果灵魂是无形体的,那么一个无形体的灵魂如何与一个有形的身体发生接触并导致后者运动?第三,与身体相对,灵魂内部如何产生动机性的、足以推动身体进行运动的力量?前两个困难实际上涉及如何结合物理层面的原理来解释心理过程的发生,第三个困难则要求在此基础上对心理活动做出进一步说明。如果能够消除这三个困难,那么亚里士多德在某种意义上就突破了将身体和灵魂/心予以区分甚至加以对立的二元论框架,并成功地结合物理与心理层面的要素说明了欲望如何导致行动。因此,在《论动物的运动》中,他先后提出了五个模型,并通过对这些模型不断地进行比较、改进和综合来回答灵魂如何导致运动这个问题。④以下并非依照自然的文本顺序来依次讨论这四个模型,而是根据从纯粹物理层面到心理—物理层面的顺序逐次考察。这四个模型在文本中本来的次序请参考文中标注的行号。
一、欲望如何导致运动:四种预备性的模型
我们首先考虑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运动》中提出的四个模型,这些模型都旨在说明欲望如何引发一个相应的行动,但是它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看成是预备性的模型。
(一)物理层面的模型(MA701b1-15)
亚里士多德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动物运动的机械规律。一个例子是活动木偶,由于某种内置的简单装置(绳索与固定其上的铆钉)就可以自己发生运动。另一个例子则是某种供孩童玩耍的小车,由于车轮的尺寸被设计成大小不同,因此当人试图沿直线推动车子的时候,车身就会以较小的尺寸为中心而发生圆周运动。亚里士多德指出,就第一个例子而言,动物的身体主要由筋腱和骨头构成,前者就像绳索而后者仿佛铆钉,这二者的松弛和碰撞导致了运动的发生。由此可见,机体内部的某个简单装置就可以引发整个身体的运动。而就第二个例子而言,一个最初的、试图使推车直线运动的推力却导致它做圆周运动。与此类似,动物的身体最初也可能受某种力量推动而发生运动,但其自身的构造将会间接地导致后续运动发生变化。因此,并非每一次运动以及运动的改变都需要一个直接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推动力尽管不能直接引发并决定每一个后续的运动,但是它也可以被视为运动的源头。按照这个最简单的模型,亚里士多德对动物运动的最基本原理给出了一个物理层面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他仍然保留了灵魂作为最初推动力的可能。①在MA701b16-17,亚里士多德紧接着指出,动物运动的改变是由想象物(phantasiai)、感知(aisth ē seis/sense-perceptions)和观念(ennoiai/ideas)引起的。
(二)中点模型(MA702b13-703a)
由于动物的身体结构通常都是左右对称的,亚里士多德于是设想了一个“中点”(meson)来说明灵魂如何能够同时驱使身体的两边运动。他首先假定运动的原因总是比运动的部分更高,而推动运动的原因必然处于运动的二者中间(MA702b15)。接着,亚里士多德构造了一个图形ABC,其中B被A推动,而根据此前说明的原则,必须存在一个自身不动的原因。因此A虽然“潜在地是一,但实际上是二,这样它就不再是一个点,而是某种量(megethos/magnitude)”(MA702b30)。同时,由于C可能与B同时运动,那么它的原因也就存在于A。因此“必然存在另外的某个事物,它推动二者运动但是自己不受推动”(MA702b34)。否则如果存在着两个原因分别推动B和C运动,它们就会彼此相抵。于是必然存在着单一的某物同时推动两个物体运动,由于它不能是空间上的量而只能是一个点,因此它必然是处于中点的灵魂。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模型其实存在问题:首先,亚里士多德没有说明所谓相互对称的身体究竟是指从中一分为二的两部分、还是指对称的四肢。其次,推动运动的原因为什么必然处于中间,而不能处于左边或是右边,亚里士多德也没有给出说明。但是他做了一个类比,即:欲望作为推动运动产生的原因,就是处于身体结构的中点A(MA703a5)。这就为我们引入普纽玛并重构“欲望—普纽玛—行动”这个重要的模型奠定了基础。①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中点模型的重要性不止于此,在伦理学著作中,他用“中点”来说明美德(EN1106a25-1107a25)。而在讨论“不能自制”这种不好的中间性品质时,他使用了“偏瘫”作为类比(EN1102b15-20),以此说明一个处于中点的致动原因(灵魂/理性)不能有效地推动一边的身体做出相应的行动。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层面上描述身体运动所使用的思路也可以扩展到他对灵魂的描述,或者说对应于他对灵魂活动的描述。
(三)实践三段论的推理模型(MA701a5-25)
较前两个模型而言,亚里士多德对第三个模型只做了简单说明,他试图用这个模型来说明灵魂中理性部分的活动如何导致身体活动。根据他的论述,两个前提(普遍前提和特殊前提)的共同运作会导致一个结论,而对于实践领域的理性推论过程来说,这个结论就是一个与理性判断相一致的运动。例如,“每个人都应该散步”(普遍前提)和“我是一个人”(特殊前提)相结合,就会促使从事上述推理的人立刻做出一个散步的行动——只要当时没有任何因素对他形成阻碍或者强制。
事实上,这个三段论模型的有效性一直备受争议,其中一个原因是,实践三段论的推导模式是亚里士多德类比于逻辑推论的普遍原则而在实践领域建立的推论模型,但是对于和实践事务相关的领域(例如伦理学和政治学)而言,由于研究的对象是可变的,因此逻辑上成立的三段论在实践领域并不必然成立。因为在推论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外部环境和行动者内心中都有可能出现阻碍和强制因素(前者例如某种不可抗的外力,后者例如一个与理性判断相反的强烈欲望),因此这个推论的有效性就十分可疑。②关于如何解释并填补前提和结论之间存在的这种缺口,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思路,例如将实践三段论的结论界定为对行动的倾向,或是在特殊前提和结论之间加入一系列动机效力逐渐增强的中项,等等。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讨论,参见P.Gottlieb:The Practical Syllogism,in R.Kraut:The Blackwell Guide to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Blackwell,2006,pp.218-233.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指出,在特殊前提部分,起作用的与其说是对于特殊事物的理性判断,不如说是针对某个具体对象的感知与欲望,而后者具有实际地引发一个相应行动的动机性力量。也就是说,实践三段论的推理模型要想成立,需要添加两个要素,即目的和欲望。这就使理论推理模型实际上转向了目的—动机模型和欲望模型。由此可见,当亚里士多德说一个行动是与理性部分相一致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说单纯的理性部分的活动就可以导致动物的运动,而是强调了这种理性计算同时伴随着与之相一致的目的识别和欲望动机。①《尼各马可伦理学》明确表示,理性部分本身不动且不单纯导致行动。参见EN1139a35-b1。
(四)目的—动机模型(MA700b5-701a5)
该模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对它的阐述也比较详尽。它不仅集中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观点,这个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为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尤其是伦理学)提供了基础,而且为后面说明从欲望到普纽玛的致动模型做好了准备。亚里士多德论述的要点如下:第一,无生命的物体是被其他的外物推动而发生运动,致动原因在它之外。而有生命的物体的运动由灵魂推动,灵魂内在于生物自身。第二,一切动物推动运动或受到推动而运动必然都是为了某个目的,这构成其运动的限制,也是运动的原因。第三,推动动物运动的原因在于理性的推理部分:想象、决定、想望和欲求,这些部分及其相应的能力使得动物的灵魂能够感知并趋向某些特定的目标物。②例如欲求趋向食物、水和性的对象,想望趋向善的事物,等等。对这方面的一个概括,参见笔者拙文:《亚里士多德论人类欲望的三种形式及其统一》,载《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3期。而“想望、意气和欲求都是欲望,决定则为推理和欲望这两个部分所共有。因此第一推动者(first mover)就是欲望以及思考的对象;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思考对象都能充当第一推动者,合格的只有那些属于实践领域的目的。所以,只有这种类型的善事物才能推动运动,而不是所有高贵的事物都能推动运动”(MA700b23-25)。而所谓“这种类型的善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就是人们从事其他事情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那些看起来是善和快乐的东西。就此而言,动物的运动与其他事物(尤其是天体)的运动有所不同,区别就在于,推动天体运动的第一推动者自身是不被推动的,而推动动物运动的欲望部分自身是由其目的所激发的(MA700b35)。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点:首先,欲望作为动物运动的原因,其自身是被唤起或者说被推动的,这个唤起欲望的因素就是它所追求的目的。考虑到这一点,仅仅将运动的原因归结为欲望并不充分。因为当亚里士多德承认欲望更直接地引发动物身体的运动时,他也强调欲望本身需要目的来唤起自身的力量,或者说赋予它以能量。这个“唤起”的过程将在普纽玛的致动模型中得到说明。第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欲望是与理性相对、诉诸身体的部分,但是它并非完全与理性相隔绝,而是具有某些理性的要素,它也要求实践理性的运作并在具体过程中体现为想象与决定的能力与施展。①事实上,单纯的生理反应被亚里士多德排除在“自愿”运动的范围之外,例如性唤起等。这种生理活动过程纯粹是外物作用于身体器官的反应,是不经过理性程序的。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此类反应不该被纳入“欲望”的范围。根据他的界定,欲望一定是对某种对象的感知与主动追求(参见MA703b3-10)。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前提,或者说按照这个前提构造的目的—动机模型就在两个方面发挥了作用,一个为欲望自身的活动提供了动机(欲望的目的),另一个则避免对动物运动的说明落入某种完全物理性的说明。后面这点尤其重要,因为它将引导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欲望致动模型理解为一种心理—物理学层面的(psychophysical)论证路线,从而避免传统的二元论解释模式。
二、“欲望—普纽玛”模型:一种非二元论的解释路线
通过构建上述四个模型,亚里士多德已经对动物运动的物理层面和心理层面分别做出了说明,成功地将运动的原因聚焦于灵魂的欲望部分,并初步指明了欲望致动的动力来源。然而,要说明动物是如何运动的,以上四个模型还不够充分,因为物理和心理这两个层面之间看起来还存在一个缺口,这二者之间还缺少一个动力性的机制。
在《论动物的运动》第十至十一章,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诉诸普纽玛(pneuma)的欲望致动模型。②普纽玛(pneuma),早期希腊哲学家(尤其是阿那克西美尼)用它指“呼吸”或“气”,以之作为某种原始的实体和基本物质形式,后来演化为“精气”。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1),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40页。G.S.基尔克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聂敏里译,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版,第216—241页。普纽玛在古代哲学文献中具有多重含义,它的本意是“呼吸”,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某种“天然的普纽玛”(connatepneuma),即动物自身天然地通过肺(某些动物例如鱼,则是通过鳃)而将某种气体吸入体内。③参见托伪的亚里士多德著作《论气息》(Peri Pneumatos),该篇作品认为这种天然的普纽玛是在动物体内运行的、某种比空气更纯净也更精细的气态存在物。尽管《论气息》被认为是伪作,但是也反映了一种关于普纽玛的观点,故此值得参考。在他看来,一切动物都具有天然的普纽玛并通过它产生能量与力量(MA703a9)④天然的普纽玛如何产生推动运动的力量与能力,相关论述参见MA703a20-25:“运动的功能就是推与拉,因此运动的工具就必须能够扩张和收缩。而这正是普纽玛的本性。因为它不受限制地收缩与扩张,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能够拉动和推动。与火相比,它具有重量;而与其反面相比,它又轻盈。任何不发生改变而推动运动的事物都必须属于这种类型”。,这构成了运动产生的直接原因。按照戴维·查尔斯(David Charles)的概括,欲望—普纽玛的致动模型大概由以下四个步骤构成:
(1)行动者思考或想象一个他所追求或躲避的对象;
(2)出现恐惧、自信或性冲动,同时伴随着热与冷;
(3)天然的普纽玛(connatepneuma)扩张或收缩;
(4)肢体做出相应运动。
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在作为运动原因的欲望和具体的身体运动之间建立起一个联结步骤(即第3步),而构成这个联结的正是普纽玛。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照前面第三个模型即实践三段论的推理模型,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时从两个层面来说明动作的发生(见图1、图2)。
A.实践三段论

图1 实践三段论
B.普纽玛模型

图2 普纽玛模型
如前文所述,如果我们仅仅主张模型A,那么从两个前提的结合能否必然得出作为结论的行动,是存疑的。但是由于特殊前提处理的对象实际上就是思考和想象的对象,所以模型B可以添加到模型A之中,形成一个整体的连续运动模型(见图3)。
C.推理—欲望致动模型①这里我有意避免使用一个垂直的图例,以避免任何关于亚里士多德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地说明身—心问题的解释倾向。

图3 推理—欲望致动模型
在C模型中,我们看到,由于从特殊前提到行动之间的过程被一个物理层面的描述加以充实并扩展,理性判断与行动之间也就具有了连续性。其中,特殊前提所针对的对象直接构成了情感的感知对象,这两个部分实际上是重叠的。根据第一个模型,普纽玛的扩张与收缩类似于活动木偶的内部装置,它的变化在最基本的物理层面引起了动物的肢体动作,并由此结合推理、想象和欲望等因素,趋向某个具体的目标。因此,普纽玛模型实际上诉诸生物学原理,并在此基础上更为细致地解释了行动者是如何从特殊前提走向一个作为结论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心理与生理两个层面紧密联结,共同发挥了作用。
三、亚里士多德的心理物理学路线以及对普纽玛的补充说明
对于如何理解并评价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这种解释思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评论是由查尔斯在他的论文《行动中的欲望:亚里士多德的运动论述》中提出的。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对身—心关系问题实际上持有某种可以称为“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cal)的思路。这种思路不仅突破了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二元论模式,②柏拉图的这种二元论模式尤见于《斐多》。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将灵魂构造为某种与身体相分离且对立的存在,能够在身体死去之后继续持久存在,并由此获得真正的知识即理念。英译本见Plato:Phaedo,trans,in D.Sedley,A.Long:Meno and Phaed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关于柏拉图二元论观点的一个简要介绍,参见H.Robinson:Dualism,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2 Edition),URL=〈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2/entries/dualism/〉.关于对这种观点在《斐多》中是否得到了有效论证的一个捍卫,参见M.Pakaluk:Degrees of Separation in the Phaedo,Phronesis,2003,vol.48.也不囿于物质主义(materialism)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的任何立场,而是采取了一种中间性的道路。①相关讨论参见:C.Shields:Soul and Body in Aristotle;R.Heinaman:Aristotle and the Mind-Body Problem;M.Wedin:Content and Cause in the Aristotelian Mind,以上均见于文集L.Gerson:Aristotle 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Ⅲ(Psychology and Ethics),Routledge,1999.根据查尔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心理物理学路线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欲望的界定;二是对于身—心联结物的强调。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查尔斯指出,亚里士多德按照某种结合情感与身体反应二者的方式来定义欲望。他援引《论灵魂》第一卷第一章来指出亚里士多德根本上主张灵魂的属性和各种波动都不能与自然的质料(身体)相分离,即使在定义上也是如此。因此,亚里士多德诉诸物理层面的因素来界定欲望,将欲望(尤其是恐惧与愤怒)视作血液的冷却或沸腾。②参见DA403a18-28,403b17-19。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普纽玛致动模型的核心步骤就是使用“天然的普纽玛”来联结灵魂(欲望)部分和身体部分。根据前文所述,普纽玛的扩张和收缩导致身体行动。而按照查尔斯的解释,关于普纽玛是如何导致行动的,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首先,普纽玛可以被看作欲望推动运动的某种“工具”(instrument),它的运行是为身体和灵魂所共有的,是一个同时在心理和物理层面运作的过程(尽管有时候这种运行可能是不被意识到的)。其次,普纽玛的扩张和收缩也是由热与冷引起,机体内部冷热的变化会导致普纽玛的形状和大小发生改变,进而引发筋腱和骨头的变化,从而导致运动。
然而,正如查尔斯自己承认的,亚里士多德对于普纽玛如何参与界定欲望、如何导致一个具体的行动,并没有给出足够充分的论证。③查尔斯试图诉诸目的来补充亚里士多德对普纽玛运行机制的说明。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目的—动机模型更适合于说明欲望内部的能量的来源,对于解释普纽玛的问题则并不十分有益。事实上,我怀疑这里存在着一个论证上的循环,因为对身—心联结物的论述要求一个已经重新定义的欲望概念作为前提。根据前文所述,这样一个欲望概念应当具备两个特点:第一,它的内部具有精细的层次,以对应不同种类的外界对象;第二,它和身体或者说质料的部分具有极其紧密的关系。有了这样一种被查尔斯称为“心理物理学”的欲望概念作为基础,亚里士多德就可以较为顺当地论证欲望如何实际地导致动物运动。但是,亚里士多德所采取的方式仅仅是指出普纽玛是一种身—心结合物,进而在欲望和行动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结。为了解释这个可能的循环,我后面会引入《论呼吸》(On Respiration)和托名亚里士多德的《论气息》(On Breath)来说明,亚里士多德使用他的(或者同时代的)生物学著作,对于普纽玛在什么意义上可作为身心结合物,以及它是如何联结欲望和行动的给出了一个说明。不仅如此,早期希腊哲学家(例如阿那克西美尼)的观点无疑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使用普纽玛作为基本联结物的思想奠定了基础,澄清二者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说明亚里士多德对于普纽玛的构想。不过这将是另一篇论文的内容。不仅如此,即使我们综合实践三段论和普纽玛模型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行动程序,以下问题仍然需要说明:普纽玛究竟是什么?它和欲望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何在?它是如何导致机体发生运动的?在此,我试图从两个方面来补充亚里士多德对普纽玛的说明,以此来捍卫查尔斯对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心理物理学解释。我将首先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论著《论呼吸》来说明他对欲望(甚至灵魂)的定义确实在根本上诉诸生物学层面的解释。其次,我将提出一个初步的思路来试着回应关于普纽玛的质疑。
首先,正如查尔斯指出的,亚里士多德主要是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层面来说明生物体的生命原理和运动机制,并在这个基础上讨论动物的情感活动以及灵魂各部分的功能与运行。就此而言,他的《论呼吸》等生物学著作为此提供了经验基础。《论呼吸》将动物的生命基础归结于肺和心,心脏提供血液和热并由此为生命和灵魂的存在提供基础,但是过度的热反而会导致生物体的耗竭和死亡,因此肺(或者鳃)就通过呼吸来造成冷却,使得生物体在心脏和肺协作造成的收缩与扩张、发热和冷却的协调变化中持续生存并活动。①参见《论呼吸》,474a25-474b25,476a10,478a12-35。由此可见,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动物会自动地去寻求使机体保持恰当温度的外部条件,例如空气和水,而热的鼓动和冷的收缩驱使它们本能地趋利避害,追求一切有益于机体生存的事物,躲避那些可能对生命造成威胁的环境,并通过呼吸来完成身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完成这些行动不需要更高层面的灵魂感知与意识。相比之下,情感和意识活动则主要通过灵魂当中的欲望部分来完成。②如前文所述,亚里士多德的欲望概念本身就从质料的层面获得了最基础的定义和说明。对此有一个很明确的论述:“愤怒本质上是结合了质料的,因为它的形式是一个结合着质料的形式:这形式即被理解为在这种物理过程中、在本质上与质料相结合”。而欲望在生理功能和心理感受这两个层面就同时具有了原初的能量。由此可见,认为亚里士多德仅仅解释了愤怒和恐惧这两种欲望的物理层面基础,从而无法建立对整个欲望部分的有效概括,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欲望的较为基础的部分(欲求和意气)都可以在物理层面上通过生物体的热与冷来加以界定。
其次,如何解释普纽玛一直是比较困难的问题,其难点大致如下:第一,如何理解并设想普纽玛?如果普纽玛是气,那么它和空气有什么差别?来源何在?第二,如果像查尔斯所说的,欲望推动普纽玛发生改变,将之作为工具再进一步引起肢体的运动,那这就意味着欲望能够推动某种实体发生活动。既然如此,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不直接论证欲望可以推动机体的某个内在组织进而导致活动?为什么还需要“普纽玛”这样一个中间环节?按照查尔斯的观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难题,恰恰说明我们仍然是从一种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角度来理解和思考普纽玛,将之看作一种弥合身与心的设施或者手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彻底地持有一种心理物理学的思路,关于普纽玛的问题就不会以上述方式出现。
必须承认,查尔斯为亚里士多德所做的这个辩护是不充分的。如果普纽玛在欲望导致行动的过程中确实是在现实层面和解释层面都有效的关键因素,那么我们就必须尝试对它的性质和活动原理提出更细致的说明。鉴于亚里士多德本人对普纽玛的说明并不充分,那么,对于托名亚里士多德的伪作《论气息》加以考察或许是有益的。这篇文献对普纽玛有如下说明:第一,普纽玛并非来自外部的营养或空气,而是由于身体内部变热而产生。第二,它是一种气息,但是比空气更精细和纯净。第三,普纽玛遍布全身,身体器官乃至皮肤、肌肉都具有内在的孔道,普纽玛通过这些孔道在周身运行流通。第四,普纽玛推动运动的开始部分在于筋腱,而非骨头。如果上述说明有其可取之处(且不管是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做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运动》中提出普纽玛作为实在的、关键性的联结物并诉诸它来说明动物身体的整个运动如何发生,就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神秘或缺少科学根据。普纽玛可以被认为是某种遍布动物身体内部的气态存在物,随着血液沸腾(尤其是心脏周边)而产生的热量而扩张,随着肺部呼吸导致的冷却而收缩。当这种不停扩张和收缩的气息随着身体各个部分的孔道进入循环的时候,在正常情况下,它就按照某种节律(例如心跳或呼吸)对身体的活动进行调节,而这部分活动往往是不为动物所意识的。当动物受到外部出现或内心想象的某种形象的刺激而本能地发生回应时,随着呼吸和心跳的改变,欲望和普纽玛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动物就会随之做出相应的行动。由此可见,如果从这个层次来解释普纽玛,那么查尔斯采取的心理物理学阐释路线确实具有一定的根据,动物(或者说人类行动者)从心理到生理的整个活动机制也就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系统内部获得了一个牢靠且顺当的解释。
然而,这里仍然可能招致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看,如果我们强调亚里士多德在根本上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主张形式赋予质料以现实性,灵魂作为类似形式的存在而赋予身体以现实性,那么即使我们承认欲望—普纽玛导致运动的作用具有物理基础,我们也依然可以得出结论说,亚里士多德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身心观——尽管它可能在很弱的意义上是二元的。①参见曹青云:《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与当代功能主义》,载《世界哲学》2015年第2期。另一方面,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看,如何证明普纽玛是实体而不是某种神秘的存在物,这依然存在问题。考虑到近代以来的科学和医学发展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迥异于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动物活动的心理—生理学图景①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致动模型的局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提问契机,即在神经科学研究极大发展的今天,我们能够推荐什么样的思路、诉诸何种更具科学性的概念来解决亚里士多德试图解决的问题?心理层面和生理层面是如何发生联结并有效运作的?这个问题值得科学家和哲学家(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然哲学家和辩证学家,见DA403a30-403b5)共同努力探讨。。因此,无论是采取“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思路,亚里士多德的欲望致动模型似乎都陷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解释的能力和可信性两方面似乎都不具有优越性。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有两个方面的理由来支持查尔斯针对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这种心理物理学的解释思路,并由此而更加重视对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理论及欲望致动模型的研究。第一个方面的理由就在于身—心二元的思考模式长久以来在某些道德心理学层面的问题上对我们形成了阻碍,例如人类的本质、人类认识能力的优越性与局限性、不能自制(意志软弱)是否可能等。如果我们依然采取柏拉图、笛卡儿的传统框架来审视这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难免会陷于某种两难境地,而这样的代价无论对于理论模型还是道德关注而言都过分巨大。第二个方面的理由则出于某种实际的伦理关切,也就是说,面对人类自身理性与欲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即使我们在理性和欲望各自的部分不断做出精细的划分(例如在理性的部分划分出决定或意志,在欲望的部分区分出理性欲望,等等),即使我们通过构造联结物和连动机制来弥合这两个部分,我们都会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捉襟见肘,即在导致一个实际行动的方面,究竟是理性还是欲望更具有实际效力?而这一理论层面的尴尬处境会直接影响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例如如何理解并规定个人和共同体所追求的最高善?如何实现最高善?如何理解并培养美德?如何在共同体之中规划并推行合理的道德教育方案?等等。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充分地重视并努力合理地解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生物学和灵魂论部分对于动物(以及人类)的欲望和行动模型,尤其是尝试着发展一种突破传统二元论思路的解释路径,对于解决道德心理学领域的基本难题和一系列应用问题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1]NUSSBAUM M.Aristotle's De Motu Animalium[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2]ROSS W D.Aristotelis De Anim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
[3]BARNES J.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84.
[4]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M].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GOTTLIEB P.The Practical Syllogism[C]//KRAUT R.The Blackwell Guide to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Oxford:Blackwell,2006.
[6]陈玮.亚里士多德论人类欲望的三种形式及其统一[J].道德与文明,2011(3):68-73.
[7]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基尔克,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M].聂敏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9]CHARLES D.Desire in Action:Aristotle's Move[A]//PAKALUK M,PEARSON G. Moral Psychology and Human Action in Aristotle.New York:Oxford,2011.
[10]SEDLEY D,LONG A.Meno and Phaedo[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1]ROBINSON H.Dualism[EB/OL].(2012-11-20)[2015-01-16].http://plato.stanford. edu/archives/win2012/entries/dualism/.
[12]PAKALUK M.Degrees of Separation in the Phaedo[J].Phronesis,2003,48(2).
[13]SHIELDS C.SoulandBodyinAristotle[A]//GERSONL.Aristotle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Ⅲ(Psychology and Ethics).New York:Routledge,1999.
[14]HEINAMAN R.Aristotle and the Mind-Body Problem[A]//GERSON L.Aristotle 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Ⅲ(Psychology and Ethics).New York:Routledge,1999:32-49.
[15]WEDIN M.Content and Cause in the Aristotelian Mind[A]//GERSON L.Aristotle 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Ⅲ(Psychology and Ethics).New York:Routledge,1999.
[16]曹青云.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与当代功能主义[J],世界哲学,2015(2).
①本文原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年4月);受到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古希腊罗马政治伦理研究”(12JJD720001)的资助。
②陈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