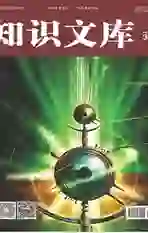浅谈中国古代史家之修养
2016-04-29王山青
本文通过各个时代学者对古代史家修养理论进行了论述,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再到唐宋明清,再到当代,各学者对于史家修养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对古人所表述的史家修养进行了补充和拓展。其中当代学者瞿东林和彭忠德先生所提出来的“史家之职责”和“史胆与史责”对于我国史学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创新。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史学理论,大致是指自先秦至清末中国历史上人们关于史学(作为一种知识、一门学问的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与撰述,它主要包含史学功用、史家修养、史学方法、史学批评等领域,而每一领域又由诸多问题构成,有广泛的涵盖面。其中,史学功用问题,是古往今来人们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至今仍有其突出的现实意义;史家修养,反映了中国史家在这方面所积累的思想、道德遗产,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的修养和学风建设多有借鉴之处;史学方法,反映了中国史学的特点;史学批评,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桥梁之一,而关于批评之标准与方法则反映了中国史家的气度、见识与风采。
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文明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视修史的国家,从古至今,涌现出许多的名家名作。战国时期以孔子和左丘明的主张为主,到唐宋元时期以刘知几、曾巩、揭傒斯的学说为主,后来到明清时代胡应麟和章学诚将史家修养理论进行了完善,最后到当代学者瞿东林和彭忠德先生以最全面的方式进行了总结与概括。
一、孔子的“书法不隐”与左丘明的“君举必书”
早在史家修养理论中就提出了秉笔直书的理论,其代表人物当属孔子和左丘明。在公元前548年,晋国执政大夫赵盾杀害国君晋灵公。史官董狐如实记载“赵盾弑君”一事,并且与赵盾发生了矛盾。孔子对此事的评价是:董狐是良臣,书法不隐。赞扬董狐不畏强权,尊重事实的良好品质。由此可见,孔子对于秉笔直书是非常赞赏的。史学家坚持秉笔直书在《左传》中也有很多记载。《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中曹刿认为,国君无论下达什么决定都要记录下来,史官在记载时,一定要以事实来记载,如果记录的不是事实,后人根本无法了解。不管是孔子所主张的“书法不隐”,还是左丘明所主张的“君举必书”这些都是史学家所必血的修养之一,即秉笔直书。
二、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
对史家修养理论进行系统、完整地论述的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刘子玄传》中有记载:史学家需要具备三个长处,能具备这三个长处的人很少,所以可以称的上史才的人也很少。三个长处指的是才,学,识三个方面。如果只是一昧学习,但是不具备才能,就像有千亩良田,有万两黄金,让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去经营,最终只会以失败而告终。如果拥有才能而不用心去学习,就像只思考而不去探索,最终也会将才能用尽。一个正直的史官,不管是善还是恶都如实记录下来,让骄傲的君主奸佞的臣子都害怕。从古至今,很少有人能完全做到这样。这里刘知几就明确地指出要成为真正的史家奇才,就要具备才、学、识,这是史家修养的核心与最高标准。但是刘知几没有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而具体的论述,从而导致后来的学者,对这三点的认识产生了分歧。以笔者的角度认为,史才,是指有对史料整理,编排,撰写的能力。史学,是指对历史有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史识,指的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有着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力,也有着忠于事实的胆识。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整体,将史家的修养问题有一个理论的认识,对于史家修养和史学的进步有着推动作用。
三、曾巩“明”、“道”、“智”、“文”的要求与揭傒斯“以心术为本”的原则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发展时期。自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作为衡量史家修养的理论之后,后来史学家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扩展与补充,并且提出新的主张,一步步丰富了中国古代良史的理论。
曾巩对史家提出了“明”、“道”、“智”、“文”这四个方面的史家所要具备的修养。著史的目的在于将是非兴衰得失,乱世治理的方法记录下来,这样的良史才能供后人借鉴,才能永远地流传下去。史家要有能够明辨是非,博古通今的能力。在对史实进行叙述时要强调史料对社会的作用,要有实践的价值。后来,元代揭傒斯提出在修史时要有“以心术为本”的原则。当纳入人才来承担史官的职责时,此人心术一定是要正直的。但是揭傒斯对于心术正这个内容没有做详细的解释说明,把这一些理论作为史家修养的标准有些不足。
四、胡应麟之“公心”、“直笔”二善说与章学诚之“史德”、“心术”说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终结时期。在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的史家人才,其中胡应麟、章学诚对史家修养的论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明代史学家胡应麟提出:才、学、识这三个方面还不足以完全概括为史家修养,还要有公正的心,大胆直述的的心态,这五个方面都具备的就有孔子。董狐、南史秉笔直书,维公正义直言。在秦汉时期,拥有才、学、识这三长的人很多,但是具有公心、直笔的人就很少能够见到了。他充分地意识到了史家心术与秉笔直书之间的关联性,并且认为这两者相互存在,息息相关,并且是不可分割的。司马迁在记录以公正的心写实,但是也存在着实虚结合。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直与公,公下直?因此胡应麟强调了一个尽字,如果不能做到完全的直笔,则公心中就会有私心存在。如果不能做到完全的公心,则直笔中就会有虚笔的情况出现。只有两者做到完全的统一,才能达到真正的公心与直笔。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史德”“心术”。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中就提出:要想成为一个良史,就要能够辨别常人无法辨别的东西。德就是著书者的“心术”。因此“心术”和“史德”是相互存在的。章学诚认为“心术”是一个君子所必备的修养,是一个贤能的人所必备的品质。“心术”是史家自身修养的最高境界。如何成为一个具有“心术”的“良史”?章学诚提出要有能够辨别历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并且尊重客观历史,不能够以自身的主观思想去改变历史的客观性。
五、瞿林东先生的“史家之职责”与彭忠德先生的“史胆与史责”
当代学者中瞿林东先生的“史家之职责”与彭忠德先生的“史胆与史责”是对史家修养理论的发掘与补充,其影响力较大。
瞿林东认为,董狐、南史所表现出来的“书法不隐”是由君臣之礼和社会秩序与演变出来的。孔子所著《春秋》也是同样的道理,司马迁所著《史记》是司马父子对社会责任的阐述。司马迁提出的叙述往事的同时,思考往事中的人物表现了他对历史与社会的思考,以及社会责任的认识。司马光所撰写的《资治通鉴》是希望能够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他所说的以前世的兴衰作为考鉴,并且审视当前的得失,明白善恶,懂得如何取舍,才能够让社会四海升平,人人享福。这里面就代表着司马光对社会的责任感。
彭忠德则提出了“史胆与史责”的说法,史胆指的是史学家的胆量,能够大胆的直书;史责指的是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梁人刘勰在《文史雕龙.史传》中就有对史家责任感的表述:史家的责任在于能够担负重担,承担四海的责任,能够明辨是非,承担劳苦。明代李贽认为史胆在史家修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如果空有才能而没有胆识,则不能以正确的态度来记录史实。这些史学家的言论证明了良史必须有史胆和史责两者来支撑。刘知几和章学诚由于当时社会的限制没有意识到这两点,而当代学者提出了“史胆与史识”的说法,是对古代史家修养理论的完善与补充,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与史学评论,涉及的方面十分广泛,又因有其传承的优良传统而不断丰富和深入,显示出独特的理论形态和表述方式。当今中国史学要有更大的发展、更大的进步,不论在历史理论方面,还是在史学理论方面,都有必要分别作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中国古代史学在这两个方面部有丰富厚重的遗产,可供当今史学工作者有计划地传承创新,进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理论体系和史学理论体系。
(作者单位:郑州城市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