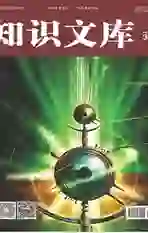诗歌翻译的文化传递与本地化
2016-04-29钟祥元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传递与文化本地化问题值得关注。本文以拜伦诗歌When We Two Parted的翻译为例,探讨诗歌翻译的文化传递与本地化对译诗效果的影响。
一、拜伦与When We Two Parted
在When We Two Parted创作前,作者拜伦经历了多段感情,每段都以分别告终。历经分别,诗人以分别为主题进行创作。本诗回忆与爱人别时及别后的心情,通过文化意象的塑造实现情感的自然传达。
When We Two Parted中文译本达十余种,本文选取流传较广的两个译本,译者分别为查良铮、程锡麟,探讨翻译中的文化传递与本地化对译诗效果的影响。
二、译诗的形式重构
霍姆斯总结翻译诗歌的第二个策略是形式的转换,建议译者考虑原诗形式的功能,并在目的语中寻求对等(Bassnett and Lefevere 62)。查良铮译本采用现代诗歌的形式,句子长短不过于苛求;而程锡麟译本采用仿古诗形式,除前两句外,每句字数相同。前两句或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欲用第二句的“默默”对应首句的“依依”,叠词对叠词,既达到形式上的统一,又渲染了离别的悲伤气氛,两个叠词的使用加强了效果。叠词是汉语区别于英语的一类词,译者再创作时使用叠词也体现出语言文化的本地化策略。若将前两句改为“昔日依依别,泪流默无言”,显然不如两个叠词的使用效果突出。这也体现出译者是“戴着脚镣的舞者”,改写的同时也必定受到文本的制约。译者“既有诠释文本的权力,也有受文本制约的一面”(吕俊 53-54)。
两首译作形式各有千秋,效果于读者而言,无好坏之分,但有强弱之分。程锡麟的仿古诗译本会使读者感觉到自己与原诗毫无距离感,增强读者的心理认同感。这种心理认同是根植于中国读者的成长历程的:中国人从小背诵唐诗宋词,整齐的形式和朗朗上口的韵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深入中国人的文化认知,因此仿古诗译本能给中国读者以熟悉感、亲切感。翻译就是文化改写,程锡麟结合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传统的心理认同,对诗歌形式进行再创作,成功实现了本诗在中国的本地化。
三、译诗的意象重塑
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再现原作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值得借鉴的(谭晓鸣,陈雅媚 215)。意象对再现诗歌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节中的vows,查良铮直译为“誓言”;而程锡麟将其改写为“山盟”。这与中西方的宗教文化有关,西方人信仰基督教,生活深受宗教影响。西方人在婚礼上双方交换誓言,表示对爱情的承诺,是在上帝面前的许诺。而“山盟海誓”一词,出自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如今又为媒体广泛传播,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同于西方人对上帝的许诺,“山盟海誓”是对自然的盟誓,是客观唯物的,无宗教色彩。中西方在“誓言”上的差异与意识形态分不开,意识形态制约着文学翻译(王峰,马琰 77)。在爱情诗中,誓言是一个重要的意象。从带有西方宗教色彩的“誓言”到中国文化的“山盟”,文化本地化大大增强了诗歌在中国读者中的影响力和认同感,也对原诗情感在中国的传递效果大大增强。
四、译诗的手法再现
在程锡麟的译作第四节中有两处使用了对比手法,可谓十分精彩,将“再创作”的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一处,In secret we met与 In silence I grieve 两句,原文是用时态的变化来体现在时间的对比,而汉语中不存在英语的时态形式,程锡麟将时态所代表的意义转化为汉语实词“昔日”、“今朝”,巧妙形成对比,体现出改写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原语作家、作品形象的引入,还在于将文学手段引入目的语文学系统(郭宇 40)。程锡麟将对比手法引入译作,既做到忠实于内容、情感,也实现了形式、艺术手段的引入。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手法的引入,实现了翻译的文化传递。
五、结语
诗歌中含有许多文化意象,用词也独具本国语言特色。译诗的过程中,译者需发挥一定的创造性,对原诗进行“再创作”,在形式、意象与意境、文学手法等方面实现文化传递与本地化。诗歌翻译的文化传递与本地化,既吸收了原语文化的精粹,又体现对目的语读者的关照,实现了中外文化在诗歌中的完美融合。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