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
2016-04-28老五
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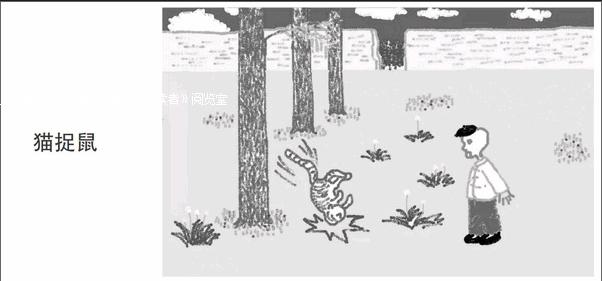

寒冬腊月,是农人们一年中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如果哪里唱大戏,那真是锦上添花、求之不得的美事,秦腔爱好者顶风冒寒、不远十里八里都要撵着去看。
那一年,黄铎堡村请了红城子村的戏,每天上午、下午各演出一场。
记不清是我的意愿,还是父母的意思,一天清晨,我被父母带着去十里外的黄铎堡村看戏。
父亲骑着自行车,后面带着母亲,我坐在自行车的横梁上,手里提着小板凳。
村子里窝着风,又是刚从家里出来,近三百米长的村道上,我没有觉得冷。可一出村,凛冽的西北风从毫无遮拦的旷野上迎面吹来,我赤裸在外的两只手很快感觉到冰凉,继而冰冷,之后紧绷绷的皮肤上就有了针刺、刀割一样细微而又清晰的疼痛感。我的手抖起来,凳子敲得车把当当响。我对父亲说,我手冻得疼。父亲说,坐稳!把板凳拿好!我不敢再言喘。想起家里的热炕,手渐渐变得不冻也不疼了。但清鼻涕开始不由自主地往下流,屁股下的横梁硌得难受,两只脚也渐渐变得冰冷起来。我想回家,但父亲的自行车还在义无反顾地往前走。我只能盼着快点到达被灰蒙蒙的树木掩映着的黄铎堡村。可这十多里全是上坡路,还顶风带着两个人,父亲的膝盖又有关节炎,自行车的行进速度实在比步行快不了多少。
终于到了黄铎堡村,进了戏场,父亲从自行车上往下抱我,两条小板凳率先落到地上。双脚一着地,就像踩到了千百根倒竖着的长针上一样刺痛,我差点栽倒。母亲抢过来扶住我,给我擦净清鼻涕,握着我通红的双手说,把我娃的手冻坏了!我恓惶地哭起来。帽檐、眉毛上结着白霜的父亲说,哭啥呢,再哭下回不领了。
绿色帆布搭成的戏台上大幕低垂,毫无动静。但戏台下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走动,地上摆着预占位置用的板凳和石头砖块。在中间地带找位置坐下来,母亲把我抱在怀里,焐着我的双手。有了温度,双手渐渐觉得又热、又胀、又疼,十分难受。我后悔竟然会欢天喜地的跟着父母来受这样的罪。
人越来越多,认识的相互打招呼拉家常,戏场上热闹起来,人声嘈杂。戏台上终于有人走动了,器乐班的人相继就位,开始吱吱啦啦地调试乐器。台上梆子几响,干鼓、铙钹、弦索紧跟着响起来,大幕徐徐拉开,戏开了。台下的人声如滚汤泼雪般顿时平息下来。刚开始,我还很好奇地看着演员们花红柳绿的服装和油彩花脸的扮相,可每出来一个人总要或说或唱一段时间,人物变换并不快。戏台两边的大喇叭声音很大,奈何说词、唱词我一句也听不明白,根本不懂所演的内容。我逐渐失去兴趣,觉得索然无味起来。可父母和那些老年人都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直着眼睛,看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脸上的表情随着舞台上戏剧的情节或喜、或怒、或悲、或乐地变化着。我在母亲的怀里坐得越来越不耐烦,扭着腰身左顾右盼地看戏场边上追逐打闹的娃娃们,也想出去跑着玩,母亲就把我搂得更紧了。我垂头丧气地盼望着戏能尽快地结束。戏台上出来两个后背上都插着旗子的大将,一个拿着长刀,一个攥着长矛,转着圈子地对打,多少又提起了我的一些兴趣。就见拿刀的挥舞着银光闪闪的大刀向拿矛的砍去,刀头突然从刀杆上脱落,直接飞向了台下,观众们惊叫着、躲闪着,惹得我哈哈大笑起来。母亲在我的后脑勺上按了一下,那意思是不许笑。刀是木头的,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被送上台去安上继续演。不过这一意外情况,倒消除了我的部分急躁和无聊,总算熬到了这场戏的结束。
已经到了午饭时分,观众忽啦啦走得一干二净。我们起身也要走,却见外爷从戏台上下来,和父母说话。外爷就是红城子的人,他是跟着戏班子来服务的。外爷把手里拿着的一盒饼干送给我,这可真是让我心花怒放的意外收获。
下午,父母问我还去不,虽然心里还怀着一丝不大确定的外爷会再送我一包饼干的希望,但我觉得还是待在家里暖暖和和、自由自在的好。再说了,秦腔有个啥看头,除了甩掉大刀头,实在没意思。我坚决不去了。
后来,有了一点岁数,回想起那次看戏的经历,我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从电视上看秦腔到底如何。肤浅地体会到,秦腔确实很好,只要愿意用心观赏、仔细品味,自会觉得余音绕梁、意味无穷。而且这么些年来,多多少少与秦腔也有了些接触,对于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也就多了一些关注和探究。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是相当古老的剧种,堪称中国戏曲的鼻祖。两千余年的时光,民间演绎、人文打磨,使秦腔无论是唱腔唱词、扮相脸谱、身段特技、器乐伴奏、题材内容等等方面,都成为精雕细琢的戏曲文化精品,将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属名至实归。就我所欣赏的为数不多的几部秦腔全本戏来看,无论其过程是悲是喜,总是通过两三个小时的精彩演绎,凸现出鞭挞假、恶、丑,颂扬真、善、美的宗旨来,引导着人们抑恶扬善,传播着正能量。
但愿源远流长的秦腔戏曲艺术,能够长盛不衰、传承发扬下去。
我能记事的时候,爷爷早已将家里的财政大权交给了父母。
但爷爷给自己留着个小金库:一坑“雨子”。
“雨子”是俗称,当地人大都知晓明白是何物,外地人可能就不知所云了。我费了点时间,想从网上搜出“雨子”的学名来,未果。只能粗略描述一下,并和人们所熟悉的芦苇作比较,以助理解。
“雨子”是一种多年生植物,形似芦苇,有着中空的茎、狭长的叶和絮状的花。但“雨子”的茎比芦苇粗,最粗可接近拇指;比芦苇高,最高可达四米多;比芦苇耐旱,生长期只需浇灌两三次透水即可;比芦苇更加坚韧。“雨子”的叶片自然也比芦苇宽长些。“雨子”长成后打掉叶子,将修长的、亮黄的茎紧密排列并用细麻绳编制成片,叫做“雨笆”,是盖房子的材料。“雨笆”覆在房屋的椽子上,方能再铺草上泥加瓦,起着搭建屋顶的重要铺垫作用。这和其他地方用芦苇编成的“苇箔”在起屋造房中所起的功用相同,不过“雨笆”更加漂亮美观、经久耐用。
从院后向西不到百米,紧挨着村小学操场北边,就是“雨子”坑。坑深约一米,面积约一亩,略呈圆形。每年阳春三月,翠绿坚挺的“雨子”苗从湿润的泥土中钻地而出。先是零零星星的几根,逐日快速地增加着数量和高度。不几日,坑里就满是圆润俊拔、疏密有致、高低错落的“雨子”苗了,就像一枚枚蓄势待发、意欲直射苍穹的箭的阵列,那幅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景象,展示着生命力的欣欣向荣和势不可当,让人看着特别长精神。“雨子”苗要长高到一米左右时,叶片才一片片一层层长出来,逐渐填充起茎与茎之间的空隙,坑地里荡漾起浓浓的绿色,恰似一池春水。
从出苗起,爷爷会指派我去看“雨子”。“雨子”坑的南边紧挨着村小的操场,学校里都是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正是玩起来毫无顾忌的年龄,倘若进入“雨子”坑里跑两圈,脆嫩的“雨子”苗必然会受到损害。我在“雨子”坑边自己玩,也看学生们玩。看着看着,“雨子”就出落得越来越修长挺拔、英姿飒爽了,无风时是一道绿色屏障,有风时便掀起巨大的绿色波涛。我会分开密集的“雨子”茎叶下到坑里去,感受那种周身被高拔浓郁的绿色紧密包围起来的奇妙感觉。后来,读到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不知怎么,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置身于“雨子”中的情景来,虽然没有“弹琴”,也不是在“明月”下,但只有这个经历,或可让我能更好地体会诗中的意境。
过了中秋节,“雨子”已经长到三四米高,经霜的叶子干枯了,依然泛着淡淡的绿色。这时候,爷爷会动员了全家人去收割。别看只有约一亩的面积,但“雨子”长得坚韧而稠密,得一根根地来割,往往一天之内还不能结束。大人们在收割,我和弟弟会按爷爷的要求,把割倒的“雨子”按粗细进行分拣:拇指粗的一堆,中指粗的一堆,小指粗的一堆,之下便不用再分。爷爷将大“雨子”每二百根扎为一捆,小“雨子”则不拘数量成捆,扎上三道用冰草或蒿草拧成的草绳,确保颀长的雨子秆在搬运过程中不被折断,用架子车拉回家里去,沿着院子的南墙立着摆放整齐待售。最大最好的每根可以买到五分钱,中等粗细的每根三、二分钱,其余则是按捆论价了。用不了半年时间,爷爷的“小金库”便实现了从“雨子”坑向帆布钱袋的转换,大概也有几百元钱的收入,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可观的一笔财富。
爷爷出售“雨子”所得的用途,一是接济当时生活条件更差的小姑家,另一个便是爷爷享点口福。虽然那时爷爷已年近古稀,但身体还很硬朗。隔上一段时间,爷爷会骑上自行车去三营镇赶集,却往往是两手空空地回来。我总是想不明白爷爷跟个什么集?后来才知道,爷爷去赶集,只是去下馆子享受一顿羊羔肉解馋而已。我觉得爷爷的这种做法不但精明而且正确。爷爷生于公元一九一四年(爷爷总自称是清朝人),从他的童年到青壮年近半辈子的时间里,正遭逢兵荒马乱、匪盗四起、生灵涂炭的乱世,在饥寒交迫中熬煎岁月,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不说,险些命丧土匪、白军的刀枪之下就有好几次,爷爷的这些经历,他都曾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们听过的。在当时生活条件还不太好、无力顾及全家的情况下,从生命这一短暂的过程来讲,爷爷完全有理由、也应该只对自己好一点。
“包产到户”给农村发展变化提供了强劲动力,生活条件改善速度直线上升。二哥、三哥又先后参加工作,他们会给爷爷零用钱,还会给爷爷提供充足的羊羔肉。年事已高的爷爷,也把他的“小金库”交了出来,可在家庭收入中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虽然兄弟们也还浇灌、施肥、收割,随便卖几个零碎钱,但再也不愿意下苦力挖地三尺去给“雨子”进行清根工作,“雨子”也就长得一年不如一年了。
爷爷去世后,兄弟们为兑换宅基地,就把爷爷的“雨子”坑兑换给了别人。
虽然只离着百米的距离,每次回家去,却再未去过“雨子”坑那里,也不知“雨子”是否依然。所谓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致就是如此吧。
小时候,家里很穷,吃的、穿的、用的都紧缺,偏偏老鼠多。
老鼠,这贼头贼脑、鬼鬼祟祟的小祸害,有着一副尖牙的利齿,它偷粮食、咬衣服、啃家具,做恶多端。又专在夜间或隐蔽处活动,听得见看不见,看得见也捉不住,恨得人牙根疼。
奶奶走亲戚,捉回来一只灰色的、带着虎皮纹的小猫。小猫小巧玲珑、憨态可掬、惹人喜爱,除了想妈妈“哭”了两个晚上外,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奶奶说,这是只米(母)猫,会生小猫的。这让我更加充满了期待。
小猫还不能自食其力,奶奶就用饭喂它。晚上,我把它搂在被窝里睡。它很快睡着了,发出匀称而持续的呼噜声。不用担心小猫的卫生问题,要方便它自会钻出门洞去外面处理,还不留痕迹。白天里,时常会看见它在认真地“梳妆打扮”。
半年后,小猫拉开了身段,变得越来越淘气。它会把母亲的线疙瘩滚成个土蛋蛋,会追逐着院子里随风飘动的鸡毛咬住又放开,会到草丛菜园里扑蝴蝶、捕蚂蚱,也会在矮墙上上蹿下跳,少不了要爬树。记得它第一次爬树,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就蹿到西壕里那棵高大的柳树顶上去了。可下来的时候,却显得笨手笨脚。它倒退着一步步往下挪,不停地“喵喵”叫着。可能是着急吧,在距地面还有近丈高的地方,它忽然掉过头打算往下跑,不料全身腾空,直接跌落到地面草丛里,摔地“哇”地一声惨叫,吓了我一跳。
猫儿不再天黑就睡了,往往是傍晚就不知所踪,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带着一身的冰凉钻进我的被窝里倒头就睡。爷爷说,猫儿开始捉老鼠了。果然,猫儿几乎不再吃饭食。这让我很高兴,老鼠们肆无忌惮的好日子该结束了。
过了两年,猫儿长得更大了,也到了谈恋爱、生儿女的年龄。在我的记忆中,猫儿一共生过两次小猫。可能是它在炕上睡惯了的缘故吧,每次总是把小猫生在炕上。爷爷、奶奶一边埋怨着一边收拾卫生,但因它捕鼠有功,却也不会过分责怪。小猫有四、五只,颜色不一,白的似雪,黑的似炭,还有米黄色的,也有和大猫一样满身灰色的。每只都像个小绒球,活泼可爱,是我们小孩子最好的玩伴。令人遗憾的是,小猫才一、两个月大,就被亲戚们一只只捉走了。谁知道大猫心里是多么伤心难过?
猫儿越来越健硕了,它的味口也越来越好,捕猎能力也越来越强。小小的家鼠显然只配做它的点心,它的正餐已经转移到了野外。我曾亲眼见过它叨回来的半截子野兔。那只野兔可真不小,要是完整着,体量应该比猫小不了多少。黑漆漆的庄稼地里,要捕猎这么一只大家伙,那该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啊!
孰料,正是野外猎食给猫儿带来了厄运。
有一天天还没亮,就听见猫儿在院子里凄惨地叫,却并不见进屋来。爷爷觉得不对劲,赶紧出去看,发现猫儿匍匐在院中,右后腿上夹着一个锯齿锋利的大捕兽夹。爷爷大吃一惊,急忙叫起父亲,费了好大劲才将夹子取下来,猫腿早已是血肉模糊,骨头断裂,仅连着些许皮肉。猫儿受了那突如其来、痛彻心肺的一击,还要强忍痛楚,挣断固定铁夹子的绳索,艰难地一步步挨回家里,那是怎样漫长、痛苦的一个过程呢?
猫儿的一条腿彻底残废了,几乎不能自己捕食了,奶奶不得不重新给它备饭。猫也失去了虎虎生气,多见它吃完饭后,慵懒地蜷缩在屋檐下晒太阳。
外婆来了,说要带了猫去。我问,已经捉不成老鼠了,要它干啥?外婆说,猫只要叫一声,老鼠就不敢出来捣乱。
后来到外婆家里去,却并没有看见猫。我没有问,也不愿意多想。
国庆节,我领着儿子回老家。
在三营站下了火车,出站口就看见二哥的车在等着,三哥也在车上,他们是从固原直接过来接站的。
八里路,十分钟不到,我们便投入了村庄的怀抱。
村子里出奇地安静。车子在柏油铺就的村道上平稳地行驶,两旁的庭院树木流水一样向后掠去,铝合金门窗、全瓷贴面墙在秋日暖阳下闪耀着熠熠银辉。
穿过宽阔的大门楼子,车子径直停到了院子里,我们往下取东西。满头白发的母亲笑容满面地从房里迎出来,却满是责备的口气:“说着啥都不要买了,冰箱冰柜都塞得满满地,放都没个地方么……”
晚上,在工地打工的大哥、在淀粉厂做技术员的八弟相继回来。大家坐着闲聊。我说:“玉米叶子都干了,村里人怎么还没有要收的动静?”大哥悠闲地吸着烟,漫不经心地说:“收割机开到地里,一两天的事,急啥呢?权当是在地里晾晒呢。”我无语。从前,国庆节是农人们多么翘首期盼的黄金周啊,上学的、上班的放假回来,正好可以帮着掰玉米。那是多么忙碌的时节啊,每天早出晚归不说,还要挑灯夜战剥玉米皮。一季秋收,快点的得十天半月,种植面积大些,那就得忙活近一个月。我知道,全靠人工的秋收大忙已渐行渐远,农人对侍弄那点庄稼,完全当成了副业,竟然变得如此游刃有余,越来越慢条斯理起来。
隔日,城里的姐姐、四哥、七弟也陆续回来了,国庆节过得和春节一般热闹。期间,唯一能做的就是兄弟们代替母亲做饭,竭尽全力地消耗着冰箱里的冻肉,也好减轻母亲的心理负担。再就是扑克玩到坐不住了,去田野里转悠闲逛,或者到八弟的茨园里去摘秋枸杞,藉此舒筋活骨。
假期的第六天,三哥他们结伴回了城里,大哥、八弟各自去忙,只剩下我和二哥,也没法耍了。母亲说:“来,给你安排个任务,把场里的玉米芯子往回背上些,天冷了我好煨炕。”我给母亲说:“我直接用架子车拉吧。”母亲笑起来:“架子车早都当柴烧了锅了,还哪里来的架子车么?”我这才意识到,不知何时,院里院外确实再没有看到过架子车的踪影了。
我只能用背篼往回背。我一边背一边想,曾几何时,架子车可谓是农家必备的“重器”,拉垫圈土、拉麦子、拉土粪、拉草、拉水、平田整地……那是多么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运载工具啊。没有架子车,大半的农活就无法进行,这对于农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岂止不能没有,往往一辆还显得力有不逮,在农忙时候,相互借用架子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记得家里最早只有一辆架子车,后来我们都长大,家庭劳动力明显增加,父亲痛下决心特意又花钱请人做了一辆更大些的架子车。于是,家里就有了两辆架子车,劳动效率提高了一倍多,那也是惹人眼热的事。架子车如此重要,除了用的时候要小心,不用时,也要好好保管。家里东拼西凑了些砖瓦木料,在院子西南角搭起个矮小的棚子,专门用于存放架子车,免其遭受日晒雨淋,就像做着要几辈人使用的打算。谁能想到,农业机械一旦牵手农民、入主农村、服务农业,便以其摧枯拉朽之磅礴力量,将生产方式推进了一个新时代,同时把原有的农具毫不留情地推出农耕历史舞台。拖拉机、小四轮、皮卡、客货两用……哪个不比架子车装得多、跑得快、用途广、省时又省力?架子车终年难得一用,越来越受冷遇。后来,家院翻修重建,院内更是没有了架子车的立锥之地,只能随便弃置在院外的柴草堆旁,任凭雨打风吹腐朽,最终沦落为柴禾,也算是发挥了最后的余热。仔细再想想,何止架子车,其实,小时候经见的众多畜力及农具,如牛、马、驴、骡、犁、耧、耱、耙、镰刀、锄头、碌碡、连枷……等等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于人们的视线、淡忘于人们的记忆。
人们淡忘着,并将继续淡忘。在这片土地上劳碌了一生的人,对曾经宝贵的旧物件的记忆只会越来越模糊。除了幸福欢乐,人们的淡忘中应该没有其他情绪。
“太阳出来一点红,我们都是年轻人。先进馆子后照相,芳芳是我媳妇!”
也不知是在哪位高人的指点下,年幼无知的我竟然编写出这么热情奔放、大胆直白的爱情诗章来。
我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扯着嗓子对芳芳喊。
芳芳笑嘻嘻地不说话。芳芳她爸是公家人,就站在芳芳的身后,抚摸着芳芳的头发,哼了两下鼻子,说:那怕不一定!
我可不管什么一定不一定,只要诗兴大发,照样扯着嗓子对芳芳那样喊。
我家在北面,芳芳家在南面,两家是前后邻居,中间仅隔着一条窄窄的黄土村道和窄浅的砂底子水渠。我和芳芳年龄一般大,正好能玩到一起。我和芳芳捏泥巴、捉虫子、画螺螺盘……也用拾来的瓷碗碎片当盘子、折下的树枝当筷子、揪来的草叶当蔬菜,置办出一大桌婚宴“酒席”来。左右邻居们看我和芳芳玩得好,笑呵呵地说我们是“两口子”。我和芳芳不但不反对,反而一个劲儿点头认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两口子”是个啥东西,就像不知道我“诗”中的“媳妇”是个花的还是麻的一样。
秋泥巴碎了再捏春泥巴、兔年的虫子死了再捉龙年的虫子、螺螺盘也越画越圆越画越大……一桌桌“酒宴”撤了残羹又换新盏。太阳从东到西再到东是一天,太阳从南到北再到南是一年。不知不觉中,我和芳芳就成了庄中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
一个班里有三十余名小同学,能玩的伙伴、游戏种类一下子变得那么多,我可以和这几个玩,也可以和那几个玩,可以玩“老鹰捉小鸡”,也可以玩“叨鸡”,就不一定非要和芳芳在一起了。芳芳在和谁玩、玩什么,我也不会去留意。我们“两口子”被另外的三十几口子给冲散伙了。这期间记忆深刻的仅有两件:一件是老师让同学们在操场上围坐成一个大圆圈,玩“丢手绢”的游戏。我把手绢攥在手里,在同学们的身后走,然后就丢在了芳芳的身后转身跑开。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芳芳的反应是那样快捷,她噌地蹿起来,风一样地奔跑追逐,我还没有跑到自己的位置,就被芳芳从后领上死死地拽住了。我感觉到脸很红很热,颜面尽失,我输了而且输给了一个女同学,成了同学们的笑柄。还有一件发生在某年的暑假里,村里几个大娃娃组织了一次近乎疯狂的比赛:把架子车推得快快地,然后将一个轮子推上路边的矮墙上去,以在墙上跑出的距离长短决胜负。三哥推着架子车,上面坐着我和四哥,跑得欢欢地,一个轮子就上了墙,斜吊着跑了一截子,臂力不支时,复又推到平路上。其他几辆架子车都或长或短顺利地进行了比赛。芳芳和她四哥坐在架子车上,由她三哥推着参加比赛。她三哥身强体壮,对跑出最长距离、斩获第一名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他特意把架子车拉得远远的,留足了助跑、加速的距离,然后深吸一口气,身子大幅度前倾开始发力,架子车迅速启动,越跑越快,向着土墙冲上去,就在大家都聚精会神观赏他们精彩表演的时候,意外情况发生了:芳芳的三哥把架子车推得太快、一个轮子上墙又太高,“哐啷”一声,架车子翻了个底朝天,两个轮子还在欢快地转动着,车厢下面压着的芳芳和他四哥大哭起来,其他的人随着欢快地大笑起来。
到了二年级,虽然生理年龄只增加了一岁,可心理年龄好像增加了十岁。男生们集体性意识到,和女生一起玩是不知害臊的丢人事。被老师分着和女生坐同桌,会感到难为情和尴尬,那是没有办法。可一但下课后做游戏,男生、女生立马就泾渭分明了。谁要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女生说话或者玩耍,就会享受到群起而攻之地讥讽和被列为第二严重的“骂人话”:谁谁谁是谁谁谁媳妇!第一严重的“骂人话”是啥?当然是被大声地喊出爹老子的名字了。客观处世环境如此恶劣,我是不愿也不敢和芳芳再有单独的接触了。我这才反应过来,多少年里,我兴高采烈地喊着“芳芳是我媳妇”,原来是自己在骂自己啊!
芳芳的学习不太好,二年级毕业时,芳芳留级了。我学得也不怎么好,勉强上了升级线,到二里开外的村小学去上三年级,就和芳芳不是一个学校的学生了。再过了一年,芳芳也升级到了村小学,可已经不是同年级的学生,而且村小有二三百学生,除了放学路上还能看见芳芳,在校园里都很难发现她。这时候对“两口子”“媳妇”之类多少有了一些模糊但尚属正确的认识,想起小时候对芳芳的隔路喊话,真是羞死人了。我见了芳芳不好意思,芳芳更是老远就低着头,看都不愿意看我呢。
芳芳她爸的能量还是很大的,在芳芳上初中之前,就把芳芳和他三哥、四哥都办成了城镇户口,到城里吃“皇粮”去了。院子由他大哥家搬过来住着。芳芳和她三哥、四哥偶尔也回农村来转,但毕竟能见着的次数更加稀少了。
二十岁的时候,我在外地参加工作,每年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几乎没有再见过芳芳的面。庄子里很多的变故都是从兄弟们的聊天中得知的。也就知道了芳芳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她爸宠爱这个最小的老疙瘩女子,宁可养着也不愿意叫她出去找工作。后来,芳芳结婚了,她老公人挺老实本分,工作又好,挣钱又多。芳芳找到了好归宿,照例不用出去工作,专一地做着贤妻良母,忙碌着家务。我心里暗自失笑,事实证明,芳芳她爸说的“那怕不一定”是正确的。而我只不过是早在二十年前,窃取了本该属于芳芳老公的诗作,提前念给芳芳欣赏了而已。
十年前回家帮七弟收葵花,听七弟讲村里的人事。说着说着,七弟忽然说:芳芳死了,你知道吗?我割葵花头的刀子差点削到手上,我说:你说啥?七弟说:芳芳死了,你听说了吗?我摇头。七弟说:唉,已经是去年腊月里的事情了,两口子都煤气中毒了,一个也没有抢救过来。幸好娃娃那天晚上送到他奶奶家去了,总算是留下了个苗苗子……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那是顺应自然规律到了该离开的季节。芳芳却像那春夏之交的一片绿叶,在本该最为繁盛的季节里突然凋零了。芳芳离开这个世界时,大概也就三十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