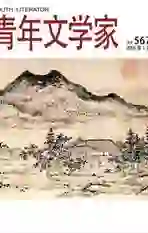《群山回唱》的空间叙事分析
2016-04-19牟李园胡笑瑛
牟李园 胡笑瑛
摘 要:随着叙事学的发展,空间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第三部小说《群山回唱》以阿富汗的一户家庭为起点,讲述了不同地点,不同人物的一系列故事。它实现了广阔的地域跨越,从阿富汗到法国到美国再到希腊,从此可以看出空间因素在本小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旨在根据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从物理空间,人物的心理空间,及社会空间三个角度来具体分析《群山回唱》,以把握空间叙事在小说构建及主题凸显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空间叙事;《群山回唱》;亨利·列斐伏尔
作者简介:牟李园,宁夏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胡笑瑛,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4
一、导言
不同于胡塞尼的前两部小说,《群山回唱》不再仅仅集中于阿富汗,而是将范围扩展到了法国,美国,希腊各地,拓宽了故事的范围,丰富了主题。书中故事时间跨度非常大,长达六十三年,而且故事叙述并不连贯,每一个叙述者在不同的时间叙述不同的事件,经历,如碎片般难以拼凑。但文中的空间地点为读者提供了拼凑的基点,作者正是借着同一人物不同空间的转移,以及同一空间内不同人物的变化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连接人物关系,凸显故事主题。
根据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我们可以将空间分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列斐伏尔曾说过“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是:第一,物理的——自然,宇宙;第二,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第三,社会的。”[1]物理空间是可感知的空间,是自然的物质的,例如故事发生的场所,地点等。精神空间是被构想的观念化的空间。“最纯粹的精神空间形式是全然观念性的,它从构想的或想象的地理获得观念,并将这些观念投射到经验世界去。这并不是说不存在物质现实,而是说物质现实知识本质上要通过思维,准确地说“思维的事物”去获得理解。”[2]社会空间既是物理的又是精神的,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每一个社会中存在的主体都有自己的社会空间,而不同的社会空间又反映不同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创造了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反过来又影响社会主体,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看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三者互相影响,密切相关。本文试从物理空间,人物的精神空间及社会空间三个方面具体分析,探讨书中的空间叙事和主题构建。
二、物理空间
小说从阿富汗的一个小村庄沙德巴格开始,随着故事的发展涉及到不同的国家,城市,地点, 可谓进行了物理空间大迁移。生活的贫困,情感的缺失造成了家庭的破散,一场场战争更是迫使阿富汗人四处逃离,寻找安身之所。文中的物理空间不仅介绍了故事发生发展的地理背景,更是通过空间的迁移变化展现了阿富汗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小说中的人物关系。
首先,故事的起点在阿富汗的沙德巴格村庄,由于家庭贫困,帕丽被卖到了喀布尔一户富人家庭,开始了第一次空间转变,这次空间转变,引起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由于帕丽养父的突然发病,妮拉便带着帕丽定居巴黎,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正是这种空间上的远离,间接导致了帕丽与哥哥阿卜杜拉的难以团聚。
由于战乱,很多阿富汗人逃亡美国和巴基斯坦。帕丽的哥哥阿卜杜拉先是到巴基斯坦后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定居,开始了新生活,而帕丽的弟弟伊克巴尔则一直长期呆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躲避着战争灾难。伊德里斯和铁木尔则是帕丽的养父的邻居,同样在战乱期间逃到了加利福尼亚且与阿卜杜拉相识。故事中的人物本在一个相对较为紧密的空间,由于贫穷,情感缺失,战乱等原因而使得紧密的空间分裂拓展,这种空间的变化不仅交代了故事背景,也让作者借此开阔了故事的边界,使得内容更为丰富。
此外,人物有去有回,展现了一个双向的过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人物陆续回到阿富汗,回到他们开始的地方。伊德里斯和铁木尔回到阿富汗,意在收回喀布尔的房子,因为战争期间房价飞涨,是发横财的好机会。而纳比则把帕丽养父的房子免费租给了马科斯,从希腊来到阿富汗的救助人员。也正是马科斯帮助帕丽了解到了自己的身世,推动帕丽回到阿富汗,而帕丽养父的房子则成为将两人联系起来的纽带。伊克巴尔一家则是由于巴基斯坦不再收容阿富汗人,难民营撤销,便回到了家乡。但回到家乡的帕丽和伊克巴尔一家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家,一场场战争使得家乡失去了原来的面貌。他们的家现在变成了“毒房”,一个战争犯,阿德尔父亲的豪宅。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战争对阿富汗人家园的破坏,使得阿富汗人无根可循。最终帕丽到美国与哥哥重聚将故事推向了尾声。从分离开始,最终以重聚结束。
文中对物理空间及其变化的描述不仅展开了故事的发展背景,描述了阿富汗所遭受的战争灾难及其历史变迁,也通过空间的拓展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让读者的眼界的眼界不再局限在阿富汗,暗示了小说的国际主题。最后的返乡情节则是体现了寻根追求,引起人们对阿富汗的关注。
三、精神空间
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空间丰富多样,但也多有相似之处,本文主要从爱的缺失,逃离——内疚——承担的心理模式以及双重身份的尴尬这几个方面探讨。
1.爱的缺失
故事中爱的缺失有多种多样,有父母之爱的缺失,例如有兄妹之爱的缺失,也有爱情的缺失,爱的缺失造就了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和精神空间,下面就分别以妮拉和瓦赫达提先生为例,来具体分析人物的精神空间。
妮拉小时候便父母离异,她与父亲住在喀布尔,而母亲则搬到了巴黎,远距离的难以相见注定了妮拉母爱的逐渐缺失。妮拉的父亲则是严肃古板的人,在妮拉小的时候,每隔几天,父亲便陪她玩几分钟,“他走进我房间,坐到床上……他把我搁到膝盖上,颠我一会,”[3](p.200)这时的妮拉还是个纯真的孩子,房间便是她与父亲亲近的场所。妮拉逐渐长大,思想越来越不受拘束,整天往外跑到街上闲逛,而父亲的做法便是将她拉回来,锁在屋里,或是用暴力手段让她屈服,追的满屋子跑。那时妮拉叛逆不羁,房间成了妮拉的禁锢场所。继母爱缺失之后,妮拉也渐渐感受不到父爱。一次大病之后,妮拉整天窝在房间里,厌倦了交际,厌倦了写作,变得脆弱而孤僻,但父亲却将妮拉的安分当做好现象,备受鼓舞。几天之后妮拉便走出房间,开始了正常的生活,那时妮拉已经懂得掩饰伤痛,房间成了她短暂的疗伤场所。妮拉因生病而注定无法有孩子,在结婚后,妮拉再次为此事伤心,躲到房间里不出门,这时她的父亲来到她的房间而妮拉的脸上“是人们那种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的表情,”[3](p.96)可以看出妮拉对父亲到来的惧怕。直至后来,当她的丈夫瓦赫达先生生病期间,她抱着帕丽呆在了帕丽的房间,逃避着众人的眼光和残酷的现实。房间这个空间意义的变化,也表现了妮拉的精神空间,从纯真到叛逆不羁再到孤僻脆弱,强装洒脱,而这种精神空间的变化与妮拉爱的缺失尤其是父爱的缺失有着重要的关联。
瓦赫达提先生是妮拉的丈夫,但他爱的却是司机纳比,帕丽的叔叔。这种情感在当时的社会是注定不会得到结果的,瓦赫达提先生便将这份得不到的爱情深深掩埋,这种爱情求而不得的情况也塑造了他严肃,孤僻,冷漠的性格。作者通过纳比总结了瓦赫达提的生活轨迹,除了一月一次的添置画具,一周一次的探访母亲,以及小部分的聚会外,他每天早晨让纳比陪他出去散步,一天中剩下的时间大部分在书房里读书,跟自己下棋,也会经常看到他在书房窗口或者游廊里涂涂画画。有时会坐在车后座让纳比载着他漫无目的的闲逛。通过纳比的描述可以发现瓦赫达提先生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从表面上看只能是认为他是一个生活规律,无趣的人,但通过后面的进一步描述,我们便会发现瓦赫达提先生的真意。外出基本上有纳比相陪,不管是每天的外出散步还是偶尔的坐车兜风。这看似惬意的状态,但其实也显露了瓦赫达提先生内心的孤单痛苦。他散步时与纳比几乎无交谈,步伐很快,将纳比落在身后。坐车外出兜风时,有时“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一副天底下最孤单的模样。”[3](p.78)借着散步和兜风的借口,瓦赫达提先生获得了与纳比的独处时间,但又不能像爱人甚至是像朋友一样相处,只能把纳比抛在身后或者是坐在车后座装作一副淡漠无谓的样子。在家中,瓦赫达提先生的几个活动场所也有相同之处,那便是能观察到纳比的一举一动。他无法正大光明地跟随纳比的身影,便通过书房的窗口,通过游廊,通过他的画笔,记录纳比的点滴也释放自己无法倾诉的爱恋。而这些记录了瓦赫达提先生爱恋的画册,也被他封藏到衣柜里的大纸箱里。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瓦赫达提先生有限的活动场所都与纳比有关甚至是以纳比为中心,表现了对纳比深深的爱恋。但这一个个限制的空间也表现出了瓦赫达提先生这份爱恋的隐秘,绝望。正是对爱的求而不得,爱的缺失塑造了瓦赫达提先生冷漠,孤僻的性格伪装。
2.逃离——内疚——承担的心理模式
故事中很多人物都存在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心理状态,其中普遍存在的是逃离情节,逃离后内疚之情随之而至,经历了内疚痛苦,有的人物则承担起责任,有的人物则是伴着内疚痛苦度过一生。纳比逃离沙德巴格,卸下了照顾残疾妹妹的责任,到喀布尔开始新生活;小帕丽(阿卜杜拉的女儿)经常幻想着冲出家门,逃离父亲带给她的情感负担和责任;妮拉抛下中风的丈夫到巴黎定居;伊德里斯返回美国后便淡忘了自己的承诺,推脱了自己的责任,最后带来了满心悔恨。马科斯则是故事中完整地经历这一模式的人物。
马科斯是故事中外来救援人员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希腊蒂诺斯岛来到了阿富汗的喀布尔。马科斯小时起便志愿当一名摄影师,走出小岛,游遍世界。他有时候看不惯岛上居民的某些心理和行为,为了不变得与他们一样,马科斯决心要走出小岛。但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马科斯与性格强硬的母亲关系的僵硬紧张,他急于冲出家门,逃离这种紧张,不满意的环境,获得自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马科斯走过了数不清的地方:智利,加拉加斯,印度,大马士革,开罗,冰岛等等。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或者说是流浪中,马科斯逃离了母亲对她的枷锁,将母亲抛在了身后,但同时也充满了迷茫。后来,马科斯来到了喀布尔长居,成为一名长期救助人员,与母亲更是无从见面,只能通过电话与母亲保持联系。
马科斯的母亲一直存在着对孤独的恐惧和对遭人遗弃的惧怕。马科斯了解他的母亲“我清楚地知道她需要什么,可还是坚定地拒绝了她,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一心让我们之间隔着一块大陆,一座大洋——更确切地说,既有大陆,也有大洋。”[3](p.309)最终,马科斯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小时候的家,虽然家中的空间并没有什么变动,但马科斯却感觉到家中物件之间的巨大缝隙,这些缝隙便是他这些年来在母亲生活中的缺失。在看到母亲苍老的境况后,心中更是充满了悔恨与内疚。母亲觉得自己是包袱,会拖累马科斯,但马科斯知道自己不会被压垮,因为“我不在,我在几千公里之外。”[3](p.351)这趟回家之旅让马尔斯的悔恨更加浓重,但也让马科斯明白母亲不是枷锁,而是永久的港湾,因为母亲永远不会离开他。在最后的场景中,马科斯将母亲的手握在了手中。通过马科斯的物理空间移动,可以看到他对自由的渴望,对母亲“枷锁”的逃离,最后的返乡团聚,与母亲牵手相握,则表现了马科斯对母亲爱的重新认识和对自己责任的承担。
3.双重身份的尴尬
由于战乱,很多阿富汗人迁往美国,两种文化形态的差异必然带来双重身份的尴尬。伊德里斯小时候在喀布尔生活,随后在美国定居,中期回到阿富汗感觉不再一样了,变成了“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变成了“观光客”。“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3](p.148)伊德里斯生在阿富汗,但生活在美国,阿富汗的印记不会消失但也在逐渐淡化,到底是阿富汗人还是已经成为美国人?这种双重身份的尴尬在伊德里斯回到阿富汗时变得格外凸显。
小帕丽即阿卜杜拉的女儿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没去过阿富汗,但从小便在父亲的阿富汗餐馆帮忙,课外到坎贝尔学习波斯语,到清真寺学习古兰经,严格遵守着伊斯兰教教义。生活在美国,小帕丽的伊斯兰背景给他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和冲突。游泳课,班级组织的水族馆外宿活动小帕丽都不能参加,甚至当交了男朋友也因男友的非伊斯兰背景而产生了诸多的顾虑。这种宗教和文化上的冲突使得小帕丽一度伤心不解,虽然最终还是慢慢了解并喜欢上了伊斯兰文化,但不可否认,小帕丽确实承受着双重身份的尴尬。
通过具体分析可以发现,故事中人物的心理精神活动不仅仅存在于故事中或者是局限于阿富汗,而是我们很多人都面临的境况。作者通过对精神空间的描写阐述,塑造了人物性格,展现了人物心理状态,不仅将故事中的人物紧密相连,更是通过共同的人性主题将故事扩展到现实世界中,引发读者深思。
四、社会空间
小说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各个方面,因此也产生了不同的空间,不同的空间也反映了多样的社会关系,“社会空间里主要有两种社会关系: 一是生物性生产关系,比如夫妻、性别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二是物质性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物质资料的占有、剥削及产品分配关系。”[4]小说是以家庭为核心,所以夫妻,兄弟姐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贯穿全文,由于阿富汗的战乱背景,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关系以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为了逃避战乱,阿富汗人民到国外避难生存,必然会存在一定的文化冲突,尤其是在二代移民当中。另外,社会中也会存在一定的等级关系例如穷与富,仆人与主人等。下面就从兄妹,朋友,主仆这三种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
1.兄妹关系
阿卜杜拉和帕丽这对兄妹是故事的主线,帕丽一出生便失去了母亲,是阿卜杜拉将其拉扯长大,兄妹之情非常深厚。帕里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总是阿卜杜拉抱着她颠上颠下,“他抱住她满村转,到处显摆,仿佛她是全天下最让人渴望得到的奖杯。”[3](93)即使帕丽两岁了,阿卜杜拉的还总是将帕丽抱到腿上坐着,晚上睡觉时帕丽也是缩在哥哥的怀里。从二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可以看出两兄妹亲密无间。帕丽曾让阿卜杜拉承诺将来一定要做邻居,住在她的旁边,永不分离。
但他们还是分开了,帕丽先是到了喀布尔后到巴黎,已经忘记了在沙德巴格的哥哥,只是在心中留下了一个缺口。而阿卜杜拉则将对妹妹的爱封在了妹妹装羽毛的盒子里和他每天的梦里。在几重波折之后,帕丽终于到了美国与哥哥重逢,但阿卜杜拉由于老年痴呆已经认不出她,即使帕丽试着拉近两人的距离,但仍收效甚微。最后帕丽返回巴黎,而阿卜杜拉住进了疗养院,兄妹俩又再次天各一方。从儿时的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到后来的天各一方,空间上的距离和记忆的缺失使这份兄妹情充满了遗憾。
2.朋友关系
文中的朋友关系也比较普遍。有的友谊不了了之,有的友谊则越来越深,堪比亲情。
纳比与萨布尔从小在沙德巴格一起长大,但自从纳比从中牵线将帕丽卖给妮拉之后,纳比每月一次的探访变得尴尬,在萨布尔表明不希望纳比再来后,纳比就再也没有回过沙德巴格,没有再见过萨布尔。沙德巴格承载着纳比与萨布尔的童年记忆和共同成长的情谊。萨布尔对纳比的冷淡拒绝,剥夺了纳比回沙德巴格的理由,切断了纳比与沙德巴格的联系,也切断了两人之间的情谊。
阿德尔与吴拉姆的友情则是刚开始就被无情地掐灭。阿德尔自从搬到沙德巴格之后便没有玩伴,吴拉姆的偶然出现给他带来了惊喜,他们在阿德尔家的豪宅与果园之间的空地踢足球,坐在树墩子上谈天说地。但阿德尔渐渐知道了自己家的豪宅是父亲推平了吴拉姆老家后建起来的,那大橡树墩子便是最好的证据。正是自己的父亲抢占了吴拉姆的家园,是自己的父亲导致吴拉姆无家可归,最后更是自己的父亲杀死了吴拉姆的父亲。当在果园中捡到吴拉姆父亲破碎的带血眼镜时,吴拉姆便认清了现实,也知道他与吴拉姆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果园及园中的大橡树墩子,既是二人友谊开始的地方,也是两人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如今的果园是以前吴拉姆的老家,在这样一个充满讽刺的地点相遇,注定了这段友谊的遗憾结局。
3.主仆等级关系
纳比被瓦赫达提先生雇佣做全职工作,包括做饭,开车,打扫等等。从两方的居住场所便能看出两人之间的等级关系,瓦赫达提先生的宅邸非常宏伟漂亮,而纳比则是住在后花园的一个窝棚里。纳比经常的活动场所有厨房,游廊,还有车中“等在商店的外头,空转着引擎;等在举办婚礼的楼外,听着音乐含混的回声。”[3](p.77)一切都是以雇主的要求为中心。但随着故事的发展,纳比与瓦赫达提先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空间也随之出现了变动。瓦赫达提先生中风后,纳比留了下来,最初是为了照顾瓦赫达提先生,尽到自己雇工的义务。但当知道了瓦赫达提新先生对他的感情后以及长久的贴身服务和相处,纳比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此时纳比以不再住在小窝棚里。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日渐亲密,纳比称瓦赫达提先生“苏莱曼”,纳比推着瓦赫达提先生出去散步,而不再是瓦赫达提先生将他落在身后,两人之间呈现了并列空间,而不再是前后空间。在瓦赫达提先生生命的最后,纳比紧紧抱住了他,亲自结束了他的生命,表现了两人之间的信任和依靠。纳比早已将这个宅邸当成家,将苏莱曼当成了他的伴侣。虽然瓦赫达提先生已将房子送给纳比,但当瓦赫达提先生死后,他又重新搬回了小窝棚,因为一个人,没有苏莱曼的陪伴,这个房子实在是太大了而且纳比“对任何一件东西都没有主人的真情实感,而我也知道,我永远也不能真的产生那种感觉。”[3](p.128)纳比死后葬在了瓦赫达提坟墓的旁边。
从窝棚——宅邸主屋——窝棚——坟墓,从前后空间到并列空间,纳比和瓦赫达提先生的关系也从最初的雇佣到后来的密友伴侣。关系虽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从对房子所有权的看法可以看出纳比心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等级观念。
五、结语
《群山回唱》跨越地理限制,通过物理空间的描写介绍了故事背景,推动了故事情节。精神空间的描写不仅表达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心理更是表现了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热人物精神空间的某些共同点相似之处例如爱的缺失和渴望,责任的逃避,内疚悔恨,弥补承担等所有人类都可能面对的心理挑战。通过社会空间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到阿富汗的社会状况,也充分探讨了夫妻,兄弟姐妹,文化,等级等各种社会共有的关系。作者不仅展现了真实的阿富汗图景,同时也揭露了人性的共性,对自由与爱的渴望,赞颂了亲情和爱情的力量,强调了责任的重要性。正如小说的标题所暗示的,这不仅仅是关于阿富汗的故事,“踉跄前行中,你总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丢失的那一部分自己。”
参考文献:
[1]牟娟.简析列斐伏尔空间理论[J].青年文学家,2009.
[2]赵海月,赫曦滢.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辨识与建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2).
[3][美]卡勒德﹒胡塞尼.群山回唱[M].康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潘可礼.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J].南京师大学报,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