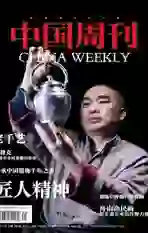麋鹿引种放归洞庭湖
2016-04-16李春梅
李春梅
2016年3月3日,洞庭湖。春寒乍暖,暖阳抚慰大地,春水无声流淌。
早上十点多,湖边的一处荒滩隐隐含着躁动的气息:用黑色围栏圈起的场地中,16头麋鹿正紧紧挤成一团。它们对这块即将成为它们新家园的土地充满了好奇。但千年前,这里却是它们的故乡。
16头麋鹿在一个月前离开“老家”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两千多个“兄弟姐妹”中脱颖而出,年轻、健壮。但到达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它们还是被进行隔离饲养观察。大丰和洞庭湖,即使仅仅相隔了数百公里,为了让它们适应洞庭湖的“水土”,一个月中,它们被混合喂养,用洞庭湖的水草拌着从江苏大丰带来的青贮饲料一起喂食。“世界野生动植物保护日”这一天,它们将被放归到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荒野之中。
两米多高的沉重围栏徐徐开启,畏缩的鹿群更加不安,湿漉漉的双眼中含着惊恐,试图从彼此身上的温暖中获取慰藉。栏外,将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洞庭湖位于中国湖南省北部,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形容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东洞庭湖是洞庭湖湖系中最大的湖泊,是中国列入《国际湿地公约》的七处重要湿地之一,依赖其生存的物种非常丰富,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认定的全球200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据WWF粗略统计,洞庭湖湿地有100多种可供麋鹿享用的食物。对于这16只将被野生放养的麋鹿而言,洞庭湖庞大的水域系统和宽广的滩涂将成为它们自由嬉戏的乐土;而洞庭湖的苔草、芦苇、菖蒲、三蕊柳等植被,都将会成为它们的饕餮美食。
但同时,这些麋鹿们也面临着更大的考验,如春夏之交的麋鹿争霸赛。每年5月,是麋鹿的交配季节,此时雄鹿会往自己身上涂抹泥土,角上悬挂青草来彰显自己的实力。而为了争夺与雌鹿的交配资格,雄鹿们将进行“生死”决斗,最后胜出的“鹿王”才能把自己优质的基因传给下一代。这是“王者”待遇,也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法则。新来的雄鹿是否能顺利参与角逐,与土著雄鹿进行较量?较量中,它们是否能够胜出?“鹿死谁手”——是实现种群交流的关键。实现种群交流,将改善洞庭湖麋鹿种群遗传结构,促进种群复壮和基因交流。
很快,鹿群发现了出路,迫不及待地,在一只雄性麋鹿的带领下,飞快而有节奏地冲栏而出,飞蹄溅起乱泥,消失在芦苇丛深处。
这是一次生命的开启。湖南省林业厅、中国绿化基金会(CGF)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这一使命的开启者,他们选取大型通江湖泊——洞庭湖作为“拯救濒危物种的希望地”,在环境急剧变化的当下,为“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做着不懈的努力。
神秘的麋鹿跟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物种一样,有太多的未解之谜尚未探索,尤其特殊的是它们英雄式的东归史诗。
麋鹿俗称“四不像”,面似马、角似鹿、尾似驴、蹄似牛,其自古就被认为是吉祥之物,形象和精神深深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据说姜太公的坐骑就是麋鹿;而在民间,麋鹿更是神奇之物,它不仅是先民狩猎的对象、崇拜的图腾和仪式中重要的祭品,麋鹿的鹿角年年落而复生更被认为是生命力旺盛的标志。
麋鹿曾经是我国特有的物种。已出土的麋鹿化石表明,麋鹿起源于距今200多万年前,距今约1万年至3000年时最为昌盛,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种群规模数以亿只,但在商周时期以后迅速衰落。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洞庭湖,水草肥美、人烟稀少,岳阳一带筑有“东麋城,西麋城”,是麋鹿的乐土。《墨子·公输》里有记载:“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距今约120~140年前,野生麋鹿在中国最终绝迹——“绝迹的地点是长江口附近沿海地区”。洞庭湖近六千平方公里的湿地上,麋鹿的奔跑声、呦鸣声无迹可寻。
至清末,中国麋鹿的数量只剩200余头,全部被圈养在北京南海子的皇家猎苑。1865年秋季,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大卫无意中发现了南海子皇家猎苑中的麋鹿,他以20两纹银为代价,买通猎苑守卒,弄到了麋鹿的一个头骨、二张皮运回法国。1866年,麋鹿被确认为从未发现的新种,而且是鹿科独立的一个属。从此,麋鹿学名定为Elaphurus davidanus,英文则称为Pere Davids Deer(大卫鹿)。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麋鹿被劫杀一空,麋鹿至此在中国本土灭绝。只有之前,被英、法、德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购等手段,从北京南海子猎苑弄走的几十头麋鹿,幸免于难,生活在各国动物园中。
1985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努力下,英国政府向中国赠送了22头麋鹿,阔别故乡85年之久的麋鹿,结束“流亡”生涯,重新回“家”。198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又从英国伦敦动物学会七家动物园挑选39头麋鹿赠送给中国政府,放养在江苏大丰,从此建立了世界第一个麋鹿自然保护区。历经三十多年的养护、保护、繁衍和扩散,至2015年,中国麋鹿的数量已经达到5000多头的规模,30年增长49倍,占世界麋鹿总数的83%。在北京的南海子麋鹿苑、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湖北石首麋鹿保护区都有稳定的麋鹿种数量群。
麋鹿一度近乎灭绝,即便人们已经在保护麋鹿的道路上,为修正自己的错误做了很多的尝试和努力,依旧任重而道远。在《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上,麋鹿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2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上,麋鹿也榜上有名。2016年,是麋鹿回到中国的第31个年头。而3月3日,是第三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在这一天,将16只幸存的麋鹿放归荒野显得意义重大。
“对濒危动物最好的保护便是将其放归自然,让它们成为自然生态链中的一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长江项目高级经理蒋勇望着鹿群消失的方向感慨道,“放在保护濒危物种的大方向上,它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具有科学探索的价值。”
选择洞庭湖作为麋鹿重回大自然的第一步,源于麋鹿的另一个传奇。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洪水过后,东洞庭湖的农民发现了麋鹿的踪迹。专家分析:洪水之时,湖北石首天鹅洲麋鹿保护区围栏被冲垮,麋鹿因此流出,部分麋鹿渡过长江到达洞庭湖,从此一直在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芦苇沼泽地繁衍生息。2009年12月,WWF组织了江豚、麋鹿、水鸟的野外同步调查,发现约有60只麋鹿生活在东洞庭湖保护区范围内。2014年8月,东洞庭湖保护区通过对麋鹿的野外监测,发现已有近90头麋鹿生活在洞庭湖。当年“迷失”的麋鹿,如今扎根洞庭湖,成为全国最大的没有人工干预的野生麋鹿种群。
洪水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说明洞庭湖仍然适合麋鹿栖居。经过近二十年的野外生存“训练”,自然野化的麋鹿已成功克服了夏季洞庭湖高水位带来的生存困难,进行短距离迁移:当洞庭湖水位上涨、栖息地被淹没时,鹿群会越过防洪大堤,到临湖的苇地、山林、农田、果园等处栖息。而它们在洞庭湖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
对“神出鬼没”麋鹿的调查研究成了难题。原来的监测只是对麋鹿活动范围的把握,它们在哪些边界活动、当地环境对它们有无干扰等,而他们的病理、生理变化是无法监测到的。监测的空白导致对动物迁徙路径、迁徙通道以及迁徙中的种群特征信息犹如马赛克一样失真、错杂,不能准确、完整地建立重点保护区域。
事实上,对于任何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研究和保护而言,借助高科技手段、利用大数据对物种进行追踪和分析,十分重要。卫星追踪已被广泛应用在熊猫、雪豹、大象、白鹤、小白额雁等众多野生动物身上,无论被追踪动物的生活环境多么险峻,跨越多少距离,都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高科技也被运用到了麋鹿的研究监测上,16只麋鹿在野放前被装上了最新的卫星跟踪器,未来将传递回它们生命的足迹,实时追踪麋鹿的活动轨迹,与野生种群交流的状况。在环境急剧变化的当下,麋鹿能否适应和如何适应野外的生存,将随着卫星跟踪器传递的信息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为研究麋鹿种群的生活习性、活动规律、环境需求等提供一手资料。
“我们在放归的麋鹿身上佩戴卫星跟踪装置,也正是出于监测的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展麋鹿的取食、繁殖、生境选择与适应等行为生态学及生存竞争、繁衍模式等种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为将来野生麋鹿的保护措施和决策提供科学支撑。”蒋勇介绍。这一行动同时也是由中国绿化基金会(CGF)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主导实施的“物种100”卫星跟踪项目(Wildlife Footprint)的开端。这个项目在未来的数年内,将在中国境内选取具有典型代表的100种物种,为其安装卫星跟踪器,以获取这些野生珍稀濒危物种的迁徙和活动数据,从而为科学研究以及管理部门实施生态保护和规划提供基础信息,推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物种保护。
归去来兮,“迷”途之鹿如今得以回归荒野,这是自然一个现实的“传说”。人类在将麋鹿逼进濒危后,开始重新保护,并希望通过此次的野化行动来摸索出一条保护濒危动物的出路来。救护和保护一个物种是历史使命,通过使命的达成,我们在保护物种的同时,也在保护我们共同生存的自然环境,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草长莺飞,麋鹿飞奔而去迹。接下来的日子充满凶险,虽不确定,但值得我们一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