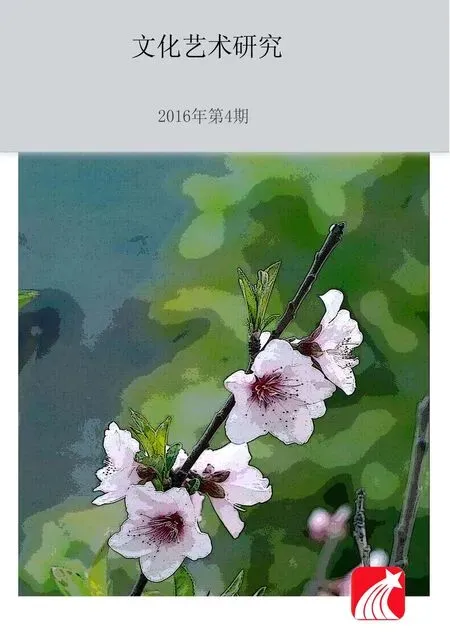春天,想到了王佐良先生和莎士比亚*
——论王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
2016-04-15李伟民
李伟民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绍兴 312000)
春天,想到了王佐良先生和莎士比亚*
——论王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
李伟民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绍兴 312000)
从宏观与微观角度梳理了王佐良先生在莎士比亚研究中的杰出贡献及办刊思想。王佐良的莎学研究体现为他对莎士比亚的总体思想与审美的把握,深入探讨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戏剧的发展史;对莎士比亚白体诗则从文体学角度分析了莎剧白体诗上格“庄严体”、下格“市井小人语”和中格所涵盖的社会阶层中人物的语言特点;阐述了中国学者的莎士比亚研究观;强调莎学研究应该在文本研究基础上结合舞台研究,才能对莎士比亚有深入理解,并对中国舞台上演出的莎剧进行了充分肯定。
王佐良;莎士比亚;研究
引 言
2016年4月,在这个飞花飘雨、姹紫嫣红的日子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戏剧家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的纪念日。纪念他们,研读他们的作品,演出他们的戏剧都是为了文化、文学经典的传承与发展。为此,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演出、研讨活动。我相信,在这样的日子里,在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年之际,纪念王佐良教授百年诞辰也是格外具有重要意义的,也是外国文学界、莎学界的一件大事。因为,佐良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莎学研究专家,也是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2001年,我在《王佐良先生纪念文集》上怀着崇敬的心情撰写了《人生似莹莎如海 词藻密处窥真情——论王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其后又经过修订,以《域外掇沈珠:王佐良的莎学思想》为题,刊载于《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莎学知音思想探析与理论建设》一书中,对王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成就和思想做了进一步阐发。白驹过隙,往事如烟,不知不觉十五个年轮已经悄然划过,在隆重纪念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有感于王佐良先生对莎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我又再三捧读佐良先生的论著认真学习,感受着佐良先生精辟的论述,创新而严谨的思想,深入的叙述和发人深省的深刻阐释,经过对原有认知大幅度的再梳理,力求进一步深化对佐良先生莎学思想、莎学研究的认识,以使一如我当年一样青涩的今天的青衿学子,在牖启后学、抉发阃奥中能够感受、了解到英国文学研究大师和莎学研究大家——王佐良先生的学术风范、莎学研究的特点和一个中国莎学研究者对莎士比亚的认知,希望沐浴在前人的智慧与精神光芒中,后来者通过不懈的努力,以翔实、厚重而富有才华的研究,为中国的莎学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一、中国莎学的重要学者与莎学基本文献的缔造者
在近二百年的中国莎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莎学研究尽管经过了许多曲折,遭遇到不少困难,但往往也能在柳暗花明中一步一步走向不断的辉煌。回顾中国莎学发展的不平凡历史,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在20世纪为中国莎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众多学者中,王佐良先生是一位重要的莎学家,同时也是文学翻译家、作家和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英国语言与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1957年6月,担任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学术刊物《西方语文》的主编,[1]其时,水天同为副主编,李赋宁、周珏良、宋国枢等人为编委会常委。[2]591959年《西方语文》更名为《外语教学与研究》。1980年7月《外国文学》创刊,王佐良担任刊物主编多年,在他主编《外国文学》期间,发表了有影响的重要莎学论文,并推动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发展,其中尤以1981年第7期的“莎士比亚专号”引起了外国语言文学界的关注。作为刊物的主编,他以开放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强调:“我们对于文学的看法,是取其广义”[3],“广义”的认知体现并定下了《外国文学》这一刊物的基调,显然不仅包括了所谓的纯文学,也是文章之学,甚至包含了文史哲等诸多门类。佐良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对英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情有独钟。他曾经说过:“对我特别有吸引力的是那些在内容上有重大意义而艺术上又多有创新的作家。莎士比亚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伟大作家。”[4]1我们从他坚持不懈的莎学研究来看,在莎学研究中,他潜心著述,抒华于春,观实于秋,自纪念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的1964年起就在《文学评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莎士比亚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莎学文章。在他大量的英国文学论著中,他的《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莎学》一书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也是全面体现他的莎学研究思想的一部重要论著,亦已成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基本文献。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王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范围主要涉及莎士比亚戏剧研究、莎作批评、莎作语言修辞研究,特别是在白体诗研究上,发人所未发之论,对莎剧语言特点结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总结与评点。可以说,他在莎学研究中读书穷理,缀集异文,荟萃旧说,考方国之语,在广搜诸家学说中,采谣俗之志,错综群言,积之而为厚焉,可算是极尽了发微烛隐、阐幽探玄之能事,他的阐发能够把莎学研究不断推向新的境界。在莎学研究中,王佐良着重于原作的仔细阅读,让作品自身说话,而论述则多有新的发现,并且能结合作品内容和艺术手法进行深入分析,强调研究莎士比亚既不能撇开形式来谈内容,也不能撇开艺术性来谈思想性。[4]2显然,敢于明确而直接表明这一研究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所形成的政治化语境中是极为可贵的,也是要冒政治风险的。我们看到,由于王佐良在莎学研究上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和在中国莎学界所享有的崇高学术地位,他在1984年12月举行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推举为中莎会副会长,[5]并为推动规模盛大的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的顺利举行和宣传中国莎学做出了贡献。毫无疑问,王佐良先生的莎研活动、莎学论著、莎学研究思想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莎学研究,成为中国莎学学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总结、学习和研究王先生的莎学思想,根本目的是要理清前辈学者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以便为21世纪的中国莎学发展提供某种借鉴,通过不断深化莎学研究,建设中国莎学研究学术平台,取得不同于域外莎学研究的新成果,沿着前辈学者拓展的有中国特色的莎学道路,不断做出新贡献,拓展中国莎学研究的新境界,最终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新世纪的莎学强国,在世界莎学研究领域获得中国莎学研究的话语权。
二、“博雅之士”与莎学研究
晚清海通以来,夷语东渐,象寄之才,随地多有,域外文学传入古老的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洞开,西方的文学、思想与文化如潮水般涌入,改变了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开创了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新生之大学,“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佐良先生乃堪称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培养的“博雅之士”。清华大学老校歌以中西文化的传承,作为自己报效国家使命意识的建立,云曰:“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6]而诞生于伟大的抗日战争烽火中的西南联大的校歌,则融坚定的意志于诗人飞扬的情感于未殄之文风中,云曰:“绝徼移栽桢干志……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7]为此,中西文化相交融的诗人气质始终萦绕于佐良先生的文论中。青年佐良劬学烝业,弦诵如恒,“认真地、几乎是放肆地品评作家作品”,读诗、背诗也写诗。他惊奇于燕卜荪的记忆力、诗人气质和职业精神。燕卜荪“拿了一些复写纸,坐在他那小小的手提打字机旁,硬是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一剧凭记忆,全文打了出来”。[8]清华“从不缺乏诗歌的素材与审美抒情的主体”[9],燕卜荪在南岳“诗随讲而长成整体/用诗来表达,不管写得多么悲壮/想起了家园,我所属的地方”*威廉·燕卜荪:《南岳之秋(同北平来的流亡大学在一起)》,王佐良编:《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年版,第686—697页。见参考文献[10]。[10]686—697。燕卜荪“不断地追求心智上的新事物,又有一般学者所无的特殊的敏感和想象力”*王佐良:《威廉·燕卜荪》,王佐良编:《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75页。见参考文献[10]。[10]675。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王佐良和穆旦都受到现代主义诗人深秀馨逸、清超醇美、灵隽幽婉诗风的深刻影响,“喜欢艾略特,但是我们更喜欢奥登。原因是他的诗更好懂,他的大学才气、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和当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赏”[11]。王佐良先生曾回忆:“三十年代后期,在昆明西南联大,一群文学青年醉心于西方现代主义……觉得非写艾略特和奥顿那路的诗不可,只有他们才有现代敏感和与之相应的现代手法”[12],感受到奥登关注诗歌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并以“摆脱抑扬格和扬抑格的传统模式,但同时又不丧失模式感”[13]的现代手法写诗是出于一种纯爱,他的每一首诗即使再短也有机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对于现代诗歌而言,“诗歌的生命正在于这种固定性与流动性之间的反差,这种未经察觉的对单调的规避”[14]使现代诗歌显得更为自由和灵活。奥登在十四行诗中“表现了一个英国青年诗人对中国普通士兵的真挚感情”*王佐良:《温斯坦·休·奥登》,王佐良编:《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01页。见参考文献[10]。[10]701尤契佐良之心,“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温斯坦·休·奥登:《十四行诗》(“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王佐良编:《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07—708页。见参考文献[10]。[10]707-708。正是在奥登、艾略特等人作品取资于精美之事物,以文新而有质,色糅而有本,造成要眇之意境的灵性,吸引佐良倾心于现代主义诗歌,他感受到“新观念、新结构、新词汇使得语言重新灵活起来、敏锐起来,使得这个语言所贯穿的文化也获得了新的生机”[15]。年轻的佐良感受到时代的嬗变,通过燕卜荪的课堂讲授与日常生活中现代主义诗歌的浸染,王佐良多方涉猎西方现代派的批评理论与诗歌创作实践,由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出发,形成了他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和评论的浓厚兴趣,并将这一份诗人的才情挥洒在对莎氏诗剧的研读中。“王佐良的现代诗写作具有一种不同于他人的抒情风姿,他以‘诗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的交融展现了别一种抒情形态。”[16]“雨过林霏清石气;秋将山翠入诗心”,佐良在青年时代就才华横溢,言谈清雅,在研读中倾向于根据原作的内容与意蕴将外国诗歌翻译为“近似于散文诗的自由诗”。[17]这种对于“博雅”的追求,使他在莎学研究中也显示出一种诗的品格和诗人的敏感。王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毫无疑问体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学派的特点,而他也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培养目标“博雅之士”的成功代表之一,佐良先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学术精神是“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18]生动而鲜明的例子,他也是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以王文显、燕卜荪、温德、吴宓、白英、陈嘉、柳无忌、赵诏熊、钱锺书为代表的著名教授们最早、长期、多角度开设“莎士比亚研究”“文艺复兴”“西洋戏剧概论”“欧洲文学史”“文艺批评”等课程的直接受益者。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939年佐良先生在西南联大担任助教。[19]369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文学课程“分为文学史和文学体裁两类,按纵横两方面同时讲授,……从编剧的角度来讲解莎士比亚的作品,为学生提供了一些戏剧知识”[20]164。而到了西南联大时期,外国语言文学系的“文学史课程减少,文学家研究的课程则大为加强”[20]331,继续开出了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一系列文学名家、名作的课程,可见无论是在清华还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多角度讲授“莎士比亚研究”课程都是清华外文系始终贯彻的方针之一。清华外文系要求自己的学子在治学和研究上必须坚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中西文化会通式的研究,恪守了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孕育自己的新的文化。这种培养方式造就了王佐良先生在文化观上具有的开放胸襟与心态。“‘博’要求‘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达到文字、文学、文化的会通。‘雅’指在‘会通东西、互为传布’的开放环境中创造出一种‘雅’的文化和精神。”*吕敏宏、刘世生:《会通中西之学 培育博雅之士——吴宓的人文主义外语教育思想研究》,载《百年清华百年外文(1926—2011)》编委会编:《百年清华百年外文: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暨外国语言文学系建系85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19]72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的碑文中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佐良在清华读书期间从贺麟先生学习西洋哲学史,曾写下长达百页的英文读书报告,而受到贺麟先生的表扬。在佐良“心里始终保持着一种清华做学问的标准……做学问必须要有最高标准,而取得学问确实为了报效国家。简单说,就是卓越与为公”[21]。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开设“莎士比亚”课程的目的主要是“为学生讲解莎士比亚之文学价值;使学生自知如何欣赏莎士比亚文学,莎士比亚之生平及其著作之精妙所在,统于两学期内教授之。读莎氏重要著作10余篇”[22]。笔者以为,王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对经典的敬畏、尊重和钻研是对当年学习莎氏作品的最佳回应,也是对“清华学派”重视莎士比亚研究一贯教学方针的传承、丰富与发展。
三、体现学术价值和研究水平的两难处境
1949年9月,王佐良从英国牛津大学回国,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政治半年之后,应聘来北京外国语学校任教,[2]44期冀在学术研究上有一番作为。1957年7月,在王佐良任首任主编《西方语文》的《创刊词》中就明确了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西方文学的研究除了适用教学上的需要以外,又可以帮助解决一些有关文学理论和文学翻译的问题,还有吸取外国人民的优秀文学传统来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活的重大作用”[23]。理想是那样美好,然而现实却异常严峻,随着整风、双反、反右运动的深入,编辑方针已经从“不适当偏重文学”不得不改为“着重结合实际”,因为“西语教学中的两条路线和两种方法的斗争也还是长期的,要反复进行的”[24];编者体现学术性的办刊宗旨和刊登具有厚重学术水准的论文的办刊思想受到了激烈批判,被指责为“《西方语文》刊登的文章缺乏思想性……只要看一看每期的目录,就会发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期刊没有什么两样,因而谈不上反映新中国西语科学研究的新面貌……从过去几期《西方语文》所刊载的某些文章看来,西语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学院式的研究倾向……一味追求所谓‘学术水平’……为了‘学术水平’,就往牛角尖里钻,往故纸堆里钻,其实,所有这些,也并不奇怪,资产阶级学者的治学方法说穿了,本来就是如此”[25],人们要求《西方语文》的“科学研究一定要政治挂帅”[26]。当我们打开这些尘封的刊物时就会看到,1958年第4期的《西方语文》,这本学术刊物编排风格变化剧烈,涉及政治与外语,外语教学实践的文章占据了所有的版面,并在目录中以黑体字强调“拔白旗,插红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外语教学和学术研究湮没在一片大跃进的声浪中,作为主编的王佐良虽然困心衡虑,裕以学问,以忧患动心忍性,而不以忧患丧气堕志,但也不得不身体力行撰写了《有关口语教学的几个问题》的长篇论文,强调口语课的改进“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拔去白旗,树立红旗”[27]。在英语教学上尤其要突出“厚今薄古”,突出政治,因为“我们的英语教学的巨大成绩,首先在于它是在越来越深入地贯彻政治思想性”。[28]有关“西方语文”的科学研究,处于巨大的政治旋涡之中,王佐良不得不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莎士比亚研究做出诘问式的猛烈批判,“问题就不止是一般的厚古薄今,而是自欺欺人地搬运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陈腐的货色”。西方莎学研究的“新目录学”“严重地、无可救药地脱离实际,而这正是英美的统治阶层的意图”。他甚至不得不在这篇文章中批判自己的《读蒲伯》[29]是“多少表现了对于西方版本与考据之学的肯定……双反以前,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命不凡,在西语科研领域里也多方表现自己,但是他们真的有什么‘学问’呢。……中国的西方语文工作者而跟在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后面有意无意地捧它,那就只能说是靠洋人的来头吓唬年轻人,借以表示自己拥有‘资料’,不但提高自己的‘身价’,还可引导他们也走上搞所谓‘非政治性’的‘纯粹’的学问的路子。但是双反运动告诉了我们: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通的;它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道路,与社会主义的利益根本相反……”*多年以后,王佐良在谈到蒲伯诗歌时认为:蒲伯的诗歌“不仅形式同内容是一致的,而且新古典主义的诗艺同启蒙时期的思想结合起来了”,载王佐良《英诗的境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页。[30]在反右斗争的政治化语境中,研究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经典作家和作品在《西方语文》中受到猛烈而集中的批判,批判者强调“学术性”显然是与“把社会主义的红旗插在西语教学和研究的阵地上”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学习、研究莎士比亚遭到质问与批判:批判者认为:“教给学生的英诗,几乎全是颓废,伤感,歌颂女人及资产阶级爱情的。每讲到爱情诗,就眉飞色舞,赞赏不绝。这一类的诗毫无批判地教给学生,就在学生的思想上起了很坏的影响。……甚至在反右斗争中还有人念这些诗以‘自慰’的。……他们对我们的新文艺是那么冷漠无情。他们很少看或者根本不看新作品,就是《保卫延安》恐怕也有不少人没有看过。想想看,这是多么令人不能忍受的‘厚古薄今’……谈到文艺复兴时代,则认为是人类文化的顶点,读一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就胜过生活二十年(这句话和马克思讲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对照一下,会令人发生怎样的感想呢?)”;有些人在课堂上教学“……宣传资产阶级男女关系”;“他们对根据古典作品拍成的片子,如《罗蜜奥与幽丽叶》可以看了又看,百看不厌,但是对我们自己的优秀影片《董存瑞》和《平原游击队》则就是不看。这又是一种什么感情?如果真是从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怎么能不和自己的学生在一起看社会主义的电影?”从政治方向的角度,批判者进一步发挥:“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两本书可读,一是红楼梦,一是莎氏比亚’……这种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难道是个别的吗?……《西方语文》面临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问题。”[31]在猛烈和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化的批判浪潮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纯洁、不朽爱情被视为肮脏、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具有腐蚀劳动人民和青年学生的危险,研究他们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的男女关系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32]。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天佑中华,历史与生命中沉重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年代的到来,晚年的王佐良在回忆《西方语文》创刊宗旨时以“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意,仍然强调“着重学术性、综合性”[33]乃是这本刊物的生命之所在。而且《西方语文》创办之初所规定的约稿原则,“对外国文学作品、作家、思潮的分析与评论”在历经六十年后仍然成为以语言学、翻译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外语教学与研究》难以忘却的办刊指导思想。
在我国外语教育史特别是英语教育史研究中,对于1949年至1976年外语与英语教育、教学与研究中受到政治运动左右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影响的情况往往语焉不详,例如,在付克先生所著的《中国外语教育史》中,仅笼统地提到外语教育在“‘左’的影响下也有些破得不对或过了头的。例如:在外语教育界批判了外语教学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强调教学要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34]。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们研究这一阶段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在外语教育领域的政治思想斗争,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外语教学与研究受到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所以,研究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辩证和客观的观点,站在历史的高度,面向未来,以翔实的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讲真话,总结研究这一阶段外语教育、学术研究状况,以便将外语与英语教育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1957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创办了《西方语文》。1959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外语教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季刊》的基础上创办了现在《外国语》前身的《外语教学与翻译》,该刊创刊虽然强调“外语教学、翻译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好地为大跃进服务”,但从该刊的第3期开始,就连载了曹未风先生的《翻译莎士比亚札记》。[35]在莎学研究中形成了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外国语学院创办的《西方语文》与上海外国语学院创办的《外语教学与翻译》形成了外语界一北一南两大外语研究学术刊物相互呼应的态势,两本学术期刊的创办为提高中国的外语研究与科研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莎学研究中的创新
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在19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那时华夏大地正在发生有史以来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远的中西文化的大交融和剧烈碰撞。学生时代的佐良正是在这种中西文化、文学的碰撞、交融中感受到莎士比亚的无穷魅力的。梳理他的莎学研究,我们认为,王佐良先生在他三十多年的莎学研究中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他对莎士比亚的总体研究。在莎学研究中,他的研究虽然“也涉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但是,他感兴趣的并不是王朝的更换,政治风云的变化,他着意探讨的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和戏剧——的发展史”[36]89-91。他认为,莎士比亚与同时代剧作家一道,将诗与剧、创新与传统、天下与世俗艺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悲剧与喜剧、文雅与通俗有机结合起来,才创造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剧的辉煌。第二,对莎士比亚白体诗的精深研究。他深入分析了莎剧白体诗上格“庄严体”、下格“市井小人语”和中格所涵盖的广大社会层面中人物的语言特点,这种区分使众多莎剧中的人物形象绝不雷同,性格鲜明,有助于人们从语言特点、语言习惯看清莎士比亚对于“人生、社会、世界、自然的观察、反应、态度”[37]119,他以殚精覃思中窥其寂隙,涵咏功深觇其文心的会通式阐发,厘清了莎剧中各色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作为经典的莎作在人类文学史上的不朽价值,使读者既能从宏观上看到莎士比亚白体诗形成的时代原因,又能从微观上深入感受到莎士比亚白体诗的特点和变化。可以说,佐良先生的品评鉴赏衔华而佩实,以情思之所寄、理趣之所蕴、美善之所存、感人之所自,深契莎氏创作诗剧之心。[38]第三,佐良先生以他的所有莎学论述,表明了一个中国学者的莎士比亚研究观。中国莎学的基础主要是由一批1949年前留学英美的学者打下的。[37]174但是,由于政治环境使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莎学研究受到了苏联开创的马克思主义莎学的深刻影响,[39]吸收、借鉴英美莎学研究成果较少。这一阶段众多的中国莎学研究论著多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只进行社会学意义的分析研究。[40]而王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则没有或很少受到这一苏联莎学大形势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不能不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莎学的一大奇迹,也是他的莎学思想的鲜明体现。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那一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没有在他的莎学论著中留下任何痕迹,但他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有自己的研究思路却是事实。王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善于从英国戏剧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独步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无愧色的莎士比亚戏剧,既阐释其丰富的内容、恢宏的气势,让人徜徉其间而不疲,又探讨其通俗与典雅的语言所带给人们的不尽的欢笑与对世间人情的冷峻思考。第四,王佐良先生认为莎学研究要“从戏剧文学的传统出发来探讨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感染力,把莎士比亚放在孕育他成长的英国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这一较大的范畴来研究莎士比亚对英国戏剧的贡献”[36]89-91。作为英国文学研究者,佐良不囿于学科的偏见,对中国舞台上演出的莎剧进行了充分肯定,热情宣传莎士比亚演出、研究、翻译在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上述四个方面,既是他的莎学研究思想的充分体现,又是他对中国莎学研究作出的最重要贡献。
1.莎剧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诗剧精神
王佐良对莎士比亚的总体观点,是把莎剧的产生放在整个英国诗剧产生的背景中进行研究的,以英国诗剧取得的辉煌成就对莎氏进行定位,他认为是莎士比亚、马洛、马斯登、查普曼、顿纳、韦伯斯特、鲍茫、弗莱契、基特、琼生,这样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协力建立起来了一种辉煌的新戏剧。它敏锐地、生动地、强烈地表达了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在技巧上自创一套,打破过去的惯例,即使着意拟古也是‘以我为主’;将浪漫情思和现实描述揉在一起”[4]3。但是与同时代剧作家相比,莎氏诗剧的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都远比他们深刻和宽广,“素体无韵诗在他的手里不止是更灵便,而是更善于捕捉喜剧性和发扬音乐性……民间色彩更浓,……形象更集中,旋律更丰富。不再为浮面的美而采用锦词和甜蜜的音乐了,一切服从主题。……这样的诗剧集中,强烈,饱含人生沧桑之感,显然不是当时英国还处于一定混乱状态的散文所能代替的”[4]26-29。由此,王佐良先生在莎学研究中援引所及,必明据依,形成了他对于莎士比亚前后这一时期英国历史的总体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处于“伊丽莎白朝盛世的普通英国民众的看法,即厌乱思治,拥护一个能平定诸侯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昔日之乱为镜子对照今天之治而庆幸自豪”[41]。所以,在莎剧中洋溢着思想活跃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变革与浪漫主义精神。同时,莎剧也比其他文学形式更接近民间,更接地气,更能反映社会现实状况,佐良提倡“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学者必先识乎此,才能领会莎剧在内容上不断更新,以及借助形式给观众带来的全新感受。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正确认识和反映,它有着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诚如佐良的老师吴宓所言,莎士比亚所著剧本“纵贯天人,穷极物态,至理名言,层层叠见,阴阳消长之理,推考尤真……胸罗宇宙,包涵万象之力……凡古今男女贤愚贵贱所有之行事及心理,靡不吐露叙述于其间”[42]27。佐良先生强调,艺术的真实构成了莎士比亚戏剧的生命之源,对现实生命意识的认识构成了莎士比亚深刻的历史观。佐良先生论莎善于从语言与文化、社会、文学的关系入手,但他并不停留在对于时代环境的分析上,而是点到为止,将重点放在莎士比亚诗剧的特点上,长于从当时文化、文学风习、观念的演变研究莎剧和莎剧中的人物。因为他始终注意到诗剧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莎士比亚戏剧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43]495莎士比亚“随着英国诗剧一起成长,壮大”[4]39,但又有自己的鲜明的创作特色。佐良先生认为莎氏是英国文学发展起点的代表,莎剧的奇险峻极之势,清蔚自然之秀为英国的文艺复兴开创了一个真正伟大的文学时代。这种气魄就是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的气魄,而莎剧在人物塑造上的穷形尽相,逼真如绘,正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成熟诗剧的体现。文之所以化人者,乃感于人为至娱,至娱之感,至美矣,莎士比亚创作戏剧和文人剧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写戏遵循的是群众性、娱乐性的路子,追求票房和盈利,故写戏也以事务之暇,心机灵变,世法通疏,搜奇索怪为要务,首要的目标是满足大众娱乐的剧团生存需要。犹如今天的电影和电视一样。[37]174同时,莎士比亚又是“深知人性与人的哲学的伟大诗人”[44]。佐良先生发现,莎氏不屑于沿着号称“血与雷”剧派的路子以浓墨重彩渲染谋杀罪行,而是另辟蹊径,将具有现代意识的缜密的心理描写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细致入微地描写剧中人物犯罪前后的心理活动,真实、传神,纤毫毕现地勾画出剧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曲线。总体来说,王佐良莎学研究抓住了莎氏诗剧的关键,推勘精密,启牖尤珅,而其所具有的理论资源和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已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45],所以在莎学研究中能够体现出中国学术的特色与理路。而且王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不盲目苟同西方莎学,而是通过自己别出机杼的独立思考,钩玄探幽,独抒心裁,广集书证,对西方莎评的讹误、偏颇之处,探赜索隐,博考参酌,弥补缺漏,提出新见。他认为,伊丽莎白朝后期,王道虽微,然文风为殄,《哈姆雷特》一剧超越复仇与淫乱而成为全面体现文艺复兴时期精神的深层次悲剧,这正说明了莎士比亚超越同时代剧作家的伟大之处。佐良通过白体诗这种韵文形式认识到,莎士比亚把当时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集中到了哈姆雷特身上。这种知识分子身份的厘定,“善与恶之间、潜在力量与实际力量之间的冲突,才是真正的冲突”[43]495。莎士比亚已经意识到哈姆雷特扭转乾坤的艰巨性,表现在哈姆雷特身上的对语言异常敏感性正是历来知识分子在两难选择中的一个特征,正是复杂多变、文采炤映的语言烘托了哈姆雷特的知识分子气度。王佐良先生指出,最擅长运用语言的《哈姆雷特》,既把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又把语言的游戏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全面、深刻地反映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又超乎文人剧之上,莎士比亚对诗剧的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从而以饱满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鲜明的性格特征达到了“在白体诗和戏剧语言的运用上更有想象力和创造精神”[46]的哲学与美学高度。
2.中国学者的莎学观与超越政治语境的解读
20世纪60年代,佐良先生发表的两篇莎学论文与当时的其他论文不同,没有过多地纠缠于莎士比亚戏剧所产生的时代特征和其作品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他在研究中强调,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中始终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和基本思想:歌颂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拥护强有力的开明君主,谴责封建集团之间的斗争,揭露阴险恶毒的政治人物的危害。作为著名莎学家,王佐良先生不但看到了莎士比亚戏剧的积极方面,而且也拈出了莎氏思想的局限性。无论是在外国文学研究,还是在莎学研究上,王佐良都认为:“面对中国读者,要把重要的史实和作品向他们交代清楚,还要搞清西方人对作品的立场,立足于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文学传统来评论作品,要有学贯中西的气魄,不能仅仅满足于以‘人民性’、‘现实主义’来贯穿一切,而要深入到文化内层。”[47]显然,佐良先生的这番话是对长期以来包括莎学研究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偏颇作出的批评。故此,佐良能够在莎学研究中注意到莎作的美学品格,并能联系文本引而申之,获得共理相贯,异论相析,知化穷冥,删芜撷秀,掇取要旨,以究万原的认知。他范示绳墨,指出莎士比亚是从资产阶级的眼光看问题,他虽然认识到当时社会黑暗和人文主义的危机,却因害怕人民群众而宁可抬出封建阶级所曾经鼓吹的等级论,这是莎士比亚晚年所遭遇的思想危机的征象。虽然莎士比亚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有所认识的,但他关心的仍是维护等级制。而随着1607年中部诸郡农民起义的爆发,他对人民的态度又从畏惧变成敌对。他原来是反对封建的健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失去了正视现实的勇气。面对王朝的危机、秩序的失落,佐良指出,在莎士比亚戏剧里隐含了一种美好的东西失去之后无法复得的哀伤和追忆,极盛之后的寂寞与悲哀,对盛衰无法预料的幻灭,沉重而无奈的沧桑之叹。于是,莎士比亚索性含含糊糊地谈人与人之间的宽恕和谅解,但是他却只宽恕篡位的公爵之类,却决不宽恕起义的“人民”、“愚民”和“土著”。王佐良先生明确指出,莎士比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局限也就在这些方面显露出来。对于西方莎学理论、观点,佐良先生悟其非,援据征文,有疑则阙,不妄臆断,辨证讹误,正本清源,批驳了某些西方莎学家的观点。王佐良认为:“中国人写外国文学史,总得有点中国特色。”[48]对于莎士比亚研究,他也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洞达真契,推勘物情,于析事剖理之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西方莎学研究中也不乏政治性的解读,如有些英国莎学家认为,《暴风雨》中少女米兰达高呼“人类是多么美丽!呵,灿烂的新世界!”是一种对于“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的憧憬”。王佐良先生则认为这不过是牵强附会的臆测,米兰达的呼喊没有多少深意,只是表达了一种欢欣。中国莎学研究应避免这类牵强附会随意性很强的解读。
作为一个中国莎学研究者必然要在研究中以比较和契合的眼光来看莎作,佐良认为:“中外主流文学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毕竟两者都遭遇了现代生活的压力,且都满怀对更美好世界的向往”[49]9,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翻译、演出、研究莎士比亚的动力。王佐良先生在莎学界影响最大的是他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莎作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莎剧的“语言本身已经成为剧情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50]223,语言给观众带来愉悦,莎剧的内容、艺术形式和语言带给观众的是美学上的享受,所以,佐良先生的一系列莎论都从文体学的角度紧扣语言分析。他从莎剧中的白体诗入手,将语言与环境、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情节、语言与艺术表现手法结合起来,分析其韵律,观察其发展,探索诗剧的兴衰与莎氏本人世界观之间的关系。[51]“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在那种限制下他还能不断发掘这种新诗剧的潜力,使之终于成为世界伟大的剧种之一。”[50]239他强调,16、17世纪是英国诗剧作家辈出的时代,只有把莎士比亚放在整个英国诗剧的背景之中,我们才能看清他与其他剧作家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莎氏独特的贡献和弱点在什么地方?王佐良先生通过多方面的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有了莎士比亚才使英国诗剧放射出更加辉煌夺目的光彩。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他们合力驯服了诗剧中的白体诗这种韵文,而且在驯服的过程中又发掘出它的潜力,使它成为一种高效率的戏剧语言,起了当时散文所不能起的作用。在创新中点石成金,才使“莎士比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而除了时代对这种文体有迫切需要这个客观因素之外,其主观原因就在于莎氏本人确实是掌握了最大量的词汇,他在同时代的诗剧创作者中间是表达得最为确切和优美动人、最富有诗意,也最善于发挥其舞台效果的一位超群绝伦的语言大师”[52],所以,在今天的经典阅读和戏剧舞台上,莎剧仍然是常备的阅读文本和常演不衰的剧目。
3.白体诗中的多调复音
有学者在研究王佐良翻译风格中注意到王佐良对莎学研究的贡献。[53]但佐良先生对莎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将白体诗放在英国诗剧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分析,同时指出莎氏在娴熟运用白体诗这种文体时能够根据语境、性格、心理、心态、情绪而因人而异塑造性格,达到“处心于境,视境于心”[54]的“相兼”“相惬”。“莎士比亚最为写得实在具体,但他也总要从具体情节里面点出普遍性的意义。”[55]王佐良的这一看法可以说是抓住了莎作的关键,为提升人们对莎作的认识提供了一把钥匙。他认为,白体诗这种文体作为一种戏剧工具虽然在莎士比亚时代已经是一种历史的陈迹了,但在它完成其使命之前,是莎士比亚用他那天才而完美的语言,犹如艺林璨珠,使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莎士比亚“总是在戏剧的一个紧张点上,让主要人物作长篇独白,剖析其内心,宣告其图谋,表达其哀乐,预示其行动,通过某一特定处境的特定人物的眼睛来观察整个世界和宇宙,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剧情不完全符合的某些言词,在实际上却是使剧情更为丰富,内容更有意义了”[4]47。王佐良先生分析莎士比亚白体诗的作用往往条分缕析,入骨见髓,他注意到,语言的发展、衰落乃至变革,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莎士比亚对于语言的运用要比同时代作家成熟得多。佐良先生在对前人未言者中补其遗缺,言而不详者中补其疏略中提出,虽然白体诗这种语言形式在莎士比亚之后就逐渐暗淡了,但是,它在莎士比亚手中所燃放出的耀眼光芒,对语言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莎氏诗剧有重要的文化与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以能文为本”,“事出于沈思,义归乎藻翰”的特殊气质,诗剧的语言中别有一番深意,要从语言中体悟到“冷眼看藏刀变脸才知人间戏还多”的戏剧性和作者对人生的认知,对人性的描绘,才会使今天的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思想深度与审美魅力。与同时代剧作家相比,在白体诗和戏剧语言的运用上,莎士比亚的语言往往存神过化,“更有想象力和创造精神”,他利用白体诗“表现了人生各种处境各种感情,塑造了几百个人物,探索了人生和社会的根本问题”。[37]10莎士比亚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他无论写什么总是才思如泉涌一般敏捷,妙语连珠。他毫不吝惜语言,把语言的张力发挥到极致,在白体诗运用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所以我们在注意莎剧朴实、自然的前提下,也需要更具匠心地体会莎剧语言的艺术韵味和别具审美情趣的台词。佐良以为在戏剧创作的初期,莎氏也有浓得化不开的时候,喜欢各种锦词警句,也同别人一样醉心于修辞术。但是,莎士比亚的语言才能是随着不断创作出的戏剧向前发展的,而且比当时其他剧作家都运用得更为纯熟。“语言风格的发展在莎士比亚是同他戏剧艺术的成熟和对世界的认识的深化一起进行的”[37]61,由此,莎氏也成就了这种文体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因为“莎士比亚谓疯人、情人,诗人,乃一而三,三而一者也,皆富想象力”[42]24,佐良先生恳挚地指出,莎氏接过了马洛的激情和历史想象力而驰神逞想,但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思想与语言表达形式,甚至不避尤多淫丽的时俗辞藻,实为文艺复兴之独绝,白体诗中蕴含了更多的民间生活体验,更宽广的诗路,更多变的韵律,更接近口语的民间词汇,更有意义的戏剧讽刺,更挑逗人们思想的形象,还有——用我们的话说——更多的辩证法和现实主义。莎士比亚“贪婪地嗜好富于表达力的文字”[56],与马洛等人相比,莎士比亚笔下的韵文在节奏上拓体卓荦,随意变化,人物描写、环境气氛渲染往往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达到了文义允惬、词理圆备的程度,调子上的口语特点相当明显,符合舞台演出的特点和规律。他利用白体诗语言的上中下“三格”描绘人物及其心理变化,可谓匪独体格之高,亦则性情之厚,人物语言不仅表现为意以曲而善托,而且也以调以杳而弥深,从而达到了情胜、气胜,乃至格胜,而入于化境之戏剧境界。王佐良先生注意到莎士比亚常常把上格限定于某些特殊场合,如戏中戏、仪式典礼性的场面;莎氏也总是使下格的语言更加口语化;莎剧中下格的俗语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而且应用得异常巧妙,与五光十色的生活联系紧密,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掌握这种语言的特点有相当难度,因为学它“教它得同时教生活”[57];莎氏不仅扩大了中格的范围,而且加强了它的表达能力,使它担任了戏剧语言过去从未担任的任务。所以,莎剧所呈现给读者和观众的是“多调复音的艺术……不同层次,不同世界各有相应的不同的戏剧语言”[58]86-90,根据人物的身份、性格、语境、脾气、心态和喜怒哀乐,多种文体并存,有时是华丽文体的白体诗,有时“富于想象力的散文达到了俗套诗体所达不到的抒情境界”[58]86-90,同时,莎氏也更多地发挥了散文在剧本中的作用,包括散文诗的作用,他比任何别的作家都更意识到传达工具即戏剧语言本身能构成剧本内容的一个特殊方面。因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生活的镜子;谁要是被其他作家们捏造出来的荒唐故事弄得头昏眼花,读一下莎士比亚用凡人的语言所表达的凡人的思想感情就会医治好他的颠三倒四的狂想”[59]就会领略到其戏剧语言的奥秘。佐良发现,到了后期,莎士比亚的白体诗通过“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更多地趋向于下格、口语化、俗语化”,语言的含义更为丰赡、细腻,以“内典语中无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出于内、显于外之涵盖,使“落难中的帝王不作帝王语,更切合剧情了”。白体诗在格律上“跨行更频繁”,追求更大的流动性、伸缩性;它更有意识地“起到更大的戏剧作用”。在《哈姆雷特》里,白体诗甚至发挥了政治作用。“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这一段台词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强烈、细致、弹性大、爆发力强,是对政治和生活进行思辨的语言。佐良先生以擘肌分理的研究指出:“白体诗在莎士比亚手里是得到了很大发展的,从仅仅能吟咏、抒情进到了充分发挥戏剧作用,在格律上增加了伸缩性,在表达上适应了新的敏感。”[60]89-90莎士比亚白体诗的核心,以各体互兴、分镳并驱的“多调复音”是他对于自然、人生、社会的观察、反映和态度。在初期,莎氏充满了自信和乐观精神,他的诗也整齐、流利、优美;到了后期,他沉思、焦虑,拿一些问题苦恼自己,在难以排遣的时候下笔,天机物趣,毕集毫端,把白体诗拆开,揉弄它,摆布它,压榨出它的最后一点表达力,这些都是为了写出那些曲折、复杂、隐秘的思想、心理、感情和性格。作为一个熟谙舞台艺术的剧作家,莎剧的戏剧语言尽管有时在格律上颠覆了他所依傍的白体诗,但是这却是为了“剧情需要”[60]89,总之,莎士比亚发展、丰富了白体诗的这种表现形式,但也为白体诗抹上了最后一道异常耀眼的光彩。
五、讲好莎士比亚的中国故事:既需要深入的文本研究,也需要精彩的舞台演出
1978年,被“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十五年之久的《莎士比亚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套外国作家全集。2013年至2015年,有四套《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它们是朱生豪、陈才宇翻译的全集,方平的诗体全集,朱生豪、苏福忠翻译的全集,辜正坤等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英汉双语本)。高校英文系和中文系开设“莎士比亚研究”课程已经常态化。自前任国际莎协主席菲利普·布罗克班克(Philip Brockbank)感慨“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以来,两任国际莎协主席吉尔·莱文森(Gill Levinson)、彼得·霍尔布鲁克(Peter Holbrooke)及大卫·贝文顿(David Bevington)等莎学家相继来华参与莎学研讨,他们惊奇于中国戏曲能以丰富的表现手段诠释莎剧。除高校的英文莎剧演出外,有话剧、京剧、昆曲、川剧、越剧、黄梅戏、粤剧、沪剧、婺剧、豫剧、庐剧、湘剧、丝弦戏、花灯戏、东江戏、潮剧、汉剧、徽剧、二人转、吉剧、客家大戏、歌仔戏、歌剧、芭蕾舞剧等二十四个剧种排演过莎剧。在中西文化、戏剧的交融中,中国戏曲与莎剧的相通与娱人结合,回归了戏剧最古老也最根本的性质。实践与理论研究都证明,莎剧能够经受各种戏剧形式的改编和演绎,中国戏曲也具有完美表现莎剧的审美张力,莎剧在中国舞台上的演出已经给中国莎学带来新的机会。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宏伟战略与伟大实践中,讲好莎士比亚的中国故事,乃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实现莎士比亚及其莎学理论与西方及其国际主流莎学学者的交流与对话,以及从单向莎剧阐释、莎学理论的中国旅行过渡到中西方双向莎剧阐释、莎学理论与演出、改编的跨文化对话。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也许就是借助于中国戏剧、中国戏曲丰富的理论成果与特有的演出实践,实现对莎剧内蕴的无穷改编和探索,并通过莎剧改编演出实现主要以“写实”为主的西方戏剧与主要以“写意”为主的中国戏剧的东西方文化特点的探讨,以及早已有成功范例的中国戏曲理论与演出实践的西方旅行。莎学研究必须要文本与舞台结合才能相得益彰,王佐良先生的意见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和极为重要的。
青年时代的佐良钟情于戏剧,早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时代就演过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小人物》。[61]王佐良先生认为:“莎士比亚不应该只是读的,欣赏莎士比亚的最好地方是在戏院里……阅读剧本显然不能代替观看演出。”[4]40莎士比亚会“让感情在舞台上燃成烈火”[37]198,所以莎学研究应该同演出结合起来,自19世纪末叶以来,莎剧演出已经成为导演主导的天下,“阐释的自由代替了对莎翁原意的追索”[62],天才的导演和演员受到时代思潮和社会风习的极大影响,佐良认为文本研究与舞台演出应该相辅相成,文本与舞台的辩证关系犹如梨柚异味,而同悦于口;施嫱殊色,而同美于魂,“用研究的成果来帮助导演和演员更深刻了解原作,而通过演出,研究者又必然会体会到书斋默读所不易发现的某些方面”[63]2。因为莎士比亚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他“最懂戏,他的剧本总是情节生动,比别人的更能利用当时舞台的特点,发挥当时演员的潜力,他善于创造人物:他的人物总是比别的剧作家笔下的人物更全面、更深刻。[4]22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应该说佐良先生对于舞台导演、表演来说是相对陌生的。但是,对于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家、戏剧家来说,研究如果只注重于文本阐释,而忽略了舞台演出的实践,甚至对导演、表演异常隔膜,顽固拒绝从舞台的角度了解、研究莎剧,其研究也是难以触及莎剧思想、艺术和审美真谛的。所以,王佐良先生一贯强调,莎剧是诗,又是戏剧。观看莎剧的多数观众是站在露天,任凭风吹雨打,而被强烈的剧情所吸引,因为“他们觉得舞台上的人物深刻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4]4,因为16、17世纪的英国诗剧根本就不是文人剧,它摆脱了文人剧的特点,一系列的社会条件造成它的独特性,“戏剧诗是英国诗的特长。莎士比亚和他的一大群同辈不仅是戏剧天才,而且是诗歌天才,而他们所写的戏剧诗是雅俗共赏的,即既是高雅艺术,又是群众娱乐媒介,无论是叙述行动、描写环境、抒唱感情、发表议论或只是引人发笑都做得极为出色”[10]3。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事件是诗剧的出现与成熟,莎剧的出现可谓正逢其时,“诗剧是用诗写的,但更是戏剧”,正可谓“舞台小世界无非是生末净旦丑悲欢离合假假真真,世界大舞台只见得公侯伯子富穷达升沉真真假假”,这是对人、社会、人生与人性在看穿之后的深刻反思与探讨。在莎学研究中,我们应该时刻牢记佐良先生的真知灼见。自1926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建系以来至西南联大和解放初期,清华外文系一直坚持“莎士比亚”等文学名著课程,当年的清华外文系被誉为“戏剧家的摇篮”,而这一“摇篮就发轫于清华外文系,而且与外文系首任系主任王文显不无关系。[19]369佐良先生热爱戏剧,热爱莎士比亚当然也与清华外文系的这一学术传统之间有深刻关系。
莎氏是英国诗剧艺术张力的实验者,是语言的魔术师,莎剧的戏剧语言能够推进剧情,刻画性格,能够应付各种场面和各色人物,是能粗能细、能雅能俗的语言。几百年来,对于莎士比亚,人们总是以各自的智慧与阅历从不同的文化层面出发演绎、研究、评论和解说,其中尤为关爱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莎士比亚创作诗剧的目的表明,他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作家”。他写剧不是为了建立文名,而是为自己的戏班能有新剧上演,着眼于舞台效果,希望能够引起观众强烈的兴趣。佐良认为:“开创英国诗剧的作家当中只有老演员、流浪汉、穷书生、泥水匠、皮匠的儿子等等来历不明、身世不清的人。”[4]320世纪60年代,上海青年话剧团曾经两次公演了由祝希娟、焦晃主演的莎剧《无事生非》。当年,王佐良先生曾亲赴上海观看,该剧以准确而富于想象的形体动作、声音造型和台词处理上的功力,把莎剧人物的精神力量传达给观众,给王佐良留下了深刻印象。祝希娟将贝特丽丝活泼而不放荡、尖利而不刻薄、不失少女纯真的角色演得活灵活现,将人物的个性刻画得入木三分。以一柄鹅毛扇衬托人物的风度和情绪变化,突出人物的泼辣、豪放性格特征。[64]佐良先生强调这种形式的演出有助于对莎剧的理解,因为通过舞台表演,能让“最发人深省的契合见于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文学之间,语言与传统都大相径庭的文学之间”[49]3。中国戏剧和莎剧纵使隔着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别,但是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和导演、表演的天才诠释,莎剧的生动情节,有血有肉的人物,俏皮风趣、揶揄嘲讽的对话仍然能够成功地传达给中国观众,甚至“连他的警句妙语也照样在中国观众之间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赞叹和笑声”[4]40。遥想当年,往事并不如烟,三十年前的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上海、北京两地同时举行。在这次盛况空前的莎剧节上出现了大量用中国戏曲、地方戏改编的莎剧演出。用中国戏曲、地方戏改编莎剧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尽管绝大多数莎学家、戏曲表演艺术家、编导对这一形式表示了肯定,但是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改编将使中国人失去对真正的莎士比亚的认识。佐良先生对争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戏曲改编莎剧表示了肯定和支持,他认为尤其应该关注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的演出,从全本莎剧的改编到京剧和众多地方戏的莎剧改编,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这“显然有助于把中国的莎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63]1。莎剧改编也应该遵循隐括有至理,剖析穷根源,在辨章风谣的基础上区分中西文化的不同情况,充分利用中国戏曲精妙的舞台艺术表现力,做到改编要摄取精华,择善而从,韵味无穷的美学效果。王佐良先生认为用中国戏曲改编莎剧是首届中国莎剧节的一大特色,也是展示中国莎剧演出特色值得期待的一件文化创新,故此在昭示中国文化民族艺术的传统中,在中西文学、戏剧的交锋与契合中,“横向范围的拓展也意味着纵向理解的加深”[49]15,也只有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三百多种地方戏, 而且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才能提供这些剧种来做莎剧改编的试验。佐良认为,莎剧的改编,应该根据中国戏剧的丰富表演手段来演绎莎剧,挖掘莎剧这类英国诗剧剧本的长处,以此来“建立我们的莎剧舞台传统,从而丰富与推进世界的莎剧舞台传统”[63]2。佐良先生相信,莎士比亚戏剧与中国戏曲的交融“必使耳中耸听、纸上可观为上”,将使古老艺术、文化在新的诠释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莎剧在中国舞台上的演出“用它那股蓬勃新颖的活劲儿扫开了中国莎剧演出中的课堂气学院气”[37]170,进入了莎剧艺术的新境界。中国的莎剧演出同当代西方的莎剧演出显示出不同的调子,同中国色彩缤纷、乐音回荡的演出相比,西方的当代莎剧演出显得过分低调、灰色,有的囿于旧窠而无多创新。[37]179作为一个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佐良先生寄希望于有更多适宜于上演的译本涌现出来,他认为:“过去的译本也有不少适合舞台演出,但也有过分书本气的。我们的语言,包括舞台语言,有了不少变化,译本也应该更符合当前语言的状况。如何在中国话剧舞台上演出诗剧,其中诗的部分虽然不唱不咏,都要有高于一般对白的节奏、韵律,也需要通过实践去解决。”[63]1
随着中国莎学的不断发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莎学学派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于建立中国莎学学派,佐良先生充满信心,“建立一个莎学的中国传统,应是我们努力的目的之一。在研究方面应该有一个中国传统,即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体现中国观点、中国学风文风的传统,发掘人所不发掘,道人所不道,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莎学成为世界莎学中的一个方面军”[63]2。但是,王佐良先生也在这种呼声中保持了一份清醒。他强调在建立中国自己的莎学学派过程中,首先应该继续搞莎学的基本建设,译出更多的风格各异的莎剧剧本,更多地了解英美以外的莎学研究,在阐释中注意对莎剧人物性格、莎剧意义、艺术特点、语言层次、修辞手法、象征、载体剧种、戏曲程式、演员修养、观众以及戏曲剧文化的比较研究,还应该对戏剧传统、舞台情况、演员训练、心理、社会文化环境进行多角度的研究。近年来,中国莎学进一步发展,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国内外莎剧展演、交流频繁,证明了佐良先生的看法是中肯的,也是极有远见的,[65]今天的中国莎学研究、莎剧演出正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着。
佐良先生认为:“写文以思想胜……总要透过语言去看背后的情调,意境,思想,特别是思想上各种微细的分别”[8]2-5,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在佐良先生的《英国文学史》的学术建构中,他一贯强调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要体现中国学派的鲜明特点。[66]他的这一思想也贯穿于莎学研究中,在文笔清新的叙述与凌厉峻峭的解释方面,他力求以中国人的视野观察英国文学的历史、作家和作品,在个性化的叙述中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流派和文学传统作出阐释,以鲜明的主体意识摆脱了转述和翻译的英国文学史的生硬窠臼,贯彻的是以中国学者的眼光和文化立场来审视英国文学的历史。在《英国文学史》一书中,他提出“要有中国观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以叙述为主,要有可读性”[67]序1-2的治英国文学史原则,点面结合,以扫描式的一般论述与重点研究的“特写镜头”达到相辅相成之研究格局,突出经典作家地位和作品的审美艺术特点,做到叙述与评论既各有侧重又相得益彰,佐良认为:“好的叙述总是包含评论的,要有新的观点——在我们说来就是经过中国古今文学熏陶又经过马克思主义锻炼的中国观点。”[68]中国人研究莎氏就是要在讲好其人其作的基础上,一针见血,画龙点睛、高屋建瓴般地概括出作家、作品主要特色。在研究中,佐良先生往往站在比较文学的角度论述问题,他认为,在20世纪,英国文学还在发展,还富有创造力,表现与戏剧的持续活跃……莎剧的存在给予英国文学以特殊光彩的地位,舞台与影视中的莎剧不断创造着新的辉煌。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王佐良先生除了担任“外国文学编辑委员会”委员、“英语、爱尔兰文学”分支副主编以外,还承担了重要条目“英国文学”、“爱尔兰文学”、“彭斯”、“蒲柏”、“拜伦”、“科贝特·W.”的撰写,用该书总主编姜椿芳的话说,编委可谓集中国“外国文学领域的一时之选”[69]。佐良先生以精髓之思,治深美之籍,结合英国文学的特点,指出英国诗歌的成就体现为无韵体诗在剧本里的成功运用,诗同剧的结合产生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最骄傲的成果:“诗剧。”[70]佐良认为:莎剧“是充分入世的,芜杂的,甚至粗糙的”,但是却“洋溢着这个活动频繁、思想活跃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莎士比亚比马洛和琼森都更懂戏“把哲学思辨带进了喜剧,增加了剧本的厚度。……《奥赛罗》从所表现的爱情来说,是一曲长恨歌”[67]31-53。同时,佐良先生也告诫研究者,中国的莎剧演出也没有必要去追随西方流行的低调,而是应该发出独特的声音,展现自己文化的独特魅力。受到东方戏剧传统哺育的中国导演、演员和观众是成熟和开放的,对于莎士比亚这位西方世界最大的剧作家的到来既不傲慢,也不应拜倒。[71]1989年,佐良先生在给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的来信中称赞举办“‘上海国际莎剧节’极好”[72]。1993年,在他给中莎会的来信中表示,尽管参加上海国际莎剧节因“腿疾越来越厉害”[73]但仍然表示要撰写一篇《〈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种读法》的莎学论文,以对莎剧节的举行表示支持。中国莎学研究的特殊性要求我们,既着眼于历史,又看到未来,从莎士比亚的原作中,从当今中国莎学现实境况与学科体系中,从经典的文化价值中,从莎士比亚的影响和固有的精神内涵中,去把握新的时代要求与研究动力;以文化大国和中华民族应有的文化自信,从历史的瞬间中寻找永恒的精神价值,从历时性中发现共时性,从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中去重新发现莎士比亚作品中所蕴含的真、善、美。[74]28—37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75]中国莎学翻译、演出和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独特审美视角,中国戏剧、戏曲所独有的审美与认识价值正是我们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生动体现,也是一个文化大国应有的文化自信。[74]28—37
结 语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在中国莎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他在莎学研究、英国文学研究中的杰出成果为这一学科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以思积而满乃有异观溢出,其方法创新、理论阐释以及资料运用等辩证方法,显示了详雅有度之阐发,他以笔扫屈曲尽意而言无不达之论多所发明,给人以丰富之启示与借鉴。佐良先生及其一批学人在莎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在于为中国莎学在深层次意义上开创、传承了一种“博雅”之学风与学统,同时在个人精神与学术风格上追求卓越。[76]我们相信,在隆重纪念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刻,怀念他对中国莎学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研究他的莎学思想,对于中国莎学来说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1]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志编审委员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志[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250-251.
[2]北京外国语学院校史编辑委员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简史(1941—1985)[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
[3]王佐良.写在卷首[J].外国文学,1980(1):1.
[4]王佐良.英国文学论文集[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
[5]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沉痛悼念王佐良教授[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2):73.
[6]方惠坚,张思敬.清华大学志:上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16.
[7]西南联大校友会.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
[8]王佐良.怀念燕卜荪先生[J].外国文学,1980(1):2-5.
[9]张玲霞.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53.
[10]王佐良.英国诗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1]王佐良.穆旦:由来和归宿[M]//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32.
[12]王佐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序1.
[13]W.H.Auden.The Complete Works of W.H.Auden:Prose,Volume III:1949-1955[M].ed.by Edward Mendels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649.
[14]T.S.Eliot.To Criticize the Critic[M].New York:Farrar,Strauss & Giroux,1965:185.
[15]王佐良.谈诗人译诗[M]//许钧.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412.
[16]陈彦.“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西南联大时期王佐良的诗歌实践[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1):40-44.
[17]熊辉.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形式的影响研究[M].台北: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207.
[18]齐家莹.清华周刊: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度)[M]//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315.
[19]《百年清华百年外文(1926—2011)》编委会.百年清华百年外文: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暨外国语言文学系建系85周年纪念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0]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1]王佐良.想起了清华种种[M]//庄丽君.世纪清华.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248-250.
[22]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47.
[23]《西方语文》编辑部.创刊词[J].西方语文,1957,1(1):1-2.
[24]《西方语文》编辑部.关于这一期[J].西方语文,1958,2(4):353.
[25]程竞.西语的科学研究必须密切结合教学[J].西方语文,1958,2(3):249.
[26]王鸿斐.科学研究一定要政治挂帅[J].西方语文,1958,2(4):422-423.
[27]王佐良.有关口语教学的几个问题[J].西方语文,1958,2(4):371.
[28]王佐良.外语教学的巨大成就——一个英语教师的体会[J].外语教学与研究,1959,3(5):257-266.
[29]王佐良.读书札记:读蒲伯[J].西方语文,1957,1(1):83-87.
[30]王佐良.这是什么样的学问[J].西方语文,1958,2(3):271-272.
[31]编者.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的红旗插在西语教学和研究的阵地上![J].西方语文,1958,2(3):250-260.
[32]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171-172.
[33]王佐良.《外语教学与研究》百期感言[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6.
[34]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74.
[35]李伟民.被湮没的莎士比亚戏剧译者与研究者——曹未风的译莎论莎[J].外国语,2015(5):100-109.
[36]何其莘.中国莎学者的新探索[J].外国文学,1992(6).
[37]王佐良.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38]李伟民.莎学在春潮中涌动——评《莎士比亚绪论》[J].外国文学,1992(6):92-93.
[39]李伟民.俄苏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J].四川戏剧,1997(6):19-24.
[40]李伟民.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与阿尼克斯特的马克思主义莎学理论述评[J].四川戏剧,1998(5):11-17.
[41]王佐良.读莎士比亚随想录[J].世界文学,1964(5):125-135.
[42]吴宓.吴宓诗话[M].吴学昭,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4]曹禺.莎士比亚属于我们——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闭幕词[J].戏剧报,1986(6):5-6.
[45]何辉斌,殷企平.论王佐良的外国文学史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3):47-49.
[46]王佐良.集大成的莎士比亚——英国文学漫笔之三[J].青年外国文学,1988(4):86-89.
[47]杨恒达.王佐良与比较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05(3):42.
[48]王佐良.一种尝试的开始[M]//王佐良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782.
[49]王佐良.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论集(英汉对照)[M].梁颖,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50]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51]李伟民.开国内莎翁语言研究先河——简评《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莎学》[N].书刊报,1992-08-30.
[52]顾绶昌.关于莎士比亚的语言问题[J].外国文学研究,1982(3):16-28.
[53]黎昌抱.王佐良翻译风格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3.
[54]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6.
[55]王佐良.语言之间的恩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132.
[56]王佐良.刘译安东尼·伯吉斯《莎士比亚传》序[M]//安东尼·伯吉斯.莎士比亚传.刘国云,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2.
[57]王佐良.语言之间的恩怨[J].读书,1993(11):40-45.
[58]王佐良.悲剧艺术的顶峰——英国文学漫笔之四[J].青年外国文学,1988(5).
[59]王佐良.作为诗人的莎士比亚[M]//孙家琇.莎士比亚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166-170.
[60]王佐良.英国诗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61]吴宓.吴宓日记(1936—1938)[M].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32.
[62]王佐良.莎士比亚与两种气氛[N].人民日报(大地副刊),1988-3-16.
[63]王佐良.保持中国莎学研究的势头[M]//中央戏剧学院莎士比亚研究中心编.莎士比亚戏剧节专刊——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22周年.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杂志社.
[64]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81.
[65]李伟民.人生似萤莎如海 词藻密处窥真情——论王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M]//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王佐良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206-217.
[66]段汉武.百年流变——中国视野下的英国文学史书写[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37.
[67]王佐良.序[M]//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
[68]王佐良.一种尝试的开始——谈外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化[J]读书,1992(3):90-99.
[69]姜椿芳.姜椿芳文集(第十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41.
[70]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编辑委员会.英国文学[M]//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II).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1211.
[71]李伟民.朱生豪、陈才宇译《莎士比亚全集》总序[J].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2013(1):31-50.
[72]王佐良.举行上海莎剧节极好[J].中华莎学(创刊号),1989(1):11.
[73]王佐良.会员飞鸿[J].中华莎学,1994(5-6):26.
[74]李伟民.借鉴与创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和演出的独特气韵——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8-37.
[7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EB/OL].(2016-05-18)[2016-09-1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76]李伟民.莎士比亚与清华大学——兼论中国莎学研究中的“清华学派”[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舞台艺术,2001(1).
In Spring, We Think of Mr. Wang Zuoliang and Shakespeare—On Wang’s Study of Shakespeare
LI Wei-min
This paper reviews Mr. Wang Zuoliang’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Shakespeare and his ideas of running publications from a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 Wang’s study of Shakespeare is reflected in his grasp of Shakespeare’s overall thoughts and aesthetics, who deeply discussed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drama during the Renaissance, analyzed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different classes in Shakespeare’s blank verse from the angle of stylistics, interpreted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 views on Shakespeare and stressed that Shakespeare’s works should be studied on the stage based on textual analysis. He also highly appreciated Chinese performances of Shakespeare’s plays.
Wang Zuoliang; Shakespeare; research
2016-09-18
李伟民(1955— ),男,四川成都人,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莎士比亚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与流变”(项目编号:12XWW005)阶段性成果。
1674-3180(2016)04-0063-16
J80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