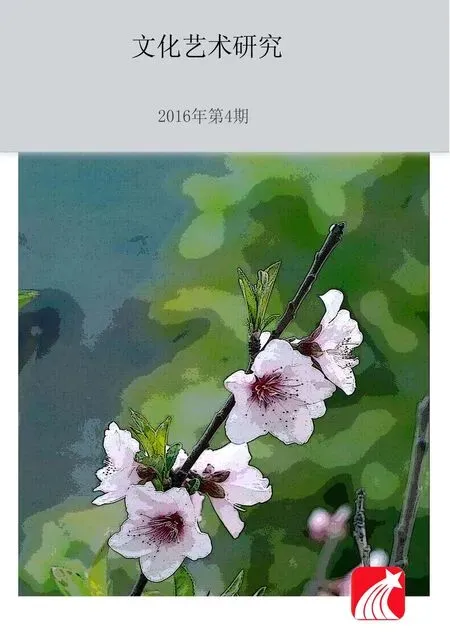捉妖记:香港的身份意识以及文化认同
2016-04-15阮加乐
阮加乐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捉妖记:香港的身份意识以及文化认同
阮加乐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捉妖记》于2015年暑期档创造的票房冠军纪录,在内地影史上意义非凡。在立足“华语电影”这一概念的广阔视野中,本文将以这部“跨区域性”、国际化合作的“国产”影片为切入,分析影片中“父亲”的缺失与重建、“孤儿”的成长与认同的隐喻性叙事,解码在“国际化”模糊了演员和制作班底各自“身份”的同时,来自中国香港的主创人员所“无意识”表达的:香港“自我”的身份意识、成长记忆以及对祖国大陆的文化认同。
捉妖记 ;香港 ;身份意识;文化认同
一、引言
真人与动画结合的华语电影《捉妖记》于2015年7月16日上映,瞬间将温吞的暑期档带到了高峰。首日票房高达1.72亿元,单日最高1.83亿元,首周四天6.7亿元,8天破10亿元,24天达到20亿元,上映63天最终以24.38亿元成为内地影史票房最高的影片。自1994年电影市场开放后,华语片从未在影史上拿到过票房冠军,因此《捉妖记》的最终登顶在内地影史上意义非凡。它不仅对于华语电影是一个鼓励,而且也引发了不少思考与讨论,学者们从“文化女权主义”“萌文化”“传统文化”“数字动画技术”等角度进行了多方评析。
“一个具体的影视文本,应被放到历史的、社会的大背景下考察,既把它看成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要考察它与特殊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1]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电影格局的转变,已经将“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进入了一个跨区域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整合的新阶段”[2]。《捉妖记》正是一部集合了中国两岸三地明星演员和制作班底,并且既有日本的美术指导,也有好莱坞特效人员参与的华语电影。在这种“跨区域性”电影制作流程的工业性统一背景下,“国际化”模糊了演员和制作班底各自的“身份”,但有关地理、文化、民族、身份认同及国籍等符号性的反思与构建,却在影片的文本中有着隐喻性的流露。
在立足“华语电影”这一概念的广阔视野中,本文将以这部“国产”票房冠军《捉妖记》为切入点,解读来自香港的主创人员这一影片中所“无意识”表达的:香港“自我”的身份意识、成长记忆以及对祖国大陆的文化认同。
二、香港的身份隐喻
法国电影家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于1948年在《法国荧幕》杂志上首先提出“自来水笔”摄影,认为电影已成为一种具有独特语言,是可以自由表达个人思想和感情的工具。[3]而后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电影手册》杂志又倡导电影“作者论”。两者都强调了创作者的个人意念在作品上的体现。《捉妖记》的主创人员为:制作人江志强(香港)、导演许诚毅(香港人,后加入加拿大国籍)、钱文锜(香港)、编剧袁锦麟(香港)。主创们的香港本地人身份,导演许诚毅漂泊的成长经历,很自然地会导致他们在个人经历和社会变迁中探询香港人的身份本质,找寻香港的身份认同。即使在电影流程工业性的“国际化”中,从制作人、导演、编剧的艺术家身份看,从电影“作者论”看,这部艺术作品印上的身份标签,无疑会使文本流露出一种香港的情绪。
(一)“父亲”形象的缺失与重建
本片中,天师堂一品带刀侍卫宋戴天,带领众妖建立了清静祥和的永宁村,然后离去,将年幼的儿子宋天荫作为保长,承担守护永宁村的责任。霍小岚同样也是,她的父亲在她十二岁时捉妖丧命,也就是从一开始,“父亲”在本片中就是一个缺失的形象。在孤独中长大的宋天荫,对于“父亲”带有一种仇恨,以至于在与奶奶的谈话中说:“抛弃妻子算什么英雄,他是个懦夫。”但霍小岚对于“父亲”的感情并不只是仇恨,还有伤痛。成为捉妖的二钱天师,对于她来说,不仅是家族传统,也是一种报杀父之仇的使命。“父亲”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一直是一个重要而丰富的能值符号,代表的不仅是血缘关系的那个父亲,也是“家庭和社会中那个精神上的领导者、权力的掌握者、制度的维护者和命运的决定者”[4]。本片中“父亲”形象的缺失正是香港“身份意识”的记忆流露,作为一个被割让的殖民地,其决定自己身份的“父亲”形象在百年沧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
宋天荫“失父”、霍小岚“丧父”,给予自己生命的“父亲”形象的缺失,这种在成长记忆中的伤痛,使影片开始投射到另一个“天涯沦落人”——小妖王出生的叙述:其“父亲”妖王被妖界叛军杀害,妖后怀上胎儿流亡人间,之后病弱的妖后将胎儿塞到宋天荫的体内。在客栈,宋天荫作为男性,只能痛苦地用嘴生出小妖王,闫妮饰演的郑夫人目睹后,惊呆地对丈夫说:“孩子可以从下面生出来,也可以从嘴里生出来。”胡巴被生下来后,因霍小岚坚持把小胡巴卖出去换成一百两银子的贪念,宋天荫虽然不舍,但还是诺诺听从了这一打算。在“大押店”卖掉后,两人残忍地离开,小胡巴在笼子里不解、无助、绝望地哭泣……小妖王胡巴的这一离奇、畸形而又曲折的孕育环节,以及酸楚地被卖、被抛弃的成长经历,从侧面看,贴合了一个关于香港身份整体的隐喻:鸦片战争后,病弱的清朝(瘸腿的宋天荫),听从当时执政的女性掌权者慈禧(霍小岚)的意见,而变卖掉自己的孩子小妖王胡巴(香港),以求影片中的一百两银子及其买来那一桌山珍海味的享受(晚清政权的维稳、求安与享乐)。中英《南京条约》这一“买卖”签订后,在当时封建文明 / 中华文化中,大英帝国却将香港单独带入了一个资本主义 / 殖民文化的“铁笼”。在当铺“大押店”中,从小胡巴在“铁笼”绝望地哭泣,可见香港一直难以释怀自己身份记忆中被“父亲”抛弃的伤痛。
伴随着这种与生俱来的伤痛,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迷茫。怀胎的宋天荫不仅是“母亲”,在片中也承担了教化小胡巴吃素的“父亲”形象。霍小岚因与宋天荫的恋人与夫妻身份,并且在山洞中给小胡巴“喂奶”的段落,又是一种“母亲”形象。片中精神有问题的奶奶对宋天荫和霍小岚谁是“孙子”,谁是“孙媳妇”的错认,都交织复合成一种身份、角色分工和性别上的混乱,彰显了香港夹杂在“历史上的中国”“新中国”“殖民母国英国”之间的对于身份认同的困惑与焦虑。
从妖王宴的决斗大战开始,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开始有一些转变。宋天荫中剑而死,代表了这个只会做菜和缝纫的阴柔形象的死去,也是隐喻“东亚病夫”“落后中国”的一去不复返。而后宋天荫以“家传”的十段锦剑法和果敢上前的勇猛气质,杀死了妖王。等宋天荫升级为一钱天师,并与霍小岚一样开始承担社会分工时,他已不再是瘸着的、羸弱的“母亲”形象,而是重新站起来的、具有强大男性权威的“父亲”。当代中国以“传统文化”的拾起和敢于担当的拼搏历程,成为令世界为之侧目的东方巨龙。胡巴为救“父亲”,吃力拔剑而割伤自己柔软的手指,期盼并使“父亲”宋天荫得以复活,不仅是自身妖性的消弭、亲情认同的感人流露,也是转变彷徨的归属感,暗含香港对祖国大陆“亮剑”腾飞的期盼与赞许。
(二)“孩子”的多重视角与认同
“父亲”形象的缺席,直接导致本片充满一种孩子视角的气质,是一种孤儿成长的记录。胡巴生出后就是一个性别不明显的小妖王,在佛教的神话体系里,菩萨是雌雄同体的。作为无性的孩子,小胡巴充满了天使和童话的意味,这也符合《捉妖记》老少咸宜“合家欢”的消费者定位。
也正是由于这种孩子视角,《捉妖记》的故事文本显得简单,甚至有些低幼,而片中数字动画技术的娴熟运用,使得本片更显满屏视觉奇观。这也因此招来学者的批评,认为是“文化化简后的技术苟且”[5]。但这种孩子视角的设定,在同期影片如《道士下山》中的精英文化情怀和自我陶醉式的哲学宣教面前,还是值得称赞的。引人思考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捉妖记》动画片式的简单叙述一样可以使影片具有丰富的所指。
竹高和胖莹被铁链拴着跳舞,伴随着长着喇叭的蛙形跳舞小妖,小妖们一边唱歌跳舞,一边掩护偷钥匙,以及胡巴吃野果后射子弹、上厕所、将布咬成温馨的图案、跑来跑去追逐嬉笑……这些都显得饶有童心。片中大反派葛千户带着五层人皮面具的伪装,是跻身上层社会的酒楼富商。但他脱下面具后,却是一个抱着胳膊瑟瑟发抖、面目丑陋的蛙形妖。这些有趣的镜头值得在都市中忙碌打拼、拥有形形色色“面具”的成人们玩味。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经济发展,人远离了山水田园的土地,在霓虹灯下、写字楼里被细分并异化成一台台工作机器,身心压抑,倍感疲惫。镜头里所有抒写的童话式的纯真、小妖王的可爱,正是对被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所扭曲的人的心灵的抚慰,使他们有摘下“面具”的一刻,反思当下并追忆自己消逝的童年。更有趣的是,本片的男主角一开始并不是由井柏然饰演,最初的那个男主角因众所周知的吸毒事件而导致本片重拍,其之前阳光帅气的明星形象也是一层“面具”,这使得《捉妖记》文本的内外构成一种巧合式的映照。
除了“孩子”式的文本故事、视听形象、观众定位,《捉妖记》的主题之一也是关于“孩子”的成长。从宋天荫、霍小岚,到被卖掉的小胡巴,这一“家庭”在身份上都是被父辈所抛弃。使得子辈在不可逆转的“丧父”中,孤独而又相互抚慰地自我成长。成长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拉康认为:“自我是在与另外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构成的。”[6]他们三者就如同金字塔般紧密结合,在他们各自成长的亲密互动中,都完成了对“父亲”的重新认识,完成了对外界的重新丈量。到他们三者分别时,“父亲”的形象在他们三者的意识里被重建后,随之而来的是无比的认同以及依恋。
小胡巴在“妖王宴”上被救出来,分别时的不舍流泪以及最后的“弃兔吃枣”,说明它懂得了向善的人性慈悲,也感悟到并且开始依恋人世亲情的温暖与珍贵。宋天荫和霍小岚在扮演“父亲”的角色中,理解父亲,寻找父亲(结尾宋天荫说要去找父亲),这一子辈对父辈的原谅、理解、认同以及寻找,是香港在长期的尴尬、彷徨、伤痛、仇恨后,开始对内地(母体/父辈)的一种血缘与文化认同倾向。影片不仅表达了香港与内地在“共同”的中华文化大家庭中享有亲情的温暖,也是香港一种社会心理、文化倾向的无意识流露。
虽然追杀它的叛军已不知所踪,但小妖王胡巴与人终不是同类,宋天荫拔剑划开了一道火光,让它走。这次的“抛弃”是充满温情的怜爱分别,而不再是把它卖掉的那种冷血的抛弃。胡巴只好不舍地边走边擦泪,在这个镜头中,我们可以窥探出香港对于祖国大陆的一种社会心理:香港脱离英属殖民地后,与社会主义的母体大陆并不是“同类”,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如宋天荫用剑划出的那道火海般的鸿沟,横亘在父与子之间。但是这道火海鸿沟,并不是最初宋天荫被父亲“抛弃”时的那种冷酷烈焰,这次横亘在小胡巴与宋天荫之间的火光,带来的有温暖、有光亮。他们虽然因人/妖,同类/异类的对立差异暂时不能在一起,但他们有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以及未来的无数可能性。
三、身份认同中的不完全性:文化认同
在身份意识上,值得注意的是,“父亲”形象的重建后,子辈对父辈的“认同”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因为在小妖王胡巴身上,隐藏着一种模糊的不彻底性,即其对亲情、对“人”的认同,与其本质为妖、以后生活在同类妖怪中的悖谬。我们知道,身份认同,既是自我对身份的认识,也是他者对自我的评价和认识。一方面,身份认同使个体获得情感和意义上的安放场所,另一方面又使群体的秩序得到维系和巩固。而胡巴与宋天荫和霍小岚离别后,显而易见是与同类妖怪生活在一起。再来分析胡巴身边的同类:竹高、胖莹作为前朝妖王的旧部,在片头对宋天荫的“肉香”有很大兴趣,即嗜血吃人的妖;永宁村的众妖,“不吃人,只吃素”;还有在妖王宴上被解救下来的一些其他妖怪,应该既有吃素也有吃人的;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妖怪。由此,即使众妖拥戴小妖王重建一个“永宁村”,胡巴身边的妖怪同类们,在对它吃素、抛弃妖的本质这一问题的评价和认识上,也会产生一点分野。为了族群秩序的稳定,胡巴在未来的身份认同上,也许会有一些取舍,而不会是彻底认同人类的世界。
这点在影片中也有展示:胡巴与“父亲”宋天荫离别后,它看到了一只兔子,本质为妖的它露出欣喜的嗜血兽性,但是它迟疑了一下,还是放走了兔子,艰难地吃素,咽下枣子。 但是当它仰头,开始期待来自“人类”父母宋天荫和霍小岚的赞扬时,可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父母的缺席,以至于“他者”对小胡巴的评价和认识,现在也只剩下身边的同类妖怪。这既包括很多吃素妖,也包括了不少吃人妖,这无疑会导致小胡巴身份认同上的不彻底性。
依照上文中小胡巴与香港的身份隐喻对照,可以分析香港在身份认同中的一点复杂的倾向。“身份意识包括政治、文化与经济等三种类型……目前香港政治身份的认同集中在本港意识,文化身份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那么经济身份则在国际大都市、国际金融中心的背景下,更认同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原则。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弹性空间。”[7]永宁村的妖大娘说:“我们不吃人,只吃素。”小武和永宁村众妖兽性的消除,无疑是宋天荫“父亲”教化的结果。而他们的新首领小妖王胡巴在结尾处的吃枣,也得益于宋天荫的言传身教。可见他们的“只吃素”“弃兔吃枣”,都是两代“宋”家人对妖怪的教化影响,是隐喻中华文化对香港精神文化根深蒂固的滋养和指引。对于处在资本主义和殖民文化中的“异类”香港,“宋”家人(中华文化)重新界定了永宁村的众妖和小胡巴对于自我身份意识的认知。但是,从众妖和小胡巴摈弃妖怪嗜血吃人的本性、“弃兔吃枣”的段落中,可见香港对于祖国大陆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对“父亲”“礼义廉耻”教化的认同,即对于祖国大陆文化上的认同,而不是彻底的三种类型齐全的认同。因为胡巴与人类父母离别,最后与妖类生活在一起,明显是香港在身份本质、身份意识中的政治认同上,保持清醒和回避。也只有与同类居住生活,才有一种“身份稳定”的安全感。所以,人与妖分别时的不舍流泪、藕断丝连的感人结尾,既是留恋血缘亲情、家庭温暖,“亲宋”下的文化认同与依恋,也是香港在身份本质上的回避、政治认同上的自觉警惕。
跳出故事文本的细读,我们整体来看《捉妖记》。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明振江认为:“《捉妖记》能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8]《捉妖记》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充满“中国元素”的世界:竹林、阁楼、村落、剪纸、符咒、木质碗筷、中国水墨画面、字幕的古风字体、铜钱与道家修真层级。还有志怪小说、唐宋传奇、西游文本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所蕴含的捉妖文化、武侠文化、修道文化等。并且在电影里面,“妖完全类人的忠诚、情义、谋略以及借妖喻人的叙事手法与蒲松龄以妖为镜、讽刺喻世、寄托情怀的策略十分一致”[9]。除了视觉传达上的本土美学、叙事手法上的古典蕴涵,最重要的是,这部《捉妖记》所蕴含的东方之“情”,那种没有距离的感情:小武与宋天荫的友情、宋天荫与村民的邻居情、宋天荫与霍小岚的爱情,以及围绕全剧的血缘亲情,都饱含温馨动人的情感与伦理。《捉妖记》所创造的一个人与妖共存的“大同世界”,正是传统文化、东方之情最重要的显现。
《捉妖记》里的故事本身隐喻了香港身份意识、成长记忆以及文化认同。而在视觉传达上的本土美学、叙述手法的古典蕴涵以及主题思想的东方情感更是亲自践行了故事中流露出的香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倾向,以至于在文本内外构建成了一种环形的照应。
四、结语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学者金耀基说:“香港华人是把‘香港人’的身份与‘中国人’的身份区隔开来的。我认为这一区隔基本上是政治认同的分别,而不是文化认同的分别……香港华人即便在政治上自认为‘香港人’,对中国文化也是有极厚的认同。”*出自金耀基的《香港:华人社会最具现代性的城市》,转引自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所以,即使在身份本质上,影片做出了回避式的结尾,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小胡巴与“父母”宋天荫霍小岚之间藕断丝连、感人至深的亲情纽带,以及他们未来无数的可能性。
在影片最后,年幼的小胡巴站在山巅。虽然年幼的香港仍然拥有一种“孩子”视角,具有孤儿般的漂泊流浪意识,但是它已有一定的归属感,它不再孤独。远视层林尽染的绚烂林海,对于未来不可知的美丽世界,它也充满了自信与期待。在祖国大陆与香港体制上保持多元化,但政治上走向统一并且关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来自文化上的认同感更能加深彼此的亲情纽带,以及创造无数的可能。对于未来小胡巴与“父母”宋天荫霍小岚能组成完整和幸福的“家庭”,我们同样充满期待。
[1]史可扬.影视批评方法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58.
[2] 陈犀禾. 华语电影:理论、历史和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4.
[3]Alexandre Astruc. The Birth of a New Avant-Garde: La Caméra-Stylo[M]//Timothy Corrigan.Film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and Reader.State of New Jersey:Prentice-Hall,1999.
[4] 陈犀禾. 华语电影:理论、历史和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00.
[5] 杨俊蕾.我要山海经的妖,你却给我迪士尼的怪——影片《捉妖记》中文化化简之后的技术苟且[N].文汇报,2015-7-24(11).
[6] 杨守森.新编西方文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44.
[7] 陈林侠.香港的焦虑:政治意识、“再殖民”及其身份认同的前瞻——以《建国大业》、《风声》在香港的传播为核心[J]. 戏剧,2010(02):136-145.
[8] 范云波 .票房直逼20亿元 《捉妖记》何以成为中国电影产业新标杆?[EB/OL].(2015-8-07)[2016-09-21].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5-08/07/c_1116184926.htm.
[9] 陈琰娇.《捉妖记》:一部保守的理想主义喜剧[J].电影艺术,2015(05):31-33.
MonsterHunt: Identity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RUAN Jia-le
The movieMonsterHunttopped the box office champion in 2015. This paper used th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 film as an exampl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creators: the identity consciousness, growth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China.
MonsterHunt; Hong Kong; identity consciousness; cultural identity
2016-9-21
阮加乐(1992— ),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影视批评研究。
1674-3180(2016)04-0126-05
J90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