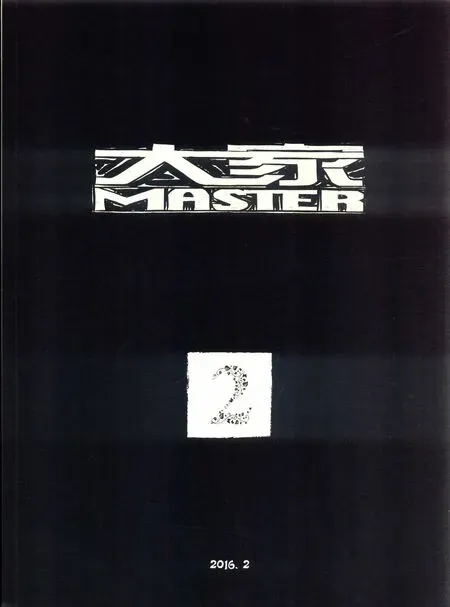小说与负面经验(主持人语)
2016-04-15耿占春
∥耿占春
小说与负面经验(主持人语)
∥耿占春

耿占春,文学批评家。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主要著作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叙事虚构》《失去象征的世界》《沙上的卜辞》等。另有思想随笔和诗歌写作。现为大理大学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看来《大家》杂志的“先锋新浪潮”并不必然意味着倡导一种纯粹的形式试验,也是为着鼓励人们寻找一种新的声音、一种新的叙述口吻,或一种与众不同的可能有点极端的话语,来传达特殊的体验。就本期的两篇作品而言,这种体验的特殊性并没有让它们失去与社会的直接关联。事实上,在学群、震海两位作家的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世界远没有他们的社会寓意更令人感兴趣。
学群沿袭了他去年发表在《大家》杂志上的小说篇名,就像学群上一篇“坏家伙”的叙事一样,《坏东西》继续以一种“坏人”的叙述话语、以一种社会地位低处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就像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阿来的《尘埃落定》从智障者或弱智者的视角讲述故事所具有的特殊魅力一样,他们都能够看待一个伪装得较少的世界。“坏家伙”因为从不伪装自己,也就看到或感受到一个更真实的世界。与“好人”不同的是,“坏家伙”就是让他自己的生活逻辑与世界的逻辑相一致,而且就像人物自身所说的,这样他生活起来也就“更容易一些”。
震海的小说与学群小说的风格迥异,或许因为他同时是一位诗人,小说的叙述采用的是诗歌式的并置而非线性叙述,没有连续性的叙述,甚至没有清晰的主题,仅仅是城市生活场景的一个瞬间,或对几个瞬间场景拼贴性的组合。在震海的这个短篇里,酒吧间的每个人物都是他人生活与情感的“闯入者”,每个人都是意外的、偶然的、陌生的存在,而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偶然性与陌生感,生存的某个瞬间显得极其神秘或隐约的恐惧。在某种意义上,“闯入者”是对一种特别当代性的城市生活或大众生活场景的讽喻。《坏东西》和《闯入者》表征着两个不同的人群颇具当下性的生存状态,但二者的一个相似之处是对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负面体验有相当极端的描述,并力图在生活的低处寻找生活的意义。
责任编辑:陈鹏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