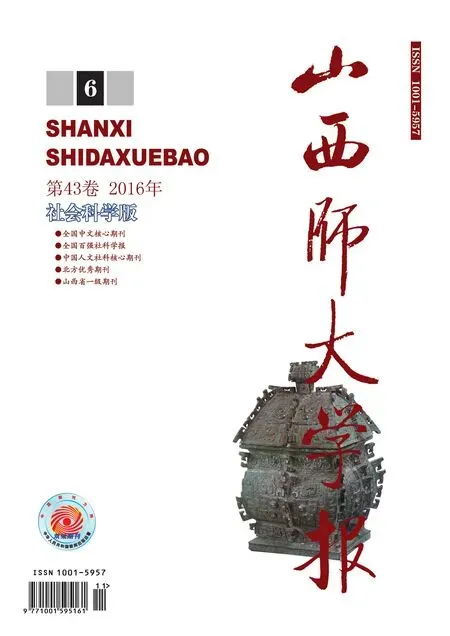复 调 的 “张 腔”
----张爱玲沪港语境下的小说和剧本
2016-04-13鹿义霞
鹿 义 霞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上海、香港不但是张爱玲的特别生命驿站,也是其文学创作的两个重要空间,两者相互对话、映衬、渗透和补充,连同彼岸的美国,共同打造出丰富的张氏小说世界。站在文化地理的延展这个空间的维度解读张爱玲笔端的风景,我们会发现,作者的创作和她生活的地域有着深层的精神血缘的联系。空间的转换,不但会改变日常生活,也会改变审美视野;不但会改变思维定势,也会促进创作转型。
1957年至1964年间,张爱玲与香港“电懋”合作,在银幕电影世界里拓展了新的创作空间——创作(改编)了十个剧本,其中既有都市爱情剧如《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桃花运》《六月新娘》《一曲难忘》《魂归离恨天》,也有社会问题剧如《小儿女》《南北喜相逢》《南北一家亲》等。比起“上海时期”的小说创作,她“香港时期”的这些剧作一改苍凉本色,多表现出无厘头式的谐闹、怪诞、戏谑之类的审美特征,迥别于其小说的艺术格调,与熟悉的“张腔”颇有不同。主色谱的变化,既与作者人生境遇有关,也留存了此时期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足迹。透过小说与电影剧本的双重视野重读张爱玲,我们会发现一个与“前阅读”经验迥异的剧作家张爱玲,一种复调的“张腔”。
一、两极之间:从苍凉之美到谐闹喜剧
张爱玲的小说多具有“苍凉”之美,无论是意象的选择、气氛的营造、人性的体察,还是故事的结局,都弥漫着一种灰暗和虚无,氤氲着一种《红楼梦》式的痛与悲。那些家庭中的女性,天生抗拒不了被规约的命运,“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这种悲剧意识,沉淀在张爱玲的文字里,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对人类生存困境特别是女性生存状态的感知与体认。她惯常以老到、幽冷的目光,不露声色地透视着世俗社会中的凡俗之轻和“被看”者的隐秘灵魂。对此,夏志清有一种形象的总结:“我们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的巧妙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1]表面上看,张爱玲聚焦世俗的情感、乱世的男女、家庭的百味、物质的欲望以及人事的纠葛,笔下的故事热闹而入世。其实,开在文中的都是冷艳的花朵。她总是比较犀利甚至冷酷地把人们从天上拉回人间,揭示人生的琐碎、平庸、苍凉以及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永远也无法逾越的“墙”。在她看来,“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即使父母与姐妹之间,也一样存在让人心寒的东西。大众讴歌亲情的伟大,张爱玲解剖人性的幽暗——你看,《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见不得儿女感情的圆满,诱导儿子长白食鸦片,调侃戏弄儿媳,揭露女儿长安有陋习,断送她的感情归宿,她无比残忍地让孩子们为她的不幸做陪葬;你看,《花凋》中的郑川嫦病在旦夕,其母舍不得私房钱,其父怕被传染,而那个年轻的男子,终究抵不过时间和现实,还是牵了另一个女孩——正所谓“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你看,《半生缘》中的曼璐为了长久的饭碗,竟默许丈夫祝鸿才强奸曼桢,搭上了妹妹一生的幸福。大众渴望美好的爱情,张爱玲总能以一盆冷水给你展示其庸俗和庸常——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就算白流苏如愿以偿了,也需要用一座城的倾覆去成全,范柳原给她的也不是完整的爱情,他们只不过是战争境遇中彼此的慰藉。所以,无论是《金锁记》《花凋》《心经》《鸿鸾禧》,还是《等》《封锁》《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都传达出作者对生存之寂寞和人生之残酷的悲剧心理,浸染着一种乱世的悲情。而这,也是众多读者所公认、众多作者所模仿的“张腔”。
1952年,因为对新政权下的写作环境心存犹疑,张爱玲在历经试探、观望之后离沪赴港。罗湖桥的两端,一个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新中国,一个是英属殖民地。而后者,凭借其特殊的商业消费、流行的快餐文化以及相对自由的言说语境,接纳了都市文学的流脉,孕育出与大陆迥异的叙事风貌。从一个都市到另一个都市,从一种语境到另一种语境,张爱玲眼中的风景在变,笔端的人物与文字的风格也在变。
与小说所承载的悲凉截然有别的是,张爱玲为香港“电懋”所打造的剧本多张扬着好莱坞爱情通俗剧、喜闹剧的热烈,洋溢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喜剧色彩:层出不穷的逗笑、不断抖落的噱头、机智诙谐的对话,极尽夸张的演绎、不可思议的巧合、虚惊一场的误会、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当然,这里还充溢着“一夜风流”“桃色交易”“舞女从良”“争风吃醋”“新娘逃跑”等流行的精彩桥段……《情场如战场》中,一女三男之间关于爱情的角力充满趣味,强劲地刺激着看客的兴趣;《六月新娘》中,新娘子的临阵脱逃充满着戏剧性,颇能激发观者八卦的欲望;《人财两得》中,机趣横生的误会与巧合接连不断,简直成为笑料的加工厂;而《南北喜相逢》《南北一家亲》更是在地域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碰撞冲突过程中,让人一次次捧腹大笑。难怪张爱玲如此发问: “这是张爱玲吗? 这么好莱坞,这么调皮的、活泼的、梦幻的世界?”[2]那位因为冷静而犀利,因为看透而残酷的上海沦陷区的张爱玲,摇身变成了热衷搞怪的大咖。她好似从看破沧桑的中老年状态一下子回到了轻狂、疯癫的青少年时代,文字中生动而饱满的逗趣俯拾即是。
张爱玲之所以大量地布设好莱坞式的轻喜剧,应该和她对文体的审美认知有关:“文艺可以有少数人的文艺,电影这样东西可是不能给二三知己互相传观的。就连试片室里看,空气都和在戏院里看不同,因为没有广大的观众。”[3]她深知电影走的是大众化路线,更需要研究一般人的心态,采取不同的写作策略,巧妙布置一个个有看点、有笑点、有泪点的情节。当然,创作转型的背后还隐含着香港彼时彼地的社会元素以及她所寄身的“电懋”体制的限定。时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文化随之繁荣,中西混杂的多元性凸显。在这种语境下,“拿来”西方好莱坞电影模式摩登而时尚,十分适合港人的口味,也便于宣泄观众的生活压力和身份焦虑。在商品消费文化的君临之下,“通俗文学”大行其道自有其肥沃的土壤。另外,“电懋”当权者的个人兴趣好恶以及该公司的片场模式也影响着张爱玲的写作倾向。最高领导陆运涛、主政的总经理钟启文和制片主任宋淇都曾接受西式高深教育,推崇洋化。该公司在管理、剧本、明星方面都有着类似好莱坞的一整套系统,讲究生旦的搭配与其间爱情的纠葛波折,趋同大众的观赏期待和消费趣味。而且,彼时彼地,香港的多半影人来自上海,在长期的政治纷扰和政局变化的历练之下,大家都不愿正面触碰政治问题,所以作品多多少少总表现出某种“逃避主义”倾向,现实批判性无疑不是公司的制作主旨。为迎合一般民众追求娱乐、逃避现实的心理,“电懋”出品以家庭通俗剧,大型歌舞喜剧为大宗。“由于喜剧人物情景易于形象化,易于讨好;悲剧需要放在一个较强的社会文化脉络中才能感人,喜剧则容许较多的想象。”[4]在“电懋”的片厂模式下,张爱玲自觉地适应观众市场,从人世的关切者演变为笑闹的炮制者——将好莱坞的“神经喜剧”、通俗情节剧模式与中国世俗男女的婚姻家庭有机结合,探索出与香港观众欣赏口味相契合的电影类型与喜剧风格。那些“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的“软弱的凡人”,迎合了普通市民娱乐自己、消遣别人的心理,当然,也体现了张爱玲创作中深层的“市民意识”。
创作的环境制约写作的心境。在香港这个“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快餐文化旗帜呼呼飘扬,商业消费刺激着泅浮其中的大众,张爱玲瞄准中产阶层的小市民生活,截取他们爱情婚姻生活的笑料与苦难,对大众来讲,既是缓解压力、释放情绪的途径,也是寻找自我的方式。
二、爱的回归:从人间无爱到天地有情
张爱玲小说的一个特别精彩之处无疑在于对人性阴暗面的洞悉和解剖。在她笔下,即便是家,也藏匿着看见或者看不见的刀光剑影;即使是父母,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自私和懦弱;就算是恋爱或婚姻中的双方,也不过是凡俗而自私的男女。《金锁记》中的家,爱情不是爱情,亲情不是亲情,鸦片的云雾缭绕其中,立着一个被戕害并继续戕害儿女的母亲,“她”异化得让人恐惧。《倾城之恋》中的家,白母保护不了女儿,哥嫂把妹妹当做摇钱树,大家彼此用心经营的,不过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的小算盘、小九九。《花凋》中的家,一对奇葩的父母在女儿垂危之际,考虑的还是自己的小金库和小安逸。《十八春》中的家,母亲为了安稳,竟然默许包庇大女儿对二女儿的囚禁。此外,张爱玲在小说世界里对爱情所持的态度也是悲观的,她总是习惯于撕开血淋淋的口子给读者看——哪有美丽的爱情?生活本就是无底的深渊。“女结婚员”辛辛苦苦追求的,大多不过是一晌贪念;男方所拿出的,大多是敷衍和权衡。《沉香屑 第一炉香》,葛薇龙爱上了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把自己的青春,一点点贱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倾城之恋》,促成白流苏和范柳原婚姻的,不过是一对自私的男女在乱世中的彼此依靠;《封锁》,那看似电光石火的爱情,也只是特殊时空下的短暂消遣和慰藉;《红玫瑰与白玫瑰》,所谓爱恋,总是得不到的才最好……
相比小说,张爱玲在香港语境下的剧本中,父母的角色被符号化、喜剧化,最不济也是从狠角演变成丑角:就算精明、自私,也是在小奸小坏中藏着可爱,让人在捧腹一笑中寄予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张爱玲一改其小说作品中对人伦亲情和男女爱情的怀疑、揶揄与嘲讽,反而以满含温情的笔触 ,一反常态讴歌家庭、讴歌奉献精神,展示细水长流中蕴含的情谊,表达对真挚爱情的赞许和肯定。比如《人财两得》,男女主人公历经巧合误会,最终各偿所愿、皆大欢喜;《六月新娘》中,汪丹林和青梅竹马的未婚夫董季方一波三折,最终还是成为欢喜冤家;《一曲难忘》,歌女南子和伍德建历经人为的误会和战事的考验,最终谱写了灰姑娘的童话;《小儿女》,不论是父亲王鸿琛还是其女友李秋怀,无论是女主人公王景慧还是其男友孙川,大家都富于牺牲精神和担当意识。此剧中,张爱玲还颠覆了定型的恶继母形象,打破了由个人经历所建构的“前理解”,通过种种巧合,使孩子们化解了仇视,终于接纳了温柔善良的新妈妈。这样的后母角色在其小说中是不可想象的。
把平面的文学幻化为立体的视听效果,这对张爱玲来说也是一个迷人的诱惑。喜剧的广泛植入和大团圆式结尾的强势进驻,使张爱玲此时的电影契合着大众的接受心理,极大地满足了市民阶层大团圆式的白日梦。这在移民的香港和殖民的香港,无疑戳中了潜隐于大众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安抚着需要无限慰藉的人生。
基于谋生的现实困境和对电影大众商品本质的自觉,电懋时期,张爱玲的剧本收敛了剑指人性的锋芒,多铺陈出热热闹闹的大团圆格局——无论是《一曲难忘》《人财两得》,还是《小儿女》《南北喜相逢》《南北一家亲》,主人公最后都收获了圆满的爱。也许这和电影工业的特点息息相关,因为世俗人生总有这样那样的不遂人愿,太多的悲欢离合,太多的不团圆,所以,大团圆式的白日梦便成了安抚人生多艰、韶光易逝的一剂精神良药。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祸乱刚刚消除,正值百废待兴;移民蜂拥小岛,泛滥家国乡愁,就更加需要喜剧化的电影来慰藉庸常人生,排解羁旅之忧,安抚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一片市民心。“电懋公司带有强烈的中原性格,大部分的影人均来自上海,家世背景又不脱中产及知识分子的范畴,作品具有强烈的‘逃避主义’倾向。”[5]不独张爱玲的剧本如此,电懋的许多作品都展现出这样的应景特征,如《好事成双》《香车美人》《长腿姐姐》《青春儿女》《空中小姐》等。在电影的内在肌理背后,是事关社会心态和文化生态的复杂符码。
三、人物主体:从封建家庭旧女性到现代都市“女汉子”
行走在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女儿、母亲、妻子,多是在父权、夫权压迫下扭曲挣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大多以一种压抑、怪诞、无助甚至病态、疯癫的状态出现。女儿们或是老姑娘,或是失婚者,或是心机女,为着一个“女结婚员”的职位处处哑忍,赔尽小心。《金锁记》中的长安作为一个“老派的闺秀”,懦弱、孤独、无助,与恋爱对象童世舫之间即将到手的幸福被母亲硬生生一句“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而完全断送;《花凋》讲述了一个封建遗少的女儿郑川嫦的悲苦人生与苍白无力的爱情,她如同一朵娇嫩的鲜花还未来得及完全绽放便过早地凋零;《封锁》中,翠远萌生于电车中的爱情,也不过是因封锁而生,也因封锁而死。即便是《倾城之恋》中将婚姻修成正果的白流苏,得到的也不过是一霎那的真心。她们,习惯了上天安排给自己的宿命。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似乎没有年长的好女人,没有积极追求健康人生的自立自强的女性,她们不是对责任麻木不仁 ,就是向子女勒索感情,不是安于旧家庭的现状,就是哀叹不能自主的人生。读张爱玲的小说,如同用放大镜来看复杂的人性——这个世界中充斥着自私、猜忌、算计,人心是莫测的江湖。
然而,在张爱玲为“电懋”写的一系列都市喜剧中,却活跃着一批敢想敢干、大胆抗争的现代都市“女汉子”,剧本中扑面而来的是现代性、都市化元素与性别战争,都市女性在积极争取着属于她们的自主权和话语权。《六月新娘》中的汪丹林要求婚姻必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为此不惜做逃跑新娘,在她看来,“做女人要保持女人的尊严”,不需要“买卖式的婚姻”;《桃花运》中的端菁是现代都市的女强人,面对朝秦暮楚的丈夫,她果敢地接手了酒店,掌握了主动权;《魂归离恨天》中的湘容,是敢爱敢恨、美丽而又有几分野性的现代型女性;《情场如战场》中的纬芳好似都市社会里的一株野玫瑰,自信、强势、靓丽,主动出击追捕自己中意的男人,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化印记;《小儿女》中的景慧和秋怀,忍辱负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处处展示出“女代父/母职”的“家庭天使”的坚韧、美丽与善德,她挺起身躯,强大灵魂,只为撑起一片天空来庇护家人。与读者习惯的“张腔”相比,张爱玲在这些剧本中展示出一种全新的女性凝视话语——她所擅长的尖新比喻、巧妙通感等手法不见了,她所习惯塑造的旧女性、遗老遗少也隐身了,站立在观众面前的,是美丽叛逆、敢爱敢恨、精明能干、热辣果敢、坚强独立的都市新女性。就是有着同样身份的中产阶级太太,剧本中的她们也有着小说中所不具备的运筹帷握、智勇双全和灵机应变。这些女性,不甘做“怨妇”,倒乐于做“悍妇”,她们以其自身的智慧与魅力,展示着对“男权/父权”的挑战和抗衡,彰显着时代女性的独特魅力。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儿,是退化了翅膀或者翅膀上系了重物的鸟儿;太太,纷纷带上了心理的或黄金的枷锁;而母亲,总是那么自私冷酷,母性常常被现实蒙上阴影。她小说中的女性是冷色的、悲凉的、在家族中湮没理想或棱角的;而其电影剧本中的女性,则是暖色的、温暖的、能够撑起一片天的。剧本中的她们多少有了自己的意志和独立自强的意识,敢于向男人、向生活叫板。这种演绎是她小说中女性形象与女性想象的延续,也是一种超越,是张爱玲对其小说文本女性形象的颠覆、补充和丰富。
也许,在风驰电掣的香港,踏实肯干、独立自主的新女性更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更能在时代舞台上拼出一片天地,也更契合香港这一商业都市的氛围和节奏。除了受好莱坞“神经喜剧”的影响,张爱玲的创作转型也和时代氛围息息相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相对于40年代的上海更为开放,所以在香港时期出现的太太多是可以独当一面的新女性,她们风风火火,展示出很辣很“man”很强势的特征。
四、空间迁移与大众审美下的“场效应”
用张爱玲自己的话来说,电影“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了”[6],她以别样的“张腔”,为我们勾绘了当年香港多元、兼容、消费至上又世俗善变的文化面貌和都市风情。当然,剧本创作对于张爱玲而言,意在“稻粱谋”的成分颇多——她移居美国后,因为文化疏离等原因,写作市场并不好打开。此时的她,出于生计考虑,也因第二任丈夫赖雅之病,急需筹措资金。基于谋生的写作困境和对电影大众商品本质的自觉,张爱玲基本放弃了个人色彩更为浓厚的小说创作,而投身于盈利更为迅速的电影剧本写作。小说可以极尽笔墨渲染之能事,立体展示那些小奸小坏、“不彻底”的人物,致力于在文字中书写和还原哀乐人生。而电影工业是反感真正的悲哀的——热热闹闹的大团圆、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性格鲜明的人物、外向型的故事主体,更有利于电影发挥“给眼睛吃的冰淇淋,给心灵坐的沙发椅”之效应。剧本比小说更需要应时应景,更需要考虑市场需求,甚至还需要借助影星的炒作。就当时的文化环境来说,似乎只有香港,才能和她相互成全。夏志清曾如此评价张爱玲此时的创作:“我想张爱玲真的因为并无固定收入才去编写电影剧本,也去翻译、节译才华远不如她的中美当代作家。因之对此项 hack work 有时感到十分厌恶。”[7]何为“hack work”?“苦力;苦工”是也。作为片场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张爱玲有时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作品对于演员、情节的合理性。她面对的毕竟是需要综合考虑大众反应和资本回收的艺术形式——电影。票房,是剧本作者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负荷者,张爱玲的创作转型,除了打破我们的审美惯性,也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地域的诸多思考。随着空间的迁移,文学创作与社会场、政治场、经济场之间存在着多重交叉的“场效应”。
作为城市文化的书写者与城市感觉的捕捉者,张爱玲早在上海时期就敏锐地嗅到电影这个新兴的跨媒介文化,所以,她在写作中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竭力与电影艺术沟通的文学精神。但是,“地狱上的天堂”上海,与“华美但悲哀的城”——香港,在城市文化、城市精神、大众审美消费以及接受期待方面,毕竟存有不同。上海成就了张爱玲,张爱玲也成就了上海——在上海,她写人与城市的纠缠与融合,更注重从细部描摹人性,解剖城市。香港发展了张爱玲,张爱玲也装扮了香港——聚焦于香港文化生态的剧本,她更关注普通人的诉求,比较而言,“香港时期的剧本确实清浅、欢快到了不必要的程度”[8]。
李欧梵说:“似乎大家心目中的印象,张爱玲是苍凉的。其实,张爱玲另外一面是很喜剧化的。其实世故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喜剧性的事物,也就是把人生看作喜剧。”[9]两副笔墨的张爱玲,在香港实现了对自己既往风格的延伸和变异,也丰富了对世俗生活的细致体察和感悟。从复调的角度看“张腔”,可以让我们更辩证地看待张爱玲,更深入地了解语境、心境和创作转型之间丝丝入扣的关系。借此,我们还可以在互为参照中看到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的种种新质。
[1] 夏志清.论张爱玲的小说[M].香港: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
[2] 李昶伟.张爱玲.借银灯之双城记[N].南方都市报,2011-11-1(16).
[3]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 刘澍,王纲.张爱玲的光影空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5] 焦雄屏.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M].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6] 张爱玲.张看 张爱玲散文结集[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
[7] 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3.
[8] 吴娱玉.张爱玲香港时期电影论:以上海时期电影为参照[J].淮阴工学院学报,2013,(4).
[9] 李欧梵.苍凉与世故[M].上海: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