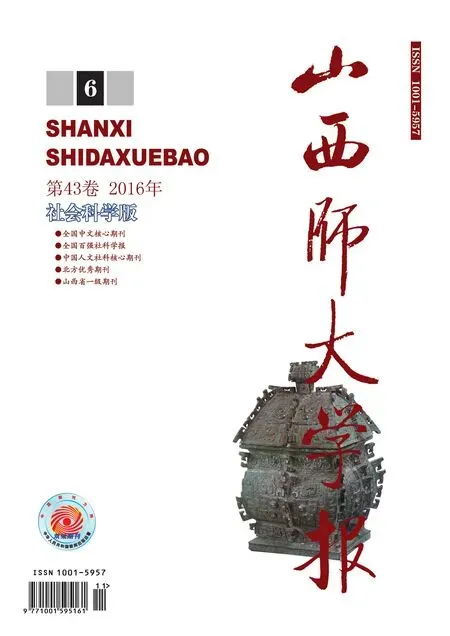朝鲜诗家李瀷论杜诗
2016-04-13王成
王 成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赵翼在《题陈东浦藩伯敦拙堂诗集》中曾说:“学诗必学杜,万口同一噪。”杜甫作为中国诗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得到了当时及后世文人、学者的广泛关注、品评,甚至出现了众人学杜、百家注杜的繁荣景象。杜甫的海外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在深受韩国历代文人喜爱的唐代诗人中,杜甫是韩国学者研究最多的中国诗人,只有杜甫的诗集出现了‘谚解’本(即翻译本),而且还从不同的角度对杜诗进行了颇具特色的研究。”[1]97可见杜甫的诗歌已经深入到了朝鲜文人、学者的精神世界。
朝鲜文坛最早论及杜甫者,当为高丽时期的著名文人李仁老(1152—1220年),其《破闲集》多次提到杜甫,如“琢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自雅缺风亡,诗人皆推杜子美为独步”[2]3—4等等。“到了朝鲜时代(即李朝时期),在王室倡导之下编辑了杜诗注本,接着翻译了杜诗”[3]68。宣祖、仁祖年间,出现了朝鲜第一部研究杜诗的专著,即李植(1584—1647年)《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标志着朝鲜杜诗学的成熟。实学派先驱李瀷也是朝鲜众多论杜诗最出色的学者之一。李瀷(1681—1763年),字子新,号星湖,李朝后期著名文人、诗论家。著有《星湖僿说》30卷,其诗学思想体现在“诗文门”三卷中,每一则论诗条目均有小标题冠之,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论诗多自得之见,水准很高,论李白、杜甫、韩愈诸条,均可供学者深入探讨。”[2]198
一、对杜诗的细读
诗歌是一门语言艺术,是值得细细品味的艺术载体。对诗歌的细读,不仅可以看出阅读者、赏析者的文学品读、鉴赏能力,更是读者与作者心灵之间碰撞和交流的过程,是一种审美体验。所谓“细读”,即指对诗文的词语、句意、结构等要素进行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阐释,进而揭示诗文的思想主题。这是历代诗家普遍热衷、推崇的阅读文学作品的方法之一。
《八哀诗》是杜甫的名篇之一,全诗共486句,最长者86句,最短者40句,描述了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璡、李邕、苏源明、郑虔、张九龄等八人一生的主要事迹。朱东润对《八哀诗》的评价甚高:“《八哀诗》是八篇独立的传记,有韵的《史记》,而且充满感情,呜咽淋漓,即使在《史记》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名篇。”[4]165李瀷就从词语、句意等角度对杜甫《八哀诗》给予了细读,颇具新意与学术价值。
《八哀诗》在朝鲜是诗人学诗、讲诗的重要素材,从李瀷的论述可见一斑:“姜主簿世贞云:‘余曾学杜甫《八哀诗》于许沧海格,沧海学于李东岳安讷。’盖有所传授口诀,仍为余道数条,颇发于注家之外。”[5]3683姜世贞学于许格,许格学于李安讷,这种学缘关系递相授受,以致对于《八哀诗》的讲授、学习“有所传授口诀”[5]3683。李瀷分别解读了《八哀诗》中《赠司空王公思礼》《故司徒李公光弼》《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等诗,其中虽然存在个人主观臆断,但新见叠出,值得深思。
李瀷“八哀解”条云:“‘愁寂’,兵少也。‘高视’,气骄也。‘平生、零落’,‘白羽扇、蛟龙匣’,皆互文,言平生之白羽扇、蛟龙匣皆零落也。凡杜作多此例。‘箱箧’,用乐羊夸书事,言必有直笔,可以洗涤其谗谤也。‘疲苶’,勤劳也,言尽瘁者更无其人也。”[5]3683这段话是对《故司徒李公光弼》个别词语、诗句的解读,细腻而精准,涉及“胡骑攻吾城,愁寂意不惬”、“高视笑禄山,公又大献捷”、“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龙匣”、“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箱箧”、“疲苶竟何人,洒涕巴东峡”等诗句。李瀷的解读精准而富有新意,有中国诗家所未曾论及之处。李瀷对“愁寂意不惬”、“高视笑禄山”缘何“愁寂”、“高视”的分析,颇为地道,认为是因“兵少”而“愁寂”,因“气骄”而“高视”。李瀷指出“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龙匣”中的“平生”、“零落”、“白羽扇”、“蛟龙匣”是互文见义,实属新见。中国诗家在解读这两句诗时,更多引用典籍印证诗中所涉及的史实,而没有对诗句给予细读,如仇兆鳌《杜诗详注》引用了诸多杜诗注本及典籍来诠释“平生”、“零落”两句:“裴启《语林》:诸葛武侯以白羽扇指麾三军。《杜臆》:羽扇零落,惜不尽其用也。《西京杂记》:汉帝及诸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为铠甲,连以金缕,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蛟龙玉匣。朱注:《霍光传》:赐璧珠玑玉衣,梓宫。则人臣亦可称蛟龙匣也。”[5]1382“将来洗箱箧”句,李瀷认为是用了战国时期魏国将领乐羊的典故,乐羊因大败中山国而成名。相传乐羊攻克中山国后向魏文侯报告时面露骄傲的神态,魏文侯察觉后,命令主管文书的官吏搬来两箱子书信,书信都是责难攻打中山国这件事的。乐羊羞愧跪谢。唐代诗人周昙《春秋战国门·乐羊》有诗句有云:“盈筐谤书能寝默,中山不是乐羊功。”李瀷认为用此典故是有直笔之用,“可以洗涤其谗谤”,[5]3683联系上一句“直笔在史臣”,李瀷的阐释是合情合理的。
再看李瀷对《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诗的解读,李瀷释“开口取将相,小心事友生”两句为“言望实如此,将一开口而将相可取,然犹小心而接人也如此”。[5]3683“飞传自河陇,逢人问公卿。不知万乘出,雪涕风悲鸣”四句,李瀷认为是“言当时公卿孰执羁靮而从于西,孰奉太子而留耶?继云‘万乘出’在何地,宁不悲乎?”[5]3683尤其是对“不知万乘出”中“出”字的解读,颇见功力,“‘出’如‘天王出居’之‘出’。《曲礼》云:‘天子不言出。’‘出’字极有力矣。”[5]3683“匡汲俄宠辱,卫霍竟哀荣”二句,李瀷认为是指“乱既平,或有如匡汲之宠辱者,如卫霍之哀荣者,独武安享禄位也。”[5]3683“京兆空柳色,尚书无履声。群乌自朝夕,白马休横行”四句,李瀷认为是“谓武宜在帝左右补阙拾遗,而出在外藩,若朝廷无人然也”[5]3683。翻阅中国诸家注本,如仇兆鳌《杜诗详注》、钱谦益《钱注杜诗》等,对《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诗的解读,都是引用典籍以正史实,如仇兆鳌《杜诗详注》释“匡汲俄宠辱,卫霍竟哀荣”二句,引用了《新书》《匡衡传》《汲黯传》《卫青传》《霍去病传》等关于严武、匡衡、汲黯、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史实,没有做过多阐释,不如李瀷的解读详尽。
相较中国诗家对《八哀诗》的解读,李瀷的阐发、诠释,无疑能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诗意。文本细读的一个维度,即是词语细读,而精准的词语细读之后,就会产生对整句诗、整首诗的审美感悟,李瀷的解读应该说更具文学色彩与诗情意蕴。
二、对杜诗词语的考释
古代诗人在用字造词方面非常考究,尤其是杜甫,更是精益求精,尝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诗的遣词造句引起了历代诗家的热烈讨论,并从各个角度进行注释、考辨。李瀷即对杜诗的单字或者词语作了深层次的注释,并且根据自己的审美鉴赏力,大胆指出前代注家的错误或不足。试举几则诗话材料予以分析。
“沉云黑”条:
古书之脱误多矣,经传犹然,况诗文之类耶?杜子美《秋兴》诗一首述昆明池物色,而其一联云:“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云”恐是“灰”字之讹也。若作“云”字,读不成说。今以古诗证之。薛道衡《游昆明池》诗:“鱼潜疑刻石,沙暖似沉灰。”虞茂诗:“支机就鲸石,拂镜沉池灰。”元行恭诗:“衣共秋风冷,心学古灰沉。”李百药诗:“大鲸方远击,沉灰独未然。”宋之问诗:“象溟看浴景,烧劫辨沉灰。”此皆咏昆明而用“劫灰”事。灰本色黑,《西京赋》所谓“黑水玄址”是也。意者“灰”字草样与“云”相类,故传写之错而然耳。且莲花出有红,而蕊无红。粉出于蕊,安有红粉?温庭筠诗云“药粉染黄那得深”,可以见矣。[5]3690—3691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句出《秋兴》(其七)。李瀷认为杜甫“波漂菰米沉云黑”中的“云”当为“灰”字之讹,并取薛道衡《秋日游昆明池诗》、隋代虞世基《赋昆明池一物得织女石诗》、元行恭《秋游昆明池》、唐代李百药《和许侍郎游昆明池》、宋之问《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等诗加以证实。“劫灰”,本谓劫火的馀灰,典出晋干宝《搜神记》(卷一三)。仇兆鳌《杜诗详注》对“波漂菰米沉云黑”句注释曰:“赵次公曰:沉云黑,言菰米之多,一望黯黯如云之黑也。鲍照诗:沉云日夕昏。蔡邕《月令章句》:阴者,密云也,沉者,云之重也。沉云意本此。王褒诗:塞近边云黑。”[6]1495仇兆鳌对“露冷莲房坠粉红”句的注释引用了他人之注:“邵注:莲初结子,花蒂褪落,故坠粉红。”[6]1495—1496仇兆鳌还借用了钱谦益的评论:“菰米莲房,此补班张所未及,沉云坠粉,描画素秋景物,居然金碧粉本。池水本黑,故赋言黑水玄址,菰米沉沉,象池水之玄黑,乃极言其繁殖也。”[6]1496仇兆鳌的引注也颇具说服力,而李瀷的猜想更是大胆而有富见地,也是历代注家所未涉及的。细察,李瀷的想法有其合理成分,如果从诗句对仗的角度考虑,“沉灰黑”对“坠粉红”似乎更为妥帖。李瀷之说,非常具有学术价值,为我们今后注释杜甫此诗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夫家”条:
杜诗:“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若谓其夫之家,则不成说。子美好用配语,以“城阙”为对,谓“夫”与“家”也。《周礼》:“媒氏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谓男之无家,女之无夫也。又:“载师之职,出夫家之征”,郑注云:“一夫百亩之赋,一家力役之征。”此谓租庸也。杜之意未知谁取,而其为“夫”与“家”,则不可改评。[5]3685
诗句出自《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李瀷认为“鞭挞其夫家”中的“夫家”,不是偏正词组,即“夫之家”的意思;而是并列词组,即夫和家同义,构成一个词语,与后面的“城阙”搭配。李瀷又引用《周礼》“媒氏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载师之职,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时徵其赋”等典进一步论证,很具说服力,这在中国诸家注本是没有提到的,属于李瀷的创见,可备一说。
“醉碧桃”条:
杜诗:“九重春色醉仙桃。”《虞注》以为桃熟烂红之喻。余考许浑《骊山》诗:“闻说先皇醉碧桃。”又《洛城》诗:“独自吹箫醉碧桃。”章孝标《送金可纪还新罗》诗:“蟠桃花里醉人参。”盖“醉”指人言者也,仙味入口,熏香浃骨,便是醉意,何必酒然后方然耶?[5]3691
诗句出自《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元代虞伯生《杜律虞注》认为,“醉仙桃”比喻的是桃子熟烂而红,李瀷则认为“醉”的主语是指人,不是桃子。为此,李瀷列举了许浑《骊山》《洛城》与章孝标《送金可纪还新罗》等诗加以佐证。在李瀷看来,仙桃入口,熏香浃骨,人因此有了醉意,这种阐释,诗意浓郁而优美。
“秋兴诗”条:
杜甫《秋兴》诗,解者多牵强。余谓“他日”者,如“他日未尝学问”之“他日”,谓“前日”也。“丛菊两开”则再经秋矣。对花陨泪,一如前日,则未还可知矣。“每依南斗”云者,南斗至秋后,则初昏在中天,夜半而后始西坠。甫日斜而东望,每至于夜半而后已,故曰“每依南斗望京华”也。[5]3690
诗句分别出自《秋兴》其一“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和其二“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一作北斗)望京华”以及其五“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他日未尝学问”句出《孟子·滕文公上》“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李瀷对“丛菊两开他日泪”中词语及句意的解释都是符合诗意与诗境的。“丛菊两开”,指诗人于永泰元年(765年)离开成都,原打算很快出峡,但这年留居云安,次年又留居夔州,见到丛菊开了两次。“他日”,即往日。去年秋天在云安,今年此日在夔州,均对丛菊,故云“两开”。“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华”句,意为在夔州高城上迎来落日,当北斗星出现的时候,诗人按照它的方位来寻找长安的所在。李瀷运用了天文学的知识,以北斗星不同时间所处方位的不同,体现出诗人驻望时间之久,对家国感情之深。
三、以比较批评论杜诗
比较批评作为传统批评方法之一,在文学批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较批评“是指运用对比或类比的手法,对所品赏与论评对象的审美意味、风格特征、创作技巧、成就高下等进行比照、辨析的批评形式”[7]94。比较批评最早出现于汉代,是针对赋体文进行的。扬雄《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此句强调的是不同身份者创作的赋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之后,比较批评作为一种重要方法伸展到了诗文批评,得到了诗家们的广泛采用。古代诗家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甚多,如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云:“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态,太白多天仙之词,退之犹可学,太白不可及也。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气吞曹刘,固无与为敌。”[8]453清代赵翼《瓯北诗话》卷一“李青莲诗”条:“(李白)若论其沉刻则不如杜,雄鸷亦不如韩。然以杜、韩与之比较,一则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则不用力而触手生春,此仙与人之别也”[9]3,如此等等。可以说,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于中国历代诗学著作典籍中比比皆是,蔚为大观。
李瀷也喜欢用比较批评法论诗,在论述杜甫时,更是大量运用此手法,在比较中见杜诗特色。如“李杜韩诗”条,李瀷认为李白的诗歌“比如玉壶明珠,交辉几席;祥鸾瑞凤,腾翥轩阶。复安容一点尘飞到门屏耶。”[5]3803杜甫的诗歌,“却是句句气力,字字精神,如冲车拐马,方隅钩连,但欠参伍机变之术。若三大篇溶溶涆涆,无容议论。至《八哀诗》亦恐有累句间之,只是江汉之火,腐胔不恤也。”[5]3803韩愈的诗歌,“笔力往往有冗卑下乘之语,然细详之,非退之之不及,乃故为此延绵气脉,以待激昂奋发。比如山势逶迤,峻必有低,过峡则徒崦,天秀自露。不然,只剑脊鳝走,不与化工相肖也。如是看,方得退之圈套。”[5]3803—3804把不同风格的三位伟大诗人放在一组,以意象批评、比较批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阐释,其各自的风格特点通过对比,非常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直观性十分强烈。
再看“退之效李杜”条:“韩退之一生慕效李、杜,然比诸李风神不足,比诸杜气骨不足。李诗:‘回飙吹散五峰雪,往往飞花落洞庭。’韩则曰:‘动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效不得也。杜诗:‘悲台萧瑟石笼从,哀壑杈桠浩呼汹。’韩则曰:‘山狂谷根相吐吞,风怒不休何轩轩。’效不得也。”[5]3831此条虽重点在说韩愈对李杜的学习,但杜诗的特色也在比较中得以彰显。相较于韩诗,杜诗更见气骨。李瀷所谓之“气骨”,当为文气、风骨两个诗学批评理论范畴之结合体。文气理论最早见于曹丕《典论·论文》,“风骨”原为品评人物的术语,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把它移用于文学批评上。李瀷则创造性地合二为一,也切中杜诗肯綮。
他如“屈原歌辞”条:
屈原云:“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此千古悲壮感慨。骚人韵客,慕效不得也。李白发之于诗云:“昨夜秋声阊阖来,洞庭木落骚人哀”,杜甫发之于律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惟此二句为近之。盖高秋凉风,叶下波涌,皆凄断世界,妆点不过数字,而令人魂销。白则言风来木落,则水波包其内,风神动人;甫则只言江水滚滚,亦带波浪,意思在中,筋骨可敬。然终不若原之彻肝透膈,尽情而哀诉。此古今之异,人情之不同也。[5]3728
李瀷把屈原、李白、杜甫三人以“秋风”、“落叶”为意象的诗作比较,指出屈原《九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句,“妆点不过数字,而令人魂销”,后李白与杜甫纷纷仿效,李白“昨夜秋声阊阖来,洞庭木落骚人哀”(《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句、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句虽“近之”,但“终不若原(屈原)之彻肝透膈,尽情而哀诉”,根源在于“古今之异,人情之不同”。这种比较,优劣高下力见,极具审美穿透力。
四、李瀷论杜诗的特点
李瀷对杜诗的审美批评,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无论是细读杜诗、注释杜诗,还是以比较批评法分析杜诗,都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尤其是注释杜诗,更具学术价值与意义。
第一,在各家注杜的前提下,肯定正确的释义,并以非凡的学术勇气,指出并纠正了许多前人注杜中的纰漏甚至错误,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见解。如“云霾日抱”条,杨用修认为杜甫《白帝城最高楼》颈联“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是“形容疑似之状”[5]3815,与杜甫《玉台观》颔联“江光隐见鼋鼍窟,石势参差乌鹊桥”用法相同,都是形容若隐若现之态,摹写登高临深时所见的一种迷离恍惚之景。李瀷却不赞同杨用修的说法,他认为:“余谓深山大泽龙虎之卧所,水渚沙际鼋鼍之所游,此与歇后体相似。盖谓云霾山泽之间,日抱沙水之际,非真有此物在也。”[5]3816为了论证的说服力,李瀷又举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句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这两句诗“此以‘兄弟’为‘友于’,则‘肺腑’者即亲戚。《汉书·赵王传》‘臣得蒙肺腑’是也”[5]3816,并指出古人此用法很多,没有他意,是后人穿凿附会了:“古人用字或多此例。如乌鹊桥、鼋鼍窟,不过谓高者上干霄汉,下者深暎坎□,岂有他意?语非隐晦,而后人凿教,使深异矣。”[5]3816这些见解有别于前代注家,虽然合理性有待商榷,但却是欣赏者自己的独得新见。
第二,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实证的方法考究杜诗,并提出了注释杜诗的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法——“以杜释杜”。对于如何注释杜诗,采取何种方法更能诠释好杜诗,是历代诗家十分关注的。仇兆鳌曾大量采用以《诗经》注杜诗的方法,据一些学者统计,仇兆鳌《杜诗详注》以《诗经》注杜诗者约有580条。[10]22朝鲜李朝时期李植(1584—1647年)则以批解的方式注杜诗,其《杜诗批解》“是朝鲜文人批解、注释杜诗的第一部个人著述,被誉为朝鲜人研读杜诗的入门要籍”[11]102。李瀷则推崇“以杜释杜”,即拿杜甫本人诗作来佐证、诠释杜诗。如“以杜释杜”条:
杜诗:“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盖清宵立、白日眠,谓夜不能寐而书或惰睡也。思家、忆弟即互言也,忆弟独不可以宵立,思家独不可以日眠耶?其善若曰:“思家忆弟之故而或夜立,或书眠也。”论诗必于其人究之,方见造意之如何。又如:“昨夜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谓玉鱼、金碗始蒙葬地,终出人间也。又如:“炙背可以献天子,美芹由来知野人”,“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龙匣”,此类甚多。读者宜以杜诗释杜。[5]3703
“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句出杜甫《恨别》,“昨夜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句出杜甫《诸将》(其一),“炙背可以献天子,美芹由来知野人”句出杜甫《赤甲》,“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龙匣”句出杜甫《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李瀷指出“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两句诗存在互文见义的情况,而论诗就要做到“必于其人究之,方见造意之如何”,[5]3703于是,他引用了杜甫其他存在此类情况的诗句来进一步印证,提出“读者宜以杜诗释杜”。[5]3703李瀷的“以杜释杜”,实乃真知灼见,值得现今学界注释杜诗以及注释一切古代诗词者加以借鉴。
李瀷的杜诗研究,不仅促进了杜诗的海外传播与影响,也为今天进一步研究杜诗提供了域外的诗评视角。参照李瀷对杜诗的论评,尤其是其中那些发中国诗家之所未见,有创见性的见解,无疑会加深对杜诗的理解、认识,其意义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1] 朱林杰.韩国古代的杜诗研究[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2] 邝健行,陈永明,吴淑钿.韩国诗话论中国诗资料选粹[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 全英兰.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之影响[J].杜甫研究学刊,2003,(1).
[4] 朱东润.杜甫叙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蔡美花,赵季.朝鲜诗话全编校注(第五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6]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 胡建次.中国古代诗歌比较批评的承传[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8]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 赵翼.瓯北诗话[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10] 曾亚兰,赵季.说仇兆鳌以诗经注杜诗[J].杜甫研究学刊,1999,(4).
[11] 左江.异域之眼看杜诗——李植《杜诗批解》评语析论[J].深圳大学学报,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