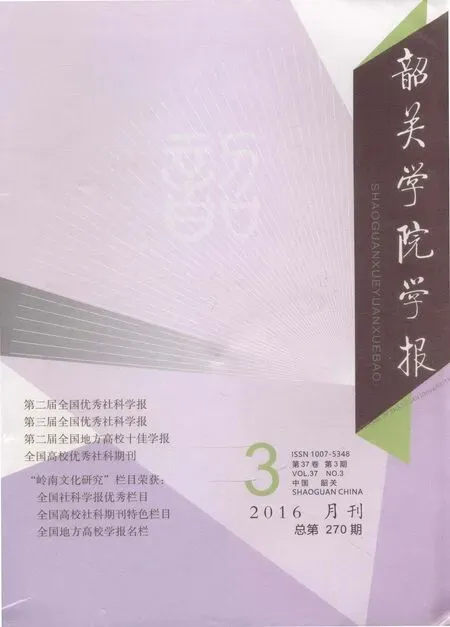从戴嵩画牛看中国古代绘画中的误笔
2016-04-13韩少春伊密里欧学院教育学院菲律宾马尼拉1000
韩少春(伊密里欧学院教育学院,菲律宾马尼拉1000)
从戴嵩画牛看中国古代绘画中的误笔
韩少春
(伊密里欧学院教育学院,菲律宾马尼拉1000)
摘要:戴嵩是唐代著名的画牛大家,与韩干画马并称于世,向有“韩马戴牛”之誉。戴嵩的传世名作《斗牛图》中的“斗牛调(举)尾”,学界一直将其视为误笔,但是由一系列的考证可知,这一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并且由此我们还可进一步认为戴嵩的画牛之误乃属艺术的自觉,与中国绘画史上的绝大多数误笔一样,是作家天才的创造。把它们视为作家对生活的失察,有违于我国古代艺术创作实际。
关键词:戴嵩;斗牛;中国古代绘画;误笔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绘画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它以独特的神韵享誉世界画林,与西方绘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得再明确一点,就是中国绘画并不像西方绘画那样追求形象,追求逼真,追求与自然物象、现实世界的高度相似;而是崇尚写意,强调象征,重视意境,重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表现与展示。正因为追求的是与人的精神境界的合一,而非与现实物象的合一,所以许多时候画家的摹写便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生活的实际,出现了所谓的有悖科学常识的疏漏,形成了令人遗憾的“误笔”。如南朝张僧繇的《群公祖二疏图》,画的是京师诸贤饯别功成身退、辞官归乡的二疏,而图中随从的士兵穿的却是只有乡间人才穿的草鞋。唐代阎立本的《昭君图》,画的是昭君出塞,可是昭君头上戴的却是直到隋代才有的帷帽。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画的是群鹤振翅高飞的景象,可是却把仙鹤飞行时总是笔直前伸的脖子画成了弯曲的脖子等等。那么,对于这些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呢?笔者认为如果把它们全都视为误笔,显然太武断。艺术创作固然离不开现实,但绝不等于是现实的照搬,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古代绘画中,那些绝大多数的所谓“误笔”,实际上都是作家有意的创造,体现了作家自觉的审美追求,说它们源于作家对生活的失察,是有违于我国古代艺术创作实际的。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不妨以戴嵩画牛为例,作一深入的探讨。
一、戴嵩“斗牛之误”以及前人对它的评价
我们知道,戴嵩是唐代非常著名的画家,曾拜晋国公韩滉为师,韩滉镇守浙西时署为巡官。擅画田家、川原之景,尤以善写水牛之状著名。与善于画马的韩干并称于世,号曰“韩马戴牛”。史载戴嵩师从韩滉学画,“师滉画皆不及,独于牛能穷尽野性,乃过滉远甚”,以至于“世之所传画牛者,嵩为独步”[1]151,就连他的老师韩滉也不得不“从之受其法”[2]44,转过来以他为师。这充分说明戴嵩在画牛方面确非浪得虚名。
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正是这个在画牛方面超出时人、独树一帜的戴嵩,却在他的传世名作《斗牛图》中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如北宋苏轼《东坡志林》曰:“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斗牛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对此,苏东坡评价说:“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3]看来,他也认为戴嵩的《斗牛图》在牛尾的处理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又,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曰:“马正惠公(马知节)尝珍其所藏戴嵩《斗牛图》,暇日展曝于厅前,有输租氓见而窃笑,公疑之,问其故。对曰:‘农非识画,乃识真牛。方其斗时,夹尾于髀间,虽壮夫臂力不能出之。此图皆举其尾,似不类矣。’公为之叹服。”[4]曾敏行与苏轼乃同一时代人,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对戴嵩的《斗牛图》发表意见,但是从其对这一故事的叙述语气看,他对马知节的“叹服”显然也是认同的。尽管苏、曾二人所述故事里,所涉人物颇有不同,一为杜处士与牧童,一为马知节与输租氓,但是在对戴嵩所画斗牛究竟应当是“掉(举)尾”还是“夹尾”的态度上,他们的看法显然完全一致。
当然,关于“斗牛掉(举)尾”的故事还有另一版本,在这个版本里出现误笔的画师不是戴嵩而是厉归真。其具体记载见于北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马正惠尝得斗水牛一轴,云厉归真画,甚爱之。一日展曝于书室双扉之外,有输租庄宾适立于砌下,凝玩久之,既而窃哂。公于青琐间见之,呼问曰:‘吾藏画,农夫安得观而笑之?有说则可,无说则罪之。’庄宾曰:‘某非知画者,但识真牛。其斗也,尾夹于髀间,虽壮夫臂力不可少开。此画牛尾举起,所以笑其失真。’”对此,郭若虚评价说:“愚谓虽画者能之(至)妙,不及农夫见之专也。擅艺者,宜所博究。”[5]如上所说,戴嵩乃是唐代人,而这则故事中的厉归真却是五代人,依常理而论,戴嵩与厉归真之中必有一误。那么,对此我们又如何看呢?笔者认为虽然郭若虚生活的年代与苏轼、曾敏行相当,但厉归真却以画虎著称。史载他“尝作棚于山中大木上,下观虎,欲见真态,又或自衣虎皮,跳踯于庭,以仿其势”,因此所画之虎“毛色明润,其视眈眈有威加百兽之意”[6]。尽管他也善于画牛,但画牛并不是他的专长,所以两相比较,我们觉得还是应以苏轼、曾敏行所述更为可信。另外,我们还需注意的是,虽然郭若虚对于《斗牛图》的作者记载有误,但是与苏、曾二家所述相较,他们所要揭示的道理却完全是相同的,即艺术创作必须做到与现实物象高度一致,作家如不勤于观察生活,是一定会闹出笑话的。
二、从戴嵩画牛的虚与实看其“斗牛之误”的艺术性
那么,对于戴嵩“斗牛掉(举)尾”的“误笔”,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呢?难道真要将其视为对于现实生活的失察吗?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是很不恰当的。之所以这样说,原因主要有四:
第一,戴嵩有着十分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这一点相关文献中记载得很清楚。如由北宋朝廷组织编著的《宣和画谱》,在解释作为老师的韩滉,其画牛技艺何以不及其徒弟戴嵩时说:牛乃“田家川原”之畜,“自是廊庙间,安得此物宜?滉于此风斯在下矣”[1]151。它的意思是说牛虽然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家畜,但它总是生活在田家场院、川原之上,朝廷廊庙中根本不见此物,韩滉作为朝廷大员,他又怎么会经常与它接触呢?由于不像戴嵩或为布衣或为下层官吏,每每出入于乡村田园,所以他的画牛水准赶不上戴嵩就自然不足为怪了。由《宣和画谱》这一分析不难看出,戴嵩有着十分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应当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戴嵩对于生活的观察十分细致。这在相关文献中记载的也同样很清楚。如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评戴嵩画牛说:“两目微红,凡戴牛皆然。”[7]又,北宋董逌《广川画跋》说:戴嵩画牛“妙于形似”,“鼻上故作润泽”,“得其性相尽处,《画录》至谓牛与牧童点睛,圆明对照,形容著目中。至饮流赴水,则浮景(影)见牛唇鼻相连。”[2]44又,明汪珂玉《珊瑚纲》说:“余所存戴嵩牛,牛目中有牧童影,犹足移夜郎王也。”[8]又,清松年《颐园论画》说:“戴嵩画百牛,各有形态神气,非板板百牛堆在纸上。牛旁有牧童,近童之牛眼中尚有童子面孔,可谓工细到极处矣。西洋尚不到此境界,谁谓中国画不求工细耶?”[9]由此可见,戴嵩画牛是非常细腻的。他不仅能展现水牛鼻子的“润泽”、眼睛的“微红”、水牛瞳仁中牧童的投影,而且连水牛饮水时唇与唇、鼻与鼻相连的倒影也能描绘出来。所有这些,如果离开了对生活的细微观察,离开了对生活的亲身体验,显然是很难达到的。
第三,戴嵩画牛非常专一,除水牛之外,几乎别无所涉。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他“不善他物,唯善水牛”[10],应该说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又,北宋所编《宣和画谱》说:戴嵩之画,“今御府所藏三十有八:春陂牧牛图一,春景牧牛图一,牧牛图十,渡水牛图一,归牛图二,饮水牛图二,出水牛图二,乳牛图七,戏牛图一,奔牛图三,斗牛图二,犊牛图一,逸牛图一,水牛图二,白牛图一,渡水牧牛图一。”通览所列,不难发现戴嵩所绘竟然毫无例外全是牛,这也再度说明戴嵩画牛确是非常专一的。也正因如此,所以《宣和画谱》评价说:“嵩以画牛名高一时,盖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苟致精于一者,未有不进乎妙也。如津人之操舟,梓庆之削锯,皆所得于此。于是嵩之画牛亦致精于一时也。”[1]151这一见解对我们正确体认戴嵩的画风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戴嵩画牛并不一味追求形似,虚实结合、形神相备才是他的主要特色。有关这一点相关文献中也同样记载得很充分。如明李日华《六岘斋笔记》说:“戴嵩放牧图,作三子母牛,一牧儿踞其背,一壮者牵牯,笔墨极草草,得简古之趣。衰柳四五株,尤横斜纵恣有态。固知象物者不在工谨,贵得其神而捷取之耳。”[11]又,明高濂《燕闲清赏笺》说:“戴嵩雨中归牧一图,上作线柳数株,丝丝烟起。以墨洒细点,状如针头。俨若一天暮霭,灵雨霏霏。竖子跨牛,奔归意急。此皆神生状外,生俱形中,天趣飞动者也。故唐人之画,为万世法。然唐人之画,庄重律严,不求工巧,而自多妙处,思所不及。后人之画,刻意工巧,而物趣(趋)悉到,殊乏唐人天趣浑成。”[12]从这两则记述,不难得知戴嵩画牛确非一味追求形似,换句话说也即是他并不片面追求与现实物象的高度合一,虚实结合、形神兼顾才是他真正心仪的境界。对于这一点我们应高度重视。
如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戴嵩既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画牛又那么专注,对于水牛的观察又那样细致,说他不了解水牛相斗“夹尾于髀”的习性,这样的论断显然有违常理。第二,戴嵩画牛既然有虚有实、形神兼顾,并不片面追求“象物”的“工谨”,也即物象的形似,并不“刻意工巧,而物趣(趋)悉到”,那么他画的牛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之牛存在出入自是难免的。第三,既然戴嵩画牛并不完全死守与现实合一,并不把照搬现实当作艺术创作的至上法则,那么为了更好地展现斗牛勇武的神采,改其“夹尾于髀”而为“掉(举)尾而斗”,这也同样合乎情理。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说戴嵩所画“山泽水牛之状”,常常能够“穷其野性筋骨之妙”[13]。如果一味唯实是求,以现实物象为最高模本,而不能将作家的精神风貌、主体个性投注到现实物象中,那么要想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显然是根本无从实现的。
三、戴嵩“斗牛之误”与王维“花草之误”的相通性
为了进一步彰示戴嵩“斗牛掉(举)尾”的自觉性、艺术性,我们不妨把戴嵩的这一所谓“误笔”与王维的同类之“误”作一对比。由现在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可以看出,王维虽被奉为中国南宗画派的鼻祖,但是他的画作中同样存在着一般百姓也能轻易指出的“错误”。比如他的名作《袁安卧雪》中,他竟无视芭蕉生长于夏的习性,把它画在了大雪中,并且因为这一“误笔”,还使《袁安卧雪》进而获得了一个新名:《雪中芭蕉》。再如桃、杏、蓉、莲也属不同季节的花卉,可是在王维的画作里却常常将它们画在一起。
那么,对于王维的这些“误笔”,前人又是如何看呢?笔者认为,相对于戴嵩的饱受质疑,学者们对王维的态度应当说是相当客观的。固然,对于王维的这些“误笔”,前代学者也有不少批评,如唐代张彦远评王维之画说:“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14]107又,宋人朱熹评王维的《雪中芭蕉》说:“雪里芭蕉,他是会画雪,只是雪中无芭蕉,他自不合画了芭蕉。人却道他会画芭蕉,不知他是误画了芭蕉。”[15]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有许多学者对王维的这些“花草之误”给予了热情的肯定。这与戴嵩的大受指摘,饱受揶揄显然是大不相同的。如宋释惠洪《冷斋夜话》说:“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诗(持)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16]又,宋沈括《梦溪笔谈》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此真为识画也。”[14]107又,明汤显祖《答凌初成》说:“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不佞哑然笑曰:‘昔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王摩诘冬景也。’”[17]又,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说:“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18]等等。
水牛相斗本是“夹尾于髀”的,而戴嵩却将它画成了“掉(举)尾而斗”;芭蕉本是生长于夏季的,而王维却把它画在了大雪中;桃杏蓉莲也是开在不同时段的,而王维却常将它们画在一处。彼此对照,不难看出以上这些所谓常识性的“错误”,历史上竟有那么多学者为之辩护,而对戴嵩却是一片批评之声,如此之大的反差,背后的缘由究竟何在呢?依常理而论,这恐怕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王维是盛唐诗坛的大家,也是南宗画派的鼻祖,像这样的人物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这显然是后世大多数学者都不愿相信的。第二,虽然水牛相斗“夹尾于髀”,芭蕉只能生长于夏季,桃杏蓉莲异时而开,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物,但是如果更严格一点说,后二者的常识性无疑还要更强一些。作为盛唐诗坛的大家,南宗画派的鼻祖,王维怎么会连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也不知道呢?这显然是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基于此,我们认为说王维的“花草之误”乃是缘于艺术自觉的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而讥刺王维“不知寒暑”的观点反而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王维的“花草之误”属于艺术的自觉,戴嵩的“斗牛之误”是不是同样也可以这样看呢?笔者认为它们是完全相通的。诚然两牛相斗并不如花草生长那样常见,但是如上所言,斗牛之事对于专以画牛为务的戴嵩来说,同样应当是司空见惯的。既然同样是司空见惯,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说王维之误是艺术的自觉,而戴嵩之误是对生活的悖离呢?这显然同样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四、余论
通过上文一系列论述,不难看出戴嵩的“斗牛调(举)尾”是对生活的失察之说确乎很难说得通。戴嵩之所以不顾生活的实际而作这样的处理,一个更为可能的原因是:只有如此才能展现水牛的勇武之姿,规避水牛相斗“夹尾于髀”的丑态,更好地彰显其昂扬向上、奋发无畏的精神。如果再进一层说,我们还可绎出如下结论:即不仅戴嵩的画牛之误是出于艺术的自觉,就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绝大多数误笔,我们也同样应以这一观念视之。举例来说,如上文所举张僧繇的《群公祖二疏图》,有人指责他图中的士兵不应穿草鞋,而实际上张僧繇之所以这样做,更有可能是希望通过只有乡间人才穿的草鞋,为疏广、疏受叔侄二人的功成身退,辞归乡里,不以贫贱为耻的高风亮节作陪衬。再如宋徽宗的《瑞鹤图》,有人指责他把飞鹤的脖子画弯了,而实际上这恐怕也是他感到飞鹤脖子笔直前伸不雅致。再如阎立本的《昭君图》,有人指责昭君不应戴隋帽,而实际上阎立本之所以这样画,或许也是因为感到隋帽较之汉帽更能展现昭君的丰姿与魅力。即使退一步说不属于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肯定阎立本在当时就没有认识到隋汉之异。因为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由于一时之间无从察知汉帽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才权以隋帽代之。众所周知,艺术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艺术家并不等于考古家,所以我们绝不能要求艺术家作画时,对其所涉及的一切物象都要像考古家那样进行一一考证。就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对于汉唐宋明的服饰差异并不怎么计较,对于阎立本的“隋帽汉戴”,我们也同样不能以“失察”论之。
参考文献:
[1]无名氏.宣和画谱[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2]董逌.广川画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苏轼.东坡题跋[M].北京:中华书局,1985:97.
[4]曾敏行.独醒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6.
[5]郭若虚.图画见闻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242.
[6]李廌.德隅斋画品[M].北京:中华书局,1985:6.
[7]周密.云烟过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1.
[8]汪珂玉.珊瑚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761.
[9]松年.颐园论画[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88.
[10]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324.
[11]李日华.六岘斋笔记[M].上海:中央书店,1936:9.
[12]高濂.燕闲清赏笺[M].成都:巴蜀书社,1985:65.
[13]朱景玄.唐朝名画录[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26.
[14]沈括.梦溪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3287.
[16]释惠洪.冷斋夜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20.
[17]蔡景康.明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86.
[18]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68.
(责任编辑:廖筱萍)
An Argument on the Clerical Errors of Chinese Ancient Paintings in the Case of Dai Song's Bull Picture
HAN Shao-chun
(School of Education,Emilio Aguinaldo College,Manila 1000,Philippines)
Abstract:As a great painter who was skilled in drawing bulls especially,Dai Song was as famous as Han Gan who was particularly good at drawing horses. Though many scholars regarded it as a clerical error that bullfights held their tails aloft in Dai song's valuable painting Bullfights,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idea is untenable by a series of researches. From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not only Dai Song's clerical error drawing bullfights but also most ones of Chinese ancient paintings were all intentional designs which demonstrated their artistic consciousness. It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ancient artistic creations if we regard them as oversights of livelihood.
Key words:Dai Song;bullfight;Chinese ancient painting;clerical errors
中图分类号:J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16)03-0114-05
[收稿日期]2015-12-16
[作者简介]韩少春(1989-),男,河南新野人,伊密里欧学院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