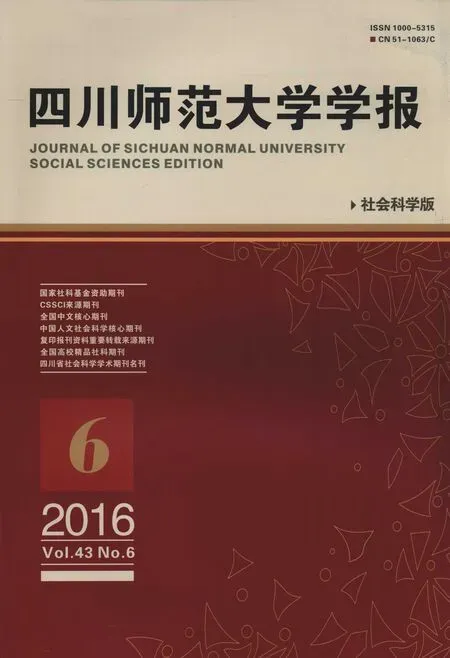南宋中期朝廷对四川的经营:以吴挺事迹为例
2016-04-13王化雨
王 化 雨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 610066)
南宋中期朝廷对四川的经营:以吴挺事迹为例
王 化 雨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 610066)
吴挺是南宋孝、光两朝四川军政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具有由地方到中央、再由中央到地方的特殊经历,取得过不俗的治军业绩,也遭受过不少的非议。透过他的一生,可以发现,南宋中期宋廷对四川的控御力度在不断增强,曾经对宋廷统治构成挑战的地方武将逐渐被改造为朝廷在四川的代理人。从经营四川的手段和效果来看,孝、光两朝的中枢决策者是颇有高明之处的。
南宋;朝廷;四川;吴挺
南宋时期,四川①作为抵御北敌的屏障,战略地位空前提升。然该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宋廷在对其实施统治时面临诸多困难,不得不将部分权力下放,结果造成了以吴氏家族为代表的地方武将势力崛起。
吴氏家族自吴玠起,三世统军,在四川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研究南宋四川与中央的关系,绕不开对吴氏家族的讨论。对此问题,学界已做了较多分析②。然既有研究存在用力不均的缺陷:吴氏基业的开创者吴玠、吴璘以及掘墓人吴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论述,而对该家族第二代掌门人吴挺的研究则略显单薄。吴挺既无太多显赫战功,又无叛宋自立这样引人注目的举动,容易遭到研究者有意无意的忽视,实属情有可原;但身为孝、光两朝手握四川兵符近20年之久的大将,其在南宋军政史上的重要性是无法否认的。若能对他的事迹全面考述,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吴氏家族的认识,更有助于我们对南宋中前期四川政局的理解。笔者特撰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 从地方武将到三衙管军
吴挺为吴璘第五子,生于绍兴七年(1137),在吴璘诸子中,才干最为突出。十七岁,吴挺任兴州御前驻扎后军准备将,不久升中军第一正将[1]11421。兴州(今陕西略阳)是南宋四川战区主力部队的屯驻地,吴挺年纪轻轻,即被授以如此要职,足见乃父对他的器重。吴璘显然想以此对吴挺加以历练,为他将来接掌兵权作准备。
绍兴二十八年(1158),吴挺受吴璘委派,前往临安奏事,得到高宗召见,被授以两浙东路兵马都监兼御前祗侯之职[1]11421。案:吴氏兄弟自绍兴初年便一直统帅川陕大军。绍兴和议缔结之后,宋廷鉴于四川的特殊位置,没有如对待张、韩、岳那样收夺吴璘之兵权,但对他的戒惕却一直存在。朝廷具有实力优势,吴璘要想巩固在四川的地位,就必须设法增加朝廷对自己的信任,派吴挺赴行在奏事,便是他显示忠诚的手段。而宋廷将吴挺留在东南,看似重用,实有用他为人质以制约吴璘之意。可以说,吴挺早年的这番经历,折射出宋廷与四川武将之间的微妙关系。
吴挺在东南任职的时间并不长。绍兴二十九年(1159)前后,金主完颜亮的侵宋图谋逐渐显现。高宗虽痴迷于和议,也不能不为可能爆发的战争预作准备。为协助吴璘整军备战,他将吴挺改任为利州路兵马钤辖,令其重返四川;不久,吴挺又被改任为利州东路御前前军同统制,成为四川大军的重要将领[1]11421。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军对四川发动进攻。吴璘被任命为四川宣抚使,负责四川防务。吴挺以中军统制的身份,随父出征。初上战场,吴挺表现出将门虎子的风范。在德顺(今宁夏隆德)之役中,他身先士卒,击败金军的先遣队,后又以所部兵马为饵,将金军主力引入伏击圈,为攻克德顺立了大功;在收复巩州(今甘肃陇西)的战事中,他也有出色表现[2]152-154。
对于吴挺在宋金之战中的表现,论者多给予极高评价。平心而论,相较于其伯父和父亲,吴挺在战绩方面还是颇有不及的。首先,吴玠、吴璘都曾担任过方面军统帅,而吴挺只是其父麾下的偏将,缺乏独当一面的表现。其次,在上述战争中,宋军最初取得了可观战果,但最终不免以败退收场,这无疑对包括吴挺在内的整个四川武将群体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功业上的局限,预示着吴挺很难在威望上与其伯、父相比肩。
半是为了赏功,半是为了笼络吴璘,宋廷给予了吴挺相当优厚的酬奖。战事尚未结束,吴挺即被擢为武昌军承宣使、龙神卫四厢厢都指挥使、熙河路经略安抚使,距建节仅余一步之遥[1]11422。战争结束后,吴挺随其父撤回兴州,乾道元年(1165)升任中军都统制[1]11422,成为四川大军中仅次于吴璘的二号人物。
乾道三年(1167),吴挺“以父命入奏,拜侍卫亲歩军指挥使、节制兴州军马”[1]11422。吴璘命吴挺所奏何事,已无从考证。从时间上看,乾道三年是吴璘的卒年,他在行将就木之时,派吴挺入朝,除向朝廷交代后事外,应是希望获得朝廷首肯,让吴挺继承兵权。而宋廷任命吴挺“节制兴州军马”,摆出允许吴氏父子世袭的姿态,则含有安抚吴璘、稳定四川军心的用意。中央与四川武将之间的微妙关系,再次通过吴挺的入朝折射了出来。
当然,宋廷并不愿四川主力部队的统帅权在吴璘父子之间传承。乾道三年五月,吴璘去世。等到局势稍稳,朝廷便将吴挺改任为金州都统制、金房开达安抚使,调离了兴州[1]11422。吴挺必极不愿离开吴家军的大本营,但他本人不具备其伯、父曾有过的声威,一旦失去吴璘的庇护,便难以与朝廷抗衡。面对朝廷的压力,吴挺所能做的,仅仅是“力求终丧”,拖延时间。这亦无法扭转局面。服除之后,宋廷将他改任为左卫上将军,旋改命为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1]11422,使之彻底离开四川。
对于吴氏家族而言,吴挺被调离蜀,无疑是相当大的打击。王智勇认为,这表明宋廷准备“削夺吴氏家族在四川的势力”[2]186。结合史实来看,“削”固然有之,“夺”则未必,宋廷尚不打算立刻根除吴氏家族在四川的势力,其对吴拱的任用就是证明。
吴拱名为吴玠之子,实为吴玠、吴璘之同父异母弟[3]688。绍兴时期,曾长期在四川担任吴璘的副手。宋金战争爆发后,被朝廷调到襄阳(今湖北襄阳),先后出任知襄阳府、鄂州诸军都统制、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讨使等职,作为中部战场主帅,屡有功勋。隆兴元年,被调回四川,协助吴璘主管军务。吴璘死后,吴拱被任命为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利州路安抚使、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2]176-180。
相比于吴挺,吴拱具有三方面优势。其一,他为吴挺之叔父,两人在家族中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其二,担任过中部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资历远胜吴挺。其三,吴挺在战争中虽有战功,但仅是局部战役中的斩将夺隘之劳绩。吴拱则以主帅的身份,保证了整个长江防线不被切断,其战绩亦凌驾于吴挺之上。
综上,如果宋廷真的准备彻底瓦解吴氏家族,便不会只调走吴挺,而留用各方面更胜一筹的吴拱。又,吴拱所镇守的兴元府,在军力配置上虽远不如兴州,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上却胜于兴州,是南宋四川防区的核心[4]29。这也说明宋廷对吴氏子弟既有防范亦有倚重。
吴璘之死,确实给宋廷创造了根除吴氏家族势力的机会,但宋廷却没有这样做。这和当时宋廷面临的局势密不可分。一方面,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吴氏家族在四川军中已经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若骤然除之,难免会引发动荡。另一方面,隆兴和议纸墨未干,宋金之间的和平状态究竟能维持多久,尚难以预判。一旦根除吴氏势力后战端再起,宋廷在四川很可能面临无良将可用的窘境。因此,宋廷在处理吴氏家族问题时,不能不谨慎从事。
此时吴氏子弟仍是宋廷统御四川不可或缺的棋子。然为何在吴挺、吴拱二人中,宋廷会选择留用吴拱?关键在于吴挺是吴璘属意已久的继承人,将他留在四川,不会令他对朝廷感恩戴德,反而会造成宋廷屈从于吴璘的印象。吴拱则不然,他在隆兴年间与吴璘有隙,曾因后者的弹劾而遭到责降[5]3976。宋廷重用吴拱,既可收市恩之效,又可借否定吴璘前见以彰显自己的权威。显然,留用吴拱,更符合朝廷的利益。
乾道年间离蜀,是吴挺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大转折。没能顺利接掌兵符,他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然而,被委以三衙管军之职,说明宋廷对他的才干还是相当看重的。此外,此时吴氏家族对于宋廷仍有利用价值。以上两点,为吴挺命运的再次翻转埋下了伏笔。
二 重掌兴州兵权
入朝任职,让吴挺有了向最高决策者展示才能的机会。淳熙元年(1174)六月,朝廷下诏:“王友直、吴挺持身甚廉,治军有律。凡所统驭,宿弊顿除。可并与建节钺。”[6]1773可见,在担任三衙管军的数年中,吴挺在治军上取得了不凡的业绩。治军之余,他还积极为未来的战争进行谋划。《宋史》载:
挺毎燕见从容,尝论两淮形势旷漫,备多力分。宜择胜地,扼以重兵。敌仰攻则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济者。帝颇嘉纳。[1]11422
出身四川,却对两淮形势有深刻认识,说明吴挺有相当强的大局观。其“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济者”一语,则显示出他不只是想固守防线,更有进取之心。孝宗素怀恢复之志,吴挺与之相当投契。
在宋代主流政治理念中,一名理想的将帅不仅应能谋善战,更必须小心谨慎,恪守法度。吴挺在这方面亦有良好表现。他入朝之初,“朝廷方议置神武中军五千人,以属御前,命挺为都统制。挺力陈不当轻变祖宗法,事遂寝”[1]11422。吴挺宁愿舍弃个人名位,也要坚守祖宗之法,无疑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可见,除了军事才能外,他也拥有清醒的政治头脑。
淳熙元年二月,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去世。此后,吴挺被改任为兴州都统制[1]11422,再度回到了四川。王智勇称:“当淳熙元年虞允文去世后,放眼当时的统兵将帅,从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的确唯有吴挺是四川兵力最强的兴州都统司帅臣的最合适人选。”[2]192其说稍显浮泛。此时距离隆兴和议已有十年,宋金一直处于和平状态,两国的军事实力也大致均衡。相比于高宗朝,四川战区所承受的军事压力明显减小。以常理而言,此时可以出任兴州统帅的人选不会很少。然则宋廷为何会在时隔七年后将四川主力部队的统帅权重新交给吴氏子弟?笔者认为,这与孝宗的恢复之志密切相关。
孝宗一直希望收复中原,隆兴北伐的失败,并未消弭他的壮志,却让他将目光从两淮转向了川陕。据李心传记载:“虞丞相再为宣威”,孝宗“始期以某日会于河南,既而上密诏趣师期。虞公言军需未备,上寖不乐。又明年,上遣二介持御札赐之,戒以面付,介至,而虞公薨数日矣”[3]631。可见,在孝宗的战略构想中,四川是北伐中原的跳板。虞允文死后,他的这一想法依然存在。如淳熙十一年(1184),“命利路三都统吴挺、郭钧、彭杲密陈出师进取利害”[1]683。又如,淳熙十二年(1185),“谍言故辽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诏吴挺与留正议之”;一年后,又“诏吴挺结约夏人”[1]685。这些史实均表明孝宗始终有自四川出师北进中原的想法。
如果兴州都统制只需承担守蜀之责,可出任此职的人选多矣。按孝宗的规划,兴州主将随时可能亲帅大军,投身北伐,但能任此职的人选却不多。吴挺善治军,才干出众,在四川军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参加过高、孝之际的宋金战争,熟悉四川、陕西之间的地理以及金国在陕西的布防情况。从各个角度看,他都堪此大任。这是其得以返蜀的重要因素。
也应指出,论才干、经验、声望,吴挺是出任兴州都统制的合适人选,却非唯一人选。如前所述,同样身为吴氏子弟的吴拱,在这几方面皆不亚于吴挺。据杨万里记载:虞允文帅蜀后,“首荐员琦为西帅,吴拱为东帅……大将得人,后进获伸,诸军欢呼,四蜀交贺”[7]卷一二〇《宋故左丞相节度使雍国公赠太师谥忠肃虞公神道碑》。若无出色业绩,吴拱不会被虞允文推荐为利州东路安抚使,更不会令“诸军欢呼,四蜀交贺”。那么,为何宋廷在淳熙元年不选择吴拱作兴州主帅,而宁愿派吴挺不远千里入蜀?
兴州都统制手握六万兵马,是四川三都统制中实力最强者。朝廷除了考虑其人选的才干资历,更要考虑其与朝廷的关系。吴拱虽受过朝廷恩惠,但从未踏足过行在,朝廷与他之间渊源不深。而吴挺在中央有数年的任职经历,与宋廷的关系远较吴拱密切,尤其是他与孝宗有很好的私人情谊,这使得朝廷更愿意将兵权交付给他。与乾道三年留用吴拱相似,宋廷遣吴挺执掌兴州大军,同样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
众所周知,吴挺返回四川时,其子吴曦并未一同前往。一般认为,这是朝廷为控御吴挺而刻意为之。其实,自宋初开始,受朝廷委派入蜀的文武臣僚,按例不得携带家眷。吴挺的中央背景,使宋廷可以更方便地利用成法惯例对他加以约束。这也是朝廷对他更为放心的重要原因。
淳熙二年(1175),吴拱被调离四川;三年,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8]卷一一二《赐吴拱诰》,成为吴氏家族中第二位三衙管军。宋廷如此安排,既可预防吴拱、吴挺二人在四川联手,又可对吴挺形成制约。一旦吴挺在兴州任上的表现不符合预期,朝廷可以很方便地用吴拱取而代之。吴挺既失去了一位强援,又多了一个潜在的竞争者,只能对朝廷更加驯服。可以说,在积累了数十年经验后,宋廷已逐步摸索出一套驾驭四川武将的方法。
对于吴挺执掌兴州大军,朝中舆论有何反应?王智勇称:“吴挺在淳熙元年返蜀重掌四川重兵”,“在南宋政治生活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引发了朝野内外的一片非议”[2]197。现存史料中确实有一些朝士的批评言论,然细细考之,这些言论大多发表于吴挺返蜀很久之后,而非孝宗任命吴挺为兴州都统制之时。如《宋史》载,赵汝愚帅福建,“陛辞,言国之事大者四,其一谓吴氏四世专蜀兵,非国家之利,请及今以渐抑之”[1]11982。赵汝愚任福建安抚使是在淳熙九、十年(1181、1182)间,距吴挺返蜀已有八、九年之久。又如绍熙三年(1192),丘崈为四川制置使,卫泾投书于他,称:“有如识者之虑,民困于重征,兵习于世将。”[9]卷一四《于四川制置丘崈侍郎札》此时距离吴挺返蜀已有近二十年。再如韩元吉称:“至于蜀道之远,与夫辇运之近,又有久任而不易者,则非某所敢议也。”[10]卷一三《上贺参政书》确切时间难以敲定,然由“久任而不易”可知,此时吴挺返回兴州已久。
在文献中,我们找不到淳熙元年朝士对吴挺重返四川的异论。这不能说明当时完全不存在此类言论,但至少证明这一任命并未引起朝士过于激烈的反对。以情理论,若淳熙元年朝中真有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阻扰吴挺返蜀,虽以孝宗之刚毅,也很难不受影响。
相比于朝士,四川本地士人对吴挺返蜀似更为敏感。吴挺甫一返回四川,“(李)蘩宰眉山,校成都漕试。念吴氏世袭兵柄,必稔蜀乱。发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为患者。’”吴挺知晓后,“以为怨”[1]12119。李蘩为崇庆(今四川崇州)人,入仕后一直在蜀中任职,可视为四川本地士人的代表。他发此言论,可见不少四川士人从一开始就对吴挺重掌兴州兵权存有抵触情绪。
对于吴氏世代掌兵,朝士必会有顾虑。然前文说过,吴挺在朝持身甚廉,谨守法度,符合士大夫心目中理想将帅的形象。孝宗仅命吴挺为都统制,而未任其为四川宣抚司长贰,又采用了留吴曦等手段对其加以制约,也有助于消解朝士的顾虑。因此,淳熙元年吴挺重返四川,在朝中并未立即引发太大的反对声浪(吴挺返蜀后,因种种“跋扈”言行而遭到朝士侧目,则是后话)。而蜀士虽曾受惠于吴玠、吴璘的御敌之功,却也长期受困于供养吴家军之苦[4]220-242。吴挺返蜀,很可能重启吴氏家族与蜀士之间的争斗,自然不免引发后者的担忧。朝士与四川本地士人的态度有异,实源于其各自的关注点不同。
吴挺返蜀前后,宋廷对四川的军政体制做了调整。虞允文在世时,四川由宣抚司执掌大权。虞允文去世后,宋廷对是否继续推行宣抚司体制一度比较犹豫。淳熙元年三月,郑闻被任命为四川宣抚使,七月改任参知政事,四川宣抚司被废罢,改设四川制置司;十二月,朝廷又命沈夏为四川宣抚使,恢复了宣司建制;但次年六月,沈夏又被改任为知枢密院事[1]659。四川宣抚司最终被罢置,制置司成为了四川地区最高军政机构。
宣抚司体制变为制置司体制,使得四川地区的权力格局有了较大变化。宣抚司兼掌军事、民政,同时可在很大程度上干预财政。制置司则不然,“财计、茶马不与”[3]220,基本没有财权。不仅如此,按制度规定,制置使虽可“节制御前军马”[3]220,但在实际运作中,与常驻河池等地、可就近控御四川大军的宣抚使不同,制置使因兼任成都知府而必须坐镇成都,与四川大军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难以真正过问军中具体事宜。
宋廷将宣司改为制司,原因比较复杂。最为重要的一点,应是在虞允文死后,一时难以找到一个既才兼文武,又熟悉四川情况,更深得朝廷信任的臣僚来出任宣司长官。吴挺返蜀,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次调整有关:制司对四川大军的控制力度较弱,宋廷必须另觅手段以保证对军队的掌控。以才干操守俱获朝廷认可的吴挺执掌兴州大军,可弥补制司体制的不足,是促成宋廷这一决断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宋廷的制度调整,多少亦含有防范吴挺的意图。四川宣抚使的人选可以是文臣,亦可以是武将,吴玠、吴璘都曾任过此职。而四川制置使按惯例只能由文臣出任,自高宗朝起,从未有武将出任四川制置使的先例。改宣司为制司,等于消除了吴挺成为四川最高军政长官的可能,可收防微杜渐之效。
宣司改为制司,意味着吴挺任兴州主将时将有较大的权力空间。然制司权力不够集中,也预示着一旦吴挺与其他官员产生分歧,制司很难居间协调。换言之,吴挺面临的政争风险增大了。在宋代,武将无论是自专,抑或与文臣爆发冲突,都难免为士大夫侧目。后来,吴挺屡屡被士大夫指为“跋扈”,从根源上看,实滥觞于宋廷对四川军政体制的调整。
三 政绩与政争
重返兴州后的十余年中,吴挺在军政上多有建树。他的种种举措,直接影响着他与朝廷及蜀中文臣的关系,给他带来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孝宗命吴挺执掌兴州大军,一是要强化他对这支部队的管控,二则是要为北伐作准备。吴挺对此心知肚明,在整军备战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上任不久,他即上奏指明四川军政中存在的弊端:“切见四川诸军近年以来,兵将官差除,虽名为出自宣抚司,其实多自诸司官属及州县官造作毁誉,推荐中害,往往罪赏不当,因此兵将官不以职事为意,专务奔竞交结,乞指挥严行戒饬。”[6]1782得到了朝廷的首肯。戒饬奔竞行径,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有莫大帮助。
整顿军风之后,吴挺着手调整了兴州大军的布防。“初,武兴所部,就饷诸郡,漫不相属。挺奏以十军为名,自北边至武兴列五军,曰踏白、摧锋、选锋、策选锋、游奕,武兴以西至绵为左、右、后三军,而驻武兴者前军、中军,营部于是始井井然”[1]11422-11423。通过这一举措,吴挺对以往“漫不相属”的部队做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使之更容易形成合力。这无论是从防御还是进攻的角度看都是非常必要的。
在修缮堡寨、制造武器方面,吴挺也取得了不俗成绩。“密修皂郊堡,增二堡,缮戎器储于两库,敌终不觉”,此后,“西和、阶、成、凤、文、龙六州器械弗缮,挺节冗费,屯工徒,悉创为之”[1]11423。经过吴挺的一番努力,四川战区的战备力量有了显著增强。虽然吴挺最终没有能等到北伐的那一天,但是他在任期间的业绩,已足以证明宋廷对他的重用是明智之举。一些士大夫对他的治军成效亦有肯定,如朱熹就曾称赞他为“得力边将”[11]3281。
值得注意的是,吴挺在履行职权时,非常注意与朝廷沟通,遇事往往先奏请后施行。上述戒饬奔竞之风,就是一例。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如淳熙五年(1178)闰六月,奏请将阶、成、西和、凤州耕种营田的军兵抽回,田地令诸州召民户佃种[6]1826;淳熙十一年(1184),上奏蜀中军队改行花装不便,请求依旧用纯装[6]1896;淳熙十四年(1187),奏请修整山寨[5]7641等。兴州主将遇日常事务频频奏请,在吴玠、吴璘时是不曾出现过的,这表明吴挺深谙宋廷对武将的忌惮,努力避免“专擅”之嫌。此外,另有两方面因素,促使其这样做。
其一,不少事务,如营田等,需要四川其他官员与吴挺配合,才能妥善处置。相比于吴玠、吴璘,吴挺在威望、地位上均有不及,单靠自身的影响力,未必能得到蜀中官员的支持,唯有先禀明朝廷,借助后者的权威以成事。
其二,至南宋中期,虽然四川与行在之间的信息传递仍比较迂缓,但此时朝廷已经有了较多的途径来掌控四川政情。很多事宜,即便吴挺不上奏,朝廷也可获知。如淳熙七年(1180),有人私贩解盐入川,宋廷即先通过其他臣僚了解到情况,再令吴挺开具已措置禁止事件以闻[6]1855-1856。对于吴挺而言,与其由他人先上报而令自己陷入被动,还不如主动奏报以取信于朝廷。
对于吴挺的恭顺态度,朝廷给予了积极回应。他所奏请之事,多数能得到朝廷的认可。此外,朝廷还逐步扩大了吴挺的事权。淳熙三年(1176),宋廷令吴挺选司兵官一员兼知文州[5]3976,使其具有一定的行政、人事权;四年(1177),令吴挺在兴州都统制外,兼任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1]11423,成为一路的军政长官。上述放权措施,表明宋廷对吴挺的信任度在逐渐增加。
与此同时,宋廷也采用了一些手段,以加强对吴挺的控制。例如文州蕃部曾劫掠两名汉人,吴挺上报朝廷:“以事细,止乞照会。”周必大则向孝宗建议:“今欲降指挥,督其根治,庶几知朝廷每事留意,不敢忽略”,孝宗表示赞同[8]附录卷二《行状》。宋廷刻意在上述“细事”上否定吴挺的意见,其实是要提醒吴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朝廷关注之下,使之不敢有侥幸之心。又,返蜀之后,吴挺的事权虽逐渐增重,但终其一生,其职权范围始终被限制在利州西路以内,也表明朝廷对他既有信任亦有防范。
吴挺与朝廷大体保持着良好关系,与蜀中文臣则时有龃龉。先看他与财政官员的争斗。吴挺返蜀后,朝廷委任李蘩为主管四川茶马,继而命其为四川总领。孝宗曾令吴挺提举买马,李蘩加以反对,指出:若买马事由武将负责,会导致“马直必增,外骄羌夷,内耗国用”[12]卷七八《李公墓志铭》。此后,李蘩又在四川大军中“申严私役之禁”[12]卷七八《李公墓志铭》,矛头指向吴挺等武将。孝宗后期出任四川总领的赵彦逾,了解到吴挺军中有六千“虚籍”,立即要求吴对这批实际并不存在的士兵加以裁减。吴挺虽然恼怒,但亦不得不从[3]654。光宗初年任四川总领的杨辅,则在核实营田、减少军中“请给”二事上与吴挺意见相左。核实营田之事,因吴挺反对而中止;“请给”问题,则因杨辅巧妙地采用了拖延战术,最终令吴挺放弃了己见[4]244-246。
再看吴挺与制置使之间的矛盾。淳熙六年,黎州(今四川汉源)五部落因买马问题与南宋交恶。时任制置使的胡元质,调内郡禁军前往征讨,大败而归。不得已,胡从绵州(今四川绵阳)和潼川府(今四川三台)征调了二千余名御前军,前往清剿,结果又败。制司再从剑州(今四川剑阁)、利州(今四川广元)、阆州(今四川阆中)征调了三千名军士,赴黎州增援。吴挺得知后大怒,密申枢密院:
制置司先调绵、潼之军二千八百人,急于星火,夜行百三、四十里,蛮人已退,而官军冒暑远涉,疲劳病瘴。光延、晃侥幸功赏,驱帅将士,败死者四百余人,瘴疫死者不在其数,黎州几至失守。今制置司又亟调两都统司剑、阆、利州屯驻军三千人,比之绵、潼军马,道里又远,岂可使不谙战阵败军之将复蹈前悔。望正其罪,以慰忠魂。虽黎州非挺等边面,而所调兵皆挺等部曲,谨具以闻。[3]857-858
表面上,吴挺是在弹劾成光延、高晃,其实“劾长文(胡元质)也”[3]858。此后,宋廷以“不备蕃部,致其猖獗”为由,罢黜了胡元质的制置使之职[1]674。
上述争斗之所以出现,如前所述,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亦和吴挺的个性密不可分。吴挺是“有气骨”之人[11]3281,性格中除小心谨慎外,还有刚直的一面。正因如此,当和蜀中文臣出现分歧时,他不肯忍气吞声,而一定要力争到底。在这点上,吴挺承袭了其伯、父之遗风。
吴挺与四川文臣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他对制帅胡元质的攻讦,在当时颇引人瞩目,后世研究者也往往将之作为他势力强大的表现。如雷家圣指出:“吴挺对于他的上司,当时的四川制置使胡元质,甚至上奏弹劾,胡元质因此罢制置使。由此可见吴挺在四川的影响力甚至在制置使之上。”[13]150然细细考察,上述看法未必确切。理由如下。
从争斗的缘起来看,多是文臣率先发难。李蘩奏请罢吴挺的买马之权,赵彦逾要求吴挺裁减“虚籍”,均是证明。胡元质抽调利州等地御前军,虽不是刻意针对吴挺,事实上也触动了吴挺的实力根基。与之相反,吴挺通常是被动应对的一方,其所作所为基本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罕有主动侵夺文臣权力的举动。故很难认为当时四川的权力格局是文臣势弱,吴挺势强。
从争斗的结果看,吴挺与文臣各有胜负。赵彦逾、杨辅都曾令吴挺受挫。逼走胡元质,可算是吴挺最为“辉煌”的胜利。然通观其事始末,吴挺也难称完胜。理由在于:胡元质被罢后,制置司并没有遣返吴挺部曲,而是将之留在黎州戍边[3]860,吴挺的实力终不免遭到削弱。既有研究称当时吴挺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制置使等四川文臣,恐难令人信服。
在政争中,吴挺之所以获胜,主要依靠的不是自身实力。以吴、胡之争为例,吴挺申枢密院后不久,胡元质即被罢,这很容易让人误认为吴挺是胡元质被罢的“元凶”。然吴挺采用“密申”而非公开弹劾的方式,以及他在申状中不敢明言胡之过错,均表明他深知这一举动可能给自己带来的风险,也表明当时他的权力并不足以与制帅相抗衡。他之所以能逼走胡,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朝廷的力量,这又涉及到一些复杂的内情。
前文说过,制置使、宣抚使虽同是四川的最高军政长官,然制置使实际拥有的军事权力较小。和平时期,宋廷多在四川设制置使而非宣抚使,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四川军政长官权力过于集中。结合史料记载,自南宋初年起,未有制置使不经朝廷许可,自主征调蜀口主力部队的先例。五部落之变中,胡元质没有预先奏请朝廷,便从吴挺等人的部队中征调了五千余士兵,虽事出有因,却不可避免地会触犯宋廷的禁忌。宋廷将胡元质罢黜,实有防微杜渐、警示来者之意。
又,对于五部落之变,茶马司长官吴揔难辞其咎。“黎州边衅,实兆于买马诛求之故,及官军失利,揔又急于成功,乃以十兵易十酋,邀功辱国”;当时主政的宰相赵雄与吴揔关系极深,“时相赵温叔颇佑之”[3]859。要想保住吴揔,势必要找一个替罪羊为他分担罪责。吴挺对胡元质的攻讦,恰好给赵雄提供了便利。可以说,胡元质之罢,最大的受益人其实是吴揔,吴挺不过顺带得利而已。
总之,胡元质之罢,一方面与四川和中央之间的人事纠葛有关,另一方面则缘自胡自己的犯忌之举。吴挺的弹劾,主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吴挺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加之曾任职于中央,对最高决策层的心态比较了解,因此,常能够把握住时机,上报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借朝廷之力,以达成自己的目的。吴、胡之争,可谓最好例证。
当然,在朝廷始终对吴挺存有一份戒心,以及四川与朝廷之间存在多元化沟通渠道的背景下,吴挺的类似举措,并不总能奏效。他曾奏劾李蘩:
公(李蘩)领饷事,挺缪奏谓军食陈腐,龙、剑米粗黑。孝庙内批,凡再赐公。公奏:“此土实不同也。”乃各缄样进呈。上大悦曰:“李蘩晓了如此。”于是挺之妄穷矣。[12]卷七八《李公墓志铭》
能否在政争中获胜,取决于自己的奏报能否得到朝廷采信。若无朝廷支持,吴挺和四川文臣周旋起来便倍感吃力。吴挺和杨辅的“请给”之争即为例证。“吴挺屡以为言,嗣勋但以俟商量答之。及再请,则以本所乏用,必更俟措画为词。每一书往返,则阅数月,久之,则遣属官一员往军中面议,自始差至还司时,又已半岁。戎司亦遣其官署来报聘,卒不得要领而归。相持久之,遂已。”[3]818明知杨辅是在拖延时间,吴挺却无可奈何。相比于屡屡凭借自身威势压服蜀中文臣的吴玠、吴璘,吴挺的影响力是比较有限的。
南宋初年四川文武官员因利益分配,常常产生激烈争斗,令朝廷极感头疼。由上文可知,到了孝、光时期,四川内部的政争依然存在,但无论武将抑或文臣,在与对手争斗时,大多须借助朝廷的力量,其胜负亦常取决于朝廷的意志。而且,文武之争看似尖锐,却很难冲破朝廷为其划定的权力界限。对于宋廷而言,此时四川官员的内斗已基本可控;利用之,朝廷可收“异论相搅,则各自不敢为非”之效,强化对四川的控御。
在士大夫看来,无论武将以何种手段与其博弈,都属逾分之举。吴挺的功绩声望本就不及吴玠、吴璘,淳熙至绍熙时期,南宋与金国又一直处于和平状态,南宋士大夫对于吴挺的种种“骄横跋扈”举动,就更难以容忍。蜀中官员率先向朝廷奏报吴挺之“强横”,朝士随后应和。吴挺治下的兴州大军“不知有朝廷”[1]11974等言论,出现得日渐频繁。其实,这类说法常含有夸张成分,有些甚至完全经不起推敲。如以下这则屡被论者引用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王炎宣抚川陕,辟(陆游)为干办公事……吴璘子挺代掌兵,颇骄恣,倾财结士,屡以过误杀人,炎莫谁何。游请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游曰:“使挺遇敌,安保其不败?就令有功,愈不可驾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验。[1]12058
吴挺屡杀人,而宣抚使不能制止,岂非正好证明吴挺骄横?实则王炎是在乾道五年到乾道八年担任四川宣抚使的[1]654,期间吴挺并不执掌四川兵权。淳熙元年吴挺担任兴州都统制时,王炎早已离蜀,且此后再未担任过任何四川职事。所谓吴挺杀人而王炎不能制止,以及陆游建议王炎以吴拱代替吴挺之说,显然都不足信。这则故事的流传,表明士人对吴挺偏见之深。
关于吴挺与文士的关系,文献中也存在一些正面记载。《宋史》本传称,吴挺“礼贤下士,虽遇小官贱吏,不敢怠忽”[1]11423。刘光祖记,淳熙后期,赵汝愚为制置使,吴挺对他尊礼有加,“吴挺遣使于公所,赉持酒十樽,梨三百颗”[14]905。看来吴挺亦不愿任由文臣将自己塑造为一介骄横悍将,在维护自身权益之余,也试图挽回自己的声誉。上述举措,应该说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并不足以完全抵消士人对他的负面描述。
既是治军有方的良将,又是骄横跋扈的军阀,返回兴州后的吴挺,逐渐具有了一种二元化的形象。绍熙四年(1193),吴挺去世,关于是否应让其子吴曦继承其兵权,朝中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意见,即光宗、韩侂胄等人赞成,而曾担任过四川制置使的赵汝愚、留正等反对[15]360。最终,反对派占了上风,吴氏世将在四川的存在暂时划上了句号。关于吴挺身后事的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是他一生褒贬的折射。
四 结论
南宋初年,如何经营四川,是摆在宋廷面前的一道难题。这一问题的棘手之处,主要在于四川地方武将的强势。而到了孝、光两朝,四川武将与朝廷的关系,日益朝着对后者有利的方向发展。吴璘晚年,已不得不遣子赴行在为人质。吴璘死后,宋廷在驾驭吴氏子弟方面,更是游刃有余。任用谁、如何任用,均由朝廷定夺。吴挺“有气骨”,敢于对抗制置使,但对朝廷却不敢稍有忤逆。可以说,到了孝、光两朝,以吴挺为代表的四川武将,已无法如南宋初年那样对宋廷构成威胁;相反,他们更多地转化为朝廷在四川的“代理人”。从这个角度看,此后的吴曦之叛,只是一次偶然事件,而非以往学者所认为的是四川武将势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宋廷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效,一方面,与种种客观因素密不可分。如: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使宋廷在处理四川武将问题时有了越来越多的筹码;孝、光两朝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宋金处于和平状态,令宋廷在与四川武将打交道时有更大的运作空间。另一方面,宋廷所采用的合理策略也是重要原因。在处理吴氏世将问题时,宋廷的举措可谓既稳健又不失时机,既在很长时间内容忍了吴氏势力的存在,又不动声色地逐渐对其予以削弱和分化,最终在不影响四川稳定的前提下,基本解决了吴氏世将尾大不掉的问题。在官员选任上,宋廷也屡有明智之举,其在吴拱、吴挺之间的两次取舍,即显现出政治智慧。又,它所任用的多名四川制置使、总领官,虽偶有举措失当之处,但大体均起到了制约武将的功效。总之,从经营四川的手段和效果来看,孝、光两朝的中枢决策者还是颇有高明之处的。
注释:
①南宋时期的“四川”,在地理范围上较今日之四川省更广,包括部分今属陕西省的地区。
②参见: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张邦炜《吴曦叛宋原因何在?》,载氏著《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M].成都:巴蜀书社,1995.
[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4]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徐松.宋会要辑稿[G].北京:中华书局,1957.
[6]佚名.宋史全文[M].李之亮点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7]杨万里.诚斋集[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8]周必大.文忠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卫泾.后乐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韩元吉.南涧甲乙稿[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13]雷家圣.聚敛谋国:南宋总领所研究[M].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
[14]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M].香港:龙门书局,1971.
[15]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凌兴珍]
A Study on WU Ting and Southern Song govenment’s management of Sichuan in the Middl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NG Hua-yu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WU Ting was the import general of Sichuan in the middl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He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field, and gained mixed assess from civil officials. By observation of WU Ting, this paper found that in the middl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imperial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its control over Sichuan. Local military officers in Sichuan, who once threatened the imperial government’s control, became the agents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at last. Top policy-makers in the middl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were laudably in managing Sichuan.
the middl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imperial government; Sichuan; WU Ting
2016-07-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攻关课题项目“7-16世纪中国南部边疆与海洋经略研究”(12JZD013)。
王化雨(1979—),男,四川成都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K245
A
1000-5315(2016)06-015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