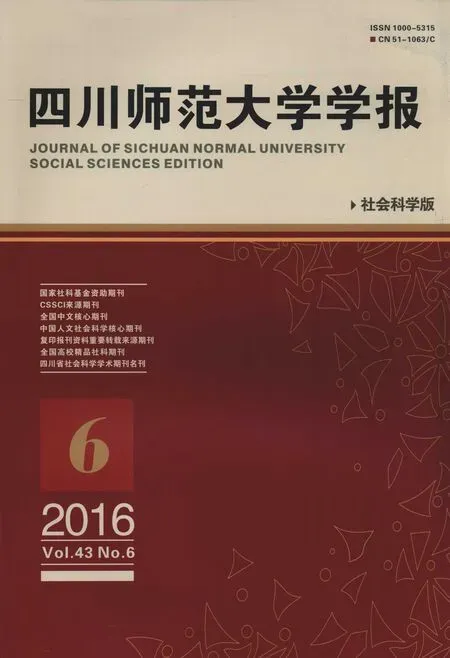铠甲舞的历史与田野考察
——兼及周人“前歌后舞”与《国殇》的仪式背景
2016-04-13万光治
万 光 治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铠甲舞的历史与田野考察
——兼及周人“前歌后舞”与《国殇》的仪式背景
万 光 治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以田野考察所获,证之传世文献,知巴人助周灭殷的“前歌后舞”、屈原《国殇》所据楚人祭祀乐舞、今仍流传民间的藏羌族铠甲舞、景颇族“目瑙纵歌”与阆中“巴渝舞”等,皆属古代与征战狩猎相关的仪式性歌舞。这些乐舞有明确的目的性、广泛的群众性、固定的程序和内容,更有年节化与即时性相结合的特点。古代宫廷仪式与民间仪式之关系,由此可以窥见。今存上述仪式皆具“活态文献”的价值,应予认真保护和研究。
铠甲舞;田野考察;历史考察;活态文献
本文所说的铠甲舞,是一种从俗的说法,确切言之,指的是至今仍流行于藏、羌等少数民族地区披甲而舞的仪式性活动。它们起源、盛行于巫文化时期,与狩猎、战争密切相关。以笔者考察所见,今所见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四川阆中的巴渝舞,与藏、羌铠甲舞相类,皆属本文所论铠甲舞范畴。
笔者在对上述铠甲舞的考察、研究过程中,还发现文献所载上古时期巴人助周灭殷的“前歌后舞”[1]卷三,2a、屈原《国殇》所据“俗人祭祀之礼”[2]745,以及刘邦所见“巴渝舞”,无论形式还是性质皆与上述铠甲舞的仪式性活动有极大的相似性。如果此说成立,则笔者经田野考察而获取的信息,似可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兹分别论列之。
一
近十年来,笔者花费了较多时间和较大精力采集民间歌谣。因有一定数量的积累,乃能通过比较,逐渐从中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存在。例如今存古老民族的传统歌舞,大都有相应的仪式为其生存背景,甚至一些歌舞至今仍附丽于古老仪式,是该仪式的重要构成部分。笔者由不同民族的仪式性歌舞及其仪式性背景的相似性中似乎窥见了某些规律,从而逐渐纠正或充实了过去有关“前歌后舞”以及《国殇》的一些认识。
首先谈羌族的铠甲舞。2005年,笔者在四川松潘川主寺镇采录两首《出征歌》,在茂县太平乡牛尾村采录一首《征战歌》,在三龙乡桌子坝采录两首《威武歌》,在曲谷乡西湖寨河西村采录一首《征战歌》。由于其歌词使用今人不解的古羌语,歌者仅知皆属族人出征打仗前所唱之歌。据尚云川《羌族词典》[3]301-302、耿静《羌乡情》[4]58,茂县赤不苏地区的羌族有“克什叽·黑苏得”和“埃古·日格沙”两种铠甲舞,前者用于纪念战死者,后者用于战前的誓师,舞蹈时男子身着牛皮铠甲,戴盔帽,执兵器,唱哀歌,且不停变换队形。笔者由是怀疑,征战歌与此所云铠甲舞属同一类型的歌舞。2012年6月,笔者再次赴茂县牛尾村、松潘小姓乡作进一步的考察,始知前所录征战歌,乃是铠甲舞的一个部分。据牛尾村的老人介绍,当地的铠甲舞分小型、中型和大型三种。小型用于一般性的节日聚会,时间、规模都适可而止;中型用于较大的集会或仪式活动,如正月初七男子的集体出行(即野餐)、正月十七的“化龙节”(即焚烧纸龙);大型的则在正月初七的“人节”举行,凡年满十三岁的男子均须参加。牛尾村依地形而分为“上寨”和“下寨”(数年前上寨人已全部迁居下寨)。人节时,两寨的领头人戴盔披甲,骑马执旗,腰系刀剑,斜挎火枪,本寨男子着盛装,举刀枪,紧随其后。两队人于下寨空地会合,双方头领发话,众人互道辛苦、作揖,然后男子沿一定的路线相互穿插,跳起铠甲舞,女子则紧随其后,踏步而行。其间为振奋士气,众人鸣枪放炮,举刀吼唱九次。仪式进行到最后,众人到上寨的神树林且歌且舞,铠甲舞至此进入高潮。歌者所唱用古羌语,或轮唱,或多声部合唱,歌词大意为:
穿上铠甲衣,背起火药枪,举起你的刀和叉。没有刀枪棍棒石块也好使。来来来,十三岁以上的男儿们,大家都来跳铠甲舞!问你铠甲歌有哪几种?铠甲歌有五种。哪五种?出征歌、兵器歌、胜利归来歌。还有两种是什么?男儿成长歌、庄稼歌。什么场合唱什么歌?一般场合出征歌,中型集会加上兵器歌,正月初七是什么节?是人节。铠甲歌舞一个也不可缺!
据该村铠甲舞组织者之一的董运周讲,铠甲舞表现持刀练兵的威武气势,意在演示武力,威慑敌人,亦有纪念战死者,祈求亡魂护佑生者之意。过去寨子之间打冤家,凡牛尾村跳铠甲舞,邻村每派人偷窥,见其势盛,乃不敢轻举妄动。牛尾村羌语叫“烁古”,意谓“尾巴上的村庄”。与此称谓相关的传说大致有三,最有代表性的是匪徒从牛角村抢劫至牛尾村,终因牛尾村人多势强,未能得逞,匪首只好自己解嘲说:“一头牛都收拾得差不多了,留个牛尾巴算了!”另一传说与此相似:唐代吐蕃征服松潘、茂县所有地区,此村独以地险势强得以自保,“牛尾”之名,由此而来。
其二是黑水藏族的“卡斯达温”。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河流域流行一种仪式性很强的歌舞活动,叫“卡斯达温”或“卡斯达贡”。在黑水方言中,“卡斯达”是“铠甲”,“温”或“贡”是“穿”,即穿着铠甲跳舞的意思。古羌族曾生活于黑水。唐代吐蕃势力逐渐强大,东扩控制黑水一带,藏羌融合进程加快。故卡斯达温无论服饰、舞蹈、音乐和方言,都有羌文化的因子。卡斯达温是先民在狩猎或征战之前举行的仪式性活动,后来也杂糅进农耕时代的特点。发展到现在,卡斯达温已成为一种年节性、祭祀性的歌舞活动。黑水地区的卡斯达温有三种不同的内容与程序。其一是扎窝乡朱坝村,其铠甲舞次第表现与狩猎有关的内容。女人持酒唱歌,祝愿出猎者平安归来;男人点燃柏枝,在玛尼堆前祷告平安;高声吼唱,举刀枪以示围猎;最后,男人行转山仪式,女人跳起锅庄,以示狩猎成功,感谢神灵。其二是红岩乡俄恩村,其铠甲舞以征战为题。男人始则穿铠甲于经堂,以示得到神佑。继则领舞者吹牛角发出征战号令,众舞者以舞蹈表现激烈的战争场面。最后是女人载歌载舞,欢迎战士凯旋归来。其三是维古乡,如为收获、节日前的祈求佛佑,不穿铠甲。其程序次第为敬神、求神、从神、欢聚、迎宾。尾声为领舞者右手持铃,女人随之跳起锅庄。如为战死英雄、期颐老人举行祭祀活动,则须穿铠甲,过程更为复杂。卡斯达温的内容与程序各地虽有不同,但其音乐和舞蹈的风格却大致相似。其唱词所用语言系远祖所传,杂糅古羌语与西藏阿里古藏语。其舞蹈无乐器伴奏,既有当地藏族锅庄特点,也有羌族锅庄元素。维古乡在丧葬仪式中,长者吹奏“色拉”,其形状、音色和“鼓腮换气”的吹奏方法,均似羌笛。可见黑水、松潘、茂县的铠甲舞皆与古羌人有关。
其三是景颇族的“目瑙纵歌”。现今生活在云南西南部的景颇族与氐羌有很深的渊源。公元7至9世纪,因吐蕃扩张,生活在青藏高原南部山区的氐羌乃沿横断山脉南迁,其中一部分生活在澜沧江以东的金沙江地区,另一部分生活在澜沧江以西至缅甸境内。15至16世纪,东部族人因战争又大规模西迁,移居德宏地区。20世纪50年代,该部始被定名为景颇。当时的景颇族信仰万物有灵,基本处于巫文化时期;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文字有景颇文与载瓦文,皆属近现代所造。由于长期生活在亚热带地区且与其他民族杂居,景颇族的居所、服饰、饮食、习俗与氐羌已有很大区别,而最终形成自己的特色。景颇族的目瑙纵歌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起,九天之内,逢双日举行,参加者可达数千上万人。关于目瑙纵歌的起源有三说:通过鸟儿从太阳神那里学来;为纪念祖先降魔除邪胜利而举行的歌舞活动;景颇族的始祖根据父母的意旨,在其死后向太阳神学会这一舞蹈。1995年春节,笔者曾在距瑞丽三十余公里的山间平旷之地,亲历目瑙纵歌。2012年正月十五,芒市举行国际目瑙纵歌节,笔者再次深入现场内外,进行学术考察。举行目瑙纵歌的广场四周围以栅栏,中心竖立四根有图腾意味的目瑙柱,亦称雌雄柱:中间两根为阴,外面两根为阳。阴柱之间,交叉绑有两柄长刀。四柱通身绘有回纹和菱形纹,象征景颇族的迁徙路线。举行前一天,杀牛祭祀,巫师行法事以驱逐鬼怪,避免场内出现刀枪伤人的事故。舞蹈以唢呐、竹笛、铓锣伴奏,领舞者头戴由孔雀、野鸡羽毛和野猪牙装饰的目瑙帽,谓之“瑙巴”,由熟悉迁徙路线的老者担任。参加群舞的男子手持长刀,女子舞彩帕或彩扇,随领舞者踏步而行,谓之“瑙双”。凡舞者无论男女,皆左右摆胯前行,其摆胯的动作与羌族锅庄依稀相似。舞队行进的路线十分复杂,两圈后队形变换,一路随领舞者沿既定路线继续行进,一路则可自由舞蹈。其间有两对舞者持刀而舞,以示驱赶邪魔或野兽。数百年来,景颇族历艰涉险,辗转迁徙,全凭勇武善战、团结互助,最终获得生存之地。故其目瑙纵歌主要道具是景颇长刀,动作特点是相互紧密依靠,沿象征性的民族迁徙路线循环往复地行进①。
其四是今四川阆中民间流行的“巴渝舞”。此舞是巫文化时期巴之先民在狩猎或出征前举行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目的在祈祷胜利,鼓舞斗志。自古迄今,每逢春节前后,无论城乡,阆中民众均喜跳此舞。今之巴渝舞宗教的意味已然消失,群众性、娱乐性是其重要的目的。其舞分“迎神”、“待战”、“搏击”、“驱魔”、“欢庆”五个部分,伴奏乐器以皮鼓为主,铜锣为辅。鼓形为双面鼓,鼓面直径约30-40厘米,绘有八仙或蛇、象图案,鼓柄长约120厘米。舞者戴面具,男性袒臂,女性束发。领舞者以鞭击鼓,余者手执弓矛,随锣鼓之声踊跃呼号,进退分合,井然有序。在阆中,巴渝舞又称“巴相鼓”、“巴象鼓”或“八仙鼓”。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有五姓,巴氏子务相被公推为君[5]2840。民间传说巴人爱戴务相,以此舞祭祀之,故名巴相鼓。又传说巴人以蛇、象为图腾,故曰“巴象鼓”。阆中又有云台山,传说东汉张道陵曾在此修道,“八仙”的传说与道教有关,此舞又被称作“八仙鼓”。无论是“巴相鼓”、“巴象鼓”,还是“八仙鼓”,不过都是“巴渝舞”的音讹或附会。因为如此,巴渝舞的道具留下后世附会的烙印,如其鼓面绘蛇、象和八仙的图形。其实剔除其后来衍生出的传说,巴渝舞与今存藏羌铠甲舞、目瑙纵歌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性质与功能。
对今存铠甲舞的田野考察,结合与之相关联的传世文献,我们不仅能窥见不同民族在相同历史阶段的仪式文化,也可以对一些学术界已成定论或尚有歧见的相关问题作重新审视,如史乘所载周灭商的“前歌后舞”,以及屈原《九歌·国殇》所据仪式的原生形态及其背景。
二
《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6]21这里所说的“巴蜀之师”,确切而言,应为巴人之师。《华阳国志·巴志》又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6]21有学者以为,《尚书》牧誓八国,并无巴人;武王伐纣之“前歌后舞”,与巴人无涉;刘邦称巴渝舞为“武王伐纣之歌”,“只是赞叹、自诩之词辞”,不足为凭;“武王封宗姬于巴”,说明并无赐巴人姬姓之事[7]。此说是。依笔者考校相关载记,“前歌后舞”之说不仅与巴人无关,且就“前歌后舞”发生的时间和性质也有三种说法。
其一,战前仪式说。《毛诗正义》卷一六之二载孔颖达疏:“伐纣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诗人反言众人之劝。武王见其劝战之甚,《太誓》曰:‘师乃鼓噪,前歌后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无怠。’是乐劝武王之事。”[8]508《礼记集说》卷五三载孔颖达疏,周因伐纣,“以登歌下管之事,歌舞其乐,以明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兴起文王武王之有徳,使众前歌后舞也”[9]109。宋人林之奇《尚书全解》释《泰誓》曰:“武王缵文王之绪,适当天人之所归。则其所处之势,固不得不应天顺人,以拯生民之命于涂炭之中”,“以伐纣之事,告于天地神祗而后行也”[10]411。由是可知,武王与其部众本皆有伐纣之心;其以歌以舞,乃是战前举行祭祀活动,且借巫之口宣示上天将佑于有德者,意在鼓励周人“孜孜无怠”,增强必胜的信心。
其二,歌舞征战说。《乐纬》:“武王承命兴师,渡孟津,前歌后舞。”[11]767《艺文类聚》引《乐稽耀嘉》:“武王承命兴师,诛于商,万国咸喜。军渡孟津,前歌后舞。克殷之后,民乃大安。”[11]224以上所说的“前歌后舞”,皆发生在周人渡孟津之后,战场之上。《华阳国志》的“前歌后舞,以凌殷人”,很有可能由此而来。有学者因此说:“武王伐纣,巴人前歌后舞,以锐不可当之势击败商军,写下中国历代战争史上唯一以歌舞破敌的绚丽篇章”[12]。笔者以为,敌对双方兵戎相见,生死只在刹那之间,巴师固然“勇锐”,但在战场上以歌以舞,打败敌人,恐不合常理。然而此说影响甚大,“前歌后舞”此后常作为典故使用。《汉书》载,更始元年,刘秀军据守昆阳,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率军四十二万围城数十重。王邑狂傲声称:“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13]4183这里的“前歌后舞”,用以形容军队的所向披靡。后之仙道传说,亦有附会为亲见者。晋宋之际,巴西阆中自称“虽万里外事皆如指掌”的范豺,即大言:“我见周武王伐纣,洛城头战,前歌后舞”[14]257。
其三,胜利献祭说。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引《乐稽耀嘉》:“武王兴师诛商,万国咸喜,前歌后舞,此恺乐之所繇昉也。”[15]164虽同出于《乐稽耀嘉》,此说的“前歌后舞”是在“克殷”之后,与前所引叙事的顺序完全相反。《周礼注疏》注“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云:“大献,献捷于祖’,“恺乐,献功之乐”[16]791。可见,“恺乐”即凯旋之乐。此说以武王伐纣在前,歌舞祭献在后,前因后果,甚为分明。
以上三说,笔者以为第一说与第三说最切近事实。第一说应为周人出征前举行执戈而舞的仪式,借神谕增强信心。第三说乃周人以胜利告祭祖宗鬼神于社稷,且以祭奠战死的英魂。参照藏羌铠甲舞,笔者于“前歌后舞”试作以下解读:一是互文,谓参与者无论前后,皆以歌以舞;二是或如黑水藏族的“卡斯达温”,男性执兵器在前,女性起歌舞于后。上古时期,歌戈属同一韵部,可相通假。若将“前歌后舞”释为“前戈后舞”,比照卡斯达温,则有更为合理的解释。
“前歌后舞”的传说与巴人扯上关系,始于刘邦。周武王灭殷之后,封姬姓于巴,以江州(今重庆市)为都。后巴北上灭彭,战国时迁都城于旧彭地。巴蜀交恶,巴迎秦军灭蜀,亦相继为秦所灭。秦惠王置郡县,命此地曰“彭道”,后改名“阆中”。《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阆中有渝水(嘉陵江支流,今名流江),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5]2842刘邦如此案断,有诸多问题难以解答。武王伐纣到西汉建立相距八百多年,其间经历春秋战国、焚书坑儒、陈涉起义、楚汉相争。以刘邦的不学无术,焉知“武王伐纣之舞”是什么样子?刘邦所见巴人歌舞,是否一定就是周伐纣之“前歌后舞”?笔者以为,经历春秋战国,周人武舞早已失传。刘邦观巴人武舞,臆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且命宫廷乐人习之,或因自己尝借巴师助战而自比武王,更借周礼之名,为汉家制礼作乐正名。或许正因为刘邦有此一说,才有《华阳国志》拼凑出巴人助周灭殷、“歌舞以凌”故事。
其后与铠甲舞性质相类者,乃有屈原《九歌·国殇》所据之民间祀仪。其辞云: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如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2]970-986
朱熹《楚辞集注·九歌》云:“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屈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17]30由注可知,屈原流放沅湘,观楚国民间祭祀舞乐,乃以其所见所感,“更定其词”,而作《九歌》。是知《九歌》当属诗人观民间祭祀而感发起兴,且由此展开文学的创造,故其中既有如实的描写,更有诗意的想象与文学的描写。似乎可以这样说,《九歌》在相当程度上是屈原在民间祭祀仪式基础上创作的歌舞剧本。因为如此,在无其它文献可考的情况下,仅就阅读诗人留下的《九歌》,读者很难具体再现楚之巫觋作乐、以娱鬼神仪式的历史原貌。朱熹又注“国殇”,“谓死于国事者”[17]45,是知《国殇》的受祭者乃为国捐躯的将士。前贤对《国殇》所述种种皆有详细探讨,唯独对屈原所见该仪式的程序、歌舞等,无法作进一步的研究。笔者以为,参照今所见藏羌铠甲舞,似可窥见《国殇》所据仪式的原生形态:藏羌铠甲舞的参与者皆以歌以舞,其歌或合唱,或一人领、众人和,歌词简短,有的无实义;音乐质朴,有的近乎呼号。其舞虽男女分列,动作有别,但其踏歌而行,动作简单重复,粗犷质朴,却是共有的特点。以此推之,两千多年前楚地之远古祭祀,风格想亦如此。对照此类仪式,屈原所作,既有依据,更多创造。如首句“操吴戈兮被犀甲”,为诗人对祭祀参与者所执道具、所着装束的直观描写,当属实录。“车错毂兮短兵接”至“霾两轮兮絷四马”六句,则是描写双方在战场的生死搏杀。可以想象,如此具体而激烈的战斗场面,祭祀仪式不可能直观复现,参祭者只可能或将其内容诉诸歌唱,或以象征性的舞蹈予以摹仿。屈原对战争的文学性描绘,正由此而来。“援玉枹兮击鸣鼓”句既是诗人对祭祀现场仪式鼓乐的直观描写,也是对战场鼓声雷动的文学联想,战争的激烈程度由此得以生动体现。“天时坠兮威灵怒”以下十句,乃屈原在现场祭歌的基础上创作的颂赞之歌,具有很强的抒情性。由此可知,解读《国殇》,对战场的实况、仪式的象征与文学的创造三者间的区别与关系,应有清晰的辨识。而三者之中,对屈原的创作起关键作用的当属仪式。屈原虽不可亲历或亲见战场之激烈搏杀与惨烈牺牲,却可以通过对仪式的观照,驰骋想象,抒发情感,《国殇》乃有今日之神采飞扬。此外,参照今之藏羌铠甲舞,笔者还推想包括《国殇》在内的《九歌》,皆可诵而不可歌。如前所言,仪式的歌舞音乐简单而朴野,显然无法与《国殇》文人化的歌词相配合。《九歌》最终能否和乐而歌,只可能取决于屈原是否为之谱以新曲。史乘于此,不仅无所记载,反倒是《汉书》所叙汉人以楚声诵楚辞,确能证明屈原楚辞的可诵而不可歌。故笔者尝云:“屈原汲取楚民歌而自铸伟词,虽未必能与原来的歌舞音乐相和,但能‘不歌而诵’却是一定的,否则汉代宫廷里就不可能朱买臣、九江被公等诵楚辞的事发生。”[18]31
三
由以上叙述可知,上古文献所载武王伐纣之“前歌后舞”、屈原所见之祭“死于国事者”,与今所见藏羌铠甲舞、阆中巴渝舞以及景颇族之目瑙纵歌,虽分属不同的时代,却都有相同的性质和相似的特点。
首先,皆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其一,用于出征前的誓师,战后的庆祝胜利。其二,培养本部族人的尚武精神。如羌族、藏族皆规定凡男子十三,皆须参加铠甲舞,不仅接受军事的训练,也借以强化对自己部族的责任感,养成勇敢无畏的品质。因为如此,铠甲头盔、长戈利剑,乃是必有的装备。一位接受笔者采访的景颇族学者甚至认为,目瑙纵歌就是具有准军事性质的仪式活动。其三,颂扬与祭奠战死者,祈求亡魂护佑自己的家园和亲人。汤炳正先生以《论语·乡党》“乡人傩”、《礼记·郊特牲》“乡人禓”中“傩”、“禓”异名同实为据,考证“傩”的本字为“”、“禓”的本字为“殇”,“《九歌》中之《国殇》,实即‘国禓’,亦即‘国傩’耳”[19]64。此说甚是。汤先生以为“行傩,乃欲以强鬼之力驱逐疫鬼”[19]62,“国殇”中的“强鬼”,实指为国捐躯疆场的将士。在先民看来,他们既足以驱逐鬼魅、保护乡民,更足以振奋士气、威慑敌人。观今存藏羌铠甲舞之功能,《国殇》所据仪式的目的,也应该与战争、狩猎等活动有关。
其次,皆有极其广泛的群众性。巫文化时期的原始宗教是全民的共同信仰,参加与原始宗教信仰相关的仪式活动,也是全民的共同义务。尤其是战争关系到每个家庭与个人的生死存亡,男女老少皆会主动积极地参与,故铠甲舞没有旁观者,只有参与者。贾公彦《周礼注疏·夏官司马》据《礼记·月令》分先秦傩为季秋天子之傩、季春诸侯之傩、季冬庶民之傩三种,汤炳正先生由此认为:“‘国殇’既非天子之傩,亦非庶民之傩,乃诸侯国之傩,则《九歌》中楚之《国殇》,亦当为楚国国家祭典中用于傩祭之歌。”[19]64然王逸序《九歌》明言:“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2]745,此“俗人祭祀之礼”应属贾公彦所谓“庶民之傩”。以笔者田野考察诸民族的仪式性活动皆见于村寨,足可为证。但天子诸侯与庶民虽有等级的差异,祭祀阵亡者的目的却是一致的。故以《国殇》属“庶民之傩”与汤炳正先生以《国殇》属“诸侯之傩”,在性质上并不矛盾;庶人之傩与诸侯之傩乃至天子之傩之间,其实是有双向互动关系的(详见下文)。
第三,皆有大抵相似的固定程序和内容。藏羌铠甲舞与目瑙纵歌必由村寨中的巫师或有威望的长老主持。正式跳铠甲舞之前,先举行祭祀祖宗鬼神的仪式,以驱逐恶魔,然后由长老带队,男子披甲持刀(或戈矛)相随,且歌且舞。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女子执酒杯或扇帕,与男子或并肩而行,或紧随其后;或齐唱,或多声部重唱。所唱内容不外颂扬、祈福、驱魔等。唯巴渝舞与目瑙纵歌只舞不唱,但其舞蹈的盛大规模,舞者的并肩而行,长刀的须臾不离,队伍的逶迤穿插,已足以表达丰富的祈祷内容(在舞蹈过程中,目瑙纵歌尚有数位男子在队伍中不时挥刀跳踉,以示驱赶混迹于场中的恶魔)。藏、羌铠甲进行到高潮,所有男子持刀模拟搏击拼杀,场景激烈,声震于野。而铠甲舞进行到尾声,则是另一场群众性娱乐高潮的开始。由上述铠甲舞的程序和内容,大致可以推想周人之“前歌后舞”与《国殇》所据民间祀典的基本形态。
第四,皆有年节化与即时性相结合的特点。笔者考察的铠甲舞、目瑙纵歌、巴渝舞,大都在秋收之后、春播之前的春节期间。其时仓有粮,人有闲,有条件举行重大的仪式活动,这一活动的年节化乃成为可能。在自然经济的背景下,年节化的仪式除了能更有效地实现上述目的,还可以通过有预期的活动,为民众提供可贵的社交机会,以便加强族群的血缘记忆与文化记忆。从目瑙纵歌对其行进路线的复现,可见景颇族对自己迁徙历史的刻骨铭心。当然,年节化仪式的最终意义,还在于有效地凝聚族群,给族群注入更为强大的生存能力。《国殇》所据原型虽不能断定其举行时日,但亦应不出这一规律。唯今所见卡斯达温不在年节之列,故很难断定它曾经有过的时间形态。
在铠甲舞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其内容与形式不断有所延伸或衍变。如景颇族目瑙纵歌的最初目的,在于出征壮行、庆祝胜利、祭奠英魂、祈求护佑、驱邪逐魔,最后却延伸出礼葬长者、祭奠祖先。随着延伸内容逐渐增多,诸如兄弟分家、新房落成、婚丧嫁娶、祝人丁兴旺、求财源广进等等,皆举行规模不等的目瑙纵歌。羌族的中小型铠甲舞则往往用于娱乐、踏青乃至红白喜事。这样的延伸和衍射,一方面使某些民族的铠甲舞具有了年节化与即时性相结合的特点,另一方面又使其仪式及其歌舞渐次失去原有的性质,而完全演变为群众性的年节娱乐活动,如阆中的巴渝舞。笔者甚至相信,所有民族在其巫文化时期,都因狩猎与战争而举行过类似的仪式。只是因为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的改变,这些仪式活动最终发生变异、淡化乃至消泯了初始的意义和形态②。即便有个别的文化符号一息尚存,却因其物象、事象背景的逐渐隐去,其面目最终变得模糊不清。更何况有的已完全失落于历史的长河,而成为民族文化史上无法弥补的永久遗憾。
四
以历史考察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观照古今铠甲舞,其学术的认知价值或远不止于此。
首先,我们可以由此窥见古代宫廷仪式文化与民间仪式文化之间的血缘联系。
春秋时期,天子失政,礼制散在民间。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13]1746,指的是将散在民间的西周宫廷礼制加以拾掇、重构,以期还原周礼。然而,我们在对铠甲舞作历史与田野的考察过程中,却看到另一个现象,即“制礼而求诸野”。上古时期,朝廷礼制的原型,其实往往来自民间。殷商处于巫文化的时期,巫文化本身就是上层与民间共有的文化,其仪式及其歌舞由全民共享。由商而周,中国由巫文化向史官文化过渡。史官文化虽属宫廷文化,宫廷制礼作乐却不可能凭空而起,民间巫文化的仪式应是其借鉴的蓝本。于是在巫文化中熟知仪式且担任司仪的人,因其技能能满足人生之需要而被称作“儒”,亦即孔子所说的“小相”[20]254。儒又可分为民间之儒与宫廷之儒。宫廷之儒是宫廷仪式文化的制作者和主持者,但他们所据的蓝本,往往是民间之儒运作已经十分成熟的仪式及其歌舞。只是因为巫文化中被虚拟化、象征化的礼拜对象已经具体化为人世的君王,更囿于宫廷为仪式演示提供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度,其仪式乃越来越规范化、程序化甚至表演化。故天子、诸侯、庶民的仪典,其性质、程序、内容应基本相同,唯奢俭繁省有异。《毛诗正义》“周公象武王伐纣之事,作大武之乐”[8]597,《毛诗李黄集解》“武王之心,见于武舞”[21]713,西周宫廷武舞之制定在“前歌后舞”、武王灭殷之后,正说明宫廷仪典的初始形态原本存在于民间。屈原放逐沅湘所见民间祀仪与楚国宫廷的祀典,关系想亦如此。
汉以继承周祚自居,以复兴周礼相标榜。然事隔久远,周礼复兴,谈何容易!叔孙通与其邀请而来的儒生共同为刘邦制定汉仪,这些儒生大抵是熟知乡野仪式的“小相”即民间之儒。他们制定朝仪所据的蓝本,大抵为存活于民间巫文化的仪式遗存,即有散在乡野的周仪;但因其沦落乡野数百年,亦不免为民间之仪所改造。故其所定汉家礼仪杂糅朝野,绝非纯粹的周礼。巴渝舞之进入宫廷,正是生动一例。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写帝王观八方舞乐,“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22]128,巴渝舞即其中之一。可见,已经上升为宫廷武舞的巴渝舞当时仍葆有其群众性的特点。但与此同时,乐师为之配备“矛渝”、“弩渝”(一作“安弩渝”)、“安台”、“行辞”四套乐曲,“其辞既古,莫能晓句读”[23]893,又可知其成为宫廷武舞后,即开始了它的雅化过程。《宋书·乐志》载,曹丕称帝后,改巴渝舞为昭武舞[24]534。唐代以后,宫廷化了的巴渝舞消亡,民间的巴渝舞依然长盛不衰。今阆中巴渝舞即其流风余韵,昭示了民间文化两种不同的走向与结局。
从周人的“前歌后舞”进入西周宫廷,巴人的“巴渝舞”进入汉家宫廷,正说明了宫廷的仪式性活动雏形来自民间。宫廷与民间的仪轨虽有雅俗、精粗之别,但其双向互动,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仪式文化的发展。以此而言,似可将孔子的话补充完备:制礼,求诸野;礼失,亦求诸野。
其次,对铠甲舞的历史考察与田野考察,还为学术的文献形态提供了新的认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这些文献因其形式与内容的固化,似可称作固态的文献。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文献值得注意,即至今仍存活于民间的歌谣俚曲、传说故事、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既是历史的文化遗存,又是当下的文化存在。他们起于何时,难以考证;对它们在漫长流传过程中的形态变化,很难做出具体的描述与分析;如果环境许可,它们还将继续生存与发展下去。正因如此,它们积淀有深刻的族群文化记忆,荷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极具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我以为可以把它们称作“活态的文献”。故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有用信息的文献,应该有固态与活态两种类型。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主要依靠传世文献或出土文献,这类文献因岁月的销蚀与遮蔽,其文化信息的完整性与生动性往往会大打折扣。如前所言周人之“前歌后舞”、楚人之《国殇》以及刘邦所见“巴渝舞”,传世文献所提供的仪式形态极其简括乃至模糊。正是因为有当代藏羌铠甲舞、景颇族目瑙纵歌、阆中巴渝舞等活态文献相与印证,我们才有了窥探历史真相,且进一步接近原貌的可能。故本文对古今铠甲舞的考察,对于抢救、保护活态文献以及如何利用活态文献,或有参考的价值与意义。
注释:
①以仪式性舞蹈象征先祖之迁徙过程与特点,亦有见于其他民族者。贵州凯里市雷山县苗族反排村每十三年举行的牯藏节,男女必跳木鼓舞。据领舞者、非遗传人万政文介绍,舞蹈动作乃模仿先祖从江西向西迁徙途中情景,如斩棘爬山、涉水过桥以及躲避鱼兽之害,等等。
②如尼泊尔塔鲁人的“木棍舞”。塔鲁人是今生活于尼泊尔奇特旺丛林地区的少数民族,公元16世纪从印度迁徙而来,至今保留有母系社会与巫文化的遗存。塔鲁族人曾经以狩猎为生。他们进入丛林时,两手各执一短木棍防身,且不时以敲打声威慑野兽。塔鲁人把击棍的技巧纳入他们的狩猎仪式,从而形成“木棍舞”。“木棍舞”的参与者围成一圆圈,圆圈中央一人击鼓,一人吟诵祈祷,其余的人或循顺时针,或循反时针跳舞,同时自击或互击木棍。可以推想,“木棍舞”不仅是与狩猎、亦是与战争相关的仪式活动的重要内容。
[1]尚书大传[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
[2]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羌族词典》编委会.羌族词典[K].成都:巴蜀书社,2004.
[4]耿静.羌乡情[M].成都:巴蜀书社,2006.
[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常璩,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7]田敏.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辩证[J].民族研究,1997,(4).
[8]孔颖达.毛诗正义[G]//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9]卫湜.礼记集说[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林之奇.尚书全解[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欧阳询.艺文类聚[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2]赵玲.巴人音乐中的“乱”与“和声”[J].长沙大学学报,2009,(1).
[1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曹学佺.蜀中广记[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何楷.诗经世本古义[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G]//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7]朱熹.楚辞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3.
[18]万光治.汉赋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9]汤炳正.渊研楼屈学存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0]刘宝楠.论语正义[G]//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4.
[21]李樗,黄櫄.毛诗李黄集解[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2]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23]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24]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唐 普]
History and Field Study of the Loricae Dance
WAN Guang-zh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By means of field study and documents, it is clear that qiangehouwu reflecting people in Ba helping the State of Zhou, Chu people’s dance in worship ceremony recorded in Guoshang by QU Yuan, Zang and Qiang people’s loricae dance, Jinpo people’s Munaozonghe and Langzhong residents’ Bayu dance are all ritual dances accompanied by music relating to wars and hunting in ancient times. Those wide spread dances accompanied by music have their definite intentions, fixed procedure and contents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court ceremony and civil ceremony can thus be seen. Those ceremonies are living documents which need to be preserved.
Loricae dance; field study;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living documents
2016-06-21
万光治(1943—),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辞赋文学、民歌与民俗文化研究。
I206.2
A
1000-5315(2016)06-012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