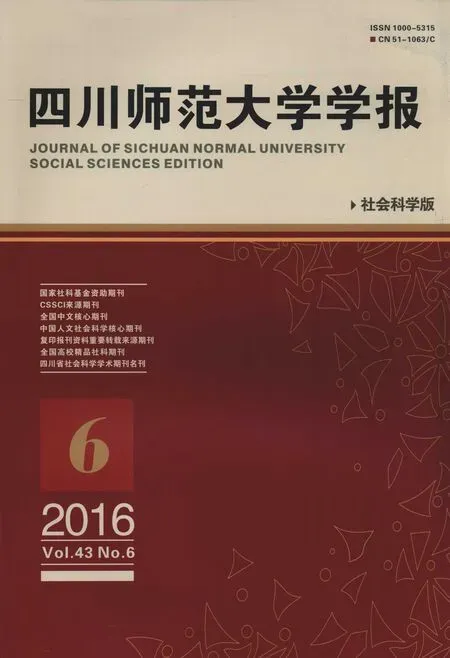黑格尔和“自我意识”的循环性问题
2016-04-13武潇洁
武 潇 洁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黑格尔和“自我意识”的循环性问题
武 潇 洁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当代自我意识理论的首要问题是主观自我和客观自我的同一性问题,关于该问题的讨论通常认为,反思理论容易导致主体的自我关系的循环性,而这种循环性正是建立自我意识理论的主要威胁。但这仅仅是在主观意识的层面上讨论自我意识。在黑格尔这里,为了表明思维和存在的内在同一性,自我意识被提高到“精神”的层面。精神是存在之唯一的、具体的总体性,在其完全发展的规定中实现自身。存在作为一个整体,表现为精神的自我规定和自我认识,思维最内在的规定性同时就是存在的规定性。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精神在其最丰富的内容中与自身的同一。在此意义上,自我意识必然是循环的,因为它是绝对的总体性的自我同一性。
黑格尔;自我意识;精神;绝对;统一性
自我意识问题一直是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自亨利希复兴了当代对“自我意识”或主体性问题的兴趣之后,学界相关的研究汗牛充栋。稍加留意便可发现,目前关于“自我意识”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主体性问题展开的,因此其意图也多集中在试图说明:(个体)自我意识何以可能。这些研究往往把自我意识作为一种意识现象,尤其强调主体如何能够反思到自身,即通过向内自省来获得自我意识是否可能。这里就涉及到自我意识的循环性或无限后退的问题。亨利希最早明确提出该问题,并试图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寻找解决它的思想资源[1]15-54[2]3-28;也有研究者对这种按照反思理论的模式来说明自我意识之可能性的路向不满,他们把自我意识和主体间性联系起来,以自我意识为社会交往的产物[3]1-17,但是这个思路并没有摆脱该问题与主体性的直接关联,自我意识仍然被视为是在主体性领域中实现的东西。
与此相关,被许多学者所忽略的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实际上为解决自我意识问题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黑格尔对该问题的思考并不是直接从“自我意识”概念出发的,而是与他的哲学的基本旨趣相关。在康德通过确定先验主体的权威而否定思维和“绝对”之间有概念性的联系之后,黑格尔看到,纯粹主观性具有形式主义的问题,他要在“精神”而非单纯主体性的层面重建真正的客观思维,即在概念中恢复作为存在整体的“绝对”。对黑格尔来说,自我意识在其最基础的层面上不是任何个体的自我意识,而是“精神”的自我意识或“绝对”的自我意识,它意味着存在在其充分发展了的内容中仍然在其自身之中,存在在客观概念的层面上就是自我完成的总体。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意识必然是循环的,它表示纯思维或纯概念的具体的、发展了的总体性。
一 问题的缘起
克劳斯·杜辛在其专门研究自我意识的诸种模式的著作中称,在当代对自我意识的讨论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进路是,对主体的自我表象或自我意识会导致的循环或无限重复的批评,仿佛这是主体性理论的最大敌人[4]97。这个颇具影响力的讨论模式就是由迪特·亨利希及其所代表的“海德堡学派”所奠定的,亨利希试图在当代一片反对传统哲学主体主义的声浪中重建主体性,即主体对自身的某种认识关系(das wissende Selbstverhältnis)[5]33-34。他认为这个目标的主要敌人就是反思的自我意识,在反思理论的模式下,自我意识会陷入循环,这会使得主体的自我认识不能实现。
首先,亨利希揭示出反思模式下的自我意识理论的困难。在反思理论中,自我通过返回自身,把自身作为对象,建立起一种直接的自我关系,从而获得自我意识或自我知识。亨利希指出,这种方案必然是循环的,它实际上预设了它只能通过这个返回才能达到的东西,如果自我没有预先知道自身,它就无法做这个返回,即在这个返回之前,它已经返回自身了[1]20-21。但是如果为了避免循环,声称进行反思的主体与反思所达到的那个主体不是同一个东西,那意识的统一就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反思所获得也就不可能是它自己所期许的关于“自我”的意识,反思本身也失去了意义。
其次,亨利希指出,费希特第一个意识到反思理论的这种循环性,并通过不断的自我修正试图建立一个完善的自我意识理论。费希特并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把自我意识作为一个奠基性的原则,而是要研究自我意识本身的性质和结构。在亨利希看来,自我意识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是“主体自我”和“客体自我”的同一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费希特把自我理解为设定自身的行动,自我既是它自身,又是设定它自身的行动,即自我既与自身明确地相区别,又与自身相同一,由此,主体既能达到自身同一,又不必预先设定一个自我在那里[1]26。
无论费希特的方案是否解决了反思循环,亨利希所延续的仍然是笛卡尔主义式的“我思”传统。自我意识还是以主体性的实现为依归的,这种自我意识往往仍然局限为一种单纯的意识现象,就此而言,与反思模式并无区别,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反思的自我意识模式不过是一种心理学的错误。哈贝马斯指出:“亨利希所依据的还是他的对手所立足的意识哲学模式,根据这个模式,主体不论是在思考还是在行动,都用一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对待对象或事态。而认识论的自我意识对于这样与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的主体性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6]376。
图根哈特也对亨利希的策略提出了相似的批评。他认为,在传统自我意识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就是一种认识论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依赖的就是主客模式,亨利希对该问题的论述正是对这个传统的延续。他的困难在于,既把主客关系理解为一种知识,即认识与被认识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坚持关系双方为同一个东西,这就出现了一个两难。图根哈特认为,知识是命题性的(propositional),某一主体的对象并不是另一个实体,不是一般的空间对象,而是一个命题,这是意识关系之所以是意识和对象的关系,而非两个对象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3]10-12。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有内容的意识关系中,一方是一个实体(人),另一方是一个事态或经验,二者具有根本差别。就自我意识而言,如果自我以其自身为对象,就不能形成任何知识,而要获得知识,自我和对象就不可能是同一的。这是亨利希坚持自我意识中主客同一所必然导致的悖论。
与此相应,图根哈特指出,自我意识不是意识关系,而是主体间的社会性关系。但是,图根哈特摆脱了意识形式,却并没有摆脱、也并不试图摆脱对重建主体性的坚持,无论是社会性的还是主体间性的,都是主体实现自身的活动,不同的只是这个实现领域的范围的大小,它的立足点仍然是个体自我。
二 黑格尔和自我意识问题的两个传统
黑格尔对自我意识的态度和当代讨论自我意识这两种方式都相当异质,但也极易引起误解。黑格尔并不否认自我意识与主体性的关系,也不否认在主体的意识行动中自我对自身有意向或知识,但是对黑格尔来说,这种意识如何产生、具有什么内容、到底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即自我意识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都不是能够在单纯的意识层面得到直接解决的问题。对黑格尔来说,“自我意识”的真正意义在于“精神”、“理念”、“绝对”这些表示绝对的整全存在具有“自我意识”或最终达到“自我认识”。换言之,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我意识”在根本上或从广义上说并不是与其他概念相并列的另一个概念,它只处在其逻辑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上。相反,黑格尔要恢复被二元论所割裂的世界的统一性,“精神”、“理念”或“绝对”就必须是自我意识的,即实现自身或自我完成的总体性。“自我意识”不是一个主词,而是一个谓词,是整体的、精神性的实在的一个谓词。黑格尔在1807年《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绝对知识”中明确指出,真正的自我意识是对“精神”的认识,并且“不仅仅是对神的直观,还是神的自我直观”[7]426。这就意味着,自我意识必须成为超越了个别自我意识主观性的普遍反思,它不仅仅是意识的真理,更是绝对的精神和理性的真理,它不是局限在一种意识现象上的东西,而是绝对精神向自身的返回。
黑格尔这样处理自我意识问题,是建立在对他之前两个传统的深刻反省之上的。当时,他关于这个问题至少有两种现成的选择:一种是笛卡尔式的,一种是康德式的。
在笛卡尔那里,只有作为思维者的自我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而一切意识都是自我意识的一种。他在“第二沉思”中就明确指出,“自我”对对象的知觉不仅仅是与对象相关的,它同时也是意识到我在进行知觉活动,即对我的主观心理状态有明确意识,一切对外部对象的知觉都只能更有效地证明我自己的心灵的性质,而且我对自己的精神比对其它事物具有更清晰的知觉,人类精神的性质比其它事物更容易被认识。由此可以看出,笛卡尔的自我意识是对纯粹思维自我的反思或内省,在一些语境下是主体对其自身心理活动的反观,是把意识本身作为意识的对象,自我意识完全是在主观意识内部发生的活动。
在关于“自我意识”以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康德远远超越了笛卡尔。康德认为,进入意识的一切内容都是表象,即便是谈到“自我”,也是关于自我的一个表象。它的内容不是关于主体自身的,而是关于进入到经验中的直观对象的。这个自我除了一种形式性的逻辑意义之外,并不意味着对作为一个持存实体的经验主体的知觉。因为无论内部表象还是外部表象都必须借助于同一种直观,我们不具备另外的直观可以把对主体的知觉与对其他对象的知觉区别开来,从而能直接把它表象为一个持存的实体。范畴层面上的先验主体本身是空洞的,只有通过把表象的杂多统一在一个意识中的功能,才能设想自我意识本身的同一性。就此而言,康德的观念论是相当彻底的,思维规定虽然有其主观的根源,但它在效用上却超出了主观性,因为作为思维驻地的主体是先验主体,它是一种普遍自我,是逻辑上的形式同一性,经验中的主体和客体作为对象都在这种先天思维诸规则的约束之下。
这样一来,笛卡尔所谓的自我意识就瓦解了,由经验反思获得的对主体的知觉根本不是自我意识,而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对象意识,因为能够成为意识对象的主体只能是经验主体。在康德看来,经验主体是偶然可变的,它与其它对象没有什么区别,主体以意向一个对象的方式来对待自身,这与它转向自身之外的它物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要服从同一套概念规定,这样的主体毫无绝对性可言。因此,笛卡尔虽然提出了主体性的原则,但是实际上没有完成对主体之为主体的任何有效规定,主体仍然是物性的。
因此,对康德来说,“我思”、“自我”或“自我意识”等所代表的并不是与“对象”并举意义上的主体,不是可计数的任何个别存在,而是主体的普遍的形式统一性,是一个悬拟的可能性条件。只有这种主体才能摆脱经验主体的偶然可变的心理学活动,建立起对象世界普遍必然的可理解性。只有以自我意识的这种形式统一性作为起点,才能证明主体的统一性同时也是关于对象的客观统一性。
康德虽然仍是从主体一侧进入自我意识,但是他以“我思”或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为范畴客观性的先天来源。他用先验而非经验的方式指出,主体之为主体的合法性并不仅仅在其自身,而且在它与对象的关系上,因为没有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经验,单纯依靠反思就不能获得对自我的经验。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比笛卡尔规定了更高的哲学任务。笛卡尔只是提出了纯粹主观性的原则,以及抽象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对他来说,确定性比真理更重要,只有思维与外部世界相关联,才会出现欺骗性的问题,而单纯的思维本身则无真假可言,所以思维应当从它自身开始,并从这个思维来推出存在。但是,这样的“我思”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由此推出的存在也不过就是思维的直接的“自身关联”[8]73。
康德则要使本身是主观的东西具有客观性,即要使思维具有普遍必然的对象相关性。康德不仅仅意识到,思维必须与存在相同一,而不是把存在视为怀疑论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试图用概念来规定实在,认为除了这种概念规定之外,就不可能有普遍必然的知识。在康德这里,概念和一般经验表象的差别不再仅仅是清晰程度上的差别,概念也不仅仅是对观念的简单复合,相反,二者具有根本的区别。概念的真正本质在于其统一性功能,它是统觉的综合统一,概念的统一性是内在于“我思”自身的本源的统一性,是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
正是这样一种源自抽象主体(先验统觉)的逻辑行动为主客统一奠定了新的基础,正是对主体的这种理解从根本上塑造了之后的整个德国观念论。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就反复赞扬康德在范畴的先验演绎中已经开始探讨纯粹概念的本性,“这个统觉的原始综合对思辨的发展来说是最深刻的原则之一,它包含了对概念的本性进行真正把握的开始,并且与那种自身中没有综合的空洞的同一性或者抽象的普遍性对立”[9]22。黑格尔认为,只有概念才能够真正达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这一点康德已经看到了,并为说明这一点进行了最初的尝试。
所以,在康德这里,主体的权威实际上是概念的权威,除了先天概念的判断活动之外,主体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康德之所以把概念放置在先验的自我意识或“我思”之中,是为了强调那些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绝对不是从知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它不受感性刺激的左右,而是先天地处在主体之中,自我意识而非经验才是其来源。只有具有先天来源的概念,才能在经验中自发地起作用。在康德这里,概念本身高于任何经验主体的知觉活动,它能够进行先天综合判断,这个判断不来自经验,却能有效地处理经验。
理性自发地产生出概念,我们借助于这些概念来与世界发生关联,这是康德为德国观念论提供的一条基本洞见。把主体和世界关联起来,个体追求自身与大全的统一,这也是德国哲学由来已久的传统[10]。然而,康德的概念或范畴仍然是空洞的、无内容的,他虽然要求范畴的经验运用,试图为概念获得内容,但是由于他把整个感性世界看作是和理性(无论是思辨理性还是实践理性)相反对的东西,是否定主体之自由的东西,所以,世界的同一性仅仅是人的理性综合的结果,世界的秩序是被知性所规定出来的秩序,是主观秩序,不是世界自身的秩序,世界仅仅对我们才是可理解的,就其自身而言,我们则无权断言其合理性或统一性。就此而言,康德只不过证明了主观性本身是合乎理性的,而世界本身是否合乎理性则不得而知。所以,在康德这里,概念的内容不是概念本有的内容,而是外来的,是由经验提供的,概念就其自身而言,仍然是空洞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并没有真正实现,二元论依然存在。
黑格尔并不否认人是在主观理性的层面上有限地看待世界的,但更重要的是,黑格尔要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有限性是内在于一个整体性的、无限的世界视域中的。所以,我们作为有限的个体,之所以具有合乎理性的经验,是因为世界本身或存在作为一个整体即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称这种合理性为概念的形式。世界的可理解性不是主体赋予的(即便这个主体是先验主体或普遍主体),相反,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这个世界,恰恰在于世界本身就是可理解的,我们主观经验的合理性与世界本身的合理性完全是内在一致的。因此,黑格尔必须证明,概念自身就是有内容的,世界的统一性是概念的统一性,思维和存在在概念的总体性中才是内在同一的。
三 精神和自我意识
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哲学必须以“绝对”为其唯一对象,而康德否认我们对绝对的无条件者具有任何具体的知识,这是黑格尔不能满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要把主体性发展到极致,似乎黑格尔认为主体理性能够超出经验直观的限制,达到对物自体的认识。这种理解不仅不能消除二元论,还会使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对立更加牢固。对黑格尔来说,“绝对”不是处在某种抽象的主体性对面的东西,而是自己规定自己的。因为存在作为一个概念的整体本身就是思在同一的,存在的统一性是事物摆脱其直接性和有限性,从而被提高到纯粹思维的形式中的本性。就此而言,一切真正的哲学都是观念论[11]142。
但是,存在在思维层面上的统一性,并不是说,存在只有在我们对它的主观理解中才是统一的,而就其自身而言,则仍然有可能是杂乱无章的个别事物的堆积,这是近代以来主客分立之后才出现的观点。黑格尔把自在的事情本身视为“纯思想”或“纯概念”,不是要把存在造成为主观的东西。相反,世界正是在思维或概念中才是真正客观的,因为世界只有作为纯思想,才能够发现自身完整的统一性,思想中的统一性是内在于存在整体本身的统一性。如果世界总是在感性经验遭遇到的杂多中流转跳跃,那就只会有无限多的有限者,而不会有就其自身而言的存在本身,也就没有“绝对”。
在黑格尔看来,一切个别的、有限的东西都是世界作为一个绝对的总体中的一个环节,这些环节就其自身而言没有现实性,不是绝对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观念的。同样,存在整体在观念上而不是在经验现实性中包含着这些环节,这个整体性并不直接呈现给经验,却是最实在的东西,因为它揭示了存在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存在是事物在思想中的存在[12]308-309。所以,存在与思维的同一,不是我们的认识与事物本身相符合,而是存在呈现在其内在统一性中,是存在成为一个总体,是存在真正回到自身或与其自身相符合。
黑格尔引入“自我意识”正是要表达思维和存在的这种内在同一性。只存在着一个“绝对”,它既可以被称为“存在”,也可以被称为“思维”。但是,这个唯一的“绝对”不是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实体,即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设定出来的绝对的完满性。如果“绝对”是一个可以现成拿来用的词汇,那么它和一个空洞的主观理念就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直接的抽象统一性处在一切多样性的对面,一切具体的东西仍然在它之外存在着,这种所谓的统一性就是虚假的,本身还是一个有限的东西,不是绝对。
黑格尔反复强调,“绝对”必须是具体的统一,“哲学当然是和一般的统一性相关的,但是不是和抽象的、单纯的同一性以及和空洞的绝对相关,而是和具体的统一性(概念)相关,并且在其整个进程中完全只和具体的统一性相关,——它的进展的每个阶段都是这个具体的统一性的独特规定,并且这个统一性的诸规定中最深刻和最终的规定就是绝对精神的规定”[13]459。那么,“绝对”作为一个具体的统一性,就必须经历一个自身规定了的过程,“绝对”是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才出现的。这个过程就是概念的总体。
所以,为了重建世界的统一性,就必须使“绝对”成为一个自身具体的东西,而非抽象的理智设定,于是黑格尔引入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意味着理性或精神的普遍内容是完全内在于世界之中的东西。世界的合理性是精神对其自身的揭示和表达,而非主观理性对外在质料赋予形式。“精神是完全自知并将自身完全表达出来的东西”[7]277。因为,概念或理性在黑格尔这里是纯粹思维的总体,是思维对自身进行思维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内容的全体,这个内容是合乎概念形式的内容,而不是经验内容,“绝对”是一个概念的具体,而非经验的具体。在这个意义上,形式与内容达到了真正的统一。在概念的总体的层面上,思维和存在本来就是同一个结构,它们没有主观和客观之分,或者说,它们都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
精神就是以概念的运动为其内在要素的绝对的大全,它不是静止的,而是活动的,它必须在其完全发展了的规定性中实现自身。“精神的发展就是自身超出、自身分离,并且同时是自身回复的过程。……举凡一切在天上或地上发生的——永恒地发生的,——上帝的生活以及一切在时间之内的事物,都只是力求精神认识其自身,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发现自己,达到自为,自己与自己相结合”[14]28。所以,存在作为一个整体,是精神性的,是属于普遍理性的,存在整体的一切内容都表现为精神对其自身的关系,是精神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认识。只有在精神的层面上,二元论才能得到克服。
这样一来,世界的无条件的总体性就不再是主客体的外在相合,而是绝对精神的自身统一性。真正的绝对是“精神”,精神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概念总体,它在其外化中也都是在其自身之中,世界的全部丰富性都是精神的丰富性。只有把自我意识提高到精神,黑格尔才能证明,没有对立的双方,只有一个唯一的存在,就是理念,这个理念是实在的。
所以,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提出关于实体和主体关系的著名论断时,表面上看,他是从实体出发,而非从主体出发,实体最终会表明自己是主体,是“履行着绝对精神的生活的”主体。但是,从根本上说,黑格尔要解决康德的问题,要超越一切形式的斯宾诺莎主义,他就既不能从主体出发,也不能从实体出发,既不能从主观性出发,也不能从客观性出发,唯一有效的立足点只能是那个绝对的总体性。这个总体性不是在一开始就完成了的,而是一个漫长的概念运动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能够表明,思维和存在其实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具有“概念”和“实在”两类名称。
至此,可以说,黑格尔并不是要用“自我意识”概念来重塑主体性的绝对权威,恰恰相反,他正是在近代哲学尤其是康德的先验学说那里看到了主观性的根本局限。如果范畴只是经验的形式规定,也即我们理解世界的工具(即使这个工具是思维先天从而普遍地具有的),那么世界永远也不可能被把握为一个整体。知性要么在脱离外部世界的抽象理念中打转,要么必须借助于直观来达到对象从而受制于这个直观。黑格尔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总是纠缠于思维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而是必须首先考察纯粹思维的内容本身,这个内容会向我们表明,纯粹的思维或概念自身就是思在同一的。在思维最内在的意义上,它必然和存在是一致的,存在在其最彻底的整体性上必然是概念的总体,而非感性经验的总体。
所以,黑格尔通过把自我意识赋予作为最高实在的“精神”,使精神成为理念与实体相统一的真正方式。一开始,精神将自身表现在意识中,这是精神要获得现实性的必经阶段。但是,在这些对象性的意识中,意识和自我意识或者实体与主体是分裂的,精神最终要实现自身为唯一的实在,就必须扬弃这种差别。它要证明,意识的任何形态都具有自我意识的形式,换言之,意识与其对象的关系都是精神与其自身的关系。可见,只有通过将自身实现为这样一种自我意识的关系,“绝对”才能消除自身的彼岸性,成为哲学的唯一对象,黑格尔对康德二元论的克服才有可能实现。
由此可见,在精神的层面上,自我意识才是可谈论的,而且恰恰是在精神的层面上,自我意识必然是循环的。因为“绝对”、“概念”或者“精神”都是无限的整体,只有整体才是最充分的自身同一性,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回到自身的东西,是最彻底的直接性。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当然是循环的,它的循环性不仅不是一个问题,还是必要的,因为精神是那个唯一的具体的总体,它不仅是一,还是一切。而自我意识就是指“绝对”从一个抽象的直接性向最终完成的总体性的前进,这种前进表现为一种返回,是从抽象的形式同一向具体的总体的返回。所以,在黑格尔把自我意识提升到精神的层面上之后,反思理论的循环性问题就无法进入我们的讨论视野了,因为它还是主体意识范围内的循环性,把该理论作为自我意识问题的最大敌人只能是对该问题的贬低。
[1]Dieter Henrich. Fichte’s original insight[C]//Contemporary German Philosophy vol.1.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82.
[2]Dieter Henrich. Self-consciousnes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a theory[J]. Man and World, Feb.1971,vol.4.
[3]Ernst Tugendhat.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Determination[M]. Translated by Paul Ster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6.
[4]Klaus Düsing. Selbstbewusstseinsmodelle: Moderne Kritiken und systematische Entwürfe zur konkreten Subjektivität[M]. München:Fink, 1997.
[5]Dieter Freundlieb. Dieter Henrich and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the return to subjectivity[M]. Hants:Ashgate, 2003.
[6]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G.W.F.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M]. Hamburg:Meiner, 1999.
[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9]G.W.F.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Zweiten Band). Die Subjektive Logik (1816)[M]. Hamburg: Meiner, 1981.
[10]布尔乔亚.德国古典哲学[M].邓刚译,高宣扬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G.W.F.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Erster Band). Die Lehre vom Sein(1832)[M]. Hamburg: Meiner, 1999.
[12]G.W.F.Hegel.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 Erster Teil.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 Mit den mündlichen Zusätzen[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
[13]G.W.F.Hegel.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M]. hg. F.Nicolin u. O.Pöggeler.Hamburg:Felix Meiner, 1959.
[1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责任编辑:帅 巍]
Hegel and the Circle of Self-consciousness
WU Xiao-jie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The primary issue of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self-consciousness is the identity of subjective ego and objective ego. Discussions on this issue take the circle of subject’s self-relation caused by reflection theory as a main threa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elf-consciousness theory. Self-consciousness is in this way discussed only on the level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For Hegel, in order to solve the immanent unity of thought and being, self-consciousness is lifted to the level of spirit, which is the only concrete totality of being and realizes itself in its fully developed determinations. Being as a whole shows itself as the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lf-knowledge of spirit, the deepest determinations of thought is also the ones of being. Self-consciousness of spirit is the self-identity of spirit in its richest content. In this sense, self-consciousness is bound to be circulate, for it is the self-identity of absolute totality.
Hegel; self-consciousness; spirit; absolute; unity
2016-07-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15年度项目“承认的政治与法的形而上学:黑格尔早期法哲学思想研究(1788-1807)”(15YJC720017)。
武潇洁(1987—),女,山东济宁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
B516.35
A
1000-5315(2016)06-0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