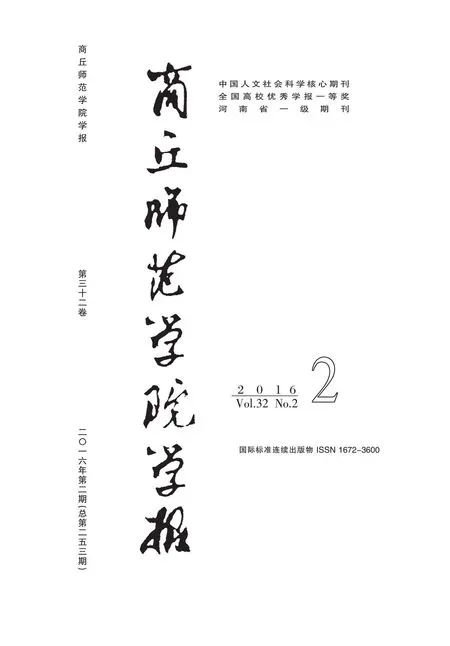《荒原》里的女性声音
2016-04-13蔡乾邵婷
蔡乾 邵婷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2.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476000)
《荒原》里的女性声音
蔡乾1邵婷2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2.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476000)
摘要:在T.S.艾略特的名作《荒原》中,女性占据诗中大部分叙述空间,成为“荒原”场景中的主要叙事声音。这些女性一方面来自艾略特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借用,另一方面来自生活在艾略特周围的现代女性。她们的叙事声音在诗歌中形成了从古到今、自上而下渐至无声的意义结构,这种结构中的趋势正是男性话语结构不断对女性施行压制和规训的结果。艾略特以此提出了“荒原”生机丧失的症结所在:两性之间的正常对话尚不能维持,那么社会发展的生机和动力又如何存在?
关键词:T.S.艾略特;《荒原》;女性声音;意义结构
T.S.艾略特的《荒原》是西方现代诗歌中的经典之作,被西方学者誉为“世纪之诗”[1]1-3。《荒原》用两性关系的堕落隐喻了20世纪初西方社会趋于颓败的文化境况[2]81:男人和女人无法正常的交流,只余下了欲望,而这种缺少了爱的滋养的欲望是贫瘠的,失去了生生不息的能力。如以性别叙事的角度通观全诗,则可发现诗中大部分的叙述空间被形形色色的女性占据,大多数典故也是始终涉及女性或有关两性关系的。相比于以男性叙事主体“我”为代表的男性声音的惜字如金,诗中众多的女性却展示出了众生喧哗之景。
在《荒原》中出现的女性叙事主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艾略特从西方文学传统中借用的女性。她们在原来的文本中就具有特定的意义指向,经过艾略特的采撷以后,她们的声音与原文本产生了互文性的互释,又生发出了新的含义。另一种是生活在艾略特周围的现代社会的女性。她们的日常话语经过诗人巧妙的剪裁同样加入了诗歌的意义构建之中。下面我们就这两种女性声音加以分析,以探寻《荒原》里的女性声音的内涵和作用。
一、互文性的女性声音
《荒原》中第一位出场的女性是题记里的西比尔,她被关在笼子里悬挂在库米城城墙上。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道:“我想死。”
题记直接来源于佩特罗尼乌斯《萨蒂利孔》第48章[3]78,更早成书的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有关于她更加详细的记载:年轻时的西比尔因为美貌得到日神的追求,日神想用馈赠的方式来打动她,让她任选一件事他一定为她办到。她要求自己的岁数和沙数一样多,但是忘记说不管活多少岁也要永远年轻。日神答应使她长寿,而且还答应使她永远年轻,但条件是必须接受他的爱情。西比尔拒绝了日神的要求,结果身体因为活得太久缩成一点点,四肢缩得和羽毛一样轻。但她认为:“虽然我会萎缩得别人都认辨不出来,但是人们还可以从我的声音听出是我,命运之神会把我的声音留给我的。”[4]293因为抗拒神的威权,西比尔的身体所代表的美貌和青春的女性身份属性消逝了,但她却不能随之死去,这使她处在一种生不如死的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声音依然表明她的存在和摆脱困境的希望。正如露丝·伊里盖雷所言:“有了声音便有路可走。”[5]209命运之神留给她的声音是珍贵的权利:能够用语言表达思想和主张是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公认的象征。西比尔的故事强调了声音的重要性,暗示了如果一个人无法发出声音,就只不过是一具在社会生活中没有身份的躯体而已。能够发声意味着有可能去解释和维持自己身份的独立性,这种解释和维持身份的权利在现代社会的混乱和嘈杂中就显得无比的重要。西比尔的状态是《荒原》这首诗中所有女性生存状态的隐喻:她们生活在无形的压迫中,或高或低地发出自我反抗的声音,以追求作为女性的自我实现。
艾略特从同时代英国作家赫胥黎的小说《克罗姆·耶娄》(Crome Yellow)第27章的情节里获得了灵感:小说中斯科根先生乔装成吉普赛女人,自称是来自米底王国首都厄克巴丹的女巫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他躲在帐篷里装神弄鬼地算命,居然大获成功[3]81-82。在第一章“死者的葬礼”中,艾略特把塞索斯特里斯改换成了索梭斯特里斯(Sosostris)太太,称她是“欧洲最聪明的女人”,并且让她用塔罗牌为诗歌的叙述者算命。但诗中的表述显示,艾略特对索梭斯特里斯太太的态度是复杂的:在诗歌中索梭斯特里斯是以“患了重感冒”的状态出场,所用的占卜道具被称为“邪恶的纸牌”,而且对独眼商人这张牌背后的牌是“不准我看那到底是什么”[6]135-141。这些描述透露出叙述者对索梭斯特里斯太太的占卜的怀疑和一丝调侃,他是不大相信她给出的模糊的结果的。Sesostris与Sosostris一个字母之差,很有可能是艾略特玩的文字游戏,用“Just so so”来嘲笑索梭斯特里斯太太的能力。而在赫胥黎的小说中,这个女巫本来就是易装而成的冒牌货。艾略特笔下展现出的是对女巫的智慧和预言能力的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这是欧洲历史上女巫迫害事件以来西方社会产生的整体社会文化语境的反映。有学者认为,“猎巫运动为强化对女性的控制和巩固男权地位提供了一种机会和手段。正是通过三个多世纪的对女巫的猎捕,男权社会得以重新巩固”[7]。从话语权的角度来看,对女巫的迫害事件其实是男性对女性解释世界的话语权的争夺,这种争夺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在《荒原》的原注中,艾略特说明了占卜中展示出的塔罗牌是诗歌中重要的形象和意义线索[3]105,但身为“欧洲最聪明的女人”的索梭斯特里斯却无法给出其确切的含义,这种耐人寻味的落差应该是由诗人的性别立场造成的。
再来看艾略特在第二章“弈棋”中提到的菲罗墨拉的故事,这个来自奥维德《变形记》的故事,也颇有深意。菲罗墨拉被姐夫忒瑞俄斯强暴。忒瑞俄斯为了避免恶行泄露,不但把她锁在森林深处的牧人小屋里,还割掉了她的舌头使她不能说话。菲罗墨拉通过把文字织进布里送入宫中来设法让姐姐了解了自己的遭遇,姐姐普洛克涅闻之非常愤恨,在救出妹妹以后,杀死了忒瑞俄斯的儿子来复仇。她们的复仇引起了忒瑞俄斯的暴怒,他拔出剑来扑向拼命逃跑的两姐妹。逃避中两人长出了翅膀,普洛克涅变成了一只燕子,菲罗墨拉变成了一只夜莺[4]119-126。
忒瑞俄斯为了阻止菲罗墨拉的揭发割去了她的舌头,使菲罗墨拉在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上都变得沉默,忒瑞俄斯由此展现了他男性角色的压迫性力量。他的暴行始终萦绕在诗篇之中,成为潜在的男性统治和压迫的阴影。艾略特有意地把菲罗墨拉的意象装入画框,放置在一间装饰奢华古典的房间里,作为“往昔的旧事轶闻”,与题记中的西比尔一样挂在墙上。这里的画框和笼子是这两位女性生存状态的一种隐喻——她们在社会中受到男性话语的压迫,在压迫中失声并被悬置起来,成了被观赏的对象。但菲罗墨拉不愿在忒瑞俄斯的控制之中失声沉默,她通过反抗变成了夜莺——一种善于鸣唱的鸟。她用失而复得的声音能力使“她那不可亵渎的歌声充塞了整个荒漠”,通过声音她向世人展现她的悲剧,维护她解释自我遭遇的自主性,这是对忒瑞俄斯的压迫的直接反抗。在《荒原》中,艾略特以“今天这世界仍继续在啼叫”[3]85来暗示:虽然真相与女性的声音可能会一时被掩盖,但不可能被抹杀。在第三章“火诫”中菲罗墨拉的歌声和忒瑞俄斯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场景中重现了压迫和控制、发声和抗争的题材。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8]2-3在《荒原》中,从文学文本中借用而来的女性声音是作为在“荒原”中生活的现代人的背景存在,文学文本意义的在场,会引起读者自然地比较,成为新的意义生成的基础。
二、现代的女性声音
《荒原》中现代的女性声音是艾略特从本人的生活经历中提炼而来的[9]57-60。
在第一章,诗人展现了一个名为玛丽的女贵族的回忆。回忆中有两个场景:一是一次带有浪漫色彩的邂逅,她与某个人在慕尼黑相识,交谈甚欢。在交谈中她回忆起童年往事,提到了小时候同一位大公表哥一起快乐刺激的滑雪,这是第二个场景[3]79-80。这些欢快的场景读起来似乎与《荒原》的整个格调不太相符,这是因为艾略特把事件后面的背景隐藏起来所致。这个玛丽就是玛丽·拉丽施伯爵夫人(Countess Marie Larisch,1858—1940),艾略特的夫人称诗人曾经同她交谈并把谈话的内容放进了诗歌里[3]80,而玛丽的表兄就是当时的奥地利王国的王储鲁道夫大公(Rudolf von Habsburg-Lorraine,1858—1889)。诗人其实是在这几句诗中暗指欧洲历史上的梅耶林事件:王储鲁道夫和他的情人玛丽·维色拉(Mary Vetsera,1871—1889)一同死在河畔的猎邸中,这是一桩王室丑闻。作为哈布斯堡王室唯一直系王位继承人的鲁道夫之死,直接导致了历史走向的改变,甚至影响到了一战的战前局势,导致了日后哈布斯堡王室的衰亡。玛丽·拉丽施伯爵夫人因是鲁道夫和玛丽·维色拉之间的介绍人而被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称为“不受欢迎的人”,又被伯爵丈夫抛弃,没有任何机会为自己辩护。她的声音实际上被主流话语结构所压制,放逐到了边缘。王室甚至用给她封口费的方式来阻止她写出事件的真相。因为被社会摒弃,她的后半生颠沛流离、贫困潦倒。在1924年的时候甚至在纽约报纸上发文称谁能提供她和儿子赴美的费用就嫁给谁,命运何其悲惨。艾略特采用的这几行诗句,是由玛丽·拉丽施带来的历史的“副文本”,她的这段话是对“逝去的好日子”的一种缅怀。这段回忆和她的自传《我的过去》中的记录都无法见诸正史,只能成为艾略特诗中的一处僻典。艾略特利用这段轶事暗示一战前欧洲的堕落是自上而下的,男女之间泛滥的情欲带来了死亡,更带来了欧陆文明的衰落。
第二章“弈棋”里描绘了一位住在奢华房间中的上流社会妇女,她的生活极其空虚无聊。尽管她作出了一连串的追问,但回答她的却是男性角色的沉默无语。她的生存状态显示她不仅是破碎的男女关系中不平等的弱势一方,而且还是浅薄无意义的现代社会的受害者。超过30行的描写她奢华房间的诗句,是在暗示现代生活缺少实质的意义,以及尝试通过对房间华丽的装饰来弥补意义的缺失。艾略特笔下的这个女人和她诸多的同伴一样,把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的想法窒息在对珠宝、香料及类似的奢侈品的占有中。这些奢侈品创造了一个迷乱的情景,使她们沉醉其中不再相信自己的感官,失去了理性的判断。这些华丽的房间以及珠宝和香料应是男性为女性所设,被放置其中的女性处在了一种“金屋藏娇”的处境,她们不但被动地沉醉于此,而且主动地用“奇异香水”去诱惑男性,“今晚我心情很乱,是的,很乱。陪着我”[3]85,这反过来加强了其中的男性的主导地位。女人发现自己局限在一个由男人决定和批准她们的存在和意义的话语结构中,所以才有了诗中女子的一连串的询问,询问男人的想法、意见和日程的安排。她试图通过对男性的不断提问,来建立自己与他相对应的身份,但她的努力却在男人的沉默中变得徒劳。因为男人相信自己高于女人,对女人的焦虑和渴望可以轻易地予以忽视而不去试图理解,她的声音因此变得无效。这两人的关系也在因男性的冷漠以及话语结构中女性面对的不平等中濒临崩溃。
接下来诗中的场景转移到伦敦的一家酒吧,比尔、露和梅这三位太太在一起谈论一位未出场的名叫丽尔的妇女的家长里短。从这三位下层社会的女性的角度来看,丽尔应该努力去讨好她的丈夫,去把不好看的牙齿拔掉换成漂亮的,打扮起来不要看上去像个“老古董”,要老老实实地继续为丈夫生儿育女。丽尔的女性朋友的谈话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男权压迫。无论是在丽尔的丈夫还是在她的三位女性朋友眼中,丽尔的身体是非自主的而且理应是男性欲望的对象。丽尔不去镶牙打扮而去吃避孕药逃避生育的行为,在她的朋友看来是“应该害臊”的、是“十足的大傻瓜”[3]88,是偏离社会和性别规范的离经叛道,她应该回到和她丈夫的“正常”关系中。丽尔在诗中没有出场更无法发声,她对男性权利的反抗行为在她的女性朋友所维护的话语结构的叙述中变得毫无意义,充满了无望的色彩。
最后一个出场表露声音的女性是“火诫”中的女打字员。她和小办事员的交往看起来是仅仅献身于这个男人的欲望和要求。虽然这个场景让读者回想起了菲罗墨拉的遭遇,但相比之下,女打字员的麻木更加深刻地反映了现今社会的悲剧。她好像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完全接受,她的麻木无语像是已经绝望地相信她在社会中的角色就是欲望的对象。菲罗墨拉的反抗在她的身上看不到丝毫的踪迹,这代表着现实中的女性的无声堕落。事实上,她脑海中出现的但没有说出来的话是:“唔,现在完事啦:谢天谢地,这事儿总算已经过去。”[3]93这句话透露出她对这个男人及他们的关系的毫无留恋,她只是无声地接受了自己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存在的现实。她所做的好像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而她只是在事后“无意识”地整理头发,放张唱片舒缓心情而已。
三、女性声音的意义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荒原》是对现代社会两性关系的探讨之作,诗歌中的众多女性声音是艾略特构建诗歌整体意义结构的重要支撑。艾略特在诗中展示的上述两组女性在对男权社会压迫的反抗程度上大不相同:在第一组女性中,神话中库米的西比尔敢于抗争太阳神的淫威,向神要求自己生命的无限。而她的一句“我想死”直接呼喊出了把握自身命运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对其生存状态的激烈的反抗。英雄传说中菲罗墨拉激烈地反抗忒瑞俄斯的侮辱,千方百计地传达自己的处境、把握自我的命运,最终通过变形重新获得了向世界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而到了现代,索梭斯特里斯太太就成了一个躲在昏暗的帐篷里面靠神秘的塔罗牌装神弄鬼的冒牌女巫。她甚至不能准确地解释每张牌面的意义,只能含糊其辞。她已经无法准确地把握女巫预测未来的能力,从而失去了预言的“合法性”。如以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对文学模式所作的从神话到“讽刺”文学的高低排列来看[10]45-47,《荒原》中的女性声音的反抗的强度和通过发声对自身命运的把握程度也是随着文学等级的降格而下降的。
在《荒原》中,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女性同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中敢于大声呼喊、顽强反抗的女性人物相比,其主动反抗的声音就更趋于弱化了。身为伯爵夫人的玛丽·拉丽施因为梅耶林事件而不为欧洲王室见容,失去了往日的身份地位,甚至无法为自己辩护,她的回忆录的出版也受到多方阻挠。玛丽本人在王室主导的话语结构中是被诅咒的边缘性人物,其后的她更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悲惨地度过了余生。“弈棋”中的上流社会妇女,如住在奢华房间里的金丝雀,她存在的意义是靠男性来赋予的。她神秘香料的诱惑和喋喋不休的问话,一方面显示了她生活的空虚无聊,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她无法主动选择自己的命运;而她的爱人的沉默更加消解了她用语言确立自己身份的努力。丽尔的那些混迹于小酒馆中靠议论他人的家常消遣的女性朋友,是男权社会话语体系的共谋者和维护者。从她们的私语中可以了解到贫穷生活和无节制的生育已经把丽尔摧残得不成样子,而她的女性朋友却因为她不去打扮讨好丈夫和吃避孕药而称她为傻瓜,把她的这些反抗看做离经叛道的行为。丽尔的声音在诗歌中的不在场,使她甚至没有说出自我生活境遇的机会,诗人这样的安排也暗示了在社会下层的她无法摆脱成为生育机器的命运。“火诫”中蜗居在公寓中的女打字员更像是完全接受了自己是男性欲望对象的处境,从她对于男人的欲望要求无声的纵容和脑子里闪过的“谢天谢地,这事总算已经过去”的念头中,已经看不出反抗和把握自我的意愿了。艾略特诗中的现代女性缺少自己的声音,她们的声音随着自身社会地位的下移也有着由强到弱、逐渐息声的趋势。她们已经被冷漠的现代社会所同化,对她们身份的压迫和规训已经击倒了她们原有的自我。
从诗歌整体来看,诗中女性声音存在着相似的渐至无声的意义趋势应该不是一种巧合。《荒原》中女性的声音并不是简单地为西方文明的匮乏和贫瘠作出注解,或是为只余下了欲望的两性关系举例,而是通过女性声音的从古到今、自上而下的逐步息声的趋势来说明社会问题的真正之所在。正是因为男权社会话语体系对女性的压制和规训,使构成社会基本的两性关系遭到破坏,使女性无法言说自我,无法以对等的姿态参与到两性之间的正常对话之中。男女之间如不能维持正常的交流,社会发展的生机和动力又如何存在?这才应该是艾略特在《荒原》中提出和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
四、结语
如果从《荒原》的主题建构角度来整体关照,现代女性的这种生存状况也可以看做是当时个人和社会关系的隐喻——如果把男性权利的社会压迫形式推至最大化,得到的就是卡夫卡笔下占据着权力、资源与声望中心的冷漠无情的官僚机构。在无处不在的冷漠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情况下,个人会发觉只能像诗中的女打字员一样逆来顺受。已经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人们只得接受和忍受自己的处境。如果菲罗墨拉式的反抗者都已无法发出自我的声音去抵抗这些习以为常的压迫,那么这种导致了文明坍圮的男性话语统治将继续使人类走向衰落。
参考文献:
[1]J.S.Brooker&J.Bentley. Reading the Wasteland[M].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0.
[2]B.C.Southam.A Student’s Guide to the Selected Poems of T.S.Eliot[M].London: Faber&Faber Press,1981.
[3][英]T.S.艾略特.荒原[M]// 陆建德,主编.汤永宽,等,译.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古罗马]奥维德.变形记[M].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5]Lace Irigaray.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M].Catherine Porter and Carolyo Bauke tran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6]Aldous Huxley.Crome Yellow[M].New York:Harper and Row Publisher.1983.
[7]徐善伟.男权重构与欧洲猎巫运动期间女性所遭受的迫害[J].史学理论研究,2007(4).
[8][英]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M]// 陆建德,主编,卞之琳,等,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9]张剑.T.S.艾略特:诗歌和戏剧的解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10][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郭德民】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6)02-0074-04
作者简介:蔡乾(1985—),男,河南商丘人,商丘师范学院讲师,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英国汉学研究;邵婷(1989—),女,河南商丘人,商丘师范学院教师,天津外国语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