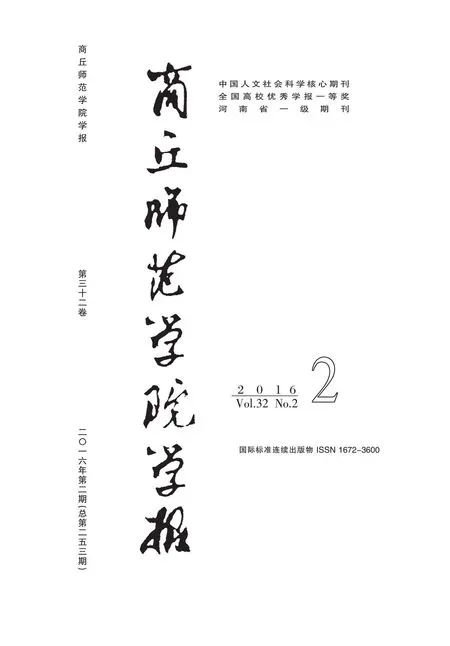曾朴、林纾小说创作所受《桃花扇》影响研究
2016-04-13王亚楠
王 亚 楠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曾朴、林纾小说创作所受《桃花扇》影响研究
王 亚 楠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桃花扇》的题材内容、文本结构和晚清民国特殊的社会情势,使曾朴和林纾的小说创作受到了《桃花扇》一定的影响。曾朴的《孽海花》受《桃花扇》的影响,也是借一两位线索型人物的行踪,来贯串和描绘众多的社会时事、政治事件,统摄广阔复杂的历史图景。林纾的多部小说的创作也具有与《桃花扇》相似的创作意图,运用了相似的情节结构,在叙事中以纪实和写情为两条线索,穿插交织,展开情节,叙写故事。其中典型的作品是《剑腥录》。
关键词:曾朴;林纾;小说;《桃花扇》;影响研究
清末民初,由于西方文艺思想的介绍和小说戏剧的翻译,以及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和影响,传统被视为“小技末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的文学地位不断上升,社会作用得到普遍重视,一变而为开启民智、宣传革命、加速进化的“利器”。在这种不断变幻、丰富复杂的社会情势下,加之文艺思想的更新和进步,众多的文人作家或为表达政见,或为抒发感慨,或为讽刺现实,或为记录当下,著、译了大量小说作品。这些小说在题材方面,最突出、最丰富的是时事小说和历史小说,形成和出现了明末之后又一个时事小说创作的高潮。而对于当时的作家和读者而言,时事小说和历史小说并非判然不同。作家创作历史小说,多数都是为了借古鉴今或影射现实。曾朴的谴责小说《孽海花》通常被认为属“时事小说”,但他自己最早却是将之视为“历史小说”的①。抱持借古鉴今、影射现实创作意图的作家纷纷将目光投射向此前的历朝历代的政治风云,而宋元之交、南宋灭亡和明清之际、明朝倾覆,因为异族入侵、汉人政权统治结束与晚清民国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社会情境具有相似性,再加上对作为异族的清人腐朽、残暴统治的愤恨,这两个政权更替时期的历史频繁进入当时历史小说创作题材取用的视野。吴趼人的《痛史》(未完成)即以元灭南宋为主要题材。而以明朝亡国为题材的,则有“痛哭生第二”所作的《仇史》。《仇史》所写“以明神宗万历年间,汉奸范文程投满起,至永历帝二十二年,台湾郑克塽降清止”,创作目的则是“专欲使我四万万同胞洞悉前明亡国之惨状,充溢其排外思想,复我三百余年之大仇”[1]153。作者并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乃继《痛史》而作”[1]153。《桃花扇》作为比较全面地表现南明弘光政权兴亡的剧作,也进入了当时历史小说作家的视野。
由于晚清民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政治事件层出不穷,延续时间又比较长久,当时多数的历史小说或曰时事小说的作者又具有比较大的创作野心,追求描绘广阔的历史场景、收纳众多的事件人物,为了能够较好地驾驭题材,他们主要采取了两种结构手法。第一种是杂缀野史轶闻,而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较典型的有林纾的《畏庐漫录》和许指严的诸种作品。第二种是以一个或一对中心人物为线索,随着人物的活动、行踪,借助人物在爱情方面的悲欢离合来描绘和展现广阔的社会图景、众多的政治事件。这一创作手法与孔尚任创作《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非常相似。这种类型的历史小说很多,本文主要分析与《桃花扇》有一定关系的曾朴的《孽海花》和林纾的《剑腥录》。
一、曾朴《孽海花》创作所受《桃花扇》影响研究
《孽海花》的最初作者为金松岑(1874-1947年)。第1-2回曾发表在1903年十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杂志第8期上。1904年夏秋之间,金松岑将原稿共6回转交曾朴,曾朴看后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于是金松岑就请曾朴续完全书。曾朴便就已有的6回,“一面点窜涂改,一面进行不息,三个月功夫,一气呵成了二十回”[2]129。1904年3月,金松岑翻译出版了记述俄国虚无党历史的《自由血》,书后附录有“爱自由者”即金松岑著、译书目的广告,其中就有《孽海花》。广告称这部小说为“政治小说”,具体的广告词为:“此书述赛金花一生历史,而内容包含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最近上海革命事件、东京义勇队事件、广西事件、日俄交涉事件,以至今俄国复据东三省止,又含无数掌故、学理、轶事、遗闻。精采焕发,趣味浓深。”[3]134金松岑后来在致友人书中也说他创作《孽海花》,“非为赛(按指赛金花)也,作此书之岁,帝俄适以暴力压中国,留日学生及国内志士,多组对俄同志会……赛于八国联军入京时,因与瓦德西昵,赖一言而保全地方不少,故以赛为骨,而作五十年来之政治小说”[4]148。可见此书最初的创作构想之一斑。曾朴看过原稿后,认为是“一个好题材”,但是“过于注重主人公,不过描写一个奇突的妓女,略映带些相关的时事,充其量,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陈圆圆的《沧桑艳》,已算顶好的成绩了,而且照此写来,只怕笔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列传》的蹊径”[2]128。于是,他提出了新的创作构思:“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2]128-129曾朴在这里所说的“主人公”,除赛金花外,应该还包括洪钧。小说林社在1905年正式出版《孽海花》前20回载的广告也说:“本书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如旧学时代、中日战争时代、政变时代,一切琐闻轶事,描写尽情,小说界未有之杰作也。”[2]134曾朴在评论胡适对《孽海花》的批评时也说:“我的确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主人公的一条线上,表现我的想象。”[2]130《孽海花》叙写的赛金花事迹与真实人物生平的差异曾在后来引起过争论,曾朴前后对于《孽海花》的创作思想也有过变化。但由上可见,参以小说本文,曾朴创作《孽海花》的结构安排和金松岑原稿的创作构思并无大的差异,均是以一二位主人公为经,以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为纬,表现“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时期中“文化的推移”和“政治的变动”[2]131。因为前后差异不大,所以对于《孽海花》来说,无论是金松岑的原稿,还是曾朴的创作,其情节结构都近似于《桃花扇》。
1917年,胡适与钱玄同曾在《新青年》上共同讨论中国白话小说。胡适在刊载于《新青年》第3卷第4期的《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中说,包括《孽海花》在内的多部晚清白话小说“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理由是“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5]31。胡适还在信中对《孽海花》有专论,认为:“《孽海花》一书,适以为但可居第二流,不当与钱先生所举他五书同列。此书写近年史事,何尝不佳?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文体(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类),而不得为佳小说也。”并认为《孽海花》远不如《品花宝鉴》[5]32。钱玄同在发表于《新青年》的回书中对胡适的看法表示了赞同。一方面由于观点的不同,一方面由于胡适的地位和影响,曾朴在《曾孟朴谈〈孽海花〉》中明确地就胡适对于《孽海花》情节结构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认为《孽海花》的情节结构不同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他说:“虽然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然组织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线;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想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谈话式,谈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丢了,可以随便进止;我是波澜有起伏,前后有照应,有擒纵,有顺逆,不过不是整个不可分的组织,却不能说它没有复杂的结构。”[2]130关于《桃花扇》的情节结构,孔尚任在该剧《凡例》第一条中说道:“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6]卷首尽管在传奇中,李香君并未从始至终一直随身携带“桃花扇”,但“桃花扇”作为李香君的象征和侯、李爱情的见证,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在全剧的许多重要关目和场次中都出现过,如《眠香》出中的赠扇、《守楼》出中的染扇、《寄扇》出中的寄扇、《入道》出中的撕扇等。虽然“桃花扇”是物件,而赛金花是人物,但所起的作用并无大的差异。
在评论《孽海花》的意见中,林纾的观点值得注意。他在《〈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中指出:“《孽海花》非小说也,鼓荡国民英气之书也。其中描写名士之狂态,语语投我心坎。嗟夫!名师不过如此耳。特兼及俄事,则大有微旨。借彩云(按即傅彩云)之轶事,名士之行踪,用以眩转时人眼光。而彩云尤此书主中之宾;但就彩云定为书中之主人公,误矣。天下文章,无妨狡狯。”[7]181-182对于林纾的观点,曾朴认为:“这几句话,开门见山,不能不说他不是我书的知言者!但是‘非小说也’一语,意在极力推许,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只囚在中国古文家的脑壳里,不曾晓得小说在世界文学里的价值和地位。他一生非常的努力,卓绝的天才,是我一向倾服的,结果仅成了个古文式的大翻译家,吃亏也就在此。”[2]131其中文字或者有误。依照曾朴的本意和“但是”表示的语意转折,他应该是认为林纾是《孽海花》的“知言者”。曾朴对林纾的原意有误解,对他的文艺思想也缺乏全面深入的考察,但也确实指出了林纾在分析和评价小说时的一个特点。林纾谓“《孽海花》非小说也”,是说《孽海花》并不仅仅是小说,其中不免有传统的轻视小说的思想在内,但他这一判断主要是就小说的主旨和作用而言的,认为《孽海花》主要记叙的是近几十年间的社会时事、历史变迁,作用则是可以“鼓荡国民英气”。林纾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翻译家,一生中与人合作翻译了近两百部西方小说,他绝不可能“不曾晓得小说在世界文学里的价值和地位”。相反,他是比较反对将小说视为“稗官野史”的,如他在《〈黑奴吁天录〉例言》中说:“是书系小说一派,然吾华丁此时会,正可引为殷鉴。且证诸咇噜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将来黄种苦况,正难逆料。冀观者勿以稗宫[官]荒唐视之,幸甚!”[8]43曾朴的主要错误是在论述中将各具不同逻辑内涵的论析对象混为一谈,因而缠杂不清。在一般的论述中,古文常与白话相对而言,小说常与经史相对而言。曾朴则将古文和小说对立起来,实则林纾以古文著译小说曾获得不少肯定评价。“白话文运动”的主将胡适就曾在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过:“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9]215周作人也曾指出:“他(按指林纾)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10]第五版
但是,林纾撰作古文私淑桐城派,论文又主桐城派的古文“义法”,著有《春觉斋论文》《韩柳古文研究法》等。他深谙古文“义法”,加上在古文存废之争中抱持较为保守的态度,又对以古文著译西方近现代小说做过大量的实践,故而他在分析中外小说的情节结构时常常移用古文的“义法”,努力寻找小说结构和古文行文方面的契合之处,有时不免方枘圆凿,强行贴合。他对许多小说的分析也转而主要注重情节结构、行文布局,却往往忽略了故事主旨和人物塑造。但许多小说常常因此而得到他的肯定。如他在《〈黑奴吁天录〉例言》中指出《黑奴吁天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8]43。他在《〈洪罕女郎传〉跋语》的开篇总结哈葛德小说的故事主题,接着却用全文大半篇幅讨论了《史记》的行文之法,然后认为“哈氏文章,亦恒有伏线处,用法颇同于《史记》”[11]181。他在《〈离恨天〉译余剩语》中先是分析《离恨天》小说的结构布局、人物设置,然后竟能转到分析《左传》的章法以至字法,并比附二者:
凡小说家立局,多前苦而后甘,此书反之。然叙述岛中天然之乐,一花一草,皆涵无怀、葛天时之雨露。又两小无猜,往来游衍于其中,无一语涉及纤亵者。用心之细,用笔之洁,可断其为名家。中间著入一祖姑,即为文字反正之枢纽。余尝论《左传·楚文王伐随》,前半写一“张”字,后半落一“惧”字。“张”与“惧”反,万不能咄嗟间撇去“张”字,转入“惧”字。幸中间插入“季梁在”三字,其下轻轻将“张”字洗净,落到“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今此书写葳晴在岛之娱乐,其势万不能归法,忽插入祖姑一笔,则彼此之关窍已通,用意同于左氏。可知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12]414
林纾对《孽海花》的分析也是如此。
据包天笑的自述,他创作小说《留芳记》时受到了《孽海花》的很大影响。包天笑之起意创作《留芳记》,就是因为《孽海花》。他曾说过:“我在青年时代,在曾孟朴所办的《小说林》出版部,见他所写的《孽海花》,我也曾有过志愿,要想把当时的革命事迹,写成小说。”[13]1包天笑又了解和熟悉《孽海花》的情节结构和创作意图,他在《留芳记》第一回中这样评述《孽海花》和自己的小说:“吾友东亚病夫(即曾朴)撰了一部《孽海花》,借着一老妓赛金花的轶事,贯串史事不少。要谈当时的情景,就在他的范围内了。虽只出了二十余回,以后就搁了笔,可是大家都希望他续成完璧。只是我这部书,却不免珠玉在前,自惭形秽了。”[14]17可见他是有意将《留芳记》视为《孽海花》的续作的。包天笑还在《留芳记》第三回中借小说人物陶庵之口分析《孽海花》的结构:“陶庵说道:‘说起赛金花来,诸位都知道吗?有个常熟名士曾朴做了一部小说唤作《孽海花》,就是把赛金花做书中的主人公,贯串着近代历史上的事,却把老夫也拉扯在里面。’”[14]51-52包天笑在此部小说中,主要是以梅兰芳为线索,描述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事件。对于这部可算做《孽海花》的续作、情节结构与之类似的小说,林纾在为《留芳记》所作的“弁言”中分析它的情节结构说:
今年天笑北来,出所著《留芳记》见示,则详载光绪末叶,群小肇乱取亡之迹,咸有根据。中间以梅氏祖孙为发凡,盖有取于太史公之传大宛,孔云亭之成《桃花扇》也。大宛传贯以张骞,骞中道死,补贯以汗血马。史公之意,不在大宛,在汉政之无纪,罪武帝之开边也。云亭即仿其制,叙列[烈]皇殉国,江左偏安,竟误于马阮,乃贯以雪苑香君,读者以为叙述名士美人,乃不知云亭几许伤心之泪,借以泄其悲。今天笑之书,正本此旨。去年,康南海至天津,与余相见康楼,再三嘱余,取辛亥以后事编为说部,余以笃老谢。今得天笑之书,余与南海之诺责卸矣。读者即以云亭视天笑可也。[15]卷首
孔尚任仿《史记·大宛列传》的行文、结构而作《桃花扇》,当然属于林纾的臆测,但他对于《桃花扇》的情节结构和孔尚任创作意图的分析却颇有见地,可谓是两百年后孔尚任的“知言者”。由此也可知,《孽海花》《留芳记》《桃花扇》三者在情节结构和创作意图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借一两位线索型人物的行踪,来贯串和描绘众多的社会时事、政治事件,统摄广阔复杂的历史图景。林纾对于此种结构手法非常重视和赞赏,他在为哈葛德的《斐洲烟水愁城录》所作序文中也以《史记·大宛列传》比附这部小说,其中说道:
余译既,叹曰: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史迁传大宛,其中杂沓十余国,而归氏本乃联而为一贯而下。归氏为有明文章巨子,明于体例,何以不分别部落,以清眉目,乃合诸传为一传?不知文章之道,凡长篇巨制,苟得一贯串精意,即无虑委散。《大宛传》固极绵褫,然前半用博望侯为之引线,随处均着一张骞,则随处均联络。至半道张骞卒,则直接入汗血马。可见汉之通大宛诸国,一意专在马;而绵褫之局,又用马以联络矣。哈氏此书,写白人一身胆勇,百险无惮,而与野蛮拼命之事,则仍委之黑人,白人则居中调度之,可谓自占胜著矣。然观其着眼,必描写洛巴革为全篇之枢纽,此即史迁联络法也。[16]2
二、林纾小说创作所受《桃花扇》影响研究
林纾自己的小说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桃花扇》的影响,而表现出相似的创作意图,运用了相似的情节结构。1913年,林纾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剑腥录》(后改题为《剑胆血腥录》《京华碧血录》),凡53章,以邴仲光和刘丽琼的爱情故事为线索,记叙晚清自戊戌变法至庚子事变间的社会历史大事②。林纾在《剑腥录》自序中说:“桃花描扇,云亭自写风怀;桂林陨霜,藏园兼贻史料。作者之意,其在斯乎?”[17]2可见他的创作意图一是借以抒发自己对晚清一些重大事变的看法和感慨,二是以小说为史书,记叙晚清一些重大事变的始末详情。关于《剑腥录》的情节结构,林纾在《剑腥录》卷首的“附记”中说,其中史实根据其门生王生孟之父王镜航的《庚辛之际月表》,而“其云邴、刘夫妇者,特假之为贯串耳”[18]2。他在小说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明,一是在第48章中借人物之口道出:
夫妇同行过行宫,至楼外楼下,仲光曰:“此吾媒氏之楼也。”因述当日奉还遗金,始得识老人于此,千回百折,始成今日姻缘。梅儿(按即刘丽琼)曰:“仲光自谓此一篇文章曲也,我则尚以为直。彼小说家,言才士美人离合之状,中间必有谗构之人,或见劫于有力,或不遂于所亲,至于颠沛流离,始谐燕好,然已筋疲力尽,尚何意趣之足言?今仲光之于丽琼,不过少有挫折。在三河遇难之一着,此亦文势之不能不曲处,谓之为曲,真诬我也。”仲光笑曰:“吾乡有凌蔚庐者,老矣。其人翻译英法小说至八十一种,多险急之笔。书中所述亦多颠沛流离之状,正如琴栖之言,读之令人意索。恨吾二人之事,不令蔚庐知之。其人好谐谑,将点染一二人踪迹,成一小说,亦大佳事。”梅儿曰:“不惟小说,戊戌、庚子之局,足资史料,何妨即以吾二人为纬也。”[19]157
其中“凌蔚庐”即指林纾,林纾号畏庐,“凌蔚庐”为“林畏庐”的谐音。可见林纾在创作《剑腥录》时,是追求以邴仲光和刘丽琼的爱情故事为经,以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等为纬,反映晚清错综复杂的历史变局。但从小说完成后呈现的情况而言,林纾并未完美地实现这一创作构想。小说前11回都是叙写邴仲光、刘丽琼两个人的情事,直到第十二回写到邴仲光上书受挫、会试落第后,林晚翠欲鼓动他从事维新变法,邴仲光婉言谢绝,才涉及社会政治事件。在其后的章节中,两条线索多数时候都是独立自行发展,相互间并未交集和联结。林纾自己在创作时也意识到这种困难和尴尬,在第32章中他就有这样的自白:
外史氏曰:“京城既破,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千头万绪,从何着笔?此书以仲光为纬,然全城鼎沸,而邴氏闭门于穷巷,若一一皆贯以邴氏,则事有不眇于京城者,即京城之广,为邴氏所不见者,如何着笔?今敬告读者,凡小说家言,若无征实,则稗官不足以供史料;若一味征实,则自有正史可稽。如此离奇之世局,若不借一人为贯串而下,则有目无纲,非稗官体也。今暂借史家编年之法,略记此时大略,及归到邴仲光时,再以仲光为纬也。”[19]109
林纾在创作中遇到如此的尴尬和困难,是因为他极力追求小说能够纪实和写情兼备,但有时又驾驭不当,不免偏重于一方,造成两者冲突,结构失衡。林纾创作小说注重纪实,一则因为晚清民初时期,社会政治事件层出不穷,当时的文人作家对此不可能视若无睹,也不可能毫无感想。二则因为林纾明确知晓小说的传统地位和尴尬处境,“小说界革命”对他又不可能没有影响,使他认识到小说巨大的社会作用,从他对众多西方小说的赞扬中就可以看到。但他自身的文化观念又相对保守,于是为了提高小说的地位,他只有以小说比附传统文化中地位最尊崇的经史著作,而强调小说纪实的功能。如他在《践卓翁小说》自序中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道:“盖小说一道,虽别于史传,然间有纪实之作,转可备史家之采摭。如段氏之《玉格》、《天咫》,唐书多有取者。余伏匿穷巷,即有闻见,或且出诸传讹,然皆笔而藏之。能否中于史官,则不敢知。然畅所欲言,亦足为敝帚之飨。”[20]414-415他同时也认识到小说写情的重要意义,如他在《不如归》自序中说:“小说之足以动人者,无若男女之情。所为悲欢者,观者亦几随之为悲欢。明知其为驾虚之谈,顾其情况逼肖,既阅犹若斤斤于心,或引以为惜且憾者。”[21]354林纾曾多次感叹叙事中“惟叙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著笔”[22]293。《块肉余生述》由于其“不难在叙事,难在叙家常之事;不难在叙家常之事,难在俗中有雅,拙而能韵,令人挹之不尽。且前后关锁,起伏照应,涓滴不漏”,被林纾自认为“近年译书四十余种,此为第一”[23]349。因为“家常之事”多繁杂琐屑,前后无紧密联系,而解决方法就是选取或者虚构一条贯穿始终的事件线索或一两个线索人物。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小说中,林纾最赞赏和称扬的是《红楼梦》,原因也是为此。他曾在《块肉余生述》前编自序中说:“史、班叙妇人琐事,已绵细可味矣,顾无长篇可以寻绎。其长篇可以寻绎者,惟一《石头记》,然炫语富贵,叙述故家,纬之以男女之艳情,而易动目。”[24]349
因为在叙事中以纪实和写情为经纬两条线索,穿插交织,易于统摄和收纳繁复的社会政治事件、广阔的历史图景画卷,所以继《剑腥录》之后,林纾在他的多部中、长篇小说中运用这一结构情节的创作手法。主要有创作于1914年的《金陵秋》(商务印书馆)、创作于1917年的《巾帼阳秋》(又名《官场新现形记》,上海中华小说社)和创作于1918年的《劫外昙花》(上海文明书局)等。《金陵秋》以王仲英和胡秋光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叙写辛亥革命,林纾在《〈金陵秋〉缘起》自述道:“其中以女学生胡秋光为纬,命曰《金陵秋》。至秋光与王仲英有无其人,读者但揣其神情,果神情逼肖者,即谓有其人可也。”[25]485可见这两人是林纾为用以贯串历史事件而特意虚构的。《巾帼阳秋》则以王醒(阿良)和素素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叙写民国历史。《劫外昙花》的创作意图和结构布局,也与之类似,林纾在该书自序中便说道:“余适观《赵勇略传》,心念勇略当日战绩烂然,乃为纳兰所遏,而蔡毓荣彰泰,又不直公,至于抑抑以卒,心颇怜之。遂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一以伸赵勇略之冤抑,一以写陈畹芬之知机。”[26]512
对于林纾的小说,特别是中长篇小说中存在的这种情况,早在1930年陈子展在其《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就明白而概括地指出:
林纾所作的小说有《京华碧血录》、《金陵秋》、《官场新现形记》几种。《京华碧血录》叙述戊戌政变、庚子拳变的事;《金陵秋》叙述辛亥革命南京方面的事;《官场新现形记》叙述袁世凯称帝和国会议员的事。这种小说以叙述时事为目的。(曾朴的《孽海花》,最初自称为“历史小说”,实则亦属此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时事小说”。这种小说,材料是新鲜活泼的史实,采集起来很容易,动手做起来也很容易,但要做成一种算得成功的作品就很难。其间最大的原因,即在小说与历史的性质不同。这正如林纾自己所说:“若无征实,则不足以供史料;若一味征实,则自有正史可稽。”他感到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他作这种小说,总是以一个虚构的人物的爱情及其遭遇为全书的脉络。他以为“如此离奇之世局,若不借一人为贯串而下,则有目无纲,非稗官体也”。不仅他的《京华碧血录》如此,《金陵秋》、《官场新现形记》亦如此。[27]236
陈平原把上述的这种小说情节结构类型称为“珠花式结构类型”,这一形象化的名称就是从前引曾朴的描绘而得来的。陈平原总结这种情节结构类型的具体内容就是“整部小说有个结构上的中心,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或贯串始终的人物。或者说,追求长篇小说情节上的统一性,防止变成互不关联的片断的联缀”[28]130。他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中列专章专节详细论述了这一情节结构类型,认为晚清民初时期有许多小说采用了这种情节结构类型来铺展情节、讲述故事,并涉及多种小说类型,“像《女娲石》这样的政治小说,像《黄绣球》这样的社会小说,像《碎琴楼》这样的言情小说,像《九尾龟》这样的狭邪小说,像《九命奇冤》这样的公案小说”[28]131。其中“以男女情事为贯串线索写历史事变”,又是这种情节结构类型中的一大类别[29]220。使用此种类别的结构手法来创作的小说,也确实有些是受到了《桃花扇》的启发和影响,如《孽海花》和上述林纾的几部中长篇小说。但陈平原认为“‘新小说’家正是从《桃花扇》吸取艺术灵感”,却未免以偏概全,也夸大了《桃花扇》的影响力[29]220。因为,事实上确实如他所说,这种情节结构类型是“源远流长”的,“借用鲁迅的小说分类法,不管是讲史小说、神魔小说,还是人情小说、侠义小说,都有贯串始终的主人公与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28]130。这种情节结构类型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还具有许多不同的表现或变体,“如《水浒传》的一环扣一环”,“如《三国演义》的纵横交错”,“如《西游记》之以取经事件为线索”,“如《金瓶梅》之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等等[28]131。当然,还有林纾极为赞赏的“炫语富贵,叙述故家,纬之以男女之艳情”的《红楼梦》[24]349。我们应该肯定《桃花扇》在情节结构上对于某些晚清民初小说的情节结构存在着影响,但也要实事求是,承认这种影响仅限于特定的一部分小说作品,而不能无视事实,夸大《桃花扇》的影响。
注释:
①包天笑《关于〈孽海花〉》记述曾朴写作《孽海花》时,常向他感叹:“写近代历史小说真不容易。”见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②《剑腥录》有《平报》社于1913年10月1日出版的单行本。封面和版权页均题《剑腥录》,内页题“冷红生著《庚辛剑腥录》。”卷首有林纾所作的“序”和“附记”。
参考文献:
[1]痛哭生第二.《仇史》凡例八条[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曾朴.曾孟朴谈《孽海花》[M]//魏绍昌.《孽海花》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曾朴.《曾孟朴谈〈孽海花〉》注释三[M]//魏绍昌.《孽海花》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金松岑.金松岑谈《孽海花》“二 致友人书”[M]//魏绍昌.《孽海花》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M]//欧阳哲生.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孔尚任.《桃花扇》“凡例”[M].孔尚任.桃花扇.康熙间介安堂刻本.
[7]林纾.《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林纾.《黑奴吁天录》例言[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M]//欧阳哲生.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开明”(即周作人).林琴南与罗振玉[J].语丝,1924(3).
[11]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2]林纾.《离恨天》译余剩语[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3]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
[14]包天笑.留芳记:第1集[M].上海:中华书局,1925.
[15]林纾.《留芳记》弁言[M]//包天笑.留芳记:第1集.上海:中华书局,1925.
[16]林纾.《斐洲烟水愁城录》序[M]//[英国]哈葛德,著.林纾,曾宗巩,译.斐洲烟水愁城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
[17]林纾.《剑腥录》序[M]//林纾.剑腥录.北京:《平报》社,1913.
[18]林纾.《剑腥录》附记[M]//林纾.剑腥录.北京:《平报》社,1913.
[19]林纾.剑腥录[M]//林薇,选注.林纾选集(小说卷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0]林纾.《践卓翁小说》自序[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1]林纾.《不如归》自序[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2]林纾.《孝女耐儿传》序[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3]林纾.《块肉余生述》续编识语[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4]林纾.《块肉余生述》前编自序[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5]林纾.《金陵秋》缘起[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6]林纾.《劫外昙花》自序[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7]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M]//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8]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9]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郭德民】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6)02-0067-07
作者简介:王亚楠(1986—),男,河南郑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和古代戏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编号:118ZD107)。
收稿日期:2015-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