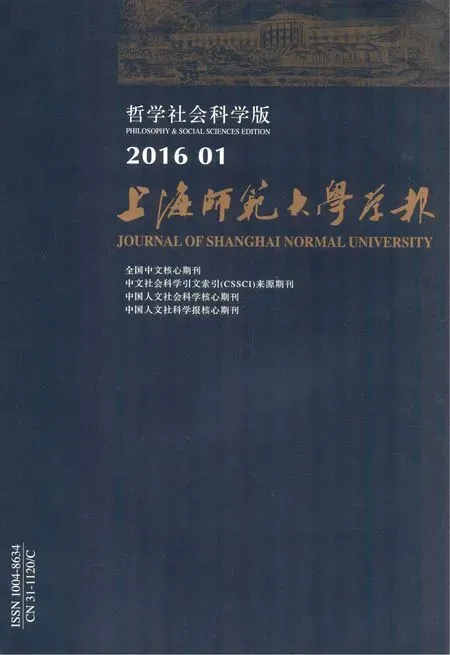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中的产业研究
2016-04-13张剑光
张剑光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产业状况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对六朝隋唐五代时期城市中的产业发展进行探索,是对城市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必将更加深入地认识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因此,本文选取江南城市经济产业进行研究,应该有助于对江南城市的整体研究。
本文所谈及的江南,大致上相当于六朝扬州的东部地区,包括丹阳、宣城、吴、吴兴、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义兴、晋陵等郡,在唐中期以后主要是浙东、浙西、宣歙三道的范围,相当于今浙江全部和苏南、皖南地区。
一、愈益兴盛的商业活动
商业兴盛是江南城市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尽管六朝以来的江南城市商业常常被限定于一定的区域之内,但商业的繁盛是各个城市的共同特点,而且商业渐渐在向城市的各个角落推进,来到了城门附近,来到了交通便利处的河边桥头。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商业从其所有者的性质来说,可以分成官营商业和私营商业两大部分,但由于江南远离唐代的政治中心,官营商业主要局限在政府控制的商品种类的经营中,如食盐、酒类等官榷商品的交易。比如唐代说浙西地区“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1](卷413,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P4231)元和十二年至长庆元年(817—821),薛戎为越州刺史,“仍以御史中丞观察团练浙东、西。所部郡皆禁酒,官自为垆。以酒禁坐死者,每岁不知数。而产生祠祀之家,受酒于官,皆醨伪滓坏,不宜复进于杯棬者,公即日奏罢之”。[2](卷53《薛公神道碑文铭》,P572)也就是说,浙东各州官制官销,城市中出售的酒当然是官营的。浙西各州情况也是如此:“榷酒钱旧皆随两税征众户,自贞元已来,有土者竞为进奉,故上言百姓困弊,输纳不充,请置官坊酤酒以代之。既得请,则严设酒法,闾阎之人举手触禁而官收厚利以济其私,为害日久矣。及李应奏罢,议者谓宰臣能因湖州之请推为天下之法,则其弊革矣。”李应上奏的实质是要将官制官酤改成私制私酤交榷钱,他认为一旦改过来,将大大有利于江南酿酒生产的发展。次年,浙西观察使窦易直又上奏要求在浙西六州都推行这样的政策,穆宗同意了,说:“不酤官酒,有益疲人,管内六州皆合一例宜并准湖州敕处分。”[3](卷504《邦计部·榷酤》,P6043)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江南各城市都是官坊酤酒,政府实际控制了酒的销售。
江南城市中的商业,大部分是民营商业,这是城市商业中的主体部分。民营商业的个体规模有大有小,有的是专职的商业从业者,也有的是官员或城市居民、农民等短期经营。民营商业分布于城市的各个市场,既满足城市上层人物对奢侈品的需求,也满足城内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是构成城市商业繁荣的最主要方面。
民营商业的大多数经营者是城市的普通居民,卷入商业活动的居民相当多。东晋应詹曾上表云:“军兴以来,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4](卷26《食货志》,P791)说明有很多百姓在从事贩卖经商,就连社会底层的僮仆奴隶也不事农桑而从事起轻便能赚钱的商业。商人是否真有十万,也许应詹有所夸大,但他的意思是经商人数众多。梁朝周石珍,“建康之厮隶也,世以贩绢为业”。[5](卷77《恩倖传》,P1935)周石珍的社会地位不高,但以贩卖纺织品为生,是一个处于商品交换过程末端的零售商人。商人经商很容易发财致富,而且还与官方权力相结合,扩大和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如梁吴郡陆验“少而贫苦,落魄无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验倾身事之。吉卿贷以钱米,验借以商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资以事权贵”。陆验与大权在握的朱异勾搭上,“苛刻为务,百贾畏之”。[5](卷77《恩倖传》,P1936)
弃本从事商业的农民也有很多,南朝时这种现象十分常见。沈约说南朝前期“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6](卷56《孔琳之传》,P1565)显然是指有不少农民进入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因而城市里的商人越来越多。也有不少官员经营商业。南朝贵族官僚经商之风盛行,“在朝勋要,多事产业”。[6](卷77《柳元景传》,P1990)宋孔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6](卷84《孔觊传》,P2155)有时官员自己不出面,让他们的仆人经营商业。如宋明帝时,晋安王刘子勋长史邓琬“使婢仆出市道贩卖”。[6](卷84《邓琬传》,P2135)
不少城市妇女投入到经商中去。如东晋时的吴中风俗,“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7](卷31《地理志下》,P887)衣冠士人家里的女性常于市肆抛头露面,从事经营活动,帮助丈夫一起赚钱。唐代妇女经商的就更多了。李白《金陵酒肆留别》云:“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8](卷15,P928)妇女开设酒店,经营上有着比男性更大的优势。
江南城市商业,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贩运和店铺零售两种形式。
江南城市中的贩运贸易,是指商人利用水陆交通路线,将产品从其他地方运输到江南地区。六朝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参与贩运贸易的商人数量众多。从商人们贩运的商品来看,品种丰富,既有大量城市上层人物需要的奢侈品,又有大量农副产品、地方特产及手工业品。大宗农产品作为贩运的主要物品,是城市贩运贸易的一个特点。刘宋大明八年,孝武帝曾诏:“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6](卷6《孝武帝纪》,P134)到了隋唐五代,贩运业更为兴盛。如唐代的江宁县城附近,“暮潮声落草光沉,贾客来帆宿岸阴”。[9](卷743,沈彬《金陵杂题》,P8456)杭州“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宾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1](卷736,沈亚之《杭州场壁记》,P7604)明州象山县和台州宁海县交界处的祚圣庙,“唐贞观中,有会稽人金林数往台州买贩,每经过庙下,祈祷牲醴如法,获利数倍”。[10](卷6《祠庙》,P4899)
城市中商业经营的主要方式是店铺零售。一般商人都是在市肆中拥有肆店或商铺。如南齐柳世隆“在州立邸治生”。[11](卷24《柳世隆传》,P452)唐末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酤酒王氏,经营“以平直称”。后来江宁大火,“此店四邻皆为煨烬,而王氏独免”。[12](卷6,P101~102)王氏开设的酒店以诚信、价格公道而著称。唐代杭州人称“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1](卷316,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P3206)虽不见得店肆真有3万家,但说城内商店众多还是可信的。江南城市商业在经营方式上有一定的变化发展,[13]市场上的商品列肆交易,分类很细,但同时零售的商业店铺又往往开设在市场之外的居民生活区。尤其是到了唐代后期,城市中新市场在孕育增加,而居民生活区的店铺渐渐增多,城市的商业出现繁盛迹象。
从总体上看,江南城市的商业活动越来越活跃。随着贩运商贸的发展,各个城市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江南许多大城市的商业活动已不再局限于本州郡或本县范围内简单地互通有无,而是在整个江南地区已初步形成市场销售网络。虽然这个网络还是简单粗疏的,但江南每个城市往往成为整个商业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新兴的生活服务业
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活服务业依托城市发展而兴起,从传统的商业中分离出来。服务业是城市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兴旺程度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服务业在城市经济中占的比重越大,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
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由于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需要大量各个行业的手艺工人来为他们服务,所以城区内生活着大量的手艺工人。如城市建筑需要木工,日常生活家具要有人来制造,大量的木匠于是出现在城市各坊里中。建康城内有木工在做家具,有人送给建康人杜鲁宾三根木棒,杜“命工人剖之”。[12](卷5,P91,P120)大城市内已有专门的清洁工,《金华子杂编》卷下云:“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这可能就是保养河道的工人。南唐周则年轻时专以制造雨伞为业,李后主曾问及其事,周则说:“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惟霪雨连月,则道大亨。”[14](卷上,第一编第二册,P86)城市还需要大量的简单劳动力,于是就出现了劳动力雇佣市场。浮梁县令张某秩满到京师,在华阴碰到了一个黄衫吏,对他说:“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15](卷350,P2775)这个脚力就是宣州的自由劳动力。而在延陵县,陈生欲“求人负担药物”,到佣作坊中寻人帮忙,[15](卷74, P464)想来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在大城市中都是存在的。
服务性商业的兴盛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六朝至隋唐,城市服务业在整个商业中所占比重明显增加,行业种类繁多。江南城市中,服务性商业主要有饮食业、服装业、房产业、旅店业、租赁业、修补业等。唐朝富人贾三折,“夜以方囊盛钱于腰间,微行市中买酒,呼秦声女置宴”。[16](P156)百姓夜间可进入市中,而且还可以购买东西。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中,夜间经商是官府允许的,只是限于照明条件,夜晚做生意总不如白天来得兴盛。大城市中,酒店特别多。杜牧曾谈到润州市中酒楼:“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17](卷3《润州》, P43)金陵地处南北要冲,酒楼最为多见。李白云:“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孙楚酒楼在金陵城西,秦淮河边。[8](卷19《玩月》,P1122)苏州酒楼特别多,有街巷以酒店闻名,“唐时有富人修第其间,植花浚池,建水槛风亭,酿美酒,以延宾旅。其酒价颇高,故号大酒巷”。[18](卷下《往迹》, P60)白居易云:“皋桥夜沽酒,灯火是谁家?”[19](卷24《夜归》, P541)苏州皋桥边白天商业活动兴盛,但到晚上仍有酒店在营业。湖州出名酒,市内有大量酒楼,杜牧曾云:“金钗有几只,抽当酒家钱。”[17](卷3《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 P54)
各种饮食摊店遍布江南城市。吴县朱自劝死后,其女入寺为尼,大历三年(768),“令往市买胡饼,充斋馔物”,[15](卷338, P2686)可知市内有专门出售饼类的商店。鲊是用盐腌制的鱼、肉食品,是人们特别喜爱而在市场上常见供应的一种食品,“池州民杨氏以卖鲊为业。尝烹鲤鱼十枚,令儿守之”。[12](卷3,P56)湖州仪凤桥南有鱼脯楼,吴越国时在此专门曝鱼脯上贡,但“春月尤多,作以供盘饤”,“今乡土鱼脯甚美”。上贡用不了这么多,就用来出售,因此鱼脯楼十分有名。[20](卷18《食用故事》,P4842)
江南各城市中,出现了许多著名食品。吴越杭州“有一种玲珑牡丹鲊,以鱼叶斗成牡丹状。既熟,出盎中,微红,如初开牡丹”。湖州有“吴兴连带鲊”,“不发缸”,被收进韦巨源《家食账》。吴兴人“敛牛乳为龙华饭”,“设客以吴兴脔团糟”。南唐金陵,北方士大夫大量涌至,讲究饮食之风大盛,金陵面点制作有“建康七妙”,如虀可照面、馄饨汤可注砚、饼可映字、饭可打擦擦台、湿面可穿结带、饼可作劝盏等名品。[14](卷下,P107)
城市内有大量公私逆旅供外地人住宿。官方有馆驿,但一般老百姓是没办法入住的。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可以入住民间开设的各种逆旅客舍。武则天时,杭州临安尉薛震将债主“于客舍遂饮之醉”,最后将其杀死。[21](卷2,P19)客舍大多开设在州县城市里。大历中,洛阳人刘贯词和蔡霞在苏州认识后互相照顾,蔡对刘说:“逆旅中遽蒙周念,既无形迹,辄露心诚。”[22](卷3,P180)说明两人都是借住在逆旅中。苏州这样的大城市,逆旅决不仅一两个。前钦州刺史李汉雄,天祐丙子岁游杭州,住宿在“逆旅”中,[12](P122)说明杭州城内的客舍数量应该很多。交通发达,人们的商品意识较强,商品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高,人员流动量大,因而在城市中开设私人客舍是十分多见的。
江南城市中房屋买卖十分普遍,还有中间人居间撮合。南齐崔慰祖“卖宅四十五万,买者云:‘宁有减不?’答曰:‘诚惭韩伯休,何容二价。’买者又曰:‘君但责四十六万,一万见与。’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岂是我心乎?’”[11](卷52《崔祖慰传》,P901)这里的买者,实为中间人,他在中间想赚一万的好处费。梁代徐陵说:“吾市徐枢宅,为钱四万,任人市估,文券历然。”[23](卷5《与顾记室书》,P1B)如果外地人要长久住在江南,许多人想到了购置、求租房产这一办法,因此江南大城市中房产出租、买卖比较盛行。苏州华亭令曹朗官秩将满,来到苏州“置一宅,又买小青衣,名曰花红……后逼冬至,朗缘新堂修理未毕,堂内西间贮炭二百斤,东间窗下有一榻,新设茵席,其上有修车细芦废十领,东行,南厦,西廊之北一房充库,一房即花红及乳母,一间充厨”。[15](卷366,P2906)从曹县令在苏州购房居住,同时添置了大量日常生活用品上可以看出,城市房屋的买卖对促进城市经济繁荣的作用是相当大的。房屋可以出租,虔化县令王瞻罢任归金陵,“自出僦舍”,租借房子居住。[12](卷1,P19)
城市中服装鞋帽的制造和销售,是服务性商业的一个重要行业。在金陵、杭州、越州、宣州有各种各样的裁衣肆,专门为城市居民制造衣服和鞋帽,同时在大城市中也出现了销售衣帽的行业。刘茂忠为刺史时,有一女养在金陵,及金陵“城陷,为兵人所掠在师,茂忠使女仆入诸营部,托鬻衣而窃求之”,[24](卷10《刘茂忠传》,,P224)可知出售衣服在城市内是比较常见的。衣帽鞋制造业主要在会稽、杭州、宣城、金陵、苏州等一些较大的城市中出现。天宝时,会稽主簿季攸“乃为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帐”。[15](卷333,P2645)季主簿不可能自己动手做,肯定是找了裁衣铺中的工人缝制。陶谷《清异录》卷下谈到“宣城裁衣肆”,说明城市中成衣制造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同书又说:“韩熙载在江南造轻纱帽,匠帽者谓为韩君轻格。”韩氏为南唐高官,后期主要活动在金陵,因此制帽匠当在金陵城内。
江南城市的服务业总体上说六朝时已有初步崭露的迹象,到了唐代渐渐在大城市中有较为兴盛的表现。服务业经营内容已扩大到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只要有利润可以赚取,服务业就会往那个方向发展。服务性行业的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如有的是白天经营,有的是全天候经营。与城市生活休戚相关的服务业,如剔粪业、修理业、拾荒业、器物租赁业等,限于史料的记载,我们无法做详细的介绍。服务业的发展,既适应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民众不同的生活需求,同时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优化了城市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直接促进了城市消费。
三、门类众多的手工业生产
手工业生产水平是衡量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与商业的发展一样,城市手工业由官营和民营两部分组成。由于六朝和南唐的中央政府在江南,因而城市手工业中官营的那部分所占分量较重。
官营手工业集中在大中城市和部分小城市中,主要有纺织、造纸、金银器制造、兵器制造、铸钱、造船等产业。六朝都城建康有众多的官手工业工人。孙权时“诸织络,数不满百”。吴景帝孙休永安年间,交趾郡太守“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25](卷48《吴书·三嗣主传》,P1161)将这部分手工业工人充实到孙吴官营作坊中来。吴幼帝、景帝时,“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25](卷61《吴书·陆凯传》,P1402)吴国的葛、麻纺织品生产在当时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东晋末年,大将刘裕率军灭后秦,迁关中“百工”于江南,在建康设立了专门的织锦机构——斗场锦署。大量外地熟练的纺织工人来到江南城市,使南方丝织业获得长足的发展。南齐时,芮芮虏(即柔然)使臣曾向南朝政府求赐锦工,南齐以“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为由加以拒绝。[11](卷59《芮芮虏传》,P1025)唐末润州的锦工享有盛名,天复二年(902)润州人徐绾在杭州发动叛乱,城中有两百余锦工,全是润州人,钱镠长子元瑛恐怕他们参与徐绾叛乱,宣布“百工悉免今日工作”。[26](卷83《钱传瑛传》,P1194)可以确定,润州在战乱前有数百人的织锦队伍。至南唐,官府里设有作坊,生产物品种类众多,数量很大。
南朝官手工业造纸技术相当高超。《文房四谱》卷4《纸谱》引《丹阳记》称,南朝建康城内有“纸官署,齐高帝于此造纸之所也。尝送凝光纸赠王僧虔”。唐《元和郡县图志》卷26载婺州开元贡藤纸、元和贡白藤细纸。《册府元龟》卷719《幕府部·清廉》云:“杜暹为婺州参军,秩满将归,州吏以纸三万余张以赠之,暹唯受一百,余悉还之。时州僚别者见而叹曰:‘昔清吏受一文钱,复何异也。’”以纸3万余张相赠,可见生产量是很大的。
六朝墓葬中出土的很多金银器,反映了城市金银冶铸技术的进步。罗宗真对南京附近有金银器随葬的18座六朝墓统计,共出土金银器411件,其中金器即达363件,金器中饰件又达232件,说明当时金器主要用来装饰或做馈赠的礼品。这些金银装饰品制作非常精细,提炼十分纯正,含纯金达95%以上,足可说明建康和南徐州的金银器制造水平之高。[27](P12)到了唐朝,江南城市中的官手工业继续保持着金银器制作的高水准。如敬宗即位后不久,诏浙西造银盝子妆具20件进内。时任润州刺史的李德裕说:“金银不出当州,皆须外处回市。去(年)二月中奉宣令进盝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乃诸头收市,方获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进妆具二十件,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寻令并合四节进奉金银,造成两具进纳讫。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星夜不辍,虽力营求,深忧不迨。”[28](卷174《李德裕传》,P4512)敬宗要浙西贡金银造妆具,证明润州所造产品由于工艺水平较高,很合皇室胃口。1962年,在西安北郊坑底村出土了唐代金花双凤纹银盘1件,盘底刻有铭文:“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29]裴肃在贞元十四至十八年(798~802)间为越州刺史,该金花银盘应该大致上是这一时期制造的。
民营手工业是六朝至唐五代江南城市手工业的主体,其发展伴随着城市商业的繁盛而兴旺起来。民营手工业的发展有这样一些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手工业门类众多。学者指出,六朝手工业形成了冶炼、造船、制瓷、纺织、制盐、造纸、制茶等七大手工业部门。[30](P144)不过从实际来看,冶炼、制瓷、制盐、制茶等一般是在城市外的,真正在城市里的手工业估计主要是造船、纺织,此外还有铜器制造、制酒等。如六朝京口出好水,因而京口酒的质量很高。曲阿县的新丰酒和曲阿酒也很有名。《魏书》卷70《刘藻传》谈到北魏南侵,魏孝文帝与将军刘藻辞别,相约于石头城相见。刘藻说:“臣虽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贼虏而遗陛下,辄当酾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孝文帝大笑说:“今未至曲阿,且以河东数石赐卿。”说明江南的曲阿酒名播北方。至唐五代,手工业的种类就更为增多,如纺织业(丝纺、麻纺、刺绣)、金银器和铜器制造、造船、漆器制造、食品制造(制酒、制糖、副食品)、服装、文具制造、印刷等,行业十分繁多。《南唐近事》卷2记载:“元宗幼学之年,冯权常给使左右,上深所亲幸,每曰:‘我富贵之日,为你置银靴焉。’保大初……语及前事,即日赐银十觔以代银靴。权遂命工锻靴穿焉,人皆哂之。”城市里有专门制靴的工匠。因为是要锻银为匠,所以这个工匠又是个金银匠。慈溪县东35里的香山智度寺,“咸通十四年,有途人负漆器五百入寺,曰:‘汤和尚于浙西丐缘,先遣至此,和尚濯足溪边随至矣。’”[31](卷17《寺院》,P5217)时浙西节度驻地在润州,文中的“浙西”应该指的是润州,说明润州是漆器的重要生产地。
第二,地方特色比较明显。江南城市手工业的门类在增多,大中小城市都有不少手工业,不过各城市的手工业发展速度并不一致。如丝绸业,在一些城市出产的特殊织品很多,技术比较先进;而有的城市丝织技术比较落后,生产不出新产品。东晋南朝时,江南蚕茧生产有突破性进展,如据左思《吴都赋》称,吴郡出现了“乡贡八蚕之绵”,即实现了一年蚕多熟。《隋书》对唐以前江南丝织业做过概括:“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7](卷31《地理志下》,P887)唐代宋之问任越州长史,曾描述越州的情形:“妾住越城南,离居不自堪。采花惊曙鸟,摘叶餧春蚕。”[9](卷52《江南曲》,P634)开元时徐延寿见到的越州:“金钏越溪女,罗衣胡粉香。织缣春卷幔,采蕨暝提筐。”[9](卷114《南州行》,P1165)天宝时,越州的绫、纱、罗作为地方特产上贡朝廷,证实能够生产的精美织品越来越多。越州绫有白编、交梭、吴绫、越绫、十样花纹等品种,名目繁多,体现了织法和纹饰的多样性。尤其是吴绫,有一般吴绫及异文吴绫、花鼓歇、单丝吴绫等品种。苏、润、宣、常、杭等城市都是丝织品较为发达的城市,但睦、婺、衢、处、温、州、歙、池等城市丝纺技术比较低。再比如金属制造和加工,润、苏、衢、杭、宣、越等城市发展较有特色,而其他城市加工水准就较低。铁器制造,睦、台等城市发展很有特点。由于各城市手工业门类在不断增多,生产技术经常在改进,但同时各城市有自己的发展特点,所以江南手工业以太湖周围及浙北的一些城市最为发达,而南部城市手工业发展速度较慢。
第三,城市周围原料的支撑是江南城市民营手工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原因。无论是丝绸、麻织类纺织工业,还是制茶、制酒类的食品工业,以及造纸、制衣等,都是由于城市四郊的农村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城市才能进行技术上的加工。因此,江南城市手工业是依赖了农村的原材料生产才发展兴旺的。当然,也有一些手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并不是本地,如江南城市的漆器制造比较发达,但漆器材料并不全是本地的;沿江沿海城市是重要的造船中心,但木材往往使用的是其他地方的,如金陵常使用的江西木材;金属制造所用矿产一般而言是本地开采的,但江南不产金,如润州的金银器制造技术较高,而原材料却是从淮南收购而来,苏州的情况也基本相同。不过从总体上看,江南各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与各地原材料的供应有着直接关系。
第四,江南城市民营手工业产品有相当部分是进入到商品市场的。由于六朝至隋唐社会的特殊性,民营手工业的生产物有一部分并不进入流通领域。比如宣州泾县城中,丝织生产十分普遍,“寻街听茧缫”,到处都是织机的声音。[9](卷588,李濒《送许棠归泾县作尉》,P6823)《元和郡县图志》谈到宣州贞元时期上贡五色线毯,《新唐书》称丝头红毯。这是一种以染色丝线织造的地毯,白居易《红绣毯》诗有详尽描写:“宣城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9](卷4,P78)这样的民营手工产品其实不是商品,而是作为贡品献给了朝廷。不过,江南的民营手工业产品大部分仍是能进入商品市场的。比如温州别驾豆卢荣妻母金河公主随婿居住在温州多年,宝应初,“时江东米贵,唯温州米贱,公主令人置吴绫数千匹”,[15](卷280,P2230)这些吴绫可能是温州本地生产的,是温州市场上的商品。李白《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说宣州是“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8](卷12,P780)可知宣州城内的手工业品是大量供应市场的。
第五,民营手工业生产规模小,一般都是以家庭作坊或个体生产为主。个体生产的技术有不少世代相传。如诸葛笔是宣州最有名的笔,《白孔六帖》卷14《笔砚》云:“宣州诸葛氏能作笔,柳公权求之,先与三管,语其子曰:‘柳学士如能书,当留此笔,不尔退还,即以常笔与之。’未几,柳以不入用,别求笔,遂以常笔与之。先与者三管,非右军不能诸葛笔也。”传说从晋朝开始,诸葛氏世代制笔,唐五代更是代出名手。大历十才子之一耿湋有《咏宣州笔》云:“影端缘守直,心劲懒藏锋。落纸惊风起,摇空见露浓。”[9](卷268,P2980)皮日休云:“宣毫利若风,剡纸光与月。”[9](卷609《二游诗》,P7028)五代宣州笔特别受到宫廷宗室的喜爱,《清异录》卷下谈到南唐宜春王“喜书札,学晋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以十金,劲妙甲当时,号为翘轩宝帚,士人往往呼为宝帚”。宣州的笔应该都是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又云:“唐世举子将入场,嗜利者争卖健豪圆锋笔,其价十倍,号定名笔。笔工每卖一枝则录姓名,俟其荣捷,则诣门求阿堵,俗呼谢笔。”笔工就是个体手工者,制笔的技术精湛,讲求质量。再比如苏州地区草鞋编织历史久远,上可推到晋朝。《说郛》卷43引唐王献《炙毂子杂录》云:“靸鞋舄……西晋永嘉元年,始尚用黄麻为之。……梁天监中,武帝以丝为之,名解脱履。至陈隋间,吴越大行,而模样差多。及大历中,进五朵草履子。至建中元年,进百合草履子,至今其样转多差异。”苏州蒲鞋远销越州,特别博得城里女孩子的喜爱,绣上花朵以后甚至可作为定情之物。民营手工业也常以作坊的形式出现在江南城市中。唐文宗开成时宰相李珏曾谈到南方的铜器铸造:“今江淮已南,铜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销钱一缗,可为数器,售利三四倍。”[28](卷176《杨嗣复传》,P4557)他认为铜器制造成肆成列,显然都是一个个作坊在销钱。
相比较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的生产都是小规模的,不过商品的总量往往超过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有时会和官营手工业生产相同的商品,但更多的时候往往会生产官营手工业所不愿生产的产品。如《清异录》卷上云:“时戢为青阳丞,洁己勤民,肉味不给,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豆腐的制作由来已久,而州县城内官营手工业是不屑于生产这种小商品的,而民营手工业就填补了空白,满足商品经营的需要。因而民营手工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日趋活跃的外贸业
随着商品经济的兴盛,江南地区的外贸业开始出现。东吴黄武五年(226),吴国交趾太守将来到交趾的大秦商人秦论送到建业,孙权曾亲自接见。时亶洲商贩常到会稽来贩布,而会稽人也有飘洋过海到亶洲的,反映了东吴和海外地区已有外贸的存在。在日本的一些古墓中出土过一些吴镜,应该是日本和东吴人员往来携带的证据。还出土了许多三角缘神兽镜,虽然生产于日本,但与吴镜有不少关联,有关专家认为“这意味着它们是中国的吴国工匠东渡日本,在日本制作的”。[32]东晋时期,江南城市与日本、朝鲜、南海诸国的来往更为密切,民间贸易出现。如《晋书》卷97《林邑传》载:“徼外诸国尝赉宝物自海路来贸货。”南朝时期,与南海诸国的交往更趋活跃,一些国家如林邑、扶南等国遣使建康贡献礼物。《梁书》卷54《丹丹传》谈到中大通二年(530)时曾献牙像及塔、火齐珠、古贝、杂香药,大同元年(535)献金、盆腔、琉璃、杂宝、香药。其时南朝也遣使往南海,带去了诸如铠仗、袍袄、马匹等物品。双方互献的都是上层人物喜爱的奢侈品,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特殊贸易。
唐五代,江南与海外之间的贸易比较常见。我们以前曾做过研究,发现唐五代江南地区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在活动,有朝鲜、日本、阿拉伯、波斯、印度、渤海国、契丹、西域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经营着珠宝业、香药、火油等各类奢侈品和茶叶、粮食、丝绸等商品的买卖,还有一部分从事着酒店业的经营。[33]
随着经济的发展,江南靠近江海的一些大城市成了对外交通贸易港口。浙东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占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外国来船众多,而国内船只也常从这些地区起航赴国外贸易。如明州是江南与日本等国商业运输和人员往来最重要的港口。唐末从明州出发到日本的船有6只,日本到达明州的船有1只。宋人称明州是“海道辐凑之地”,“南接闽广,东则矮人国,北控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是“东南之要会也”。[34](卷7《庆元府》,P121)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唐末五代就已是如此。台州是江南与日本、高丽等国海上商船来往的重要城市之一。浙江南部地区的瓷器出口,一般认为是直接从台州出口的。有学者认为台州地区瓷器对外贸易时,“从临近的海门港、楚门港和松门港出口,远销日本、菲律宾和南洋群岛”,[35]这大致上是可信的。温州也是日本船只靠岸的重要地区,温州向南的船只经南海可直通印度、阿拉伯。越州也是外国商人上岸的一个港口。日本岛东面海中有岛屿邪古、波邪、多尼等,“北距新罗,西北百济,西南直越州,有丝絮、怪珍云”。[34](卷220《日本传》,P6209)吴越时期的杭州,前来的外国人很多,高丽人和日本人最为常见。僧契盈陪侍忠懿王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凑,望之不见其首尾”。[26](卷89《契盈传》,P1290)谭其骧认为杭州是唐五代重要的通商口岸,他引述了杜甫诗“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认为西陵是当时海船出入杭州的必经之地,“唐代西陵之所以时有商胡踪迹,其目的地亦必在杭州”。[37](P420)
沿长江的各大城市不时有外国船只前来。五代时的金陵,是江南的重要港口之一。金陵城内居住着一定数量的外国商人。曾有大食国使者前来进贡龙脑油,南唐元宗爱惜异常。郑文宝《耿先生传》云:“南海常贡奇物,有蔷薇水、龙脑浆。上实宝之,以龙脑调酒服,香气连日,也以赐近臣。”[26](卷34,P479)王贞白《娼楼行》云:“龙脑香调水,教人染退红。”[38](卷11,P465)看来大食国带来的龙脑油数量不少,连一般的娼楼中也在大量使用。润州常见外国船只,许棠《题金山寺》云:“刹碍长空鸟,船通外国人。房房皆叠石,风扫永无尘。”[9](卷603,P5973)李栖筠为常州刺史,城下“海夷浮舶,弦发望至”,到常州城来贸易的中外海船必定不少。杨琎任常州司户参军时,“海税孔殷”,[39](开元一一《大唐故杨府君墓志铭》,P1230)说明地方政府向前来商贸的外国商人征取一定比例的商税。
江南有对外贸易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沿岸,其中以明州、台州、杭州、金陵等城市贸易最为兴旺。频繁的交易,必然是大量的货物相互往来。从实际情况来看,江南运出的货物往往是本地区的特殊产品。日本自奈良朝以后,对唐朝的物品极其嗜好,每每以拥有某种唐货互相夸耀。如光孝仁和元年(885),日本政府下令大宰府司,禁止王臣家使及管内吏民私自以高价抢购舶来品,说明唐朝货物是十分受人欢迎的。[40](P115)
江南内陆腹地较为广阔,各地生产的货物集中于各大城市,再输向国外。运向城市的货物主要有以下数种:
一是瓷器。江南各地生产的瓷器,大多运向明州,再向外输出。1973年,在宁波遵义路唐宋时代的渔浦门城门遗址的清理中,在唐代城墙墙基下出土了700多件唐代瓷器,其中绝大部分是越州窑瓷器,还有部分为长沙窑产品。林士民认为唐代的明州北面紧临余姚江水路,东南是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汇合的地方,“设有海运码头,是对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应该说是比较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况。[41]这些瓷器,显然是当时外销的一部分,而长沙窑瓷器是从长江水道运抵后在明州中转的。
二是丝绸。丝绸是江南较有特色的一种手工业产品。后周广顺三年(953),吴越商人蒋承勋代表吴越王钱弘俶向日本送上锦帛,而日本右大臣藤原师辅托蒋承勋带回吴越的信中说:“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因而估计蒋承勋所运货物中有不少丝绸织品。木宫泰彦认为:“客商等输入的商品虽属不详,但可能和前代一样,以香药和锦绮等织物为主,而日本方面用来做交易的似乎以沙金等物为主。”[40](P226)
三是香药、中药和家禽、牲畜动物等。《三代实录》载清和贞观十六年(874)六月,大宰府令大神己进、多治安江等人入唐求香药。3年后,多治安江从台州回国,带回货物众多,估计主要是香药类商品。《扶桑纪略》载延喜三年(903),唐朝商人景球到达日本,献羊1头,白鹅5只。其时北方战争不断,景球或许也是江南商人,有可能销往日本货物中的一部分是家禽、牲畜。天庆元年(938),吴越商人蒋承勋向日本大臣进献羊2头。
从这些输出的产品来看,一般不是城市自己生产的,大多来自周围农村地区。不过城市作为运输的关节点,将这些产品运向国外,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
五、其他产业
除商业、服务业、手工业、外贸业外,江南城市还有一些其他产业,对城市经济同样也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城市中有一部分较为富裕的人从事高利贷业。作为城市金融业的一种,高利贷是六朝至唐五代江南城市常见的一种赚钱方式,从事的人数也有一定的数量。吴郡人陆验“少而贫苦,落魄无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验倾身事之。吉卿贷以钱米,验借以商贩,遂致千金”。[5](卷77《恩幸传》,P1936)陆验通过经商致富,但最初的资金是向郁吉卿借贷的。虽然并没有明说他是通过高利率借钱给陆验,但利益追逐的本性决定了陆验的借贷不会是无息的。在江南城市,放贷的人还真不少。南朝宋明帝时,“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桡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6](卷57《蔡兴宗传》,P1583)放高利贷带来的利润吸引了王公妃主。梁临川王萧宏在“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券,期迄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5](卷51《梁临川王宏传》,P1278)他是举放高利贷,以田宅邸店为抵押,逾期不还,所押不动产即被没收。
城市中还有少量的种植业。如有的豪族在京都为官,赐田就在都城建业附近。东吴名将潘璋死,其“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25](卷55《吴书·潘璋传》,P1300)复客应是依附农民,是一种区别于编户的奴仆,所以推测建业城内应该是有农田的。这部分复客是城市居民,主要是靠农业劳作而生活。建康城北地区在六朝以前人烟荒芜,当时为了安置北方移民,曾在此地设郡县,结果城北地区人口增多。杨吴筑城时,将这些地区划至城外。城北地区人口相对较少,城内的交通不如城南繁忙,故仅开一个城门出入。这些地区的居民利用玄武湖,发展养殖业,获利甚丰。南唐时,玄武湖中“每岁菱藕罟网之利不下数十千”。[42](卷1,P210)由于城北地区面积广大,尚不具备发展工商业的条件,所以即使到了南唐,金陵城周围仍有很广大的农业区,居民以农业人口为主。
运输业也是重要的产业之一。吴都建业时,就已“楼船举帆而过肆”,市肆中的商品是远道运输而来,时“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25](卷48《吴书·孙休传》,P1158)刘宋大明八年(464),孝武帝诏曰:“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6](卷6《孝武帝纪》,P134)作为商品的粮食,全是通过运输后再贩卖的。《唐国史补》卷下云:“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扬子、钱塘二江,则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江南城市的商品都得靠运输,所以长江运输就极为繁盛,成为当时的主要航路。《中吴纪闻》卷4云:“夜航船,唯浙西有之,然其名旧矣。古乐府有《夜航船》之曲。皮日休答陆龟蒙诗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榨酒三瓶寄夜航。’”皮日休诗收在《全唐诗》卷614。江南重水上航运,客货运输以船运为主,从很早以来就发明了夜间航行的船只,可以日夜兼程地赶路。开元时,张九龄在江宁县,见到长江中间“万井缘津渚,千艘咽渡头。渔商多末事,耕稼少良畴”。[9](卷49《候使登石头驿楼作》,P604)这些商船中,想必很多就是专门跑运输的。开元时,长城县尉陈利宾从会稽出发,沿浙江回东阳,“会天久雨,江水弥漫,宾与其徒二十余船同发,乘风挂帆。须臾,天色昧暗,风势益壮。至界石窦上,水拥阏众流而下,波涛冲击,势不得泊。其前辈二十余舟皆至窦口而败,舟人惧”。[15](卷104,P705)这些舟人都是通过交通运输作为生活来源的。此外,运送货物用船或车辆外,还有靠人力的。茅山陈生,“偶到延陵,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却归山居。以价贱,多不肯”。[15](卷74,P464)佣作坊就是专门雇人的区域,通过人力挑担运输货物。
高利贷业、城市农业、运输业,对江南城市的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它们完善了城市的经济结构,推动了城市经济产业的多样化、多层次,使城市的经济功能更为多样化。
六、余论:江南城市产业的特点
城市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六朝以来的江南城市经济,以商业为主、手工业为辅。到隋唐五代,城市服务业开始兴盛,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经济结构上呈现出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性并存的特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手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不断加重,城市的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产业特色渐趋纷呈的局面。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经济产业,大体而言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江南城市产业结构基本合理。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在逐渐显现,这主要归功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商业长足发展后,不再是政治性城市的依附,而是有自身独立的发展体系,商业不断展现出一些新现象。城市手工业尽管技术要求不高,还是比较粗放的,但手工业门类在增多,利用了有利的材料供应,手工业发展越来越有特点。城市服务业是城市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为人口增多的城市居民生活服务的一个新兴产业,它直接辐射到周围广大的农村地区,使更多的城郊农村卷入商品交换中来。对外贸易等行业虽然在整个城市经济中所占比重不算太高,但在完善城市经济结构体系上的作用不可忽视。江南城市创造出的经济实力,通过水陆交通线路,与相邻地区的城市,乃至中原地区的城市,构成经济网络,大大有利于全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认为,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产业结构基本合理,可以大体满足一个城市发展对经济的需要,符合当时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当然,这些产业还是比较粗疏和简单的,与宋朝以后城市经济产业的发展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过,宋朝以后城市产业发展的色调在六朝唐五代已经显现,只不过宋朝以后更加浓重而已。
第二,江南城市产业地域性明显,不同城市形成了各自的产业特色。比如江南城市商业的发展在大城市发展较快,而小城市,特别是县城,商业的发展比较缓慢。处于江南运河沿岸、长江沿岸、钱塘江沿岸的城市,由于倚恃了交通业的发展,商业和城市服务业发展较快。六朝的建康、山阴,唐中期以后的苏州、杭州、越州、润州,唐末五代的金陵、杭州,城市规模较大,城市经济的内涵比较丰富,影响力较大。手工业的发展更是与各地的原材料提供密切相关。如金银器制造主要分布在润州、苏州、宣州等地;沿海、沿江城市的造船业比较发达,而内陆城市没有发展造船业的条件;外贸业的发展主要在明州、台州、温州、杭州、金陵等一些有港口的城市中。
总体上说,苏州、建康(金陵)、杭州等大城市的产业门类比较齐全,商业和城市服务业发展比较兴盛;而沿海、沿江的城市发展交通运输、外贸业等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有自然资源的城市手工业发展具有地域特色。
第三,江南城市产业分工与城市发展相适应。城市产业分工与城市的规模比较一致,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城市中的产业分工就越来越细化。城市人口增多,城市中既居住着贵族官僚、军队、各种政府服务人员,同时又居住着大量的普通居民,这时分层次的各色商业服务就会应运而生,就会产生对不同质量和档次的手工业品的需求。官员及其子女、士族子弟对商业服务和手工业品的需求,与城市中的各种从业人员,如出卖体力者、巫医卜相、娼妓、奴婢、官户、杂户、乐户及太常音声人、僧尼道士等,肯定各不相同。因此,城市中人口的多少、阶层的不同,直接会促使商业、手工业、服务业和外贸业的发展起落。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现象,表现在产业结构上,服务业和外贸业快速发展。这与同时期各地其他城市的发展有较大的不同,是江南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我们在评论江南城市发展不应忽略的。不过从总体上说,我们也不应夸大城市经济生产的作用,因为江南城市主要是消费型的,并不是生产型的。无论是商业、手工业还是外贸、服务业和其他一些产业,最主要的是为了满足城市中日益增长的消费。城市中有些部门的生产力的确超过了城市本身的需要,但这种生产局限在一定的领域,生产能力还是有限的。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产业时应该注意的一点。
注释:
①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815《布帛部二·锦》引山谦之《丹阳记》:“斗场锦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624页。
[1] 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元稹.元稹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0] 张津.乾道四明图经[A].宋元方志丛刊[C].北京:中华书局,1990.
[11]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2] 徐铉.稽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3] 张剑光.六朝唐五代江南城市市场的形制与变化[A].唐史论丛(第十五辑)[C]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
[14] 陶谷.清异录[A].全宋笔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5] 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6] 冯贽.云仙杂记[A].笔记小说大观[C].台北: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4.
[17] 杜牧.樊川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8]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19] 白居易.白居易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20] 谈钥.嘉泰吴兴志[A].宋元方志丛刊[C].北京:中华书局,1990.
[21] 张鷟.朝野佥载[A].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2] 李复言.续玄怪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3] 徐陵.徐孝穆集[A].四部丛刊初编[C].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
[24] 龙衮.江南野史[A].全宋笔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25]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6] 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7] 罗宗真.探索历史的真相——江苏地区考古、历史研究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28]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9] 李长庆.西安北郊发现唐代金花银盘[J].文物,1963,(10).
[30] 简修炜,等.六朝史稿[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1] 方万里.宝庆四明志[A].宋元方志丛刊[C].北京:中华书局,1990.
[32] 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J].考古,1984,(5).
[33] 张剑光.唐五代江南的外商[J].史林,2006,(3).
[34] 祝穆.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5] 台州地区文管会、温岭文化局.浙江温岭青瓷窑址调查 [J].考古, 1991,(7).
[36]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7] 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A].长水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8] 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A].全唐诗初编(第三编)[C].北京:中华书局,1992.
[39]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0]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1] 林士民.浙江宁波市出土一批唐代瓷器[J].文物,1976,(7).
[42] 郑文宝.南唐近事[A].全宋笔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