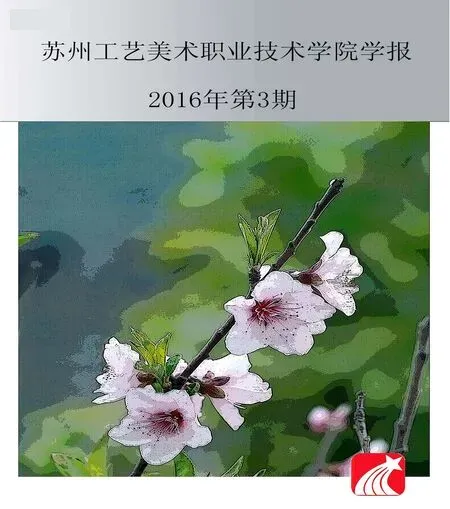美术范畴的工艺美术综论(上)
2016-04-12董波
董 波
美术范畴的工艺美术综论(上)
董波
工艺美术是以装饰为本的美术,就其最宽泛的意义而言,就是要让形象满足时宜。美术概念的源头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迪塞诺,即人类用双手表达的逻各斯。苛刻的眼与听话的手造就了工艺美术,宽容的眼与自由的手造就了“纯艺术”。工艺美术与“纯艺术”并存,是美术发展的方向。
美术 工艺美术 装饰 逻各斯 迪塞诺 眼 手 “纯艺术”
一、何谓美术?工艺美术是什么样的美术?
(一)“工艺美术”:从词组到词
“工艺美术”源于英文Arts & Crafts,它本来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并列词组,即“工艺(Crafts)与美术(Arts)”。因此晚清民国时期并用“工艺美术”与“美术工艺”两种表述,且两者往往可以互换。但自从1954年“工艺美术”成为学科名称以来,“美术工艺”这种表述便停用了,“工艺美术”则完全成了一个词,其中的“工艺”成为“美术”的修饰语;所谓工艺美术,便是“具有工艺性质的美术”。
(二)“美术”一词的内涵与外延
目前我国学术界较多认为,“美术”一词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对英文Fine Art(Fine Arts)的汉字翻译,最初指那些凸显审美内涵的创造行为。诗人作诗,作曲家作曲,画家作画等等,都属于“美术”。这样的“美术”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艺术”。但后来“美术”狭义化了,专指“视觉艺术”。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这个世界上最能跨越“距离”的是光,而捕捉光的人类器官是眼睛,因此凸显“美”的艺术最终会走向视觉。
美术中的视觉必须彰显其跨越时空的能力,并非所有依赖于观看的艺术都是美术。比如舞蹈和戏剧之类的表演艺术,也需要人们观看,但一旦表演结束,观看也随即结束;只有将表演场景用图画描绘下来,或者把演员表演的样子做成雕塑、拍成照片,才算是美术,因为这一定意义上让人们在表演结束后仍能“观看”表演。美术中的视觉还必须具有独立价值,不能成为其他感觉的附庸。比如文字,若作为记录有声语言的工具,便属于文学;但若作为一种图画,便是书法,属于美术。综上,美术就是能够凸显视觉跨越时空的能力、彰显视觉独立价值的艺术,现如今它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以及摄影和书法。在所有美术门类中,绘画最能凸显视觉跨越时空的能力、彰显视觉独立价值,因此绘画可谓美术的核心。我们当然不能说美术仅仅是绘画,但一个对画画毫无感觉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美术家的。
(三)造型与装饰之辨
视觉跨越时空的能力首先体现在速度上。视觉捕捉的是光,而光是世界上最快的东西,能在瞬间为眼睛提供高保真的信息。对人而言,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采取行动,首先需要眼睛来捕捉信息。一个汽车司机耳朵不灵或许可以容忍,但绝对不能是盲人。从这个意义上,视觉最具有时效性。另一方面,视觉也最具有历史性。侦探再现案情,考古学家再现人类历史,地质学家再现地球的过去……所有认识过去的行为,都依赖眼睛来观察过去发生的事所留下的痕迹。也就是说,通过视觉,你变得既善于把握时尚,也善于把握永恒。
任何一种视觉形象都是时尚与永恒的奇妙融合,这使得美术兼具“装饰”和“造型”两种属性。这里的“装饰”是广义的,并不单单指用漂亮的纹样来包装,而是指针对具体的时空与场合创造出形象合宜的事物。“造型”则正好相反,它强调永恒性。“型”不是“形”,而是理想典范,有着放之四海皆准的性质。“装饰”彰显时尚,“造型”彰显永恒,任何一个门类的美术都有这两种性质。因此就其性质而言,美术可以分为“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两类。所谓工艺美术,指的就是这里的“装饰艺术”,其根本特点就是具有时尚性与合宜性。英语中,“工艺美术”除称为Arts & Crafts外,亦可称为Decorative Arts,即“装饰艺术”。
美术中的任何一个门类既可以成为造型艺术,也可以成为装饰艺术——它们既可以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去珍藏,也可以用来装点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绘画,人们常称其为“造型艺术”,若指的是那些博物馆中的名作,那的确如此;但世界名画毕竟是少数,更多的绘画是挂在我们的客厅或卧室里,其主要属性不是造型,而是装饰,甚至有不少绘画就称为“装饰画”。其实,又有哪种美术不是为了适合具体的时空、具体的生活而造的呢?在这个意义上,工艺美术作为“装饰艺术”,可以涵盖到美术中的任何一个门类。
(四)工艺美术:以装饰为本美术
必须承认,在不同的美术门类中,造型性与装饰性的比重是不同的。比如绘画和雕塑就更能凸显其造型性,有些绘画和雕塑,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而存在的。梵高(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同时代的人并不喜欢用他的画来装点房间,这些画其实属于梵高死后的博物馆和藏家。现如今,你想用梵高的画来装点房间,大概就只能去买复制品或印刷品了。由此,梵高的画成了一种“型”,人们会以拷贝它为荣。相比之下,建筑和工艺美术则富含装饰性。一幢房子或一件工艺美术品若不能尽快用上,岂不是浪费?正是基于这种实用属性,建筑与工艺美术常被称为“实用艺术”;而凸显造型性的美术门类则常被称为“纯艺术”,其代表便是绘画和雕塑。实际上,英语Fine Art(美术)可直译为“纯的艺术”。在今天的美术学府,可以没有建筑和工艺美术专业,但一定会有绘画和雕塑专业。在很多老百姓心目中,“美术”指的就是绘画和雕塑。
即便是实用艺术,其造型性也是存在的。比如在建筑中,装饰性与造型性是并显的。建筑当然得满足具体场合的需求,但它也是彰显人类文化永恒魅力的能手。通常只有建筑存在,其他门类的美术才会保留下来,这说明建筑不但是一种美术,还是所有美术最好的载体、最好的“仓库”。墓葬为什么能成为考古学家关注的对象?就是因为墓葬建筑往往比其他建筑更持久,里面所存之物会更丰富。即便是非墓葬的地表建筑,也可以成为历史的缩影。中国的长城、古希腊的雅典卫城、古罗马的斗兽场、中美洲玛雅人的神庙、西方中世纪的大教堂……这些耳熟能详的例子,哪个不是这样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志,采用的就是古希腊神庙的正面形象。我们生活中的“型”,真的有太多是来自建筑。建筑虽不算是“纯艺术”,但它的造型性却一点也不弱。
相比之下,在实用美术中,工艺美术的造型性便没有那么强了。工艺美术当然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那些以被收藏为初衷的工艺美术也算是造型艺术,但无论如何,“装饰”才是工艺美术的主心骨。当你对博物馆中的工艺美术品赞不绝口时,不要忘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当年都是供人日常使用的。比如当年景德镇的官窑瓷器,若未能进入宫廷成为皇家日用品,便会被销毁。离开了装饰性,工艺美术便不复存在。
可见,工艺美术就是最能凸显装饰性、以装饰为本的美术。而所谓“装饰”,就其最宽泛的意义而言,就是要让形象满足时宜——让那些我们看得见的事物变得时尚而实用。
二、美术从哪里来?
(一)美术概念的精神背景:灵魂与肉体的纠葛
最早提出“美术”(Fine Art)这个词的学者,大约是19世纪英国文艺评论家约翰 · 拉斯金。1859年,拉斯金在他的演讲稿《艺术的统一》(the Unity of Art)中将“制造”(Manufacture)、“艺术”(Art)和“美术”(Fine Art)三个词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制造”仅是动手;“艺术”不仅动手,而且动脑;“美术”则不仅动手、动脑,而且动心。“制造”“艺术”“美术”乃是动手的三个层次:“制造”层次最低,因为手只属于肉体范畴;而“美术”层次最高,因为手已经成了心灵的表现。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灵魂高于肉体,但“美术”的原初含义却体现出这样一种观念:肉体其实并非灵魂要全然抛弃的东西,肉体发挥得好,也可以达到灵魂的高度。一方面灵魂要超越肉体,另一方面肉体却抓着灵魂不放,灵魂与肉体的纠葛由此而体现。
宏观地看世界文化可以发现,灵魂与肉体的纠葛尤其体现在西方文化中,非西方文化则缺乏这样的主题。比如伊斯兰教强调“两世吉庆”,灵魂解脱到天国固然是终极目标,但在此世的肉体中灵魂也要很好地度过。在印度,最能代表本土文化的印度教发展出了一对彼此互补的教派:毗湿奴教(Vaishnavism)和湿婆教(Shaivism),前者是神灵化作肉身的教派,后者则强调肉身通过某种办法来通灵。源于印度、后来在东亚与东南亚产生很大影响的佛教强调灵魂抛弃肉体,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呈现向灵魂一边倒的局面;佛教禅宗还强调通过“顿悟”来消解灵魂与肉体之间痛苦的冲突。而在古代中国,最具本土特色的道教则从未把灵魂与肉体分开,以长生或成仙为目的的炼丹术就是强调灵魂与肉体相融的代表。可以说,美术这个概念的精神背景正是西方文化中灵魂与肉体的纠葛。在伊斯兰、印度、中国这些非西方文化中,手作为肉体的一部分,并非心灵的有力对手,很多时候,手与心灵恰恰是相融的。手工劳作没有必要分出所谓“制造”“艺术”和“美术”三个层次。因此我们今天谈非西方的“美术”或“艺术”时,不仅要谈绘画、雕塑,更要谈器物制作。比如在伊斯兰世界,绘画和雕塑因伊斯兰教义而受到限制,所以伊斯兰美术其实主要体现在精美的伊斯兰生活用品上。打开任何一本《世界美术史》,凡是介绍非西方美术的部分,器物制作——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通常都会占据很大篇幅。
中国的情况略显复杂。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美术有“文人之作”与“匠人之作”之分,二者似乎分别对应于拉斯金所说的“美术”与“制造”。其实不然,“文人之作”与“匠人之作”不同在于创造主体的不同,而拉斯金所说的“美术”和“制造”却拥有相同的创造主体——动手制作者。在拉斯金看来,动手制作的人如果“用心”,就是在创作“美术”;而传统的中国匠人即便再“用心”,也不会创作出“文人之作”,因为他不是文人。“文人之作”与“匠人之作”的区分缘于社会分工,而与灵与肉的纠葛无甚关系。中国传统文人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瞧不起工匠。我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文献《考工记》有言:“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而到了宋代,文献中开始出现“百工之艺”的说法,如北宋四大部书之一《册府元龟》(1005-1013成书)和欧阳修的《集古录》(1063成书)等,由此可见匠作在当时文人心目中的地位。
(二)源自古希腊的理想:眼睛是手的主人
“美术”的概念只萌生于彰显灵与肉纠葛的西方文化中,而引发这种纠葛的,是西方文化的始作俑者古希腊人。古希腊人强调灵魂超越肉体,但也深知这绝非易事。古希腊的神灵不在天上,而是住在奥林匹斯山或各城邦的神庙里,他们其实是人间万物的化身,彰显着人的七情六欲。古希腊人无法把与肉体相关的东西“送”到天上去,只能在人间小心地应对他们。
要消灭肉体,得靠杀戮,而大规模的杀戮来源于战争。正是从战争中,古希腊人找到了灵魂超越肉体的途径。战俘通常不被杀死,而是成为了奴隶。奴隶就是原则上能被完全操控的肉体,而操控者就是自由人。放眼古希腊社会,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其实就是自由人与奴隶的关系。没有奴隶去做繁重的事,自由人便不可能“自由”。古希腊社会需要奴隶,因而需要战争,但战争也会让自由人沦为奴隶,这让自由人很矛盾。于是古希腊的自由人就定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此定期休战。两败俱伤的战争变成了相互促进的竞争。失败者不会被杀死、也不会沦为奴隶,在肉体上没有损失,他失去的只是冠军头上的那个象征和平与尊严的橄榄枝冠。在这里,肉体的拼搏完全是为了灵魂的荣耀。
古希腊人的灵魂观念突出体现在他们建立了感觉的等级。人的基本感觉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和视觉五种。触觉、味觉、嗅觉依靠的是感觉器官与被感觉对象的直接接触。比如触觉,便是依赖于感觉器官和物体的宏观接触;而味觉和嗅觉,则是依靠感觉器官和某些分子的接触。听觉和视觉不一样,它们依靠的是能量的传导作用。听觉依靠声波,视觉则依靠光波,所以从跨越时空的角度讲,听觉和视觉超越了其他感觉。动物的世界往往凸显触觉、味觉和嗅觉的作用,而人类的文化传承则主要依赖视觉与听觉。我们可以说触觉、味觉、嗅觉更靠近肉体,更具动物性;而听觉与视觉则更能彰显人类灵魂。古希腊人认为灵魂高于肉体,他们因此认为视觉和听觉高于触觉、味觉和嗅觉,并努力用前两者控制后三者。
古希腊人尤其推崇视觉。在古希腊哲学泰斗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的名著《蒂迈欧》(Timaeus)中,哲人蒂迈欧(Timaeus of Locri,约前420-前380)说:“在我看来,视觉乃是我们最大利益的源泉,因为我们若是从来不曾见过星辰、太阳、月亮,那么我们有关宇宙的谈论一句也说不出来。”显然,“星辰”“太阳”“月亮”都只能看到而不能摸到,所以蒂迈欧所推崇的视觉是远离肉体的。但蒂迈欧接着说:“神发明了视觉并且将它赐予我们,其目的在于让我们能够看到天上的理智运动,并把它应用到我们自身的理智运动上来,这两种运动的性质是相似的,不过前者稳定有序而后者则易受干扰,我们通过学习也分有了天然的理性真理,可以模仿神的绝对无误的运动,对我们自身变化多端的运动进行规范。”可见,远离肉体的视觉恰恰应该成为肉体行动的准则。
肉体不可及,却又能支配肉体,这样的视觉对象柏拉图称之为“理式”(Idea)。所谓“理式”,可以理解为“理想状态”。比如要做一百个形状一样的饼干,单纯用手捏制难以成功,但如果使用一个饼干模子,便很容易达到目的。对于饼干这个模子就是理式,它并非饼干,而是饼干的“型”,是抽象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之口,以床为例来阐述理式。苏格拉底指出,床的原型只有一个,即“理式之床”,它大概是神造的;工匠依据“理式之床”造出具体的床,画家则依据工匠造的床来画床。工匠造床、画家画床都得靠眼睛,所不同的是,工匠依据的是抽象的理式,而画家依据的是可以摸得到的东西。结果是工匠做出了切实可用的东西,而画家则造出了骗人的幻象。由此可见,视觉以抽象的“型”为起点,可以生出具体可靠的事物;若以可以触摸的东西为起点,生出的则是幻象。所以正确的感觉顺序应该是视觉在前、触觉在后。若追溯视觉的源头,你发现的是抽象的“型”,而非具体的物品。其实理式一词的本义就是“看”,这里的“看”指的是洞察力,而非单纯的肉眼观察。
古希腊人主张“看了再做”,而不是“做了再看”。眼睛是手的主人,而不是相反。一个人越善于“看”,他就越自由;而一个人仅仅擅长“做”,他就可能沦为奴隶。在古希腊,自由人与奴隶的关系,其实就是看与做、眼与手的关系。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就是最擅长“看”的人,因而应该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一旦一个人靠动手吃饭,那他的社会地位便不可能高。据古罗马人记述,即便是古希腊雕塑名家菲迪亚斯(Phidias,约前480-前430),虽然他创作了著名的奥林匹亚宙斯像(Statue of Zeus at Olympia,“七大奇迹”之一)和帕特农神庙雅典娜像(Athena Parthenos),也被认为仅仅是一个工匠而已。正如古罗马学者塞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前4或3-公元65年)所言:“我们在神像前祈祷和供奉物品,却轻视那些制作它们的雕塑师。”在古罗马,古希腊雕像已经成为典范,我们今天所见的“古希腊雕像”很多都是古罗马的复制品。显然,古罗马人崇拜的是古希腊雕像的视觉形式,而非古希腊工匠制作雕像的能力。古希腊人主要是通过他们的慧眼,而不是巧手,才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像古希腊哲学家这样善于“看”的人,也得把他们看到的道理说出来,以便让别人理解。哲人看出的道理古希腊人称为逻各斯(Logos),它是“逻辑”一词的词源。据说是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斯(Heraclitus of Ephesus,前535-前475)最早提出了逻各斯这个词,用来指事物多变的表象背后不变的道理。汉语常将其译为“道”,其实逻各斯与中国道家所讲的“道”是有区别的。中国道家的道本义是道路。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可见道路是踩出来的,是触觉的产物,而不是说出来的。《道德经》开头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即道若能够说出,便不是真正的道。而逻各斯正好相反,其本义就是“话语”,是“说”的意思。对于只能看到而不能摸到的东西,谈论它正是让人认识它的根本手段。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而在古希腊人看来,只有奴隶才应该这样,自由人恰恰应该“敏于言而讷于行”。在古希腊,受人尊敬的职业倾向于动口而非动手。比如诗人就比工匠地位高得多。古希腊语“诗人”一词的本义是“创造”。古希腊的诗是诗人吟唱出来的,由此又派生出了音乐。柏拉图的《国家篇》中,苏格拉底指出“曲调和节奏必须符合言辞”,古希腊的音乐正是源于语音的和谐。英语音乐一词称为Music,其词源正是古希腊文艺女神的名号——缪斯(Muse)。缪斯女神最善于歌唱。在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Pindar,前522-前443)的诗作中,“带着一个缪斯”意思就是“唱一首歌”。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叫塔米里斯(Thamyris)的人物,他骄傲于自己的歌唱天赋,居然要和缪斯女神一比歌喉,结果失败了,被缪斯弄瞎了双眼,也失去了做诗和演奏竖琴的能力。古希腊人总是将听觉与视觉紧密相连。按照古罗马学者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116-前27)的说法,古希腊的缪斯是三位女神:一位诞生于水流,一位能够震动空气而发出声响,还有一位由人声表征。这里彰显的均是听觉因素。后来缪斯女神又各自一分为三,数目上升至九个,分别掌管史诗、历史、抒情诗、音乐、悲剧、赞美诗、舞蹈、喜剧和天文。这里面没有绘画、雕塑、建筑,没有强调动手制造的活动,因为缪斯的神力聚焦于人的耳朵,而不是手。与视觉一样,听觉也是属灵的感觉,在古希腊,与视觉崇拜直接相伴的是听觉崇拜。
与佛教徒不同,古希腊人并不轻视肉体。相反,正是因为觉得肉体难以驾驭,古希腊人才特别强调控制肉体。通过推崇看得见却摸不着的东西,古希腊人将视觉凌驾于肉体之上,而哲人所“看”到的真理又以逻各斯(话语)的形式传达出来。一般人可能看不到真理,但听了哲人的阐释便能明白真理。在古希腊,听觉是促进普通人思索、让他们也能“看”到真理的手段。缪斯一词的本义就是“记忆”和“思考”,与令人迷狂的音乐相去甚远。古希腊哲人普遍对迷狂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迷狂正是肉体力量的集中体现。肚子饿了看到美味会不想吃?手碰到火苗会不往回缩?肉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容反思。不容反思的生活是被动的,事情都是不得不做的。古希腊人从肉体那里发现了人的奴性。所谓奴隶,就是纯然的肉体,他所做的事都不容他反思;而自由人的标志就是有能力反思,可以有选择地生活。可见,逻各斯是让人获得主动性、获得自由、获得尊严的条件。在古希腊人看来,缺乏逻各斯,人就会沦为奴隶,甚至沦为动物。
就肉体而言,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在于拥有灵巧的手。手是触觉器官,但通常是主动地去接触世界并改变世界。手的主动性缘于它是最能接受逻各斯的肉体器官,这是源自古希腊的观点。古希腊人最忌讳“盲目”动手,手必须接受眼睛的指导,而聪慧的眼睛看到的是逻各斯,是抽象的道理。
(三)基督教的“道成肉身”
西方世界,古希腊的直接继承者是古罗马。古罗马人说的是拉丁语,其语法极其复杂,德国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曾风趣地说,如果古罗马人都弄懂了拉丁语法,他们就没时间去征服世界了。与古希腊人不同,古罗马人偏爱的不是言说,而是实干,他们是出色的征服者与管理者,最终建立了文化多元的奴隶制帝国。古希腊的理想似乎在古罗马变成了现实。然而,古罗马再也没有出过能与柏拉图媲美的哲人。新的文化主题不是思辨,而是信仰。在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古老的希腊文化和犹太文化碰撞出了新的精神果实——基督教。
现今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就是以基督耶稣诞生之年为元年。对于西方文化,基督教的意义怎样夸大都不为过。耶稣是犹太人,而犹太人与当时其他民族不同,崇拜独一的、万能的、无处不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的神。他们甚至不敢直呼这个神的名号,仅用四个字母表示神名(拉丁字母通常转写为YHWH,意思约是“我就是我”),后人通常将其读作“耶和华”(Yahweh)。耶和华通过话语来传达意志,他说啥有,啥就有;要怎样,就怎样。谁听他的话,谁必有福;谁若不听,必受惩罚。耶和华偏爱信他、听他话的人,犹太人由此获得了优越感。然而,完全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却非常困难。于是,耶和华化身为人来做示范,这个人就是耶稣。神的话语成了拥有肉身的人,这便是“道成肉身”。被耶稣打动的人,自觉地效仿耶稣,成为基督徒。
犹太人将耶和华视为他们的上帝,而耶稣却可以成为所有人的上帝。基督教包含了诸多非犹太文化要素,其中最主要的源自古希腊。“道成肉身”中的“道”就是逻各斯。古希腊哲人强调用逻各斯来控制肉体,然而大道理谁都说,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身教是胜于言传的。耶稣就是以身作则的神,他教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每个人都有肉体,灵魂要从内部控制自己的肉体,而不是从外部控制别人的肉体。基督教兴起后,奴隶制就逐渐解体,身心合一的体力劳动受到重视,毕竟肉身应该作为道(逻各斯)的载体而存在。即便是贵族,也会从事手工劳作,因为这是一种修行的方式,让自己的心灵更加接近上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拉斯金“美术”概念的影子。如前章所言,拉斯金正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其思想对工艺美术概念的萌生影响深远。
但基督教的主宰,却并不意味着工匠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出色的手工制品被视为圣灵做功的结果,而非工匠的功劳。在基督教兴盛的西方中世纪,工匠很少会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姓名。与古希腊人一样,基督徒视灵魂为主、肉体为奴,关键在于肉体听命于什么样的灵魂。《圣经》开头就说上帝是“灵”,基督徒称之为圣灵。上帝还造出一些灵魂来传达他的旨意,称为天使。天使若不听上帝的话,便堕落为魔鬼。魔鬼觉得自己也是“灵”,于是敢于与上帝抗衡。按照基督教的观念,人一旦自大,便是魔鬼在做功了。
听上帝的话始终是基督教的核心,由此凸显的是听觉的意义。这影响到基督徒的文艺观。中世纪基督徒认为艺术有七种,其中三种和言语相关,统称为“三艺”(Trivium),分别是语法、修辞和逻辑;四种和数相关,统称为“四艺”(Quadrivium),分别是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从中显然可以找到古希腊缪斯的影子。
基督教崇尚听觉,却也不忽视视觉。毕竟耶稣是活生生的人,是可以看得到的榜样。但与古希腊的情形不同,视觉和听觉在基督教文化中并不和谐。尤其在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激烈碰撞的东罗马地区,视听间的矛盾逐渐变得难以调和,导致了拜占庭帝国的“圣像之争”。一部分人延续犹太人的传统,认为神不能被看见,主张去除一切神像;另一部分人延续古希腊的传统,推崇视觉,主张制作神像。双方互不相让,冲突持续了一百多年,流了不少血。结果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允许给耶稣塑造画像,但不能为他塑造雕像。神圣者只能被看到,而不能被摸到,这里更多体现出古希腊的传统。在基督徒看来,耶稣就是逻各斯——即便拥有肉身,也可望而不可即。拜占庭的圣像画并不强调生动写实,而是具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尤其偏爱使用金色。神被看到的同时,和人保持着永恒的距离。
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的政体继承者,其居民主要讲希腊语;而在拉丁语流行的西罗马地区,伴随着基督教兴起的是一批日耳曼人建立的小国,罗马教皇由此占据了原先罗马皇帝的位置。在圣像的问题上,教皇不像拜占庭人那样“讲原则”,而是遵循了古罗马注重实效的传统。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Ⅰ,590-604在位)有这样一句著名的论断:“读书人可以根据文字理解教义,不识字的人只能根据图像理解教义,因此,圣像是不应该销毁的,因为教堂设置图像不是供人崇拜的,而是可以启迪无知者的心灵。”这里的“圣像”既可以是绘画,也可以是雕塑,只要能让当时众多的文盲基督徒明白圣经故事就行。而且,这些绘画和雕塑应该尽量生动写实,这样才更能打动人。因此在罗马教皇的势力范围(主要在西欧),中世纪的绘画和雕塑越来越写实生动,直至文艺复兴巨匠作品的到来。
基督教的本质是道成肉身。逻各斯不是从外部强加于肉体,而是变成了肉体,以感化那些尚未接受逻各斯的肉体。然而,道成肉身却并不意味着“肉身成道”。纵然基督徒礼拜时总会宣称“我信身体复活”,但即便是最虔诚的基督徒,也没有一个能像耶稣那样肉身复活。对于肉体,与其让它死了以后复活,不如让它在活着的时候多承载上帝的意志。这种明智在中世纪晚期率先被一些基督徒所拥有,正是他们带来了文艺复兴。
(四)美术概念之源:文艺复兴的迪塞诺
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人十分崇拜上帝,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贬低了人。恰恰相反,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人正是上帝在凡间的代理。所谓“凡间”,就是肉体所能触及的范围。既然道成了肉身,肉身就要充分发挥它的主动性。对于圣灵,肉体是接受者;而对于那些能够摸得到的东西,肉体则是施动者。文艺复兴的本质就是对肉体的肯定。
人接受圣灵,靠听上帝的话;若要发挥肉体的主动性,则首先依赖于眼睛。一个基督徒即便再相信上帝能决定他的命运,也不会闭着眼睛过马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圣经·新约·路加福音》也有同样的记述。人的眼睛是“主动的”器官,想看可以多看几眼,不想看可以闭上眼睛或调过脸去;而人的耳朵则是“被动的”器官,无论想听不想听,它都在听。基于对肉体主动性的强调,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将眼睛置于耳朵之上。
在文艺复兴的故乡意大利,“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观念很快流行起来,这与意大利语的成型不无关系。意大利语从中世纪晚期的通俗拉丁语演变而来,其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单词都以元音结尾,且音节组合和重音很有规律。由于把语音的曲调感和节奏感结合得如此完美,所以意大利语获得了“世界音乐语言”的美誉。但说话毕竟不是唱歌,我们宁可话音不悦耳,也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当意大利人迫切地想说大白话,而他们诗歌般的语言又不给力时,便想到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传达语义。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与新的意大利语文学相呼应的,是绘画、雕塑大师的出现,他们擅长动手制造形象来代替言语。美术概念的源头正在这里。
古希腊哲人推崇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他们喜欢仰视天空;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有识之士则推崇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们喜欢平视世界。仰视天空带来了逻各斯,平视世界则引出了定点透视法,二者都是眼睛所建立的秩序。透视法是一种表现真实可见世界的绘图方法,所表现的事物“近大远小”。人眼与其所见相比实在是太小了,因此视野是一个以人眼为顶点、不断向视线方向拓展的锥体。视野延伸得越远,能包纳的范围就越大。4米高的房子可以挡住双倍距离之外8米高的房子,也就是说,8米高的房子看上去就像4米高,只要它离开眼睛的距离翻一倍。为了让视野中所有的物体按“近大远小”的原则建立稳定秩序,眼睛和视线最好保持不动,这便是定点透视法的由来。按照定点透视法画出来的景象,就像一个目光固定的、视力很好的、能瞬间捕捉视像的、没有视觉变焦的独眼龙所看到的,与其说它是现实的视像,不如说体现出一种理想。人作为上帝在凡间的代理,就应该能看到这样的秩序。
透视法就是通过物体看起来的大小来判断它和我们身体间的距离,也就是通过“看”来度量“摸”。为了表达视觉和触觉的直接关联,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发明了一个词——迪塞诺(Disegno),它的意思是“素描”。与其相对的词是“色彩”(Colorito)。色彩是纯视觉的,只能看到而不能摸到;而素描总是在用视觉形象来表现那些可以摸得到的东西。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重视素描甚于色彩,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五颜六色,而是因为他们更强调“看”与“摸”的关联。
对素描来说,画轮廓线很重要,因为那是物体可触摸的边界。意大利文艺复兴学者型巨匠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在其名著《论绘画》中说:“如果没有好的轮廓限定,就谈不上好的构图和色彩,也就是说,迪塞诺本身必须是好的、优美的。”这里迪塞诺就是轮廓线的意思。轮廓线只是对画面上各种视觉要素的一种限定,并不一定非要清晰地画出来。就正如很多老师给学生作范画时,并不用线条起稿,却可以很好地安排构图与色彩。可见迪塞诺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本身并不可见,但受过训练的人却能够通过迪塞诺塑造出美好的视觉形象。
迪塞诺颇似于逻各斯或理式,只不过它不是口舌阐释的对象,而是双手塑造的对象。某种意义上,迪塞诺就是能够摸得到的逻各斯或理式。用双手塑造迪塞诺,塑造的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事物的“型”。“造型艺术”的概念由此而生,它主要包括绘画、雕塑和建筑。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雕塑家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1378-1455)就曾指出,迪塞诺是绘画、雕塑和建筑“共同的父亲”,是“内在理念的可视表征”。到文艺复兴盛期,巨匠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1475-1564)总结道:“迪塞诺的科学,或者说基于线条的素描——如果你喜欢用这个词的话——是绘画、雕塑、建筑,以及其它所有表现形式的源泉和本质,也是所有科学的根源……每当沉思于此,我就会发现,只有一种艺术和科学,那就是迪塞诺,人类大脑和双手的所有成果,要么是迪塞诺本身,要么就是它的派生。”1563年,一群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成立了一个机构,称为“迪塞诺艺术阿卡德米”(Accademia delle Arti del Disegno),米开朗琪罗被推举为领袖。“阿卡德米”(Accademia)即“学院”。与“大学”(University)不同,阿卡德米不是源自中世纪,而是源自古希腊。第一所阿卡德米由柏拉图创立,它是学者畅论哲理的象牙塔。迪塞诺与阿卡德米并置,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也就成了“哲人”。“迪塞诺艺术阿卡德米”一般被视为是第一所“美术学院”,但它并非教学机构,而是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组成的协会,其档次高于工匠行会,凸显出迪塞诺阳春白雪的性质。
绘画、雕塑和建筑本是手工劳作,而文艺复兴却出了一批受人尊敬的绘画、雕塑和建筑大师。英语称“大师”为Master,与其相对的是Slave,即奴隶。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西方人一直强调肉体的奴性,强调灵魂对肉体的主宰。但到了文艺复兴,肉体终于出现了翻身的迹象。在绘画、雕塑和建筑这三种活动中,人发现自己的双手可以触摸到逻各斯,触摸到灵魂。灵魂与肉体的纠葛终于带来了美术的源头——迪塞诺。
(待续)
(董波,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