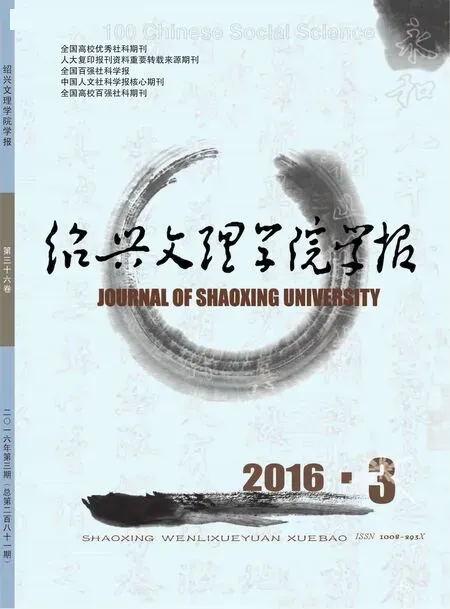翻译社会学视角下张翎小说《金山》英译传播研究
2016-04-12岑群霞
岑群霞
(浙江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2)
翻译社会学视角下张翎小说《金山》英译传播研究
岑群霞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2)
摘要:基于翻译社会学视角,探讨张翎小说《金山》的英文翻译和传播,包括作者创作、译者原文本选择、译本翻译、出版、传播过程,评述其翻译和传播策略可取之处。
关键词:翻译社会学视角;张翎;《金山》;英译;传播
张翎出生杭州,幼年移居温州,从此无论上海求学,还是加拿大工作、生活,目光从未游离“乡土”。她不仅书写华人的价值冲突和内心苦难,更延伸到由人物引发的家园想象及中西冲突历史。其代表作《金山》通过底层移民方得法家族五代人闯荡加拿大淘金、谋生故事,钩沉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跨时150多年,空间横跨中加两国。小说英文译本GoldMountainBlues2012年由加拿大企鹅出版社(Penguin Canada)发行,英国汉学家Nicky Harman担任译者,亦受好评。下文从翻译社会学重要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还原GoldMountainBlues伴随着激烈场域斗争的翻译、传播的曲折过程,评述其翻译和传播策略可取之处,意图为中国当代文学译介提供一个范例。
一、布迪厄场域理论简介
布迪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既是一个力场,又是意图转变或保持自身力量关系的竞技场:每一个介入者利用以前场域争斗所获资本制定策略,策略总方向取决于该参与者在权力争斗中的地位,即他所拥有的特定资本(主要是文化资本)[1]。
场域理论重要概念为场域、惯习和资本。场域是个社会空间,其特点可概括为:场域具独有规则;场域相对独立;权力场域处支配地位[2]。权力场域指的是在社会中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的能力的结构空间,是各种场域的整体和斗争场所。各种场域既相互联系又彼此隔离[3],处于不同地位。如文学场域规则主要基于文化资本,而权力场域规则主要源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所以文学场域在权力场域处于被支配地位[4]。场域概念亦可应用于翻译,因为翻译场域也是“斗争的场域”[2]。翻译场域在文学场中处于被支配地位。
惯习指人在成长、学习、工作、社交等过程中,逐渐学习、内化并强化社会规律而产生的思维和行为倾向。个体在场域中通过个体互动形成惯习,又通过惯习对场域施加影响。换言之,他们将社会惯例内化于思维和行为,后者又反过来影响环境。这种与环境互动的思维和行为特点,就是所谓“惯习”。
布迪厄用经济学“资本”概念表示人们的场域地位由他们在该场域的资格来决定。资格卓越者占统治地位并维护规则。不同场域要求的资格即资本不同,其基本形式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5],以及符号资本。经济资本指用以购买商品、服务的金钱。文化资本指人们从教育背景、职业等方面所获文化资源,如文凭、职业地位、著作或译作等。社会资本指个体所获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义务[5];符号资本指个体享有的社会信誉[6],又称象征资本。资本运作有赖特定场域,而转化是资本在场域中起作用的先决条件。经济资本可以转化成文化资本,如教育投资;文化资本也能转化成经济资本,如教育背景好常意味着拥有好工作;文化资本也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如学术地位高常意味着人脉关系广。但其它形式的资本都源于经济资本[5]。参与者们在各场域培养的惯习,使他们确认在某个场域需要哪些资本,才能使自己有利可图,因而努力寻求有价值的资本形式,获取场域利益[5]。
基于布迪厄社会学分析的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翻译场域中则表现为[译者(惯习)译者(资本)]+翻译场域=翻译实践,即:译者带着惯习和资本,进入翻译权力场域争斗[7]。除了自身惯习,还需利用各种资本,以争夺更多场域利益。与翻译联系最紧密的资本是象征资本。译者先是得益于原作拥有的象征资本,然后进行行为干预,将原作投射到目标文学场域机制中,从而授予原作者及作品若干资本[7]。下文将具体描述张翎在文学场的资本积累、译者在翻译场的惯习形成和资本积累、译作翻译、出版和传播过程。
二、张翎《金山》写作过程——惯习形成、文学场域竞争和资本积累
张翎从小耽于幻想,寂寞封闭的童年环境更给予她想象空间。曾担任代课教师、车床操作工,后自学英语进入复旦大学攻读英美文学,研究生期间大量阅读狄更斯、哈代、艾略特的原版小说。这些作家多关注故事和情节,使她在审美偏好方面对情节和细节留意甚多,远超叙述方式。1983年毕业后在北京煤炭部任科技翻译。1986年远赴加拿大,在加、美两国分获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后闯荡加拿大,尝试过行政秘书、翻译等职业,积累了学历、职业方面的文化资本。现定居多伦多任医院听力康复师,拥有了写作的经济资本。之前漂泊的生活、不断寻求的个性、多种职业和生活方式的尝试则奠定了写作的生活基础。
张翎在国内曾有零星发表,连贯写作则始于90年代的海外。她认为国内对物质的崇尚使人浮躁。与本土文化相隔太近,则难以产生理性思索和审美距离。在国外,一则经过长期沉淀的感受需要表达;二则加拿大表达的自由空间较大,而且医生的职业提供了压力和收入都适中的写作环境,不需为生存写作,也不至陷入物质主义,更得以触摸各族裔的文化脉搏,写作状态比较理想,因此不惑之年重拾创作梦想。因受大陆成长经历的影响,新移民作家主要用母语写作,作品主要发表在汉语报刊上,重要传播载体是中国大陆的重要报刊和出版社,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8]。张翎也不例外。她在《收获》《十月》《人民文学》《香港文学》及《世界日报》等处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望月》,中短篇小说集《雁过藻溪》《盲约》《余震》等,并获第七、八届十月文学奖(2000,2007),首届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2005),第四届人民文学奖(2006),《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度优秀小说奖(2008)等,这些作品和奖项构成更多文学资本,奠定了她在国内文学场域的地位。
张翎早期作品多植根温州,描述小家碧玉的儿女情长,随着创作日益成熟,笔端不再限于女性视角,开始追求宏大叙事,关注重大历史命题,深入人性、历史深处。据张翎自述,写作《金山》最初萌芽于1986年郊游时看到墓碑上的中国名字、日期和照片上先侨黧黑的脸,意识到是个好题材。感动之余,所恨时间、精力不够,因故事所涉历史框架和细节需要大量案头研究,并有被文坛彻底遗忘的风险。但2003年侨乡广东开平邂逅碉楼和永恒等候的女人形象,使她进入写作状态。她压抑激情,“零度介入”,保证了历史理解的客观多面,其客观、自由、平静的态度构成了《金山》的写作伦理[9],完成了不吐不快之作。
《金山》从劳工和留守的妻子两条线索展开,除了永恒的劳作和等候的生存问题,也涉及劳工下一代的主流融入、个人脸面和宗法社会等问题。如同许多女作家,《金山》历史描述更多是作为背景,人物命运刻画和曲折的情节、故事才是主线,但历史仍不容忽视。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教授黎全恩[10]回忆,张翎除了搜集图书档案资料,曾多次通过邮件或面谈向她了解加拿大华人历史,向华裔和土著文化历史研究专家Henry Yu询问印第安部落事宜,跑遍东西两岸华人遗址,并数次去开平访问学者和知情人,联络华工后代询问乡村生活和风俗。她的小说其实是“故事形式的历史”。在调研、写作过程中,张翎的文化资本积累已久,但经济资本尚缺。她倚仗诊所工作作经济后盾,自费调研也所需不少,只能利用社会资本住在朋友、《环球华报》主编张雁家省点费用,并通过关系查询资料。
语言惯习方面,许多旅外作家会选择英文写作,张翎学过七年英美文学,英文书写似乎顺理成章。她则认为英文是通顺优美达意的工具,但自由传神的感觉非母语莫属,使写作有兴奋感。再则用中文写作,思维是完全中式的,所谓“情绪化游戏空间”,大量阅读、与国内的学术交流,更使她的中文鲜活有味。《金山》译者Nicky Harman也赞同作家坚持母语写作。母语写作姿态虽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其作品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效果[8],却使她在中文界声名鹊起。
其实张翎主动选择用母语而非英文写作,也是出于文学场域地位的考虑。与国内作家比,她自然有外语优势,但与海外华人作家相比则不占优,势必湮没在海外华文女作家的海洋中,因为不同于国内男作家占优势,海外华人以女作家为主,且题材多为家族小说、移民身份认同等。与其以英文写作直接参与海外华文作家乃至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文学场域竞争,不如先与国内同行竞争,以旅外作家和母语写作作家的双重身份,在国内发表赢得文学地位和文化资本后再争取外译,同样能积极参与英美文学场域竞争,且胜算较大。此外,张翎是50后,年岁不小,闯劲稍逊,不比同为浙籍女作家的70后郭小橹,在英国英文写作,并利用出身电影学院的学历背景,自任编导,利用电影形式传播作品。
《金山》完成后,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金山》责编韩敬群(2009)介绍,《十月》副主编周晓枫认为《金山》是近年读过的最好作品。“十天左右,我们就和张翎谈妥了出版事宜”。并认为该题材之所以能引起许多共鸣,是他乡的拼死挣扎和故乡的深情守望,不止适合华侨。在国内打拼的人,同样是在“异乡”和“他乡”间纠结挣扎,国内国外都能体认书中情感。《人民文学》编者按则说,每个中国人都能从中感到共同的悲怆、共同的血气和情怀。《金山》由中国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和中国台湾时报出版社(2010)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关注。国内首印2万册,读者反馈几乎是没有例外的赞美。后斩获多项文学奖,包括《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华语传媒文学奖年度小说家奖、中山杯华侨文学奖评委会特别大奖、香港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等,张翎在国内文学场域的文化资本日益增加。张翎朋友、《环球华报》社长张雁(2009)援引多伦多《环球华报》分社主编评论:这是一部海外版的《活着》。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特别关注中国的小说类,《金山》进入国际视野,并一举卖出加拿大、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十国版权。其中第二位国际买家、加拿大企鹅出版社的艾德里安·柯尔的做法颇为典型:出于对张翎文化资本的信任,在连译文样品尚且没有的情况下,却抢先以五位数高价买下版权:“对这本书好评如潮,它在中国已经得了几个奖了,所以我们决定把它拿下”[11]。这样,《金山》通过国际书展获得国外知名出版社的经济资本,并通过出版社的文化、符号和社会资本,招募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知名女译者,进入译本翻译阶段。
三、译者Nicky Harman惯习形成和翻译场域的资本积累
2010年初,企鹅出版社委托Nicky Harman担任《金山》英文译者。她是在英国颇受尊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习中文,喜欢英国东方学者和翻译家Arthur Waley译的中国古代诗歌,以及《西游记》。“我喜欢那种语言非常精确且具诗意性的书。”曾任伦敦皇家学院翻译专业教师,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翻译,业余从事翻译。曾在香港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6)、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2008)访学。在学术、翻译场域积累足够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后,2011年辞掉教职,全职从事汉译英工作,主攻小说和诗歌翻译。译作有虹影的《K》(2002)、韩东的《扎根》(2009)、严歌苓的历史小说《金陵十三钗》(2012)等。与Eric Abrahamsen共同创立了“纸上共和国”(Paper Republic)网站,用以推广中国文学翻译,并在国际书展上推广该网站。她还设立了伦敦中国小说读书俱乐部,中国语言文学爱好者两月一聚。同时附设有Twitter,在会员聚会上朗诵中文小说或学术文献并讨论。
K是Harman翻译的首部中文小说,这是她喜欢的作品,销路也很不错。2003年她在中国经朋友认识了韩东,为后者的《扎根》倾倒,精心翻译后设法在美国找到了出版商。在2006年获PEN 翻译基金奖资助后,Banished!(《扎根》)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大提高了她在翻译场域的文化资本和地位。
Harman热爱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工作:“我发现自己不喜欢协商合同的经济条款……我知道自己在译者角色上的局限,可我从来不怀疑我热爱翻译,能从事翻译工作真是很幸福!我一直在努力做得更好,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并孜孜于中国文学推广:“在翻译生涯之初,我为中国文学做了很多推广的工作,今天我仍在做着这项工作。”[12]。刘云虹、许钧[13]评论,文化、翻译界一致认同的翻译模式是汉学家译者模式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相结合的翻译模式。汉学家译者模式的选择标准为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以及中国情谊。如上所述,Harman完全符合上述标准,是个理想的译者。
总而言之,Harman已经拥有雄厚的翻译场域的资本,使她有足够空间发挥译者惯习。译者惯习不仅影响其翻译策略、措辞等微观方面,还在宏观方面影响其对文本的选择[2]。译者惯习包括翻译选材、翻译观和翻译策略[14]。
关于翻译选材,Harman自述[12]选材标准是作品质量,甚至不论题材。如她曾翻译曹锦清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黄河边的中国》(2004)。选材过程也与众不同:她每年都去中国短期居住,与作家们直接交流,然后选择、判断这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在英国出版可能性较大,之后进行翻译。在中国行走不易,有时通过文学节,或个人邀请作家们来英国。这种面对面“发现”、结识作家,了解作品的即时交流方式,为翻译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中国当代文学浩如烟海,所以近年更常利用网络结识作者,不曾谋面。近年翻译了陈希我、安妮宝贝等新生作家和巫昂、颜歌等新锐的作品。这种做法与美国译者徐穆实建立“驻地翻译”基金的倡议,如征募外国翻译家到中国结识作家、翻译家和出版人;使自由翻译家发现中国新生作家,将作品节译后向国外文学杂志和出版商推荐;设立透明网络平台以便作家、翻译家、文学经纪人和出版商互动等不谋而合,只不过Harman直接进行了实践。张翎《金山》虽是企鹅出版社委托,其作品风格实与Harman的标准多有吻合:具语言风格,有出版可能,有市场销路。
Harman的翻译观是:在翻译大异于英文的中文时,为了让译文获得一种自然的效果,译者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注释文化词项,重组语言,从而不同译者所提供的译本读起来感觉不一样,因为每个译者的语言选择都是独特的。这使译者成为活跃的“重写者”,但译者同时需为作品负责,具有忠实的义务,以忠实传达原作者的交际目的为己任。
她的主要翻译策略是忠于原著。在她看来,译者会下意识地如变色龙般呈现出原文的色调和情绪。所以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的感觉,并在译作中加以反映,而不必纠缠于具体翻译方法。她本人常着迷于各种语言风格,种种新旧语体,以及语言的不同语域——优雅的、俚俗的,并力求把原文风格忠实再现于译作。
四、《金山》的翻译、出版和传播过程
1.翻译和出版过程
Harman致力发现中国当代重量级女作家,和张翎曾在自己组织的读书会上有交集,后者本属她的社会资本,又受拥有巨量文化和符号资本的企鹅出版社委托,自然义不容辞。
作为译者,Harman发现除了故事情节外,同一译本常需采用不同语言风格/语域,以与作者的语言风格相对应。比如,在《金山》原著中,男女主角写信采用相当正式的19世纪的中国文言风格。而劳工的用语是广东的俚语和粗俗语。加拿大华裔后代则讲现代汉语和加拿大英语。她力图找到一系列的英语语域使这个家族传奇听起来较为真实可信。然而翻译至半时风波顿起。
凭借文学场域地位,作者招募到企鹅出版社的经济资本,又借企鹅出版社的资本力量招到了名译,可以借助后两者力量进行作品推广。但无论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隶属于文学场域)内都有争斗,其他场域力量试图破坏作者和译者的文学资本,挤压甚或占据他们的场域地位。该书在大陆出版获奖、广受赞誉之际,即被有心者关注并攻击。2010年11月新浪网首先有文指控《金山》“搅拌式”抄袭了加拿大成名华人作家郑霭龄、李群英、崔维新、余兆昌作品,“使用”其英文小说中“最精彩构思和情节、内容”。华文传媒纷纷转载。作家面临的最严重的职业操守指控就是抄袭,能对其文学名声和场域资本、地位产生致命性打击。如果指控成立,遑论英语文学场域,国内地位亦不保。张翎不用英文写作,原为避华人和英语作家锋芒,不直接投身海外文学场域竞争。但此时她风头正健,大有冲击其他华人作家场域地位的可能,因此对手借机挑起争端。张翎奋起反击,竭力维护自身文学场域地位。在2010年12月《文艺报》的声明中,她以人格保证《金山》是久经锤炼的原创小说,大量公共史料包括历史及学术资料、实地考察和采访,经得起权威鉴定,意为疑似“重合”的部分是共享史料,实非情节抄袭。在温哥华《环球华报》采访中,则自陈是嫉妒和怨恨导致的“周密策划的攻击的受害者”。此后事态加剧,2011年10月李、崔和余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侵犯版权控告加拿大企鹅出版社、张翎和英译者Harman,索赔巨资,并要求图书下架、销毁。此时,不仅原作者,出版社也面临文化和经济资本受损的威胁。原打算2011年推出《金山》英文版的企鹅出版社暂停计划,致力澄清抄袭嫌疑。2010年12月,Harman翻译及半,企鹅出版社请她暂停工作,比较张翎原著与那五本据称被抄袭著作间的相似之处,并撰写评估报告。Harman通读了这些书,并比较张翎原著,认为中国博客传播的信息是“全不相干、有毒的、很可怕的东西”。虽不否认有偶然的情节雷同,但她坚持认为,雷同之处不易捉摸,很难构成剽窃的充足理由,从而为原作者和出版社的资本、地位作了坚定维护。更有McLaren[11]对该事件的“调查”称,两者情节间确乎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然而所取用情节已被融入体现张翎自身笔调和风格的故事中,因此抄袭不成立。
Harman的评估报告被企鹅出版社认定有了完成该书翻译工作的保证,在随后的声明中指出,经详尽调查,《金山》没有对任何作品构成侵权,“抄袭”指控缺乏依据、毫无道理。张翎也得到其他拥有高额文化资本的社会资本的支持。加拿大华裔文学研究学者徐学清(张翎举办的中国语言沙龙常客)认为[15],指控文章从理论讲很荒谬,论证缺乏实据,逻辑自相矛盾,且都是匿名攻击,根本不能成立。以严歌苓为代表的50多位海外作家联名声援张翎。这些作家有的是张翎的社会资本,也说明这些作家有捍卫自己文学场域利益的需要。否则他们的著作亦会遭受断章取义的解读和指摘,对作品传播大为不利。后法院驳回控诉,《金山》英译本终在2012年3月出版。以上纠葛显示了英汉文学和翻译场域内资本斗争的激烈程度,《多伦多星报》认为是“中国文坛内斗令书的出版在加拿大受阻”。加拿大学者孔书玉也认为[16],该诉讼反映了海外华人写作圈的内讧、文人相轻和人性妒嫉,甚至近年因华人英文写作和中国作家的国际市场竞争引发的文化资源和资本的争夺。张翎则感叹那两年是她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所幸她胜出了,维护了自身场域地位和资本。
2.译作的传播
译作出版后,各个行动者,尤其是出版社、译者和原作者,利用资本和场域地位,进行积极推介、传播。
首先是出版社,利用文本形式进行推介。英译本附有原作者的序,回顾了本书写作过程、资料构成及其查找过程、向专家请教过程,体现了严谨的文风。译本还保留了中文版的原书人物关系表(族谱),加强读者对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的理解。文后有推介。企鹅出版社还安排作者到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城市巡回演讲,使读者有机会在新书发布会上和张翎见面,促进译本传播。
译者Harman也是译本传播的重要行动者。她认为[12]GoldMountainBlues沉重描述了150年来加华人在加拿大的淘金史和受难史。她结合翻译和批评,对张翎进行热情赞扬和推介:“我认为这是张翎最好的书,我花了13个月翻译它”。她认为网络是强有力的传播平台,可资利用。因此在译者建立并主导的“纸上共和国”网站,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译本(对“金山”概念的解释、故事背景和历史意义等)、作者、译者、出版社等信息,促进传播接受。译者主持的翻译和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网站——中国小说读书会(CHINA.FICTION.BOOKCLUB)也对该书进行了推介。读者也对该书进行了热心反馈,评论之余,更有近百人打分,得分接近五分制的4分。
原作者自然也热心于作品传播。写作之暇,她前往世界各地参加会议和活动,讨论和推介译作;还操办了中国语言沙龙“知识之翼”,常客有怀雅逊大学中国语言学者约翰·爱德华·斯托,以及约克大学的徐学清等,每月聚会,探讨思想和文化问题,也利于作品传播。总之,网络和当面交流保证了作品传播的即时性和对话性。
但张翎对作品传播模式和文学场内的资本形式仍然有所选择。作家安顿[17]在采访她时曾问及,假如《金山》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她会否担任编剧,张翎给予了否定回答。编剧费时过多,且妨碍写作计划。既然编剧不能在文学方面有所超越,就是重复劳动,即便能带来更多经济资本,也不为她所取。可见在文学场内,文化资本,而非经济资本才是她的追求目标,显示了一个女作家的姿态。可以说,她重文本、译本传播模式甚于电影传播模式(虽然有时也不反对),重文化资本甚于经济资本。
有意思的是,几乎与原著出版同时,2009年中加两国联合出品的同名电影《金山》(IronRoad),由Pearson和Storey担任编剧,彼得·奥图、梁家辉、孙俪主演,描写了同一段历史,但没有证据表明基于张翎原著。但相信有读者会认为如此,即便不如此认为,也会借机了解该段历史,阅读同名小说,因此客观上促进了张翎原著和Harman英译本的传播。
除了英译文本本身,翻译也可以从文本以外的社会学视角来分析。《金山》英译本翻译、出版和传播过程是资本积累、场域地位维护、竞争、争夺的过程,程度之激烈,超乎想象。
参考文献:
[1]Bourdieu, P.InOtherWords:EssaysTowardaReflexiveSociology[M]. (Trans.) Matttew Adamson, translation of Choses dites, 1987:143. 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2]王悦晨.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J].中国翻译,2011(1).
[3]Bourdieu, P. & L. J. D. Wacquant.AnInvitationtoRefiexiveSoc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111-112.
[4]Bourdieu, P.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EssaysonArtandLiterature[C]. Cambridge: PolityPress,1993:37-40.
[5]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A]. In A. H.Halsey,H. Lauder, P. Brown &A.S. Wells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6]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M]. Richard Nice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0.
[7]邵璐.翻译社会学的迷思——布迪厄场域理论释解[J].暨南学报(哲社版),2011(3).
[8]洪治纲.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J].中国社会科学,2012(11).
[9]陈福民.向无名者敞开的历史书写——关于张翎的《金山》及海外华文文学写作[J].南方文坛,2010(2):22.
[10]黎全恩.一本好书的诞生——杂忆与《金山》作者张翎的交往[N].文学报,2010-07-22(11).
[11][加拿大]McLaren,Leah.借来的东西——关于张翎“抄袭”事件的调查[J].牛抗生译.华文文学,2013(1).
[12]Aart,Greta & Harman, Nicky Translation as Self-Expression: Nicky Harman[J].Cerise Press,2012(9).
[13]刘云虹,许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J].外国语,2014(3):8.
[14]邢杰.译者“思维习惯”——描述翻译学研究视角[J].中国翻译,2007(5).
[15][加拿大]徐学清.论张翎小说[J].华文文学,2006(4).
[16][加拿大]孔书玉.金山想象与世界文学版图中的汉语族裔写作——以严歌苓的《扶桑》和张翎的《金山》为例[J].华文文学,2012(5).
[17]安顿.张翎:一生呐喊放进《金山》[N].北京青年报,2009-08-13(A15).
(责任编辑张玲玲)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Zhang Ling’s NovelGold Mountain Blues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en Qun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2)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Zhang Ling’s novel Gold Mountain Blues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cluding the author’s writing, the translator’s selec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s, the process of its translation, publishing and circulation, and the comments favorably on the relevant translation and circul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Zhang Ling; Gold Mountain Blues; English translation; circulation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6)00-0071-06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6.00.014
收稿日期:2016-03-23
基金项目:本文为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翻译社会学的当代杭籍作家小说英译传播研究(Z16JC050)”的最终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岑群霞(1973-),女,浙江慈溪人,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