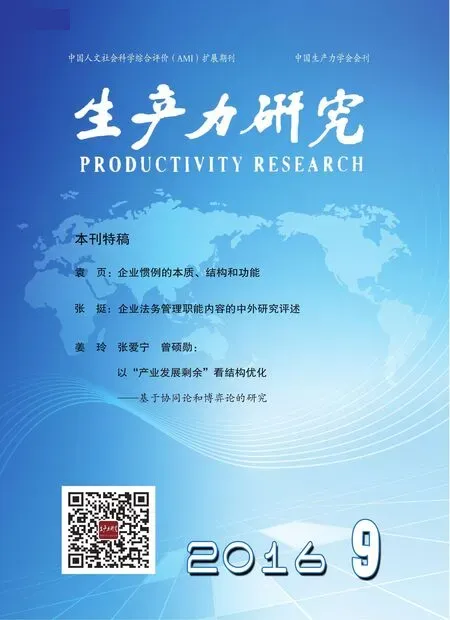传统与超越:苏南乡村治理变迁中的社会资本
2016-04-12黄晓晔
黄晓晔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传统与超越:苏南乡村治理变迁中的社会资本
黄晓晔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乡村社会资本是村民通过关系网络展示集体行动能力的表征,它是乡村治理的村庄基础。从历史脉络来看,传统苏南乡村水平网络中的关联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而言是较弱的,这使得村庄自治所需的社会资本先天不足。集体企业改制前,苏南乡村治理主要通过垂直网络中庇护或强制性的权威推动水平网络中关联甚弱的村民,以实现村庄的秩序。随着快速城市化和国家力量的退出,苏南乡村的网络结构和力量发生改变,虽然缺乏传统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存量,但也为建立现代新型社会资本留下了空间和契机。为实现社会资本的更新与增值,苏南乡村应改变由垂直网络中的力量强行干涉农村自运作体系的治理模式,引导和培育水平网络中的力量,以形成村庄治理的合力。
乡村治理;社会资本;嬗变;超越
乡村秩序的维持是村庄发展的前提,也是当下乡村治理的首要目标,乡村秩序的获得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村庄的内在结构表现为村民的在一定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关系网络,乡村社会资本是村民通过网络展示的集体行动的能力,它是村治依托的村庄基础和内生力量。从共时性来看,不同地区的乡村治理有着不同的村庄基础;从历时性来看,不同时期的村治基础也有着不同的历史痕迹。选择苏南乡村并将其置于历史的脉络中分析其社会资本的嬗变,既有助于我们观察到中国农村村治的共同缩影,也有助于我们把握特定地区和特定时代村治的特征、探索村治发展的可能路径。
一、乡村社会资本生发的网络形式
社会资本研究者认为水平网络和垂直网络都是构成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帕特南坚信水平网络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来源,社区结构越是呈现出水平状态,便越能促进制度成功[1];而另有研究者则认为垂直网络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他们提出:当地领导人和中介人能够促进贫穷社会和外部发展机构之间的联系……因而构成链接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2]。如果从社会资本的本质来看,已有很多研究论证其并无善恶之分,只要是行动者进行“投资”而建成的提高“产出”的网络或合作关系都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因此,如果垂直联系有利于参与者的合作,也可以被视作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
在当前乡村,村民之间的水平关系网络和村民与村组织的垂直关系网络构成村庄结构。村庄中的水平网络源于人们面对共同的经济、生活目标而形成的竞争或合作的关系。而村庄中垂直网络由经济或政治上的依附关系构成,其中强势者可以凭借自己手中的资源,使弱势者依附甚至屈从于自己。如解放前的地主与佃农、现在的私营企业主和工人或者掌握村庄集体资源的村组织、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
水平网络的影响力来自于历史上人们的关联强度和交往频度。当人们交往频繁、联结强,网络力量就越强,容易形成稳定的遵守共同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个体在行动时由于顾及到伦理道德、舆论、面子等因素,在社区中形成自律和他律机制。同时,密切的关系也容易产生利他行为,基于对别人的认同而将他人利益包含于自己的主观利益之中。一个村庄的社会资本是否雄厚往往和水平网络中关系联结的传统相关。如果村民在历史上就交往频繁、每个个体对这种客观联系具有自觉的主观认同,则容易形成集体认同的历史积淀,传统社会资本雄厚,有利于成为现代村治的资源。
垂直网络的影响力源自国家对于乡村社区的教化或强制塑造的传统,当时的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和象征等级制,将大批地方精英吸纳到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利用他们的网络实现对民间社会的控制[3]。但这种传统只有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才能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否则一旦强制力削弱,它的影响力便可能迅速消失。
垂直网络或水平网络中任何一方力量的强大都可能暂时性的保持村庄秩序。而这两种网络力量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会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度和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也和人们主观世界中对意识形态、价值规范的认识密切相关。在目前的乡村治理中,水平网络和垂直网络中的力量都将存在,乡村社会资本的强弱取决于村民水平网络的自组织能力以及垂直网络中村庄领袖或组织的推动能力,两者的力量对比以及能否形成合力,将影响着村庄集体行动的走向。
二、苏南乡村社会资本的历史传统
苏南乡村自古以来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由于生活尚能维持,社会相对稳定,村庄抵御外来侵扰的压力不大,村民无需组织起来对付匪患,也无需对付国家的苛捐杂税,其团结互助的需求不强。同时由于当地土地的稀缺,产生农业的“过密化”或“内卷化”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逼迫农民到土地之外寻求生路①即虽然土地单位面积的产出不断提高,但土地的人均收益反而是下降的,黄宗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过密化”或“内卷化”,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因此,在20世纪初苏南的大多数乡村,村民间基于血缘而形成水平网络的“机械性联结”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是较弱的。学者们曾公认传统乡村自我治理的核心是士绅阶层,但前提是士绅应该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这个共同体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具有以血缘为基础、以长期的地缘为补充的强亲合力和高利益关联度。苏南乡村人口密集而土地资源稀缺,投资土地的赢利可观,形成了一批以出租土地为生的地主阶层②“到本世纪上半期该地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已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出租土地占到了耕地面积的一半,而华北地区仅占18%”,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这些地主自明代起往往已迁居于城里,他们很难与当地农村的利害产生一致的联系。苏南士绅阶层的大量外流,使得乡村中精英以“保护型经纪人”的身份成立有组织的社团(议事会)发动村庄网络的动力是微弱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苏南乡村,无论是水平网络还是垂直网络中的关联都是较弱的。这种状况对后来的村治有很大的影响。
人民公社时期,强有力的党政组织对乡村进行了有效整合,集体组织几乎掌握了村庄的所有资源,导致村民对集体的全面依赖。这时每个村民与集体的垂直关系是非常牢固的,但是村民相互之间的水平关系却十分弱。村民虽然天天在一起进行劳动和其他集体活动,表面上交往较解放前密切,但是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又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疑忌,村民之间不信任感的加剧不仅削弱了原本就不强的水平关系,而对集体的过度依赖也阻碍了他们之间新的水平关系的形成。村民在经济上虽然拥有共同的公共资源,但制度安排导致他们不可能通过合作或竞争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反而强化了村民与集体之间的垂直关系。
土地承包制的改革,使得村民获得了经济自主权,国家权力从农村后撤,村集体组织萎缩。但与此同时,苏南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乡镇企业由集体掌管,实行“(准)行政经济模式”(或曰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干部经济模式)[4],村集体与村民之间有着较为紧密的组织关联和经济关联,因此垂直网络中的关联仍然相对紧密并成为维护村庄秩序的主要力量。此时的苏南农村,虽然产生了一批经济精英,但其中一部分人的生活面向却在村庄之外,而另一部分也尚未形成自觉组织起来维护群众利益的意识。至于普通村民,虽然社会流动增强、经济自主权恢复,但是彼此之间的社会关联依然不强。总体而言,村庄网络结构与人民公社时期并无大的改变,垂直网络中因乡镇企业与村庄经济保障上的联合和互益,使得集体组织的权威尚能维持村庄的秩序,成为村庄治理的主要力量,但是垂直网络中的关联程度比起人民公社时期已大为削弱。
梳理苏南乡村社会资本生发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发现,村民之间水平网络中的关联一直很弱。这使得村庄社会资本的存量先天不足,有学者就曾说过:“苏南乡村就从未有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5]而乡村垂直网络的强势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社会资本的生长。也就是说在苏南乡村,蕴藏着社会资本可能性的村庄传统基础较弱。
三、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苏南乡村社会资本与村治困境
随着苏南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民之间组成的水平网络处于断裂重组阶段。本来苏南村民之间的水平关系较之东南沿海、华北地区就弱,而经过20年的工业化,村庄日益由封闭走向开放,村民的社会流动不断增多,村民间的交往较以前大大减少了。当地村民虽然不离乡,但年轻一辈都居住在村庄之外的本地城市,村庄中的网络基本由老人、妇女和孩子构成,作为村庄行动主体的青壮劳力忙于赚钱而基本游离于村庄公共事务之外,村庄亲熟关系网络因利益先行的经济理性逻辑而被扯破,网络中关系的紧密度已大大松弛。如果说乡村社会资本关注的是村民在应对公共事件时调动村庄内部关系的能力,那么在当前的苏南乡村中,并没有构成一张强有力的关系网络,大部分的村民并不具备通过谈判、博弈在乡村公共生活中经济地获得公共物品的关系资源,从而也降低了其集体行动的能力,整个村庄的社会资本程度较低。可以说,农民的原子化状态在苏南乡村并没有得到改观,只是由于苏南乡村经济富足,在公共事务中政府给予的政策性扶助和经济支持较多,使得乡村治理在表面上仍维持相对的平稳状态。但农民始终处于分散和被动的状态,没有自觉积极参与村庄事务的意愿和行动,在苏南经济相对贫困的村庄,这种状态更加明显。
从村庄的垂直网络来看,乡村精英的流失和干群关系的紧张,网络中的信任与合作也显得匮乏。随着20世纪90年代苏南集体企业的改制,村集体的“保护型经纪”的部分功能丧失,在村庄治理中的权威和整合力弱化。当前村委会的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进行调解①事实上这种调解作用也是有限的,村民对村委的裁决往往持不信任态度,或者是因为村委的违规,或是村委的不作为,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苏南的乡村精英在集体企业改制后基本脱离与村庄的社会关联,他们利益的重心已远离村庄,主要的交往圈也不再是村庄中的关系。至于在村庄建设的公共事务中,由于村庄水平网络中人与人之间非常疏离,社会资本薄弱,垂直关系中的村委会干部或村庄精英无法获得有力的支持,导致在发动集体行动时无法将分散的农民集合成行动的力量。同时,水平网络中社会资本的缺失,也使得村民无力形成制约村干部违规行为的力量。
从目前来看,苏南的乡村治理仍主要依靠垂直网络中的力量,通过庇护或强制性的权威来驱使或推动横向网络中关联甚弱的村民,以实现村庄的秩序。由行政力量强行干涉农村这个自运作体系,并与农民形成支持和被支持关系,这几乎被当成推进乡村集体行动中的法宝。行政力量的介入重在对于物质和硬件设施的投入,它侧重于完成上级摊派的各项任务,而不是对村民自治意识的培养和引导。在垂直网络中,如果“庇护人和受护人”之间垂直关系之性质是单向度的依赖而非平等对待,那么很难产生互利规范、社会信任以及对集体事业的共同责任感[6],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抑制了乡村社会资本的增长。村民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基本处于漠视和观望状态,被动地接受政府提供的援助,并不能激发其自愿参与和服务意识,彼此没有合作的动力。而乡村精英在发起和组织集体行动中,采取依附于国家权力的原则,也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甚至有可能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
当前的苏南农村,经济的发达使得提供给农民的公共服务设施已大为改观,但并没有改变乡村内生力量日益衰落的状态。村民虽然因自身需求产生合作的需求,但这种链接形成的力量非常微弱,远远没有形成自我组织和制约的力量,乡村社会资本的存量和质量不容乐观。而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村委会、村庄精英、地方政府在激活和推动村庄社会资本中乏力,垂直网络中信任的缺失、不对等关系中可能导致的不公正现象以及与水平网络相互嵌入中谋取私利的隐患,都有可能削减或抑制乡村社会资本的增长,由此极大的增加了乡村治理的成本,形成村庄表面上稳定而实质上破败和失序的局面。
四、苏南乡村社会资本超越的可能性
目前观察到的苏南乡村似乎有着市场经济洪流裹挟中的中国农村的共同缩影:构成乡村治理和社会秩序基础的内生结构发生改变,而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进一步导致乡村的陌生化和疏离化,依托于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解体,市场伦理和市场逻辑正在替代传统的乡土伦理和乡土逻辑,乡村越来越丧失内生获得秩序的能力[7]。但是苏南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有着与中国其它乡村不同的历史脉络,因此其社会资本培育和重塑的方向也应该不同于其它乡村。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河道纵布耕地稀缺的自然环境导致村民分散而居,离开土地从事商业等非农活动的人口较多;经济的相对富庶和生活的稳定导致村民团结互助的需求不强。因此,传统的苏南乡村,村民间基于血缘而形成水平网络的“机械性联结”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是较弱的。新中国成立直至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前,由于集体组织对村庄资源的掌控,导致村民对集体的全面依赖。这时每个村民与集体的垂直关系是非常牢固的,但是村民相互之间薄弱的水平关系并没有改观。村庄结构由原子化的村民与强有力的集体组织组成,垂直网络中的关联强而水平网络中的关联弱,集体行动的动力来自集体的强制渗透所造成的村民对组织的依赖。较强的社会主义集体传统和村庄领袖的个人能力,维持了现代苏南乡村的村庄合作。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后,随着成功者的离去和集体传统的削弱,垂直网络已缺乏构成村民强有力行动的力量。村民原子化状态更加显露无疑。可以说,苏南乡村治理一直依靠垂直网络中的力量,通过庇护或强制性的权威来驱使或推动水平网络中关联甚弱的村民,以实现村庄的秩序。而村民在其中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当这种外力一旦撤除,水平网络中的村民就又会回到原子化状态,乡村就会陷入无序状态。
如果说当今华北农村的衰败来自于:因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导致村庄传统宗族关系的破坏,使得传统关系中孕育的社会资本流失,以致在乡村建设中无法发挥原有的动员力量,那么在苏南,社会资本的传统存量本身要相对弱一些。因此,华北农村解决村庄凋敝困境的路径可能是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到村庄利用亲熟关系网络再建设村庄。而这条道路在苏南乡村治理中显然不太合适。
和华北等农村相比,苏南乡村虽然缺乏传统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存量,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少受传统关系网络负面作用的束缚,为建立新型社会资本留下了空间和契机。从传统乡村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中形成的互助合作互惠的关系,到解放后的人民公社制度中国家与村民之间的庇护关系,蕴含着乡村社会资本的可能性,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真正的社会资本,涉及到两个特征:一是有一个成员愿不愿意加入,并按照规章积极参与相关活动的问题;二是关系联结的基础:基于自由原则、平等原则、效率原则之上的契约精神,和以此为原则而形成的自组织,对法治精神的认同和对法律的尊重。苏南乡村村民之间的水平联结一向较弱,这种弱一方面似乎表现为村民之间不易整合成集体行动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也契合了未来农民社会网的变化趋势,村民之间没有太强的血缘地缘关系的束缚,容易为形成新的关系留下了空间。当地工商企业的发达,所带来的平等、尊重和契约的观念也容易深入人心,使得村民之间容易形成基于自由原则、平等原则、效率原则之上的关系,这也是现代乡村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基础。
在苏南乡村治理中,虽然村民的关系网络还远远没有形成一种村庄自觉行动的合力,现代化因素的渗透也破坏了传统功能性组织延续的文化及制度性因素,但是现代性因素本身也可能在中国农村生长出新型的超出家庭的认同和行动单位来。我们在苏南一些村庄也发现①笔者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在2014年5月至8月期间,带领学生深入苏南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村民自觉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开始萌芽,有一些年轻人开始有志愿服务他人的意识和行动。原本不认识或疏离的村民在公共事务合作中提升了团体意识,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信任,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生存的前提。而有趣的是,苏南农村网络结构虽也以老幼为主,但孩子成为联结关系的纽带和润滑剂,尤其是妇女之间常常带着孩子走街串巷和出入公共场所,消息的传播就在这一网络中达成,而基于对家庭的关注、妻子的劝告建议或是对孩子的关爱,某种程度上也把有行动能力的男性间接带入到这一网络中,参与到村庄的公共事务中。由此可见苏南乡村网络具有一定的张力和辐射力。
依托于村庄的社会资本实现乡村自治是苏南乡村治理一个总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一开始完全摆脱垂直网络中的行政力量是不太可能的,关键是政府在其中应该把握好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行政力量介入的重点在于:挖掘、引导和配合水平网络中的力量,并为其提供适宜生长的空间,从而实现社会资本质量的改善和存量的增加,为村治奠定良好的村庄基础。
[1]Putman,Robert D.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p.174.
[2]Woolcock,Michael.Managing Risk,Shocks,and Opportunity in Developing Economies: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in Gustav Rains(ed.)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 New Heven,CT:Yal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1999:197-212.
[3][5]董磊明,2002.传统与嬗变——集体企业改制后的苏南农村村级治理[J].社会学研究(1):11.
[4]秦晖.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D].香港中文大学,1998.
[6]Boix,Carles and Posner,Daniel N.Making Social Capital Work:A Review of Robert Putman's 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The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University,1996:4.
[7]贺雪峰.乡土中国之三变[N].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10-21(007):1.
(责任编辑:C 校对:T)
F323
A
1004-2768(2016)09-0056-04
2016-06-01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苏南乡村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研究”(13SHB007)
黄晓晔(1971-),女,江苏南通人,博士,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