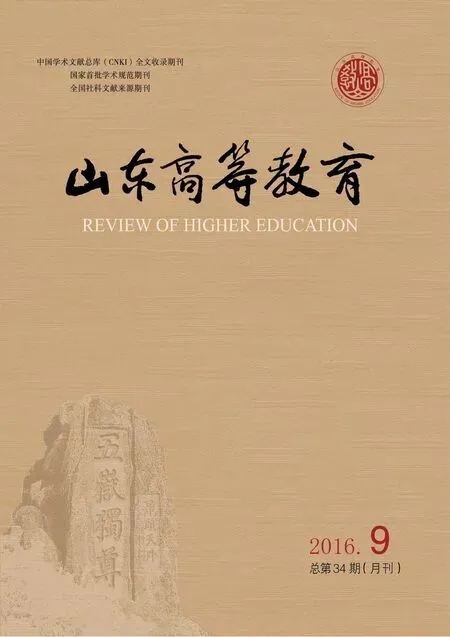近代中国大学心理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2016-04-12项建英
项建英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近代意义上的心理学科不是从古代发展而来的,而是从西方导入和引进的。但最初导入的是心理学知识和思想,逐渐在大学设置课程,进而形成学科,并创建学科体制,心理学从思想之维逐渐走向学科学术之维。迄今为止,许多学者对心理学学术思想和代表人物进行分析,以此揭示心理学科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而学术研究还有外在理路的视角,旨在阐明影响和制约社会科学发展的各种外在社会因素,它们在近现代主要表现为政府、大学、企业及各种研究机构等。[1]74-83本文拟从外在理路的视角,通过近代中国大学心理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力求揭示心理学学术的发展。
一、近代中国大学心理学知识的导入
中国传统的学术体制,主要研究经、史、子、集为主干的“四部”之学,其知识分类体系中,并没有心理学的地位。尽管“四部”之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但本质上还是没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正如有学者所说:“我国古代思想家的心理性命之说是心理学思想,不即等于心理学。”[2]1不过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接触的逐渐增多,特别是中国知识界开始由古代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心理学知识开始由西方传入和引进。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心理学知识传入近代中国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被动输入。即作为传教的附属产品而被带入中国。早在明末清初,一些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后,为利于传教,曾撰书立说,其中已蕴含着一些心理学思想。如利玛窦写的《西国记法》一书,其主要内容讲的就是记忆的功能和方法,涉及到记忆心理学的思想。不过,这一时期西方传入的心理学思想对中国文化和教育体制等影响并不很大。
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大批传教士随之入华,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心理学知识。如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翻译的《治心免病法》一书提到:“空气传声,以太传思念,同一理。不问路之远近,与五官能否知觉之事物,凡此人发一思念,则感动以太,传于别人之心,令亦有此思念。一遇同心,则彼此思念和合;如遇相反,则厌之而退。人虽不觉思念有形声,然实能感通人心。……人心思念,既可令身生病,又可令身治病,其理法颇似用电。”[3]13虽然傅兰雅翻译的《治心免病法》一书中主要讲述了除病的方法,但很多内容已开始涉及心理对于生理的重要作用;花之安(Ernst Faber)所著的《德国学校论略》一书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近代教育的专著。在该书中,花之安以较大篇幅论述了德国高等教育机构,介绍了西方高等教育机构的四大专业:经学、法学、智学和医学,其中智学专业包括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等,第一次向中国学者介绍了高等教育中应包含有心理学学科的观点;[4]谢卫楼(D. Z. Sheffield)则对心灵学作了更为细致的阐述,他认为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有三:“一、心灵诸才由何理启发习练;一、人与人之心如何相感相连;一、世人之心与上帝之心如何相感相连。”[5]1同时他亦认为“此学之奥旨,本难以言语形容。中华历代之人又未尝精心探讨。强以旧日之文词,发明此学之新意,是以每形枘凿,扞格难通。况中华生徒素习之科学,足为此学之基础者,又属寥寥也”。[6]57这其实是谢卫楼对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知识所作的简单介绍。为使心理术语更快被国人理解,丁韪良(W.A.P.Martin)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创作了《性学举隅》一书,书中涵盖了近代西方心理学的“知”、“情”、“意”三分法的知识体系,并介绍了生理心理学、催眠术与颅相学等相关内容。该书由李鸿章作序,其“序言”和“总论”在当时权威的《万国公报》(1900年)上刊印。但这些传教士传播心理学知识主要是为宗教服务的,正如狄考文(C.W.Mateer)在《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一文中所说的:“学校里的宗教影响是最重要的事情。有了它,就有希望取得伟大成果;没有它,学校至少是废物。”[7]24所以,有学者认为“心理学在我国最初的传播与外国传教士及其所设立的教会学校分不开。”[8]98
第二种是主动引入。国内一批有识之士也开始主动引进并介绍西方心理学知识。1897年大学士孙家鼐编印的《续西学大成》列出了18种西学书目,其中在文学类中列有《心智学校》、《西学渊源记》、《新学刍言》等心理学、教育学书籍;1898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含15门类,在理学门中有心理学,包括25种心理学书籍。[9]655-657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中的分类,打破了传统“四部”之学的分类体系,在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为近代心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此后,心理学知识和内容被广泛引入。如王国维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要》(英国西额惟克著)、《伦理学》(牧濑五一郎著)、《心理学》(元良勇次郎著)等,很多内容都属于科学心理学的研究范畴。通过有识之士的引介,心理学从知识门类的导入到知识体系的建构,国人通过日本迅速了解和吸收西方心理学知识,心理学也开始被大家所认可,这为近代大学心理学课程设置进行了铺垫。
二、近代中国大学心理学科课程的设置
随着心理学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和扩大,心理学开始在人们心中悄悄地发芽。大学作为近代学术的重镇,开始设置心理学课程,承担心理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任。
最早设置心理学课程的是教会学校。1841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开设的玛礼逊学校,就已设置心理学课程。1876年,山东文会馆正斋第六年规定开设:“心灵学,是非学,富国策,易经全,系辞,读文,微积学,化学辨质,天文揭要。”[10]222有学者经研究发现,文会馆首任校长狄考文要求学生学习一些西学中的社会科学,“包括世界历史和地理,以及最后一年要学的心理学、逻辑学和政治经济等,这后三门课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课程。”[11]248187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书院成立之初便开设了心理学课程。此后,圣约翰大学一直重视心理学课程的设置,如西斋正馆普通科规定第三年开设心理学课程,1911年更是规定文艺科和医学科也开设实验心理学课程。与此同时,其他教会大学也纷纷设置心理学课程,而且“在当时心理学一般被视为必修课和神学的预科,为其宗教服务的,是很受重视的一门课程。”[12]104教会大学心理学课程的设置,为清末中国其他大学设置心理学课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清末新教育改革的展开,大批新式学校需要大量的师资,而长期以来中国教师远未达到专业化、科学化的境地。为使教师自身先受专业教育,故师范教育又成为当务之急。作为培养师资机构的师范学校,急需开设“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对教师进行专门训练,以提高教师的专业化程度。因此,新教育改革把“心理学”课程设置提到了议事日程。加之,当时留日学生的大量归国,他们看到了日本对心理学课程的重视,“日本新学界现最重心理学,为教育之基础,故高等师范四学部中课程表,第一年皆无教育一门,然未有无心理学者,盖心理伦理诸科为教育之预科也”。[13]717可以说,多种原因促推国人自办大学纷纷设置心理学课程。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设置心理学、北洋师范学堂设置心理学、山东优级师范学堂设有心理学、奉天师范学堂设有心理学等等。由于心理学是一门新兴课程,当时主要师资主要以日本教习为主,课程设置也比较随意。如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办之初,京师大学堂聘请了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任总正教习,并承担心理学、教育学和伦理学课程。据有关文献记载,服部宇之吉讲授心理学时曾引起一场风波,最后导致心理学课程被取消。有一次,服部宇之吉讲授记忆时张之洞来听课,当时服部正在讲中年时由于繁忙,容易将少年时的事情遗忘,到了老年则容易将中年时的事情遗忘,而容易记起少年时期的事情。张之洞以为是对他的嘲笑,因服部是外国人,不好发作,但到讨论学堂章程时便将心理学课删除了。[14]3这说明最初心理学课程在大学的设置人为因素很大。但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定,心理学课程在大学的设置开始趋于制度化。《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对优级师范学堂的课程分为公共科、分类科和加习科。在四类分类科中,“人伦道德、经学大义、教育、心理、体操,则一概通习无异致”。[15]684章程明确规定心理学是必修课目,还就心理学课程的学习顺序和学习时间进行了详细说明,这4类学科中第一年设置“普通心理学”,第二年开设“应用心理学”,学习时间除第一类为每星期2个钟点外,其余三类为每星期1个钟点。此外,加习科中还设有“实验心理学”。此外,《学制》还规定大学堂设“心理学”为随意科目,高等学堂只有入经学、理学科者,第二年才学“心理学”,第三年就可以不学习“心理学”。整体来说,清末《癸卯学制》保证了心理学课程在大学的合法地位。但这一时期心理学课程设置不多,而且主要设置在师范学校。
民初,《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其中《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英语、体操”是本科各部通习之科目。在规定高等师范学校必须设置“心理学”课程的同时,《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亦规定哲学门下的中国哲学类和西洋哲学类,亦必须设置“心理学”。[16]698-714从此,国立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置心理学课程的越来越多,如北京大学曾在哲学门下设置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课程。
综而言之,《学制》的颁定使得心理学课程在大学的地位逐渐稳固。《学制》对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时数、教学内容、课程宗旨等明确规定,使心理学课程在大学逐渐走向系统化规制,对大学心理学学术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这一时期心理学课程只是附属于大学哲学系、教育系或师范学院教育理论课程中,并没有形成学科。
三、近代中国大学心理学科体系形成
随着心理学课程的增设,心理学逐渐摆脱哲学和教育学的樊篱,独立的大学心理学系科开始建立。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1921年燕京大学创设了心理学系;1924年大夏大学成立了哲学心理学系。随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光华大学、辅仁大学等均创设了心理学系或教育心理系。随着各大学心理学系科建置的增多,心理学课程结构渐趋合理,专业师资队伍开始形成,心理实验室初具规模,心理学会、报刊杂志相继创办,心理学科在大学的地位逐渐稳固,学科体系遂渐形成。
(一)课程结构渐趋合理
随着心理学系的建立,不仅心理学科课程设置逐渐丰富,而且课程已形成了结构体系。
当时各学校心理学课程设置发展非常迅速。如北京大学1920年仅在哲学系开设了1至2门课程,1922年共开设心理学课程8门,1926年心理学系成立后制定了课程指导书,规定课程分为主科、辅科两种,主科又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其中必修课程为15门,分别是科学概论、西洋哲学史、伦理学、生物学、生理学讲授、实习、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各派心理学、高级实验心理、晚近心理学问题。这时,北京大学心理学科课程结构已十分明显,主要注重生物、生理和实验等,希望心理学科能纳入自然科学的轨道;东南大学是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展而来,1920年,东南大学心理学系有6门课程,到1922-1923学年,课程则达到23门,它们分别是心理学入门、试验心理学、心理学之生理基础、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青年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研究、动物心理学研究、宗教心理学、中国宗教心理学、中国人之美术观念、系统心理学、心理学略史、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心理学研究、教育心理学、心理测验与教育测验、智力测验、变态儿童之研究、应用心理学入门、商业心理学。这23门课程中有儿童心理学、青年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研究、教育心理学、心理测验与教育测验、智力测验、变态儿童之研究等,很多都与教育直接有关。后东南大学改称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先后制定了《心理学系课程标准》、《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选课指导》等课程方针,心理学科课程设置形成了理论与实践并重、师范特色鲜明的课程结构。可以说,随着各大学校课程制度的颁订,各大学心理学科课程设置不仅丰富,而且结构合理,课程特色也日益凸显。
(二)专业的心理学师资队伍形成
最早心理学科教师并不一定受过专业心理学训练,可能是学哲学或教育学的,心理学教师也往往由教育学教师兼任。随着心理系科的形成,各大学心理学科开始汇聚了一批高素质的专业心理学者,稳定的教师队伍开始形成。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大学教员资格审查条例》、《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等法令、条例的颁布,心理学科已形成了“一个以具有正当资格的研究者为中心的研究社群”。[17]29他们中很多毕业于当时世界心理学,如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师有陈大齐、唐钺、樊际昌、汪敬熙、陈雪屏、潘渊、刘廷芳、陆志韦、孙国华、周先庚、叶麟等;暨南大学心理学科教师先后有谢循初、章益、杜佐周、董任坚、孙贵定、高君珊、廖世承、曾作忠、鲁继曾、韦悫、章颐年、郭一岑、沈有乾、深履等。[18]224这些教师对心理学科充满着强烈的挚爱之情,就如张耀翔所说的:“心理学好比我的宗教。我既信崇这一教,就不乐意宣传别的教了。”[19]231因此,他们上课认真,在上课之前,他们都要作充分的准备,张耀翔曾说:“我每晚要点蜡烛预备功课,还要编四种讲义。学校按时发给的几支烛往往不够用,只好自己添购一些。情形仿佛学生时代的‘开夜车’。所不同的只是每晚都要‘开’,不限于考试的前夜。”[20]232-233这些心理学教师学识融贯中西,态度又十分认真。因此,在课堂上,他们都深受学生的喜爱。如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潘凤韶同学说:“我之所以听了黄师(黄师指黄翼——笔者注)的儿心(儿心指儿童心理学——笔者注)、教心(教心指教育心理学——笔者注)和变态心理等课后,又选修生理学,生理心理学,兼攻梦的研究、幻想的研究、顿悟的研究,甚至旁及‘阿特勒’学说、心理治疗和催眠等学科,盖都因在黄师启迪有方,引我入室的。”[21]19许多心理学科教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独领风骚,如潘菽的理论心理学、汪敬熙的生理心理学和动物心理学、陈鹤琴的儿童心理学、艾伟的教育心理学、陈立的工业心理学;等等。各大学心理学教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采用共同的研究方法,并出版一批高质量的专著和编著,专业的心理学者队伍已初步形成。
(三)实验室为大学心理学科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周先庚认为“中国在最近的将来,心理学不欲求发展则已,苟欲求发展,创办心理实验室实在是第一要务”;[22]1019郭任远也特别重视实验室的重要性,他强调“离开了实验室就无所谓心理学。”[23]636因此,各大学特别注意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1917 年陈大齐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心理实验室;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时成立了心理实验室等。各大学为发展心理学科,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建设心理实验室。北京大学成立之初,虽然资金匮乏,办学条件恶劣,但蔡元培和陈大齐分别了考察美国和德国的实验室。陈大齐到德国后,想方设法为北京大学心理实验室购置实验仪器,他曾在给校长蔡元培的信中分析:“北大心理实验室里,虽有几件实验用的仪器,但为数太少,而且制造不精,实在不敷实验之用。现在学校不知经费如何?倘能照政府所定办法,按月发给,或可提出一笔款子来,作为购买心理仪器之用。现在研究心理学,无论是论理方面还是实用方面,都不能不借助于实验。”[24]19经过蔡元培和陈大齐等人的努力,实验室图书仪器已“略具规模”。[25]22之后,虽然举步唯艰,但心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蔡元培等人还是苦心经营,经常与海外学子讨论图书仪器之事,如心理学家郭任远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提到:“我近来很热心中国建设心理学实验室;常常和美国各心理学家,和造心理学仪器的公司磋商办法。北大若真要创办,我在这里一定能从旁援助”;[26]23清华大学心理学科经费相对充裕,每年用在图书仪器的经费约一万余元,而且设置精良,大都从德国和美国选购。到1934年秋,“实验室置备的仪器设备约值四万元,足供基本心理实验和专题研究之用。”[27]215清华大学心理学科不仅实验仪器设备精良,而且实验室面积宽敞,“有普通实验室三间、动物实验室一间,此外,尚有动物饲养室、工作室、隔音室、暗室等。动物饲养的暖气管,自成一系统,以便保持适当的温度。”[28]214-215周先庚就曾评价道“现在清华心理实验室,以面积算,我敢说不单在中国要算第一,即在欧美,他们那些随随便便的心理实验室,也很少有这样宽敞完备的房间”;[29]1012复旦大学心理学科经郭任远的募筹,建成了一幢欧式风韵的四层楼“子彬院”,内设人类实验室、动物实验室、生物实验室、图书室、讲厅、影戏厅、照相室、教室等,并且都装有暖气设备。各大学心理实验室已初具规模,为大学心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四)心理学会、报刊杂志等学术平台的搭建
心理学会、报刊杂志等是构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大学心理学科学术体系形成的重要媒介。1921年,中国成立了最早的中华心理学会,该会“以研究各种心理问题为宗旨。”[30]4681931年成立了中国测验学会,1936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同年中国心理学会成立。随着心理学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各大学教师纷纷参与到学术组织中来。与此同时,为使研究者能共同分享学术研究成果,各大学又相继创办杂志。如清华大学教育心理学系创办半年刊《教育与心理》、辅仁大学教育科学研究会创办《教育与心理》、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创办《心理半年刊》、《心理附刊》、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实验所创办《心理教育实验专篇》、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创办《心理季刊》、燕京大学中国心理学报社创办《中国心理学报》(季刊);等等。心理学会的成立和心理杂志的创办,心理学者有了发表话语的平台,学术研究机构和期刊已成为学术交流的公共论坛,许多学术问题得到厘清和发展。
总之,近代中国大学心理学科的发展走过了从无到有、从青涩到成熟的历程,近代中国大学心理学科的学术体制逐渐完善,学术研究不断发展,近代中国大学心理学科发展史就是一部心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正如学者汪敬熙所言:“在心理学本身说来,中国的心理学实已由翻译外国的时代走入了国人自己研究的时代了”,而且“在这些研究之中,确有些能站得住,并且能引起外国同行的赞许的”。[31]13-16诚然,在大学心理学科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各大学课程设置杂乱、教材内容西方化、心理学著作以翻译和编著为主、缺乏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实验等。不过整体来说,近代中国大学心理学科的建立和学科体制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学学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Kuhn T.S. The History of Science[A].Sills DL.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14)[Z].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2]高觉敷.中国心理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3]乌特亨利.治心免病法(上卷)[M].傅兰雅译.上海:格致书室,1896.
[4]肖朗.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初探[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2).
[5][6]谢卫楼.心灵学[M].通州:华北协和书院, 1911.
[7]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8]杨鑫辉. 心理学通史(第二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9]康有为. 康有为全集(第3集)[M].姜义华编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1]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12]杨鑫辉.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13]璩鑫圭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14]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A].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
[1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6]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7]Roger L Geiger. To Advance Knowledge: The Growth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1900-1940)[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8][19][20]张耀翔.心理学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1]黄文宗.儿童训导论丛:黄翼羽仪先生纪念文集[C].香港:羽仪书屋,1984.
[22][29]周先庚.清华之心理实验室[J].清华周刊,1931,(11-12).
[23]汪凤炎.中国心理学思想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24][25][26]《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简史》编写组.北京大学心理学简史(1917-1998)(征求意见稿)[Z].1998.
[27][28]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0]燕国材.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31]汪敬熙.中国心理学的将来[J].独立评论,193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