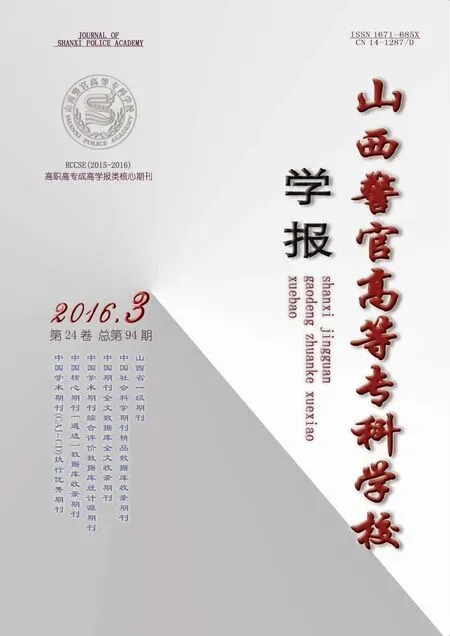经营者集中法律规避初探
2016-04-11纪文哲葛晨亮
□纪文哲,葛晨亮
(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法学研究】
经营者集中法律规避初探
□纪文哲,葛晨亮
(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经营者往往会通过设计严密的合并方案,以规避反垄断调查。对于这种名义上符合反垄断法要求,实质上却可能危害自由竞争的行为,应区分不同情况,根据是否实际对市场竞争秩序构成破坏或者威胁,以及结合情节严重程度,分别予以处理,并保持公权力的法律规制与私权利的市场创新之间的平衡。
自由竞争;法律规避;经营者集中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竞争是一种最理想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与竞争既对立又统一的‘孪生兄弟’则是垄断。垄断表现为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对有利的生产经营条件的独占活动或者寡头性控制,垄断的结果则是阻碍和破坏公平有序的竞争,加剧各个生产经营者之间和商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1]因此,以竞争秩序和竞争效率作为价值目标的反垄断法便应运而生。[2]作为传统上反垄断法三大支柱之一的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经营者合并;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
一、经营者集中法律规避现状
所谓规避,是指“设法避开,躲避”,法律规避则是“当事人为避开或者排除特定法律规范适用而采取各种策略行为”。[3]具体到规避经营者集中法律制度的行为,是指经营者实施的为了避开或者排除反垄断法对其适用,而利用一定的连接因素,通过精心的交易方案设计,在名义上符合反垄断法要求而实质上却有可能危害自由竞争的行为。根据当前司法实践,该规避行为现状主要表现如下:
(一)利用反垄断法颁布后和生效前的执法空窗期实施规避行为
从2007年8月30日至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通过到正式实施有将近一年的执法空窗期,经营者即使实施反垄断法明文禁止的行为,也不能依据该法进行处理,这就给规避行为提供了条件。例如2008年春节前夕,国美“接管”大中,采取第三方“托管”模式,虽然设计精妙,但仍然没有逃脱《反垄断法》第20条*《反垄断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规制范围,依然属于禁止实施的“经营者集中”行为。[4]但由于《反垄断法》尚未实施,导致对这种严重影响市场竞争的行为无法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理。
(二)利用反垄断法生效后法条空白地带实施规避行为
反垄断法生效之后,由于仅对三种形式的经营者集中行为予以规制,故市场经济活动中经营者可以通过合并方案设计,有效规避反垄断调查。例如力拓与必和必拓合资案中,合并后的公司中两家占有等额股份,地位相当,不存在相互控制的风险。此外,铁矿石的销售数量也会在各自营销与运输过程中保持均等,为彼此留足独立空间,表面看来在未来市场中双方的竞争依然存在,从而逃脱反垄断调查。[5]再比如为避开反垄断审查,“58同城”与“赶集网”合并交易分两次进行,同时58同城在赶集网中的持股率只有43.2%,避免了由于控股部分遭致的反垄断调查,从日后发展的角度来看,58同城作为赶集网的第一大股东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用以增持股份。[6]
(三)利用反垄断法生效后法条的严格构成条件实施规避行为
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规制设置限制性条件,如果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理解适用,会使一些具有垄断性质、对市场自由竞争构成破坏或威胁的行为逃脱法网。例如判断是否达到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是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20亿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需要对“营业额”作准确理解。在滴滴快的合并案[7]中,如果将营业额简单理解为销售额,两公司合并后的营业额并未达到《反垄断法》规定的相关标准,因此也就不具备申报经营者集中的条件。但如果将双方为抢占市场而对乘客和司机提供的现金补贴也算入营业额,甚至连司机账户流水也计入,两者营业额将远超过反垄断要求的申报标准。
二、经营者集中规避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法条本身存在模糊性及审查标准不明确
《反垄断法》条文以文字为载体,但文字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现实经济秩序运行的复杂多样,并非能够全部被法条涵涉。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于社会不断演变发展的特性,现实生活中始终有一些严格和明确的语言所无能为力的细微差异与不规则情形。[8]同时,经营者集中实质审查标准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根据《反垄断法》第28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进行反垄断调查过程中,判断是否具有经营者集中的情形,需要考虑的因素大多是基于竞争政策,如审查所谓的市场集中度。但同时是否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影响这一产业政策因素似乎也纳入考量范围,这些因素导致出现审核标准的政策导向不明确。[9]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不仅给执法带来困扰,也会致使法律规避行为的出现。
(二)社会经济、政治、伦理观念的发展导致反垄断法立法及执法的滞后性
立法是基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经验的总结,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会使得法律的规定总是滞后。[10]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不断深入改革的关键阶段,反垄断立法处于起步阶段,与之相关的监管实践仍然存在经验不足等问题,故导致《反垄断法》没有及时针对经济运行中新出现的情况予以调整。同时,市场经济注重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领域中,市场主体可以自由地通过创新行为配置生产关系要素,以促进经济发展。如何科学区分经济创新行为和阻碍市场自由竞争行为,成为经营者机制法律规避制度构建的关键一环。此外,反垄断法所具有的宽领域、多角度的性质,导致无法对各类特殊行业进行规制以便做到面面俱到,再加上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以及监管手段的不足致使执法过程中无法对形态各异的经营者集中行为予以识别判断。诸此种种都为经营者集中的监管设置了重重阻碍,也为规避行为的存在提供生存的土壤。
(三)经营者非法集中的责任体系构建不足
当前,经营者实施非法集中影响市场自由竞争的行为责任承担方式仅为行政处罚,缺少刑事责任为后盾,并且仅有的行政处罚设定标准过低,导致违法成本不高,威慑力不足。根据《反垄断法》第48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这种惩罚力度基本都在涉事企业承受范围,并不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相对于动辄数亿资金的经营者集中行为,根本无法发挥制度设计初衷。同时,刑事规制的欠缺,也影响了监管效果。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垄断行为也日益增多,其对经济秩序健康有序发展的破坏也越来越大,而以惩罚手段最严厉性为显著特征的刑法不应缺位。但我国反垄断领域刑事介入存在严重不足,只有《反垄断法》52条和54条涉及,实际上规定的是妨害公务罪、渎职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没有涉及到垄断行为本身。《刑法》在扰乱市场秩序罪中226条和223条分别规定了强制交易罪和串通投标罪,但是由于该类犯罪存在隐蔽性强,发现难度大等特点,除非在案件中包含有暴力因素,[11]一般很难追究刑事责任。而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在应对垄断行为时,非常强调起诉个人并寻求监禁判决,其目的在于对违法者和潜在的违法者警告:他们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12]当然,我国刑法对反垄断领域的缺位,主要源于对垄断行为造成的危害认识存在问题,随着反垄断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入,将会得到改观。
三、经营者集中法律规避行为的性质界定
经营者集中法律规避行为的顺利实施一般是建立在法律漏洞的基础之上,厘清规避行为的性质,首先需要对法律漏洞属性进行客观评价。所谓法律漏洞,有观点认为是立法者在草拟一项法律之时,往往可能碍于社会的快速发展,或者疏于预见或者因疏忽而没有预见一些主客观的情况,致使出现一种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的事实出现,而无法得到法律的规范以及用以制裁犯罪,此时,如果这项事实不利于社会发展、秩序稳定,我们可以认为出现了所谓的法律漏洞。[10]也有学者认为,法律漏洞是指立法者无意沉默的情况,而立法者有意沉默即已经认识到法律规定可能与客观发展的事实存在对立,但“有计划性”的放任不属于法律漏洞范畴。[13]上述观点的分歧在于是否将立法者有意为之产生的法律规制不足纳入法律漏洞的概念范畴。笔者认为法律漏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静态现象,本身不掺杂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也不会对法律保护利益造成侵害或者威胁。而法律规避则是行为人对法律漏洞进行有目的的利用,进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的行为,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将静态的法律漏洞予以动态展现的活动,两者不属于一个层面的概念。
关于法律规避行为的性质以及是否需要对规避结果予以否定,学界分为两种观点:否定论者认为,规避法律即“钻法律空子”,放任将有损法律制度权威性和统一性,影响法治建设。而肯定论者认为,规避行为本身表明规避者意识到国家制定法的存在,其在国家制定法不合理情况下不可避免或有必要实施的规避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家法律的规则,故应肯定其正当性。[14]笔者认为,否定论者的观点过于严苛,忽视法律规避行为的积极作用,毕竟该行为虽然是“一种游离于法律之外的行为,它可以是罪恶的,深深的违背着道德并且侵蚀着法律的尊严,但它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法律的改革以及立法的进步。”[15]是否对法律规避行为产生的结果予以否定,应当以该规避行为的实施是否对法律保护利益构成侵犯为基础,而不是一概作违法行为处理。肯定论者的观点肯定规避行为存在的有益一面,却没有对规避行为造成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法律条款设定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客观事实予以分析。针对本文论及的在经营者集中制度领域内的规避行为,要客观地看到该行为具有的积极意义。规避者与立法者并非永远处于绝对对立层面,尤其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阶段,经营者集中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减少恶性竞争,扩大国际竞争力。故新的经济行为出现并非意味着对法律保护利益的侵犯。正如有学者借助交易成本理论论证,立法机关需要从交易成本、社会成本以及法律监督成本等层面综合衡量法律对策,如果新交易模式具有‘帕雷托效率改进’功能,那么立法机关的最优选择是予以认可,进而修改法律以回应市场实践的需求。[16]当然,规避行为危害性一面也不容忽视,经营者绕开监管举措,非法实施的集中行为对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产生破坏或者威胁,也需要及时予以否定,并根据其本质行为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以使其不致损害第三人或社会公共利益,促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四、应对经营者集中法律规避行为的路径选择
立法者设定经营者集中监管制度根本目的,是为保护市场自由充分的竞争秩序,对该领域法律规避行为应对的路径选择也应当以此为标尺,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打击边界。
(一)及时对立法作出调整以有效应对规避行为
规避行为的存在,很大程度是立法不完善的结果,因此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调整。
1.修改反垄断立法。首先应加大行政处罚力度。有学者认为罚款的力度应当以违法者的违法行为所获得的收益为基准,实行高额罚款制度。但现实中,由于大多数经营者缺乏支付能力,而不具有可行性。此外,高额罚款也会使得社会成本增加,违背了比例正义的原则。[17]笔者认为,当前反垄断法行政处罚简单以具体数额为标准过于刚性,毕竟经营者集中的情形复杂多样,不同地域、不同行业适用统一数额标准而带来的处罚威慑力也不相同。从长远来看,还需要构建具体数额为基准,辅以违法数额的百分比例的综合行政处罚体系,这样方可实现处罚的公平性与多样性,实现经营者集中管控制度设计宗旨。其次,增加法律禁止的经营者集中行为模式,当前规避行为能够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利用法条仅列举的三种情形,将新的行为模式纳入或者采取兜底条款予以规制是妥当的。最后,增加刑事制裁条款,当然作为附属刑法的反垄断法并没有独立设置刑事制裁条款的权限,故需要与刑法修改予以配合。
2.修改刑法规定。当前刑法在应对经营者集中法律规避行为方面存在缺位,可以通过出台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增加刑罚的供应量,扩大犯罪圈。针对包含经营者非法集中在内的垄断行为是否应该予以刑法规制,理论界有以下几种观点,肯定论者认为“非法垄断行为直接侵害自由、公平的有效竞争秩序,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由根基,进而损害国家利益、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应刑罚性’,故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责任制度。”[18]但否定论者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出发,根据反垄断法中的慎刑原则,认为应对垄断行为作非刑化处理。[19]还有学者认为监禁这种威慑方式完全可以通过对违法企业的高额罚款来达到。[20]折中论者认为“反垄断法应强化刑事立法,但应有其限度,其措施、手段的运用应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已达到最佳的威慑效果,否则形成过度威慑”。[21]笔者认为,应对该类行为,不应完全放弃刑罚这一具有显著威慑力的利剑,也不应不加以区别的全面适用,应根据刑法保护法益将严重危害市场自由竞争行为入罪处理。刑罚的威慑力应与其带来的社会效益相互协调,争取以最少的成本来实现刑罚的威慑作用,提高司法效率。如若刑罚的威慑力超过了必要的限度,社会将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平衡犯罪所造成的破坏。故此,刑罚的适用应当与行政处罚和民事制裁进行衔接,将没有达到入罪数额标准的垄断行为不作为犯罪。
具体而言,第一,可以增加新的罪名,将核心垄断行为入罪处理。第二,在对经营者非法集中行为入罪的基础上,考虑其在经济领域的特殊性,可以在刑罚配置方面设置罚金刑。当然,这里的罚金和行政处罚中的罚款并非仅仅是数额上的区别,通过刑事制裁手段的适用,表现对该行为最强烈的否定,可以更好地发挥刑法的指引作用。当然,由于经济领域犯罪一般采取空白罪状表现形式,需要与反垄断法作好协调工作。同时,对经营者非法集中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应该予以科学衔接。
(二)科学采用法律解释方法以消减法律模糊地带
反垄断法的准确适用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解释,当前监管部门在应对经营者规避反垄断法进行非法集中行为时出现的认定标准混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并非法律缺失,而是没有采用合理的解释方法。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出台经营者非法集中的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消减法律的空白与模糊地带。实务中也可以综合采取法律解释方法,释明法律条文具体含义,以提高执法的准确性。例如在判断企业发生兼并后一个企业所占另一个企业的股份是否构成经营者非法集中时,有必要提出一个量化标准,以提高法律的透明度,使企业能够对其法律行为的后果有可预见性。而这也在西方国家反垄断实践中得以体现,如欧共体委员会认定取得39%有表决权的股份足以控制被取得企业。[22]对某些规避反垄断法进行经营者集中的行为,可以采取扩大解释,或者看其行为是否实质破坏或威胁市场竞争秩序,从而选择适当的应对方案。当然,对法条的解释不能超出其投射边界,更不能违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对反垄断法生效前的规避行为进行规制。
[1]贾林青.中国保险市场垄断行为的认定和预防——从我国保险行业首例垄断案件谈起[J].保险研究,2013(4):89-94.
[2]刘继峰.反垄断法益分析方法的建构及其运用[J].中国法学,2013(6):20-33.
[3]王 军.法律规避行为及其裁判方法[J].中外法学,2015(3):628-648.
[4]黄春华.行业并购加快步伐意在规避《反垄断法》?[N].检察日报,2008-02-16(1).
[5]周馨怡.“两拓‘香蕉球’依靠设计精巧的交易方案,两拓处心积虑地试图规避反垄断法”[N].21世纪经济报道,2009-06-19.
[6]小 峰.“考虑反垄断审查58赶集合并交易或分两次进行”[N/OL].[2015-04-17].http://news.mydrivers.com/1/416/416139.htm.
[7]李淑平.快的滴滴市场占比高达99.8%“反垄断法没有限定市场份额”[N].东方早报,2015-02-15.[8]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86.
[9]王晓晔.《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经营者集中的评析[J].法学杂志,2008(1):2-7.
[10]任彦君.论我国刑法漏洞之填补[J].法商研究,2015(4):101-110.
[11]郑鹏程.美国反垄断刑事政策及其对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启示[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5):95-100.
[12]Baker,D.I.The use of criminal law remedies to deter and punish cartels and bid-rigging[J].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2001(5-6):693-714.
[13]刘艳红.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类型及其适用[J].法商研究,2002(3):52-61.
[14]苏 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59-73.
[15]E.W B.Evasions of the Law[J].Law Magazine and Law Review,1857(4):247-258.
[16]董淳锷.公司法改革的路径检讨和展望:制度变迁的视角[J].中外法学,2011(4):820-836.
[17]Claus-Dieter,E.Isabela.A,Effective Private Enforcement of EC Anti trust Law[M].Hart Publishing,2003,392-393.王 健.威慑理念下的反垄断法刑事制裁制度——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改稿)》的相关规定[J].法商研究,2006(1):3-11.
[18]邵建东.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制裁制度[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4):13-19.
[19]李国海.论反垄断法中的慎刑原则——兼论我国反垄断立法的非刑事化[J].法商研究,2006(1):12-16.
[20]李国海.反垄断法制裁手段研究[M]//漆多俊.经济法论从,第10卷.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198-199.
[21]王 健.威慑理念下的反垄断法刑事制裁制度——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改稿)》的相关规定[J].法商研究,2006(1):3-11.
[22]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07.
(责任编辑:王战军)
Exploration on Evasion of Law of Managers in Concentration
JI Wen-zhe, GE Chen-liang
(Schooloflaw,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1106,China)
Due to the nature of going after profits and avoiding disadvantages, managers often evade antimonopoly investigation by designing rigorous merge scenarios. The behaviors that meet the demands of antimonopoly law nominally and harm free competition actually should be deal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ituation, whether they did real harm or threat to market competition order or not and the severity degree of plot and keep the balance between legal regulation of public right and market innovation of private right.
free competition; evasion of law; managers in concentration
2016-03-28
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KYLX_0006)。
纪文哲(1991-),女,山西大同人,南京大学2014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刑法;葛晨亮(1988-),男,安徽阜阳人,南京大学2013级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刑法。
D922.294
A
1671-685X(2016)03-0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