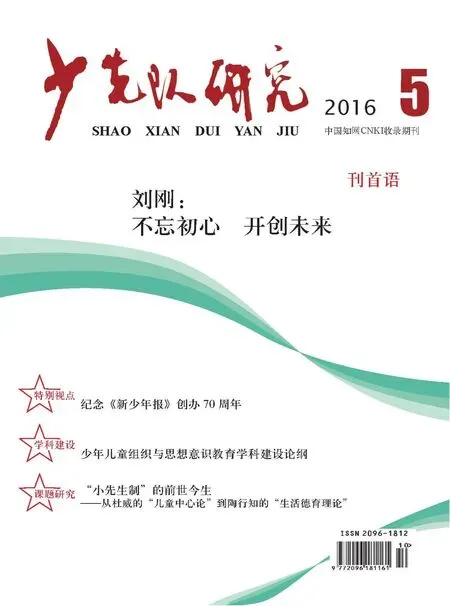“小先生制”的前世今生——从杜威的“儿童中心论”到陶行知的“生活德育理论”
2016-04-10上海市宝山区美罗家园第一小学范英俊
□ 上海市宝山区美罗家园第一小学 范英俊
课题研究
“小先生制”的前世今生——从杜威的“儿童中心论”到陶行知的“生活德育理论”
□ 上海市宝山区美罗家园第一小学 范英俊
杜威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他的名字似乎一直以来与“儿童中心论”捆绑式地带到了教育者的视野中。而作为他的学生——陶行知,从杜威的教育理论开始深入学习,再到翻转老师的儿童论。这个过程既有其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新的变革与突破。
通过学习杜威“儿童中心论”,进一步研究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教育理论,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着眼于“小先生制”的探究。本文将从杜威的“儿童中心论”谈起,分析陶行知“生活德育理论”,进而为作者后续进行“小先生制”的实践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一、杜威的“儿童中心论”
杜威(1859—1952)是著名的美国教育家、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呼吁民主教育,将教育经验与教育实践相结合,至此,教育不再只是依托于教育理论,而是富有实践的教育活动。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教育从何而来?教育就应当是来源于生活体验、成长经历和经验感悟。脱离生活和经验的教育,也就无法称之为“教育”,“生长”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杜威所提出的教育哲学是“属于经验的、操诸经验的和为着经验的”。也是基于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的理论,杜威首先重视的就是“儿童”,即我们都熟知的“儿童中心论”。“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种革命,是哥白尼在天文学中从地球中心转移到太阳中心一类的革命。在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一切措施要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这是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对“儿童中心论”的阐述,“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社会是教育的归宿点,正像两点之间形成一条直线一般,在教育出发点的儿童和教育归宿点的社会之间,形成了教育历程”。
试想一下,以“教师中心论”“教材中心论”为出发点,儿童在学校被安排的学习内容就无法吸引他们,会觉得学校教育枯燥乏味,甚至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而杜威提出的“儿童中心论”则以参加现实社会为载体,儿童在活动中习得知识,兴趣被激发,进而更好地运用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这样的课堂是儿童的乐园,学校不再是“书斋或学府”,而是“快乐的生活园地” 。目光回到现代教育社会,在课改的提出之下,我们已经逐渐有了“学生主体”思想的认识,备课也不仅仅是“备课标”“备教材”,更要“备学生”。这种“儿童中心”的教育理念,源起杜威“儿童中心论”,让儿童成为教育的主体,鼓励儿童全面参与课堂教学,而不再只是教师的盲目随从者、教育的无知旁观者。教育发挥儿童的主动性,教育才能起作用,影响才会扩大。
二、杜威的“教学论”
杜威提出的“从做中学”是他的教学论观点,这来源于他的哲学认识论。真理的检验,需要实践探求,因此,真理与生活本就无法分割。在教育问题上,这种实用主义认识论就是杜威所说的“教育即生活、即生长、即经验改造”;而“从做中学”,则是在教学上的实际运用。知识的传授,不应该是直接的、单一的、正面的,这种“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只能造成教育的“畸形”。杜威也是坚决反对“学习知识从生活中孤立出来作为直接追求的事体” 。如在我们现代教育教学中,就拿小学数学学科中“认识时钟”“认识货币”教学实践为例,研究者认为不应该只是简单地作为一堂教学课进行讲授,而是与家庭融通整合,帮助儿童在生活实际中识别、习得;回到课堂,教师再进行指导并归纳,进行系统地形成认知概念。再者,作为一名少先队工作者,在开展少先队活动时,更需要引导儿童“求知”“调研”,找到现象背后的原因,再回到课堂,一起探讨、研究、活动、提升。将少年儿童自由支配的时间或家庭生活的闲散时间融入学校课程之中,充分利用“儿童的游戏本能”,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知识,掌握技能,而不是生搬硬套、死记硬背地掌握知识,这种表象的“掌握”实则是无法运用开来的。
从杜威的“从做中学”论证中,我们不难发现教学是从儿童实际情况出发的,教学也是来源于生活的,也依附于儿童的现实生活。这种不脱离于生活的儿童学习,可以更好地激发儿童的求知欲。当面对自我的知识匮乏时,产生解决问题的动力和勇气。
要知道,在杜威时代以前,学校一直以来都成为“儿童心灵的屠宰场” ,没有尊重儿童的发展。尽管在18世纪,卢梭的《爱弥儿》问世,让教育开始思考“自然的发展”,但并没有让当时的儿童受惠。直到杜威提出“儿童中心论”和“从做中学”,儿童的教育才迎来了春天,学校教育才得以改变。
三、陶行知生活德育理论的产生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教学上的运用和延伸,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并开始学习和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深受杜威的教育理论影响,却始终没有做到将杜威教育理论日本化。而此时的中国教育,因为一个人正悄然发生着变化,他就是伟大的中国教育家陶行知。那时候的他,已经在中国将杜威的教育理论结合中国现实,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进而适用于解决中国本土的教育问题。
时间追溯到1914年,陶行知在美国获得政治硕士学位,又于1915年秋,开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师从杜威,开始研究教育。求学期间,陶行知信奉老师所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论。
1919年5月,杜威应邀来到中国讲学,陶行知为其做翻译,并发表了一篇题为《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的文章,旨在宣传杜威的教育思想和主要著作。但是,陶行知也清醒地认识到杜威的教育思想能在资本主义美国发挥重大作用,甚至能在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未必可行。可是他又深信老师的教育思想是能在学校教育中、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陶行知见到中国落后的现状,结合教育实践经验,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全新理念。“生是生活。先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先生,后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生,学生便是学过生活的人,先生的职务是教人过生活。小孩子先过了这种生活,又肯教导前辈和同辈的人去过同样的生活,是一名名实相符的小先生了。”
陶行知做了这种大胆的尝试,将杜威的教育思想来了一个“大反转”,强调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儿童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通过实践体验来总结归纳经验,上升为教育理论,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那些对于杜威的教育思想认识不深、对陶行知教育理论解读不到位的人,则盲目地认为陶行知与其师的教育思想完全相反,以为当时的中国教育同杜威的教育思想背道而驰。其实不然,杜威的教育思想对陶行知在中国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发挥了重要的启示作用。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中国本土化,符合唯物论的“实践检验真理”“物质决定意识”。
陶行知先生本人也是一贯秉承着这一教育理念,通过自己的教育实践,他对于先前提出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于1927年,在晓庄学校正式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也将自己的名字更名为“行知”;至此,可作为陶行知生活德育理论的萌芽期。
四、“小先生制”的产生和发展
1. 关于“小先生制“的理论研究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生活德育理论的实践途径,直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虽然“小先生制”的产生,依托于当初旧社会的现实背景,但这是陶行知普及教育的产物。陶行知也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变革和教育改革的实践先驱,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形成和确立现代生活教育学说;坚决不做“把外国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的东洋车夫” 。北京师范大学高奇教授在《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中分析到:“陶行知的全部教育实践,围绕着一个核心,即普及大众教育。” 在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中,研究者把目光聚焦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践活动中——“小先生制”。
2.关于“小先生制”的实践研究
21世纪初之后,“小先生制”的新发展,被充分运用到学校的各学科、班级建设管理、品德教育、幼儿教育等各领域内。以西南大学孙卫和陈文怡撰写的《陶行知“小先生制”在小学英语教学中之应用初探》为例,提出了“‘小先生制’促进群体智力互补、为未来的小班化教学做铺垫” ;但在类似的学科运用中,还存在教学组织形式、实施环节、效果反馈等方面的问题。通过查找大量有关“小先生制”在各学科中运用的文献,不难发现谈实施方法、步骤的少之又少,更多的是侧重于策略研究,换言之,仅仅停留在“纸上”。
在幼儿教育领域,“小先生制”也正被广泛运用着。秦纯一所写的《我是能干的“小先生”——浅谈“小先生制”在幼儿园班级管理中的运用》一文,通过运用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理论,引导幼儿自主参与班级管理,激发潜能,促进个性发展。很明显,在幼儿教育中施行“小先生制”要比在学科中的运用,更如鱼得水,有的放矢。这同袁文娟在《班主任》杂志上发表的《“新基础教育”班级岗位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上)》 一文,有着不少融通点:在“新基础教育”岗位建设中,学生是主体,教师也是主体,因为岗位建设是老师与学生合作进行的教育实践。所以,从师生在此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来讲,“新基础教育”的岗位建设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重建。由于和幼儿教育一样,几乎没有牵涉到知识点的“学”和“教”,更多的侧重于自我行为控制、班级管理工作等,自然简单、易操作。
3.“小先生制”在德育领域中的研究
无独有偶,“小先生制”也可在品德教育中熠熠闪光。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的吴艳华在《新时代的“小先生制”》中提到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强调的以学生为主体,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师生教学相长、共同发展,学生自评同伴互评等理念都是新时代‘小先生制’的体现” 。传统教育中,教师管理学生,而“小先生制”则是学生主体性的充分体现。她还提到利用好“小先生制”,可以“配合学校做好捐书、捐款、绿化美化教室、书法绘画比赛、讲故事等活动,增强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做具有爱心的学生”。
无论是在学科中的运用,还是在班级管理,抑或是品德教育中的实践应用,“小先生制”一直着力于推动学生主体化思想的发展。尤其在二次课改的春风下,“小先生制”有了新的发展之路。也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有了新的理解。正如李明尚在《当代教育科学》上发表的《在“小先生”课堂改革的道路上前行》 中指出:可以将“小先生制”看作是课堂改革的一种模式;也可以看作是上课变革的思想和方法。如果课标发生了改变,人的思想、观念、态度、方法,包括行为的方式都可能发生改变。
五.“小先生制”的新运用
1.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小先生制”
“以教人者教己”乃小先生制推行的指导思想,即学是教的前提。当学生在做小先生的过程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便较好地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他们回到课堂,会更努力地汲取知识,继续不断地学,才能不断地教。
也就是在“教”的过程中,小先生们常常会感到“知识到用时方知少”,所以更好地激发他们刻苦钻研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进而会主动要求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以此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小先生制”提倡“教、学、做”合一的“三字”教法。陶行知先生说:“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因为“三字”要求,所以小先生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教、学、做必须一以贯之,周而复始,循序渐进。也正是把操作过程下放给了小先生,充分享受主体性,小先生们在教学中享有自主权,不受拘束,创造性和想象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今天,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少年儿童的主人翁意识、自主学习的素养。过去为了弥补旧中国师资匮乏而建立的“小先生制”,也将被赋予新的时代定义: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师生教学相长共同发展,学生自评、同伴互评等教育教学活动。
2.陶行知教育创新发展区里的“小先生制”
1994年,宝山“大场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区”的成立,行知中学市级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的立项,标志着全区教育界整体“学陶”的开端。
在学陶经验与区域发展的整合过程中,凭借着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底蕴,创生了学生学习方法和教师教学方法的新形态,即教学做合一的创新性学习。渐渐地,陶行知教育思想成了宝山区教育之魂;“学陶师陶”不仅是宝山教育发展的主要标志和鲜明特色,也是宝山教育综合改革的思想源泉和不竭动力。
2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宝山教育是这样的:“行知中学的‘真人教育’成为宝山学陶和宝山教育文化的标志性坐标;进修学院附小的‘艺友式活动学习’成果被《人民教育》杂志连续两期进行介绍,被誉为‘静悄悄的革命’;通河中学的‘说做’教学法培育出上海青年教师的师德楷模徐宏杰;宝山中学的‘民主和谐的创造教育’使得宝山中学从一家普通高中正向着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方向前进;长江二中的‘让老百姓的孩子也能成才’的平民化教育温暖着淞南动迁人口地区老百姓的心窝……都已经成为在上海市拥有发言权的品牌项目。”
宝山教育对于陶行知理论的深入研究,在《宝山区教育综合改革方案(2015~2020年)》文件中已作了明确,提出打造“陶行知教育创新发展区”。以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为研究基础,力求“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立足“学生未来生活和终身发展”。宝山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特长、服务特长学生,创新实施“新陶行知‘小达人’培养计划”。当然,现代“小先生”的培养,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进一步全面“完善特长人才培养的服务支撑体系”。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周洪宇在2011年11月30日所作的《陶行知研究的现状与前景》报告中,这样提到:“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实验,是出于一种本土情怀;不是为了研究实验而研究实验,而是为了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也是为了今天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来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开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验。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而不能舍本逐末。当然,我们也不宜简单照搬陶行知的术语概念或简单模仿其做法,关键是学习与借鉴其精神实质,这才是真正地学陶、研陶、师陶和用陶。”
笔者领衔的上海市少先队课题《在少先队活动课中民主推行“小先生制”》正在积极实践与探索研究中。在这过程中,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实践积累,笔者愈加坚信“小先生制”现代教育的重要意义。
叶澜教授也在《回归突破》一书中写道:“今日教育已发展到贯穿于人的终身,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区别不限于年龄之差,它在不同的年龄层与同一年龄层之间都有发生的可能。”笔者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因此,凭借着本土化的良好“教育底蕴”,依托陶行知教育发展创新区的地理优势,“小先生制”对于区域教育的发展与创新,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本栏责任编辑 鲁 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