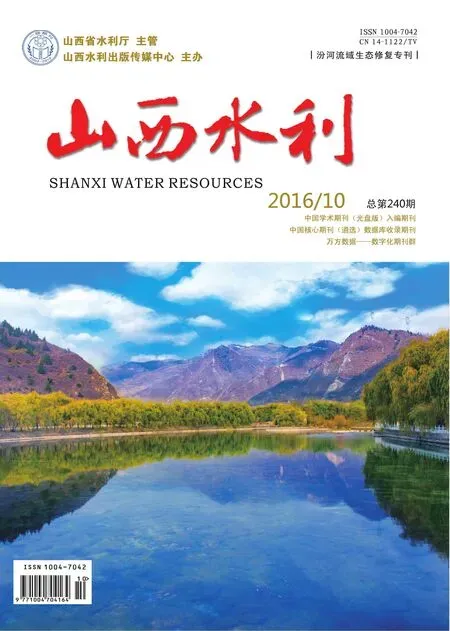汾河历史阅读
2016-04-07张荷
张荷
汾河历史阅读
张荷
自从人类在这个蓝色的星球诞生之日起,就与水结下不解之缘。水,浮天载地,无处不在;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泉,是世间万物的生存之本。人类因水而生存、延续与进化,因利用和改造所依傍的河流得以繁衍和创造文明。
河流,是地球上最基本的自然形态之一,是地球上最具活力,延续最长久的生命带。人与河流唇齿相依,同生共进。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不朽的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生长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两岸及其流域。万里黄河与长江则滋养和哺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古老而悠久的文明历史,故而为亿万炎黄子孙尊称为中国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1 汾河,山西的“母亲河”
山西,自古有“三晋”之别称,“表里山河”之美誉。在这片15.6万km2广阔的黄土高原上,日夜奔腾不息地流淌着一条自北向南纵贯大半个省城的大河,她的名字从古到今一直被称为汾、汾水、汾河。汾河,是黄河流域内第二大支流,是山西省境内流域面积最大、流程最长的第一大河。从源头到入黄口,主河道干流从宁武县境内的管涔山脚下走来,穿过千山万沟,跨越太原、临汾两大盆地,一泻千里,奔流入黄河。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处于黄河流域中游腹地的汾河及其流域,从原始时代起,人类的远祖先民就生息繁衍在汾河这片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的原野河畔,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开辟了人类文明社会的新纪元,创造孕育了古老灿烂的三晋文明与汾河文化,使这一地区无可争辩地成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之地。
从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直到公元前21世纪的远古传说时代,尧、舜、禹三代圣王一直生息活动在汾河这片宝地。世人皆知的“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和“禹都安邑”(今夏县),无一不是分布在汾河下游和曾是早期汾河故道的涑水河流域。从尧帝立都平阳为开端,5000年来,华夏大地发生了巨大变革。“帝尧时期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尧典》;大禹治水,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兴修水利的先河;仓颉造字,开创了中国文化纪事的新纪元;后稷稼穑,使中国由此进入农耕文明时代。”正是尧建都于平阳,华夏大地首次出现了一个管理万民的政务中心,即国家机构。在尧的带领下,远古先民们终于开始用智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去探寻、创造前景灿烂的文明之路。如此惊天动地之壮举,恰好扎根于山西南部地区的汾河与涑水。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升腾在三晋大地和汾水之畔。
自人类跨入文明时代起,走过漫漫征途。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历朝历代,时兴时衰,不断变革与进取。悠悠三千年间,汾河上下,三晋沃野,虽历经群雄争霸,风起云涌。然风平浪静之后却长久呈现着一派生气盎然的繁荣景象。这正是那条得天独厚、常流不息的巨川大河——汾河之水。汾河,用她那母亲般的博大胸怀和取之不竭的乳汁,滋养哺育着世居在河流两岸千秋万代的子民百姓,同时孕育和积淀了悠久而深厚的“汾河文化”与“三晋文明”。正因如此,汾河,这条古老文明的巨川大河,被山西人民亲昵地喻为“山西母亲河”!
2 台骀治汾,“肇始太原”
在史前历史中,一提到远古传说时代的治水英雄人物,首先想到的就是“大禹治水”。其实在大禹治水以前,已有一位非凡的治水人物,他叫台骀。据古典文献史料和现存的古文化遗址查证,确有台骀其人,他先于共工和鲧禹父子,最先承担起治理水患的大任,并取得治理汾水、肇始太原的丰功伟绩,被世人奉为“汾河之神”。更有甚者,称之为“华夏治水第一人”。
关于台骀的传说,散见于《左传》《山海经》《史纪》与《水经注》古代文献之中,最早见于成书在公元前541年的《左传》。是书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负责治水的官吏),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这段见诸《左传》的史载与记述,向今人揭示了距今约四五千年前发生在山西境内汾河流域的一段生动而传奇的史实。展开一点讲就是,远在新石器晚期的部落联盟时期,即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荒蛮上古时代,史传的“三皇五帝”中,名列五帝之首的古帝少昊——金天氏其子曰昧,其裔孙即是台骀。台骀受帝颛顼之委派,子承父业,承袭了父亲昧的水官职位(即玄冥师),担负起治理汾河水患的重任。台骀所处的时代是黄帝与颛顼(继少昊之后脱颖而出的东夷部族首领,名列五帝第二位、亦称高阳氏,被视为黄帝之后又一位华夏共祖)的远古时代,比尧、舜、禹时代大约还早几百年。台骀当时生活的环境正是人类同洪水频繁搏斗的非常之时。据史料与民间传说,是他开创了古代治理汾水之先河。台骀在治水方面有两大功绩,一是“宣汾、洮”。汾,指今汾河,洮,指今涑水河上游一支流(即涑水南源)。上古时汾河下游河道在今侯马、闻喜、新绛一带,烟波浩渺,洪流行迹无常,主流向南向西摇摆不定。台骀经过艰苦细致的实地察看,决定将汾河主流顺势利导,即在今侯马东台神、西台神两个村庄汾河拐弯处开凿出一条新河,迫使南北流向的汾水拐向西行,彻底与涑水河道分离。二是“障大泽”。大泽者,即湖沼或大薮泽。障泽即筑堰拦截客水之意。台骀所障的大泽是指古代汾河中游的两个著名泽薮,一为“昭余”或“昭余祁薮”,另一大泽为“台骀泽”。“昭余祁”水域在今祁县西南,介休之东北,为当时全国的“九薮之一”。而“台骀泽”水域则位于今太原晋源区之南至晋祠、清徐、汾河东岸地带。台骀采取筑堤围湖的办法,把洪水四溢的汪洋大湖区限制缩小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空出四周大片土地,为先民提供大片耕作良田,这就是“障大泽,以处太原”。这里所说的太原者,在古代泛指汾河流域高而平、广而大的地貌地域,即今日之太原盆地范围。“宣汾障泽、肇始太原”就是台骀一生所完成的两件治水伟业。台骀死后被尊称为“汾河之神”。后晋时追封台骀为昌宁公,宋代又加封台骀为灵感元应公。因其历史功德,人们立庙造像,世代供奉祭祀。至今宁武、太原、汾阳、侯马等地建有多处台骀庙。每逢农历五月十八日,汾河沿岸民众都要举办传统庙会,盛况空前。
3 大禹治水,既修太原
禹,是我国原始社会父系氏族末期部落联盟的领袖。是中华民族妇孺皆知与史学界共识的一位传奇式治水英雄。禹,又称夏禹、伯禹、大禹。相传禹生于西羌(今甘肃、宁夏、内蒙南部交界一带)姓姒,名文命,后随父鲧迁居嵩山下(今河南登封)。大禹所处的时代,仍是一个洪水泛滥、久治不息、水患无常、环境恶劣的年代。禹受舜帝之命,担负起平息水患之重任后,一改其父沿用共工“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筑堤堵流的失策之法,亲自率领治水大军“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夏本记》),制定了“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国语·周语下》)的治水方案。当时四野横流的滔滔洪水,经大禹疏浚河道,清除阻水物体,畅通流入大河大海。同时利用已有的泽、薮和洼地聚积储存一定水量(即钟水之意),以备日后农耕灌溉与人畜用水。由此可知,大禹的治水不仅仅是单纯的消除水患,而是在治水的同时“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意为尽力考虑农田灌溉。
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立下丰功伟绩,数千年来黄河上下,长江南北无处不在传颂和称赞。据古籍史书记载,大禹治水的足迹虽有可能遍及华北、西北、华东、华中等广大河川地域,但主要活动地区应在黄河中下游流域范围,而中原地区(即夏代主要活动的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则是重点。大禹治水最早的记载,见诸于我国地理名著《禹贡》。《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该书首段便说:“即载壶口,治梁及歧。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这段话中有五个古代自然地名:壶口即位于山西吉县境内的壶口瀑布;梁、歧都为山名,梁山,在今陕西韩城东南约10公里处,又说是今吕梁山;歧山,在今陕西歧山县东北,又说为今孝义县境内的狐歧山。壶口、梁歧两山均处在黄河北干流晋陕峡谷东西两侧,夹河而峙,隔河相望。“既修太原”是说在大禹治水前台骀“宣汾障泽”之后的汾河中游太原盆地。“至于岳阳”系指古代霍太山之南,即今太岳山南麓霍州境内。这段史载告诉我们,大禹治水先从壶口开始兴工,一路南下开凿了梁岐两山,并劈开龙门(即今河津禹门口),使黄河畅通南流,这就是史书中说的“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疏通黄河之后,禹返折向北到太原,开始治理汾河。此时的大禹为何急于北上治汾呢?《晋乘搜略》说的很清楚:“洪水方割时,壅汾水不出,震及帝都(指尧都临汾)”,“鲧极意崇防,因汾治汾,而不计汾之不泄”。这段话的意思是:黄河洪峰来到时,滔天洪流壅塞漫溢,而由南向西的汾水进入黄河之路被阻塞在下游河道,排泄不畅,日聚成灾,致上游河畔之尧都处于水患之中,民不得安生。这时大禹吸取先人治水的教训,“先疏而后防”。率众疏通拓宽黄河故道,使其顺流南下,后迅速挥师北上,到汾河中游河段,凿石劈岭,疏浚河道,开挖沟洫,一直到霍太山南麓的岳阳为止。大禹这段治水经历正是史载中所说“即修太原,至于岳阳”。至今盛传于太原和晋中民间的“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故事,正是大禹当年率领治水大军北上太原,疏通顺直汾河中游河道,凿开灵霍山峡百里河道,使汾河之水畅通下泄,空出浩渺无际的晋阳湖,为两岸民众提供了安定的生存环境。《水经注·汾水》曰:“又南过冠爵津”,此冠爵津俗称雀鼠谷,又名鹳雀津,即指今灵石至霍州一段汾河峡谷。正是当年大禹治水,打通灵霍山峡中最为艰苦的一段。
大禹治水离乡背井,在外治水十三载,“身执耒锸,以民为先”,“劳神焦思,泽行路宿”,“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使“洪波安息”,“水患大治”,为三晋人民乃至华夏民族的安危与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华夏炎黄子孙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大禹治水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公而忘私、不辞艰辛、褒善惩恶、大公无私、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以及对待事物求真务实、敢于创新、不断超越的献身精神和科学态度。大禹治水的宏伟业绩流传百世,大禹的崇高品德和为治水事业奉献毕生的坚韧意志,为我们新时代的水利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4 历史时期汾河航运的兴衰与水文变迁
《山西通志·太平县》中记“秦穆公元年(前659年)泛舟之役,自雍及绛。相继,晋惠公(前650年)都今太平晋城,秦人舟止于绛,盖避柴寺村、史村之险也。”太平,今襄汾汾城。雍,今陕西凤翔南,时为秦都。绛,今翼城县东故城村,时为晋都。“泛舟之役”,始见《左传》僖公十三年(前647年)记有:“晋饥,使乞于秦……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这段史载说明,远在公元前的600多年,晋国遭受饥荒,派使者到秦国求援,秦国慷慨允诺给与支援。于是那年冬春时节,即派出大批船舟运粮,从渭河顺流而下进入黄河,逆水北上到达汾阴(今万荣荣河),等待春汛消冰开河之后,再次逆水驶入汾河,经皮氏(今河津),入浍水,到达绛都(翼城)附近靠岸。这是古代经由渭河、黄河、汾河、浍河多条河流共同完成的一次大规模的水上航运。此事足以说明,古代汾河与浍河曾是一条能行大船的河流,就是在冬春水小的季节,也能浮起承载万斤粮食的大船行走。近人王伯祥所著《左传文选·注释》曰:“自秦输粟入晋,当从渭水运入河、汾,故曰汛舟之役”。
在春秋“泛舟之役”后,汾河中下游有两次较大的航运活动,一次是汉武帝刘彻曾率领群臣乘龙舟大船幸巡河东,由黄河入汾水,到达万荣县荣河入黄口一带,祭礼后土。并在楼船上大宴群臣,此时他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秋风辞》,而辞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这样两句,让后人回味无穷。据史载汉武帝公元前120多年前曾8次乘船入汾河幸巡,7次到汾阴后土祠祭祀。说明2100多年前的汾河下游不仅水量充沛可以让承载数百名皇宫大臣的“龙舟”畅游汾河,而且水色清澈,碧波荡漾。另一次船队航运是在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因长安(今西安)仓储空虚,诏漕汾、晋之粟以给京师。《晋乘搜略》记:“漕舟由渭入河,由河入汾,以漕汾、晋也。”到开元之年的唐玄宗时,裴耀卿主政漕运事时,“益漕晋、绛……租输储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隋唐时代,汾(州)、晋(阳)、绛(州)均在汾河中下游,时为全国最富庶之地。通过这条水路把大批粮食转运供给长安皇室享用,当时的汾河可谓是一条黄金水道。
汾河之航运自春秋“泛舟之役”,到隋唐繁忙兴旺之时,先后长达1500多年。五代之后,尤以宋之后,古籍典史中就少有大船在汾河航运之记述,现存最为深刻记忆的只有“汾河晚渡”为太原八景之趣闻,明代汾河“秋夏置船,冬春为土桥以渡”之类的小型船舟游渡。清代有人曾想“通舟于汾,制船如南式”,但此时汾河水量已无船运之力,充其量也只能在春秋水大时用筏舟运载少量山木而已。
历史上汾河航运的兴衰,充分反映出汾河及其流域的水文变迁,而引发河流水文变迁的主要因素不外乎自然营造力和人为活动两方面,即同本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特点与趋势息息相关。史前时期,太原盆地曾是一片汪洋大泽,被通称为晋阳湖,古湖造就了汾河中游盆地丰富的地面与地下水资源,而中游两侧支流均来自太行、吕梁两大山系,因断裂构造发育之缘故,期间形成众多泉水溪流,加之史前东西两侧山区森林茂密、植被完好,水流冲刷侵蚀极小,水土流失轻微,这些原始形态的水文与生态环境无疑是形成汾河干流及其支流河水清澈、水量充足、季节变化小的根本原因。进入历史时期,尤其是大开发的春秋战国时期,汾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日益发展,人类为了生存,不断垦荒种植,伐木为薪,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改变着自然的本来面貌,久而久之致使自然界的生态环境逐渐失去平衡,从而波及水文条件的急剧变化。
5 河泉灌溉,历史悠久
由于汾河中下游在历史时期的初、中期水利资源较为丰富,世居两岸与流域内的劳动人民充分利用着这一自然优势,引水灌田、发展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从公元前453年战国初期人民群众利用“智伯渠”引晋水灌溉农田开始,汉、晋、隋、唐历代,一直延续至清明两代,期间跨越与经历了2500年的漫长历史。据方志和史典资料不完全统计,自春秋到清末,山西古代共兴修水利工程389项,在全国名列第10位,其中汉代4项名列全国第9位,隋唐35项,仅次于陕西、浙江名列全国第3位,北宋25项,少于浙江、江苏、福建名列全国第4位,元代29项,少于浙江、广东与江苏并列全国第3位,明清两代253项,名列全国第10位。这些水利工程大多集中分布在汾河中下游两岸及其主要支流。引泉水兴灌溉之利,最早的水利工程应是战国初期引晋祠泉水。《水经·晋水注》曰:“难老、善利二泉,大旱不涸,隆冬不冻,灌田百余顷”,说明在北魏之前晋泉已能浇灌农田近万亩。此后,在东汉元初三年(116年)安帝时,再度“修理太原旧渠,灌溉官私田”,并在翼城境内开凿滦地渠,引皋翔山泉灌田;在曲沃县境内引绛水(沸泉)灌田;隋开皇十六年(596年),临汾县令梁轨在绛州“开鼓堆泉十二渠,溉田百余顷”。到唐代汾河中下游的引泉灌溉已有很大发展,除晋祠泉、鼓堆泉之外,贞观年间在洪洞广胜寺“引霍泉分南北十二渠,灌赵城、洪洞二县九十一村,民田八百九十一顷”;在临汾“开南横渠和北磨河渠,引龙子祠泉溉田”;在龙门(今河津),凿引三峪泉水兴灌溉之利。北宋嘉祐(1060年)时,在介休县,洪山泉“开东西中三河,自南而北流出,可溉田一百五十顷”,金、元、明、清各代汾河中下游主要泉域普遍得到开发利用。
汾河流域的河渠灌溉,大约要比引泉灌溉要晚300多年。引汾河水灌溉农田的最早记载是汉武帝继位10年之后的公元前128年,即引汾河与黄河之水灌溉河津、荣河一带滩地。此举虽半途而废,但它却开创了引汾与引黄灌溉的先河。到唐代,汾河中下游两岸以及浍河、文峪河、潇河、昌源河等支流已多处开渠引河灌溉,中游文峪河于贞观三年(629年)“民相率引文谷水(即文峪水)溉田数百顷”。唐贞元时(785—805年),由绛州刺史韦武主持引汾水灌溉农田1.3万顷有余。金代兴宝二年(1218年),在洪洞、赵城县境汾河干流上兴修通利渠,使沿渠18村民众大受灌溉之利。清代中期汾河流域以民间兴办为主要特点的河渠灌溉工程已相当发达。据《嘉庆一统志》记述,那时的灌溉工程仅太原府就有69条,其中文水县引文峪河水14条,祁县引昌源河水11条,榆次引潇河水30余条。光绪版《山西通志》记,太原县引汾渠道由清初的11条到清末增至30条。阳曲县引汾渠道由清初的14条增至28条。当地群众俗称“泥渠”。光绪三十年(1904年),汾河中游干流太原至晋中河段,拦河构筑土坝,以壅高水位,逼水进渠,渠内设闸,激水入田形成固定的“八大冬埝”,沿河收益村庄190个,可浇灌两岸农田30万~40万亩。今日的汾河灌区就是历史上“泥渠”与“冬埝”的延续和发展。
综观上下五千年历史,从传说中的台骀、大禹治水,到西汉王朝开渠引汾灌溉的尝试;从唐代汾河流域引泉灌溉的蓬勃兴起,到明清两代汾河中下游民间大规模的开渠引河灌溉,无可争辩地说明,古代山西水利的起源与发达之地在汾河中下游,并由此形成古代山西农业经济繁荣的两大基本经济区,一个是以太原为中心的经济繁荣区,另一个是下游以临汾(平阳)为中心的经济繁荣区。
6 结语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奔腾不息的滔滔汾水,为山西这片黄土地创造了许许多多珍贵灿烂的历史文化。今日汾河流域,从上游到下游,从干流到支流,随处可见从久远历史传承延续下来的的名胜古迹、金石碑刻以及历代文人名士的千古绝唱,并以她独有的人文景观特色名副其实地融合于“黄河文化”、“三晋文化”之中。充分展示了河流文化生命的传承功能和经久不衰的教化作用。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河流的水资源体系支撑着人类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人类由此得到了河流的巨量恩惠。在历史时期内,每一条有人类涉足的河流,都无条件的被人类改造、利用,被无休止的索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需求,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年复一年的毫不吝啬的消耗着自然资源,无休止的改造所处的生活空间,这就势必打破自然环境原始生态的平衡,进而对河流的自身规律产生难以逆转的恶果。
今日之汾河,一方面我们从不掩饰地赞美与肯定她为三晋大地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和面对汾河严重存在的水资源衰减、河道频繁断流、水体污染严重、泥沙不断淤积、流域自然生态系统功能遭受损伤与失衡等。千里汾河从遥远的历史时期流淌到今天,已经面貌全非,古老的汾河——三晋儿女的母亲河,能否维持其“清澈、碧波、千里汾水哗啦啦”的健康生命,长流不息,重新展现出“河畅泉涌、碧波荡漾、鱼鸟翱翔”的美好景象,这是历史留给我们这一代人艰巨而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也是新时代水利人共同追求的梦想!■
(作者系省水利厅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