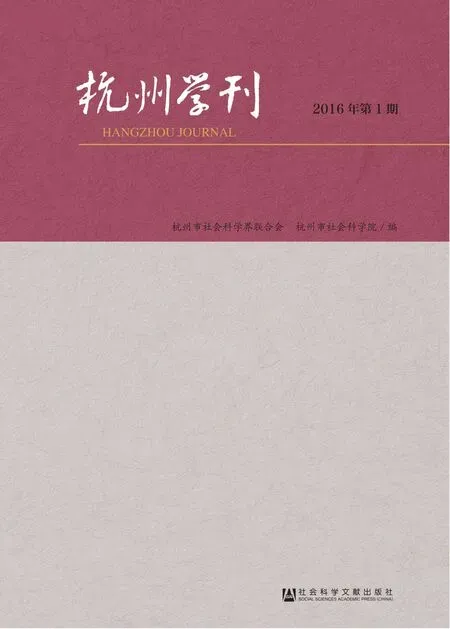杭州方言的历史发展脉络、现状与保护策略∗
2016-04-06罗晓岗
◎ 罗晓岗
杭州方言的历史发展脉络、现状与保护策略∗
◎ 罗晓岗
本文通过梳理杭州方言官话特征形成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分析杭州方言官话特征与宋历史间的相关联系,从而解决杭州方言官话特征来自北宋汴音还是清时期北京官话的问题。通过对杭州方言在初中学生中的使用现状的调查,获得了杭州方言处在衰退过程中的第一手资料,进而分析杭州方言衰退的主要原因。在检视国内外方言保护措施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杭州方言这一南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议。
杭州方言 北宋官话 文化遗产 活态保护
作者罗晓岗,浙江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邮政编码 310012)。
杭州作为南宋故都,留至现今的文物遗产大多已被充分认识并受到保护,而另一重要且具有地域特征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杭州方言却处在衰退过程中。
杭州方言(杭州话)虽然被划为吴语太湖片杭州小片,但受官话的影响很大。赵元任1928年做吴语方言调查时,首次指出杭州因曾是南宋首府,杭州方言受官话的影响很深,“其口语与周围的吴语有很大区别”[1]。一般学者也都认同在南宋时期,杭州城内的北宋汴梁官话与土著语言接触100余年,形成的杭州话融合了北方官话与当地土著语言的用词和发音特点[2],从而在以柔见长的吴语系中,形成了相对硬朗的独特语种,体现了官话与吴语融合的许多特点。杭州方言的一些语言特点成为宋代中原官话研究的重要佐证材料,并受到国外汉学家的关注[3]。但也有学者认为杭州方言的官话特征在清末受驻杭州旗营的影响更大[4]。因此,梳理杭州方言形成的历史条件,可以确认杭州方言作为宋中原雅音研究资料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随着国内交通的便捷、人口流动的增加,以及普通话在学校的推广,作为地方文化表征之一的方言普遍存在衰退的现象。而杭州方言的现状及其保护策略也成为紧迫问题。
一 杭州方言官话特征的历史发展
杭州方言的范围集中在杭州核心城区,作为浙江吴语中最小的方言点之一[5],在其被划分时就存在争议。虽然杭州方言符合吴语的基本特征,塞音、塞擦音声母分三类,但是在发音及词语使用的一些特点如文白异读不发达、梗摄二等韵与曾摄一等韵相混,以及一些常用词的用法上与杭州周围的吴语差别很大[6]。史皓元用16条标准比较典型吴语、杭州方言、杭州郊区方言以及北方典型官话等六个地方方言的特征后,发现杭州郊区方言与苏州方言等吴语高度拟合,而杭州方言却更接近官话[7]。对于杭州方言中的官话特征成型于南宋,历来学者都无争议。但对于清朝驻杭旗兵的北京官话对杭州话的影响却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清朝驻杭旗兵及其家属与杭州本地人相混杂,其浓重的北方官话色彩对杭州话中的官话特征产生了一定影响[8]。还有学者认为八旗兵居杭闹市区中心,占有向周围扩散官话影响的有利地位,杭州方言的官话特征主要来自清朝驻杭旗兵[9]。而徐越认为,满人被解散后都极力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并努力学习杭州话,没有对杭州话造成什么影响[10]。下面我们从杭州方言的特征、形成的历史条件方面来分析,从而对杭州方言官话特征正本清源。
(一)杭州方言特征的历史形成过程
文白异读,是指外来权威方言(主要是北方官话)以外来形式(文读)循着少数新兴词汇→文化词汇→一般词汇逐渐扩散,而本地形式(白读)保留在某些词汇中[11]。文白异读是吴语区方言的典型特征,体现了北方官话几百年来对吴语从文读到白读的逐渐渗透过程。但处于吴语中心区的杭州话文白异读却不明显,显然北方官话对杭州土著语言的影响不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而是一个快速覆盖和替代的过程。很明显,只有外来权势语言在短时期内达到一个高峰才可以做到快速覆盖本地语言,而在杭州历史上只有在宋室南渡时期才符合这一条件。
宋金战争后,建炎三年(1129年)杭州升为临安府,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杭州,其间北方特别是汴梁人士大量涌入杭城,“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12],使杭州城内人口激增。由于宋对人口统计注重男丁,对人数统计不太精确[13],因此本文用户数来比较人口变化。根据《宋史》《地理志》[14]《乾道临安志》《淳佑临安志》《咸淳临安志》的记载和林正秋的修正[15],杭州府的户数见表1(宋时杭州城包括钱塘全部和仁和县大部)。

表1 宋杭州府户数变化
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杭州府的户数变化有两个特点。一是户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钱塘、仁和和富阳三个县。因此,虽然没有崇宁年间每个县的数据,但是根据后面的数据变化可以推断出从崇宁年间到乾道年间户数的增加主要在这三个县城,由此推算崇宁年间钱塘县与仁和县的户数为50000户左右。二是户数的变化不是线性的。乾道到淳祐年间,户数变化不大。而崇宁至乾道年间、淳祐至咸淳年间是两个人口突变的时期。而这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正是自宋靖康之难(1127年)起到宋金议和(1164年)间的宋金战争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第二次蒙宋战争开始(1253年),蒙古开始大量夺取南宋江北国土。这两个时期杭州人口激增正是因为战乱引起的北方人口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据徐越估算,宋金战争期间从汴梁过来的仅官员、家属和士兵就有22万人,大大超过杭州城内的土著居民[16]。而这些人同时具有朝廷政治特权上的优势,也使汴音能在短时间内覆盖原土著语言。元灭宋时,杭州府未遭大难,因此到明时,杭州城内汴音依旧。郎瑛的《七修类稿》有记载,“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17]。
反观清代驻杭旗兵却不具备这样的语言优势。其一,驻杭州旗营士兵人数较少,据记载,至顺治二年(1645年),旗兵人口为5000人[18],算上家眷,其人口与杭城人口相比也是微不足道。其二,清旗兵开始在城内驻扎时,经常与民众发生冲突,做“强占房屋,殴打百姓”这类事,为民众所痛恨[19]。而后用城墙将旗营围起来,将他们与城内百姓隔开。由于平时与杭城平民交流机会较少,且满汉极少通婚,因此于情于理都不太可能对杭州当地方言产生大的影响。
另外,从语音特征上分析,如果旗兵的北方官话能渗透到杭州方言中去,其渗透过程必然较为缓慢,那么杭州方言就会和其他地区的吴语一样,产生文白异读。但在民国初年,赵元任先生调查时,杭州方言中罕见文白异读。因此,不论是从方言的扩散条件和杭州话的本身特点来看,我们都可以断定杭州方言的官话特征应该是来自宋。
(二)杭州方言的典型词汇显示了其历史起源
杭州方言中的一些最常用词有许多与现在的北方官话相同,如我、你、他和复数词尾的“们”字,以及杭州方言中最具特色的“儿”尾词。那么,这些词是在清朝成为杭州方言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元末小说《水浒传》中,大量出现杭州方言的特色词汇。现在从《水浒传》中的用词,对杭州、江淮地形的描述,以及对作者籍贯的考评上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施耐庵是杭州人[20]。表2是鲍士杰先生摘取的《水浒传》的用词[21],限于篇幅,我们只列举几个,但是《水浒传》中的杭州方言特征暴露无遗。

表2 水浒传用词对照
《水浒传》还有个重要的字——“们”。吕叔湘考证在元代北方官话(现代燕京官话的前身)中用的基本是“每”[22]。也就是说,《水浒传》中的“们”字要先于现代北京官话,这也证明杭州方言直接继承于北宋汴音。
(三)近代周围吴语对杭州方言特征的影响
杭州方言中也含有一些吴语特征,尚不能确定是南宋时杭州土著语言的遗留还是明清时期周围吴语对杭州方言的渗透。少量有记载的可以分辨出来,如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提到,“呼玉为玉(音御),呼一撒为一(音倚)撒”[23]。这说明在明朝时,清入声与次入声已入派三声。因此,现代杭州方言中的入声,应该是从周围吴语中吸收而来的。
尽管如此,总体上来说,在民国杭州城墙被拆除前,杭州方言中文白异读字较少,吴语对杭州方言的影响不大。罗杰瑞认为是“给杭州话涂上了一层吴语的粉饰,但是基本上须把它看作一种官话”[24]。究其原因,一是杭州城一直是浙江的经济文化中心,一般语言的扩散都是由中心权势城市向四周扩散,从省内流入杭州的居民会尽力学习当地方言。二是杭州的城墙也将杭城中心与四周郊区隔离开来,以减缓这一过程。
民国后,城墙逐渐被拆除,杭州方言与周围吴语交流逐渐频繁。在杭州方言内部出现新老两派方言。老派发音人很少有文白异读现象。而近年来进行语言调查时发现,新派发音人的一些发音对周围吴语全部借用,如泥日疑母字在细音前,老派发音人大部分读[n]声母,然而新派发音人除你字读[n]外,其他一律读[ȵ],和周围吴语一致。而另一些音,如微母“味蚊闻吻问忘望网”日母“肉热”及“借写谢野夜爷”等字都产生了与周边的吴语区(如绍兴)相一致的第二种白读音,产生文白异读现象[25]。
总结以上三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杭州话的官话特征来源于北宋汴梁的中原雅音。而近年来与周边吴语区的交流,使得杭州话中的吴语特征逐渐明显。
二 杭州方言使用现状
近年来,普通话的强势推广,对各地方言都产生了冲击。特别是在浙江、江苏等国内经济交流频繁的省份,方言出现逐渐衰弱的趋势。如在建立江苏有声语言数据库试点工作中,就发现不太容易寻找纯正的苏州话(吴语代表)发音人。与杭州邻近的上海市政府对上海话现状更加关注,对上海话使用状况进行了数次调查摸底。根据2010年对上海小学生上海方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听、说都流利”的小学生占45.1%,“完全听懂,能说一些”的占46%[26]。而在2006年孙晓先等所做的一项上海话使用情况调查中,上海学生在家里全家一起使用上海话交流的比例,初一学生为45%,用上海话+普通话的比例为33%;而在使用能力评价中,初一学生上海话能力为强、中、弱的比例分别为82%、13%、5%。结合其他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学生不可能也没有不愿意讲上海话。从调查数据可见,上海学生在掌握普通话的同时,都基本具备了说上海话的能力”[27]。
与之相比,杭州话虽是吴语中分布范围最小的独自成片的方言[28],但杭州作为省会城市人口交流频繁。新中国成立后,杭州人口逐渐增加。同时,普通话的强势推广,使得我们有理由感受到杭州方言处在消亡中,但是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数据调查。为此,我们于2014年6月对杭州西湖区一所公立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之所以选择调查初中学生,是因为之前的另一项调查表明,在会讲杭州话的人中,只有7.7%的人是在中学或中学以后学会的[29]。因此,初中生中掌握杭州话的比例基本反映了未来杭州青年人中掌握杭州方言的比例。
(一)杭州学生方言使用现状调查
本次调查共抽取样本156份,剔除一些自相矛盾的样本,有效样本为142份,主要调查问题包括对杭州话掌握程度的自评、在家庭和学校杭州方言的使用状况以及父母的出身背景和方言使用状况等。
由表3得知,在被调查学生中,掌握杭州方言比较好的只占19.01%。与上海初中一年级学生相比,上海学生自我评价沪语水平为“流利”“会说,不准确”“能听,不会说”的比例分别为48%、45%、7%[30]。显然,在被调查的杭州学生中会杭州话的比例较小。从表3还可看出,方言中“说”能力的学习源主要是父母。我们自然会提出疑问,杭州方言掌握比例低是因为父母会说杭州话的比例低吗?我们也对学生父母掌握杭州话的程度进行了统计。

表3 学生对杭州方言掌握的自评和学习来源
表4显示父母掌握杭州话的比例远高于其孩子。与表3的19.01%相比,父母掌握杭州话的情况较好,其孩子能较好使用杭州话的比例不到一半,由此可知,杭州方言确实处在快速消亡过程之中。

表4 父母杭州话的掌握情况
(二)杭州话衰退分析
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杭州方言已让位于强势的普通话。显然,普通话的强势地位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使普通话使用人群的比例提高;二是普通话的权势比以前得到加强。
根据人口统计与记载,杭州人口自抗战后持续增加,杭州城区(指杭州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拱墅区和江干区)人口在1947年为43.4万人[31],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5年为124.67万人[32],38年间增加了187.3%,年均增长率为2.8%。到了2010年人口为324万人[33],从1985年到2010年的25年间人口增加了159.9%,年均增长率为3.9%。这说明杭州从20世纪40年代起人口一直是以较高速度增加的。
将表5和杭州人口变动联系在一起分析,可以解读出人口流动并不是杭州学生方言掌握率低的原因。

表5 出生在杭州的父辈(20世纪60~70年代出生)掌握杭州话的情况
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国民党撤退、南下干部进城等各种原因,学生父母(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父辈较多为外地流入人口。但由表5可知,不管父母来自哪里,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杭州人熟练掌握杭州话的比例高达78.8%。这证明了杭州方言学习氛围的消退造成了杭州方言的衰退。
最后我们调查了学生在家庭中杭州话的使用情况。表6说明不论学生父母的方言背景如何,杭州话极少能在家庭中获得使用。

表6 家庭中语言使用情况
显然,由于年青一代在家庭中和学校中学习杭州话的氛围消退,“00后”学生接触和使用杭州方言的机会大大减少。
相比较而言,上海方言在家庭中的使用比例就高得多,这说明上海人对其身份的认同,愿意通过学习上海方言来构建其身份。
三 杭州方言的保护策略
(一)国外对方言的保护
国际上对方言的保护研究日渐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3年颁布了《濒危语言方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提出,“保护世界语言多样性,现在已经是而且将来也仍然是教科文组织全部职责中的重要工作”。方言作为地域非物质文化的重要部分,不少国家,如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保护方言,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保护这种沟通思想、传递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4]。
美国在1992年和1993年陆续出台两部法规并拨专款保护方言。2011年出版了《美国地区英语词典》。该词典收录了全国各地的方言词汇,记录了词语的地区特征,还特别记录了一些单词在美国国内不同地区的发音变化。该词典完成后,电子版本已公布在网上,方便民众查阅[35]。英国各地区口音较重,因此英国图书馆网提供了地区英语的典型发音有声资料,并在网上展示出来[36]。
其他西方国家也积极实施地方语言保护政策,如澳大利亚颁布的《语言问题国家政策》,其中包括支持土著语言教学、开展双语及双文化教育等。法国政府在学校开设阿尔萨斯语等方言课程[37]。
(二)国内方言保护现状
由于普通话的强势崛起,许多方言已陷入危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方言是文化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方言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而这些特有的地域文化都是以方言为载体的[38]。另外,从语言学习角度讲,不同的语言发音特点不一样,在掌握普通话的同时会一种方言,能及早培养语音的学习能力,取长补短。如英语语音中的b、p、g属于全浊音,对北方学生的学习就是一个较大的困扰;而南方方言前后鼻音不分,对一些单词的发音不准确[39]。掌握普通话和方言的学生对各类语言语音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国家语委也认识到了保护方言的重要性,开始建立有声数据库的试点工作。不过语言是交流工具,即使录制下来,失去了使用人群,依然会失去生命活力。2014年2月18日《人民日报》第14版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方言传承:回到生活现场》。文章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文化注定是多元的,方言不可能被圈在笼子里保护,而应回到语言使用的具体环境里,在听中说,在体验中学,在变化中保护”。
上海政府较早地意识到上海方言的保护需要在幼儿园及中小学层面进行。上海已出版上海话小学生课本,沪语教学试点纳入《2014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工作要点》,并且明确提出“教学语言使用普通话,生活语言使用上海话”。2013年,上海市已有100多所中小学开设“上海话”课程[40]。
(三)杭州方言的保护策略
杭州对杭州方言作为南宋古都文化标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禁止和打击杭州方言在学校内的使用也是杭州方言衰退的重要原因。
借鉴国内外一些方言的保护做法,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杭州方言的保护。
一是加强杭州方言作为南宋中原雅音的历史遗产的宣传,提高对杭州身份的认同感。在这方面上海做得比较好。调查表明,市民对上海普通话有亲切感,在家庭中父母与小孩之间使用上海话交流的也较多。
二是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杭州方言的字词、音档并不只是保存在库中,还应该公布在网上,做成教材,将杭州方言作为南宋文化的重要标签进行推广。本课题组已录制了数千个常用杭州方言字词,文本对照放在因特网上,为公众提供杭州方言学习和培训的资源。
三是加快在幼儿园教育阶段推行杭州方言的介绍和学习。杭州方言与普通话在发音和用词上具有许多共通点,这为学习和认识杭州方言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在国家语委的政策没有制定之前,可以借鉴上海的经验,尽快在幼儿园开展杭州方言试点,做到上课用普通话,课间用杭州话。
杭州方言的许多词汇存在于古典名著中,如《水浒传》中“拳打镇关西”这一回,用了很多杭州话中的儿尾词,使得语言更加生动。因此,保护杭州方言在动态的使用中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 结论
根据方言形成的历史条件和语音特点,可以推断杭州方言是宋音的宝贵历史遗产,对研究北方官话的发展、吴语的变化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杭州方言特有的价值也一直受到国外汉学家的关注,如罗杰瑞以杭州方言为例讨论吴语标准[41],史皓元出专著讨论杭州方言和中国吴语分区的问题[42]。
然而,我们却没有重视杭州方言这一南宋故都的历史遗产。杭州某知名小学提出了“禁止在校内讲脏话和杭州话”的口号。显然对杭州方言这一历史瑰宝缺少起码的尊重,并在孩子的潜意识里树立起对杭州话的负面印象。杭州话作为南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可再生性,因此对其保护也就显得刻不容缓。苏州、上海等地都启动了“本地方言走入课堂”的保护活动。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在普及普通话的基础上,使杭州方言这一南宋历史文明体现出其应有的文化价值。
注 释
[1]赵元任:《现代吴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第18页。
[2]慧子:《杭州方言的文化特色及其成因》,《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3]罗杰瑞:《关于官话方言早期发展的一些想法》,《方言》2004年第4期。
[4]王福堂:《文白异读和层次区分》,《语言研究》2009年第1期。
[5]李荣、鲍士杰编《杭州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16页。
[6]李荣、鲍士杰编《杭州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19~20页。
[7]〔美〕 史皓元:《南通话、杭州话跟吴方言的比较》,《方言》1988年第2期。
[8]鲍士杰:《说说杭州话》,杭州出版社,2005,第53页。
[9]王福堂:《文白异读和层次区分》,《语言研究》2009年第1期。
[10]徐越:《从宋室南迁看杭州方言的文白异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
[11]王洪君:《层次与断阶——叠置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的交叉与区别》,《中国语文》2010年第4期。
[1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中华书局,2013。
[13]徐越:《宋室南迁和杭州话的形成》,《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4]《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第四十一》,中华书局,1985。
[15]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人口数考索》,《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
[16]徐越:《宋室南迁和杭州话的形成》,《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7](明)郞瑛:《七修类稿》卷二百六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277页。
[18]潘洪钢:《杭州驻防八旗与太平天国》,《江汉论坛》2013年第12期。
[19]鲍士杰:《说说杭州话》,杭州出版社,2005,第51页。
[20]许勇强、邓雷:《近20年 〈水浒传〉作者研究述评》,《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21]鲍士杰:《说说杭州话》,杭州出版社,2005,第102页。
[22]吕叔湘:《现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第58~59页。
[23](明)郞瑛:《七修类稿》卷二百六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277页。
[24]〔美〕 罗杰瑞:《关于官话方言早期发展的一些想法》,《方言》2004年第4期。
[25]徐越:《杭州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方言》2007年第1期。
[26]房娜:《上海市小学生上海话和普通话语言态度研究》,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
[27]孙晓先、蒋冰冰、王颐嘉、乔丽华:《上海市学生普通话和上海话使用情况调查》, 《长江学术》2007年第3期。
[28]徐越:《从宋室南迁看杭州方言的文白异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
[29]耿志红:《杭州城市语言文化的构成与发展对策》,《杭州研究》2012年第3期。
[30]孙晓先、蒋冰冰、王颐嘉、乔丽华:《上海市学生普通话和上海话使用情况调查》, 《长江学术》2007年第3期。
[31]《杭州市志》(第一卷),中华书局,1995,第407页。
[32]《杭州市志》(第一卷),中华书局,1995,第408页。
[33]杭州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了周边吴语的白读音对杭州方言的渗透。http://www.hzstats. gov.cn/web/ShowNews.aspx?id=nvO2o6kIbto=。
[34]王健:《西方国家方言保护的启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35]“American Dialect Society 2011”,Dictionary of American Regional English,http://dare.wisc.edu.
[36]British Library,“Accents&Dialect”,http: //sounds.bl.uk/Accents⁃and⁃dialects.
[37]王健:《西方国家方言保护的启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38]陈红莲、张立平:《方言的生存现状及保护》,《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8期。
[39]黄晨:《浙江方言对英语学习的影响及对策》,《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40]《本市已有100多所中小学开设“上海话”课》,http://news.sina.com.cn/c/2013-05-24/081127 212239.shtml。
[41]罗杰瑞:《关于官话方言早期发展的一些想法》,《方言》2004年第4期。
[42]Richard Van Ness Simmons,Chinese Dialect Classification: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Harngjou,Old Jin⁃tarn,and Common Northern Wu,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1999.
(责任编辑 王立嘉)
∗ 杭州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杭州方言网络有声语料库建设研究”(A12YY03);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杭州方言网络有声语料库建设研究”(2012Z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