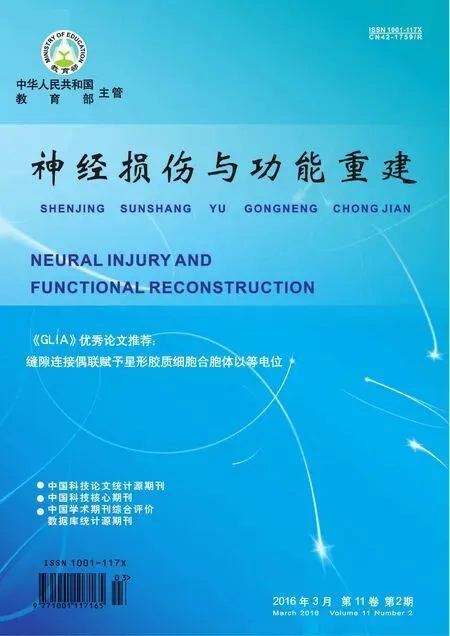早期或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症的研究进展
2016-04-04林婕李唯薇唐占英刘丹方国正胡志俊
林婕,李唯薇,唐占英,刘丹,方国正,胡志俊
早期或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症的研究进展
林婕,李唯薇,唐占英,刘丹,方国正,胡志俊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症(AIS)是发生在青少年生长发育期间以脊柱侧凸伴有三维旋转的骨质结构畸形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本文对早期、轻度AIS的进展、转归、临床表现进行综述。
脊柱侧凸;青少年;早期;轻度;椎旁肌;神经损伤
脊柱侧凸是一种发生在骨骼生长发育期间的脊柱向额状面偏曲至少10°的三维脊柱畸形,其中发生于10~17岁的青少年人群、且病因和进展机制不明的,称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症(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此病好发于女性,大量研究显示,男女患病率大约为1∶1.5[1]。AIS患者的身高相对于同龄人偏高,而体重偏轻,一部分患者容貌具有一定的特点。男性患者的发病率高峰出现在16岁,女性发病高峰出现在13岁[2]。
AIS的症状表现有隐匿性,AIS患者很少能察觉到不适,尤其是年纪偏小,轻度脊柱侧凸的患者(Cobb角<40°)。当患者出现双肩不等高、一侧肩胛骨隆起、骨盆倾斜时的外观改变时,才可能被周围的亲朋好友发现,一部分患者的发现主要来自于学校体检普查。AIS患者本人可能只会感受到久坐或站后腰部无力、背部肌肉紧张等不典型症状。因此,早期、轻度AIS患者的脊柱畸形很可能在患者毫无察觉下的情况下进展。
目前AIS的诊断主要以全脊柱站立位正位片Cobb角(Cobb>10°)为标准,以Risser征预测脊柱侧凸的进展程度。Lonstein[3]对大量AIS患者普查9年后发现,Cobb角与侧凸进展呈正相关,与年龄和Risser征呈负相关,如Cobb<20°,Risser征>Ⅱ度,仅有1.6%发生进展;20°<Cobb<30°,Risser征<Ⅱ,进展率却高达 68%。国内的文献报道结果与Lonstein类似,刘朝辉等[4]通过15年追踪随访204例Cobb>10°的AIS患者,发现消退29例(32.2%),减轻21例(23.3%),未变30例(33.3%),进展10例(11.1%)。Cobb角<20°的AIS多数不会进展。进展的危险因素包括:Cobb角>20°,女性,双胸弯、胸腰双弯、右胸弯型,侧凸顶椎旋转度≥Ⅱ度.但是有一些学者观点不同,他们认为即使AIS患者进入成年后,脊柱侧凸仍会进展,随着骨质成熟、年龄增长,以及在负荷、外伤、衰老等因素下,畸形的脊柱将发生凸侧肋椎关节关节的不同程度的脱位、畸形性骨关节炎、椎间关节僵硬、过早的骨质疏松样改变等。
一直以来,AIS的进展是以Riss征来判定的,Riss征>Ⅳ度,表示骨骼生长潜力较低,侧凸进展可能性较小。然而现在的文献却发现,有相当一部分AIS患者进入成年后,侧凸仍有发展。因此现在有研究者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Riss征不足以预测侧凸的进展,应以骨龄、颈椎骨成熟度判定椎骨旋转度判定脊柱旋转的症状[5]。Riss征在Ⅳ度以上,进展的可能性不大,但Cobb角>40°,每年进展超过5°的患者具有极高的进展危险。因此,对于仍有生长潜力的脊柱来说,需要每6月跟踪监察一次侧凸的进展。
1 AIS的病因
早期的研究认为AIS患者在胚胎时期就受到来自父母的影响,并认为可能的影响来自于父母不良的生活习惯[6],例如吸毒、嗜酒等。此外,母亲在怀孕期间患病、服药等影响胚胎发育的因素,血型、RH因子不相合等因素也有可能。一些临床观察发现高龄产妇容易娩出AIS患儿。一部分AIS患者也有不同的程度的特征性样貌。但是AIS的发生发展原因仍不清楚。
大量研究发现AIS的发生与遗传、前后脊柱生长失衡、异常生长模式、结缔组织[7]、神经肌肉、神经内分泌、骨密度[8]、微量元素如硒元素[9]的异常相关。朱峰等[10]通过对比研究手术中采集的软骨组织(髂软骨或棘突软骨)进行细胞培养,发现AIS组软骨细胞的OD值远小于正常组,因此认为能够促进正常软骨细胞增殖褪黑素却无法促进AIS患者软骨细胞的增殖,推断AIS患者中褪黑素信号通路调节软骨内成骨的过程可能存在异常。王其飞等[11]通过对AIS患者骨髓血全RNA进行Affymetrix 3'IVT表达谱芯片检测后,发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在成脂分化过程中有111条基因表达上调,189条基因表达下调,Western blotting结果显示Thrsp蛋白在脂肪细胞中高度表达,因此认为由Thrsp基因介导的MSCs成脂分化相关差异表达的300条基因可能参与AIS的发生和发展。周松等[12]通过鉴定和统计中国汉族人AIS组(512例)与正常组(512例)的人群IL-17RC基因rs708567和rs279545多态性位点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分布频率后,发现AIS组rs708567多态性位点GG基因型和G等位基因的分布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布频率;携带GG基因型青少年中AIS的发病率约为携带AG基因型青少年的1.5倍(OR值=1.55;95%CI1.45~3.11),由此认为IL-17RC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AIS的发生相关。马俊红等[13]通过对比AIS患者与正常人全血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发现AIS患者血清中硒元素含量(23.45±10.99)μg/L远低于正常人(57.91±47.83)μg/L,铁、铜、锌含量却无差异,认为硒元素缺乏可能导致脊柱侧凸,机理是硒元素缺乏将导致椎间盘胶原纤维和胶原蛋白合成障碍,降低脊柱稳定性。刘晓阳等[14]利用基因芯片筛选AIS患者外周血中差异表达的lncRNAs和mRNAs,发现AIS患者外周血中存在差异表达的lncRNAs和mRNAs,并推断lncRNAs可能通过调控mRNA的表达参与AIS的发病或发展。
2 生长发育
脊柱侧凸的病理性改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AIS患者的生长发育,研究显示,AIS患者在生长发育高峰期比健康同龄人高,但逐渐成熟后,生长缓慢,最终的身高较正常人无明显差异。上世纪80年代,Drummond等[15]发现AIS患者存在明显的发育迟缓,尤其是Cobb角>20°的人群。邱勇等[16]通过对48例女性单胸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症患者(T-AIS)与同龄健康青少年骨盆生长发育模式相比较,发现T-AIS患者的全脊柱、胸椎长度均显著超过正常青少年(P<0.05),T-AIS胸椎纵向生长的速度较腰椎生长速率快,骨盆的宽度和高度未见明显差异。AIS患者存在侧凸区域的椎体过度生长,并且导致脊柱不稳定。该研究还发现10~12岁的T-AIS患者真实全脊柱长度与T1~T2胸椎高度与正常人无差异,但>12岁的患者却均超过正常组。因此AIS患者存在明显与生长发育有关的异常生长。
3 骨性结构改变
AIS患者脊柱骨性结构改变包括椎体楔形变、骨密度下降、椎间盘楔形变、软骨生长板、椎体旋转等。大量研究发现AIS患者骨密度较正常同龄人降低,局部承受压力负荷的软骨生长板的纵向生长与脊柱侧凸进展呈正相关[17],而骨密度与骨组织塑形直接相关,因此骨密度降低极有可能增加AIS进展的风险,孙旭等[18]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轻中度AIS患者骨密度与侧凸进展的关系,发现骨量降低是脊柱侧凸进展的独立影响因素。
轻度AIS患者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椎体、椎间盘楔形变[19]。丁旗等[20]测量110例AIS患者的每个椎体的楔变角,并与Cobb角比较,发现Cobb角<40°的患者也有不同程度的楔形变,Cobb角>40°的患者椎体与椎间盘楔变角均显著大于Cobb角<40°(P<0.01)。而且根据以往研究报道,AIS患者脊柱椎体生长在侧凸两侧应力失衡的生长调控下,即生长板压力增加阻碍其生长发育,反之促进其生长,因此脊柱侧凸患者脊柱中存在不同严重程度的椎体与椎间盘的楔形变[21]。徐宏光等[22]测量37例AIS患者手术、支具治疗前后影像上的椎体、椎间盘的楔形变的角度,并与Cobb角对比,发现椎体和椎间盘的楔形变同侧凸的进展明显相关,与侧凸的程度呈正相关(r=0.69)。AIS患者椎体楔形变是椎体生长的力学调节作用的结果,由于力学的差异性,楔形变的出现也有特点,杨晓明等[23]通过量化比较AIS三维有限元模型应力值,发现脊柱侧凸节段中,椎体应力分布以顶椎区域集中,楔性变最为严重,楔变和应力向端椎逐渐减小的趋势。楔性变不仅以顶椎区域向端椎的分布,还根据主弯位置不同,表现其特异性,例如主弯在胸突的患者以椎体楔形变为主,而胸腰弯和主腰弯则却以椎间盘楔形变为主。
一些研究发现,AIS患者的椎弓根也有异常改变。王景明等[24]通过对比测量56例CT扫描重建的男性右胸弯AIS患者的胸椎两侧椎弓根的各项形态学指标后,发现主胸弯顶椎区凹侧椎弓根宽度小于凸侧,椎弓根尾倾角度小于凸侧。椎弓根矢状面宽度自头端向尾端逐渐增加,平均值范围为0.68~1.36 cm;轴面椎弓根宽度平均值范围为0.30~0.70 cm。冠状面椎弓根最小径略小于轴面椎弓根宽度,平均值范围为0.28~0.67 cm。
特发性脊柱侧凸的骨性结构改变涉及椎体、椎间盘、椎弓根、椎旁肌等形态、功能的改变,这些改变将促使AIS患者的脊柱稳定性低于同龄正常人,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乘车、运动中导致脊柱将承受轴向载荷,在正常人群中,脊柱不会发生旋转,但是由于AIS患者脊柱稳态下降,由此产生的失衡应力将促使脊柱内部的应力不平衡,因此继发脊柱椎体向额状面偏曲伴旋转畸形改变,因此在胸椎部易发生剃刀背、凸侧肩部高位移位与畸形变、肩胛骨本身的改变以及胸廓的结构异常,甚至影响骨生长与重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胸廓畸形变,在正常人体中,胸廓发挥着稳定胸椎的作用,其主要来源于肋椎关节对椎体的轴向稳定性的保护功能[25]。胸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胸椎侧凸以上椎体的旋转改变,李新峰等[26]通过收集AIS患者CT扫描数据,对比分析由此构建的有无胸廓的两种三维有限元模式后发现,负载后,胸廓结构对T1~T6存在明显的影响,对这些椎体的旋转角度与方向影响显著。李志鲲等[27]通过回顾性研究对比手术前后30例女性AIS患者胸椎和胸腰椎椎体矢状面旋转度与临床上获得的躯干倾斜角(ATI)以及Cobb角改变,证实躯干倾斜与脊柱的胸椎和胸腰椎横断面畸形的相关性,减轻躯干畸形能限制胸椎畸形。
脊柱侧凸导致的胸廓结构的异常改变可导致呼吸功能、血氧合作用和血流动力学系统的功能受损。对于腰椎,易促使腰椎生理前凸消失,甚至发生后凸畸形,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畸形的凸侧面侧弯增强部位出现侧方的小关节融合,动静态负荷将促使成年人畸形节段的过早退变,产生相应的疼痛症状[6]。以上改变将继发骨盆倾斜改变,导致双下肢不等长。或是继发颈椎曲度改变,加速颈椎的病理改变。
4 生物力学改变
AIS患者生物力学异于正常人,周旋等[28]应用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及足底压力鞋垫系统检测AIS患者的步态运动学与足底压力分布数据,并与同龄正常人比较,发现AIS组在运动中其足底压力表现出双侧不平衡现象,以主弯凹侧下肢支撑时的足底最大压力高于以主弯凸侧下肢支撑时的足底最大压力,认为AIS患者确实存在失衡的情况。
AIS患者生物力学的改变可能源自于两方面的改变,其一是脊柱侧凸以及生理曲度改变导致的,正常的脊柱在人体站立时其重力线应通过每个生理弯曲的交界处,例如颈胸、胸腰、腰骶结合处,重力由此通路将经过骶髂关节传递至下肢,椎间盘在此过程中发挥着缓冲振荡的作用。脊柱侧凸的形成导致重力线改变,人体脊柱两侧受力不均匀,椎旁肌发生相应改变。而且侧凸的形成以及椎骨的旋转促使生理弯曲改变,继而诱发生物力学的异常,促使椎间盘、椎体、椎旁肌结构功能的变化。其二,AIS患者本身的前庭-平衡功能的异常,脊柱侧弯患者不仅脊柱存在有别于正常人,小脑等区域也存在异常改变,一些研究发现脊柱侧凸患者的前庭功能功能异常,表现为平衡功能降低。1993年Byl等[29]通过比较50例AIS患者与正常人,发现AIS患者的平衡功能明显较正常人差。2010年香港学者shi等[30]通过对比观察20例AIS患者与正常人前庭功能,发现右胸弯AIS患者左侧前庭功能异常。全脊柱长弓性侧弯最常见的是躯干失代偿性倾斜。
5 椎旁肌改变
一直以来,人们对AIS患者的椎旁肌关注颇多。椎旁肌主要由背阔肌、下后锯肌、骶棘肌、横突棘肌、横突间肌、棘突间肌等肌肉组成,这些肌肉保证人体直立,保护脊柱与相关脏器,维持运动功能,最重要的是辅助呼吸功能。因此,椎旁肌的结构功能改变将导致脊柱功能损伤,诱发或加重脊柱侧凸,许多学者也在这方面进行大量研究。椎旁肌的改变目前有以下几种:横截面积、构成物、椎旁肌神经及终末神经支配、肌蛋白、褪黑素、微量元素受体、肌电活动的改变。人们发现AIS患者的椎旁肌与同龄正常人在结构功能方面不同,两侧椎旁肌的特异性改变也不例外,椎旁肌结构功能的改变与AIS有一定的相关性,是AIS患者侧凸曲度加重的原因之一。
此外,椎旁肌的作用还在于保证脊柱的柔韧性。Deviren等[31]研究发现AIS患者的脊柱柔韧性与其Cobb角、年龄呈显著性正相关,当Cobb角每增加10°时,脊柱的柔韧性降低10%,年龄每增加10岁,柔韧性降低5%。周旋等[32]对204例AIS患者(40°<Cobb角<105°)的脊柱柔韧性与年龄、Cobb角的相关性研究证实,女性AIS患者的年龄、Cobb角与脊柱柔韧性呈明显负相关(P=0.015,r=-0.22;P=004,r=-0.409)。脊柱柔韧性也与进展相关,Clamp等[33]发现年龄、月经初潮、主弯Cobb角及顶椎旋转度都会影响女性AIS患者的脊柱柔韧性,男性AIS患者则只受主弯Cobb角的影响,并且发现胸弯的脊柱柔韧性明显低于腰弯。
目前的文献虽然均偏向椎旁肌改变是继发性于脊柱侧凸的,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椎旁肌的病理改变并不是单纯的生物力学改变,或继发性改变,而是基因、细胞水平的原发性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脊柱侧弯患者经治疗后恢复正常的解剖结构后,仍会复发的原因之一。提早干预,可防止椎旁肌异常改变的启动,或是通过保守治疗保护残存的肌细胞,促使其有效代偿,阻止脊柱侧凸的恶性循环。
6 神经损伤
脊柱畸形并不能直接导致AIS患者神经根的损伤,脊柱侧凸导致的神经损伤是继发性损伤,主要涉及脊髓以及周围神经根。有学者认为脊髓向两侧发出的神经根在脊柱侧弯的影响下,围绕自己的纵轴发生旋转,同时在椎管内发生异常方向的折弯。侯刚等[34]通过对28例AIS患者横断面MRI图像测量顶椎区脊髓偏移和旋转情况后发现,脊柱旋转角度越大,脊髓越发偏向凹侧,AIS的发展过程中,脊髓会随着椎体的旋转而旋转,由于神经根或齿状韧带的牵拉,加重脊髓的偏移。随着畸形的加重,畸形的脊柱节段上方的2~3个节段平面相对应的脊髓血液供给系统被破坏,导致肢体、躯干脊髓感觉神经支配区皮肤感觉下降。逐年形成的僵硬的脊柱畸形促使患者继发椎管狭窄,加深脊髓池血供不足,进而继发神经功能损伤。尤其在畸形突然加重和脊柱突然长高的情形下,会骤发脊髓损伤。
其次,脊柱的畸形生长导致硬脊膜过度牵拉,而过度牵拉的硬脑脊膜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侧弯定点水平的椎管内空间。有临床研究发现,椎管狭窄主要集中在椎管凹侧部分的前后径上,并且在此位置的脊髓随之异常移位。脊髓受压后,相应的神经根损伤,继而发生神经营养障碍,如果时间较短,经过病因治疗可以缓解或消除由此产生的症状。这种神经根受压的症状多产生于腰凸患者。胸凸患者多见于植物神经功能、下颈段神经根、相应神经根的功能改变,例如心血管功能异常、皮肤温度调节失控、感觉异常等。王智伟等[35]通过对比68例右胸弯AIS女性患者与28例正常女性的交感神经皮肤反应(sympathetic skin response,SSR),发现AIS患者上肢潜伏期右侧/左侧比值(1.01± 0.05)显著大于正常年轻女性(0.98±0.04,P=0.036),女性AIS患者上、下肢潜伏期和振幅右侧/左侧比值在小角度(40°)和大角度(≥40°)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7 讨论
根据文献资料,AIS患者的脊柱侧凸畸形的发生发展可能与以上各种因素均相关,其机制可能为在诱导脊柱侧弯发生的因素下,脊柱侧弯的病理改变启动,患者脊柱骨性结构、椎间盘可能处于异常生长模式中,继而脊柱生物力学失衡,椎旁肌亦随之病变,即使椎旁肌代偿性的改变肌力或做功,却可能加剧了肌肉的损害,加之可能存在的前庭功能异常,反而进行性加重脊柱侧凸。此外,椎骨的旋转、椎间盘病变等可能致使脊髓、神经根受压或损伤,异常生长的椎旁肌也影响着穿梭其中的神经。文献显示,基础角度<30°的AIS患者进展小于基础角度>40°的AIS患者,笔者认为当侧弯较剧时,为维持人体平衡,椎旁肌所需做功相应增大,同样,受损的几率亦增大,脊柱进一步加重的可能性也越大,佐证了椎旁肌对脊柱侧凸的加剧作用。
骨骼生长潜力较大的患者中,脊柱侧弯进展也较快,由于可能存在自身的先后天的前庭功能异常,以及相关文献提及的脊柱侧弯患者的椎骨生长前后速度不一致的情况,因此,脊柱侧凸患者相比同龄正常人在异常模式中生长较快,尽管其中有一部分代偿和修复,但可能不足以修复损伤。因此,早期干预有其必要性,对于AIS患者的治疗,大多数观点认为当患者Cobb角>40°,每年进展超过5°时,或者严重影响重要脏器生长发育、造成功能障碍的建议手术矫正;而Cobb角<20°的患者一般建议观察随访,不做干预,但是根据本文的综述及推论,早期或轻度的AIS患者有其早期干预的必要性,笔者认为适当的保守治疗如运动疗法、推拿、导引操、手法、感觉统合训练等[36]可应用于早期或轻度AIS患者的治疗,促使患者在生长期,通过椎旁肌肌力改善、调整运动模式[37]、纠正生物力学失衡的作用,诱导脊柱及周围神经组织的代偿修复超越其破坏的程度,并且通过长期的坚持干预,维持动态平衡状态到患者骨骼成熟期,阻止脊柱侧凸的进展。
虽然很难修复已经形成的损伤。正常人幼年时期椎间盘内存在血供,损伤的椎间盘可由盘内血供提供营养支持用以修复,但是成年以后的椎间盘内却无此血供,因此对于幼年AIS患者,由脊柱侧凸畸形改变引发的椎间盘损伤仍可修复,损伤与修复尚可维持动态平衡,但成年AIS患者的损伤却无法修复。即使如此,对于轻度AIS患者尤其是接近成年的患者仍有其干预的必要性,因为轻度AIS患者直至成年时,侧凸角度虽然变化轻微,但是随着年龄、负荷、微损伤的累积,AIS患者会因异常的骨质结构异常生长模式而并发神经、肌肉、骨质相关的多种疾病。因此,即使早期、轻度AIS患者初期无不适的主诉,随着年龄,衰老、精神压力等因素,患有疼痛、双下肢无力,后背紧缩等感受却比正常人早发,并且持续时间更长。由此可见,对于早期或轻度AIS患者,通过保守治疗早期干预的临床意义仍旧显得相当重要。
[1]柯扬,何家雄,潘志雄.佛山市青少年脊柱侧凸患病率调查[J].实用医学杂志,2012,28:832-834.
[2]任凯,龚晓明,章荣,等.自贡市中小学生特发性脊柱侧弯患病率的调查与分析[J].四川医学,2014,35:853-855.
[3]Lonstein JE.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J].The Lancet,1994,344: 1407-1412.
[4]刘朝晖,李子荣,李中实,等.青少年轻度特发性脊柱侧凸的自然转归[J].中华骨科杂志,2003,23:611-614.
[5]张涤清,陈自强,李明.颈椎骨成熟度用于女性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骨骼生长发育评价的初步研究 [J].中华外科杂志,2011,49: 218-221.
[6]费申科著,陆明译.脊柱侧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44-45.
[7]Mahaudens P,Banse X,Mousny M,et al.Gait i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kinematics and electromyographic analysis[J].Eur Spine J,2009, 18:512-521.
[8]戚德胜,戴哲浩,吕国华,等.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与骨密度 [J].中国骨质疏松杂志,2014,27:589-592.
[9]柴耀凤,赵胜,郭锦丽.微量元素硒与特发性脊柱侧弯相关性研究[J].中国医学创新,2014,27:142-144.
[10]朱锋,邱勇,张兴,等.褪黑素信号通路对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软骨细胞增殖的影响[J].中国脊柱脊髓杂志,2013,23:156-160.
[11]王其飞,杨军林,范恒伟,等.Thrsp蛋白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MSCs成脂分化过程中的差异性表达和作用 [J].中国矫形外科杂志, 2015,23:263-269.
[12]周松,朱泽章,邱勇,等.汉族人群白介素17受体C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相关性[J].中国脊柱脊髓杂志,2013, 23:161-165.
[13]马俊红,郭锦丽,赵胜,等.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全血中硒元素和血清中铁、铜、锌元素含量的变化[J].脊柱外科杂志,2014,12:35-37.
[14]刘晓阳,邱贵兴,翁习生,等.长链非编码RNA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中的表达研究[J].中国骨与关节外科,2014,7:235-240.
[15]Drummond DS,Rogala EJ.Growth and maturation of adolescents with idiopathic scoliosis[J].Spine(Phila Pa 1976),1980,5:507-511.
[16]鲍虹达,刘臻,邱勇,等.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存在异常的脊柱骨盆生长发育模式[J].中华外科杂志,2014,52:350-354.
[17]Hung VW,Qin L,Cheung CS,et al.Osteopenia:a new prognostic factor of curve progression i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J].J Bone Joint Surg Am,2005,87:2709-2716.
[18]孙旭,朱泽章,邱勇,等.初诊骨密度对女性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早期支具治疗效果的预测价值 [J].中华外科杂志,2008,46: 1066-1069.
[19]Xiong B,Sevastik JA,Hedlund R,et al.Radiographic changes at the coronal plane in early scoliosis.[J].Spine (Phila Pa 1976),1994,19: 159-164.
[20]丁旗,邱勇,孙旭,等.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不同弯型患者椎体和椎间盘楔形变的差异及临床意义 [J].中国脊柱脊髓杂志,2011,21: 708-713.
[21]Stokes IA,Aronsson DD.Disc and Vertebral Wedging in Patients With Progressive Scoliosis[J].J Spinal Disord,2001,14:317-322.
[22]徐宏光,邱贵兴,王以朋,等.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椎体及椎间盘楔形变的影像学研究[J].中华骨科杂志,2008,28:465-468.
[23]杨晓明,顾苏熙,李明,等.特发性脊柱侧凸椎体楔形变有限元模型分析[J].中国矫形外科杂志,2008,16:1493-1495.
[24]王景明,张永刚,郑国权,等.中国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胸椎椎弓根形态学三维CT分析[J].中华骨科杂志,2013,33:459-466.
[25]Horton WC,Kraiwattanapong C,Akamaru T,et al.The role of the sternum,costosternal articulations,intervertebral disc,and facets in thoracic sagittal plane biomechanics:a comparison of three different sequences of surgical release[J].Spine(Phila Pa 1976),2005,30:2014-2023.
[26]李新锋,刘祖德,汪正宇,等.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胸廓对椎体轴向旋转影响的力学研究[J].中华外科杂志,2010,48:1646-1649.
[27]李志鲲,江远亮,王飞,等.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躯干倾斜与脊柱畸形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2014,29:436-438.
[28]游国鹏,杜青,陈楠,等.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步态运动学及足底压力特征分析[J].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2013,35:537-541.
[29]Byl NN,Gray JM.Complex balance reactions in different sensory conditions: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idiopathic scoliosis[J].J Orthop Res, 1993,11:215-227.
[30]Shi L,Wang D,Chu WC,et al.Automatic MRI segmentation and morphoanatomy analysis of the vestibular system i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J].Neuroimage,2011,54:S180-S188.
[31]Deviren V,Berven S,Kleinstueck F,et al.Predictors of Flexibility and Pain Patterns in Thoracolumbar and Lumbar Idiopathic Scoliosis[J].Spine (Phila Pa 1976),2002,27:2346-2349.
[32]周璇,杜青,赵黎,等.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静态平衡功能研究[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10,25:953-956.
[33]Clamp JA,Andrews JR,Grevitt MP.A study of the radiologic predictors of curve flexibility i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J].J Spinal Disord Tech,2008,21:213-215.
[34]侯刚,陈建庭,张宇,等.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顶椎区脊髓位置变化及其临床意义[J].中国脊柱脊髓杂志,2009,19:894-898.
[35]王智伟,邱旭升,王渭君,等.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交感神经系统活性左右侧对称性的观察[J].中国脊柱脊髓杂志,2014,24:923-927.
[36]胡春维,魏玉珊,孙艳萍,等.综合康复训练对孤独症儿童康复效果分析[J].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2015,10:131-133.
[37]林婕,唐占英,金晟,等.Bobath康复疗法的研究进展[J].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2014,9:515-518.
(本文编辑:王晶)
R741;R681.5
A DOI 10.16780/j.cnki.sjssgncj.2016.02.02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康复医学科
上海卫生系统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No.2013SY014);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研究生创新计划;上海市杏林新星计划(No.ZYSNXD011-RC-XLXX-201300 52)
2015-05-13
胡志俊hzjz106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