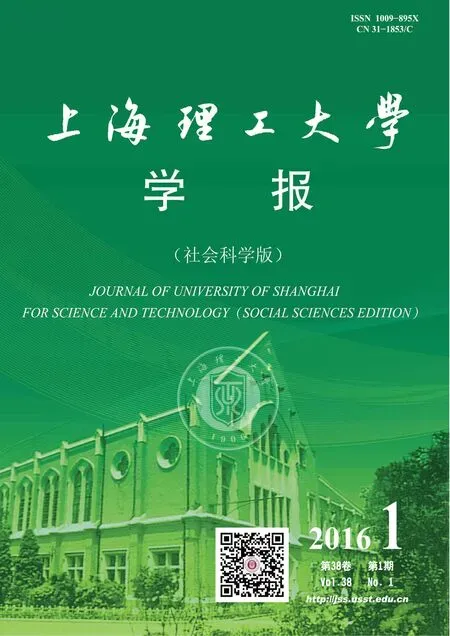论译者的翻译个性
——以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
2016-04-04冯全功
冯全功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 310058)
论译者的翻译个性
——以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
冯全功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 310058)
摘要:创作个性是文论中的重要论题,受之启发,提出翻译个性的概念,指译者基于自己对翻译活动的独特认识与体验而形成的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这就决定了译者翻译个性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译者与作者的个性差异,译作偏离原作的现象普遍存在,创造性偏离越明显,译文往往越有审美性与艺术性,译者的翻译个性也就越鲜明,如霍译《红楼梦》体例的更新与变异、整合补偿的广泛运用等。翻译个性有利于推进译作与译者本人的经典化进程,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论题。
关键词:翻译个性;创作个性;霍译《红楼梦》;经典化
翻译研究一直游走于众多学科之间,如语言学、文化学、哲学、美学、文论等,通过移植与改造其它学科的理论话语与学术资源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等理论话语无疑是基于翻译实践提出的翻译方法与翻译策略,然而,更多的理论话语却是从其它学科借鉴而来的,如中国早期的“文质”说、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传神”说、钱钟书的“化境”说、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刘士聪的“韵味”说,等等。这些论说都得益于中国传统的文论(画论)资源,在新的领域被赋予新的内涵,形成了极富活力的翻译理论话语。解释或拓展这些话语固然重要,学界多有讨论,有些也不乏真知灼见。文论中可利用的话语资源还有很多,如何引入新的话语资源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学术价值不容小觑。创作个性便是一个值得引鉴的文论话语,改造之后(翻译个性)可望为翻译话语系统增添一个新的理论术语,对文学翻译实践与批评以及整个翻译研究都不无启示。
一、从创作个性到翻译个性
创作个性在中国古典文论中也有所涉及,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体性”篇。其开篇言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1]67由此可见,“才、气、学、习这四种因素、或约为性情所铄与陶染所凝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作家的创作个性”[1]67。这种创作个性是发于内的,形于外便形成了作品的风格,所谓“吐纳英华,莫非性情”。虽然刘勰的“体性说”对后来的文论有很大影响,但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国内对创作个性的系统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其不仅继承了中国古典文论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借鉴了国外的相关文论资源。
创作个性是作家成熟的标志,那么到底什么是创作个性呢?王元骧认为创作个性就是作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的才能特征,包括表现自己题材的“特有的感受方式、理解方式和传达方式”[2]。徐放鸣认为“创作个性是艺术家在其长期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创造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又鲜明突出的创作独特性”[3],强调创作个性的审美性与独创性。童庆炳认为:“所谓艺术家的创作个性,既包含了艺术家先天所有的气质悟性、情绪记忆、形象思维、意志冲动等特性,又包括了艺术家在后天实践中形成的生活经验、思想倾向、趣味理想、艺术能力等精神特点。总的说,创作个性是指在一定生理基础上并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艺术家个人的独特的较为稳定的全部心理特征的总和。”[4]6陈宪年认为“创作个性是一种审美个性,是作家反映、认识生活的独特方式,是他们特有的心理体验和思维运行方式”,并强调作家“审美潜能结构”的独特作用[5]。综观各家言论不难发现,创作个性主要是指作家的一种具有独创性与审美性的心理特征或思维方式,体现了作家的气质、才情、体验、价值观、人生观等。曾奕禅把创作个性的特征归为五个“结合”[6],即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自觉性与自发性相结合、一般性与独创性相结合、稳定性与变异性相结合、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充满了辩证色彩,有利于全面认识创作个性。在众多特征之中,独创性,即“艺术家对生活的独特的认识和反映生活的独特的艺术表现方法”[6],是创作个性最基本的特征,没有独创性就没有创作个性,也没有作家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另外,作家的创作个性对作品的风格具有决定意义,作品风格反映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创作个性的主要载体[3],刘勰所谓“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是也。
作家有自己的创作个性,翻译家也有自己的翻译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基于自己对人生或生活独特的体验与认识而形成的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翻译个性则是翻译家基于自己对翻译活动的独特认识与体验而形成的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主宰着他们的翻译观及其译作风格的形成。翻译个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者创作个性的再现上(表现为再现原作风格),更体现在对作者创作个性的创造性偏离上,是译者再现作者创作个性与表现自我创作个性的辩证统一。“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刘勰《文心雕龙》),若用刘勰的“物”借指作者的创作个性,“心”便是译者的翻译个性。再现作者的创作个性要求译者“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7]。这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泯灭译者的翻译个性,做一位“隐身人”,但这并不排除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有时可能是一个更艰辛的过程。然而,由于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译文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文,再现原文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文学翻译。在文学翻译这种典型的再创造活动中,译文对原文的创造性偏离越多,译者的翻译个性往往越强。当然,这种创造性偏离是在无法忠实再现原文(或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者是为了提高译文本身的可读性与艺术性而进行的修辞改造或创造性叛逆,前提是译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这与译者的审美心理有关,体现了译者的才能与性情。翻译个性不仅可通过对原作的创造性偏离窥视,也可通过与其它译者的对比得以体现,尤其是同一原文的不同译者。翻译个性不同于译者风格,前者是内在原因,后者是外在表现。然而,从翻译风格可推测出译者的翻译个性,所谓“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刘勰《文心雕龙》)是也,还可从译者的理论著述以及其它相关言论中得以印证。总之,要想窥探译者的翻译个性,分析译作的艺术特色是最便捷的方法,同时还可辅以其它相关认识手段。
翻译研究持续发展的动力莫过于对其它学科资源的有效借鉴与充分利用。从创作个性到翻译个性,就像从“文笔”到“译笔”[8]381-392一样,体现了翻译学界对文论资源的自觉借鉴与主动吸收,可望为文学翻译实践与批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霍克思的翻译个性在《红楼梦》英译中的表现
大多有造诣的翻译家都有自己的翻译个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的喜欢凸显自己的翻译个性,有的喜欢掩藏自己的翻译个性(传达作者个性,再现原作风格)。有的有自己独特的译论以及相应的译作,有的有大量的译作却很少发表自己的译论,这也促成了翻译个性的隐显之别。许渊冲的翻译个性就十分明显,从他的译论与译作中都很容易识别。杨宪益的翻译个性就比较隐蔽,他强调“必须非常忠实于原文”,“过分强调创造性是不对的”[9]6,所以他的译作大多四平八稳(如《红楼梦》英译本),相对缺乏自己独特的个性。相对而言,霍克思 (D.Hawkes) 在翻译《红楼梦》时表现出的翻译个性更明显,更具艺术性与审美性,再加上母语译者身份以及译作由国外权威出版社(企鹅出版社)出版等客观因素,所以“一问世即受到西方广大读者的喜爱,同时拥有专业汉学家、普通知识分子以及文学爱好者三个层面的读者群”[10]。那么,霍译《红楼梦》的独到的艺术特色到底有哪些具体表现呢?
(一)体例的更新与变易
霍译《红楼梦》的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体例的更新与变易上。具体包括:1)书名的翻译与分卷并且加以命名。霍译书名为TheStoryoftheStone[11],在封面后面的介绍为TheStoryoftheStone(c.1760),also known asTheDreamoftheRedChamber…霍克思舍弃“红楼梦”而选择“石头记”作为书名,体现了自己独到的审美眼光与版本意识,也避免了与正文中“变红为绿”的翻译策略发生冲突。五卷本的各卷命名依次为:The Golden Days,The Crab-Flower Club,The Warning Voice,The Debt of Tears,The Dreamer Wakes。这种根据小说内容添加的分卷书名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红楼梦》译文本身的艺术性,对其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应该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杨译是三卷本,各卷40回,霍译是五卷本,各卷根据小说情节与故事内容进行切分,回数并不固定。2)霍译本每卷都有卷前介绍与卷后附录以及一些其它信息,如人物关系、家族关系等,这些信息增加了译本本身的“丰厚度”,为译文读者提供了有用的阅读(交际)线索。在各卷介绍与附录中,霍克思与闵福德还结合红学研究的相关内容(如新红学),对作者及其家世、原文本身的人物与时间矛盾、各种游戏风俗以及自己的翻译策略等也有相关介绍,体现了霍译《红楼梦》艺术性与学术性兼顾的翻译思想。王宏印[8]245-253也曾以霍译为例,强调文学翻译体例(体制)“更易与创新”的重要性。
(二)整合补偿的广泛运用
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这就需要对翻译进行补偿,包括加注补偿、整合补偿等。其中,整合补偿指在目的语文本中,把所补偿的内容和译文本身的内容有机地融合起来而不加任何有关补偿的标记。霍译《红楼梦》中存在大量整合补偿,具体可分为语言上的整合补偿、文化上的整合补偿和诗学上的整合补偿[13]。有的学者把这种整合补偿称之为“扩展译法”[14],有的则称之为“细节化”[15]。这种补偿翻译有利于弥补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的语境视差,为译文读者充分解读原文提供了必要的语境,并且不会打断读者的阅读思路,同时又有效地传达了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质。诗学上的整合补偿(如根据原文语境添加的一些类似于英语行文的段落主题句)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译本本身的可读性与逻辑性。偶尔使用整合补偿是译者的常用技巧,但像霍译运用如此广泛的还并不多见,这也是“深度翻译”的具体表现。杨译采取的主要是加注补偿,加注补偿是译者常用的翻译策略。另外,霍译对整合补偿的大量运用使其译文风格整体上呈现出“趋繁”的倾向(相对原文与杨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译文风格对原文的“偏离”,但也正是这种创造性“偏离”体现了译者的翻译个性。
(三)形貌修辞的巧妙使用
形貌修辞是一种旨在利用字体字形、排列方式、标点符号、图形图表等来提高文本视觉效果的修辞方式,在文学创作中多有应用。霍译《红楼梦》中也存在大量的形貌修辞,并且运用得都比较巧妙,视觉效果也比较明显,很好地实现了强调译文相关内容的语用目的。霍译中的形貌修辞具体包括字体字形的变易(如大小写、斜体等),排列方式与标点符号的独特运用以及副文本(如前言、附录)中的图表图形等。如霍译中字母全部大写的“GO AND TELL MY PAGES”[11]147,叹号连用的“…I send you this bag it shows you what I dream of !! PLEASE KEEP IT!!!”[12]477根据具体语境更改字体的“I will!”(字体比其它行文小一号,凸显了小耗子精的娇小与柔弱),等等。霍译诗体有的用居中排列的方式,视觉效果十分明显,如对第28回云儿、冯紫英、蒋玉菡等曲子的处理。霍译《红楼梦》中的形貌修辞体现出很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具体语境中的认知凸显度十分明显,为其译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贡献了一份力量。杨译中也有形貌修辞的存在,如斜体的运用(多是对人称代词加以标识)等,但远非霍译运用得如此广泛与丰富。译界有“还形式以生命”[16]180-231的命题,霍译对形貌修辞的巧妙使用便是很好的榜样。
(四)散体向诗体的转换
诗体在这里主要指有分行与押韵的行文,这也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形式标志。《红楼梦》也可视为是一部诗化小说,行文兼融了大量的诗词曲赋,诗意时时扑面而来。霍译一般把原文的诗体译为诗体(译文也分行与押韵),也有很多把原文的散体(包括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译为诗体的做法,增强了原文的诗意效果与译文的形式美感,同时也从形式上突出了相关话语的具体内涵。如把原文的“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译为“Sometimes by chance/A look or a glance/May one’s fortune advance”[11]68;把描写宝钗的“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译为“…to some her studied taciturnity/might seem to savour of duplicity;/but she herself saw in conformity/the means of guarding her simplicity”[11]188;把袭人说的“就是朝廷宫里,也有定例”译为“Even in palace hall/Law is the lord of all”[11]387;把秦可卿说的“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译为“The full moon smaller grows,/ Full water overflows”[11]255,等等。赵长江、李正栓曾对此类现象做过专门研究,肯定了霍译这种转换梯度“由易至难”的做法[17]。显然,这种散体向诗体的转换在译界极为罕见,霍译的转换也体现了他在翻译过程中迎难而上的勇气与独特的审美眼光。
(五)诗体韵律的严格遵循
诗歌翻译一般可分为韵体(押韵)和素体(不押韵)两种,霍译《红楼梦》中诗歌的最大特点是基本上严格押韵(有时原诗即使不押韵也被译为韵体诗),如第5回的人物命运诗与曲子、第28回的“女儿诗”、第50回的即景联诗以及原文中众多引用的古典诗词(原文引用的诗词本身一般不押韵),等等。如《飞鸟各投林》的韵脚为ABABCCDDEEFFGG,《晚韶华》的韵脚为AABBCCDEDEFGFGHIHIJJ,第28回的宝玉等五首“女儿诗”的韵脚全是AABBCCDD的形式(其中奇数句的措辞完全一样,如“The girl’s upset”,“The girl looks glum”,以照应原文的“女儿悲”、“女儿愁”等)。第76回黛玉、湘云与妙玉的“即景联句”霍译一韵到底(如 emulate,pulsate,celebrate,scintillate,eight,gestate 等),并且把押韵与情节关联起来,实为难能可贵。再如把引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译为“Each grain of rice we ever ate/Cost someone else a drop of sweat”[11]292,把王安石的“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译为“What brush could ever capture a beauty’s breathing grace?/The painter did not merit death who botched that lovely face.”[12]258对比原文与译文,可以发现霍译诗体的主要策略是“据意寻韵”并辅以“因韵设意”,同时还有一些通过改变故事情节创设韵脚的,整体效果十分理想,在小说中也显得比较圆融调和。只要不影响小说思想性的传达(如对人物命运的暗示等),这种诗歌翻译的设韵策略也是值得提倡的,有利于提高小说的整体艺术性。杨译红诗也有部分是押韵的,但更多的是译为素体,艺术个性不如霍译那样明显。
(六)附加疑问句的增添与再现
附加疑问句,又称反意疑问句,是英语中常见的疑问句型,在霍译《红楼梦》中也大量存在(前80回共有186个),表达各种语用功能,如寻求证实、表达情感、请求命令、强调反驳等。这些附加疑问句绝大多数是从原文中的非附加疑问句转化而来(只有16个是再现的)。如霍译的“Crying won’t make it any better.You came here to enjoy yourself,didn’t you?And now you’re here you’re miserable,right?Then the thing to do is to go somewhere else,isn’t it?”[11]408原文为:“宝玉道:‘难道你守着这件东西哭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要取乐儿,倒招的自己烦恼。还不快去呢。’”[18]235霍译添加的三个附加疑问句就非常合适,使人物语气更加委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宝玉不分尊卑(如兄弟之间)的性格特征,对塑造人物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原文中的“难道你守着这件东西哭会子就好了不成?”也是一个附加疑问句,译者并没有再现,而是把下面的两句话转化为三个附加疑问句,体现出很大的灵活性,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译文作为独立文本的价值[19]。另外,附加疑问句的原型功能是使语气更加委婉,具有典型的女性特征,霍译中大量存在的附加疑问句也正好与《红楼梦》这部主要描写女性的小说相吻合。
(七)文化负载词的杂合策略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学界一个重要的话题,尤其是在提倡异化策略、存异理论、文化传播的当代语境中。有些论者往往抓住霍译对一些文化负载词的归化处理不放,以偏概全,草下结论,认为霍译主要是一种归化策略,不利于传播中国文化,从而对之进行负面评价。
霍克思把“悼红轩”译为“Nostalgia Studio”,把“怡红院”译为“Green Delights”,把“阿弥陀佛”译为“God bless my soul”,把“龙王”译为“The King of the Ocean”,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归化处理,但霍译中还有很多对文化负载词的异化处理,评论者却往往视而不见(抑或没有发现),如霍译(包括闽译)中共出现了54个“dragon”的意象,158次“red”,也曾把“阿弥陀佛”译为“Amitabha”。其实,霍译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整体上采取的是一种杂合策略,既有归化也有异化(且后者也可能是主要的),这种杂合策略在特定的跨文化交流语境中似乎更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毕竟文化传播不是硬性的单向传递,其更需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洪涛[20]曾针对霍译《红楼梦》中的宗教文化负载词批判了某些论者“孤立取义”的现象,从语篇整体的视角揭示了霍译的“杂合现象”。
(八)独具特色的翻译底本
《红楼梦》版本众多,有脂本系统,如甲戌本、有正本、庚辰本等,还有程本系统,即程甲本与程乙本,版本差异有时比较明显,艺术性也有区别。这对译者的底本选择构成了一定的困难。霍译《红楼梦》的底本主要是程乙本,同时也广泛参照其他版本,如程甲本、庚辰本、甲戌本、俞校本、戚序本等,择优选择,取长补短,体现出很强的自主性以及敏锐的审美眼光。这从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笔记》中也可略窥一斑。霍译中有这么一句:“Jia Zheng himself was deeply affected,and tears as round as pumpkins rolled down both his cheeks”[21]150,其中程乙本为:“贾政听了,那泪更似走珠一般滚了下来”[18]400,庚辰本(包括有正本)为:“贾政听了,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22]457。可见此处霍译舍程乙本而取脂本,比喻、夸张(泪如滚瓜)同时再现,艺术性较程本更为可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翻译《红楼梦》时多底本相互参照的必要性。若把霍译《红楼梦》进行还原,便可得到一个独特的霍氏《红楼梦》版本,这在学界基本上已经实现。关于霍译底本选择的问题,学界多有探讨,此不赘述。
三、翻译个性与译者的经典化
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本在国外的传播比较广泛,影响也比较大。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霍氏的翻译个性,表现在译文中便是修辞改造或创造性“偏离”较多,提高了霍译本的艺术性及其作为独立文本的价值。当然,除了上述艺术特色外(主要是基于笔者的阅读体验总结而出),霍译本还有很多特色值得挖掘与深入研究,如修辞格的增添与改造、人名的翻译策略等。霍氏把“跪在地上乱颤”译为“The boy knelt down…,trembling like a leaf”,把“宝玉是相貌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译为“Bao-yu is like a bad fruit—good to look at but rotten inside”等,便是增添了一些比喻修辞格。霍译的这些艺术特色使其显得灵性十足,可读性很高,并且极具研究价值。霍译《红楼梦》的翻译个性可概括为:1)重视小说思想性传达的同时,更加注重艺术性的提升与改造;2)照顾原文与作者的同时,更加注重读者的接受能力与译文本身的文学性;3)致力于再现小说文学性的同时,兼顾译文的学术性与“丰厚度”;4)尽力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适当地融合西方文化,体现了文学翻译的杂合性。
译作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译者同样也会经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毫无疑问,霍译《红楼梦》是一部经典译作,也奠定了霍克思作为经典译者的地位,这主要得益于霍氏鲜明的翻译个性。综观中外文学翻译史,大凡青史留名的译者,其翻译个性都是很强的,尤其是“创造性叛逆”比较多的译者,如菲茨杰拉德 (E.Fitzgerald) 英译的《鲁拜集》、庞德 (E.Pound) 英译的《神州集》、严复汉译的《天演论》、朱生豪汉译的莎士比亚戏剧、许渊冲英译的中国古典诗词,等等。再现原作风格(忠实于作者的创作个性)也会促成经典译作与经典译者,然而,由于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表现与彰显译者个性似乎更有利于译作与译者的经典化进程,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谢天振对“创造性叛逆”的命题多有论述,其表现之一便是“个性化翻译”[23]75-79。个性化翻译,归化也好,异化也好,改写也好,都是译者翻译个性的具体表现。如果把“创造性叛逆”视为译者的一种审美心理机制的话,其与翻译个性的概念便比较接近了(后者涵盖前者,但狭义上的翻译个性似乎也可等同于“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译介学强调译作的接受与传播,译者的经典化便是在其译作的接受与传播中形成的。试想,如果霍译《红楼梦》没有那么多明显的“创造性叛逆”,没有体现自己鲜明的翻译个性,没有相对广泛的读者群体,霍克思《红楼梦》英译者的经典地位似乎是难以确立的。译作的经典化造就译者的经典化,译者的经典化也促进译作的经典化,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换言之,经典译作一般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与审美性,具有很高的作为独立文本的价值以及研究价值,经典译者也藉此而生,并进一步巩固经典译作的经典地位。译者与译作的经典化有外部因素使然,但更重要的则是内部因素,即译者翻译个性的存在及其表现在译作中的审美特质。
如何才能促成译者的经典化呢?第一,要认识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本质,彰显自己的翻译个性。真正的文学翻译不可能是对原作的简单复制,“信于原本,基本照搬,不作或很少作翻译处理或艺术处理”,“忽视乃至否定文学翻译亦需发挥译者的创造性,亦需有译者的艺术个性”[24]。真正的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不是拜倒在原作前,无所作为,也不是甩开原作,随意挥洒,而是在两种语言交汇的有限空间里自由驰骋”[24]。所谓“有有我之译,有无我之译。有我而精神出,使其言皆若出于我之口,其意皆若出于我之心,上焉者能成高格,时见精彩。无我之译,是原作简单的复制,历来不少见,惜乎纷纷落马”[24]。这就要求译者在“有限空间里”发挥自己的翻译个性,“取熔经意,自铸伟辞”,使译文达到一种“不信而信”,“隔而不隔”的圆融境界。第二,译者要树立自己的翻译观与审美观,逐步建立自己的翻译个性。文学作品都具有审美性,译者也要有自己的审美观,以便敏锐地感知原作的审美特质,创造性地再现到译文之中。翻译观的形成首先要对文学翻译的本质有所认识,然后才是相应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手段。许渊冲的翻译个性就十分鲜明,这与他的翻译观(外在表现)亦密不可分,尤其是他提出的“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译学理论。许氏理论强调发挥译语优势,与原作进行竞赛,通过“三化”(浅化、等化与深化)方法(再)创造出“三美”(音美、形美与意美)之译文,从而使译文读者“知之”、“好之”、“乐之”[25]241-242。虽然许渊冲的译学理论(包括他的译作)饱受争议,但谁又能否认其独具特色的翻译个性?谁又能否认许渊冲作为译者的经典地位呢?这种张扬自己翻译个性的做法理应受到尊重。第三,译者有了自己的翻译个性,还要为充分发挥自己的翻译个性提供实现条件,设法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审美素养、信息素养等。翻译,犹如写作,需要译者有敏锐的信息感知能力与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尤其是文学翻译。唯有充分理解了原作的意义与美质,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方能“下笔抒词,自善互备”[26]202。当然,理解是基础,表达才是目的。霍译《红楼梦》之所以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语言功底(表达能力)十分到位,译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美国翻译家葛浩文 (H.Goldblatt) 也经常阅读英文小说,“看他们如何遣词造句”以便“从中学习”,并建议汉译英的人“要多读些英语书籍”[27]。葛浩文作为经典译者,作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首席翻译家,恐怕与他本人较高的语言能力与文学素养很难分开吧。总之,译作要想成为经典译作,译者要想成为经典译者,都需要译者修炼自己的“内功”,逐步建立并充分发挥自己的翻译个性。
四、结束语
虽然创作个性与翻译个性本质上都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两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前者是原创性的,后者是衍生性的;前者主要基于作家对人生的独特认识与体验,后者主要基于译者对翻译本身的独特认识和体验;前者的表达主要受制于作家的语言运用能力,后者的表达要受原作本身以及译者的语言运用能力的双重制约;前者主要是作家针对其他作家而言的,后者主要是译者针对所译作家以及其他译者而言的。强调翻译个性并不是提倡滥用翻译个性,或者把任何偏离原文的现象都视为译者翻译个性的表现,只有创造性偏离,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的偏离,能够提高译文审美性的偏离,才是译者翻译个性的外在表现。
翻译个性研究的意义主要包括:1)有利于突破翻译忠实观的局限,肯定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鼓励译者建立并发挥自己的翻译个性;2)有利于批评者的视点从修辞再现转移到修辞改造,挖掘译作的艺术特色,把译文视为独立的文本进行批评;3)有利于从整体上对翻译家个体进行研究,从翻译家的译作和译论出发探寻其翻译个性;4)有利于区分译作特色形成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从译者的翻译个性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对译作进行综观研究;5)有利于把文本研究、主体研究与文化研究整合起来,最终落脚在译者研究;6)有利于研究者继续向其它学科借鉴话语资源,推动翻译理论的建设与发展。
参考文献:[1]王元化.王元化文论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2]王元骧.论创作个性[J].文艺理论研究,1987(6):32-38.
[3]徐放鸣.论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的区别和联系——兼谈中国古代“文如其人”说的得与失[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7-12.
[4]童庆炳.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5]陈宪年.创作个性与人物个性[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6(1):85-89.
[6]曾奕禅.论创作个性的基本特征[J].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1-7.
[7]王佐良.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次专题翻译讨论会上的发言[J].中国翻译,1987(5):2-4.
[8]王宏印.新译学论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9]杨宪益.杨宪益对话集:从《离骚》开始,翻译整个中国[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10]王丽耘.“石头”激起的涟漪究竟有多大?——细论《红楼梦》霍译本的西方传播[J].红楼梦学刊,2012(4):199-220.
[11]Hawkes D.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1)[M].London:Penguin Group,1973.
[12]Hawkes D.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3)[M].London:Penguin Group,1980.
[13]冯全功.霍译《红楼梦》中的整合补偿及其对译文风格的影响[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4):9-15.
[14]洪涛.解码者的渠道与《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扩展译法”[J].红楼梦学刊,1997(3):290-307.
[15]谢军.霍克斯英译《红楼梦》细节化的认知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16]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17]赵长江,李正栓.汉语散体译为英语诗体转换研究——以霍译《红楼梦》为例[J].中国外语,2011,8(2):87-92.
[1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底本为程乙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19]冯全功.霍译《红楼梦》中附加疑问句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22(1):107-110.
[20]洪涛.《红楼梦》译论中的孤立取义现象和“西方霸权”观念——兼谈霍译本的连贯和杂合 (hybridity)[J].红楼梦学刊,2011(6):290-311.
[21]Hawkes D.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2)[M].London:Penguin Group,1977.
[2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底本为庚辰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3]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4]罗新璋.释“译作”[J].中国翻译,1995(2):7-10.
[25]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6]严复.《天演论》译例言[C]∥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7]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1):57-60.
(编辑: 朱渭波)
On the Translator’s Individuality:Exemplified by D.Hawkes’ Translation ofHongLouMeng
Feng Quang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Abstract:A writer’s individuality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literary theory,and this paper,enlightened by writer’s individuality,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ranslator’s individuality which refers to a translator’s unique esthetic and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based on his or her unique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Due to the different individualities of the writer and translator,there are bound to be deviations of the translated text from the source text,which proves the existence of the translator’s individuality.Generally speaking,the more evident and creative the deviations,the more prominent the translator’s individuality,as can be seen from the unique artistic features of D.Hawkes’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A translator’s individuality helps to accelerate the canonization process of both the translator and the translated works and it also provides a fresh topic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Keywords:translator’s individuality; writer’s individuality; Hawkes’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 canonization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16.01.005
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16)01-0021-07
作者简介:冯全功(1984-),男,讲师。研究方向: 《红楼梦》翻译研究、翻译修辞学、职业化翻译、生态翻译学。E-mail:fengqg403@163.com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5NDJC138YB);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5YJC740015)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14-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