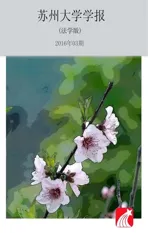论中国引入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法律障碍与突破进路—基于中国自贸区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构建的几点思考
2016-04-04刘晓红
刘晓红 王 徽
论中国引入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法律障碍与突破进路—基于中国自贸区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构建的几点思考
刘晓红*王徽**
国务院《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已颁布一年多,如何落实好该方案中关于“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的条款,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鉴于我国现行仲裁法律规范的滞后性,无论是在入驻前,亦或是在入驻后,国际仲裁机构在我国开展仲裁服务均存在障碍和诸多不确定因素。具体涉及约定外国仲裁机构在华仲裁的协议效力、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以及国际仲裁机构的市场准入等问题。为了更好地落实《深化改革方案》,需以自贸区为试验平台,加快构建相关配套制度,如明确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准入条件、摸索国际仲裁机构入驻区内的多元模式、调整《仲裁法》部分条款在区内的适用、明确“仲裁地标准”,以及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等。
国际商事仲裁;自贸区;国际仲裁机构
一、问题的提出
纵观诸多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多边及双边条约,其中争议解决机制条款始终占据重要席位。就争议解决而言,各方均强调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的构建,这俨然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和潮流。国际商事仲裁作为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中的一种方式,其在各国均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是重要的国际商事仲裁法域,《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下称《仲裁法》)颁布并生效至今已有20年。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共受理商事仲裁案件逾10万件,①林一飞:《业内:仲裁已悄然成资本市场解决争议主要方式》,载经济网-中国经济周刊:http://www.ceweekly.cn/2015/0126/ 102558.shtml,访问时间:2015年5月15日。2015年全国仲裁受案量更是突破了13万件。②《2015年全国受理仲裁案件136 924件增20%》,载法制网:http://www.legaldaily.com.cn/Arbitration/content/2016-03/29/content_ 6545612.htm?node=79488,访问时间:2016年4月12日。一方面,这表明我国仲裁业硕果累累,商事仲裁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较之于动辄成百、上千万的诉讼案件,商事仲裁在我国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此背景下,作为多元争议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我国商事仲裁的创新与发展也迎来了崭新局面。特别是,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以设立上海自贸区仲裁院、出台自贸区仲裁规则等为代表的改革和创新成果接踵而至。
2015年4月,国务院《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深化改革方案》)的发布,标志着上海自贸区建设正式进入“2.0时代”。①《专家解读上海自贸区深化改革方案》,载中国证券网: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20150420498718042.html,访问时间:2015年5月19日。令人关注的是,《深化改革方案》明确指出:“进一步对接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规则,优化自贸试验区仲裁规则,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提高商事纠纷仲裁国际化程度。探索建立全国性的自贸试验区仲裁法律服务联盟和亚太仲裁机构交流合作机制,加快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透过这段规定,可以看到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引入将会为未来我国商事仲裁的国际化发展注入新的元素。截至2016年6月,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和国际商会仲裁院(ICC)已分别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办事处。但这是否意味着国际仲裁机构未来在华开展业务就畅通无阻呢?换言之,在现行的中国仲裁法律体系下,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究竟有哪些法律障碍?为此,本文拟具体分析国际仲裁机构入驻前和入驻后的若干法律问题,并藉此提出相关建议。
二、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法律障碍
事实上,早在《深化改革方案》出台之前,我国仲裁实践中便已存在国际仲裁机构在华开展仲裁的相关尝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相关实践的合法性不甚明朗。随着《深化改革方案》提出“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国际仲裁机构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再次引发了仲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切。下文拟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相应的分析:
(一)境外仲裁机构入驻前存在的法律问题
1. 涉国际仲裁机构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
在境外仲裁机构入驻以前,国际仲裁机构在华仲裁需要面临的一大法律问题是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对于国际商事仲裁而言,仲裁协议的效力不仅关系到管辖权,也关系到裁决效力等一系列议题。对此问题以下案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件一:旭普林公司案②参见无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04)新民二初字第154号民事裁定书。
德国旭普林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旭普林公司”)与中国无锡沃可通用工程橡胶有限公司(下称“沃可公司”)于2000年签署了工程承包合同。合同中争议条款如下:“Arbitration:ICC Rules,Shanghai shall apply”。案件的主要争议在于该仲裁协议的有效与否。2004年9月2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无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最终做出了否定仲裁条款效力的裁定。理由是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确认仲裁条款效力准据法的情况下,根据确认仲裁条款效力准据法的一般原则,应当按照仲裁地的法律予以认定,即本案应根据我国法律确认所涉仲裁条款的效力。根据我国《仲裁法》规定,有效仲裁条款应当同时具备仲裁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仲裁机构三方面内容。本案所涉仲裁条款从字面上看,虽有明确的仲裁意思表示、仲裁规则和仲裁地点,但并未指定仲裁机构。因此,法院判决该仲裁条款无效。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四他字第23号。
案件二:瑞士德高钢铁公司案①参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甬仲监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
2003年1月23日,宁波市工艺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宁波公司”与瑞士DUFERCOS.A.(下称“瑞士德高钢铁公司”)在宁波订立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仲裁条款中文版载明:“一切因执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执,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如果经协商不能得到解决,应提交给仲裁地位于中国的国际商会仲裁委员会,按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进行仲裁。该仲裁为终局仲裁,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除非仲裁委员会另有决定,由败诉一方承担。”②该条款英文版为:“Arbitration:All disputes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act or the execution thereof shall be settled by friendly negotiation. If no settlement can be reached the case in dispute shall then be submitted to The Arbit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the award of which be accepted as final and binding upon both parties. The fee for arbitration shall be borne by the losing party unless otherwise awarded by the Commission.”双方争议产生后,ICC管辖了该案,并做出了不利于宁波公司的裁决。此后,由于宁波公司拒不执行裁决,瑞士德高钢铁公司遂向宁波市中院申请执行。期间,宁波公司提出了仲裁协议无效的抗辩,但遭到了宁波中院的驳回。其主要理由是宁波公司在收到ICC仲裁庭关于案件《受理事项书》和《临时时间表》后,没有对ICC仲裁庭的管辖权和依据ICC规则进行仲裁程序提出异议。根据ICC规则和《仲裁法司法解释》第13条的规定,宁波公司丧失了主张仲裁协议无效的权利。最终于2009年4月22日,宁波市中院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下称《纽约公约》)执行了该裁决。
案件三:龙利得包装印刷案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BP Agnati S.R.L.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的复函》([2013]民四他字第13号)。
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下称“龙利得公司”)与BP Agnati S.R.L.(下称“BP公司”)订立的合同中规定了如下仲裁协议:“任何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其有关的争议应被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并根据国际商会仲裁院规则由按照该等规则所指定的一位或多位仲裁员予以最终仲裁。管辖地应为中国上海,仲裁应以英语进行。”本案的焦点之一在于该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考虑到这是一起典型的涉及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开展仲裁服务的案例,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逐级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由于当事人没有约定确认仲裁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根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16条,审查该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应为仲裁地法律,即中国法;该仲裁条款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约定了仲裁事项,并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故符合《仲裁法》第16条的规定,该仲裁条款有效。
案件四:朝来新生案④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特字第10670号民事裁定书。
2007年7月20日,北京朝来新生体育休闲有限公司(下称“朝来新生公司”)与北京所望之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所望之信公司”)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甲、乙双方合作经营甲方现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高尔夫球场,并就朝来新生公司的股权比例、投资金额等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合同中写明签订地在中国北京市。合同中还约定:“如发生纠纷时,甲乙双方首先应进行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对于不能达成协议的部分可以向大韩商事仲裁院提出诉讼进行仲裁,仲裁结果对于甲乙双方具有同等法律约束力。”双方产生争议后,大韩商事仲裁院最终做出了仲裁裁决。在随后的承认与执行过程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不予承认与执行的裁定。理由是,朝来新生公司与所望之信公司均为中国法人,双方签订的《合同书》,是双方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营高尔夫球场设立的合同,转让的系中国法人的股权。双方之间民事法律关系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我国境内,诉讼标的亦在我国境内,不具有涉外因素,故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涉外案件。北京二中院进而指出,《合同书》中关于如发生纠纷可以向大韩商事仲裁院提出诉讼进行仲裁的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相关规定。鉴于我国法律未授权当事人将无涉外因素的案件交由境外仲裁机构仲裁,故该仲裁条款无效。
由上述案件可知,在境外仲裁机构未入驻的情况下,约定境外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需要区分争议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倘若案件具有涉外因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龙利得包装印刷案”中的批复来看,仲裁协议被认定为有效。但这么做的一个不确定性在于,其对我国《仲裁法》第16条做了扩张解释。根据该条规定,有效的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境外仲裁机构从字面上讲,并不完全等同于我国法律下“仲裁委员会”的概念。从我国《仲裁法》的上下文来看,也并没有将境外仲裁机构纳入考虑。这表现为《仲裁法》中涉及一系列关于仲裁委员会设立和管理的内容。这种扩张性解释可能会对仲裁案件的司法监督和执行产生相应的影响。
倘若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我国司法实践拒绝承认约定境外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的效力。如果当事人依旧制定了此类条款,从境外仲裁机构的管辖权角度看,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境外仲裁机构不会以案件有无涉外因素来认定管辖权。但问题是,如果境外仲裁机构做出的裁决需在中国大陆承认执行,它便会碰到朝来新生案的遭遇。与此同时,此种解释背后,实际上也暗含出我国对于仲裁性质呈“准司法说”的导向。因为如果将仲裁仅作为一般跨境服务来认定,依涉外因素之有无来判断仲裁协议效力并不具有很强的理论依据。该等推断也能在其它类似案件中得到验证。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六盘水恒鼎实业有限公司与张洪兴采矿权转让合同争议管辖权异议案中指出,“非涉外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约定发生争议由我国大陆境外的仲裁机构裁决,因违反司法主权原则,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①苏泽林、景汉朝主编:《立案工作指导2011年·第1辑(总第28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此外,国内争议的开放与否也会是影响国际仲裁机构进一步入驻的因素。一方面,如果“龙利得包装印刷案”模式被彻底承认,那么国际仲裁机构在海外便能完成对中国涉外案件的管理,设立“商业存在”恐非必须之举;另一方面,如果可以通过设立“商业存在”的方式,进而受理中国国内争议,那么从经济激励和成本收益的角度看,“入驻”才可能更成功地落地。
2. 我国法院对国际仲裁机构的司法监督
就我国目前现行仲裁法律规范来看,对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仲裁活动的司法监督尚无明确规定。特别是对诸如“龙利得包装印刷案”而言,其后续如何开展司法监督是存在模糊性的。举例而言,从仲裁裁决撤销权的主体看,我国《仲裁法》规定的是“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但这样的条款实际上会对我国法院就国际仲裁机构在我国开展仲裁活动的司法监督造成一定困难。例如,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至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但仲裁地为中国,适用中国仲裁法。裁决做出后,如涉及裁决的撤销,根据我国的《仲裁法》,将会出现两难境地:一方面,SCC并非我国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委员会;另一方面,就算将“仲裁委员会”做扩大解释,从而纳入SCC,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对该案件有撤销权的法院也应为机构所在地,即瑞典法院。但矛盾的是,瑞典的司法制度中并没有“中级人民法院”一说,如此一来,司法监督至少在管辖权层面便具有不确定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仲裁法》在审查国际仲裁机构做出的仲裁裁决时,特别是在国际仲裁机构未设立“商业存在”时,是存在“先天不足”和“自洽性不够”问题的。目前,我国尚未有公开披露此类案件的撤销,其原因可能正与《仲裁法》的局限性有关。之所以如此,通过立法展开倒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国在《仲裁法》中仅预设了两种类型案件的撤销:其一,中国仲裁机构审理的国内仲裁案件;其二,中国仲裁机构审理的涉外仲裁案件。这样的预设,加之采取的“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法院对境外仲裁机构在华仲裁的监督。伴随《深化改革方案》的进一步落地,此种模糊性、亦或者说是盲点也会日益凸显。从实践角度看,这也是阻碍当事人选择境外仲裁机构在华仲裁的不利因素之一。
3.国际仲裁机构在中国做出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我国立法在区分中国裁决和外国裁决时,采取的是“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而非严格的“仲裁地”标准。根据这样的标准,外国仲裁机构做出的裁决只能是外国裁决。①参见王天红:《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确定》,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9期。举例而言,诸如“将争议提交至SIAC仲裁,适用SIAC规则,仲裁地为上海”这类案件,在中国法律下,原则上其应被认定为是新加坡裁决(机构所在地),进而当作外国裁决从而适用《纽约公约》。但是,这样的解释本身与《纽约公约》的仲裁地标准产生矛盾。②参见刘晓红:《非内国仲裁裁决的理论与实证论析》,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5期。鉴于该裁决是在上海做出的,故根据《纽约公约》的仲裁地标准,该裁决应解释为国内裁决。下述两个案件反映的正是这一问题。
案件五:龙华汽车配件公司案③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成民初字第531号民事裁定书。
美国TH&T公司与成都华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之间达成的仲裁条款规定:“因市场销售、货款支付产生的商务争议,根据国际商会的调解与仲裁规则在洛杉矶进行仲裁。”争议发生后,ICC做出了仲裁裁决。因龙华汽车配件公司不执行该裁决,美国TH&T公司遂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最终认定,该裁决为法国裁决,因为ICC的机构所在地为法国。此处,法院并未考虑案件的仲裁地美国。④参见杨弘磊:《中国内地司法实践视角下的〈纽约公约〉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8-69页。
案件六:山西天利实业有限公司案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予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10334/AMW/BWD/TE最终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4]民四他字第6号)。
山西天利实业有限公司与伟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约定:“适用ICC仲裁规则和英国法在香港进行仲裁。”我国最高院在该案件的复函中又一次适用了“仲裁机构标准”。将该案件认定为法国案件,而非我国香港地区裁决。以此为基础,法院最终适用了《纽约公约》,而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⑥参见肖扬总主编、万鄂湘主编:《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2004年第3辑(总第9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境外机构入驻前,在案件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境外仲裁机构在华仲裁的不确定性同样存在。仅以“龙利得包装印刷案”为例,该案一方面承认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效力;另一方面,却又未能就该案件承认与执行的法律标准做进一步的阐释。理论上讲,这里涉及该类裁决的国籍问题。究竟是依“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将该案认定为法国案件进而适用《纽约公约》,抑或是采取“仲裁地标准”,将其认定为国内裁决后,进而适用国内法律,目前均未有定论。更复杂的是,面对诸如“龙利得包装印刷案”,如裁决被认定为非内国裁决,还存在《纽约公约》是否具有适用空间的问题。理论上讲,当仲裁地同样也是执行地时,若依据该地法律裁决不被认定为是本国裁决时,鉴于该裁决又不是公约项下的外国裁决,故可作为“非内国裁决”(无国籍裁决)来认定。⑦参见赵秀文:《非内国裁决的法律性质辨析》,载《法学》2007年第10期。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非内国裁决条款,《纽约公约》允许做出互惠保留,我国便是该保留国之一。一旦做出该保留,非内国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便不会是一国的义务。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非内国裁决标准”完全没有适用的可能性呢?对此问题的回答同样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尽管瑞士德高钢铁公司案中涉及到非内国裁决的论述,但鉴于该案得到了承认与执行,故案件说理未能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最终确认。⑧参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甬仲监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实事求是地说,在“仲裁地标准”都未获完全确立的情况下,采取“非内国裁决标准”并非易事。更不要说这里还涉及到《纽约公约》保留的解释问题,司法机关在这方面的裁量权恐怕有限。从政策层面看,若采取“非内国裁决标准”,还可能导致大量案件“策略性”流向国际仲裁机构。
(二)境外仲裁机构入驻后的潜在法律问题
如前所述,国际商会仲裁院(IC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均已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办事处。但截至目前,三家入驻的国际仲裁机构均未能受理并管理案件,它们更多还只是停留在市场推广、协助境外受理案件在大陆开庭等领域。透过该现象可知,即便是在境外仲裁机构入驻之后,相关法律障碍也依旧存在。本文认为,其中较为突出的法律问题是国际仲裁机构的市场准入。除受到入驻前相关法律不确定性的影响,市场准入和仲裁业开放程度同样影响着境外仲裁机构入驻后能否发挥重要功能。
鉴于国际商事仲裁兼具契约性、服务性、法律性和专业性的特点,理论上它属于法律服务业的一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我国开展有关仲裁业务,依国际服务贸易之视角,它实际上涉及市场准入问题。①参见李健:《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不可行》,载《法学》2009年第12期。但无论是中国的WTO入世议定书,特别是其“附件9”中关于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亦或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下称《15版负面清单》),均没有对仲裁机构法律服务作出明确规定。除市场准入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外,如有学者认为境外仲裁机构并非当然能在华设立分支机构,②参见赵秀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及其影响》,载《仲裁研究》2005年第2期。境外仲裁机构入驻后能否在华享受同国内仲裁机构相同的待遇尚不明确。
具体而言,境外仲裁机构的驻华办公室是否可以受理和管理纯国内案件、境外仲裁机构的管理、仲裁协议效力认定、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模式等均是亟待回答的事项。对此,我国现行的仲裁法律体系尚缺乏先例和经验,故如何应对上述问题均有待立法和司法的日后确认。而从商业角度出发,如果已入驻的境外仲裁机构无法提供更全面的仲裁服务,或是倘若“龙利得包装印刷案”背后的模式被彻底打通,境外仲裁机构的入驻动力和必要性便可能会大打折扣。有鉴于此,欲将上海打造为亚太仲裁中心,如何消除相应的法律阻碍,理清现有的模糊问题,摸索并树立一套符合“境外入驻仲裁机构”的管理模式和业务发展路径是未来必须考量的内容。
三、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中国发展的突破进路
进一步落实《深化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势必会伴随诸多既有法律规范的变革。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开展试点,从而探索国际仲裁机构在华开展业务的模式。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本文认为自贸区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尝试。
(一)明确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准入要求
适度开放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中国的仲裁业务,有利于为当事人提供更多的选择,也有助于倒逼国内仲裁机构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更加市场化和独立化。作为特殊的法律服务,自贸区引入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离不开市场准入方面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区内可以参照外资律师事务所的模式,明确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准入标准与条件,特别是是否将国内争议也放开给外国仲裁机构。本文认为有必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开放模式:一方面,我们需要承认开放国际仲裁机构在华业务的种种优点;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过快的全面开放,可能对国内正在成长中的仲裁业务产生巨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法律服务业的开放需要考虑WTO的“棘轮效应”,因为一但开放,如果再关闭或者降低开放标准,会有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风险。
(二)摸索国际仲裁机构入驻区内的多元模式
国际仲裁机构入驻自贸区会面临具体设立模式的问题。参考外资企业的模式,国际仲裁机构入驻自贸区可采取的模式可分为独资、合资和合作三种模式。就目前已入驻上海自贸区的国际商会仲裁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来看,它们采取了类似于独资的模式。该种模式也可见于域外的实践。譬如,国际商会仲裁院除了在法国和上海以外,还在香港和美国设有商业存在。设立商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辐射区域内的案件。这种模式一方面可以保障国际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兼顾到国际仲裁机构对于机构声誉的考量。除独资以外,迪拜金融中心(下称DIFC)的实践也很具有特点,迪拜本地仲裁机构通过与英国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合作,在DIFC内设立了LCIA的机构。未来,境内外仲裁机构的合作也不失为一种可供参考的途径。借此模式,域外先进的仲裁理念和管理模式和中国国情可以得到有机结合。不仅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缓解国内仲裁机构和国外仲裁机构的商业博弈状态,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方式。
(三)调整《仲裁法》部分条款和法律标准在区内的适用
为了避免突破《仲裁法》,在现有法律未做修改的情况下,可以参考“三资企业法”暂停实施的模式,在区内实施特殊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该事宜上,可以考虑给予自贸区一定的支持。自贸区的制度创新,需要顶层法律制度的支持,面对特殊需求,适时、适度调整法律的实施,不仅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先例。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将仲裁法中关于“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委员会”等法律条款做调整适用。特别是,很有必要在自贸区内明确“仲裁地”标准。除此之外,DIFC的实践同样可供参考。为了更好地提升DIFC内仲裁的国际竞争力,DIFC内实施了特别法,即对《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转化适用。尽管DIFC的实践得益于其顶层法律设计(如宪法层面的保障)和联邦制的国家体制,①United Arab Emirates's Constitution of 1971 with Amendments through 2004,available at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 United_Arab_Emirates_2004.pdf,visited on July 2,2015.这与我国的国情大不相同,但在区内实施特殊规范的做法至少从短期看,它可以使得仲裁准据法和国际仲裁机构的实践良好融合,有助于亚太仲裁中心的构建。
(四)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鉴于我国现有法律规范对调整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我国的仲裁活动存在诸多真空地带,在相关法律修改调整或新的法律出台之前,可采用由最高人民法院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内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的方法作为弥补法律不足的权宜之计。作为补充,与上海自贸区仲裁关系紧密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通过类似于《关于适用自贸区仲裁规则仲裁案件司法审查和执行的若干意见》的方式对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细化。实践中,前文所列举的诸多司法判决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司法实践对中国仲裁国际化的支持以及对仲裁司法监督所采取的“适度与谦抑”态度。②参见万鄂湘:《仲裁司法审查的适度与谦抑》,载中国仲裁网:http://www.china-arbitration.com/news.php?id=3301,访问日期:2015年5月18日。此类先进的司法理念也应反映在我国引入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问题上。具体来说,司法解释需要着重规定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境外仲裁机构中国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境外仲裁机构中国仲裁的管辖和撤销、境外仲裁机构中国仲裁的执行等。但困难的是,司法解释具有局限性,过度的扩张解释恐有造法之嫌。不仅如此,很多问题是立法本身缺乏自洽性和良好的可适用性所导致,司法解释无论如何解释,都会面对一些矛盾的释义,难以自圆其说。
(五)大力推动我国《仲裁法》的修改
仲裁法生效至今已二十周年,鉴于当时立法的局限,其中一些法律规则对于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制约作用。如前文所说的“仲裁机构所在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仲裁法的修改过程中,有必要考虑当下国际商事仲裁的主流做法,参考《示范法》和《纽约公约》,明确以“仲裁地”标准取代“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不仅如此,还有必要消除一些诸如“仲裁委员会”的措辞,因为这样的术语不能清晰地涵盖所有境内外仲裁机构。除此之外,《仲裁法》在修订过程中,也有必要纳入仲裁庭临时措施发布权、友好仲裁、紧急仲裁员制度等,这将有助于我国《仲裁法》与境外仲裁机构规则的配合。①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与我国仲裁法之间存在不兼容的部分内容。以ICC 2012仲裁规则为例,其规定仲裁庭是有权决定是否采取临时措施的。再比如,境外仲裁机构一般不采取仲裁员名册制度。最后,就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的法律地位、设立和管理模式、以及可从事业务范围等方面,也有必要纳入《仲裁法》的修改过程。
四、总结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以及《深化改革方案》的出台,为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由于我国现行仲裁法律规范的滞后性,国际仲裁机构在我国开展仲裁服务尚存在诸多障碍和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ICC、SIAC和HKIAC已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办事处,仍未能受理并管理案件的原因。欲打造亚太仲裁中心,呼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突破:其一,明确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准入要求,适度开放仲裁法律服务的市场;其二,探索国际仲裁机构入驻区内的多元模式;其三,调整《仲裁法》部分条款和“法律标准”在区内的适用;其四,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应对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其五,加快推进《仲裁法》的修改,实现中国仲裁法律规范的“现代化”升级。
The Legal Barriers and Breakthroughs for Foreign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 Several Points Based on the ADR Construction in China Free Trade Zone
Liu Xiao-hongWang Hui
With the “Notification of Advancing the Reform and Open up in China(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referred as FTZ) being implemented for about 1 year,how to enforce the relevant provision herein,that is to “encourage famous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institution to enter Shanghai FTZ”,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bo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and legal practice. Due to the lagging development of the existing Chinese arbitration legal system,there are certain legal barriers and uncertainties for foreign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ir establishment in FTZ. The specific issues include “the legitimacy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s made by foreign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in mainland China”,“judicial review,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such arbitration” and “the market access of foreign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To settle these issues and uncertainties,it is suggested to clarify the market access standard of foreign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introduce multiple mode of establishment,adjust the application of certain arbitration law provisions and legal standard in FTZ and introduc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Pilot projects in the FTZ will eventually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modifi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rbitration law.
Arbitration;FTZ;Foreign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D997
A
2095-7076(2016)03-0010-08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东政法大学研教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治引领推动自贸实验区建设的难点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4ZDC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卜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