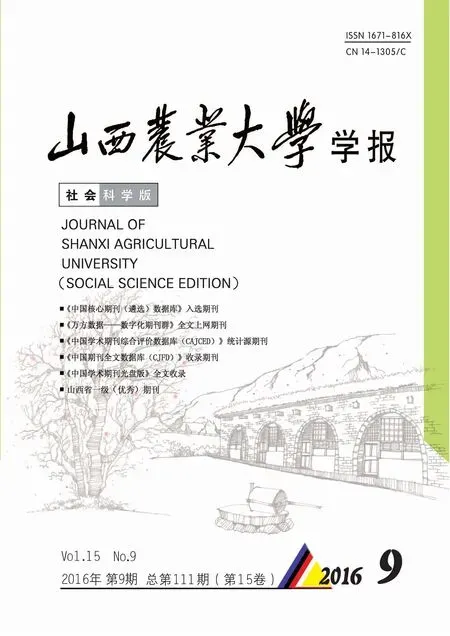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2016-04-04连杰
连杰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连杰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一方面,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工人和资本家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中,个体受到庞大体系的摆弄,似乎无力改变现状。而另一方面,这种发展还有一种“外推”的趋势,如果单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来看,也是难以发现这种趋势的。为此,一种总体性的观点,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清、把握这样的趋势,并在此中寻求突破。
发展;剥削;外推;总体性
一、人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而不能自拔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手稿》)的“工资”一节中曾指出“对人的需求必定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1]尽管没有直接写出来,但是考虑到与“工资”对应,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工人;而从紧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么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工人成了商品……工人的生活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1]当然,如今看来,不仅是工人,即便对于更广义的劳动力及其对应群体来说,马克思上述“需求调节人的生产”的论述,也同样是适用的。
与此相对,马克思形容资本家和地主为“享有特权的和闲散的神仙”[1],看上去,仿佛资本家就是与劳动者截然不同的、高高在上、随心所欲而不受束缚的一群人。不过,在随后的“资本的利润”一节中,马克思却也这样谈到:“下面我们将首先看到,资本家怎样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力,然后将看到资本的权力怎样支配着资本家本身。”[1]这至少说明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并不是真正的“神仙”。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源看来,资本家和劳动者一样,不是自由的——当然,这个观点并不能用来否认两者在现实中可能出现的境遇差异。
“对人的需求必定调节人的生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调节着劳动者的工资,影响着其生存状况,调节着其群体的人数。那么资本家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对劳动者的需求取决于“资本家的兴致”,那么这兴致是什么呢?一般而言,这当然不是指那种心血来潮的兴致——也许除开一些开拓了新领域的突发奇想、创新等——而应该是指资本家对钱的兴致,对利润的考虑,精确的谋划和计算等。甚至可以说,资本家的这种兴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市场之“兴致”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同样调节着资本家的生产。
适应市场需求,追逐利润,这已经不能说是资本家个人的兴致了,有时即使仅仅是为了达到不至于亏本这一目标,资本家也必须迎合市场,他的行动要受到市场这一外在于他的总体的限制,甚至是控制。有时候市场需求是潜在的或者还未被多数人发现的,抓住机会的资本家们被人们称赞为创新,而他也的确发挥了更多的主观能动性,但他仍然是在为市场需求而创造;作为反例,不能在一定时间内引发足够市场需求的创造,似乎容易沦为笑谈、逐渐为人遗忘,即便这种创造有可能在很久之后被认为是伟大的。这使得人们往往愿意围绕那些显而易见的、短期而有效的需求来思考,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实践总是要背负巨大的风险;无论如何,首先要看市场的反应。
这还影响到了资本家对资本的转移能力的发挥。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曾经谈过:“正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于其他方面的这种能力,才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1]不过在现实中,也只有占比不多的资本巨头有能力涉足多个领域:对于中小资本家来说,在其领域内部站稳脚跟、求得生存,已经是足够忙碌的任务了。甚至就连大资本家,有时候也难以轻易地转移资本。能力和能力的发挥是两回事。尽管可以设想,这种行业束缚力,也许对劳动者——当然,这里面的程度区分,不只这几种,在劳动者之内也可以继续考察技术型、管理型等的不同情况,在此仅是举例说明——比对资本家要大,对中小资本家比对大资本家要大;但是已足以说明,社会分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生存对某项市场需求的依赖,人的专门化或碎片化,绝不仅仅是劳动者群体所特有的。
在上面的论述中,看上去过分强调了市场需求对人的单方面的影响。诚然,市场最终是由人的活动而形成的,市场需求实际上也是人的需求;这样,即使不说这两者是一体的,那至少也具有很深刻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问题在于,众多人的经济活动组成了市场,人对市场的决定和影响总是以群体影响的方式显现出来的。市场这个总体对个体来说似乎总是显现出某种自律性——尽管这“自律性”也是由于群体活动而显现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难以感受自身对市场的影响,而却很容易感受到市场对自己的作用力;这种感受,正是多数个体在面对市场这个总体时,难以改变只能顺应的状况的反映。而笔者在此想要讨论的,正是这多数个体的状况。
与市场供求变化相互影响的市场竞争,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状态。根据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的描述,在最极端的竞争状态下,的确会有这样的状况:工人不断压低自己的工资直到仅够维持其生存、不断利用闲暇时间提升自己的技能以至于过劳,从而使其自身的生存状态变得十分糟糕;[1]而资本家在竞争中,大资本家总是利用他的资本优势制造出足以压垮中小资本家的价格优势,使得许多中小资本家破产,逐渐形成行业垄断。[1]一些行政法规的出台,为竞争设下了一定的规则,目的是使得这种最极端的情况不至于出现,这种改良也的确有其效果。不过首先,这是把竞争的限度做出了调整,并没有改变市场竞争对人们生存状态的影响方式;其次,关于其限度是否已被调整为合适的,是值得仔细考察的,然而有时候,甚至连这个限度也会不被遵守。在工人竞争激烈的地方,“血汗工厂”屡见不鲜,工人敢怒而不敢言;在资本家竞争激烈的地方,总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钻规则的空子和漏洞,甚至不惜违反规则。为了取得价格优势,偷工减料引发质量问题,甚至成为行业潜规则,曝光后造成行业失信等,都是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的,正如马克思所描述过的那样,“商品质量普遍低劣、伪造、假冒,无毒不有,正如在大城市中看到的,这是必然的结果。”[1]
看来,在最赤裸的市场竞争状态下,最终的情况是资本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的集聚:一方面,工人劳动不断积累,另一方面,中小资本家不断破产和被吞并。在私有制的背景下,这样的集聚造成的社会富裕状态,无疑是社会的不幸:社会发展的成果最终成为少数人的私有物了。不用说在各大发达经济体统计出的贫富差距有多么吓人,只要看看时下一些创业者的心声,便能明白这无奈的处境:“如果能被大公司看上并且收购,这就算是一次成功的创业了。”
良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似乎可以减少人们切身体会到这种压迫的程度,然而,这需要社会总财富的不断积累,而这种积累如果是按照上述模式进行的,那么人们遭受的压迫在实质上就并未发生变化。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少部分大资本家、利益集团对政治发挥巨大影响力,迫使当局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断。另一方面,尽管劳动者在生存的基本需求上受到的压迫减少,但是由于其劳动所遭到的严重剥削、创业和实业受巨头排挤的艰难处境,以及对以上种种不合理处境的认识,也容易使其丧失劳动创造的动力。
二、发展的“外推”模式值得警惕
具体说来,如果不把视野局限于一国内部的话,那么甚至会发现资本主义的压迫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甚至加剧;发达国家内劳动者生存状况上的某种改善,并不代表这种压迫被彻底根除消失,而很可能只是一种转移或外推。随着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展开,人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当年在撰写《资本论》时描述的那些具体的恶劣现象,仅仅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来看的确是绝大部分都已消失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转移、外推到了不发达国家那里;在这个意义上,也许甚至可以说“任何世界体系都需要多数人为少数人的享受与幸福承受大部分的痛苦、劳累、贫穷、无权利”。[2]甚至这种外推的压迫,似乎也很少能再激起那种马克思设想的对反抗的必要性的意识,形成有效的反抗行动——这一方面可能由于剥削手段变得高明之故,另一方面可能由于被剥削者本来的生活条件之差,使得这种剥削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改善”。也许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洛维特指出马克思甚至也“轻视了无产阶级遭受苦难的长期性和摆脱苦难的难度”。[2]
这种由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外推的机制,与某种“发展理论的生产中心与消费外围”的现象是紧密相连的:“关于发展知识的生产与消费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处在垄断地位……关于发展的知识也与其他社会学知识一样,是在中心(西方)国家生产出来,而在边缘(第三世界)国家消费。”[2]造成这种现象的具体产生机制,也许并非一篇论文能够完全说清的,但在此也可以稍作推断:一方面,工业革命给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种正面效应;另一方面,殖民、热兵器战争所展现的强大力量被看作“先进”的标志,对被殖民、被侵略地形成某种反面刺激;在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下,“落后”的国家即便不照搬,也都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制度、发展经验,对这种发展模式抱有信念,而往往又对这种模式的潜在风险等等不细加考察甚至视而不见(或者说不被主流认可),似乎就不奇怪了。这几乎成了某种“规律”(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国家对这点是有警觉性的)。不过这样一来,借鉴经验的一方或多或少都会踏上被借鉴的一方所走过的道路,因而被借鉴者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顺理成章地将其前期产业向借鉴者转移,所谓“各取所需”,双方就这样走在相似的发展道路上,而在这种发展中占有先机的一方就更容易在这一进程的各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如果现状的确如此发展着,那么从洛维特的上述观点出发,也许可以设想,资本主义的命运,是否只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在一段很长的时期过后,全球各地市场的利润趋于平衡,资本失去转移的动力之后,才可能迎来终结或飞跃。但是,如果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等理论,后来者不可能具有先行者那样的原始积累优势,会在发展的中间阶段陷入停滞甚至衰退,那么就连上述预想恐怕也很难实现。
而且,有人可能不禁要发问:地球给我们人类提供的生存环境,是否能够维持到这一进程的结束?如果说某些恶(污染企业、血汗工厂等)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这种外推,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一种“你情我愿”的话(暂不考虑这种“情愿”之中有多少真正的自觉性、自主性的成分,无论是对个体而言还是对群体而言),那么其向大自然(无论是自国内的还是他国的)的外推则是一种赤裸裸的暴政。这样的外推,可以说既是一方面借了空间上日益全球一体化的便利,但另一方面也正是人们在实际上仍然被国家、地区等观念限制,并未真正达到一种全球化的视野的标志。“随着现代性空间延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制度、技术水平的日益提升,外推空间愈来愈大,外推逻辑愈来愈隐蔽。特别是外地、外国的遥远自然,构成最远和最有效的外推空间,此即生态困境不断恶化的奥秘。”[3]
如果换成风险社会理论的说法,这就是生态风险不断积累,并越来越不可控。局地的生态恶化对全球环境产生影响,影响的不断积累导致全球的环境问题出现,发达国家最终也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如果把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温室效应的加剧视为一个例子,那么这一问题的解决,则仰赖于某种全球性的共识或协定。不仅如此,风险的积累也绝不仅仅局限在生态领域:有理由设想,这样的外推也将会影响到全球核风险、金融风险等等的积累,甚至形成不可控的核危机、金融危机等等。因此,必须要说,在更高的——全球化的,甚至不局限于地球本身的——层面上来考察发展的制度、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三、需要一种总体性的发展视角
综上所述,无论是就第一部分提到过的、个体对于总体的认识和行动上的困难来说,还是就第二部分提及的、真正的全球化多样化视角的要求来说,一种包含有总体性视角的方法是必要的。关于这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之一卢卡奇在其名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的“总体性辩证法”的观点,便十分具有参考意义。
追随着马克思的步伐,卢卡奇也关注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着这些现象:“生产者同生产总过程的资本主义分离,劳动过程被肢解为不考虑工人的人的特性的一些部分,社会被分裂为无计划和无联系盲目生产的个人等等。”[4]他观察到,个人在面对作为巨大总体的社会现实时,往往会感到无能为力而陷入某种消极的状态,例如犬儒主义:“相信自身的存在对世界历史毫无意义,而只维护自己赤裸裸的存在。”[4]基于以上种种,卢卡奇意识到,“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4]
所谓“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在这里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着眼于现实总体中的多样性。卢卡奇指出,总体是“具体的总体”,是“真实的总联系”,“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4]这也就是说,总体内丰富多样的要素都必须作为“把握和冲破”的前提。
这一方面就要求人要有自觉意识,不能仅从自身当下的立场、利益等方面出发来思考和行动。卢卡奇指出,马克思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在《资本论》中展开论述时,没有“立刻而且仅仅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去考察每一个方面,从这样一种片面性中只能产生出一种所谓把符号颠倒过来的新的庸俗经济学”,而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看成是构成它的诸阶级,即作为整体的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的问题”进行论述。[4]尽管马克思将社会分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似乎仍显简单;不过卢卡奇强调,马克思的这种分析也是作为方法论的起点,随着其展开也将扬弃这种抽象简单性。
另一方面,则应该使用适当的方法。例如,卢卡奇提出要运用中介范畴的方法。“中介的范畴……不是什么从外部(主观地)被放到客体里去的东西,不是价值判断,或和它们的存在相对立的应该,而是它们自己的客观具体的结构本身的显现。”[4]对此,卢卡奇举例说明:例如在关于劳动时间的问题中,一方面“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而另一方面“工人也要坚持他们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而在“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4]劳动时间问题,通过一系列的中介,可以转换为力量的问题。这就是说,面对看似孤立的对象,我们应该仔细分析其与其他对象的联系,才能达至更全面、更真实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行动。
此外,着眼于多样性,并不等于把总体的观点消融于某些特殊性之中;同样,具有多样性内涵的发展理论,决不等同于把发展理论消融在多样性之中、拒绝某种总体性的观点;而依然需要一种关注具体现实的总体的总体性辩证法。只抓碎片、只关注小事件、只抓住多样性中的一种或几种特殊性,或是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等,这些实际上和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犬儒主义、和简单的线性的发展观、和抽象的同一的“总体性”等没什么区别,其实反而是对多样性的漠视。
尽管,由于每个主体的认识限度所限,不可能要求“总体的全部丰富内容全都被有意识地包括在行动的动机和目的之内”[4],应该时刻对主
体的认识能力和行动能力保持一种限度意识,不要盲目追求某种包罗一切的面面俱到的总体;但是,我们也必须在一定限度内保持某种总体性的观点、宏大叙事的观点:因为,存在着一些“只有在总体中才能出现的那些令人无奈、甚至令人伤心的东西”[5],而这些东西往往就是被我们所忽视、所轻易外推的东西。当然,同时也必须注意避免陷入某种机械二元对立、或者还原论本质主义的总体观点当中,避免重新落入西奥多·阿多诺所批评的拒斥多样性的、同一抽象的整体观点之中。
[1]马克思.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7-8,12,21,8,9-10,27-29,28-29.
[2]刘森林.重思发展——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08-212,213,18-19.
[3]刘森林.外推:生态困境的奥秘[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9(00):137-146.
[4]卢卡奇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7,126,92,58,79,249,269-270,296.
[5]刘森林.外推背景下的总体性:对总体性的一种辩护[J].学习与探索,2003(1):23-28.
(编辑:程俐萍)
The development: several inspirations from Marxism
Lian Jie
(InstituteofMarxistPhilosophyandChineseModernization&DepartmentofPhilosophy,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The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s a main focus of Marxist theories. On one hand, both workers and capitalists are involved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in which individuals seem to be helpl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tendency of "extrapolation", which can hardly be found if observed only from one point or one aspect. Thus we need a holistic view which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is tendency, or even for a breaking through.
Development;Exploitation;Extrapolation;Totality
1671-816X(2016)09-0640-04
2016-05-22
连杰(1990-),男(汉),广东潮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研究。
B0-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