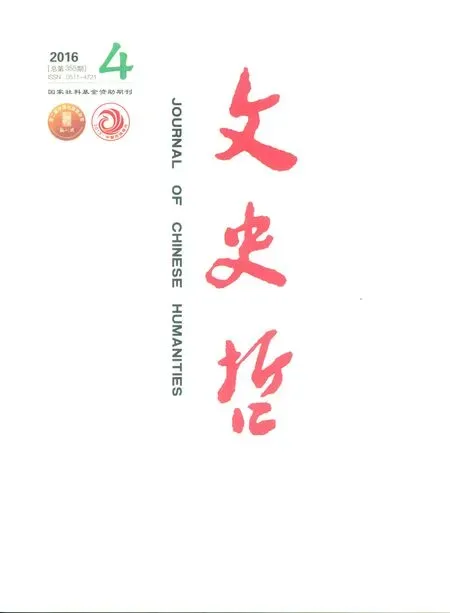六朝贵族的自律性问题
——以九品官人法中乡品与官品、官职的对应关系为中心
2016-04-01李济沧
李济沧
六朝贵族的自律性问题
——以九品官人法中乡品与官品、官职的对应关系为中心
李济沧
摘要:自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官品较乡品低四品起家的观点以来,中日两国学术界围绕乡品与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了不少研究,尤其是中国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乡品与官职对应的新思路。乡品只是与起家官品存在着对应关系,而不是与官品有规律性对应;其次,这种对应呈现出一定的趋势,相差四品应是一个大致的原则,有着上下的浮动;再次,乡品与官职之间的确有紧密联系,但并不能以这种关系替代或者否认乡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这种联系并非某些具体官职与某些乡品相对应,而是如晋宋六品官以上或梁朝十八班内官职需由乡品二品者担任那样,九品官制以内的绝大多数品官都需要具有乡品这一资格。此外,针对官职所作的乡品规定,南朝以前,还不能确认为国家法律或条文;南朝以降,这些规定主要出现在乡品三品及以下。在研究九品官人法的实质和历史意义之际,探讨乡品与官品或乡品与官职的对应关系固然重要,但乡品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更应得到澄清,对获得乡品二品的门阀贵族阶层具有相对于皇权的自律性特质,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六朝贵族;九品官人法;乡品;官品;官职
在中国历史上,六朝时期最突出的社会现象是门阀贵族阶层的形成与活跃*国内外关于六朝贵族的研究综述,成果可谓丰富,这里举出两篇代表性论文。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魏晋隋唐专号》(日本),2001年10月。此文开首对六朝贵族研究作了如下定位:“门阀士族的形成、发展及其衰落是中国中古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汉唐之间,士族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统治力量,对于六朝士族的认识和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理解和把握,长期以来,士族问题的研究一直是魏晋南北朝领域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显学’。”[日]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史朋》40号(2007年),杨洪俊译文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日本的六朝制贵族研究,保持着内藤湖南六朝隋唐中世说以来的传统。”也就是说,六朝贵族的研究与时代区分理论密切相关,是认识六朝隋唐时代性质的核心因素。另,日本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六朝贵族研究作了大量学术回顾,其代表性论文,可参见本文注②。。近年,日本学者渡边义浩对六朝贵族及其特点作了五个方面的归纳:(1)作为一个阶层,直接或间接统治农民;(2)世代世袭国家高官;(3)与“庶”相对,拥有“士”这种高贵的地位以及身份;(4)在文化上具有一般庶民无法参与的文化创造能力;(5)相对于皇权,有着一定的自律性。进一步而言,如果将这一时期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代相比,则(1)是从汉代豪族到清代乡绅的统治阶层都具有的性质,(2)、(3)是周代的卿、大夫、士所具有的性质,(4)是宋代以后的士大夫所具有的性质。而最能体现其特色的就是(5),即相对于皇权的自律性*[日]渡边义浩:《“所有”与“文化”——对于中国贵族制度研究的一个观点》,《中国——社会与文化》(东京)第18号(2003年6月)。。
上述归纳建立在众多前人研究成果之上,有一定参考意义。可是,门阀贵族究竟如何获得了相对于皇权的自律性呢?对此,渡边指出了重视血统的名门主义和形成封闭性通婚圈的人际关系,以及严格区分贵族与非贵族的同类意识等等。然而,这只是一种针对现象的陈述而非原因的分析。不能不说,内藤湖南对六朝贵族自律性的提示至今仍具启迪性:
这一时代的中国贵族,不是在制度上由天子授与领土与人民,而是由于其门第,作为地方名门望族延续相承的传统关系而形成的。当然这是基于历来世代为官所致。当时社会上的实权,是掌握在这些贵族的手中。这些贵族都重世袭家谱,因此当时系谱学颇为盛行。*[日]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收入夏应元选编并监译:《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24页。
据此可知,在思考门阀贵族的所谓自律性特点时,来自与地方乡村社会的支持与否,应成为关键要素。一般而言,六朝的贵族往往以家族为背景,修习家学、礼法,同时依靠家族、宗族以及乡里社会的支持,通过九品官人法步入政界,持续占据王朝的高官高位,在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享有威望。也就是说,获得乡里社会的支持,体现了门阀贵族的社会性特点,而当他们成为王朝官僚,构成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时,则呈现出代表王朝的一面。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应怎样从社会性、王朝性的角度来分析门阀贵族自律于皇权以外的特质呢?
在学术史上,谷川道雄援引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极富想象力的线索。众所周知,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官僚人事制度,其最大特色是确立了官品体系,官分九品,对官职的高下作了区分,一直影响到了清末。但是,这项制度还有一个其他时代不曾有的特点,这就是在官品以外,还有乡品的存在。20世纪50年代,宫崎在其《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中,首次揭示出官僚候选者起家任职时,其官品要较乡品大致低四品的历史现象。学术界围绕这一对应关系及其评价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此,谷川作了如下阐述:
按宫崎氏所理解的乡品与官品的相互关系,就本质而言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有关这一点,我在上述几篇书评中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我以为,就官品依乡品来决定的事实来说,贵族身份和地位虽可认为是由王朝权力所赋予的,但在本源上仍是由其在乡党社会之地位和权威所决定的,王朝只不过是对此予以承认的机关——当然这种承认具有很大的作用。直截了当地说,贵族之所以成为贵族,其本源不在王朝内部,而在其外部。而这种承认手续,可以认为就是所谓九品官人法。如果这样考虑的话,不论六朝贵族有着怎样的官僚制形态,其本质也应该是比拟封建制的,换言之,可以视其为一种封建制的变形,这就是我对宫崎的本意的理解。

无论逻辑还是思考方法,这一评介对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然而从正面对此加以论证的研究迄今尚未得见。例如,围绕乡品与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中日两国学术界都做了不少研究,尤其是中国学者或否定、或修正,用力较勤,不但如此,还进一步提出了乡品与官职对应的新观点,这些都大大丰富了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内涵。可是,探讨九品官人法中的对应关系,究竟对六朝贵族的自律性问题或者六朝时代特质的分析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遗憾的是,这些并没有引起前人的足够关注。
本文首先对前人的相关成果和论点作些梳理,在此基础上,重新探讨乡品与官品以及乡品与官职的对应关系及其问题所在。研究目的在于,从乡品的角度,论述九品官人法的历史意义以及六朝贵族自律于皇权以外的性质。
一、乡品与官品
关于九品官人法之中的官品,马端临曾有一个概括,“然此所谓九品者,官品也,以别官之崇卑”;“盖官品之制,即周之所谓九命,汉之所谓禄石,皆所以辨高卑之等级。其法始于魏,而后世卒不能易”*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十七《职官二十一》,北京:2011年,第2056页。。也就是官品的作用在于区别官职的高下崇卑,与周汉的九命、禄石的性质相似。

马端临对乡品也有一个概括:“陈群所谓九品者,人品也,以定人之优劣。”这里的人品,就是乡品之谓,由各个地方的中正对官僚候选人定品。那么,官品与乡品之间有何关系呢?马端临认为:“二者皆出于曹魏之初,皆名以九品。然人品自为人品,官品自为官品……若中正所定之人品,……然决与此官制之九品不相干,固难因其同时同名,而遂指此为彼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十七《职官二十一》,第2056页。
马端临尽管指出了中正所定“人品”与“官制之九品”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但是对于两者的联系,并没有说清楚,其中最后一句“同时同名,而遂指此为彼也”,针对的是南宋岳珂的观点,因为后者对官品与乡品有一个重要的分析:

之所以重要,因为在此之前还从没有人意识到乡品与官品的关系问题,更谈不上有明确的认识。岳珂首先使用了“九品官人之法”这一用语,也意识到了乡品并非官品,然而对两者的关系,却不能理顺,只是使用了一个“逆设”的说法,也就是乡品二品意味着其人将来可以达到官品二品。对此,马端临进行了批判:“岳氏合而为一,以为官品者逆设之以待某品之人,此说恐未然。”
两人虽然观点不同,但是都认识到乡品与官品为两套系统,并非一回事,至于两者之间有何对应或者联系,则完全没有谈到。
20世纪50年代,首次对官品和乡品的关系发表独特观点的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根据宫崎的看法,乡品是中正官给予希望当官的候选人的评价,政府根据此乡品的上下授予适当的品级官位。官品与乡品的相互关系,例如乡品为二品的人才,初任官职的时候,会委任他当低四级的六品官。此后,随着年资的积累,其政绩得到承认,那么逐次晋升,最终可达到二品官。但是如果要晋升为一品官,那就必须要有中正重新审核,改授乡品一品*[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后收入《宫崎市定全集》6,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中译本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53页。本文所引均出自中文版。。
乡品是否有一品,迄今尚无定论,中国学者倾向于持否定性看法,这一点暂且不谈。我们看宫崎的上述概括,大致包括两层含义:首先是官僚步入政界之初,所任官职也就是起家官的官品一般比其所拥有的乡品要低四品。这应该是首次明确了乡品与官品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其次,例如乡品二品的人物,最终可以达到与乡品相等的二品官。这一点实际上与岳珂“逆设”之说相似,不过与岳氏相比较,更加明确了乡品和官品的不同,并且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以上简要回顾了官品与乡品的存在及前人的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一部分中国学者之中,重新对两者的对应关系产生了研究兴趣,以下择其代表性的例子略作说明。
陈长琦将中正所定的乡品称作“资品”*笔者曾经对“资品”一词作过分析,认为是官资与乡品的合称,并不等同于“乡品”,而“中正品第”、“中正品”、“人品”等也是不同学者对“乡品”的称谓。参见拙稿《九品官人法中的乡品称谓考论》,《江海学刊》2012年第6期。另,除引文以外,本文均使用“乡品”一词。,以此探讨了其与官品之间的关系,认为某种官职如标明官品二品,就表示这种官职需要乡品二品的人来担任,标明三品,就表示这种官职需要乡品三品的人来担任。同时,某人如获得乡品二品,就表示有了任二品官的资格,若获得乡品三品,就表示有了担任三品官的资格。也就是对宫崎所言乡品与起家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了扩展,进一步指出乡品与官品之间有着明确的对应关系。至于宫崎所说乡品与起家官品之间相差四品的观点,陈长琦也进行了修正,认为曹魏时期,两者之间大致对应关系是相差三品。西晋以后,乡品二、三、四品的起家官品与其乡品之间的差距,由相差三品变为相差四品,乡品五品的起家官品,在与乡品相差三至四之间浮动,乡品六品的起家官品仍然保持着与其乡品相差三品的距离*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上述观点首先参考了岳珂“逆设”之论以及宫崎的说法,也就是乡品二品中的“二品”,其实是指该乡品获得者能在政界所能升到的最后官品。而在乡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方面,也以宫崎说为基础进行了细分,建立了更为整齐的对应关系。
针对陈长琦的论述,张旭华认为,无论从一个人起家官职的官品、迁转官职的官品还是仕途生涯中的最高官位及其官品来看,乡品二品与官品之间均不存在这种虚拟的对应关系即统一性。根据他的看法,应将乡品区分为上品与下品。曹魏时期,名列上品的士族子弟可分别从五品、六品、七品三个任官层次起家。入晋以后,出现同是上品而起家官品分为四个层次的铨选格局,也就是(1)帝室亲茂和三公子弟可起家为五品官;(2)高门子弟和某些身有国封者可起家为六品官;(3)中级士族子弟多起家为七品官;(4)低级士族子弟则起家为八品官。由此得出结论,在起家入仕这一环节上,乡品第二品与官品二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张旭华进一步指出,门阀子弟获得的上品二品,仅仅是表明其等级身份及其所取得的入仕资格,并不表明他已经获得了就任二品官的资格。再以入仕后的官职升迁而言,魏晋时期的门阀子弟虽可以上品二品起家为官,但只有少数人获得二品高官,多数人终其一生也难以跻身二品高位*张旭华:《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九品中正制略论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由以上所述可知,陈长琦承认乡品与官品尤其是起家官之间有着对应关系,同时作了进一步的细分,并且通过逆设之说,揭示乡品与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张旭华通过对乡品二品的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对应关系或是不能成为固定的模式,而且乡品仅仅是等级身份的一种反映和进入官界的资格。
二、乡品与官职
从前引温峤的例子可以看到,每当晋升官职的时候,都因为乡品不过,而需要皇帝特别发诏。这显示出,乡品与官职之间有着某种关联性。还是看马端临的分析,他认为乡品在吏部授官时具有参考作用,即:
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审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谓免乖失及法弊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八《选举考一》,第812页。
也就是说,吏部委托中正审核人才,品定乡品,然后在任命官职之际予以参考。
关于乡品与官职的关系,唐长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中正品第并非只是一种褒贬虚名,而是和入仕途径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官位必须与品第相符,降品等于免官”,“从卑品升迁官职的虽不乏其人,但升了官必须同时升品。魏晋之间寒门升上品已非易事,晋宋之间除了军功以外,就绝无仅有了”*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第107、111页。。即乡品不够而升官的话,需要提高其乡品,反之,乡品出现下降意味着免官,由此可见乡品与官职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一定的联动性。
与唐长孺的上述见解不同,胡宝国认为乡品只是与具体官职之间有关系。胡宝国首先指出,乡品与起家官品之间有相差三级、四级、五级的,两者在品的次第上并无固定联系,由此否定了宫崎所云两者之间相差四品的观点。同时认为,乡品仅仅是与具体官职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也不只限于起家官职,如《晋书》卷六十六《刘弘传》载:
被中诏,敕臣随资品选,补诸缺吏。……南郡廉吏仇勃,……尚书令史郭贞,……虽各四品,皆可以训奖臣子,长益风教。臣辄以勃为归乡令,贞为信陵令。
胡宝国认为,仇勃、郭贞被刘弘任命为县令前已经出仕,但他们进一步升迁仍须参考乡品品级,这就说明乡品并不仅仅在起家做官时有意义*胡宝国认为刘弘先称被中诏随资品补选,后又列两人乡品,那么资品就是乡品。再引《晋书·贺循传》“才望资品”,指出这里的资品同样是乡品。。进而分析《北堂书钞》卷六十八“从事中郎缺,用第三品”,《宋书》卷六十《范泰传》“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以及公府掾、长史、祭酒、司马、东宫官属与诸王师友文学等职多由获得乡品二品的人物担任等事例,指出:“乡品与任官确实有一定联系,或是制度上有所规定,或是不成文的习惯。就官职与乡品而言,某些具体的官职须具有某些乡品的人担任。所以,就个人的乡品与任官而言,乡品决定的只是他可以担任的具体官职。当时人从不提乡品与官品的等次有何联系。”*胡宝国:《九品中正制杂考》,《文史》第36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也就是说,通过从事中郎用第三品、助教用二品等例子,认为乡品只是在官僚就任某个具体官职的时候发生作用。
阎步克在探讨了各种对应说之后,认为胡宝国的观点最为中肯,应当支持,并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补充。
首先根据具体史料否定官品与乡品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此仍然举出《北堂书钞》卷六十八“从事中郎·山简不拘品位”条引《镇东大将军司马伷表》:“从事中郎缺,用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内山简清精履正,才识通济,品仪第三。”*根据版本的不同,“从事中郎缺”一句后,或为“用第二品”,或为“用第三品”,关于此点,参见王铿:《山简乡品考——以〈北堂书钞〉版本异文为线索》,《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另,王铿在此文中,主张山简的乡品并非三品,应为二品。并作如下分析:中散大夫官品第七,同为七品之官的有太子洗马,号称“清选”,其乡品应为二品,这与官品之间相差五品。由此可见,乡品并不与官品的各等级相对应,而是与官职相对应*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339页。。
在地方一级,例如县令长的乡品也有等级之差,例如“二品县”(《太平御览》卷二六九引《宋武帝诏》)、“秣陵令三品县耳”、“句容近畿,二品佳邑”*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第2007页。等,可见就乡品而言,既有二品县令、三品县令,也有四品县长。尤其是秣陵令与句容令,同为官品第六,但是乡品却一为三品、一为二品,这仍然显示了乡品与官品的不相对应,乡品因具体官职而异。
其次,强调乡品与官职的对应关系源自当时的法律和规定,如“从事中郎缺,用第二品”明显是在传述法规条文,它显示乡品是就具体官职而具体规定的。《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载南齐国学“典学二人,三品,准太常主簿;户曹、仪曹各二人,五品;白簿治礼吏八人,六品”,这是王朝为上述官职规定了乡品。另如《齐职仪》有三条材料:
每陵令,品第七,秩四百石,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旧用三品勋位,孝建三年改为二品。
太祝令,品第七,四百石,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用三品勋位。
(廪牺)令品第七,秩四百石,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今用三品勋位。
这些都是以相当典型的格式,对官职、官品、禄秩、印绶、冠服以及乡品资格所作的完整规定,应是王朝选簿之原貌。
据此阎步克得出结论如下:“不管把官品和中正品的对应弄得如何细致入微,它也只是一种大致趋势而已,而不是法制规定。当时王朝从没在制度上把二者一一对应起来,如果墨守‘差若干品’则无异胶柱鼓瑟;另一方面却有充分证据显示,中正品是针对具体官职而具体规定的,从而证实了胡宝国先生的论断。”*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338页。也就是说,诸如二品令史、三品令史、四品令史、五品令史、六品令史及二品县、三品县、四品县等现象的存在,以及上述政府《选簿》所作的正式规定,都说明王朝并没有对乡品与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作出明确规定,就制度而言,也没有二者形成对应关系的根据,相反倒是说明一个官职只对应着一个特定的乡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342页。。
由以上所见,针对乡品与起家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胡宝国、阎步克两位予以了否定,认为王朝并没有作这样的规定,而且根据史料,主张乡品是针对具体官职而具体规定,乡品决定的是可以担任的具体官职。
三、乡品与官品的对应及其问题所在
迄今针对乡品与官品、乡品与官职之间的对应关系所作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二点:乡品与官品的对应与否,乡品与官职的对应关系。尽管前辈学者的研究相当精致,极具启发性,但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节首先探讨第一个问题,即乡品与官品的对应关系。
在讨论乡品与官品对应与否时,有必要先回顾一下首开论题的宫崎市定的论述:
要言之,制定了起家的官品大概比乡品低四等,当起家官品晋升四等时,官品与乡品等级一致的原则。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想来会允许在上下浮动一个品级的范围内酌情调整。如果上述对应关系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可以从人物传记中知道其起家官品,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推测出乡品等级。*[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66页。
我们在正史列传中能见到的人物经历,更多属于打破标准形式的特殊情况。但是,如果因为各个人的情况不相符合,就完全否定原则的存在,那就麻烦了。*[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76页。
值得注意的是,宫崎反复指出的所谓对应关系,乃是乡品与起家官品,而非乡品与官品。而且还强调指出,这种对应关系虽然是一项原则,但也有着上下浮动的可能,并没有那么严整。回头看国内学者批判这一观点时,所针对的正是相差非四品以及官品与乡品的不对应。不能不说,这种批判从开始就似乎没有对准靶心,而这当然也影响了对九品官人法制度的正确认识。

将两位先生的解释作一比较,可以清楚看到,阎步克是从官品推测乡品,由此判断两者的不对应,而宫崎则是从起家官的官品来推出其与乡品的关系。进一步而言,宫崎强调的是起家官品与乡品,而非官品与乡品的简单对应。所以说阎步克对这条史料的解释,似过于重视官品与乡品,而忽略了起家官品与乡品的关系。
稍微回顾一下,在宫崎提出了乡品与起家官品之间存在四品差之后,就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如矢野主税*[日]矢野主税:《针对魏晋中正制性质的一个考察——以乡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为线索》,《史学杂志》第72卷第2期(1963年)。另可参见[日]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论》,谷川道雄编著:《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后收入氏著《六朝政治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夏日新译文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周一良*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七第与六品”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7页。等等。而胡宝国、阎步克的观点则更加鲜明,认为宫崎自己举出的例子中就有很多不是相差四品的,因而否认两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但是,宫崎本身已经说明这种对应并非严格,而是有着浮动和例外,所以将批判对准这四品之差而发,似非问题核心所在。
相比较而言,陈长琦基本赞成宫崎的观点,并且根据时代的变化,对乡品与起家官品之间的差距作了详细的区分,但是受到了张旭华的批判。张旭华原意是要否定陈长琦的起家与乡品之间有着对应关系的观点,但是仔细阅读张文,就会发现,两者的结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宫崎指出所谓相差四品,只是一个原则,至于其中存在种种不符合四品的例子,只能是非原则。当你举出例子论证非四品的时候,同时也有大量例子证明的确是四品。更有意思的是,有些例子还显示出,一旦起家为六品官,第二官相反却是就任七品。例如大名鼎鼎的王羲之,起家秘书郎,官品第六,而第二任官却是庾亮的征西参军,官品第七*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第2094页。。再如王彪之,也是起家六品的著作佐郎,第二任官却转为七品的东海王文学。这不就暗示,从乡品二品起家,就任官品六品的官职,其间相差四品是一个标准或是一种习惯吗?当然,对此作过多的论证,意义并不大,其实宫崎只不过说有了乡品以后,进入官僚世界的时候,要低于这个品级起家,发现并掌握这个大致趋势就是意义所在。
但是,中国学者在乡品和起家官品之外,似乎找到了另外一种对应关系,例如前面所见陈长琦的一个论断,“某种官职如标明官品二品,就表示这种官职需要资品二品的人来担任,标明三品,就表示这种官职需要资品三品的人来担任”。不得不说,这种寻求乡品与官品的统一性的说法看似比较新颖而且整齐,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陈长琦并没有举出一条相关的史料来证明这个结论,因而只能说是一种推论。再如,官品六品的秘书郎,几乎肯定是由乡品二品的获得者担任的。此外,如官品三品的尚书令、中书令,显然不可能让乡品三品之人担任。
进一步而言,倘若某人从官品三品升到二品,难道他的乡品也要由三品升到二品吗?实际上并不需要,因为晋宋之后除了个别的例子,也就是唐长孺所言的军功以外,能够做到官品三品的人,一般都是乡品二品获得者。就这些人而言,首先获得乡品,然后进入政界,从六、七品的官职起家,一直升到三品、二品,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会出现乡品遭到贬降的情况,例如温峤就是如此,但一般而言,乡品的变化并不显著。所以陈长琦寻求乡品与官品的统一性的这一说法,或可再论。
四、乡品与官职的对应及其问题所在
如前所见,否认乡品与起家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重新提出乡品与官职对应关系的是胡宝国和阎步克。胡宝国认为:“乡品与任官确实有一定联系,或是制度上有所规定,或是不成文的习惯。就官职与乡品而言,某些具体的官职须具有某些乡品的人担任。”应该承认,发现乡品与官职的对应问题是中国学者的一大贡献。以下,我们就来分析这种对应关系。所谓“某些具体的官职须具有某些乡品的人担任”,按照二位先生所举材料,最典型的就是从事中郎用第二品、助教用二品。但是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从事中郎、助教均为六品官,由乡品二品获得者担任。晋宋以降,就任六品官以上者基本上都是获得了乡品二品的,到梁武帝天监改革以后,十八班官制之下有流外七班,即“位不登二品者,又为七班”*魏征等撰:《隋书》卷二十六《百官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33页。,也同样说明十八班内的官职全都由乡品二品的人物担任*宫崎市定的研究首先认为,梁代十八班由宋齐以来六品以上官组成。张旭华后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梁之十八班是将宋以来的八品以上官分为十八班,九品官则无一进入十八班。见《萧梁官品、官班制度考略》,《九品中正制略论稿》,第241页。祝总斌也对宫崎的研究作了修正,指出梁代十八班不是宋制六品以上,而是七品以上的重新组合。祝总斌:《门阀制度》,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7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后以《试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为题收入氏著《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下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即便按胡宝国、阎步克所论,朝廷规定了从事中郎、助教与乡品二品的对应,但进入六品官这一级别的几乎全是乡品二品的获得者,那么专门对这两个官职作出乡品的规定究竟有何意义呢?更重要的是,以这两条材料来强调“某些”官职和“某些”乡品的对应,则似乎忽略了更多的官职与乡品的关系。
实际上阎步克在回答汪征鲁“乡品是与所有的具体官职对应,还是仅仅与某些具体官职对应”这一疑问时说“我们明确回答以后者为是”*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343页。,也似乎没有将这种个别对应放大到整个九品官制之中。拿温峤为例,前面已见,他首先是举秀才、灼然,也就是获得乡品二品,再据《晋书·温峤传》看其后的官历(括弧内为官品):
司徒辟东阁祭酒(七)→补上党潞令(七)→平北大将军(刘琨)参军(七)→平北大将军从事中郎(六)→上党太守(六)→司空(刘琨)右司马(六)→丞相(司马睿)左长史(六)→散骑侍郎(五)→骠骑王导长史(六)→太子中庶子(五)→侍中(三)→中书令(三)→丞相(王敦)左司马(六)→丹阳尹(三)→江州刺史(四)、持节都督(二)、平南将军(三)→骠骑将军(二)、开府仪同三司(一)。
按照胡宝国、阎步克的观点来看,温峤的乡品二品显然是与其平北大将军从事中郎这一具体官职相对应的,可是难道就与他所就任的其他官职无关吗?如果无关,为什么会出现因乡品不过亦即遭到贬降之后,需要皇帝特别发诏的问题呢?由此可见,乡品是与温峤所升任的每一个官职都有关系的,不可能在他所有的官历中,存在某些官职需要乡品,而某些官职无须乡品的情况。
综合以上所述,考虑到进入六品官以上或者说十八班以内的几乎全都为乡品二品之人,用“某些”官职与“某些”乡品对应的说法,就显得不太全面。即便六品官以下,例如七品、八品之中,存在着乡品二品及其以下者就任的例子,但这只是乡品等级的不同,而不是某些官职与某些乡品的问题。
接下来需要探讨的的是,这些官职是否都由王朝作了乡品的规定呢?
胡宝国、阎步克判断乡品与官品不对应以及乡品与官职对应的主要标准,就是认为王朝对乡品和官职的关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也就是强调有法律、法规的支持,按照阎步克的话来说,“王朝正式规定了某官的任用资格为中正某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344页。。这里主要依据的史料为两类,一类还是从事中郎和国子助教。针对前者,即“从事中郎缺,用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内山简清精履正,才识通济,品仪第三”作了如下分析:
玩“从事中郎缺,用第二品”语气,这句话显然是在传述法规条文。这种条文显示,中正品是就具体官职而具体规定的。因为从事中郎须用中正二品之人,而中散大夫山简“品仪第三”,低下一等,所以司马伷在打算辟他作从事中郎时,就必须上表特请开恩了。*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339页。
“从事中郎缺,用第二品”,是司马伷上表时的一句话,是否就是法规条文或王朝的正式规定,实际上并不能确定,或许是在陈述一种惯例。而“中正品是就具体官职而具体规定的”,这一句就比较费解了。按照阎步克的意思,似乎乡品二品是针对从事中郎这一具体官职而具体规定的。一般而言,乡品是由中正为20岁左右的年轻人所下的评价,吏部在授予官职时需加以参考。温峤正是带着这个乡品进入政界的,而且因为他是二品,所以可以就任从事中郎这一职位。但绝不能说,他的二品就是具体针对从事中郎这一官职而具体规定的。前面已述,其所历所有官职都与这个二品有关。由此来看,阎步克解释此条太过注意“具体”,而忽略了二品之人可以就任包括从事中郎在内的其他官职。因此,将此句解释为“从事中郎缺人,该职位是由乡品二品者担任的官职”,似更符合原意,而不必从王朝的规定上理解。
如果说“从事中郎缺,用第二品”这一句是否为法律条文,还需斟酌的话,《宋书·范泰传》中的“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一句,则基本可以排除法规的可能性。首先看此文:“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颖川陈载已辟太保掾,而国子取为助教,即太尉准之弟。”再看阎步克的分析:
《宋书·范泰传》曾提到“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可知西晋朝廷为国子助教一官具体规定了中正二品的资格。……而这也是就具体官职来作具体规定的,并没有涉及官品高下。*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339页。
范泰为刘宋时人,他在谈论西晋国子时,援引了此例,即陈载起家太保掾,其乡品自然为二品,后来国子取其为助教,这也就是西晋时乡品二品任助教的情况。从前后语句来看,并非强调西晋朝廷在法律上为国子助教一官具体规定了乡品二品的资格,而只是在作一般性的陈述,更何况范泰根本没有必要使用前朝的法律或规定。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即如果认为这两个例子是法律条文的话,那就似乎没有理由仅仅只对这两个官职作出乡品的要求,因为比起从事中郎和国子助教,还有相当多更为重要的官职。而针对这些官职的乡品规定,完全不见于正史或《通典》、《唐六典》等。尽管该时期的相关史料极其有限,但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例如同为第六品的秘书郎,据《唐六典》卷十引《晋令》:“秘书郎中品第六,进贤一梁冠,绛朝服。”再看著作佐郎,同样是《唐六典》卷十引《晋令》:“著作佐郎品第六,进贤一梁冠,绛朝服。”《晋令》以外,《北堂书钞》卷六十六引《晋起居注》也有一条记载:“武帝太康八年诏曰:‘太子率更仆,东宫之达官也。其进品第五,秩与中庶子、左右卫率同职,拟光禄勋也。’”需要注意的是,晋武帝通过诏书的形式提到某个官职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涉及乡品如何。即便是国子助教,据《唐六典》卷二十一的记载:“晋武帝初立国子学,置助教十五人,官品视南台御史,服同博士。”同样看不到针对乡品的规定。
以上种种,都在说明根据现有的史料,还无法得出晋代在法律上或条文上为具体官职规定了乡品的结论。尽管如此,阎步克在判断朝廷对某些官职作出了乡品的规定时,另外举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材料。如前引《南齐书·百官志》所载南齐国学中的典学、户曹、仪曹、白簿治礼吏以及《齐职仪》所载每陵令、太祝令、廪牺令等等。应该承认,这些的确是政府对上述官职所作的乡品规定。对于这些史料,应作如何理解呢?对此,笔者想提出两点看法:
第一,这些例子全都属于南朝,也就是门第日趋固定的时期,前述唐长孺已经指出,此时除了军功以外,从卑品亦即二品以下升迁到上品亦即二品的可谓“绝无仅有”。

从这两点来看《南齐书·百官志》以及《齐职仪》有关官职与乡品的记载,似乎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南朝时期,朝廷能够作出规定的仅仅限于乡品三品及其以下者。如前所述,进入梁代十八班制以内的几乎全为乡品二品获得者,因此对于这些官职的乡品,无需朝廷另外作出特别的指示或规定。
综合以上两节所述,首先,乡品只是与起家官品存在着对应关系,而不是与官品有规律性对应;其次,这种对应呈现出大致趋势,相差四品应是一个大致的原则,有着上下的浮动;第三,乡品与官职之间也有紧密联系,但并不能以这种关系替代或者否定乡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这种联系,并非如胡宝国、阎步克所言,为某些具体官职与某些乡品相对应,而是如晋宋六品官以上或梁朝十八班内官职需由乡品二品者担任那样,九品官制以内的绝大多数品官都需要具有乡品的资格。此外,针对官职所作的乡品规定,南朝以前,还不能确认为国家法律或条文,南朝以降,这些规定主要出现在乡品三品及以下的获得者身上。
五、结语
具有相对于皇帝权力的自律性,这是理解六朝门阀贵族所具有的历史性,进而探讨中古社会性质的重要线索。谷川道雄针对九品官人法中乡品与官品的对应关系作了独到的理解,即乡品决定官品,说明贵族的本源不在王朝内部,而在其外部。本文据此重新审视乡品与起家官品、乡品与官职之间的对应问题,得出如下结论:乡品不但如宫崎市定所言,与起家官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而且还与九品官制之内的绝大多数官职相联系。
然而,在九品官人法的研究中探讨上述对应关系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胡宝国说:“当时人从不提乡品与官品的等次有何联系。”这句话很重要,的确没有将乡品与官品高低联系起来的材料,但是宫崎所推论出来的乡品与起家官品之间的大致对应关系,也是通过史料得出的一种结论。阎步克说:“中正品较高则起家官品也较高一些,对此趋势我们并无异辞,但至今没人能够确凿举证,王朝明文规定了任何直接对应。”也就是并不否定这一大致的对应。我们可以就此提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王朝没有明确规定,但却会出现这种趋势呢?我们所要研究的,难道不正是这种趋势所反映出来的史书记载背后的历史真实吗?阎步克还有另外一个表述:“不管把官品和中正品的对应弄得如何细致入微,它也只是一种大致趋势而已,而不是法制规定。”*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338页。在我们看来,或许并非法制规定,但却是一个大致的趋势,这实际上也就说明,乡品与起家官品之间的大致对应关系是法制规定以外存在着的某种影响官僚体制的习惯或意识。应该说,这一点才是问题的核心之所在。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乡品的存在,也就是说为什么乡品会在贵族起家、王朝任命或晋升官职以及贵族官僚的整个官历之中持续不断地发生作用?可以说,前辈学者在研究乡品与官品或者乡品与官职的对应时,承认大致的趋势也好,主张具体的对应也罢,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从温峤这样拥有乡品二品之人所经历的官历来看,首先是有乡品,有了乡品才能起家,才能就任具体的官职,当乡品遭到贬降后,晋升官职时便需要皇帝特别发出诏书。十分清楚,在乡品、官品、官职这三者中,乡品最为重要。唐长孺说,乡品与贵族入仕的途径关系密切。张旭华也指出,乡品决定了贵族的入仕资格。对此,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即乡品还是贵族就任每一个官职的前提。一个贵族从起家到其后的晋升官职,整个过程始终摆脱不掉乡品的存在和影响。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乡品的这种特性呢?根据本文的分析,可作以下提示:前面反复谈到,进入晋宋时期的六品官以上或梁朝十八班以内的全是乡品二品获得者。这就显示出,并不需要王朝对其中每个官职都做乡品的规定,同时与王朝对乡品三品以下者所做的规定结合起来看,国家权力所能实施的影响似乎只及于乡品二品以下。也就是说,探讨乡品与官品或乡品与官职的对应关系固然重要,但是具有独立于官僚任职制度以外,并且得到乡论支持的乡品与国家权力发动之间的关系更应受到关注。我们认为,源于乡论的乡品,是门阀贵族在社会性与政治性这两方面呈现出自律于皇权的决定性因素,它的存在,除了反映九品官人法的独特性以外,还充分说明,探讨中古社会的时代特质时,不能过分强调皇权自上而下的作用或者围绕皇权的强弱变迁而立论,而应对门阀贵族具有源于地方乡党社会的自律性因素予以更多的重视。
[责任编辑范学辉]
作者简介:李济沧,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2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9世纪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关系研究”(15BZS03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