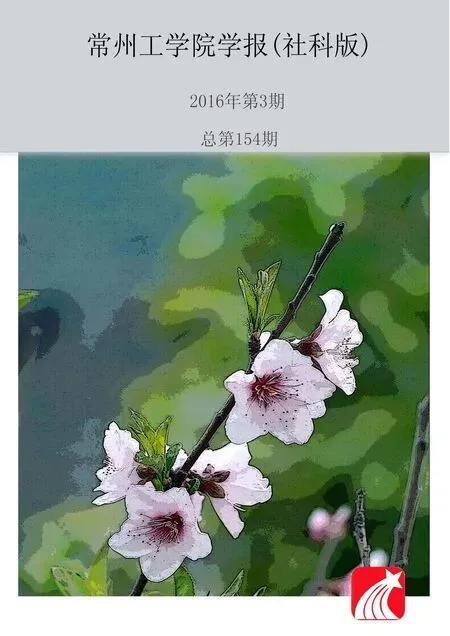论福克纳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
——以《台北人》为例
2016-03-29孟飞庄若江
孟飞,庄若江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论福克纳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
——以《台北人》为例
孟飞,庄若江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摘要:福克纳与白先勇,同是美国和台湾20世纪文学中现代派文学的“大师级”人物。从《文学杂志》中领略了现代文学魅力的白先勇,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无疑都受到福克纳小说的深刻影响。文章试图通过对《台北人》内容、形式的解读以及与福克纳小说的比较,在分析白先勇小说特色的同时,揭示出白先勇小说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关系。
关键词:白先勇;《台北人》;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图分类号:I206
白先勇,作为当代台湾短篇小说名家,其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短篇作品集就是《台北人》。他的小说创作,往往从个人出发推衍到历史、文化层面,藉由个体生命体验中的生存困境来透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其中不乏作家对那代人命运和中国传统文化前途的思考。这也是他的作品打上深深历史烙印的原因所在。
作为台湾现代派创作的主要代表,白先勇创作伊始就涉猎了大量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夏济安教授主办的《文学杂志》和由白先勇及其同学主办的《现代文学》杂志大量译介了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等西方现代主义著名作家及其作品,以及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夏祖丽在访谈中曾经询问“哪些西方作家对你影响最深”,白先勇的答案是“福克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除此以外,白先勇的好友欧阳子也在讨论《台北人》主题的论文《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中提到:“虽然白先勇和福克纳的作品,有很多不同处,却觉得这两个作家有几点相似:一、他们都偏爱喜回顾,有情,但逃避现实的失败者;二、他们都采用痴狂、堕落、死亡等现象,影射一个上流社会大家庭之崩溃,更进而影射一种文化之逐渐解体。”[1]329
本文拟从内容、形式两个角度分析白先勇《台北人》的创作特色,兼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做比较,以探究白先勇创作特色与福氏影响的关系。
一、“峥嵘岁月”时代的怀想
白先勇的《台北人》描绘了一个“民国战乱”时代的生活样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则构建了一个“南方没落”的时代。他们笔下所描写的“时代”,都是一个可以称之为“峥嵘岁月稠”的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在这种不平凡的时代面前,更容易突显出人的渺小与卑微,也更容易流露出对“失落家园”的怀恋与追悼。这也正是欧阳子所谓的,通过“影射一个上流社会大家庭之崩溃,更进而影射一种文化之逐渐解体”。
小说集《台北人》通过“台北人”的群体形象,再现了一个不平凡的动乱时代,这是一部由历史碎片与个体的人勾连起来的民国史。正如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白先勇论》中的评价:“《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2]诚然,无论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台北人》前言中白先勇自己的题词“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还是引用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抚今怀古意味极浓的诗,都与夏志清教授的论断不谋而合。
“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1]317:《梁父吟》回顾了辛亥革命;《冬夜》记录了五四运动;《岁除》重看了北伐战争;《秋思》再现了抗战胜利后班师回南京的盛况;《一把青》刻画了国共内战;《国葬》更是对国民党从大陆的最后撤退进行了描写。《台北人》带我们回到了民国那段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乱年代。
《台北人》14篇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梁父吟》中衰老的儒将朴公,抑或《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健壮的男工王雄,还是《游园惊梦》中上流社会的贵妇窦夫人,或者《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下流社会的舞女金大班,从表面上看,这些人物之间似乎没有任何交集和共同点,顶多就是他们都是“台北人”,但他们身上最大的共性是:他们都来自中国大陆,也都是随着国民政府的撤退才漂泊到台湾这座海上孤岛,他们同属于“政治的移民”。他们来的时候,还是黑发青年或壮年人,时代和家乡记忆深刻地烙印在他们心里。故事开始时,他们已经步入中年或暮年,随着乡愁日深,他们大多都沉湎于对过去岁月的怀念之中。尽管,随着青春逝去的那些岁月也许辉煌,也许不足为奇,但这些沉重的“峥嵘岁月”的回忆,都没有因为时光的久远或适应了一个新环境而逐渐被淡忘,这些沉在心底的积淀,反而日渐浓重地影响着甚至改变着他们现实中的生活。
如果说上述人物还停留在现实的、世俗的生活阶段,那么《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则早已超脱现实成为那个过去时代的记忆与精神象征。“尹雪艳总也不老”[3]3,“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3]3,“在人堆子里,像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踏着风一般的步子”[3]6,“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替那些作战的人们祈祷和祭祀”[3]14,“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3]19。小说中的这些描述,让“尹雪艳”不再是一个凡俗世界里的普通交际花,而似乎更像一个活在现世中的“幽灵”,更多地具有象征的意义,她冷冷地以一种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从她面前掠过一群又一群客人,见证了“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3]15。明明安全抵达了台湾,所有人本应得到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可是尹雪艳的客人们再也没能爬起来重新攀上人生的巅峰:他们的人生黯然失色,只能洗尽风华蜗居俗世,沦为一介庸庸碌碌的小市民。不管他们是否忘却或放下那个曾经的峥嵘岁月,他们现今都只能在海上孤岛偏安一隅,得过且过、声色犬马地混日子罢了。而尹雪艳本人,除了见证人,也是亲历者。她“从来不肯把它(台北的新公馆)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3]12,是因为她忘不了、更不想忘那段峥嵘岁月。她既怀念着曾经的自己,又想和那时的自己一较高下而不至于跌了份儿。她对自己的青春、自己的过去,对“失落家园”的那份执着中,也有着白先勇对自己的童年、往昔和“繁华家园”的无限回顾与眷恋。
同样地,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跟踪了美国南方社会几大家族从南北战争结束(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段长达60多年的历史中,众多人物的人生起落与坎坷轨迹。这段岁月,美国南方社会受到了来自北方工业文明的巨大波及和影响,传统农业文明迅速崩溃,日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所取代。短时间内的巨变,让许多习惯了南方旧有社会秩序、生活模式的原住民一时间难以接受和适应。于是,他们奋起反抗了,虽然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自己最钟爱的一部作品。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发生在杰弗生镇上康普生一家的故事。故事从1910年6月开始,到1928年4月结束。康普生家族在历史上曾经叱咤一时,出过一位州长、一位将军,家中良田广布、黑奴成群,家族势力强大。可是到了康普生先生这一代,却只剩下了一栋摇摇欲坠的旧宅,只有黑奴迪尔西带着她的外孙一家心甘情愿地伺候着旧主。故事发生的背景是那个工业文明快速崛起的时代,外面的世界每天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剧烈变化,而这个家庭的内部却在继续腐朽糜烂。康普生先生在世时,名义上是一位律师,却从不接洽业务,尽管如此,靠着祖上的积累全家生活尚能勉强支撑。然而,随着1912年他的去世,这个家庭就开始日渐瓦解、崩塌,不堪风雨了。为了继续维持家族表面的荣耀,家里卖掉了唯一的、原本属于小儿子班吉的一块草场,以筹措学费供大儿子昆丁去读名校哈佛。可是,昆丁却辜负了家人的期望,在花完了预交一年的学费后,投水自杀了。女儿凯蒂未婚先孕,生下孩子后又遭丈夫抛弃,只好把孩子寄养在母亲家中,只身跑到大城市里寻求出路。小儿子班吉是个先天性白痴,1928年时,尽管他已经33岁,可智力水平却仍停留在3岁孩童的阶段。这个破败的家中,只有二儿子杰生一人能够应运而起。随着金钱物质的影响和势力在美国南方的不断攀升,他逐渐学会了顺应潮流,一步步蜕变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物欲至上的自私自利者。他对家里的每个人都没有亲人之间的爱,而只有恨。他最恨的是自己的姐姐凯蒂,认为是她的不轨行为害自己失去了进银行工作的良机。所以他费尽心机把姐姐历年寄来的给外甥女的赡养费全都据为己有,以此作为报复。可是,无比自私的他千算万算没想到最后外甥女偷走了他的钱同一个推销员私奔了。而外甥女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出于报复,出于舅舅对自己管束、扭打的报复。
福克纳冷静地讲述着这些故事,作为同样从这样的背景中走出来的人,这一切正是他成长和经历的故事,他无法置身事外,却也只能以客观冷静的旁观者姿态讲述这一切。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者,福克纳的内在思想矛盾也清晰地显示出来:他无情地揭示出南方社会旧秩序在变革中的日渐解体,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完全自私利我的价值观,对时代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前行表现出些许无奈。同时,作为曾经的成员,福克纳不无留恋地表现出对南方社会曾经辉煌荣耀历史的眷恋,流露出对“失落家园”的怀念之情。而类似的“由盛而衰”的家族经历,同样的对过往的眷恋与失落交织的情感,也许正是福克纳能够打动和影响白先勇的重要原因。
二、意识流手法的取舍
白先勇是公认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与旗手,这不仅表现在内容和主题上,在创作手法上也有颇多体现。这一定程度也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识流手法以及与之适应的多变叙事角度的应用上。意识流虽未成为一个专门的流派,却是现代派文学最普遍使用的一种创作手法。它主要通过人物主观思绪流动、心理时间来结构纬文,因而具有动态性、无逻辑性和非理性的特征。运用这一手法最著名的西方代表作家有乔伊斯、福克纳、普鲁斯特等。这也就是欧阳子所说的两人都“偏爱喜回顾,有情,但逃避现实的失败者”,正是这一类型的人物才会与意识流产生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关系。
在《台北人》小说中,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最典型的就是《游园惊梦》。白先勇在《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回忆道:“我写这篇小说最苦,至少写了五遍,所以印象深刻。为什么我写得这样苦?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技巧及形式。”[4]172“我写第一、第二遍也不好,到第三、第四次时,稿子已丢了好几桶,还是写不出来。后来我想,传统的手法不行,而且这篇小说与昆曲有关,昆曲是非常美的音乐,我想用意识流的手法把时空打乱来配合音乐上的重复节奏,效果可能会好得多。”[4]173正是因为作者找到了“表现这小说最合适的方法,选到最合适的语调和结构”[4]172,才有了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一版本。
《游园惊梦》里,钱夫人因为受到程参谋和蒋碧月在一起的刺激,借着醉意朦胧,溯时间逆流而想起从前自己身上发生过的类似一幕。这段意识流描写和现实完美地穿插交织,借着灯红酒绿、喧嚣热闹的气氛渲染,让人读来感叹唏嘘、况味颇深。“虽说花雕容易发散,饮急了,后劲才凶呢。没想到真正从绍兴办来的那些陈年花雕也那么伤人。那晚到底中了她们的道儿!”[3]254这是钱夫人意识流活动的前兆。她刚刚在旧日姐妹们的劝说下饮了几杯,神思开始迷离恍惚。“他喝得两颧鲜红,眼睛烧得像两团黑火,一双带刺的马靴啪哒一声并在一起,弯着身腰柔柔地叫道:夫人——‘这下该轮到我了,夫人。’程参谋立起身,双手举起了酒杯,笑吟吟地说道。”[3]255这里,酒精开始发挥作用,钱夫人的神经已开始被麻痹,想起了自己心底最温柔的那一幕。旧情人的一声“夫人”使她陷入迷离,而程参谋的一声“夫人”却又无情地把她从回忆中叫醒,拉回到现实中来——这是十几年后的再重逢。酒意渐浓,花雕开始发力了,钱夫人一边看着眼前蒋碧月、程参谋两张油光闪亮的脸咧开白牙朝自己笑着,一边听着笛子洞箫伴奏下响起的《游园》曲调。“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3]260-261,这昆曲里的警句,让她想起了记忆深处的故事。年轻英俊的程参谋让她想起自己旧情人同样的风采华年:“他笼着斜皮带,戴着金亮的领章,腰杆扎得挺细,一双带白铜刺的长筒马靴乌光水滑地啪哒一声靠在一起,眼皮都喝得泛了桃花,却叫道:夫人。”[3]261昆曲里的警句又让她不由得想起瞎子师娘的“警句”:“你们这种人,只有年纪大的才懂得疼惜啊。荣华富贵——只可惜长错了一根骨头。”[3]262多么似曾相识的旧景重现,多么凄凉的触景生情!
“天——完了,荣华富贵——可是,我只活过一次——冤孽、冤孽、冤孽——天——(吴师傅,我的嗓子)——就在那一刻,就在那一刻,哑掉了——天——天——天——”[3]265这是最后钱夫人的意识流动达到了高潮,她已经分不清现实与回忆,找不到出口与方向。恰在此时,蒋碧月的一声“五阿姊,该是你《惊梦》的时候了”[3]265,一语双关,叫醒了沉迷醉梦中的钱夫人。“惊梦”的一层意思是指轮到钱夫人上场表演昆曲《惊梦》选段,另一层意思也暗指钱夫人被现实从迷梦中的惊醒。这里,白先勇意识流手法运用得恰到好处。现实中的情节不断地推展铺扬,回忆里的世界渐续地勾连生衍,两条线索交叉前行,故事也随之达到了高潮,最后曲终人亦散。
钱夫人对当年秦淮生活的回忆,也浸润着白先勇对自己那段南京生活岁月的追思与怀想。那时候,父亲白崇禧是地位显赫的高官权贵,家中经常会举行类似的活动,他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和昆曲结下不解之缘。雍容的贵妇,戎装的军官,美艳的戏子,歌舞升平的夜晚……,这些都是白先勇小时候的亲历,如今通过窦夫人的宴会、钱夫人的回忆,一一得到了再现,烛照着白先勇内心忆旧与失落、悲怆交织的复杂心情。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各式各样,从政府要员到退伍老兵,从豪门名媛到风尘舞女,从工厂主到小学教员,看似千差万别,仔细审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也都同作者一样,从大陆故土连根拔起,移植到了孤岛台湾,对故国,对往昔岁月,对“失落家园”,都留存着难以磨灭的记忆与怀想。
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是英美意识流小说中的杰出典范,也堪称扛鼎之作。小说前三章的三个叙述者,无论是白痴班吉,抑或后面的昆丁、杰生,从某个角度审视之,可以说都是心智不健全的人。而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一方面可以更直观地向读者展示人物生活和心理片段,增加作品中生活的真实感与可信度,另一方面也更好地配合了塑造特殊人物的特殊需要,心智不健全的人思维逻辑自然也不正常。如,昆丁在1910年6月2日这一天终于决定自杀。一整天里,他都在为最后的一刻做着准备,他的精神状态始终处于一种极度的紧张与亢奋中。尤其是中间十几页描述昆丁与吉拉德打架而陷入昏迷时的潜意识活动,文字没有标点没有分段,不停地变换情节。“我抓住了她的手腕 停一停别撞了 我知道他不会打你的我知道不会的”[5]160这短短的三句,里面已经包含了四个人物。第一个“我”指“昆丁”本人,“她”指凯蒂,第二个、第三个“我”指“施里夫”,“他”指吉拉德,“你”也指昆丁。这种极度的混乱、含混与纠缠,必须紧密联系上下文才能读懂昆丁到底在想些什么。和许多大家族成员挥之不去的恋旧恋故情结一样,福克纳虽然对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崛起持冷静接受的态度,但他还是流露出了对旧有伦理和秩序的挽留神情。小说中,每次班吉从球场周边路过都会哼哼唧唧,表示出一种不情不愿的委屈姿态,这也正是福克纳心中情感的折射,“也许那一切必须接受,但是我并不喜欢”。
白先勇的出色,在于他对西方现代派的接受是有选择的,他的作品虽然融入了诸如意识流这样的西方艺术技巧,却并没有一篇是纯粹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大多作品仍然有着现实主义的基调。他的小说大多都是按照正常的时序开始情节的铺展,以情节来推动人物命运的发展,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代清楚,故事的可读性较强。意识流手法只是在创作需要时才被采用。《游园惊梦》从表面看,主要正面描述了钱夫人来窦夫人府上赴宴的一段经历。小说以钱夫人乘车来到窦公馆开篇,结局又回到了曲终人散钱夫人等车离去。只是在中间部分借着几分酒意,恰如其分地插入了意识流的描写罢了。
比起福克纳铺张扬厉、空穴来风式的意识流,白先勇的意识流手法不仅有迹可循,也比较含蓄内敛。白先勇的意识流,是现实与回忆交织流动,互相推动情节向前发展。虽然不断有现实的打扰,回忆暂时中断,可是一有机会,它还是会自动连续下去,形成一个按照正常时序推演的完整情节。纵使中间被暂时割裂,但仍能还原为一个完整故事。而福克纳的意识流描写则完全融入现实的骨髓之中,它们全都是支离破碎的片段式记忆,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只有读罢全篇才能从断裂琐碎的细节中对作者所讲述的故事有一个大概的把握。
必须承认,为了更好地发挥意识流手法的特色,福克纳在叙述角度上也有许多大胆的尝试。《喧哗与骚动》全书四章,每章各有一个不同的叙述者。前三章的叙述者分别为康普生家的三个儿子:班吉、昆丁、杰生。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一遍自己的故事。最后一章才从黑女仆迪尔西的角度,其实就是作者的“全能视角”,讲述了剩下的故事,填补了前面故事的留白。虽然看似每个人只是自说自话,可是读者们最后才发现从未正面出场的凯蒂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角。正是她,才串联起了这个家庭,串联起了整个故事,所有人包括讲述者的所作所为都和她有着紧密的联系。
白先勇对福克纳在叙事角度方面所做的变革与创新也进行了有益的模仿与借鉴。在小说《国葬》中,他使用了同《喧哗与骚动》中前三章相同的视角,从次要人物秦副官的角度,观察和描写了葬礼主角李浩然将军的一生经历与众人评说。这种手法在早期小说《玉卿嫂》中,也已经显露端倪。《玉卿嫂》中的“我”,既非主要人物,也非作者,只是一个讲述视角,通过他的观察讲述,读者才得以知晓玉卿嫂的故事。只不过,这种现代派的手法,在白先勇的《台北人》中运用得更为娴熟。
总体看,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1]318。 在刘俊教授的《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访白先勇》一文中,白先勇曾说:“我很小的时候,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的感觉,感到世界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人世之间,事与物,都有毁灭的一天”[6]427,并希望“能够把‘家’和‘国’合在一起”[6]462。他把自己的创作主题归于表现“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7]。他虽然是“台湾现代派小说的旗手”,事实上他所秉持的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文化立场和思考角度,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气度;同时他吸纳了传统白话小说注重细节刻画和白描手法,兼顾了古典传统与现代技巧,将二者进行了很好的融合,从而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与白先勇由己及人的立场不同,福克纳的思考更多是基于对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的叩问。他的作品主题思想可归于《圣经》,终身追求的主题也是一种宽泛的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他的作品,对传统妇道观念、父权制度、种族矛盾等问题的思考与批判超越了民族、国家,而适用于全人类。他的爱也超脱了民族国界,而具有悲天悯人的基督精神,因此被白先勇尊为“文学的最高境界”而极为推崇[8]。这大概也是白先勇崇尚、效仿福克纳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M]//白先勇.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白少帆.现代台湾文学史[M].沈阳:辽宁出版社,1987:433.
[3]白先勇.台北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白先勇.我的创作经验[M]//白先勇.树犹如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6]刘俊.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访白先勇[M]//白先勇.树犹如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白先勇.蓦然回首[M]//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夏祖丽.握笔的人[M].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
责任编辑:庄亚华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6.03.003
收稿日期:2016-05-27
作者简介:孟飞(1993—),男,硕士研究生。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6)03-0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