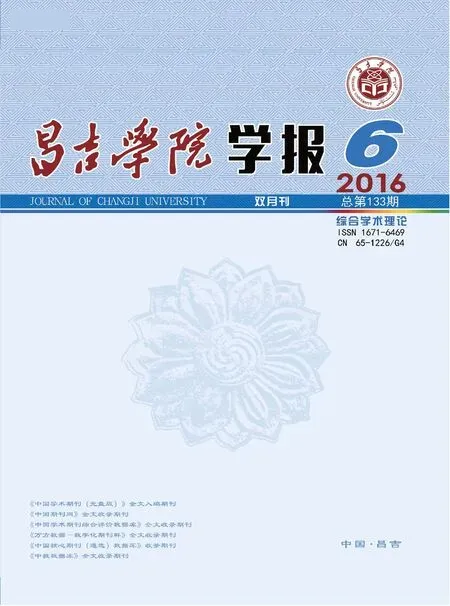族群·女性·现代化
——里慕伊·阿纪文学创作的几个关键词
2016-03-29代亚平
代亚平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1)
族群·女性·现代化
——里慕伊·阿纪文学创作的几个关键词
代亚平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1)
文章以台湾泰雅族女作家里慕伊·阿纪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族群书写、女性悲剧命运、原住民与现代化三个方面来探析里慕伊·阿纪文学创作的特色,并简要分析其原因。
里慕伊·阿纪;泰雅族;文学创作
一、里慕伊·阿纪(Rimuy Aki)及其创作
里慕伊·阿纪(Rimuy Aki),汉名曾修媚。1962年生,台湾泰雅族新竹县尖石乡葛拉拜部落人。她从事学前教育十余年,曾任幼稚园园长,目前于北县小学担任泰雅族语教师,以及泰雅族语配音员。主要写作种类有学前教育专文、青少年心灵成长专文、生活散文和小说。她的作品曾多次获得台湾山海文学奖和原住民文学奖,目前已出版随笔集《山野笛声》(2001),泰雅族神话传说故事集《彩虹桥的审判》(2002),两部长篇小说:《山樱花的故乡》(2010)与《怀乡》(2014)。
身为女性作家的里慕伊,与台湾同时期其他原住民作家相比,她显得有点特别。当同时代的原住民作家都以慷慨激烈、义愤填膺的言辞大声批判,为原住民发声抗争之时,她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淡定温柔的气质、清新质朴的文风。她的文字始终极为细致婉约,带有女性独有的细腻柔和气质。她很少用愤怒的语气、激昂的文字去叙说原住民的悲情与伤痛。因此,“有些人质疑里慕伊作品缺少原住民文化质素与基因。”[1]但当阅读完里慕伊的全部作品,就会发现,这种质疑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纵观里慕伊的创作历程和作品,她始终都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她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原住民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之上。对部落族群的观察与书写、对原住民女性命运的关怀与反思、对现代化给部落与族群带来一系列问题的思索与反省,这些都成为了她创作的关键所在,本文也试图从这三个方面来探析里慕伊的创作特色。
二、坚守者:族群书写与文化关怀
里慕伊陆续出版的几部作品,几乎都将目光聚焦在了对族群的书写上。2001年出版的随笔集《山野笛声》,里面不仅收录了里慕伊信手写来轻巧有趣的部落族人、山上家人、城市友人、学前儿童平凡与琐碎的故事,也有对现代化冲击下部落与族人出现的深刻变化与种种弊端的严肃审视,如传统文化传承的断裂,涌入都市在夹缝中生存的原住民、族群少女的堕落,原住民儿童教育,等等。2002年出版的《彩虹桥的审判》是里慕伊对泰雅族神话传说进行重新收集整理写成的一部作品,是面向青少年推出的介绍原住民山海文化的丛书,以儿童喜爱的故事形式讲述泰雅族的族群起源、信仰禁忌、传统习俗等神话传说。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樱花的故乡》讲述泰雅族堡耐一家的迁徙史以及与其他原住民相处交往的故事,并在小说中详细呈现了泰雅族的社会组织、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等。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怀乡》则描述了20个世纪40年代泰雅族部落一位自幼家庭支离破碎的女子——怀湘的悲惨命运故事。
里慕伊的书写焦点从开始至今仍然是以族群为重心,她始终怀着深深的爱去描绘族人的生活家园,部落居民互持互助的生活,亲人间真挚的情感,以及泰雅族的传统文化。她既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和传承者,在她作品中有一个显著的特色,便是对族群传统文化的高度关注,第一部作品《山野笛声》虽是没有明确目的,只是出于自身爱好断断续续书写而成,但整部作品的潜意识目光也都在关注和书写族群文化的发展和变迁,而《山樱花的故乡》和《怀乡》这两部长篇小说更是将泰雅族的传统文化有意识地在其小说中展现,小说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描绘泰雅族的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传统文化,甚至将族人之间的泰雅语对话都以音译的形式镶嵌于文中。这些都体现了里慕伊对本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她以不断关注和书写族群和部落生活的方式表达了作为一名泰雅族作家的责任感。但里慕伊并不是一个盲目的讴歌者,作为一名泰雅族现代知识分子,她始终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族群和部落的文化,当族群遭遇歧视和不公对待,她勇敢为族群发声,但族群和部落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她针砭时弊,给予毫不手软地揭露和批判。如,《怀乡》中揭示了女主人公怀湘在男权中心为主导的泰雅族部落所遭遇压迫的悲惨命运,看似温和细腻的文字背后却透露出里慕伊对泰雅社会长期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给予了批判和反思。里慕伊在《怀乡》《山野笛声》中反映的女性命运、部落土地、教育、就业、婚姻等问题都是沉重的话题,但她的文字仍然以婉约细腻呈现,这也是她作品的一大叙述特色。
里慕伊在书写族群和部落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将目光仅仅局限于泰雅族,她的视野是开阔包容的,她不仅写泰雅族人的日常生活,也写泰雅族和其他原住民、汉人之间的接触和往来,如在《怀乡》中怀湘的好友秀芳就是汉人,而《山樱花的故乡》中也描绘了堡耐一家迁徙到高雄那玛夏乡之后和其他原住民之间的交往、互助的生活,里慕伊的族群书写不是狭隘地只关注泰雅族的生存与发展,她更关注的是“人”共同的情感,这也是她的作品在情感上使人感同身受的原因所在。里慕伊形容她最初的写作是“浪漫的外遇”,而在她这些年持续地书写过程中她早已“把这个外遇扶正”。她对原住民部落和族群的高度关注和持续书写,体现了她作为一位原住民作家对民族文化的坚守;而她对族群命运变迁与沉浮的观照与关怀,恰好彰显了一位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
三、控诉者:原住民女性悲剧命运
里慕伊·阿纪作为一位泰雅族女性作家,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腻敏锐和切身之感一直关注原住民女性的生存境遇和困境。而在她对女性命运的书写过程中,她尤其关注到长期在父权制度下受欺压和受到不平等对待的泰雅族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这些部落女性在面对社会变迁所表现出的阵痛和不适。命运多舛、悲剧人生也成为了这群女性的共同伤痛。里慕伊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将原住民女性的境遇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不禁对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原因进行思考和反省。
《小公主》中的甜甜从人人羡慕的小公主沦为婚姻失败、家庭破碎、一无所有的落败女性。长篇小说《怀乡》则呈现了泰雅族女性不幸与卑微的凄惨命运史,经历了不幸婚姻的生母哈娜和大女儿梦寒,和至始至终贯穿小说的主要人物怀湘。女主角怀湘从小就过着支离破碎和缺少关爱的童年生活,懵懂无知的年纪却奉子成婚,婚后丈夫的懒惰和家庭的贫穷逼迫她将所有的家庭重担一人承受,但最终换来的却是无能丈夫的背叛和抛弃。第二段都市婚姻,虽有短暂的浪漫,但也并没给怀湘的命运带来转机,反而使其再次面临失败婚姻所带来的一切苦果。最后在无奈之下,怀湘带着女儿小竹回归部落,但回到部落之后等待她的却是兄妹之间激烈的遗产争夺之战,亲人的相继离开,养育幼子的凄凉现实处境。
怀湘具有泰雅族女性所有该有的美好品质:坚强、勤劳、善良、自重、贤惠、宽容、独立、坚韧,但她得到的却是苦难和悲剧串联的人生。思索泰雅族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显然是里慕伊创作的一个“隐而未发的心情”。里慕伊作为现代泰雅族女性,她自觉以女性身份感同身受地观照这些命运悲苦的泰雅女子的生存际遇,含蓄温和的文字中透露着对泰雅族女子悲剧人生的根源思索。对那些正发生在部落的丑陋现象和风俗进行了不露声色地揭露和批判,正如孙大川对其的评价,“里慕伊笔下既不隐瞒也不找借口,她直接让我们面对丑陋的自己。”[2]
里慕伊笔下这些女性的命运如一首首凄凉的挽歌,我们审视甜甜、哈娜、怀湘、梦寒的命运,发现她们最终殊途同归地陷入了悲剧性命运的深渊,且依循着某种可怕的恶性循环。探析这些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显然无法绕过站在这些女人背后的男人们,以及熏陶和塑造泰雅男性和女性的传统文化环境。传统的泰雅族社会属于父系社会:男人至上,女人为次,是典型的重男轻女社会。在泰雅族社会将男子称为“Panasalu Qa⁃lang”,意思是社会的中坚。而将泰雅族女子称呼为“Nanigan Pinta”,意思是煮菜和觅食的人。泰雅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也是“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此种性别分工带上了一主一附的意味,它暗示了男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女性所处的附属或辅助角色。“而看似出于自然或两性生理条件的分工,实际逐渐成为了男性家长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依据,成为整个父系统治秩序的最基础的一部分。”[3]在长期的男权文化中,女性处于被压迫、受支配的客体地位。处于男权文化中的怀湘,不管她再怎样努力,还是无法将自己的命运转向自己所期望的轨道,而最终还是被驱赶着一步步踏上了回不了头的悲剧之路。里慕伊以温和的态度批判和抨击了女性悲剧的真正根源——传统文化所塑造的男权中心思想。但让里慕伊觉得更可怕的却是,泰雅族女性在漫长的父权制社会历史中,已经潜移默化地认同和接受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标准,并逐渐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泰雅女性命运的悲剧性就在于沉默坚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准则,这个思想根深蒂固地盘踞在女性的意识深处。以至于当这些成为女性悲剧的根源时,她们却无力挣脱,最可悲的是她们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因为在男权文化的环境中,男人的中心性和主宰性从未改变。
正如里慕伊在《怀乡》序言中的坦白:“这故事在我心中沉淀了十余年,始终想要把它说完,献给在我生命中遇见的各位‘怀湘’姐妹,她们或许也在你的身边,或许就是你自己,我以这本书向生长在山稜上的冷杉——‘怀湘姐妹们’致敬。”[4]里慕伊通过书写泰雅女子怀湘的生命际遇,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了当代台湾泰雅族女性的生存现状和困境。作为一位泰雅族的女性作家,当面对本族的姐妹遭受如此悲惨境遇,她是既悲愤又怜惜,她试图以文字来抚慰像怀湘这些在男权文化下受压迫的女子,也期望透过自己的文字能够给予她们一些无形的力量,让她们有勇气去打破世俗的、不合理的束缚,去追求男女平等的生命权利,活出女性的精彩人生。
四、反思者:原住民与现代化
时代的巨轮轰然碾过,社会的变迁与现代文明与时推进,似乎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台湾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与措施,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而“山地现代化”一系列的政策实施,也迫使原住民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之中。“部落的社会共同体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面临解体,传统农业的式微导致了大量的部落青年直接流向城市。”[5]而大部分原住民青年没有接受相应的教育,也没有掌握都市生存的技能,因此进入都市往往从事的都是最底层的职业,成为在城市“讨生活”的边缘群体。结婚之后就定居都市的里慕伊一直以一颗敏感、忧虑的心观察着原住民的现代化变迁历程,并对多元的现代文明给族群带来的一系列阵痛、迷茫、质疑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山野笛声》是由一个个篇幅不长的短文组成的随笔集,但其中所反映的一些社会问题却十分沉重和无奈。《商店》中的原住民少女沦为“幼妓”在都市卖笑,反映了原住民少女进入都市生活的卑微和无奈处境。《老顽童和他的王国》中父亲坚决拒绝出高价想要购买部落土地而进行旅游开发的商人,父亲对土地的坚守其实也是对现代化入侵部落家园的一种强烈反抗。《祖灵祭与老猎人的叹息》中祖灵祭的变迁和猎人已经无处狩猎的现实,流露出了传统习俗面临失落的无奈。
《到此为止》一文中,里慕伊审视了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泰雅族的传统风俗Gaga的演化与变迁。Gaga是泰雅族社会组织结合最重要的要素,Gaga包括了泰雅族的伦理道德、法律、禁忌、宗教信仰、礼俗等规范要求。一对年轻人因为触犯了族群的道德禁忌,长辈们自觉遵循传统习俗,决定按照Gaga来做告解仪式,以便求得祖灵原谅。长辈面对Gaga的一系列仪式以庄严肃穆的态度认真待之,但两个犯错的年轻人不仅没有意识到触犯了族群的伦理道德,且在合解仪式当天拿着手机漫不经心地玩着电子游戏,俩人还在一旁调笑,对祖先传承的习俗轻慢以对,毫不在意。里慕伊对此不禁发出悲痛地感慨:“哎!难道过去泰雅族群谨守分寸的严谨生活态度,在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里,必然要被淘汰,真正‘到此为止’了吗?”[6]里慕伊敏锐地意识到由于现代文明的入侵,年轻族人的心灵和精神逐渐被所谓的都市现代文明填塞,而族群的传统文化却面临被冷落甚至被抛弃的尴尬处境,里慕伊为泰雅族传统文化的式微而深深担忧。
《八个男人陪我睡》讲述的是在里慕伊外婆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泰雅族部落还保留了非常传统的男女恋爱习俗。当一个女子成年后,也就是纹面之后,若有男子对她有意追求,就可以通过长辈的推介后,安排男子在女方或男方家里与女子同睡一床。但男女双方并不会逾越传统习俗的要求,整个夜晚一般都是聊天或唱歌。里慕伊外婆年轻的时候,最多的一次有八个男人陪睡,且从未逾越族群的道德规范。而这一传统现在已经在多元的现代社会逐渐失落,部落的青年男女早已在都市社会中学会了新的恋爱方式。而青年男女相继出现的同居、怀孕、早婚现象却也成为了丢失传统约束的代价。传统道德瓦解后的空虚、部落尊严丧失后的颓废,成为里慕伊最深沉的忧虑所在。
《Ja-ki里梦我来看您》讲述了里慕伊站在外婆的坟冢前,回忆过去与泰雅族外婆在一起的美好往事,抒发了对外婆的浓浓思念。通过追忆小时候外婆给她讲述与泰雅族相关的神话、传说、习俗、信仰、禁忌,对比如今部落由于现代化开发建设大潮的兴起,身处大自然腹中的山海部落被迫改变了容颜,人心追求物质而衍生出的浮躁和贪婪,面对都市纸醉金迷的诱惑,族人抛弃了祖先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而到最后“连怎样生活都给忘记了”。变样的部落,迷茫的族人,失色的山林,使里慕伊痛心疾首,悲情地呐喊出,“台湾的山河变色,大地受伤了。岛上的人们因着贪婪,逾越了大自然的法则,正在哀哭中挣扎生活。我们的心被厚尘蒙蔽了,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祖先的灵。”[7]
里慕伊对在现代化进程中族群和部落出现的扭曲和丑陋现象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但在情感和自我归属上却不断地向本族文化进行靠拢。她也试图通过自己的书写,希望能够唤醒那些被都市文明迷惑的族人,希冀能够给寻找文化之根的族人开辟一条回归之路。显然《山樱花的故乡》就是她自觉溯源族群文化的一部力作,这部长篇小说是她以文学的方式来再现与重构泰雅族的历史与文化的作品。表层故事内容讲述了堡耐·雷撒一家从北部的斯卡路部落迁徙到高雄那玛夏乡开垦的迁徙史,而深层意蕴却是里慕伊用一贯细腻的笔法将泰雅族社会组织要素Ga⁃ga、传统风俗、宗教观念、神话与传说等族群传统文化有意识地嵌入小说中,充满了对族群文化细节地捕捉与铺陈。里慕依也尝试以语言这把钥匙来打开族群人们熟悉的心灵世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包含着不同族群的文化积淀、文化含义、文化精神。泰雅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里慕依一直用汉语进行创作,但在《山樱花的故乡》和《怀乡》这两部长篇小说中,她有意识地将泰雅族人之间的母语对话以音译的形式镶嵌于文中,而只要出现泰雅族特有的名称或事物,她会详细地解释其历史及含义。里慕伊试图通过文学来再现与重构泰雅族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作家对抗族群文化失落与遗忘的方式;她的书写也为族群能够重新感受传统文化提供了可能,或许还能从中汲取祖先传承的生存智慧,这是一位原住民作家对族群的终极关怀。
结语
“文学的发声,初时确是微小的星火,而星星之火,亦可燎原”[8],恰好形容了里慕伊的创作历程。她始终以一颗真诚的心去感受和观察所处的世界,也一直以她细腻朴实的笔触为族群勇敢发声。对部落与族群的持续关注与书写,使我们看到她对部落变迁的关切,及对族群文化的认同与坚守;对族群女性悲剧命运的控诉和反思,让我们看到她作为女性作家的细腻与悲悯;对现代化带给部落与族群的冲击和扭曲给予了无情批评,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女性作家的理性与勇敢,同时她试图通过文学来再现与重构泰雅族的历史文化记忆,让我们看到了她对传承族群文化所作出的努力。
[1]里慕伊·阿纪.山野笛声[M].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1:06.
[2]里慕伊·阿纪.怀乡[M].台北:麦田城邦文化出版,2014:06.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3:05.
[4]里慕伊·阿纪.怀乡[M].台北:麦田城邦文化出版,2014:19.
[5]王志彬.山海的缪斯: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3.
[6][7]里慕伊·阿纪.山野笛声[M].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1:122,177-178.
[8]董恕明.山海之内天地之外:原住民汉语文学[M].台南:台湾文学馆,2013:111.
I041
A
1671-6469(2016)-06-0034-05
2016-07-12
代亚平(1991-),女,新疆阿勒泰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硕士生,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