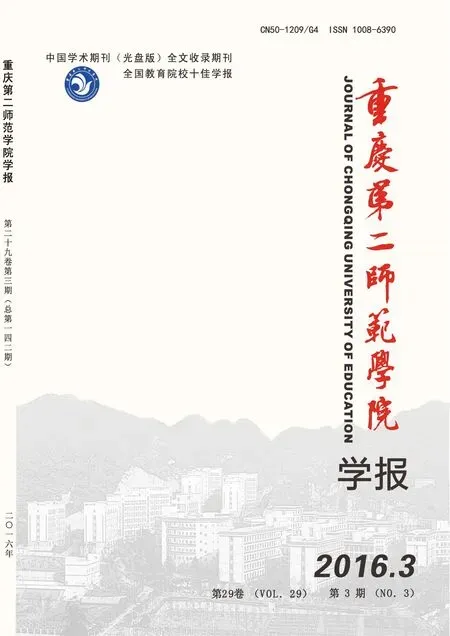《西游记》的形象学阐释
2016-03-29刘楚
刘 楚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西游记》的形象学阐释
刘楚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摘要:《西游记》充满了各种光怪陆离的关于异域异国的想象性“形象”,从形象学的视角阐释这些形象,能揭示创作者在书中贯穿的迷恋与批判的双重意识,由此生发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张不同面孔,以及创作者最终想象性确立的以人身、中土、佛法为本位的华夏式建构。
关键词:《西游记》;形象学;阐释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中新兴的一个学科分支,它侧重于文学作品中的异域异国“形象”问题的研究,其意义并非单纯地复制、再现真实,而在于研究这类形象是如何制造、想象出来的。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不但对认识异域异国这一“他者”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而且对认识制造、想象异域异国“形象”的主体也至关重要。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充满了异域异国①的想象性“形象”,但自其成书以来,很少有人从文学形象学的视角进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形象学视角阐释《西游记》,揭示其文本中复杂的思想蕴涵。
一、两种意识:迷恋与批判
从整体上看,《西游记》采取的是顺叙的叙事视角,以取经为叙事主轴,以时间先后顺序用不同篇幅串联叙述取经缘起、取经旅途,以及唐僧师徒取经最终成功封神成佛。从回目上看,《西游记》第一回至第十二回可以说是交代取经缘起。在第一回至第七回,作者吴承恩以纵横恣肆、诡谲振荡的笔墨叙述孙悟空出生学艺,大闹天宫直至被佛祖压于五指山的故事,仙界用武力暂时稳定了天地、人神的秩序,对当时信奉“强者为尊”的孙悟空来说未必心服口服。第八回这一取经缘起部分起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上回写佛祖武艺“西方称第一”转向写其“福德无疆”,意图寻得东土取经人取回佛法“劝化众生”。第九回至第十二回,作者叙述玄奘的身世经历、唐太宗入冥也是极尽浪漫奇幻之能事,最终选定玄奘为佛家要找的取经人,从而从容地叙述完取经缘起,占全书最大篇幅的取经大幕继而拉开。
保尔·利科为形象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他把历史上所有的想象理论归纳为两条相反的轴:“在客体方面,是在场和缺席轴;在主体方面,则是被迷惑的和批判的意识轴。”[1]43《西游记》充满创造性的想象,以想象变幻多端著称。作者吴承恩作为想象的主体,在作品中时常显现出迷恋和批判意识,两者充满张力却又纠结缠绕。在取经缘起阶段,作者的迷恋和批判意识纠结缠绕突出表现在孙悟空取经前和唐太宗入冥两个叙事段落。
先讨论孙悟空取经前的故事。吴承恩在叙述孙悟空出身不凡,拜师学艺,学成大闹冥府和天宫时,一边用欣赏的眼光对其“明心见性”、“福至心灵”和“英雄气概”赞不绝口,并将其命名为颇具褒义色彩和肯定意义的“美猴王”、“齐天大圣”,一边又斥责其“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规箴”,还将其命名为具有一定批判意识和贬义色彩的“妖猴”。在孙悟空被压五指山后,作者一边叙述众神一派欢欣鼓舞,认为孙悟空“恶贯满盈今有报,不知何日得翻身”,一边又不无同情地暗示孙悟空“若得英雄重展挣,他年奉佛上西天”、“恶贯满盈身受困,善根不觉气还生”的命运;一边描写仙界举行安天大会“仙姬仙子歌舞,觥筹交错”时的热闹逸乐场景,一边又对比鲜明地描写孙悟空饥时吃铁丸子,渴时喝铜汁之凄清冷落场景。作者通过对孙悟空美丑互渗、善恶交织的形象塑造,以及颇具对比反差的场景描写,体现了其迷恋意识和批判意识肆意纠缠并难解难分的创作心理。作品出现了缝隙,却也正因为此,作品才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审美质素,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现代审美价值。
再讨论唐太宗入冥的故事。据鲁迅研究,俗文《唐太宗入冥记》“盖记太宗杀建成元吉,生魂被勘事;讳其本朝之过,始盛于宋,此虽关涉太宗,故当仍为唐人之作也”[2]71。也就是说,鲁迅直言在这篇俗文里,太宗入冥的缘由是其发动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杀害兄弟李建成、李元吉而“生魂被勘”,并认为该俗文乃唐人之作,只是为本朝讳,才从宋朝开始盛传。《西游记》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作品,其集大成和对前作“原型”的继承、超越和布鲁姆所说的“创造性误读”值得注意。对于太宗入冥之事,试将俗文《唐太宗入冥记》与《西游记》对读比较。《西游记》第十回将太宗入冥的缘由改写为魏征梦斩泾河老龙王,龙王怪罪于太宗食言“许救反诛之故”而导致其病死。在吴承恩笔下,太宗入冥的缘由虽不是“杀建成元吉,生魂被勘”,但太宗在崔判官陪同下入鬼门关游冥府时却还是让建成、元吉露面了。吴承恩对这一场景的叙述如下:“那青衣将幢幡摇动,引太宗径入城中,顺街而走。只见那街旁边有先主李渊,先兄建成,故弟元吉,上前道:‘世民来了!世民来了!’那建成、元吉就来揪打索命。太宗躲闪不及,被他扯住。幸有崔判官唤一青面獠牙鬼使,喝退了建成、元吉,太宗方得脱身而去。”由此可见,吴承恩虽然难免为尊者讳,没有如《唐太宗入冥记》将太宗入冥的缘由归为 “杀建成元吉,生魂被勘”,但运用了文学家“重写事实的虚构的权力”[1]49,将太宗父子在冥界相见时的尴尬,兄弟之间由至亲变为仇寇的人伦惨剧揭示得震撼人心。作者暗示玄武门之变的人间悲剧,隐含的批判之刃不可谓不锋利,有直指人心的力量。
将《西游记》里太宗在崔判官引导下游冥府与《神曲》里但丁在维吉尔的引导下游地狱比较一番,倒是别有风味。在此,本文比较吴承恩和但丁在他们各自的杰作中所共有的迷恋意识和批判意识。说但丁迷恋自己在《神曲》中的道德律令应该不会引起太大争议,借此道德律令,他如上帝般批判各种人间罪责;而吴承恩借道德律令进行的批判则要温和、谦逊得多,且并无鲁迅所说的“私怀怨毒,乃逞恶言”[2]155之弊。吴承恩作为中华古代士子,凭借的自然是主流的儒家之仁义、民间盛行的佛家之善恶果报等伦理道德,即如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借崔判官之口所说的“人生却莫把心欺,神鬼昭彰放过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作者迷恋冥府中的善恶果报,其善恶、是非观念在冥府或许能得到在人间可望而不可即的想象性补偿。作者这种对“彼岸”的迷恋,是否间接将批判之刃指向“此岸”之人间呢?与此同时,对于“枉死城”里的“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处草寇,众王子、众头目的鬼魂;尽是枉死的冤业,无收无管,不得超生,又无钱钞盘缠,都是孤寒饿鬼”,作者也是满怀怜悯之心。即使“玄奘入竺,实非实诏,事具《唐书》”[2]107,作者也还是利用文学家虚构的权利和便利,使其怜悯之心在《西游记》中借太宗还魂后下诏玄奘取经以超度亡魂得到想象性落实。
由取经缘起的叙述来看,迷恋与批判是吴承恩在这部小说创作伊始的两种基本意识。其实,吴承恩的迷恋和批判意识不仅表现在孙悟空取经前、唐太宗入冥这两个叙事段落,更表现在取经途中这一叙事段落。本文接下来将分析这两种基本意识在取经途中的表现形态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义。
二、两张面孔: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西游记》从第十三回玄奘踏上西游取经路途,陆续收服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等徒弟,一路西行,一路磨合,一路降妖除魔,直至写到第九十八回,唐僧师徒“在路上”的篇幅在全书所占比重最大。作者吴承恩在塑造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种种形象时,迷恋和批判之双重意识主要反映在借异国这一他者,表现其对中华的迷恋和批判,从而呈现其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两张不同面孔。
据前文所引,按利科的总结,在想象理论客体轴的两端分别是休谟和萨特的“再现式想象”和“创造式想象”理论。学者孟华解释:“把这两种理论运用到形象学研究中来,前者就使人把异国形象视作人们所感知的那个异国的复制品;而后者则将现实中的异国降为次要地位,认为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主要不是被感知的,而是被作者创造或再创造出来的……当代形象学明显倾向于萨特的理论。”[3]6《西游记》作者通过创造性想象,在唐僧师徒取经途中投射出的自我与他者,使中华与异域异国形成了微妙关系。
先分析异域异国人对中华的打量和想象。唐僧师徒途经宝象国时,该国国王便称“唐朝大国”,文武官员“无不叹道:‘上邦人物,礼乐雍容如此!’”,对唐王朝充满尊重,以至使用“大国”、“上邦”这样抬高唐朝而具有自贬意味的称呼。途经乌鸡国时,其“鬼王”叙说该国官员励精图治、全力抗旱时,也使用中华大禹治水之典故,称“仿效禹王治水,与万民同受甘苦”,同样充满对中华传说之明君的景仰。途经车迟国时,该国国王“兴道灭僧”,欲法办唐僧,太师忙对国王启奏,连称“东土大唐……号曰中华大国。到此有万里之遥,路多妖怪。这和尚一定有些法力,方敢西来。望陛下看中华之远僧,且召来验牒放行,庶不失善缘之意”,则揭示了该国太师眼中的“中华大国”之威慑力。在唐僧师徒与该国国师斗法,悟空诈死,唐僧说要为徒弟烧纸钱时,该国国王已对唐僧师徒有了几分敬意,称赞“那中华人多有义气”,到最后唐僧师徒斗败该国妖怪变的国师,国王对唐僧师徒已是彬彬有礼,言听计从。途经西梁女国时,驿丞叩头称唐僧为“上邦老爷”,称赞唐僧“相貌堂堂,丰姿英俊,诚是天朝上国之男儿,南赡中华之人物。那三徒却是形容狞恶,相貌如精”,唐僧之相貌与“天朝上国”呈正相关关系,还拿其徒弟之相貌与其形成美丑对比。唐僧师徒计拒该国女王成婚之请,腾空而去时,慌得该国君臣跪在尘埃,都道:“错认了中华男子。”又道出“唐御弟”之“有道”,并间接道出“中华男子”品德之高尚。途经祭赛国时,国王听说唐僧师徒欲倒换公文,即宣其上殿,表现得不卑不亢,虽礼节性地称“大唐王”,却也自称“西域上邦”,直至看到唐僧师徒有腾云驾雾的本领,才称其为“圣僧”。途经木仙庵时,拂云叟直言“道也者,本安中华,反来求证西方。空费了草鞋,不知寻个甚么?”认为道在中华,而怀疑西天取经是否有意义。而后与唐僧以诗唱和,又称“我等皆鄙俚之作,惟圣僧真盛唐之作,甚可嘉羡”,对唐僧和唐朝文化景仰不已,也不管唐太宗时期是否为盛唐。途经朱紫国时,国王显然对唐朝不太了解,问道:“法师,你那大唐,几朝君正?几世臣贤?”及至听到唐太宗派唐僧西天取经以超度冤魂时,叹道:“诚乃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此时已不是因唐朝的国力之威慑而尊重唐僧,而是因唐朝“君正臣贤”而礼遇之。途经狮驼国时,连三怪都称唐僧为“上邦稀奇物”。途经比丘国时,国王虽喜称“远来之僧,必有道行”,但那妖怪变的国丈却对唐僧师徒倨傲无礼。及至唐僧师徒挫败妖怪变的国丈,救下婴儿之后,国王则“苦留求救”,百姓感谢其救命之恩则直道“唐朝爷爷”,俨然唐朝来人已成本领高强和文明正义的化身。及至途经唐僧师徒所称道的“极乐之乡”天竺国的金平府时,竟然还有和尚说“我这里向善的人,看经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华地托生,才见老师丰采衣冠,果然是前生修到的,方得此受用,故当下拜”,这简直将中华神化到肉麻的地步了。当看到唐僧的三个徒弟相貌丑陋之后,才一惊一乍地认识到“原来中华有俊的,有丑的”,可以推想,由于距离遥远,交流阻隔,其对中华只有美好的想象,而没有半点理性成分。后面唐僧师徒所经之地的人,虽没有像上述僧人对中华膜拜到近乎无知的地步,却也对唐僧礼遇有加,当然不乏好奇地打量和询问。由此看来,作者吴承恩叙述异域异国人对中华的打量和想象,表现的是其对中华硬实力和软实力各方面的迷恋和欣赏。在此,稍加思考便知,作者笔下异域异国人对中华硬实力和软实力各方面的迷恋和欣赏,并非完全出于客观再现,而是作者经由对异域异国人言行的想象,曲折地表现自己对中华的迷恋和欣赏。
再分析唐王朝人(以唐僧师徒为代表)对异域异国的打量和想象。唐僧师徒途经宝象国时,作者以唐僧的视角写道,“猛抬头,只见一座好城,就是宝象国。真好个处所也……九重的高阁如殿宇,万丈的层台似锦标。也有那太极殿、华盖殿、烧香殿、观文殿、宣政殿、延英殿……”对该国的这座“好城”的描绘,作者为何使用“也有”一词?也就是说,是唐朝“本有”。这说明唐僧在打量和注视他者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来理解、消化或许带有异质性的他者,因而也就能理解唐僧观察异域异国的风土人情、建筑物貌时常用的“与中华无异”之类的说辞。巴柔曾在《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中说:“这个‘我’要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3]5由此可见,在自我和他者这个二元对立项中,他者和自我之间的力量对比并非势均力敌,等级关系也并非平起平坐,而常常是自我单方面否定、言说、驯化、同化了他者。萨义德认为,东方常常作为西方的他者出现,东方学是西方人建立的注视、研究东方的带有浓厚意识形态性的一门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机制,这一权力话语机制是“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4]4。东方学作为一门学术研究的学科尚且具有意识形态性,人们自然不能否认吴承恩在写作《西游记》时带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当然,自不能苛责文学家写作一部文学作品时还要保持不偏不倚、客观中立的态度,因为“超意识形态”本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无法企及的乌托邦。正如利科所坦言的,“不论何种‘超结构’也都能进行意识形态的运作,科学、技术和宗教是这样,哲学的理想主义也是如此”[1]62。作者对中华的欣赏和迷恋充分体现在《西游记》中掩盖不住的意识形态性及其话语操作的痕迹。作者利用自己作为创作主体的权利和便利,在写异域异国人对中华的打量和想象时难以掩藏中华的优越感,对异域异国的打量和想象也会出现以中华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途经乌鸡国时,作者以诗为证:“海外宫楼如上邦,人间歌舞若前唐。”别国的繁华也只能“如上邦”、“若前唐”,如是而已。途经西梁女国时,作者写道:“你看那西梁国虽是妇女之邦,那銮舆不亚中华之盛。”该国再繁华,也终究只是“不亚中华之盛”。此外,玄奘作为唐人自不待言,而孙悟空一干徒弟也常常以“天朝上邦”人自居。更不要说唐僧师徒途经诸国常常妖魔盛行,君王或昏庸或力弱,需要唐僧师徒出手相助,匡扶正义,并常常需要他们教这些国家的君王治国之道。比如,途经原本杀和尚的灭法国时,唐僧师徒经过一番打斗力挫妖魔之后,国王求玄奘改换国号,孙悟空挟着恩威紧接话头说:“陛下‘法国’之名甚好,但只‘灭’字不通,自经我过,可改号‘钦法国’,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胜,风调雨顺万方安。”此时的悟空俨然已驯化且自命为佛家的急先锋和代言人。
如果将大唐作为唐僧师徒取经的起点,天竺作为此行的终点的话,那么沿途诸国终非唐僧师徒的久留之地。正因为唐僧师徒充其量只是沿途所经诸国的过客,所以作者搦笔为文时难免对唐僧师徒所经诸国进行矮化,甚至是妖魔化的意识形态式想象。而在唐僧师徒对天竺这一“西方佛国”、“极乐之乡”的注视和打量中,体现了作者的乌托邦式想象。让-马克·莫哈曾区分过乌托邦和意识形态这两张不同面孔的功能:“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形态恰要维护和保存现实。”[5]60前文已揭示了《西游记》中唐僧师徒途经诸多异域异国时,作者对中华的迷恋和那种以中华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操作,而作者对天竺这一“他者”的想象则充满了乌托邦色彩,其指向是“质疑现实”、批判中华这一“自我”的——在作者看来,中华不应以武力之霸道治国,而应以仁义之王道治国;以儒释道三教并立还不够,而应突出佛教的地位;佛教之小乘佛法还不够,而应去西天求取大乘佛法。文韬武略兼备之雄主如唐太宗者若以霸道治国,也终究难逃冥界的审判和冤魂的缠绕;只有佛家之大乘佛法才具有无边的法力,“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作者借佛祖的愤怒,展开对“东土”中华的批判可谓有雷霆万钧之势:“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 这里作者写佛祖的愤怒,可以说完全是儒生对佛教原始教义的改写和挪用,名为佛祖,毋宁说是借重佛祖的权威诉说儒家之忠孝仁义和民间之原始道德。当然,作者在对“东土”中华进行批判之余,对“西天”天竺的仰慕仍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换句话说,他者并没有压倒自我,作者的乌托邦色彩也并没有否定其意识形态性。在描写天竺部分,天竺这一他者与唐朝这一自我平分秋色,作者此时兼具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张面孔。比如说,唐僧师徒经过天竺之下郡玉华县时,作者以诗为证写其热闹非凡时也只是称之“不亚长安风景好”,并经唐僧之口说“细观此景,与我大唐何异!所为极乐世界,诚此之谓也”,在作者笔下,天竺再繁华也是不可能超过唐朝的。
三、想象性建构:人身、中土、佛法三位一体
《西游记》结尾仍然是中国古代小说常有的大圆满结局,第九十九回至第一百回叙写唐僧到达西天取得真经,并“径回东土,五圣成真”,至此,西天取经圆满结束。在作者吴承恩笔下,西天取经的筹划者、支持者和执行者各有所得:佛家归化唐僧师徒,诚如谢肇淛《五杂俎》所言:“《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服,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6]315并借唐僧师徒之手驯服不敬佛,乃至灭佛之人,将大乘佛法远传至东土;唐太宗借求取的真经“超脱幽冥孽鬼,普施善庆”,并借唐僧西天取经之旅使唐朝声名远播;唐僧师徒历经磨合,相互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和谐,同时也成功地“将功折罪”,为自己“正名”,跻身仙佛之列。在西天取经途中,作者曾借玄奘之口公然说“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其为《西游记》设定的最终结局即是以人身、中土、佛法为本位的意识形态的想象性确立,也即作者的迷恋意识最终压制批判意识。
以人身为本位,这反映了作者对人貌的迷恋。在作者笔下,妖怪不具人身人貌,形象丑陋,并且妖怪也往往因为形象丑陋而承担吴承恩施加在其身上的道德之恶,故而理所当然地排除在作者所说的“天、地、人、神、鬼”这“五神”之外,等级低到不入流。妖怪从形象、称谓到道德属性都被污名化,这反映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集体政治意识。平心而论,细读《西游记》,其中的确存在以人身为本位的取向,妖魔自不必说,就是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这三个唐僧的徒弟,即便具有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政治正确性”,也难免因容貌丑陋而被人歧视。虽然《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神魔小说中的瑰宝,其中充满了奇谲怪诞、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吴承恩亦展现了古人现世理性之外难能可贵的往世、来世观念,以及人之外的天、地、神、鬼等多重视野,这方面接续了中华文化在远古及至夏、商时期重鬼神的文化精神,但归根结底,《西游记》仍然难脱中华文化从夏、商至周朝历史大转折时代确立的文化传统——由重鬼神转变为以人为本位,以及儒家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强化、夯实的“不语怪力乱神”之实用理性。
以中土为本位,前文已有详论。或许是囿于自己的经历、视野、见识、知识储备的限制,抑或是受自己思想意识的主导,唐僧历经十四载重回长安时,作者才会写下“果是中华大国,比寻常不同”,这既道出了哪都没有自己家好的人之常情,更可视为作者眼中他者与自我、中华与异域之等级秩序的最终定论——自我压倒他者,中华高于异国;他者沦为自我自说自话的镜像,异国作为中华之他者最终被遮蔽。在作者设定的大圆满结局中,其对中华的迷恋意识和批判意识之间的纠结终于得到想象性解决,对中华的批判意识渐渐削弱,直至消弭得无影无踪,而最终被迷恋意识所取代。
纵观《西游记》全书,虽有鲁迅认为的“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处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2]115之硬伤,但作者以佛法为本位的思想仍隐然可见。途经车迟国时,作者虽借孙悟空之口讲出“三教归一”的理想,但细读文本,作者在书中还是写出了佛道之间的微妙关系,在佛道斗法时也总是渲染佛家的法力无边,并为佛家占据道德制高点,而《西游记》也是在佛家“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的同声赞歌中结束。麻天祥在《中国宗教哲学史》中提出,宗教哲学的终极追求本是超脱人生存空间和时间的有限而寻求无限的,但在现实层面,宗教哲学逐步被制度化,最终只局限于有限的宗教制度中,讲究法力、权威和等级,从而形成宗教哲学追求无限与宗教制度局限于有限的二律背反。[7]29-45由此观之,《西游记》虽然有对佛教原始哲学——如追求良善和普度众生——的表现,但更多的是一种制度化改写和挪用,强调法力、等级、权威,作者从而在佛教哲学与制度化佛教的二律背反中不断向制度化佛教趋近和靠拢。
注释:
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这里有必要指出,在《西游记》中,很多异国是作者利用文学家虚构的权利和便利想象出来的。而这种想象,有文学家天马行空的想象成分,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所描述的近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想象”并非完全相同。书中中华与异国的区分,并非现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与异国的区分。
参考文献:
[1]保尔·利科.从文本到行动[M]∥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代序)∥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5]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M]∥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谢肇淛.五杂俎[M]∥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7]麻天祥.中国宗教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于湘]
收稿日期:2015-12-15
作者简介:刘楚(1988-),男,江西吉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6)03-008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