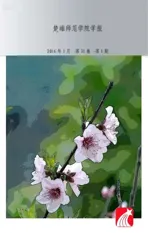民族“特色”食物与食物的“民族性”* 1——以云南德宏州景颇族、德昂族为例
2016-03-29王晓艳
王晓艳
(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650201)
民族“特色”食物与食物的“民族性”* 1——以云南德宏州景颇族、德昂族为例
王晓艳
(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650201)
摘要:食物是自然人的“食物”,也是社会人的“食物”,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民族生境的变化中,食物体现出的适应性表明民族对食物的选择源于其传统功能在民族社会中的继续发挥。然而,食物的本质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民族认同不断提高,食物的“特色”与民族身份联系在一起后被不断强调,使食物有了新的社会意义,即食物标榜了“民族性”,传递着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
关键词:民族;特色食物;功能
食物,延续了作为自然人的生命,也凝聚着作为社会人的价值和文化象征意义。“食物的人类学研究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发掘作为物的食物背后的人、社会和文化意义,即食物与生态、认知、象征、历史和社会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从中更深刻地了解特定族群的文化特点。”[1](P271)继往的人类学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到了食物所传达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但对于食物所呈现出的族群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却较少涉及。在人类学倡导的田野调查中,作为文化的“他者”最容易涉猎“异于我”的文化,食物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类。但在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比以往更容易参与观察到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例如,在如云南这样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随处可见各种少数民族特色餐饮店,又或在被政府开发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也有标识该族群饮食文化特点的农家乐,更为普遍的是当作为非同族人到少数民族家庭做客时,主人家一定会在餐桌上强调这是“我们民族”的特色。在少数民族的观念中,食物似乎具有了某种专属性,而他们也在积极地构建这种专属性,那么,是何种力量驱使着“特色”食物被强调?基于此,本研究通过云南德宏州景颇族和德昂族的田野调查尝试进一步的思考。
一、云南德宏州景颇族和德昂族饮食特点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滇西南,西南与西北与缅甸接壤,辖区内居住着傣族、景颇族、傈僳族、德昂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其中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属云南八个人口较少民族中的三个,均为跨境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景颇族与德昂族同为山地民族,在食物方面有着相似性,这与居住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相关。德宏地处低纬高原,地面接收到的太阳辐射量大,热量丰富,气候温和,属南亚热带气候,无明显的四季之分,只有干湿季之别,年均温度在18. 3~20. 0℃,降雨量集中在5~10月。在如此生境中,景颇族与德昂族的饮食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野味”。德宏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也成为居住在山林中的景颇族和德昂族的重要食材。20世纪末民族植物学研究者在德宏对景颇族食用野生蔬果的调查中记录到:“野生种子植物蔬菜97种、蕨类7种、苔藓2种、食用真菌107 (地衣1种)种,野菜类共计213种;野果46种。”[2](P3)德昂族的野菜种植资源也较为丰富,近些年可“收集到67份蔬菜类、野菜类种植资源,其中蔬菜类14个属,38份,野菜类29份。”[3](P1607)除了野生的蔬菜瓜果,在田野调查中长期食宿在村民家,也可偶尔品尝到野生物种的肉,如竹虫、竹鼠、蜂蛹、蚂蚁卵、蚂蚱、知了、麂子、野鸡、田螺、河鱼、螃蟹、黄鳝等。对于野生食材的采集和获得,景颇族和德昂族并非刻意去山林间寻找,常用的作为辅料的食材在房前屋后亦能找到,如香蓼、刺芫荽、吉龙草、香茅草、野茄、红茄、刺天茄等,需要时随即采摘。有些生长在田间地头或山林河边的野菜,通常是人们在劳作过程中发现而顺带采摘,如马蹄菜、蕨菜、野芹菜、水青苔等。
从野生动植物到餐桌上的食物,是民族对自然物种的认知和利用,体现了“可食”的确认过程,包括了获取食材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长期居住在山林中,景颇族和德昂族对于野生食材的采集时间、地点和用途了若指掌。竹子与景颇族和德昂族的生活密切相关,建房盖屋、生活和劳作用具都会使用到,而竹笋也是他们不可缺少的食材。在德昂族聚居的德宏芒市三台山乡,村民将竹子分为很多类,并作为不同用途,一种被村民叫做“容不来”的野生山竹,因其竹笋味道甜而被普遍采集,每年七、八月是采摘的重要季节,采回后通常晒成干笋或腌制成酸笋。在德昂族家做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与竹笋相关的菜肴,酸笋煮鸡、酸笋炒肉、酸笋野菜汤。在景颇族人家,煮螺蛳是被特别推荐的一道野味。即使在集市中购买,景颇族也能正确的区分出可食用的野生螺蛳。每年6~10月是捡螺蛳季节,水田、水沟等有水的地方是螺蛳较多的地方。景颇族要做一道煮螺蛳非常费事,首先要在清水中放置2~3天让螺蛳吐出肚中的污秽,制作前要在加入盐的水中反复搓洗,并不停换水直到水不再混浊,之后用刀将螺蛳的锥形顶端切掉,以便于食用。洗好的螺蛳放入煮锅后,加入缅芫荽、臭菜、酸笋、葱叶、香辣溜、补芽、帕哈、嫩姜叶、香菜、大蒜等香料,加盐煮半小时即可。螺蛳肉煮出的汤也非常美味。每当食用煮螺蛳时,餐桌上几乎很少有其他食物,特别是景颇族认为的与之相克的牛肉、瓜果豆类或凉性食物,即便如此,一盆螺蛳配上一碟舂菜在景颇族看来已是一顿野味大餐。
第二,“生食”。生食指的是食用烹饪中未使用明火加工的食物,景颇族和德昂族都有较为普遍的生食菜肴,多采用舂和凉拌的方式。生食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食材的本味,辅之以各种野生佐料。景颇族有句俗语:“舂筒不响,吃饭不香。”在景颇族村寨,每户人家都有一个舂筒,几乎每顿饭都有舂菜。舂菜的原料除了一些烤熟的肉类外,许多蔬菜都可以舂食,如生姜、新鲜带壳蚕豆、豇豆、鱼腥草、马蹄草等,洗净的蔬菜放入舂桶,加入盐、小米辣、豆豉、芫荽、野茄等佐料一起舂碎就可食用。景颇族人家每顿饭都需有一道舂菜,数量不多,苦、酸、辣是基本的味道,多作为开胃菜。生食的习俗与德宏一年中较长时间的热带气候相关,生食保持了食材极酸、极苦或极辣的味道,对外人来说难以接受,但却是景颇族和德昂族正餐中不可缺少的。
景颇族和德昂族都有一道非常出名的生食菜肴叫“撒丕”。景颇族多称之为“苦撒”,德昂族称之为“橄榄撒”。两种撒丕的味道因为食材的差别稍有差异。苦撒为苦味,苦味来源于其中一个重要食材:苦水,景颇族认为最好的苦水是杀牛时从牛胃里取出的汁水。苦撒需要准备米线,配上一点烤熟的牛肝或牛肚,另外制作一碗用苦水为主要原料的蘸料,即在苦水中加入韭菜、缅芫荽、香柳、小米辣等调料,再加入剁碎的生牛肉或生猪肉,有时还会配上一盘切丝的生莲花白,随后,将米线、牛肝等食物放入苦水里蘸一下便可食用。德昂族的橄榄撒为酸味,食用的方式和苦撒相同,但用于蘸食的汁水为酸水,酸味来源于柠檬、羊奶果或酸多依等野果的汁,酸水中的回甘味和清香源于橄榄枝的皮和去核舂碎的橄榄,用于蘸食的食材有米线、烤熟的猪皮、生的莲花白或茼蒿等蔬菜。之所以可以放心食用汁水中的生肉,两个民族都有着相似的解释,即苦水和酸水都有杀菌的作用。
第三,“酸苦辣味”。景颇族和德昂族均有好食酸苦辣的饮食习惯,村民认为这与天气热相关,酸、苦、辣可开胃,有清凉解暑的作用。景颇族和德昂族村民家一般较少购买和使用的食用醋,但餐桌上每顿都离不开酸味。食物中的酸味主要来自于新鲜野果或水果的酸味,如青柠檬、酸木瓜、树番茄、野番茄等,这些果木有的野生,有的被村民栽种,获取非常方便。爱食酸的村民们还会制作凉拌酸果作为零食,如凉拌羊奶果、木瓜、酸多依、山杜英、盈江省藤、芒果等,制作使用的佐料是盐和辣椒面,腌制一会就可食用。另外的酸味来自腌制品,如酸笋、腌姜丝、腌辣椒、腌菜、干酸菜等,其中以干酸菜在餐桌上最为常见。干酸菜的主要材料是青菜叶和萝卜叶,但景颇族和德昂族制作干酸菜的方法各有不同。景颇族将菜叶洗净后放入大缸内浸泡,待有酸味后捞起,装入大铁锅后,放一点刚蒸出来的米饭用大火煮,再放入大缸内浸泡,如此反复两次,直到菜叶成亮黑色,捞出后晒干就成了干酸菜。德昂族的制作方法稍简单,洗净的菜叶放入缸中,加入稀饭搅拌,待有酸味后,取出置于蒸锅中蒸,之后晾干即可。干酸菜可储存较长时间,食用也非常简单,主要食用的是汤水。中午劳作回家,取出一小把干酸菜放入锅中加入水、盐和一两个小米辣,煮沸即可食用,有时甚至不用煮,用开水烫后喝汤。
景颇族与德昂族的苦味菜肴,不是外人能轻易习惯的,其苦味远远超出常见的苦瓜。苦味多为野生植物的味道,如龙葵、红茄、野茄、水茄、刺天茄、南山藤、刺五加、芭蕉花、马蹄草等。大部分苦味菜可以加入酸菜、辣椒、蒜等佐料凉拌或作舂菜,也可加入酸茄等佐料煮汤。一些苦味的食物也经常出现在景颇族特色餐厅中,如凉拌刺五加和马蹄草,炒芭蕉花或芭蕉花煮汤。辣味也是景颇族和德昂族食物味道的重要特点。几乎每户村民家的菜园中一年四季都种有辣椒,多为小米辣。炒菜、煮菜、舂菜、凉拌等都会放入新鲜的小米辣为佐料,也有将小米辣摘来后放入酱油中腌制,待有酸味时直接取出作为咸菜食用。
上述景颇族与德昂族的饮食特征既是被村民认可的归纳,也是笔者作为调查者与“我”的饮食所做的对比——选择不同的参照对象,特点也许呈现出不同。如与同聚居在德宏的傣族相比,两个民族的这些特点便不是独有。由此可见,食俗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很大程度上受生境以及参照对比的影响。
二、食物的“适应性”:少数民族食物的传统功能体现
食物由“物”变为“食”,是人类适应能力的体现,则人类的食物也必然具有适应性,这一适应不但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更是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在人类学的话语中,作为文化一类的食物处于变迁中。若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对单一族群考察,食物功能的变迁尤为突出。
食物最本源的功能在于满足人类生理的需要。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远古人类的食物相对单一,且多从自然界中获得。随着人类获取食物方式以及对自然认知能力的变化,饱腹不再是问题,则某些食物逐渐消失或被替代,尚留存下来的食物所体现出的功能便不仅仅只是饱腹。在学会农业耕种之前,景颇族的先民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唐代樊绰的《蛮书》中记载:“其妻入山林,采食虫、鱼、菜、螺、蚬等归,啖食之。”元代《云南志略》记载:“不事农田,入山林采草、木及猎杀动物而食。食无器皿,以芭蕉叶籍之。”明代天启《滇志》记载:“执勾刀、大刀,采捕禽兽,茹毛饮血,食蛇鼠。”[4](P37)史料记载中的景颇族,有着以野生动植物为食物的历史,自元代开始,先后经历了刀耕火种和旱地农业的发展,最后南迁定居德宏后,还发展了水田农业,但农耕的发展并未改变采食野生的习俗。直到今天,在景颇族的饮食结构中,野菜仍然是日常食物。野生肉类食物因环境的变化和国家禁止捕猎变得稀少,但景颇族男人依然酷爱打猎,烧得一窝野蜂,捕得一头麂子,又或抓到一只竹鼠,便是极大的美味,犹如过节,要邀请亲朋好友来,一起将野味烹饪,便可聚餐大半天。笔者在2011年的田野调查中,村民抓获一只竹鼠,便被邀约去品尝,不足一公斤的竹鼠,宰杀时流出的血滴入米酒中,来聚餐的好友们轮流喝了这血酒,据说有强身健体的作用。竹鼠的肉与骨被一起剁碎,加入了缅芫荽、小米辣、姜末、盐爆炒,盛出来仅有一小碗,加上主人家做的撒丕、舂菜等,六、七个人从中午吃到天黑。这样的饮食习俗在异文化者看来,难以理解之处在于:一小碗野味,何以能聚餐那么久?但置身其中可发现,竹鼠肉不仅仅满足的是味蕾,亲朋好友聊天中对捕竹鼠过程、经验、技能的分享,对捕猎生活的回忆和向往表明:在变迁中留存下来的食物,凝聚着族群的历史记忆。由此,今天少数民族的一些特定食物,会成为族群认同的标识。
当更加科学的分析人类的食物时,食物便与营养和健康密切相关,但健康与营养的食物具有相对性,以地域和食之群体为参照,即食物具有地域的自然环境特征,其健康和营养功能也在很多程度上是相对于居住在该地域的族群而言。例如,景颇族和德昂族的食生对很多外地人来说不见得适应,以生肉为主食材的撒丕,一些人食后会拉肚子数日,村民给予的解释一般为:不适应或不正宗。不适应,意为“你”的肠胃不适合这一食物,而“我们”生长在这个地方,经常吃且还会吃一些抑制不健康情况出现的食物;不正宗,意味这一食物中的很多食材只有“我们”本地有,而且必须放齐全,才能吃着放心。上文中提到,景颇族与德昂族好食“苦”,村民认为“苦”的食物通常有药用功能。景颇族有句俗语:“我们景颇族在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去都是药材。”确实,景颇族和德昂族经常食用的几种苦味野生植物,均有药用功能。用于煮汤或凉拌的龙葵,在《中国植物志》中记载:全草药用,能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用于做舂菜的刺天茄,根药用,能祛风燥湿、散结消肿、清热解毒,果能治疗咳嗽及伤风,内服可用于难产及牙痛,亦用于治发烧、寄生虫即疝痛。[2](P142)在德昂族山寨中,随处可见一种高2~8米植物,村民称之为“苦凉包”树,主要采食叶尖,可凉拌、煮汤或炒鸡蛋,味道极苦,但村民认为它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另外岩姜、老虎姜等常见野生食材都具有不同的药用功效。由此可见,在景颇族和德昂族针地方性知识中,食物的药用功能较为明显,这样的认知是在长期的饮食实践中习得,并延续至今。
若少数民族的食物仅具有饱腹或健康功能,则在具有众多可替代性食物或医疗卫生条件来保证人类健康生存的今天,某些难以获取或制作费事费力的食物就有着逐渐消失的可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原因在于饮食行为是族群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亦是一类文化,与族群互动共生。当族群社会结构相对稳定时,某些食物便在文化体系中被不断利用和食用。在大多数民族中,食物与宗教、社会关系、人生礼仪等相关,作为重要的物化形式表达,并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景颇族有一句俗语:“汉族财富一幢楼,景颇族财富一厩牛。”景颇族养牛,也好食牛肉,并将牛视为财富的象征,尽管现在养牛的人家越来越少,牛的价钱也很贵,但在景颇族的婚丧嫁娶、节日庆贺、处理纠纷中都一定会使用牛。例如,订婚时,男方家要到女方家舂牛干巴吃,意为两家婚事就此确定,以后便不能离婚;婚嫁中,有着“趟路开道牛”、“彩礼牛”、“姐姐害羞牛”、“舅舅牛”①“趟路开道牛”:要婚配的两姓人家,历史上如果没有结过亲,现在要结亲,男方家就要给女方家一头“趟路开道牛”。两家定亲时,女方家要向男方家要“彩礼牛”,各家的经济状况不同,“彩礼牛”越多,女方家越光荣,女方的身价也就越高,男方家也感到自豪。“姐姐害羞牛”:女方的姐姐如果还没有出嫁,妹妹的丈夫就要给女方家一头牛。“舅舅牛”:女方家在得到“彩礼牛”中,要拿一头送给女方的舅舅。;老人去世,要杀牛请客,有“挖坟牛”、“送终牛”和“火炭牛”②“挖坟牛”是死者家里自己杀的牛,必须是公黄牛。杀牛前,家里人要将死者生前用过的被子等装进牛驮上的竹箩里,放在牛背上。牛被杀死后,把牛驮取下来。表示这头牛已驮着死者生前用过的物品伴随死者同去。“送终牛”是死者女儿拿出的一头牛,这头牛一般是老水牛,因为它肉多。这头牛的头剥下皮以后,要用一根5厘米粗、2米多长的木棍将牛头穿起来插在死者的坟头上。“火炭牛”是已出嫁女人死后,其侄儿或孙子要的一头牛。男方家付了这头牛,两家间的这桩婚事就算全部结束。水牛、黄牛,公牛、母牛,大牛、小牛都可以用做“火炭牛”。之分。在景颇族社会中,牛是食物,更代表着礼节,维续着亲属关系。又如德昂族,在其创世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开篇中这样写道:“茶叶是茶树的生命,茶叶是万物的阿祖。”[5](P114)德昂族将茶奉为祖先,只到今日依旧种茶、土法制茶,爱喝茶,茶叶也是重要的社交礼仪之物,看望亲朋、举办红白喜事、发送请柬甚至赔礼道歉,都要送上一小包茶叶,意思为“茶到礼到”。[6](P152)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物”,食物功能的逐渐丰富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表现,而传统食物的现代留存本质上是食物就族群而言的适应性反映,这种适应不仅仅是“物”本身的价值,而是“物”凝聚的社会意义推动着其的留存。简言之,在一个文化体系中被族群认同的食物的传统功能影响着民族对食物的选择偏好,这一影响可认为是一种内生的传承力量。那么,是否有外部的力量影响着食物功能的变迁?其功能是否就局限于族群内部?
三、食物的“民族性”:少数民族“特色”食物的凸显
就少数民族饮食历史而言,食物是客观的存在,但在所谓的“现代”,便有了符合于“他者”“胃口”的“传统食物”这一称呼。传统与现代本是一对延续的时间序列,但在文化研究者那里,常用作为一组二元对立的关系,则更多的文化被用其来分类,有了不同目的的价值判断,如旅游者到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希望寻找的是“传统”以满足其猎奇心理。与“传统”这一学术词汇相对应的、一个更普泛被大众使用的词是“特色”。在现代社会,似乎“他者”总在寻求少数民族生活与文化中的一种特色,特色食物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类。在外界的力量下,民族便积极地强调着“传统”,以建构一种“他者”想要的“特色”。
在云南的省会昆明以及地州一级的县级城市,总能轻易找到某某族风味的餐厅。德宏为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族、景颇族特色的餐厅最为普遍,特别是在城市边的民族村寨中,以农家乐形式存在的民族餐厅更受欢迎。另外,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建设中,一些被官方认定的民族村寨成为了代表性的“传统”,在不断的旅游开发中,餐饮自然是最重要的一项,政府给予村寨的“标签”也成为“特色”民族饮食的认证。若将民族强调特色食物的现象归因为民族经济发展中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则显得有些片面,因为在普通民族家庭长时间同食同住,会有不一样的解释。作为异文化者,笔者所居住的景颇族和德昂族家庭,当某顿饭出现一道与以往不同的食物时,主人家都会主动介绍该食物的特有性,并说明“只有我们景颇族(德昂族)才这样吃”,当笔者询问“傣族(或其他民族)也吃这个时”,他们会表示“我们才正宗”,或会从烹饪方式、佐料等方面的不同来强调“他们和我们的不一样”。那么,为何在普通的人家,民族也在积极地强调着自己食物的“特色”?
在民族强调自己食物特色的过程,一些食物的社会意义发生了变化。现在景颇族特色的餐厅或普通村民家,都有一道叫“鬼鸡”的菜肴。“鬼鸡”实际上是凉拌鸡肉,是将祭祀用的鸡煮熟之后,把肉撕成小条状,加入剁碎的姜、蒜、缅芫荽、棕檬叶,再加入新鲜柠檬的汁水,配入盐、味精等调料做成。之所以被称为“鬼鸡”,是因为过去这道菜使用的鸡是祭鬼用过的鸡,“鬼鸡”具有一定的禁忌,只有祭司和老人才能食用。但如今,这道菜蕴含的宗教意义和伦理道德已消失,成为随时都可以制作、任何人都可以品尝的食物。又如在景颇餐厅中最具民族特色的“绿叶宴”,主要体现的是景颇族传统的饮食方式。过去,景颇族多人在野外聚餐时,米饭是用绿叶包(多采用芭蕉叶或冬叶),菜也是绿叶包,喝汤用的碗和勺子是用竹木枝叶折叠而成。后因这种饮食方式看上去满席翠绿、不用碗筷而得名“绿叶宴”。20世纪80年代初,景颇族过节、结婚、丧日等活动都以“绿叶宴”的形式招待客人,分发给客人的是包饭、包菜。吃完饭可以丢弃包叶、竹筒等盛器。现如今在特色餐厅中,绿叶宴上所呈食物充分体现了景颇族烤、煮、炸、腌等烹制方式,凡被认为是景颇族的特色菜肴,都能在一桌绿叶宴中吃到,紫米饭、鬼鸡、舂菜、野菜、包烧、烤鱼等。与绿叶宴相似,还有手抓饭,且傣族、景颇族餐厅中都有。可见,人们品尝的不仅仅是民族的特色菜肴,而是分享了“民族”这一身份背后的文化习俗。
“食物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可以分辨你我的东西,为什么经常人类会强调我群与他群的区分的时候,常常主观的将食物当作一个符号。”[7](P84)这是因为身份的认同通过媒介来传递,而食物可成为重要的一类媒介。居住在各地的同一少数民族,文化可能具有差异性,但在国家对于民族身份的法定承认以及相关法规和政策促成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外部作用下,民族自身也通过各种方式推动着内族群内部的认同。尽管食物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难以评测,但民族“特色”食物的出现表明:少数民族对食物的文化认同从“自在”的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在自觉的状态下,民族有着更为积极的行为能动性把食物与身份相匹配后进行饮食文化的复兴与创造。
食物成为身份媒介,目的上与民族寻求自身的发展有关。在如云南这样以政府为主导的强调民族文化特色的区域,民族认同度不断提高,作为最具表现性的食物也就成为民族身份建构和认同的主要标志之一。少数民族群众积极标榜着某一食物与本民族的自然社会生境相关,表面上是为了获得某些利益,但更为深层次的是提升自我身份的认同,进而凸显“我”与“他”和“你”的不同,使之成为被“他者”也认同的民族中的“少数”或“特有”,进而转化为一种无形的竞争力去获得更多的权利。将景颇族与德昂族相对比,上文中以归纳了两个民族的食物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并不能系统的将食物打上专属某个民族的标签。但无论在芒市三台山乡德昂族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农家乐中,还是在国家批准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陇川县广山村景颇园中,相同的食物已经具有了不同的民族性。
结语
食物本质是一种“物”,但其并非一种完全的客观存在,这源于“食”所体现的是一种行为。食之时空、食之群体、食之目的等基本要素的组成,可说明食物的变迁是一个永恒的定论。以少数民族食物作为一个小小的窗口窥探食物的变迁,不难发现的是食物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外界力量的推动,民族认同不断提高,一些新的权利场域形成,在这些场域中,民族“特色”食物不断被强调,且在建构“特色”的同时,食物也成为划分民族边界的一类媒介。由此,食物在如中国这样的现代多民族国家中成为民族身份的标识。当然,食物本质的丰富是以食物所存在的生境以及在民族社会中的传统功能为基础的,即便食物的社会意义有了很大的变化,都不能改变食物具有的地域性和族群性限制的特性,即民族的“特色”食物,也仅能在一定的地域中被一部分的族群所“消费”。
参考文献:
[1]瞿明安.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2]许本汉.德宏山野蔬菜[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01.
[3]张林辉,刘光华等.云南德昂族地区农业生物资源调查[J].西南农业学报,2011,(4) .
[4](唐)樊绰.蛮书.转引自《景颇族简史》编写组.景颇族简史(修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5]张蕾梅,陈巧英主编.德宏世居少数民族民间神话、传说及故事梗概[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
[6]《德昂族简史》编写组编写.景颇族简史(修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7]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 .
(责任编辑陈兰)
Ethnic Food and Ethnicity by Food: -Cases on the Jingpo and the De’ang in Dehong Prefecture,Yunnan Province
WANG Xiaoyan
(College of Marxism,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unming,650201,Yunnan Province)
Abstract:Food matters not only on human’s basic necessity,but also on their social life.It can tell some connections like human and nature,people and people,and human and society.In the change of an ethnic group’s circumstances,foodways got its great adaptation,which implies that food and foodways are normally chosen because their traditional function still works in particular society.However,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food are not that stubborn.Along with the ethnic identity getting stronger,the connection between ethnic food and ethnic identity becomes sticky,which brings their food specialties new social meanings.It turns out to emphasize the ethnicity of food and being the symbol of ethnic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ethnic group; ethnic food; function
作者简介:王晓艳(1984—),汉族,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学。
*收稿日期:2015-12-15
中图分类号:TS97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 (2016) 01-0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