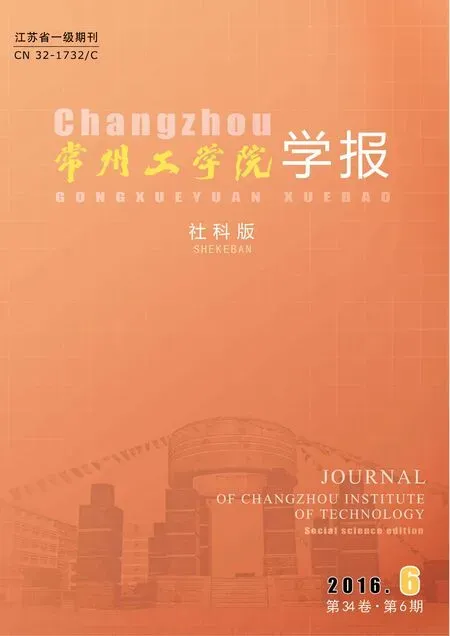泰华文学的中华性与本土性
——以《春色满园——十年散文选集》为研究对象
2016-03-29计红芳
计红芳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熟215500)
泰华文学的中华性与本土性
——以《春色满园——十年散文选集》为研究对象
计红芳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熟215500)
泰国“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的《春色满园——十年散文选集》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特色鲜明。作品的字里行间渗透出的佛国人以坚韧善良、真诚质朴与包容豁达为特点的本土色彩,用汉语言文字包裹起来的浓浓的中华情怀,以及本土性与中华性的互渗交融,是泰华文学的生命力所在。
泰华文学;《春色满园——十年散文选集》;中华性;本土性;互渗交融
与泰华文学的结缘源于2007年10月到2009年10月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的任教经历,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泰华文学,虽然离开泰国已经多年,但我的心时时记挂着南方,记挂着那些为泰华文学的发展默默耕耘的老中青三代的文友们。时值“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十周年之际,翻阅着文友电邮来的《春色满园——十年散文选集》(以下简称《春色满园》),笔者感受到那字里行间渗透出的佛国人的坚韧善良、真诚质朴与包容豁达,也感受到那份用汉语言文字包裹起来的浓浓的中华情怀,这种本土性与中华性的水乳交融,在泰国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中确是一大特色,也是泰华文学的生命力所在。本文以《春色满园》为研究范围,试图阐释泰华文学的中华性与本土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渗与交融,以期更深入探讨泰华文学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怀乡之旅的终点
泰华“留中文艺写作学会”的作家们以汉语为写作语言,汉语不仅成为他们写作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汉语写作本身所蕴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作家都有在中国留学或生活的背景,回到泰国的他们自觉地承担起了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泰华作协永远荣誉会长司马攻先生曾经说过,他不希望华文文学在泰国断根,因而不断鼓励年轻一代进行华文创作。在司马攻看来,“泰华作协这一组织的影响,使一些华裔青年对文学产生兴趣,学习华文创作。而通过华文创作,可以传播中华文化,也可把泰国文化介绍到中国,这样可以起到文化传播的桥梁作用,促进中泰世代友好”①。“泰华作协”自1986年成立以来,在方思若、司马攻、梦莉等几届会长的领导和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下,泰华文学正在稳健地向前发展。而“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虽然是“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中的一个组织机构,但是这个写作组的成员和“泰华作协”的成员有很多是交叉的,他们互相扶持,共同担负着培养年轻作家、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
这本《春色满园》精选了“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近10年来老中青三代作家较为优秀的散文,大致按照作者留学中国大学毕业的年代排列,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延伸到新世纪,作品的内容较多是对自己在中国留学岁月中的人、事、情的回忆。传统节日、故乡风物、留中大学、初恋情怀、父母恩情、落叶归根等一些“怀乡”意象都承载着作家永远挥不去的乡愁和中国文化情怀!不管是泰国艰苦创业时期还是功成名就、生活富足之际,作家们不时进行着“怀乡”之旅,以此释放内心的疏离感和缓解文化精神上的困顿感。
中秋,一个全球华人魂牵梦绕的传统文化节日,怎能不令人思绪万千?梦莉的《心中月色长不改》一文,中秋之夜情感的起起伏伏,更是震颤着读者的心灵。与久居大陆的儿时玩伴——曼谷“小朋友”重逢的满怀期待、西湖泛舟赏月无端受到船家无礼对待的委屈与愤懑、“小朋友”因出差无法飞来杭州共赏明月的落寞与惆怅,在梦莉的字里行间表露无遗。这些情感的孕育与发酵无一不是对年少情感的深情回望与期盼。“月亮”本是中国传统文化抒情言志的意象,作者借“月亮”特别是“中秋满月”寄寓着“有情人终能团圆”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却因种种缘由未能实现。尽管有点怅然若失,但作者仍然坚信:“我心中月色长不改,明月永远在我心中。”一个“长”字道尽了作者埋藏心底的那份幽怨绵长。
岭南人的《故乡月圆——一九八六》则写尽了他对山西大学中文系的深情厚意。1957年去港探亲的岭南人由于内地政治动荡,没能回山西大学完成学业,带着遗憾回到了泰国。30年后,踏上故国家园、重返山西大学校园的岭南人因为梦想成真,竟觉得“回到故乡的月亮胖了!”作者运用通感的手法,把视觉拟人化为触觉,一个“胖”字浓缩了作者30年来对祖籍国的深情牵挂。
杨搏的《梦里来复少年身》,想必是受了沈从文《边城》和汪曾祺的《受戒》等诗意化小说的影响,那对高考失利的男女生的感情朦朦胧胧,却无疾而终,二人从此再无相见。作者写道:“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我们慢慢变老的同时,很多人从我们生命中走过,我们曾互为风景,互相装饰对方的梦。”人事的沧桑无常与恋旧情怀显露无疑。《故乡的小溪》是作者周沫的精神家园,一想到那流淌的湄南河水中,“是否会有那么几滴是从我故乡的小溪流过来的”的时候,“想着想着眼眶就湿了”。罗铁英的《我当北京奥运志愿者》,她把对祖籍国的爱化为一种到北京为中华民族服务的实际行动,终于实现了她作为炎黄子孙久盼的梦想。更有甚者,吴静敏《心系祖国》中的岳炎,死了以后还想把遗体捐给祖籍国的医疗事业,可惜年老多病已经无力返回,这成了他永远的心结。多么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
父母恩情永难忘。晶莹的《续命春天》,用充满深情的笔触追忆着父母亲的故事,以此释放他的情感伤痛。父母都在春天离世,经过时间的沉淀,伤痛和思念依然如故。羁旅天涯,最牵挂的人莫过于父母,为爱情、为梦想渐行渐远的作者“子欲养而亲不在”,这种伤痛如此刻骨铭心:“我常为此极度恐慌,不敢深究其竟,甚至抗拒怀念。”作者害怕“那融在骨子里难于割舍的血脉,是否会随着家园视线的模糊,最终迷失在历史的尘烟中?”。然而怀念是人类最普通的情感,虽然小时候曾经因为淘气、学习不认真而挨过母亲的骂、父亲的打,但现在想来却是温馨有致:“与父母亲曾同生活在乡下的岁月,是迄今最安逸、最快乐的了,特别是春天阡陌上追逐父母脚步的嬉戏,当是我人生最精美、最难忘的生活桥段了。”故乡田园、儿时生活,在作者的记忆中都被抹上温情的色彩,并最终凝化成为他心中圣洁的净土。
“怀乡”是作者对已逝的经验和记忆的追寻,中国是怀乡之旅的最终目的地。对作家们而言,不管出于何种途径和目的从中国到泰国,或者往来于泰中之间,“怀乡”是正常而合理的情感。当然,记忆里的过去,往往会在想象中变形,事实上,过去的亲情、友情、爱情、师生情、家乡情、祖国情都无法恢复旧貌,但透过作者的想象,“过去”在观念上依然完整美好,想象中的“过去”,风景依旧,人情不变,甚至更加完美,而作者就在这种变形的文学想象中释放自身的情感焦虑与文化焦虑。
不管是对故国家乡、田园小溪等地理上的怀乡,还是对父母恋人、留中生活等情感上的怀乡,抑或是对传统节日、潮汕民间艺术等文化上的怀乡,其源头都离不开具有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祖籍国——中国。正如刘华所说,无论华人飘向何方,“中国情结”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不停地唤起飘零游子心灵深处的家园记忆和乡土情感”②。
二、泰国:安身立命的家园
《春色满园》的作者成员年龄差距极大,有的作者已经驾鹤西去,有的还在中国的大学继续留学深造。但不管是老一代的华人移民作家,还是中青年一代的新移民作家,抑或是这些移民作家的第二代,泰国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家园。司马攻先生曾说:“泰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继承和重建,它的继承是立足于泰国的继承,并在现实基础上的重建。泰华文学要在泰国的土地上植根,就必须承认现实。承认泰华文学是泰国文学的一部分。”③司马攻先生的话充分说明了泰华文学的中华性与本土性以及它们之间彼此相依相存的关系,同时也给泰华作家们指明了创作的路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故事,《春色满园》中收录了很多作者艰难创业的故事。创业的艰辛与成功的喜悦,语言、文化的疏离与融合,点点滴滴诉诸作者的笔下,敲打着读者的心灵。例如廖锡麟的《创业于湄南河畔》、陈汉涛的《湄南河畔艰苦创业的故事》等等。作者们一路走来,历尽各种挫折磨难,不断求新求变,打拼奋斗,如今这些作者早已立稳脚跟,事业有成,造福泰国一方水土。如果说早期的他们由于语言、工作等问题与泰国社会还有一些隔膜的话,那么事业成功的他们离泰国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近了,他们认同泰国,喜爱泰国,早已把泰国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园,甚至还有很多作者做慈善事业,回馈社会。
泰国虽没有中国江南四季分明的景色变换,但美艳的金凤花却几乎整年开放。路边、街上、河岸、公园里,那既像蝴蝶又像凤凰般的金凤花开得那般热情奔放,有的纯黄如金,有的鲜红如火,有的金红晕染……煞是好看,惹人喜爱!作家老羊就是一位金凤花的超级粉丝,爱到极处便出口成章,请看他的《金凤花开》:“河沿成排的金凤,是一团团的烈焰,是一支支的火炬,是一首首激情的诗,是一支支奔放的乐曲。”“要是你也到这金凤怒放的河沿来,你不想写诗也得写诗。”寥寥数语,不仅写出了泰国的风物之美,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老羊也跃然纸上。
泰国一年四季中,大部分泰国人都喜爱冬天,岭南人也不例外。在他的笔下,“佛国的冬天”一点儿也不像冬天,倒像北方的金秋,温暖舒适而又凉爽少雨。那时,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飞来佛国寻梦:“乐山的到清迈,到美斯乐,到金三角,看山、看塔、看树、看花、看鸟,以及搜寻流传在山野间的传奇。乐水的到普吉岛,到苏梅岛,到博他耶,到华欣,潜水、看鱼、看虾、看龟、看珊瑚,看海底神奇的世界,以及玩形形色色的水上项目。”泰国真是一个度假休闲的天堂!在这篇散文的字里行间,岭南人无法抑制地流露出对泰国山水风物的喜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发自肺腑的欣悦!“冬天,佛国的山,依然叶绿花红;佛国的海,依然温暖而翠绿。”请问,这样的佛国冬天谁不喜爱?
泰国不仅是一个自然环境很好的国度,而且是个极富民族特色的佛教国家,90%以上的人信仰小乘佛教,其国民的宗教情感非常浓厚。目前全泰国共有寺庙3万余座,佛寺遍及各地各区,在闹市区见到金碧辉煌的佛寺也是常事。去庙宇进香许愿、依例布施是泰国人的重要生活内容。而“行善积德”“因果轮回”“宽容慈悲”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道德约束等早已成为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春色满园》的大部分作者信仰佛教,他们不仅对佛笃信无疑,在文化心理上也深受其影响,因而在处理作品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矛盾冲突时,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佛教的情感意识,也常常用宗教的感化来解决矛盾、平衡心理、劝恶从善。
曼谷大皇宫的玉佛寺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外化物。当我们跟随作者林太深的脚步走进玉佛寺,“一股庄严肃穆扑面而来。进了门,里面别有洞天,这洞天是属于神仙的;也属于放牧自由解放人性的人的天地;而凡人一到这里,因受那种神圣气氛的感染,那属于尘世的俗念或带罪的心灵,多少得以净化和洗涤”。面对高高在上、高深莫测的玉佛,人类显得如此渺小卑微,不敢轻举妄动,“这种深入人类灵魂的威慑力量,不正是人类情愿匍匐在宗教座下心灵自律的原因吗?”玉佛寺,真不愧为“泰国人的精神支柱”!
“水灯节”是泰国极具特色的传统节日。伴着美丽的民间传说,听着古老而动听的《放水灯》,人们在湄南河边放盏水灯,许下自己的心愿,送出美好的祝福。曾心的《放水灯三境》就是这样的一篇佳作。但他的“放水灯”却不是纯粹的习俗描绘,而是他自身生命流程的浓缩。“生命是流动的,水是流动的。我心中的水灯,随着流动的生命和流动的水,飘呀飘呀,飘过我的童年—中年—老年。”年年都有水灯节,而作者只是选取了童年、中年和老年的三个片段进行集中描绘,结构安排巧妙。最欣赏的是他晚年放的那盏心灯。他说,步入晚境,每当水灯节,依然喜欢听那首《放水灯》的老歌,但却不再去河边放水灯了。文中写道:“我喜欢独自在庭院的石头上盘腿而坐,心境宁静,眼下那块青青的草坪,仿佛变成碧绿的湖,蔚蓝的海。更奇妙的是,它竟能无限延伸,延伸到泰海湾,延伸到五湖四海。啊,一条跨国界而不分皮肤种族的大河在我眼前奔流。我轻轻地把心灵编织的水灯放飞,让它飞到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地方,飞到那悬挂着古典的月亮,古典的星星的古老宇宙空间里。”从具象的水灯到抽象的心灯,从个人到不分皮肤种族的人类,从现代到古典,从本土到宇宙,境界之大,已经超越种族、国界、星球,着实令人敬佩。
彰显泰华文学本土情怀的作品举不胜举。不管是老一代还是新一代华人移民,泰国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家园。纵观《春色满园》的作家们,他们立足本土现实,一方面书写人世的沧桑、创业的艰难,一方面抒发对泰国自然风物、佛寺精神、民俗文化的深爱之情,透露出浓厚的本土情怀。曾心先生说得好:“随着作者闯过一个陌生的背景和语境,在生存、温饱、爱情、家庭、事业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他们文学意识的取向也会与当地本土文化磨合,其作品的移民意识特色也将逐渐消失,渐渐融入泰华文学中。”④曾心先生身体力行,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本土性。为了能更好地融入泰国文学的大环境,曾心把自己的小诗翻译成泰语,其中有一本《曾心小诗点评》由泰国一个有名的发行公司投放到泰国市场试销,很快售罄。这成为泰华现代诗歌打入泰国主体市场的首部诗集,同时也说明了泰华文学的“本土性”已经逐步受到泰国文学的认可,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互渗交融:生命因此而精彩
对祖籍国中国的温情回望,对居住地泰国的深情厚爱,中华性与本土性互渗交融在一起,这是泰华文坛大多数作家共同的特点,也是泰华文学的生命力所在。更可贵的是,有着两国不同生活感知和文化体验的作家们,经过多年细致的观察与省思,他们能够更加客观地审视两国文化的优劣,为中泰文化的融合和再生制造各种可能性,有些甚至超越种族而具有世界性。
晶莹的《风采湄南河》就是这样一篇美文。犹如长江、黄河之于中国,湄南河是泰国的母亲河,它柔美绰约,风情万种。作者羁旅泰国数十年,早已熟稔湄南河的习性。他说:“我于若干年中的若干次观察比较后,终于了然了湄南河的两百年前,与两百年后——一直地、永远地就这样慢条斯理,悠然自得。”湄南河不是没有遭受过帝国主义的蹂躏,然而泰国人民的抗争始终是柔韧有致的,这是他们“以静制动”的生存大智慧,也是东南亚各国中唯有泰国免遭殖民命运的主要原因。晶莹在文中如此写道:“我已谙熟并习惯了这片土地上的这种以静制动的处事哲学与行为方式,我想以此表达我对湄南河的尊重和敬仰。”但是,作者也没有一味地赞扬泰国人民“慢条斯理”的国民性格,也并不因为自己是龙的传人而对中国的国民性褒誉有加。在无数次的对话场景中,作者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泰人因懒惰而愚笨而质朴,华人因勤奋而聪明而奸诈。”若干年来,这样的回答几乎没有改变,有时甚至因为华人游客在泰国的种种不文明行为而“略有轻视海那边华人的些许意识了”。追溯中泰交往的历史长河,作者一直在反省两种国民性的碰撞与融合,终于明白:“是华人的勤奋与泰人的质朴的完美对接,完成了泰华族群特质的华丽转身。”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中泰两国国民性的审视与思考客观辩证,理性公允,因而极具普遍性。
冯聘的《成都印象》也是一篇好文。久居泰国到成都旅游考察的作者对大中国交通拥堵、浮躁性格的生动描绘,对酒吧和茶社的精细描摹,令人佩服。自嘲他讽,嬉笑之间,一个老练通达、又随性率真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谈起交通堵塞,他写道:“这场阵势分明的对峙大概持续了半小时左右,不知是直行车阵的某一辆车慢了一分还是调头车阵的某一辆车快了几秒,反正对方被迫停了下来,这边厢趁着前面有所松动,立刻纷纷左转弯调头,我们的梁爽在十公分距离内突围成功,而且往右边急速斜插过去,直抵酒店门口。”作者运用“对峙、突围”等阳刚的意象来描绘中国人面临此种困境时的应变智慧,并把中国人的浮躁与泰国人的平和做了鲜明的对比,幽默中又见批判中国陋习的锋芒。再看描写酒吧的一段。“无数的年青人三一群五一伙地聚在一起边喝酒边点着下巴轻轻摇摆着身子,震耳的乐声一刻也不停,这种气氛最容易撩拨人的兴奋神经。可惜我适应不了,如果一个头发半秃的家伙喝得五迷三道之后躬腰撅腚地乱扭,那该是多有失体统的举动呀。体统说起来不值多少钱,却是我们这些需要假正经的老派男人最注重的。”冯聘的散文语言颇为老道精练,寥寥数语,把一个“假正经”却又要“注重体统”的老男人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道尽了人性的复杂多面和生活的睿智通达。
再看苦觉的散文《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对于孤旅天涯的苦觉来说更是有着揪心的思乡疼痛,他说,在泰国的许多年,最不想过的日子就是中秋节和情人节,而中秋节犹甚,每逢中秋,他常常是“对月成三人”,孤独地饮着孤独。而2006年的中秋对于苦觉却有点不同。农历八月十六,受驻泰大使张九桓的邀约,以及明月的邀约,还有乡情的邀约,相聚佛村酒楼,谈诗论酒,共度中秋佳节。这是一个温馨而令人激动的夜晚:“朦胧的月色,香醇的美酒,醉人的氛围,我们尽情享受的同时,缕缕的乡情,总有一丝丝的问候,总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乡情诗意的包围中,孤寂的苦觉不再梦乡、归乡,从文友的眼睛里,他似乎读懂了什么:“是来也是去,是空也是色,他乡是故乡,心就这样地踏实了,我将不再茫然,一支秃笔,他池宿墨,就够了。我要学习月亮,此刻中秋的月亮,一生也只有一种白的颜色,却能尽现五彩之色。”好一句“他乡是故乡!”,惟其如此,移居异乡的人们才能安身立命,才能融入无间,才能游刃有余。
总之,有着双重故乡、双重生活经验的泰华作家们,他们的散文往往具有和常人不同的观察和书写视角。移居或久居泰国、生活经验断裂的泰华作家在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冲突面前常常感到失落和迷茫,于是在“怀乡”的咏叹中企望寻找精神家园,同时又立足泰国本土,关注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继而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和泰国商业文化的优劣,来确立自己泰中交融的文化坐标。多元的身份使得作家们具有更广阔的视角,他们一般不会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往往具有中华性和本土性的双重视角。无疑,这是一笔独特的文化财富。不仅可以充盈自己的生命,而且可以丰富泰华文学的内涵。
四、结语
《春色满园》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很多人说这本散文集中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犹如梁实秋先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批评某些散文时说的那样,“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是文调,没有!”⑤也许这是部分客观事实,但有谁规定散文必须是形神俱佳的“美文”?郁达夫对此就不以为然,就散文的范围来说,他与林语堂的观点比较接近。林语堂认为:“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钟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故善冶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而成现代散文之技巧。”⑥《春色满园》中的部分散文虽达不到林语堂所要求的高度,但都是自我个性和真挚情感的流露。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春色满园》毫无疑问算得上是近十年泰华文坛贡献给读者的一场精神盛宴。我们期待中老年作家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也希冀年轻一代奋力跟进,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开创泰华文学的美好明天。
注释:
①蔡金才:《记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司马攻》,http://www.csmynet.com/1abd2097-a69b-4a54-b0ef-9a6800e34859.aspx,2008-03-23。
②刘华:《论“新移民文学”的文学意蕴》,《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89页。
③司马攻:《桴鼓相应,将伯助予——八十年代泰华文学专辑序》,曼谷:《新中原报》,1991年3月22日。
④曾心:《移民意识在泰华文学的取向》,见曾心:《给泰华文学把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⑤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⑥林语堂:《发刊〈人间世〉意见书》,《论语》,1934年第38期,转引自周红莉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经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9页。
责任编辑:庄亚华
10.3969/j.issn.1673-0887.2016.06.003
2016-07-17
计红芳(1972— ),女,教授。
I206
A
1673-0887(2016)06-0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