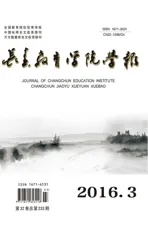司空图“意象”理论之内涵
2016-03-28吴鹏
吴 鹏
司空图“意象”理论之内涵
吴鹏
摘要:司空图对中国后代的诗歌创作与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诗歌意象的形象感成就了中国诗歌意象具体、表达无限的深层内涵;对于意象中的视觉感构成了诗歌与绘画艺术的桥梁;注重整体的表现而不局限于局部的再现,色彩的平淡也符合中国古代思想的追求。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并加以辨析。
关键词:意象;形象;整体;视觉;色彩
①《二十四诗品》是否为司空图所作,目前说法不一,本文对作者问题暂不予以讨论,以司空图著为基点。吴鹏/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北京100048)。
司空图是我国伟大的文学批评理论家,他在发展唐代之前的诗歌批评理论的同时也对旧有的观点进行了许多改造,中国唐代之后乃现代的美学发展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都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司空图的对于理论著述主要集中在各个论诗、论文的著作中,要而言之,主要是通过对文学创作和鉴赏心理过程的描述来整体把握诗歌的,即便是文艺心理学相对发达的今天,有些理论也难以达到如此之水平。
因此,对于司空图文艺心理学发展应该详细地加以研究,由于古代文学批评与发展和现当代文学间隙较大,由此找到沟通古代、现代文学的契合点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司空图关于诗歌意象的性质之一即关于诗歌的形象与视觉感的融合理论对于研究诗歌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意象”中的意是内在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是意的寄托物。它指的是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处理技巧。在《与李生论诗书》《与极浦书》等论诗著作中,司空图详细叙述了诗歌创作和鉴赏中关于形象与视觉感之间的关系,并论及由此产生的审美快感之间的问题。
一、形象感
形象感的作用主要是论及诗歌中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所产生的语言意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理论中提出在共时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的概念。但是在具体的诗歌中,语言的作用却是各有偏差,因为诗歌的表现不可能追求完整性的概念化描述,或者说诗歌本身的表达效果之一就在于“陌生化”,按照诗歌的语言来说就是表达出的语言带有模糊性,故意表达出朦胧的意象来让接受者乃至创作者本身体会到诗歌的形象,留下想象的空间,类似于中国古代画技的“留白”。而所谓“形象感”也并不是语言本身所构成的画面,而是在语言叙述表达意象时对于意象本身的要求。由此,“形象感”是对于诗歌的一种要求。
众所周知,司空图对于“意象”理论的贡献对后代影响极为深远,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曾以文学史的观点罗列了一些有代表意义作家的风格,强调诗歌的表现要“宏思”,此是“极矣”,诗歌的意象要“趣味澄夐,若清之贯达”[1],强调诗歌的创作要表现新颖的、扩大而雄壮的形象,抑或表达出来优美的审美形态,坚决反对大历诗歌与元白的创作,对于贾浪仙等人的创作也认为是“警句”。在笔者看来,司空图之意在于追求语言之间的表达要相对和谐,较少有对立,较少语言之间的紧张关系,体现了一种儒家的理想的美学观,也就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中的“诗贯六艺”的自觉追求,即追求中正平和的表达。
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到以咸酸等味觉的体验来比喻诗歌的批评方式,通过对于这种批评方式,一方面强调诗歌表达出的意象要形象生动,使得人能够切身体会到诗歌意象的存在,并且强调“醇美”的理想的表达,“近而不浮,远而不近”[2]的形象观,强调诗歌的意象能够真实地贴近,能够真实表达出事物。此后,在具体的摘句批评的实践中,又举出了理想的“二十四联”诗歌,用以具体的叙述,并且认为“神而自神”的神来之笔是诗歌创作中最为理想的、最富有审美魅力的“妙笔”。
二、视觉感
“视觉感”是中国诗歌中独特的一种表达,苏轼在评价王维的诗歌中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但是在西方的艺术观点中,诗歌与艺术的表达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在莱辛的《拉奥孔》中,特别提到了诗歌与绘画艺术的区别在于绘画能够适用于表现静态的艺术,而诗歌则更能在强烈的情绪中感染接受者。另外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也提到了动态与静态的艺术魅力在于“日神与酒神”交相辉映,“日神”的力量在于使静态的艺术体现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语),而“酒神”精神则在痛苦之中放荡不羁地挥洒激情。但是在司空图所表达理想诗歌形态美并没有体现出诗歌感情之中的情感的分裂状态,相反的,对于诗歌意象的创作,他更强调意象的整体、色彩的效果体现的要符合“中和”的诗教观,追求一种和谐的态度。
(一)整体感
“整体感”不是为了表达意象的完整传达性,事实上意象的完整性是不能够达到的。诗歌的语言要求传达出意义的主干而不是对于事实的完整刻画,因此所谓的“整体感”在于使诗歌所传达出来的画面能够将自身不带死角地表现出来,实现自身的表达。而不受到技巧的限制。按照宗白华先生的说法,即是“四维透视法”,即不限制画面中的构形是否符合现实情况,而纯粹以表现心中的形象为主。
按照司空图所言,意象传达出来的画面的理想效果在于达到一种“近而不浮,远而不出”的程度,在整体上能够全方位地表达出作者所理解的“此在”的情感所刻画出来的意象,这个意象并不运用用语言文字这个中介来表达,而是运用带有情感的意象本身来刻画。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司空图有提到诗歌所表达的极致境界是“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为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其容易哉”?[3],意思在于意象自身所表达出来的意象能够真实地还原作者的情感与他所理解的形象,而传达出来的这种意象则是最能够体现出司空图理想的美学形象,也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理想。
当然,除了意象本身不经过语言这一中介的自否定之外,司空图的“二十四联诗”也体现了这一美学思想。笔者以为,“二十四联诗”除了大多运用清淡澄澈的意象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利用语言的模糊性来传达超视觉的美感,这当然与人的认知结构有关。语言文字的一般性质就在于将眼前的景物表述成为普遍意义上的可传达的符号,并利用这一性质来传递情感。但是“二十四联诗”所体现出来的理想的审美意象则并没有这个层面上的意思,如司空图所言“诗家之景,如蓝天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4]模糊性的语言预留了整体的某些独特性质,使得意象所指更能契合思维之中“应当如此”的景物,而诗歌中隐喻的情感与某些意向性的表达使得原本没有在物质直接刻画的层面上的景物变得内涵丰富起来。因此,尽管意象之中的景物表达可大可小,但是情感的丰富性使得原本没有细致刻画的景物能够蕴含更多的情感上的丰富性。
(二)色彩美
与西方的诗歌、绘画艺术不同,中国的艺术并不追求色彩的浓与暗对比,而是运用线条的勾勒表现画面的神韵与意境,并把其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即是“以气为主”,主要以作者或欣赏者自身的修养来作为评判画的价值标准,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价值原则,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色彩感也与纯粹刻画景物的色彩有所不同。对于色彩感的描述乃是中国诗歌的重要问题,正如上文所指,中国诗歌的另一种追求——留白提示了色彩感的重要性,平铺直叙的景物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意向性的表达和隐喻的情感来给人回味的余地,这里色彩的表达也是意向性的一个重点。
对于诗歌的整体意象,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意象的模样,在于“趣味澄夐,若清之贯达”,也就是在色彩上追求“无色”,不设置五光十色的形象,否则在意象的创作上就会趋于雕琢,拙于技巧而不会表达出情感本身,这也就是中国古代诗歌表达出澄澈意象的色彩方面的原因之一。
在具体的创作及《与李生论诗书》中“二十四联诗”中,司空图将这一原则应用到具体的批评和创作中,在《二十四诗品》①中,专门设有批评诗歌色彩美的《洗炼》《绮丽》与《自然》篇,其中色彩的追求都是以修饰平淡的意象为主,在《绮丽》篇中,还强调“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淡者屡深”。[5]认为浓墨重彩的意象带给人的感受必定是肤浅的不能维持长久的,只有表达浅淡情感的诗歌才能够深入人的内心,给人以深度的审美感觉。
之所以形成重清淡的审美意象,除了与佛禅思想有关之外,笔者以为,还在于汉语诗歌本身的逻辑情感。如前所述,对于整体感的追求使得中国诗歌重抒情,而对于具体物象的描写则并没有详细的叙述。而作为语言的一种属性,对色彩的描述会直接刺激人的视觉感,给人以一种直觉上的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不属于一个形象的范畴,反而是事物所特有的属性,属于可传达的抽象范畴。当然笔者并不是说色彩没有“感觉”,而是在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带有一种概念上的传递性,它必须以普遍事实的基础之上的理性认识,借用其附属的在每个人心中的特定含义传递下去。同时,色彩所赋予的情感可能带有强烈的意志目的,相反的,清澈的意象则不能刺激人的感官,这也是古代意象所追求的平淡意象的内在目的。
三、语言模糊性效果
以往一提到语言模糊性的效果,绝大部分人都会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对于文学语言模糊性的思想一直都在文学的发展中延绵不绝。无论是《论语》中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还是魏晋南北朝的“文笔说”,中国古代的文人一直生活在文学与非文学的判断中,因为语言模糊性不仅是文学本体的问题,还涉及到文学的民族化,即中国古代人的文学评价标准问题,甚至延续到今天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上来。
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以咸酸喻诗,用咸酸的效果来比喻诗歌的审美效果,其中就提到了诗歌与日常用语的表现之不同在于其“辨于味”,并把陌生化的极致效果称之为“韵外之致”,以此说明诗歌的语言与其他问题,尤其是日常用语的不同之一在于能够表现出含蓄而无尽的意义。当然,相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理论更重视语法与结构不同的是,司空图更重视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意象,在《诗赋赞》中提到“知非诗,诗未为奇。”强调意象的创作“神而不知,知而难装”,即诗歌的语言美在于能够创作出“不知”却能够有情感传达性的意象。
至于语言模糊性的效果,前文已有论述,在此不赘。这里主要论述的是陌生化的方法。除去汉语的本身结构与用法方面的特殊性,笔者以为,司空图所论述的诗歌最重要的效果之一在于“思与境偕”五言诗的效果上。“思与境偕”在字面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作者能够创作出浑融一体的艺术形象,相对于西方语法方面的文学性而言,中国古代文学更强调语言内涵的扩大和外在意象的收敛,而相对浑融的审美意象就恰好符合中国审美的内在要求,因此对于意象的要求也就成了司空图所理解的诗歌的重要特点之一。而对于这种诗歌的独特意象,也正是我们现代文学创作中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所需求的创作标准,为现代文学中东方现代性的构建创作留下了宝贵的话语。
司空图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观点是围绕着“象”展开的,他关于“象”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是以其为中介,运用感悟和体会的方式来论述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的文艺心理学的问题,提出了古人关于诗歌理论的重要观点,为后来的文学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以现代的视角来看司空图诗歌理论中视觉、听觉与味觉的感受范畴,尤其是对于视觉感的描述,也会对中国的诗歌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对司空图的理论详细加以分析并转接到现代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的可行性,对于中国文学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3][4][5]司空图著,祖保泉、陶礼天校注.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6]祖保泉.司空图诗品解说[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4.
责任编辑:郭一鹤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531(2016)03-00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