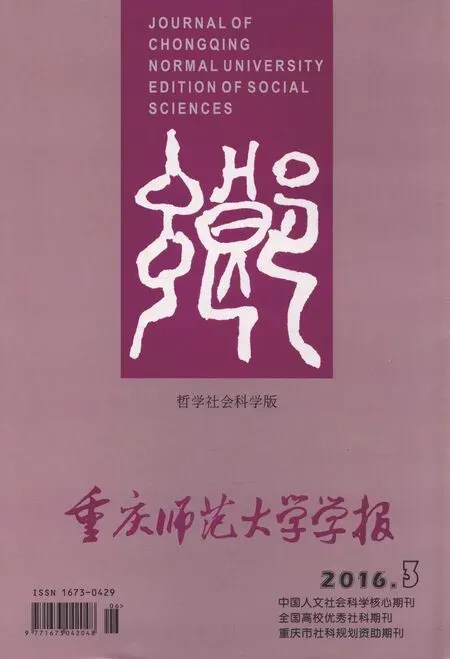墓志所见北魏秘著起家现象探研
2016-03-28刘军
刘 军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墓志所见北魏秘著起家现象探研
刘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六朝起家官明辨清浊,秘书郎和著作郎乃清官首望,素为甲第冠族独揽。北魏中叶贵族化运动继承摹仿,安排胡汉贵胄释褐秘著,出土墓志资料对此高调标榜,足可充当研究样本。北魏为秘著出身设定异常严苛的候选资格,只有世资旧令三品官爵以上的四姓膏腴之家方能入围。鉴于秘著解巾的崇高声望和坚挺效力,引发高门之间的激烈竞逐,导致任职者乡品超品与一品高下混淆。以宗室为首的代人勋贵呈现压倒中原旧族的绝对优势,凸显北魏的国家性质。秘著起家预示仕途飞黄腾达,首次迁转即破格提拔,最终官至显职,诱惑士族趋之若鹜。胡人大量秘著解褐还标志着文化水平的整体跃升,引领贵族时尚潮流的文史之学为其必备素养,这与南学北渐休戚相关。墓志反映的秘著起家现象是透视中古北方士族制度的重要窗口,也是解析北魏统治结构和身份等级序列的绝佳样本,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关键词:墓志;北魏;秘书著作;起家官;士族制度
谈到六朝门阀士族语境下的所谓“清官”,应首推掌管图籍艺文的秘书郎和负责国史编修的著作郎(合称“秘著”)。研究清浊官制的郑州大学张旭华先生明确指出:魏晋秘著的清官属性取决于与君主关系的近密性、文化士族的文翰性、职务待遇的舒适性及仕途发展的优越性,归根结底就是完美契合士族的利益诉求和文化旨趣[1]。因此,秘著成为士族登仕最为青睐的起家官,以此释褐乃汇集头等家世门第、崇高社会声望与杰出综合素养诸多优势的显著标志,令人神往、备受瞩目。南朝政权秉承中古贵族主义潮流之正统,始终将秘著起家与顶级阀阅紧密挂钩,搭建森严的身份阶梯。《唐六典》卷一○《秘书省》:“江左多任贵游年少,而梁代尤甚,当时谚言:‘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陈著《令》:令、仆子起家为之。”本文关注的是追踪南朝时尚、摹仿贵族制度的异族政权北魏,结合客观真实的墓志资料考查其秘著起家现象的具体情况,进而透视拓跋鲜卑的进化道路及北朝士族社会的特点。相关成果中,台湾学者郑钦仁先生《北魏官僚机构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极具启发性。拙作《邙山墓志所见元魏宗室起家制度初探》(《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北魏庶姓勋贵起家制度探研——以墓志所见为基础》(《人文杂志》2016年第4期)和《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见北魏起家制度举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3期)亦曾有所论议,然意犹未尽之处颇多,故撰此小文予以阐发,妥当与否,敬请方家指正。
一、墓志记载北魏秘著起家实例
研究证实,北魏墓志无论思想内容还是镌刻形制,均流露出浓郁的贵族气息,反映了当时如火如荼的贵族化情势,即将单纯政治意义的统治阶级改造为彰显婚嫁宦学,示范道德义务的社会场域的乡望士族[2]。惟有把胡汉贵胄纳入同一等级评估体系,恪守魏晋贵族既定的游戏规则,方能紧跟历史车轮,消弭民族隔阂,实现长治久安。这般氛围使世人生前以跻身膏腴为荣,死后亦不懈标榜,在墓志文着重渲染的贵族特质中,高度浓缩家世背景和仕宦资格的起家官往往被放在篇首的显要位置,以奠定华美的基调。而秘著释褐犹如士族皇冠上的明珠璀璨夺目,俨然甲第冠族傲视群伦的厚重资本。汇总该类素材,尝试在士族体制下分析其内在逻辑和深刻内涵,此乃笔者的创作意图。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赵超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记载14例,起家官的鉴别方式有三:一是根据专有词汇,《元灵曜墓志》:“起家为秘书郎。”(页137)《于纂墓志》:“释褐为秘书郎。”(页201)《王翊墓志》:“解褐为秘书郎中。”(页253)《元玕墓志》:“起家为秘书郎中。”(页315)二是参考入仕年龄,《韩显宗墓志》:“弱冠之华征荣麟阁(任著作郎)。”(页39)《元崇业墓志》:“弱冠誉高,拜秘书郎中。”(页154)《元熙墓志》:“年未志学,拜秘书郎中。”(页169)《李颐墓志》:“年十八,征拜秘书郎。”(页179)《元融墓志》:“年十二,以宗室令望拜秘书郎。”(页205)《元袭墓志》:“弱冠除著作佐郎。”(页295)《李宪墓志》:“年十有二,为秘书内小。”(页329)三是查找履历首职,《元璨墓志》:“擢秘书佐郎。”(页152)《元湛墓志》:“永平四年,旨征拜秘书著作佐郎。”(页239)《崔混墓志》:“永安二年拜秘书郎。”(页327)另外,中华书局2012年刊印的齐运通先生《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收录2例,均有表示起家的典型语词。《穆景胄墓志》:“起家为秘书郎。”(页25)《穆景相墓志》:“释褐秘书郎。”(页38)当然,本文取材范围相对有限,结论还有待新资料的进一步证实和补充。
综合生卒年和起家年龄等已知信息推算各例的入仕时间,发现密布于铨叙规章成熟稳固的中期以后,王翊、韩显宗、李颐、元融、李宪在孝文朝,元灵曜、于纂、元玕、元崇业、元熙、元袭、元璨、元湛、穆景胄在宣武朝,穆景相在孝明朝,崔混在孝庄朝。这时北魏的国家政体建设步入正轨、日臻完善,贵族化运动也在有条不紊地渐次推进,据此还原阀阅体制下的秘著起家制度具备技术可行性。但并不是说大族秘著解巾是改革的产物,其出现实际要早很多。《魏书》卷二四《邓渊传》:“性贞素,言行可复,博览经书,长于《易》筮。太祖定中原,擢为著作郎。”同书卷五二《阴仲达传》:“少以文学知名。世祖平凉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启仲达与段承根云,二人俱凉土才华,同修国史。除秘书著作郎。”同书卷七九《成淹传》:“好文学,有气尚。……皇兴中,降慕容白曜,赴阙,授兼著作郎。”三例分别事发道武、太武、献文朝,皆是朝廷遵照魏晋传统优礼汉族知识精英,通过提升地位换取其转变立场之权宜举措。只有经历了孝文帝太和改制,秘著才成为名门望族的专属起家官,并严格限定入围条件。《通典》卷一六《选举四》引《魏书》旧本佚文:“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可见,秘著作为高档起家职务与厘定姓族后新生的门阀序列协调匹配,共同开辟特定的官僚晋升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秘著解褐者的墓志喜欢夸耀中选的缘由。表彰道德名望的有《元灵曜墓志》:“孝友之誉,夙彰于闺门;贞白之操,备闻于乡国。宗党钦其仁,缙绅慕其概。”《崔混墓志》:“始逾弱冠,祸延陟岵。君丧毁病,肌削形存。虽及授琴,余哀尚切。”《穆景胄墓志》:“仁孝早闻。”突出才性涵养的有《于纂墓志》:“幼以聪慧,长而机悟。用能茂实之名,羁角巳高;藉甚之称,巾弁踰远。”《元玕墓志》:“盖兼资之伟人,岂倜傥而已哉。”突出时尚风貌的有《王翊墓志》:“宗致玄远,志尚清高,有如水镜,无异珠玉。”《元袭墓志》:“工名理,善占谢,机转若流,酬应如响,虽郭象之辨类悬河,彦国之言如璧玉,在君见之。”《穆景相墓志》:“超然自远。”强调文学天赋的有《韩显宗墓志》:“载籍既优,又善属文。”《元熙墓志》:“文藻富赡,雅有俊才。”《李颐墓志》:“文章高雅,超于时伦。”《元湛墓志》:“性笃学,元好文藻;善笔迹,遍长诗咏。”凸显声威影响的有《元崇业墓志》:“士流挹其万顷,帝宗叹其千里。”《元融墓志》:“以宗室令望拜秘书郎。”《元璨墓志》:“君以帝胄美名,夙招令问,特被优诏。”《李宪墓志》:“(先祖)忠而为戮,卒逢宽政,遗薪复荷。”看似注重个人的综合素养,实则唯家格门第是从。因为在物质、精神产品配置严重失衡的六朝社会,良好基因的遗传、高雅品味的熏陶、完善人格的塑造、施展舞台的搭建都离不开优质资源的深厚积淀,而具备这种实力的只有主宰时代的高门士族。既然一流门户孕育卓越资质,秘著起家对修养的要求便间接转化为门第甄别,符合标准的士林翘楚必定出自天下闻名的四海大姓,本文的问题意识就在于此。
二、北魏秘著起家者的门第背景
众所周知,魏晋南朝视秘著起家为甲第专利。《梁书》卷三四《张缅传附张缵传》:“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晋书》卷四八《阎缵传》载华峤评价著作郎:“此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步其后尘的北魏原样照搬,别无二致。《魏书》卷六○《韩麒麟传附韩显宗传》:“太和初,举秀才,对策甲科,除著作佐郎。……显宗进曰:‘……不审中、秘书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来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高祖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按照惯例,秀才成绩甲科对应授予士族上品[3]80,推知著作郎本是高门的囊中之物;所谓膏腴,即膏粱、华腴的并称,乃阀阅序列之首席,说明秘书郎须有显赫家世作为支撑。墓志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现以北朝门第的两种规划方法进行归类。
古人常用“四姓”概念泛指特定时期或区域内势力最盛、名望最高、交际最广、影响最大的至尊豪门,如同晚近的“四大家族”。北魏全国范围内的汉人四姓实为五家,即雄踞中原、经久不衰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厘定胡人姓族,诏鲜卑勋臣八姓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同四姓;与君主有血缘关系的帝室十族元、胡、周、长孙、奚、伊、丘、亥、叔孙、车跻身其列更是不在话下[4]卷一一三,3006,3014。从具体家族来看,墓志所载秘著释褐者几乎全部出自胡汉四姓。元灵曜、元玕、元崇业、元熙、元融、元袭、元璨、元湛为帝室十族,于纂、穆景胄、穆景相为勋臣八姓;李宪望出赵郡,崔混望出清河。又王翊望出琅琊,领衔江左侨姓,与北方四姓相埒。惟南阳郡望李颐和昌黎郡望韩显宗未入四姓,疑二人才学出众,朝廷破格委任。16人中有14人四姓出身,占比高达88%,足证北魏秘著起家乃头号望族的特权。
四姓的另一解释见《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柳冲传》:“‘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即士族按三代官资划分的若干等级。前引《通典·选举四》里秘著出身搭配公卿令仆家世,系层次最高的膏粱和华腴。《魏书·韩显宗传》印证秘著专属膏腴之家。依六朝蓝本晋官品令,三公位列一品,尚书令、仆射位列三品[5]卷三七,1003,表明北魏膏腴身份的世资底限就是三品。参考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官品与禄秩的换算法,魏晋三品对应汉代中二千石的九卿,属重点关照的中央核心权力圈,因而极具体制象征意义[3]62,72。那么,墓志所见北魏秘著释褐者的阀阅是否达标呢?依孝文帝定姓族采用的翻版晋令的前《职员令》衡量,元熙、元融、元湛曾祖景穆帝、祖、父一品王爵,均值一品;元璨曾祖景穆帝、祖一品王爵、父一品公爵,均值一品;元崇业曾祖景穆帝、祖一品王爵、父一品车骑大将军,均值一品;元灵曜、元袭曾祖景穆帝、祖一品王爵,均值一品;元玕曾祖、祖一品王爵,均值一品;穆景相曾祖一品王爵、祖一品公爵、父二品侯爵,均值一品;于纂曾祖、祖一品公爵、父二品散骑常侍,均值一品;李颐祖一品骠骑将军、父一品征北将军,均值一品;韩显宗父一品公爵,均值一品;李宪祖一品太尉、父二品安南将军,均值二品;穆景胄祖一品王爵、父三品通直散骑常侍,均值二品;崔混父二品侯爵,均值二品;王翊祖一品镇北将军、父五品司徒从事中郎,均值三品。可见,若排除人生和官场上的个别偶发因素,秘著起家者的世资均值整体凌驾旧令三品以上,恰处四姓中膏粱、华腴的档次,与史书记载完全契合。笔者甚至怀疑,陈朝令、仆之子起家秘著的法令就袭自北魏。实际上,基于四姓定义的两种分类并不矛盾,无与伦比的家境本身就代表全国首屈一指的大族。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北魏秘著起家是胡汉顶级贵胄把持的禁脔。
还有个现象值得思索,堪称北魏政权柱石的代人集团构成秘著起家的候选主体。墓志所载16人中元灵曜、元玕、元崇业、元熙、元融、元袭、元璨、元湛、于纂、穆景胄、穆景相、王翊属于代人,只有李宪、崔混、李颐、韩显宗4人是被征服的中原士族,前者占据压倒性优势。台湾学者康乐先生研究揭示,开创北魏王朝的代人是以拓跋氏为轴心,囊括各草原同盟部落,广泛吸纳姻戚、恩幸、宾客为附庸,涵盖众多民族成分,靠利益纽带紧密凝聚的血缘、政治、地域三位一体的社会团队,他们凭借“国人”殊荣掌控国家的命运,顺理成章成为贵族化运动的主力[6]53。在标识独一无二贵族性的秘著起家问题上捷足先登,无疑是保持北魏代人国家本色的必然抉择。简言之,北魏秘著起家制度贯彻代人优先的原则,旨在加速其门阀化进程,时刻领跑贵族竞赛,极力争取“有自尊的汉化”[3]25,政治意图不言而喻。
三、北魏秘著起家群体的乡品异动
探讨秘著起家与乡品的关联,既可深入考查选拔资格,又能折射社会对它的推崇程度。六朝铨叙采取九品官人法,中正斟酌士人的德、才、簿伐,评估其仕途潜质,颁授相应资格——乡品。乡品是起家的决定要素,宫崎市定发现:“起家的官品大概比乡品低四等,当起家官品晋升四等时,官品与乡品等级一致。”[3]66当然,就像户调式执行的九品混通,它只是朝廷统筹把握的基准,未必尽皆适用。晋令秘著列六品官,以此起家者的乡品理论上应为二品,这是标识士族身份的唯一高品,从而确保本阶层对秘著职位的独占。皈投贵族主义的北魏同样发挥乡品的制约调控功能,《元瞻墓志》:“后为汝南王以茂德懿亲重临京牧,妙简忠良,铨定乡品,召公为州都,委以选事,区别人物,泾渭斯叙。”[7]228当门第固化后,乡品径直改称资品、门品。《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高阳王雍传》载元雍奏疏:“臣又见部尉资品,本居流外。”同书卷六○《韩麒麟传附韩显宗传》载李冲质询孝文帝曰:“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然而,北魏的乡品体系要比魏晋南朝繁杂许多。宗室中亲尊莫二的皇王子孙和异姓元功上勋后裔逸出中正品第,特授超品乡品,前引《元瞻墓志》亦云:“架群辇而崚嶒,超流品而苕蒂。”即为此意。中正管辖的高门二品则分化出上、下两等:上等世资均值超越旧令三品官,实则就是士族不敢轻易妄诩的乡品一品[8];下等世资均值旧令四至五品官,留守当初的乡品二品。超品乡品旧令四品、新令六品以上入仕;一品乡品旧令五品、新令七至八品入仕;乡品二品旧令六品、新令八至九品入仕[9]。北魏官僚基于家世背景的起家序列由此清晰呈现,有助于分析秘著起家者的乡品结构。
案《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墓志里充当起家官的秘书著作郎和秘书郎、著作佐郎在太和十七年(493年)前《职员令》中分列正、从五品,太和廿三年后《职员令》中皆列正七品。其前令品级照比晋令浮动一级,表明声威与效力的提高,以此起家的乡品随之由二品升到一品。如前所述,兑换一品乡品的世资至少三品,而这恰是解巾秘著的硬性条件。这样,乡品、世资、起家官三大要件精准衔接,内在联系融会贯通,验证了秘著起家的身份资格问题。
然而,严密的逻辑替代不了复杂的现实,出身秘著者的乡品并非都是纯粹的一品,还羼杂着宗室超品,元熙、元融、元湛、元璨、元崇业、元灵曜、元袭、元玕8人的世资数值与普通一品无异,但曾祖、祖父、父亲三状中皇帝、宗王之至尊成分终究令其与众不同。他们照理也应旧令四品以上官释褐,墓志中类似事例比比皆是,如曾祖皇帝、父祖至少一代为王的元毓释褐三品通直散骑常侍,元彦释褐三品骁骑将军,元焕释褐四品宁朔将军,元略释褐三品员外散骑常侍,元朗释褐三品步兵校尉,元仙释褐四品散骑侍郎,元诱释褐四品通直散骑侍郎,元彝释褐三品羽林监,元子邃、元子永、元礼之、元昉、元顺释褐三品给事中,元廞、元显魏、元广释褐四品员外散骑侍郎;三辈至少两代为王的元显释褐三品通直散骑常侍,元炜释褐四品谏议大夫,元悰释褐四品中书侍郎,元賥释褐四品散骑侍郎,元士深释褐三品羽林监,元均、元赞远、元爽、元乂、元倪、元悦释褐四品员外散骑侍郎[10]。这些职衔尽管尊崇,但多系冗散,存在贬值风险,威望远逊秘著。毋庸置疑,正是秘著清流上选的桂冠,吸引超品宗室自降身价,甘愿倒转屈就,从而造成起家乡品层位的叠加错乱。这种以退为进、李代桃僵的策略在贵族猎官博弈中频繁演绎,《通典》卷一四《选举二》:“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于迁。”可谓精辟。
六朝贵族积习,秘著领衔起家清职,有限的员额和坚挺的效力引发激烈争夺。《宋书》卷六六《王敬弘传》:“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求奉朝请,与恢之书曰:‘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著作佐郎亦“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11]卷四八,1350。北魏新贵同样对此趋之若鹜,以致“秘著本为起家之官,今或迁转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违明令,非所谓式遵遗范,奉顺成规”[5]卷一六,391。排队等候者甚众才扰乱了既定规则。竞争压力除了来自一品高门内部,还包括沽名钓誉主动降品的超品皇亲。总之,秘著起家群体乡品的异动客观反映出该职的紧俏,亦反证提高入围标准的必要。
四、北魏秘著起家者的仕途前景
笔者曾通过截取未来仕途的两个重要节点——首次迁转官和平生所任最高官来研判某个社会集团的贵族属性[12]。后续成果证实,这也是分析具体官职发展潜力的有效途径。清官破格超迁、坐取高位,浊官饱受限止、沉滞累年。北魏秘著头等清望的特质连带赋予起家者锦绣前程,仿佛出人头地的保险,利用墓志存录的完整履历就可加以逼真还原。
秘著起家意味着平步青云,首次迁转便异乎常态。本文墓志志主的晋升多晚于太和末叶,故采用彻底贯彻贵族流品原则的后《职员令》衡量升迁幅度。他们俱从正七品秘著起步,元融擢正四品骁骑将军,元璨擢正四品镇远将军,跨越六阶;李颐擢从四品中书侍郎,跨越五阶;李宪擢正五品散骑侍郎,跨越四阶;韩显宗追赠五等男爵,跨越三阶;元玕擢正六品中书舍人,元崇业擢正六品司徒录事参军,元袭、元璨擢正六品司徒主簿,穆景胄擢正六品司空主簿,穆景相擢正六品西荆州司马,跨越二阶;元灵曜擢从六品司徒骑兵参军,于纂擢从六品符玺郎中,元熙擢从六品给事中,元湛擢从六品司空骑兵参军,跨越一阶;王翊擢正七品员外散骑侍郎,虽平级调动,但班位大大前移,总平均值接近三阶。不仅突破朝廷考课“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4]卷二一,553的人事章程,而且超过散骑诸职、幕府上佐、流内武官等北朝典型清要职普遍首迁二阶的待遇,彰显秘著清望之冠的高贵性。此外,六朝秘著迁转迅捷,“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13]卷三四,493。《于纂墓志》:“寻转符玺郎中。”《王翊墓志》:“俄转员外散骑侍郎。”《元玕墓志》:“俄兼中书舍人。”《元璨墓志》:“俄迁司徒主簿。”也都表示短期内的蹿升,无须正常三、四年的间隔。总之,秘著非比寻常的升迁幅度和速度是其在起家阶段就备受垂青的关键诱因。
乡品既是对士人才堪几品的预判,蕴含乡品的起家官便与其承诺的仕宦峰值成比例地联动。反之,日后能否飞黄腾达也是考验起家官成色的重要标尺。我们预设三道参照线:一是比拟上古宗法贵族公卿大夫层位的五品官僚线,旧令五品乃士庶分野的鸿沟,新令五品则是清流内部区别高下的天堑,跻身其间才能为名流社会所接纳。二是对应汉代九卿的三品线,若世资真按任子原则传承,累代三品以上的一品、超品门第就能确保三品的仕进底限,这是顶级阀阅的利益专区。三是与高门乡品吻合的一、二品,除了拥有天下首望的实力,还要适逢良机方能兑现乡品的预期。据此衡量墓志中的秘著起家者,最终官至新令一品有穆景相骠骑大将军,二品有元融车骑将军、王翊镇南将军、李宪征东将军,三品有于纂辅国将军、元玕平南将军、元熙安东将军、李颐洛州刺史、元袭平东将军、元璨太中大夫、元湛廷尉卿,四品有元灵曜骁骑将军、元崇业宁朔将军、崔混镇远将军,韩显宗和穆景胄起家不久离世,姑且省略。他们全部超过五品线,八成跨越三品线,三成迫近人臣极品,秘著起家官的助推力由此可见一斑,堪称仕途的强劲跳板。
中古官贵仕宦,起家年龄至关紧要,越早越易抢占优势。有两个岁数需要留意,20岁左右的弱冠之年乃士族常制,15岁前后的成童之年则是对皇室至亲和异姓勋臣的格外恩赏[14]。北魏墓志中秘著起家年龄可考者11人,崔混25岁,元灵曜、韩显宗、元崇业、元袭、元湛20岁,李颐18岁,元熙15岁,元融、李宪、穆景胄12岁,平均18岁,介于弱冠与成童之间,足证秘著起家群体在士族阶层中的上游地位。概言之,秘著出身帮助士族提早入仕,尽快通过既定的仕进通道,顺利攀登官僚金字塔的顶点,是维系门阀等级秩序和冠族权益的利器。
五、文史之风北渐与胡人秘著起家
北魏统治者注重发挥秘著的文化职能,坚决杜绝前朝频现的尸位素餐的现象。《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天兴中,给事秘书,转著作郎。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同书卷六六《崔亮传附崔光韶传》:“敕光韶兼秘书郎,掌校华林御书。”同书卷六○《韩麒麟传附韩显宗传》载孝文帝督责著作郎韩显宗:“著作之任,国书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闻。若欲取况古人,班马之徒,固自辽阔。若求之当世,文学之能,卿等应推崔孝伯。”文教事业的蓬勃发展对秘著的知识水准提出极高的要求,故前期选任一边倒地倾向汉族文士精英。孝文帝太和改革彻底扭转形势,出身秘著的胡人日益增多,见于墓志的有元灵曜、元玕、元崇业、元熙、元融、元袭、元璨、元湛、于纂、穆景胄、穆景相11人,占比69%,官场格局为之巨变。
不少墓志颂扬胡人秘著的学术声望和撰述之功,以示称职尽责。《元灵曜墓志》:“声标麟闱,朋徒嗟尚。”《元崇业墓志》:“秉牍麟阁,厘校坟艺,洋洋之美,典素载清。”《元熙墓志》:“文艺之美,领袖东观。”《元袭墓志》:“缉厘东观,毗赞槐庭,籍甚有闻,声实无爽。”《元璨墓志》:“时寻有敕,专综东观,坟经大序,部帙载章,所进遗漏,缉增史续。”《元湛墓志》:“追扬雄之踪,义赏名贤,文贬凶党。”《于纂墓志》:“石渠载芬,麟阁斯蔚。”《穆景胄墓志》:“注述焕于麟阁,声绩周于四宇。”这些言辞看似溢美虚夸,实则是胡人文化气质类型根本蜕变的真实写照。随着与中原先进文明接触渐深,胡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也在悄然转换,创造精神财富的文士取代驰骋疆场的武将乃大势所趋[15]97。浓缩贵族时尚旨趣,讲究语言文字运用技巧的文史之学成为胡人晋身主流社交圈之必备,所获成就举世共睹。《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常山王遵传附晖传》载,痴迷文史的元晖“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同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下·彭城王勰传》:“勰敦尚文史,物务之暇,披览不辍。撰自古帝王贤达至于魏世子孙,三十卷,名曰《要略》。”同书卷二七《穆崇传附穆建传》:“颇好文史,起家秘书郎。”文史之学在胡人内部蔚然成风[16],这是其堪任秘著的先决条件。
六朝文史之学的中心本在江左,它顽强冲破南北对峙的壁垒,席卷内徙胡人社会[17]。除广泛流传的名人佳作可供揣摩玩味外,降臣作为文化使者也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胡人倾慕进而师承江南学术离不开他们的正面引导。太和十七年(493)投诚的琅琊大族王肃常与彭城王元勰等胡人重臣切磋诗文,展示南朝文风的魅力,其侄王诵、王翊皆文采飞扬,辅佐汝南、清河二王,与胡人学术交往频繁[4]卷八二、六三,1412,1413。再如避难北归的大文豪温子昇,相继效命广阳王元渊、东平王元匡麾下,文书信札俱代为执笔,才藻令胡人叹为观止[4]卷八五,1875。其所引领的文学新潮在胡人贵族化运动中推波助澜,使之后来居上,逐渐胜任秘著工作。
综上所述,六朝贵族主义的思想精髓无外八字:清浊流品、家格门第,累代积淀的家世背景是区别身份地位、配置权益资源的唯一尺度,不同等级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形成互不干扰的层位秩序。这个原则在士人起家阶段便集中凸显,清官首望的秘书著作自然被顶级高门垄断,就此踏上独一无二的仕进坦途,唾手可得高官厚禄。北魏孝文帝援引贵族原理改造统治集团,“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4]卷二四,631,据此精心设计秘著起家的人事格局。他并行编织国家政权与社会族望的双条线索,融汇世资等第、政治立场、种群归属、文化修养四大要素,通盘权衡候选资格,透射出北魏政权与阀阅体系的内部构造和运行机理,特别是揭示出内徙胡人勋贵演进的历史规律。从制度传承来看,北魏秘著起家绝非魏晋南朝旧制的简单延续,而是借助其框架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度系统整合,将中古门阀士族制度推向极致。出土墓志之宝贵就在于如实保存了这些信息,亟待后人的挖掘梳理。
[参考文献]
[1] 张旭华,张斯嘉.魏晋清官探源:贵势垄断“秘著”新论[J].史学月刊,2016,(2).
[2] 刘军.河洛北魏宗室群体的贵族化趋势——以元寿安墓志为例[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3]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 [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 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M].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
[7]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8] 方北辰.释九品中正制度之一品虚设问题[J].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1).
[9] 刘军.北魏庶姓勋贵起家制度探研——以墓志所见为基础[J].人文杂志,2016,(4).
[10] 刘军.邙山墓志所见元魏宗室起家制度初探[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11] [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 刘军.北魏宗室阶层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09.
[13] [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4] 刘军.两晋、萧梁、北魏宗室起家制度比较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6,(2).
[15] 孙同勋.拓拔氏的汉化及其他——北魏史论文集[M].台北:稻禾出版社,2005.
[16] 刘军.论北魏迁洛宗室的知识素养与文化价值取向——以洛阳邙山墓志为中心[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17] 刘军.试述元魏宗室墓志中的江南元素[J].江苏社会科学,2015,(2).
[责任编辑:刘力]
On the First Founding System of the Mishu and Zhuzuo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from the Epitaph
Liu 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Documents, Jilin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The Mishu and Zhuzuo were the highest rank of the first founding official that was monopolized by the top famil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ix dynasties. The system was inherited by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was faithfully recorded by the epitaphs. Only the family background of exceeding up the third rank could achieve the qualification. It was just the reputation and effect of the position that caused the fierce competition and led to confusion of the country grades. The Dai person group took the overwhelming advantage to the central plain gentry to ensure the state character. The Mishu and Zhuzuo first founding system indicated the bright future to attract the noblemen and the huns’ improvement of the culture level.
Keywords:epitaph;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Mishu and Zhuzuo; the first founding; aristocratic system
收稿日期:2016-10-18
作者简介:刘军(1979—),男,汉族,辽宁抚顺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古北方民族史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研究”(编号14D031)。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6)03—0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