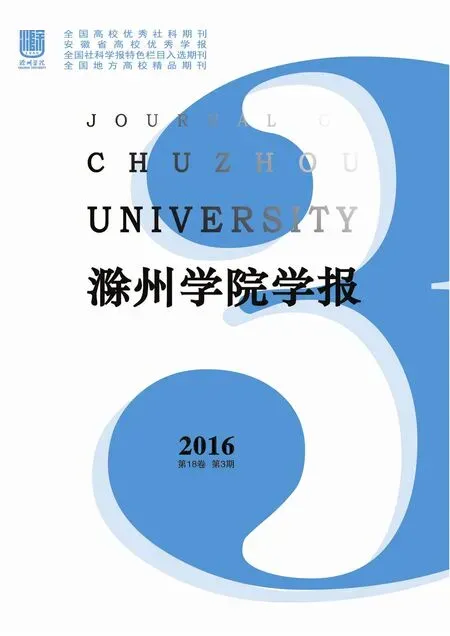探秘、寻找背后的忧郁与浪漫的重拾
——潘军小说论
2016-03-28徐莹
徐 莹
探秘、寻找背后的忧郁与浪漫的重拾
——潘军小说论
徐莹
摘要:潘军的小说可分为三类:即解秘的叙事、历史的叙事和城市的叙事。叙事的主题是探秘与寻找,叙事的切入点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而贯穿其创作始终的则是对形式的一贯重视,以及叙事背后的忧郁与浪漫的重拾。
关键词:探秘;解秘;叙事;寻找;忧郁;浪漫
潘军喜欢讲故事。翻开他的小说,大多讲述着一些引人入胜而又令人深思的故事。故事的总体主题是探秘与寻找,故事的总体色调是略带罗曼气息的忧郁的蓝色。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潘军当然注重故事的讲述方式,并且试图把写什么和如何写很好地统一起来。在潘军的小说中既有博尔赫斯迷宫式的叙事策略、塞林格辛辣的戏谑嘲讽,又有浓郁的情节性和戏剧性,使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先锋形式试验的躁动与诗人式的忧郁与浪漫贯穿在一起。
一、探秘的故事与解秘的叙事
(一)探秘的故事
潘军在中途搭上80年代中后期那列先锋文学快车。尽管1987年前他已发表了20多万字的小说,但真正的成名作还是这年发表的《白色沙龙》。这篇小说用幽默而辛辣的笔调叙述了一种含泪的痛苦,皇甫对权力的小心迎奉,达令的愤激,“我”的无聊,二郎的游离,这些无可奈何的小人物展示着各自非本真的生存状态。文中闲散随意近乎嘲讽的笔法在展示人物心理真实,生存困境方面虽见功力,但还显得粗糙杂乱。但其后创作的《南方的情绪》(以下简称《南》)、《省略》、《悬念》、《流动的沙滩》(以下简称《流》)、《爱情岛》等则标志着其形式试验的逐渐成熟。这些作品总的主题是探秘故事。潘军套用了侦探或探险小说的模式,主体(主要是第一人称“我”)因若干原因,来到陌生地(蓝堡、爱情岛、沙滩),进行探秘活动,最终以或奇异或荒诞的方式结尾。当然,不用侦探小说中情节的步步严谨的逻辑推理,最后揭开谜底,让读者恍然大悟,以飨一开始被高吊起的窥秘心理,探秘在故事的主题和形式上是统一的。潘军在这类小说中一方面不断地设置一个个陷阱,让读者掉进去,另一方面又把陷阱中残存的秘密打扫干净,让人一无所获,怅然而归。探秘走向了解秘,因而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解秘式的叙事。探秘与解秘的叙事置于同一个文本,使小说具有不确定性、开放性。
(二)悬念与解秘的叙事
悬念,悬念的设置与解构在潘军这类小说的叙事中处于关键位置。这类文本中都存在着一个总领全篇的悬念作为结构全文的依据,如“一个被名叫老板的人邀去蓝堡度假的电话”(《南》)、一本名叫《流动的沙滩》的书(《流》)、“一个匿名包裹”(《那年和行吟诗人在一起的经历》)、“一个带口红的烟蒂”(《悬念》)等。探寻这个悬念时又会出现许多新的悬念,使探秘过程不再变得清晰可辨,当然不会产生明确的结果,而整个文本就变成由许多悬念相联缀的整体。潘军不揭示最终的真相,只提出一个个悬念、秘密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并且在对探秘的故事进行虚构时和解秘的叙事相交织。如《流》中,“我”逃亡到南方的岛屿是为了写一本《流动的沙滩》的书,而这同样是一位丢失了铜刀的神秘老人要写的书。老人、铜刀、书便成了结构全篇的悬念,使整个故事成了探秘的故事;而写作过程便是解秘的过程,闯入写作过程中的少女和警察无疑是写作的添加剂,也成了新的疑点。最后那把铜刀破掉了救生圈与老人的动脉,老人溺水而死,而《流》也不过是一本关于虚无的书,秘密到了最后被消解掉。而且在“说明·新小说”“小说者言”“博尔赫斯的记忆”等篇章里,作者更是说出了虚构探秘故事的方法。潘军在小说中既扮演叙述者(悬念的建立者),又扮演被叙述者(悬念的解构者),“这是对传统小说元叙事的肆意破坏,使故事从传统小说的模式下降为叙事中的一个因素,一个成份”,[1]从而带着浓厚的解构主义的色彩。这种解秘式的叙事也是作为先锋小说家的潘军的独到之处。
解秘叙事背后。同余华的暴力叙事、孙甘露的语言狂欢一样,潘军的解秘式叙事都是对传统小说创作规范的背叛,小说在他们看来更要关注怎么写。当然,这种背叛的涵义也可以从话语范畴扩大到意识形态。它冲破了元叙事(包括话语权威)的辖制之后作了自由的表演。作家无力主宰、干预、重塑外部世界,只得退缩到话语领域,使用语言、技巧建筑自己的王国。《南》、《流》等作品中的“我”不再是主宰现实的“大我”,而是局囿困顿于现实的“小我”,“我”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幻想的浪漫之旅在以警察(《流》)、列车长、经理(《南》)为代表的权势面前被阉割、嘲讽。当然这也可看作是对现实的曲隐的反映。但近乎纯技术的实验又导致了对现实生活本身的遗忘,对作品内在深度的开拓,使得先锋小说永远只是先锋式的高蹈,而落实不到现实的维面。为此,和其他小说家一样,潘军将笔触投至于历史,在对历史的再叙事中弥补这种不足,但又不失却先锋的文本实验。
二、历史的两种叙事
(一)两个系列
潘军笔下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系列。一是它承续其先锋式的解秘叙事,对历史进行再叙事,在一个个历史之谜最终被解开之后,展开出历史本身的荒诞,完成对历史的解构。这类作品以《蓝堡》、《夏秀传说》、《桃花流水》、《风》、《结束的地方》为代表。另一类则被潘军自称为历史自我小说,[2]即历史自我叙事。包括《我的偶像崇拜年代》、《1962年,我五岁》、《1967年的日常生活》、《重瞳》、《秋声赋》等。它们共同的主题是对历史真实的深刻怀疑与颠覆,历史在潘军笔下是暧昧的、朦胧的,无法用理性来加以言说的。
(二)历史的探秘
此类小说对历史的再叙事更多地延续了其早期的解秘式的叙事。主题是对历史的探秘。因而在这类作品中,历史中的秘密、悬念也成了结构文本的中心环节,只是对历史探秘时退去了明确的自我解构色彩,让故事更加完整一些,但仍存在许多未知可解的悬念。如《蓝堡》中,蓝堡的倒塌、余怡芹的死、临川词等历史之谜在“我”的寻找与探秘中并没有获得答案,相反更显得神秘,可疑与不真实。潘军表面上是想在对历史的寻找中建构一个故事,但实际上现实中却又出现了许多的冲突与矛盾,究其原因,蓝堡是虚幻的,它只是“作家记忆里的彩云霓。”而在《风》中,作者用历史的探秘与虚构、现实的记叙,作者的创作手记相互穿插,消解现实与历史的界限,从而对历史的巨大神话进行了怀疑与颠覆。更具故事性的《结束的地方》和《桃花流水》中,作者围绕着历史之谜——支队长宋英山被杀、船长王崇汉被杀进行探秘,却发现“历史呈现为接二连三的错误,当小说最终把‘真相’揭示出来,历史已无法更改,而‘真相’本身的而显得无足轻重了。”[3]人在历史面前只有被捉弄,人的存在只是个宿命。
(三)历史的自我叙事
在这类历史自我文本中叙述主体直接进入历史语境中,直接自我言说、评判,历史也就成为了个人的历史。在以故乡石镇历史为题的一组小说中,潘军大多以一个孩子“我”的眼光来打量文革这段历史。孩子眼中的暴力、夺权、革命和吃饭、睡觉、逃亡等日常生活没什么两样,因而历史的沉重与崇高在孩子的眼中也就变得那么可笑与荒谬。《我的偶像崇拜的年代》中作者用塞林格式幽默而辛辣的笔法记录了文革中石镇的一场革命夺权大战,而最终死去的却是无辜的赵老师。“我”则更关心的是毛主席有没有老婆,童趣的真实恰好反衬了历史的荒谬。历史的自我叙事中,《重瞳》无疑最具代表性,潘军没有采用“历史注我”的方法,而是采用“我注历史”的方法,让二千多年前的霸王项羽复活,让这个历史书上一直描述为“力拔山兮”的鲁莽英雄直接叙说“我是人,是个有诗人气质的男人,是出色的军人”,“我希望将来能带虞姬,骑着乌骓,浪迹四方,去过那种诗剑逍遥的生活。”这当然不是传统的历史小说的写法,而是非常现代的超现实手法。作者“纠正了历史书上对我的错误描述”,而把项羽塑造成一个忧郁而浪漫的文人形象,颠覆了历史的前文本。项羽最终兵败乌江被解释成历史对文人渴求正义、忠信,渴望自由,诗意地生活的理想的嘲弄与扼杀,传达了现代文人的生命体验。在历史、暴力、战争、权力面前,文人是弱小的,虽然他自视甚高;文人是孤独而又脆弱的,虽然他们有崇高的理想。
三、城市状态的叙事
如果说早期的文本试验和后来的历史的叙事更多地体现出作为先锋小说家的潘军对形式的重视与偏爱的话,那么对城市生活的记述则更贴近生活,大多也带有自传色彩,记述了92年以后下海从商的切身感受。潘军在这类小说中或以主人公身份的出现、或以旁观者身份谛听,传达了现代都市人的感受。这类小说中主要围绕着都市男女情爱故事为中心来叙事,通过对都市男女在物质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到相互的隔膜、无奈与孤独,反映了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困境。困境背后便是对逃离困境之路的寻找,因而,早期的探秘的主题到了城市系列中便成了寻找的主题。
(一)城市的状态
关于城市小说,潘军曾说过:“我的视点不在所谓的城市信息上,也不太关心时尚。感兴趣的是城市人的状态。城市与电脑呀歌厅呀什么实际上没有多深必然的联系,那些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标策而已,重要的还是城市生活的状态。”[2]的确,城市生活的关键是都市人的生活状态。而潘军笔下的城市生活状态是漂泊、孤独。漂泊是身体的流浪,而孤独则是心灵的流浪。在日益物质化的都市生活中,人也逐渐被物质化、符号化。人与人之间筑起一道道无形的栅栏,阻隔了相互的交流,人变得孤独,人正被逐渐异化。而知识、能力、才情、性灵、意志在同金钱的较量中相继败下阵来,在金钱面前,人的身体、心灵相继流浪,因而潘军笔下的都市男女似乎都不在状态,似乎总有种宿命。他们在纷乱的城市里备感孤独与失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躲在酒吧陌生的角落里(《和陌生喝酒》、《对话》)、素雅的茶楼里(《关系》)、海边的弃船上(《海口日记》),忧郁地看着繁杂的都市,不在状态正是他们的状态。这是存在的一种困境,来源于城市日益物质化的现实对个体的压抑。如《三月一日》中在一场车祸中差点丧命的“我”重新回到曾熟悉的现实中,才发现周围的同事、领导、妻子隐藏于内心的丑陋,而这之前自己竟一无所知,因为“我”和他们一样失却了纯真的自我。《关系》中男人女人如雨中西湖般缠绵的情爱经不住八万元钱的检验。漂泊与孤独成为他们生存的困境。
(二)寻找
寻找是为了摆脱存在困境,寻找到逝去的本真自我。潘军试图通过男女纯真情爱重拾来捅破人与人之间相隔的那层纸或那堵墙,让他们交流,彼此安慰,彼此抚平各自难言的伤痛。因而这种寻找便常带有一种古典的浪漫情怀。《海口日记》中那位作家自我放逐海口是逃避现实的困境,追寻逝去的纯真爱恋——外语系的女生,拖着长辫读大部头的前妻李佳,然而这种追寻在躁动的城市却显得极不现实。而与红尘女方鱼儿的情缘便是寻找失落后的一种寄托,方鱼儿这个古典小说中的青楼女子的现代版本使“我”暂时逃离了孤独的困境,但又是短暂的。方鱼儿最终一去不返,“我”浪迹海口同浪迹街头的瞎子一样孤独,没有方向。寻找被打上了重重的问号。《三月一日》中重新回到现实的“我”无法面对真实的现实(困境),而只有回到曾经插队的乡村,体验年少纯真的爱恋时,“我”不再做梦流泪的左眼才滴下热泪。然而,那个知道“我”小名的初恋情人已在“我”出车祸的同一天——三月一日死去。
(三)寻找的反讽
潘军想借都市男女情爱来摆脱都市人的生活困境,但又在不乏感伤浪漫的叙事最后,指出这种寻找的不现实(《故事》是一个例外),这也使小说笼上雅淡但却挥之不去的忧郁。而在另一些有关城市的小说中更是对这种寻找的本身作了反讽。《对窗》、《抛弃》中的于先生和柏教授因偶尔的一次对视或随意的一夜情而欣喜不已,自认为找到了平淡无聊生活的久违的激动。一番处心积虑的寻找知己之举最终却以喜剧的讽刺结束:柏教授的一夜情人差点记不住他并且刚新婚,而于先生追慕的对面爱看厚书的少妇原来是个精神病患者。寻找仅仅是一厢情愿罢了,寻找是种徒劳。正如加缪所言,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荒诞,而人的种种渴求这种荒诞的处境的寻找与选择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如西西弗神话般的精神劳役。
四、先锋与忧郁气质
如果说潘军在其解秘的叙事、历史的叙事与城市的叙事中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东西的话,这便是作为先锋小说代表作家的先锋姿态。先锋的首要要求便是自由。因而必须打破传统的创作规范对小说创作的制约。而先锋小说家对小说文本的试验便是以技术来背叛、颠覆传统。可以说先锋小说带给当代中国文学最大的收益莫过于促使作家对形式的重视。潘军当然不例外。
(一)形式的先锋
潘军对小说形式一贯重视。早期的作品《南》、《流》中的解秘的叙事几乎带有纯技术的形式试验,而后来对历史的探秘叙事融进了故事的情节性、戏剧性,则使形式的运用日益成熟。即使是后来贴近现实的城市的叙事也不缺乏形式的试验倾向,《三月一日》和《陷阱》无疑受到卡夫卡影响,前者中“我”的左眼能洞穿别人梦境,后者中“我”整天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都有超现实手法的影响。《海口日记》、《对门·对面》对心理刻画的细致入微,更类似心理小说。而潘军在有关城市题材的小说中则更多地采用了电影的技巧与手法。《故事》类似于一个剧本,《关系》中以对话结构全篇并穿插地使用蒙太奇手法,而《对白》和《陌生人喝酒》更像是一个高焦距的摄影机下的一个电影片断——淡雅的酒吧、一个倾诉者、一个聆听者、一段故事。可以说,正是对形式的一贯追求,才使96年后由先锋走向当下的潘军的小说有了内在的连贯,同时也不至于平庸下来。
(二)激情抑或浪漫
当然,先锋不仅是形式、技术上试验,更为内在的则是先锋的精神高度。以先锋文学为标志的“80年代中国文化进行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现代性文化的乌托邦”,它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色彩”。[4]虽然伴随着经济的来临,这场动动最终以狂热的极端形式告终,但先锋的精神依然保留在这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潘军身上。先锋意味着背叛与不承认。他早期的文本试验便是对现实合理性的不承认,而历史的叙事文本则是对具大的历史神话的不承认。先锋式的激情化为探秘的执着与解秘的迷幻贯穿于文本始末。而浪漫精神则在激情背后凸现,当然这里的浪漫不是只抒情,现代主义是反抒情的。浪漫是潘军处理现实与理想矛盾,填补其间裂痕的一种方法。如《南》中,时时被捉弄的作家“我”逃不回过去,最好的选择是与女人一些不挂地“骑着一头老虎,从林子里穿过,进入大山的怀抱。”《重瞳》中潘军让项羽自刎的乌江边来年开了大片的虞美人,老人与孩子来观赏,寄托了对作为“诗人项羽”悲剧人生的怀念。而在城市题材的小说中,男女之间情爱的浪漫与纯真则是都市男女困顿人生渴求的一剂良药,也是苦苦寻找的目标,不管它是否真能出现,毕竟昭示着一种希望。
(三)忧郁
与浪漫相连的是忧郁,这是一种必然。潘军有忧郁的气质,在《关系》中他就借文中的记者之口表达出来。对蓝色他也情有独钟,无论是《蓝堡》、《独自与手势·蓝》等小说中作为总体意象的蓝色,还是1993年他在海口所搞的“蓝星笔会”,都把蓝色与他的忧郁气质紧密相连。当然忧郁的气质更多地来自于对现实中个体生存境遇的感受。早年,体制内的身份与这一身份所带来的种种束缚在他的早期文本中均出现逃离与探秘行为,但无论是荒岛还是在蓝堡城,主体永远逃脱不掉环境的巨大压抑,因此宿命更成为了主体的唯一必然接受的结果,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主体的焦虑与忧郁,这是由外部异己力量造成的。如《南》中的经理、《流》中的警察就是外部异己力量的象征性表达。而被潘军称作“自我放逐”的海南四年虽然带来了体制外的自由,但确实是过着“沉重的自由”的生活。[5]物化的都市生活与追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是很难有内在的一致性,新的环境带来了新的束缚,也就带来了新的焦虑与忧郁。这时期潘军笔下的都市男女身上也打上了这种忧郁气质。所以,始终把笔触置于人物与环境关系之上,考察人物在其中的状态,便成了潘军小说中忧郁气息的根源。孤独忧虑的状态是绝对的,寻找也只能以失望或自我嘲讽告终,那么潘军唯一能做的便是上述的重拾浪漫了。
[参考文献]
[1]南帆.文学的维度[M].三联书店,1998:206.
[2]牛志强,潘军.关于潘军小说艺术的对话[J].小说评论,2001(6).
[3]吴义勤.论真实飘在风中、结束的地方·附录[M].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73.
[4]肖鹰.后先锋时代的文化空间:90年代中国文化透视[J].文学前沿,2002(1):26.
[5]潘军.漂泊与选择[J].山花,2000(6).
责任编辑:李应青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794(2016)03-0042-04
作者简介:徐莹,苏州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江苏 苏州 215000)。
收稿日期:2015-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