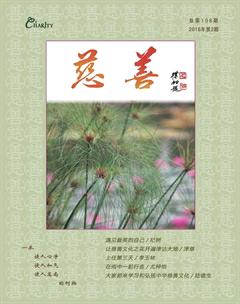小冬喜儿,你在哪里?
2016-03-28刘国林
● 刘国林
小冬喜儿,你在哪里?
● 刘国林
又到隆冬时节。40多年过去了,塞北普通农家那个叫冬喜儿的17岁男孩和他的一家,仍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低矮破旧的农舍,那朴实善良的齐大爷,与部队告别时冬喜儿眼里那不舍的泪花……像一幅幅画面,长久地留在记忆里。
1
1970年冬季的一场大雪过后,一夜间北方大地已成了银色世界。这是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入伍的第一个冬季,恰好赶上一年一度的冬训——野营拉练。当时部队流传“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口号,新的考验可想而知了。
根据上级命令,我们的部队要从驻地吉林省辽源市向塞北草原进发,跨越千里冰封雪地抵达驻训目的地。凌晨4点军号响起,连队开始配发物资做行前准备。尽管事前演练多次,尤其像我这样刚从学校分配来的新兵还是有些手忙脚乱。二班长陈德乙从连部领来“四皮”,即皮大衣、皮帽子、皮手套和棉皮鞋。大家把这种鞋子也叫大头鞋。几位老兵想上前去挑选,被他当场制止。“帽子、鞋子和手套,一会儿大家可按预报的号码领取。大衣先别动,我先找一件分量轻一点的给老刘同志。他身单力薄,第一次参加拉练就负重50多斤,走起路来会很吃力。”他高声说:“大家有意见没有?”“没有!”不等我争辩和请求,瞬间大家已把“四皮”分光。初到部队的这次特殊照顾,令我十分感动。再看看比我还弱小的年轻战友,领的大衣比我的还厚还重,特别是班长把那件最重的皮大衣留给了自己,我心里一时感到很愧疚,有些不是滋味。是呀,论年龄,我这个25岁入伍的学生兵已成全连的士兵之最。论身体,从家门儿到校门儿这二十几年缺乏实践锻炼的生活,体质自然远不如那些生龙活虎的战友。心想,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加强锻炼,好好补上这一课。“我现在干着士兵的活,却拿着干部的待遇。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吧。”我暗暗下定了决心。
第一天行军80公里,还安排了两个战术科目。黄昏时分,我们正翻越一座大山。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这么艰苦的路。被汗水浸湿的棉衣紧贴在背包上,阵阵寒风袭来直透心底。一双沉重的大头鞋以缓慢的节奏踏在雪地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步一步攀爬,好像不是穿在自己的脚上。二班长走过来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吗?”“放心,没问题。”我喘了口气,尽量以平和的语气回答。刹时,我感到轻松了许多。原来是他在身后用力地托着我的背包,并随手把一块硬硬的东西塞到我的嘴里。“啊?是块糖!”我差点惊叫出声来。心想,这位比我小好几岁的班长考虑问题可真周到细致,很让人打心眼儿里佩服!刚下部队时我已经了解到,我所在的三连,是在著名的淮海战役中被二野授予“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锦旗的英雄连。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荣誉可不能毁在我们手里。想到此,心中油然产生出一股巨大能量。我们互相鼓舞着、坚持着,终于顺利爬过雪山,在冬天寒彻的星夜里赶到第一个宿营地。
这一夜,我们按照打前站小分队预先分配好的住户进驻老乡家。因村子小容量不够,附近又没有合适的村庄,大家只好受点“委屈”。为不打扰老乡休息,我们入户后,静悄悄地打开背包,铺好皮大衣,以地当床,在老乡家的炊事间、堂屋过道里倒头便睡。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闪烁的火光惊醒。原来,住户的主人,一位头发斑白、60多岁的老大娘,看着我们这些年轻的战士实在辛苦和劳累,便悄悄地架起柴火,一边让大家取暖,一边帮助我们翻烤着那一双双不知是被汗水还是雪水浸湿了的大头鞋。“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大冬天为了百姓的安宁还得遭这份罪……”她边烤着鞋子边低声嘟囔着。多好的老乡啊!又和战争年代一样,以火热的支前情结,呵护支持着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我和二班长翻身坐起来,同大娘一起为睡梦中的战友们翻烤着大头鞋和潮湿的鞋垫。此时此刻,千言万语化在心中,似乎说什么感谢的话都有些多余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部队像一条绿色的长龙,在冬日阳光照耀下,踏着皑皑白雪继续前行。回首望去那座渐行渐远的小小村落,想想那些素不相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乡亲们刚刚熟悉的面孔,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
2
这一天,行军的路程不算太长。下午4点钟,我们便早早地到达了第二个宿营地——吉林省梨树县一个叫刘家崴子的村庄。吃过晚饭,二班长找到我说:“连里给了我们一个任务。今晚这里要召开村民大会,派我们二班代表参加。村里一方面欢迎我们的到来,另外也希望我们给大家讲讲当前的形势。你肚子里墨水多,我一口答应了,你看……”他是担心我太累,欲言又止。我想起毛主席当年总结红军长征时讲的话,“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虽说今天和平年代与战争时期已大不相同,但人民军队宗旨未变,我们仍然有这个义务啊!“好吧,让我准备一下。”看着二班长那真诚的眼神,我没有理由拒绝,爽快地答应下来。
在生产队“青年点”的一座大房子里挤满了男男女女的村民。吊在房间正中的煤气灯照得满屋通亮,事先摆好的小木桌上放着一壶冒着热气的开水和几个茶碗。队长和二班长分别讲了军民团结之类的开场白后,我便开讲。讲着讲着,我感觉额头上直冒冷汗,接着身体便瘫软下来。蒙眬中好像听到有人在大喊找医生,并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到一个小屋里……不知过了多久,我清醒过来。发现正躺在一户老乡家中,身上盖着东北人办喜事时用的那种崭新的大花被。二班长和几位乡亲们围坐在我身旁,不知是住户主人还是邻里,做了满满一盆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鸡汤。我没做多大贡献,反倒给乡亲们和部队添了麻烦。看到眼前这一切,心里感到很内疚,两行热泪不由得洒落双颊……
3
第二天一早,部队按计划中的行军路线继续前进。7天后我们顺利地到达了本次冬季野营拉练的驻训地——茂林。这是坐落在内蒙古哲里木盟边缘的一个地图上很难找到名字的塞北小村。全村大约有四十几户人家。小村周边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广袤大地。大地被白雪覆盖着,强劲的北风卷走积雪,偶尔可见灰褐色的片片裸露的地表。这里不通铁路,也几乎见不到汽车,偶尔有几辆军车驻停,村民们便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观看。在这严寒的冬季,似乎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空旷沉寂。唯见随风飘起的缕缕炊烟,才给这贫困的小村带来一线生机。用当地老乡的话说,“这些年由于当地头头胡搞,人心散了,集体经济垮了。生产队那点家当,绳头麻袋谁逮着谁拽……”听后,让人不免掠过一丝悲凉,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村子里的房屋比较破旧,多半都是干打垒的泥土房。不论房子大小,按照东北乡下习惯,多数人家屋内都是南北炕。这既方便居住也利于存放谷物。分配给我们二班的这户人家只有一间半房屋。主人齐大爷,60开外的年岁,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脸庞,讲起话来嗓门儿洪亮十分健谈。原来他带着二女儿小新和小儿子冬喜儿一家三口在这里居住。老伴儿不久前因病去世,大女儿和同村的一位青年结婚成家另过。因我们的到来,齐大爷让二女儿去了姐姐家,自己到一位邻居老哥家“找宿”,家里只留下小冬喜儿陪我们。知道部队要在这里驻训10天,他把一切方便让给了我们。
我们放下背包开始整理房间。大家争抢着担水、打扫庭院。按照部队传统,每到一地都要做到“柴满垛、地扫光、水满缸”。我环视一下这个不大的庭院,只在角落处堆放着不足一立方米的柴草。在这寒冷的冬季荒原上,地下无煤地上无山无树,当地村民又不习惯种高梁玉米类的秸秆作物,烧柴比金子还珍贵。透过齐大爷那为难和无奈的眼神,我似乎明白了一切。于是,便主动向二班长建议:“这点柴不够烧两天的,我们是不是趁着天未黑先到地里弄些柴来。”“真是和我想到一块儿了。”二班长表示完全赞成。站在一旁的齐大爷插话说,“不瞒你们说,这垛柴还是接到你们要来的通知后,我和冬喜儿忙活了一周准备的。原来地里有点杂草残叶,不是被大雪盖上了就是被狂风卷跑了。这里是不毛之地,拾点柴真难哪。”齐大爷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大竹耙子。这大概是专门为冬天到雪地里搂柴草用的。一排浓密的耙齿有1米长,加上耙把子足足有10多斤重。
我们扛起大竹耙来到村外,大家轮番地拉着这个“庞然大物”在空旷的荒原上反复“耕耘”,哪怕有几片残枝败叶挂在耙齿上,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丝惊喜。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还是有所收获。我们抬着一大筐柴草,高唱着《打靶归来》的军歌回到齐大爷家中。入夜,北风呼啸着吹动窗子和柴门吱吱作响。按照齐大爷的安排,把向阳的南炕留给我们,北炕上存放着一个装着玉米棒子的粮仓,小冬喜儿裹着件陈旧的羊皮袄就睡在粮仓顶上。一铺小小的炕上挤下我们一个班,翻身都很困难。这里条件有限,大家也都毫无怨言。经过一天的劳顿,我的那些年轻的战友们倒下便睡了,有的已发出了呼呼的鼾声……
不知过了多久,忽闻地面上传来响声。我警觉地睁开眼,借着微弱的火光惊奇地看到,竟然是齐大爷。老人家正曲着身子蹲在地上,点燃放在破旧铝锅里的干豆叶,为使火苗更旺些,一边轻轻地向里边续着豆叶,一边用小木棍拨拉着。原来齐大爷是怕我们冻着,深夜里不放心又来屋里生火。自己的孩子还睡在冰冷的粮仓上,而老人首先想到的却是别把我们这些战士们冻着。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感动!
见到如此场面,我和身旁的二班长再也无法安睡,我们两人几乎同时坐起来。他把自己的皮大衣轻轻地盖在小冬喜儿的身上,在这漫漫的长夜里我们一起同这位可敬可亲的齐大爷低声唠起了家常……
齐大爷老家在河北昌黎。1962年困难时期,粮食吃光了,菜根儿啃没了,为了生存,只好举家来到这里。初到这个荒凉的小村,举目无亲。正是那些素昧平生的乡亲们,自己还填不饱肚子,硬是从牙缝里挤出一把米一棵菜帮助他们一家,使其度过那无比艰难的岁月。提及往事,老人几度哽咽。“人心善,无灾难。人家对你哪怕有一点一滴的好,一辈子都不能忘啊!”老人喃喃地重复着。“我一见到你们,心里格外高兴。”齐大爷接着说,“其实我也是半个兵哩!解放战争那阵子,部队攻打昌黎,我是村里民兵担架队长。带着十几个弟兄到前线去救伤员。有一次,我们抬下一个大个子伤员,他胳膊穿了个洞伤得不轻。一边用手捂着伤口一边骂骂咧咧,老子这么卖命,也他妈的没弄个一官半职,连个娘儿们也没讨上。等伤好了,我非找老蒋算账不可……”“我一听这话,有点不大对劲。你是国军吧?我是来抬解放军的。你们把老百姓坑苦了,老子也没有义务侍候你。”“见他没有吭声,我让伙伴撂下担架就把他甩在一个水塘边儿。见鬼去吧,老子还要去抢救我的真正好兄弟!”齐大爷那种爱憎分明的态度和行为,令我们肃然起敬。我们聆听着那一段段并非神话的故事,困意全无。不知不觉间,已迎来第一缕晨光。
与齐大爷一家渐渐熟了,相处得像亲人一样。部队开展训练时,小冬喜儿每天都围前围后地观看。趁我们间休时还好奇地打听这些枪炮怎么用。每到休息日,我们以班为单位自办伙食。赶上包饺子改善伙食,就把他们全家都请过来,包括他的大女儿、二女儿和老人家那个外号叫“猫仔”的可爱的小外孙女。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
4
转眼间部队在这里的驻训任务结束。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要整装踏上归程。时间虽然短暂,我们边训练边派出工作队,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帮助村里重建了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大家心气振作起来,并着手做着开春的备耕准备。但愿小村从此会发生新的变化,会有一个好的前景。
部队出发前,为不惊扰当地老乡,贯彻上级“静悄悄来静悄悄去”的要求,我们事先做了缜密工作。但还是没有逃过齐大爷的眼睛。出发前的那个晚上,他找到二班长说:“知道兵事难挡,留也留不住。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把冬喜儿带走。这辈子我没当成兵,留下遗憾。但这孩子你们也看到了,是块好料,在我身边就毁了。我恳求你们……”这对我们是个大难题,我们既没有这个权力和政策,又不能伤害老人那拳拳之心和一片真情。经请示连里,决定还是做好齐大爷思想工作。老人通情达理,同意先不把离开的消息告诉小冬喜儿。
第二天凌晨5点钟,部队在村口紧急集合,经过低声点名后便列好纵队,在灰蒙蒙的晨曦中离开这座不舍的小村和善良热情的乡亲们。此时,路边突现了一群人影。原来,齐大爷和部分乡亲们还是早早地等在这里,挥手为我们送别……部队大约行进了两公里,天渐渐亮起来,这时我们才发现那个小冬喜儿一直尾随在队伍后面,把头低低地埋在那件破旧的羊皮祆里,默默地走着。二班长不得不跑步向连长作了报告。队伍暂时停下来,委托二班长和我一起去给他做工作,动员他立即返回家去。我们无法做出承诺,相信有一天他可能会实现自己的愿望,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小冬喜儿听了我们的劝阻,但还是一时无法控制情绪,突然呜呜大哭起来。那揪心裂肺的哭声,在寂静空旷的雪地里传得很远很远……懂事的小冬喜儿渐渐恢复了理性,答应不再坚持追赶部队。部队又走了一程,我回头望去,那个用羊皮袄裹着的小男孩儿,仍然像雕塑一样矗立在雪地里,目送部队远去。
5
40年后,我曾阴差阳错地与专职的慈善工作结缘,有机会接触和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捐赠事务,并亲眼目睹无数感人至深的善行义举,每时每刻无不受到人间大爱的震撼和教育。每当联想到当年发生在我身边的人和事,心中总是激动不已。想想那段往事中的战友情,军民鱼水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亲情友情,深深感悟道:人间无处不在的真、善、美,不正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同时也是慈善的真谛吗!
正是常怀这颗感恩之心,那些遥远的往事,总是让我牵挂,令我感动。小冬喜儿,我的好兄弟,你如今在哪里?一切还好吗?那个老是逗人发笑的小“猫仔”恐怕也已年近半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