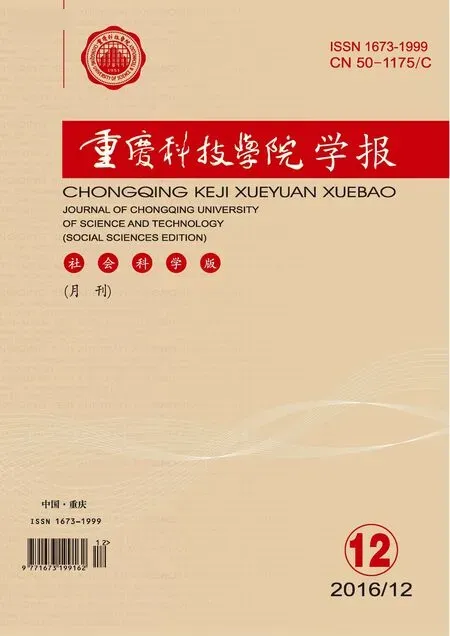论“魁阁”的“卡里斯玛”特质
2016-03-24刘晨光
刘晨光
论“魁阁”的“卡里斯玛”特质
刘晨光
20世纪30~40年代,以费孝通为首的“魁阁”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民国时期的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运用“卡里斯玛”理论分析“魁阁”的“卡里斯玛”特质,认为“魁阁”的出现具备“卡里斯玛”产生所要求的主客观因素,其领袖人物具有“卡里斯玛”特质。非制度化体现了“卡里斯玛”型组织的制度与结构特征,经济来源符合“卡里斯玛”组织的“非经济性”特征,甚至其解体也验证了“卡里斯玛”型组织的宿命。
“魁阁”;“卡里斯玛”特质;主客观因素;领袖人物;制度与结构特征
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9月,费孝通留学回国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得到了社会学系的创办者吴文藻的支持,在社会学系附设了一个研究工作站——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以方便费孝通等人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因昆明遭到日机的频繁空袭,工作站于1940年10月迁往昆明附近的呈贡县老城墙村的魁星阁,继续从事调查研究工作。于是,“魁阁”成了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代称。抗战结束后,工作站于1945年9月迁回昆明本部。在历时6年中,以费孝通为首,包括谷苞、胡庆钧、李有义、林耀华、史国衡、陶云逵、田汝康、王康、许烺光、袁方、翟同祖、张之毅、张宗颖等人先后进入“魁阁”从事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著、论文,开创了民国学术史上著名的“魁阁时代”。
当代学者对“魁阁”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魁阁”的源起、学术成就、人物经历等方面的史料性挖掘,而很少注意到这个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学术团体非常吻合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笔下的“卡里斯玛”特质。不论二者的吻合是巧合还是必然,但借助西方学者视域下的“卡里斯玛”理论对“魁阁”进行深入解读,探讨“魁阁”学术辉煌的深层原因,揭示未来中国学术发展之路,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卡里斯玛”理论的历史流变
(一)韦伯的“卡里斯玛”理论
“卡里斯玛”是早期的基督教术语,鲁道尔夫·索姆在《教会法》中将“卡里斯玛”解释为“魅力”“天赋特质”“感召力”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卡里斯玛”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使“卡里斯玛”成为其政治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之一。韦伯认为“卡里斯玛”魅力型领袖的人格特征是:他们具有超自然或超人的智慧、力量和品质,能够把众多的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其追随者和信徒,并共同为实现某种伟大的目标而奋斗。据此,韦伯将具有“卡里斯玛”型人格特征的魅力型领袖统治,视为历史上存在过的3种合法性统治类型中的一种,即“卡里斯玛”型统治是建立在对“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1]241。“卡里斯玛”型统治服从的是具有非凡品质的领袖,在相信“卡里斯玛”适用范围内,“由于个人信赖默示、英雄主义和楷模榜样而服从他”[1]241。在韦伯看来,“卡里斯玛”型统治具有以下特征。
1.“卡里斯玛”的合法性源于个人魅力
“卡里斯玛”的合法性直接取决于追随者的承认。所谓承认就是追随者依据使命和实际考验产生的对领袖人物的信赖。但追随者对“卡里斯玛”合法性的承认则源于“他被视为(天分过人),具有超自然的或者超人的,或者特别非凡的、任何其他人都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或者被视为神灵差遣的,或者被视为楷模,因此也被视为领袖”[1]269的品质。简言之,“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的天赋性、神圣性等特质,即非凡的个人魅力是其合法性获得追随者承认的前提。
2.“卡里斯玛”的权威具有不稳定性
“倘若实际考验不能维持持久,则表明受魅力的恩宠者被他的上帝所遗弃,或者丧失他的魔力或英雄的力量,倘若他长久未能取得成就,尤其是倘若他的领导没有给被统治者以幸福安康,那么他的魅力型权威的机会就会消失。”[1]270简言之,“卡里斯玛”如果不能经受实践的考验,其权威即合法性就随之消失。因此,“卡里斯玛”型统治续存的关键是合理地解决接班人问题,如能出现新的魅力领袖,“卡里斯玛”就得以延续,否则“卡里斯玛”便宣告终结。
3.“卡里斯玛”的统治方式具有神秘性和任意性
“卡里斯玛”型统治与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卡里斯玛”型统治并不存在鲜明的等级制度,也不受传统先例的约束,而是按照魅力的品质进行选择,其合法性适用的原则为:承认即合法。就此而言,个人的魅力品质及其经受实践考验形成的社会关系造就了“卡里斯玛”型统治的方式:没有规章,没有固定机构,没有任免,没有等级制度,也没有特权,而是“依据默示、神谕、灵感或者依据具体的创造意志”[1]271。
4.“卡里斯玛”的经济来源具有“非经济性”
“卡里斯玛”拒绝平庸的日常生活,拒绝合法的或传统的日常经济事务,不直接从事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因此其在经济来源上具有“非经济性”。“如果它的使命是一种和平的使命的话,它在经济上的必要的物资供给,或者通过个人的捐助或者荣誉馈赠,或者通过使命所指的人的会费或者其他自愿的奉献”[2]447,甚至掳掠。因此,从合理的经济角度讲,“卡里斯玛”“是一种‘非经济性’的典型政权”[1]273。
5.“卡里斯玛”的英雄主义信仰具有强烈的革命性
“魅力统治的权力是建立在对默示和英雄的信仰之上的。……这种信仰‘从内部’出发对人进行革命化,并企图依照它自己革命的意愿,来塑造事物和制度。”[2]451“魅力在其最高的表现中,从根本上突破规则和传统,干脆推翻所有神圣的概念。它不是让人孝敬历来就习以为常的、因此是神圣的东西,而是强制服从,还未曾存在过的、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是神圣的东西。”[2]452“卡里斯玛”的英雄主义信仰之所以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在于“卡里斯玛”承认非凡魅力的真实性,在实践考验中听从其内心的召唤而行动。当内心的体验达到某种狂热状态并产生新的思想时,会毫不留情地颠覆一切与之相悖的传统与规则,从而焕发出巨大的革命力量。
(二)后韦伯时代的“卡里斯玛”理论
韦伯心目中的“卡里斯玛”“生于忧患”,凭借其非凡的“超自然”特质经受实践的考验。具体说,韦伯心目中的“卡里斯玛”具有强烈的宗教性、神圣性。韦伯之后的学者则尝试从不同的视角阐释“卡里斯玛”,试图寻求“卡里斯玛”的平凡化存在。希尔斯认为“在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广泛的倾向,即将“卡里斯玛”的特质赋予平凡的世俗角色、制度、象征,以及人们的阶层或集合”[3]。“卡里斯玛”的平凡化或者世俗化倾向,使得“卡里斯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希尔斯之后,凯瑟琳·伯克和梅林·普林可弗认为“卡里斯玛”具有宗教的、社会学的以及现代的3种形式。宗教或精神领袖以“先验”“先知”造就的“卡里斯玛”组织属于宗教范畴;韦伯笔下由天赋的个人魅力品质及经受实践考验造就的“卡里斯玛”组织属于社会学范畴;现代的“卡里斯玛”应以韦伯理论为基础,通过科学量化的形式来具体阐释“卡里斯玛”的特质。为此,伯克和普林可弗提出了10项双变量量表具体研究不同领域的“卡里斯玛”[4]。林德荷姆则从群体心理和社会文化着手,试图通过查尔斯·曼森以及吉姆·琼斯的案例分析论证他的主张,对“卡里斯玛”的描述则从单纯的现象分析转向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在他看来,“卡里斯玛”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走向了兴盛,这种现象背后折射的是社会系统无力满足人们对共融需求的现实状况[3]。总之,后韦伯时代“卡里斯玛”的内涵渐趋明确、外延渐趋扩大。学者们对“卡里斯玛”平凡化的论证以及对“卡里斯玛”存在形式的不断细化,同样有助于对“魁阁”的解读。
二、“魁阁”的“卡里斯玛”特征
无独有偶。抗战期间,以费孝通为首的“魁阁”极其类似西方学者笔下的“卡里斯玛”型组织。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尚未将“卡里斯玛”理论运用于对“魁阁”的解读。因此,笔者从6个方面来揭示“魁阁”所具备的“卡里斯玛”特征。
(一)“魁阁”的出现具备“卡里斯玛”产生所要求的主客观因素
在韦伯看来,“卡里斯玛”产生于社会困境或危机中,类似于中国语境下的“时势造英雄”。在社会困境中,“卡里斯玛”取决于追随者对领袖在实践考验中体现的非凡魅力的信赖,这种信赖又与追随者的强烈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魁阁”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出现,完全具备“卡里斯玛”产生所要求的主客观因素。
首先,抗战爆发后,高校被迫纷纷南迁,西南边陲昆明迎来了大批学者,这为“卡里斯玛”型学术领袖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就“魁阁”而言,费孝通就是其领袖人物。他以非凡的学术功底和道德品格,吸引着战火纷飞年代的学人,从而促成了被人们称道的“魁阁”的出现。
其次,“魁阁”的出现,不仅仅与“卡里斯玛”型学术领袖的出现有关,而且与战时恶劣环境中的学人普遍抱有的知识或科学救国的信仰有关。费孝通在《云南三村·序》中写道:“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5]173换句话说,“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和把中国“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的使命,成为了“魁阁”学者的普遍共识和强烈信念。
最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弦诵不绝”对中国长远发展的意义。因此,战后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已经成为了爱国学者们的第一要务。事实上,“魁阁”不仅是社会学的实地调查工作站,而且也是培养新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的教学研究基地。“40年代,他(费孝通)的学生形成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学者集团。”[6]79这些年轻的学者聚集在简陋的魁星阁里,虽“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6]78在经受实践考验中,“魁阁”学者凸显了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躬身实践精神。
(二)“魁阁”的领袖人物具有“卡里斯玛”特质
“卡里斯玛”是魅力型领袖的人格特征,具有吸引和团结众多追随者或者信徒的卓越的智慧、力量和品质。戴维·阿什古在《费孝通传》中写道:“费孝通是头儿和灵魂,……他似乎有把朝气蓬勃的青年吸引到他周围的天才。……他的创造性头脑,热情、好激动的性格,鼓舞和开导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反过来,他们同志友爱的热情,生气勃勃的讨论,证实了他们对他的信任与爱戴。”[6]79在1940—1945年,被吸引到“魁阁”工作站并培养他们做社会调查的共有十几个人。“魁阁”成员张之毅在解释自己加入“魁阁”的动机时说:“当我在联大快要毕业的那一年,我才认识了费孝通先生,他是到联大来代课的,立刻我对他的讲授感受到特殊的兴趣,于是我决定跟随他做研究,这是我加入魁阁的简单动机。”[7]99张之毅成为“魁阁”成员的动机,一方面体现了当时费孝通作为“魁阁”灵魂人物的感召力;另一方面,费孝通作为“魁阁”灵魂人物的使命感体现在为现实抗战和未来建设寻求科学真理的出路上。为此,费孝通自称是“魁阁”的总助手,他期盼其他成员的成功,带领和鼓励他们进行创造,在短短几年内,“魁阁”成员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魁阁”的另一代表人物陶云逵也是社会学领域的传奇人物,费孝通在《物伤其类——哀云逵》中写道:“在呈贡三台山上,听吴文藻先生说起,城外有个‘魁阁’,‘魁阁’里有位陶先生。当时我们在山顶远远望去,在一丛松林里,隐约有个古庙。湖光山影,衬出夕阳缭乱里的归帆。找到这地方去住的,定是个不凡的人物。云逵本是个诗人,血里流着他阳湖望族爱美的性格,尽管他怎样对他天性遏制,怎样埋头在数字或逻辑里,但人静酒后,娓娓话旧时,他那种不拘泥于实际、富于想象、沉湎洒脱的风致,就很自然地使人忘却眼前的一切丑恶。”[8]5云逵的魅力在这段描述中栩栩如生,他超凡不俗、洒脱、富于创造的品质,恰恰符合“卡里斯玛”的典型特质。
(三)非制度化体现了“卡里斯玛”型组织的制度与结构特征
“卡里斯玛”型组织没有固定的制度与结构,一切都依靠领袖和追随者的智慧相机行事。“虽然‘魁阁’没有成文的纲领和约定,但成员彼此之间有自觉形成的共同为学术努力的信心和精神,这决定了他们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7]101“‘魁阁’没有事务人员,从经营公款到购买文具,从写钢板字到用油印机都是自己动手。”[7]108“魁阁”的这种反传统、反程序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没有成文的纲领和约定,没有具体的行政管理班子,既不存在等级制度,也不依赖家族或传统的力量,因此与传统型组织和官僚体制的组织形式具有本质区别,充分体现了“卡里斯玛”型组织在制度与结构方面的特征。
(四)经济来源符合“卡里斯玛”型组织的“非经济性”特征
“卡里斯玛”型组织依赖大规模的资助或战利品或偶尔的收益作为供应,“魁阁”亦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资助和捐款。有关“魁阁”的经费来源,阿什古在《费孝通传》中写道:“在云南时,他(费孝通)掌握一笔由英国理事会给予的庚子赔款奖学金,而他的云南研究所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国共同创办和资助的。”[6]86“洛克菲勒基金用完后,他们从农业银行、教育部及其他政府机构得些赠款。1943年,他们的大部分经费由云南实业家缪云台领导的省经济委员会资助。”[6]78“他(费孝通)请求太平洋关系学会捐1万美元,该会答应给一部分。哈佛-燕京学社提供4000美元。”[6]84可见,“魁阁”与“卡里斯玛”型组织的“非经济性”特征是吻合的。
(五)“魁阁”具有迸发出革命性力量的“魁阁”学风
“卡里斯玛”型组织成员听从领袖和内心的召唤,敢于从根本上突破一切原有的规则和传统,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以求真、进步和救国为使命的“魁阁”成员,形成了一种能够迸发出革命性力量的“魁阁”学风。“魁阁”的学风是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传来的,特点是采用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到选定的社区里去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在‘席明纳’(Seminar)里进行集体讨论,个人负责编订论文。”[8]13“魁阁”学者采取了与中国文人“读死书”截然不同的学问之道:第一步确定专题;第二步实地调查;第三步集体讨论。不同流派、不同见解的学者经常会因为所持观点的不同而辩论得面红耳赤。正如陶云逵评价的:“我们不是没有辩得不痛快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会。”[7]108虽有矛盾,但“魁阁”成员在研究工作中形成了合作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源于其精神的相通、信仰的一致。通过集体讨论,“魁阁”成员不断否定既有的认识并在否定中寻求全新的境界,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与矛盾,并在解决矛盾与冲突中达到超越。由此,“魁阁”工作站以其特有的反传统精神,在民族危亡时刻,迸发出了巨大的革命性力量,由内而外地作用于成员,改变了他们对生活环境和生活问题的态度,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进而确立了全新的价值取向。
(六)“魁阁”的解体验证了“卡里斯玛”型组织的宿命
韦伯认为“卡里斯玛”型组织的产生与社会困境或危机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困境一旦变换或危机一旦消除,则意味着“卡里斯玛”型组织的终结,除非其领袖人物能够不断证明和挑战自己,不断赢得新的追随者。抗战爆发、中华民族的危机和费孝通本人的学术与人格魅力等主客观因素促成了“魁阁”的形成,而抗战胜利后,这些因素的变化最终导致了“魁阁”的解体。首先是客观环境的变化:抗战胜利,内战爆发,“魁阁”已经进行的研究被迫中断;其次是一部分学者先后离开“魁阁”,尤其是其灵魂人物费孝通的离开,直接导致了“魁阁”的解体。
三、“魁阁”的学术成就及其地位和影响
综上所述,“魁阁”具备“卡里斯玛”型组织的典型特征,将“魁阁”视为“卡里斯玛”型组织具有充分的理论和事实依据。这一结论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魁阁”学术辉煌的深层原因,认识“魁阁”在民国学术史上的地位,领会“魁阁”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影响。
“卡里斯玛”型组织的典型特征是在一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时代中,一个怀着相同理想和信念的群体,在某一具有非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感召下,不拘形式,调动一切力量,向困难和危机开战,由此焕发出强大的革命力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就。“魁阁”正是如此。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一批学人团结在其领袖人物费孝通的麾下,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学术成就。在1940—1945年的短短几年间,“魁阁”学者取得的学术成果主要有:《禄村农田》(费孝通)、《化城镇的基层行政》(谷苞)、《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胡庆钧)、《汉夷杂区经济》(李有义)、《昆厂劳工》(史国衡)、《个旧锡业矿工生活》(史国衡)、《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陶云逵)、《西南部族之鸡骨卜》(陶云逵)、《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陶云逵)、《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内地女工》(田汝康)、《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许烺光)、《易村手工业》(张之毅)、《玉村农业和商业》(张之毅)、《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张之毅)等。在这些著作中,一部分当时被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大部分在改革开放后经过编纂进行了重新出版。
“魁阁”在短暂而艰难的岁月中所取得的辉煌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它在民国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成为后世学者效仿的精神榜样。谢泳先生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文中评价道:“魁阁”是“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7]98“马·弗利德曼称他们这项工作为‘社会人类学在中国的运用’,‘可以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北美和西欧之外,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蓬勃发展的地方,至少从这类知识分子的水平方面看是如此’。”[6]73更为重要的是,在抗战爆发后国家处于危难之际,“魁阁”学者展现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一座小小的古庙背后折射的是学者群体对于科学救国的执着追求,承载的是学者群体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可见,“魁阁”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在民国学术史上,以及世界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魁阁”精神对于中国未来学术发展的影响则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四、“魁阁”成功的历史经验
“魁阁”作为一个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学术团体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魁阁”艰难而辉煌的历史却给后世学者的学术之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魁阁”学者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魁阁”学者的坚定理想和信念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和建设中国”。这一坚定理想和信念使他们具有一种强烈而崇高的使命感,不畏环境险恶,不计个人得失,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依然坚定地埋头自己的学术研究,从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辉煌成就。反观当下,学术研究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在功利主义、官本位思想以及市场化的强烈冲击下,学者们长时间地潜心学术研究似乎成了一种冒险行为。于是“速成式”的学术研究到处泛滥,随之而来的不是学术精神的弘扬,而是学术研究的严重异化。相比之下,“魁阁”学者的“魁阁”精神和坚定信念,无疑是当代学者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
(二)“魁阁”学者具有文化自觉意识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与欧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并未盲目地崇洋媚外,在借鉴西方学术理论的基础上,“魁阁”学者在特殊的战时环境中,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性主体。他们不仅将西方的社会学思想引进到中国,而且还将中国的学术经验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的精神财富。“魁阁”学者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正确研判,并通过他们的躬身实践,使社会学在当时取得了和西方双向交流的学术话语权。因此,“魁阁”的学术研究体现了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意识的早期实践。
(三)“魁阁”学者具有躬身实践精神
“魁阁”学者在进行实地调查中遭遇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如战争环境险恶、物质条件匮乏、语言交流不畅等,但他们不畏艰险和困难,仍然坚持进行躬身实践。费孝通夫妇在新婚后去广西进行实地调查,于1935年12月16日遭遇意外,费夫人王同惠在意外事故中牺牲,费孝通腿部受伤在医院做了两次手术,这种献身学术研究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学界同仁。陶云逵年仅40岁就因贫困和积劳成疾而病逝。田汝康在访谈中曾这样描述他的田野研究工作:“客居异地的孤独寂寞加上生活上的不适应使得他曾一度想过从楼上跳下去。”[8]284类似的描述在研究“魁阁”的论著中还有很多。“魁阁”学者的传奇人生经历,就是对他们躬身实践精神的最佳诠释。
(四)“魁阁”具有自由、平等、开放的学风
费孝通虽然是“魁阁”的领袖人物,但他并非学霸式的学术权威,他充分尊重每个成员的学术自主权,注意营造自由、平等、开放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具体表现在:一是甘为人梯。他对“魁阁”成员,一方面在学术上予以指导和帮助,另一方面在工作上帮助克服遇到的困难。二是尊重成员。费孝通对“魁阁”成员的具体选题不加以严格的限制,而是鼓励他们根据个人兴趣选择或发掘题材。三是平等切磋。对学术问题进行自由、平等、公开的切磋,这是“魁阁”学术精神的灵魂。如在“席明纳”里,成员可以就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向每个成员公开征求意见。相应地,每个成员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费孝通作为“魁阁”的灵魂人物,在学术批评上也不例外。
[1]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G].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G].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刘琪,黄剑波.卡里斯玛理论的发展与反思[J].世界宗教文化,2010(4).
[4]SANDBERG Y, MOREMAN C. Common Threads Among Different Forms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2011(9).
[5]张冠生.费孝通传[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
[6]戴维·阿什古.费孝通传[M].董天民,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
[7]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8]潘乃谷,王铭铭.重归“魁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编辑:文汝)
G122
A
1673-1999(2016)12-0074-04
刘晨光(1975-),女,硕士,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淮北235000)信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2016-08-22
2016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当代大学教师学术品格培养策略研究”(SK2016A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