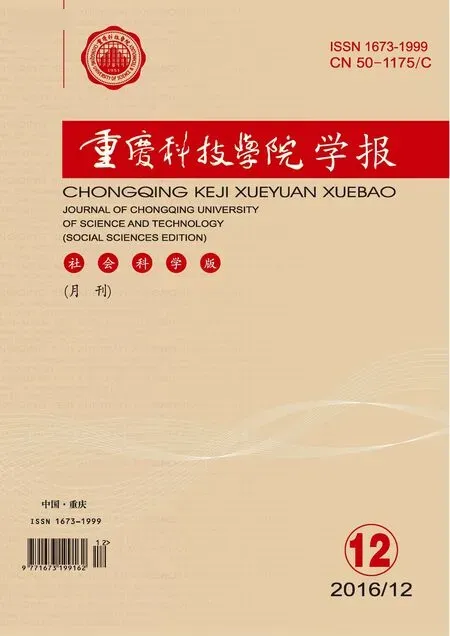老舍作品中的侠义精神及其困境
2016-03-24史玉丰
史玉丰
老舍作品中的侠义精神及其困境
史玉丰
老舍对侠义精神情有独钟,通过小说中的侠客以及侠义精神的书写,表达了他独到的思考。老舍注重表现的并不是侠客纵横江湖的潇洒和急人危难的豪情,而是侠客遭到时代戏谑的现实以及侠义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困境。通过侠义精神的祛魅性、闹剧性及荒诞化的书写,表达了他对侠义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其逐渐走向末路的悲哀情怀,他为侠义精神在现代性中的困厄和没落唱出了一曲悲哀的挽歌,并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进行了深沉的文化思考。
老舍作品;侠义精神;困境;荒诞化;挽歌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侠文化发展过程中,侠义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积淀于我们的文化心理中。侠义精神包含“侠”和“义”两个方面。“侠”最初指侠客,是中国侠文化的重要体现者,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其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704,彰显了侠客追求信义的诚信品质、赴士困厄的牺牲精神、不矜其能的道义观念以及自由不羁的精神气质。后来也引申为侠气:“人生精神意气,识量胆决,相辅而行,相轧而出。子侠乃孝,臣侠乃忠,友侠乃信。”[2]11可见,“侠”不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集团,而是演变为一种人格性情、意志精神和道德风范。“义”可以分为三层意思:一是指义气。主要是指舍己助人的精神,张扬英雄主义。二是指正义。为弱小者伸张正义、匡正除恶,彰显伦理价值。三是指道义。追求大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具有一种道德的高度。“侠”和“义”又是互相彰显的:“侠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3]7277由此可见,侠义精神的内核包括任侠义气、锄强扶弱、扶危济困、行侠仗义、自由不羁、重义轻生等高贵品质,是侠文化的主要精神追求和价值支撑。
侠义精神是从中国民间文化中体现出来的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20世纪的“国民性”改造中,曾被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鲁迅和老舍都曾对其进行过深刻的思考。面对未来的虚妄,鲁迅仍然对侠义精神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在鲁迅的作品中,侠义精神的代表宴之敖者,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体现了鲁迅对整个社会的思考以及对黑暗和邪恶的复仇精神。出身贫民的老舍从小所经历的艰难辛酸使他的内心充满着强烈的“侠义”需求和渴望。他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从启蒙立场出发对侠义精神正面的弘扬,而在于他从平民立场出发,通过审视侠义精神的现实遭遇来表达自己对侠文化的理性思考。鲁迅笔下的宴之敖者虽然一身黑色、冷峻可怕,但却具有高超的武功和无坚不摧的坚强意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侠义精神的抽象符号;而老舍笔下的侠客们却深陷世俗琐事的纠缠,具有凡人的一切缺点。在轻松的调侃和辛酸的幽默中,老舍对侠义精神的民间性进行了深入的刻画和思考,这种形而下的方式更具有人间烟火气息,体现了老舍现实主义的理性和民间主义的立场,他在寄希望于侠义精神改造国民性的同时,也对其表现了深深的怀疑和颠覆。
在老舍的小说中,这一思考主要是通过“侠客”形象来表现的,与武侠小说中叱咤风云、豪情万丈的侠客不同,他所刻画和描述的并不是侠客纵横江湖的潇洒和急人危难的豪情,而是侠客无力救赎世界或遭到时代戏谑的困境。通过对侠客形象的塑造,隐含着他对侠义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其逐渐走向末路的悲哀情怀,他为侠义精神在现代性中的困厄和没落唱了一曲悲哀的挽歌。
一、“侠客”凡人化
好武几乎是男孩的天性。对于老舍来说,这一点并没有意外,充当他辛酸贫苦童年生活精神食粮的除了他所念及的诗文,还有那些从家人、街坊听来的故事,最吸引他的就是那些侠义故事。上了小学之后,他有了到小茶馆里去听《小五义》和《施公案》的机会,在那样的乱世里,那些扶贫济困的侠客们激起了少年老舍的倾慕,以至于他把自己想象成为“黄天霸”纵横江湖。这个时期的生活对老舍的性格、思想以及文学创作都有着很大的影响,成为老舍独特的文化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他具有了“文人侠”的特点。那么,“侠”在老舍的文学世界中究竟占有何种地位?它是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又寄托了老舍怎样的历史情怀和现实隐喻呢?
老舍的作品中始终贯穿了对“侠客”的描写,如《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四,《二马》中的李子荣,《赵子曰》中的李景纯,《离婚》中的老李和丁二爷,《牛天赐》中的王老师、虎爷,《黑白李》中的白李,《断魂枪》中的沙子龙,《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茶馆》中的常四爷,《八太爷》中的王二铁,《火葬》中的石队长,《国家至上》中的回族拳师张老师等。他们身上都存在着侠客的影子,甚至《骆驼祥子》中虎妞和小福子也有着某种侠气……然而,老舍描写的侠客们却失去了想象中侠客的英武气概,他们或者如孩童般不谙世事(如赵四),或者以爱国为名实则莽撞天真(如李子荣、李景纯和王二铁),或者软弱无能而又浪漫冲动(如老李和丁二爷),或者是英雄末路隐退江湖(如沙子龙),或者满腔愤懑而无路可走(如常四爷),与其说老舍是在抒发自己的侠客情怀,不如说他是在写侠客的被压抑、被边缘化,以致走向消亡的悲剧。
佟硕之(即梁羽生)曾对“武”和“侠”之辩证关系有过一番论说:“‘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目的的手段。”[4]1强调了“侠”与“武”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在老舍的文学世界里,我们却看到了有“侠”无“武”的尴尬,他们没有那种“报恩仇,除奸邪,豪气冲天”的精神气概,却表现出一种犬儒色彩。救赎的无力感充斥了老舍的整个文学世界,他所表现的不是侠客英雄化的一面,而是世俗化、凡人化的一面,失去了“武功”的侠客们不再寄托拯救世界的希望,相反却证明了拯救的无望,正是通过“侠”之退隐乃至消亡,老舍表达了对世界的悲观认识。老舍小说中侠客的救世行为具有如下表现:
一是暗杀。如《老张的哲学》中王德刺杀恶棍老张不得反而自己生了一场大病,《二马》中的李景纯铤而走险,做了恐怖分子,虽然不爱己身勇气可嘉,比起混日子的赵子曰有更高的追求,但是正如夏志清所说,恐怖主义作为侠义观念的夸张和扭曲,在“救国乏术,失望之余……只能当作济急的药”[5]119。这种药并不能够救治久病的中国,这种暗杀行为除了损失国家的好青年,几乎于事无补。而且,还生出另外一种后果,即他们行动的暴力性质和不顾死活的程度与恶人们的行径如出一辙[6]195。这种铤而走险的行为既显示了“侠客们”的鲁莽和草率,也显示了他们的末路技穷,是侠客困境的一种表征。
二是借助外力。如在《老张的哲学》中,赵四虽然拥有侠义心肠,但是却没有适当的行动能力,他不得不借助于孙守备的力量去阻止老张和李静的婚事。然而,他的侠义行为并没有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他的出现只是证明了自己的“无用”,他是身处困境而不自觉的侠客代表。
三是以暴制暴。面对社会的黑暗和人间的不公,《黑白李》中具有侠义精神的白李组织工友们进行暴动,在被当局抓住制裁的时候,却是深爱他的哥哥黑李当了替罪羊,“侠客”白李在行侠仗义的时候,既没有周密的安排,也没有很好的善后,对于事情的发展没有丝毫裨益,只是失去了深爱自己的哥哥。老舍清楚地看到了侠义精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并对白李勇气有余、智慧不足的侠义精神所体现的鲁莽提出了善意的批评。
锄强扶弱是侠客侠义精神的重要表现,但是锄强扶弱有一个前提,即侠客在与恶人的争斗中要占有优势,然后他才能够发挥扶危济困的侠义功能。如果侠客本身处于弱势地位,甚至不能自保,那么,所谓的锄强扶弱也只能是空谈而已。如《离婚》表现了侠客不但无力救助别人,而且也无力自救的人生尴尬。作为浪漫的生存者,老李是那个泯灭良知的“混沌世界”里想认真“活着”的人之一,他的侠情义举,既是对于芜杂、琐碎、平庸、敷衍的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抗和回击,也是他对另一世界、另一自我的浪漫向往。他的侠情义举与其说是自然生发,还不如说是被无聊庸俗的生活逼迫出来的;与其说是要救赎别人,还不如说是救赎自己——在“他者”那里,老李找到一个释放自己和证明自己的空间,他是在平庸里追求崇高,在残缺、混乱的生活里寻求突破,显示了他对旧生活的反叛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所以,“他者”的困境给了老李一个挣脱自己困境的理由和驱动力,自我的拯救建立在“他者”的拯救的基础上,侠义行为已经成为他拯救自身的力量,是使他从封闭的生活通往另一个世界,即他的“诗意”世界的桥梁。但是,老李善良和软弱的“羊性”在“狼性”的小赵面前不能取得丝毫的胜利,他的失败早已注定。老李面对老张一家的困境,自己毫无解救的能力,只有把自己押给恶棍流氓小赵,任凭他随意处置自己,以换得小赵的帮助,老李的侠义行为是以向小人、恶人的妥协和乞求为代价的。“侠义”的可怜与卑微不能不让我们产生一种啼笑皆非的屈辱感,在心中压抑、愤懑的同时也感到无限的凄凉,而《离婚》所展示的正是侠者无力救赎的困境。
老李们所表现的正是侠客们“凡人化”的过程,或者说是祛除“神性”的过程,他们的困境不同于古代英雄的落难,有好人或者美人前来搭救,日后再展雄风。老李们的困境是来自于现代存在意义上的,显示了侠客的凡人性和救赎的无力感。这是现代历史背景下的“风景之发现”,这一尴尬的历史图景让我们看到了侠客的人生困境和日益消亡的文化悲哀。
二、戏谑与荒诞
侠义精神作为庄严、神圣的人类精神之一,历来能激起人们的崇敬之情。但是,在老舍所描写的侠客的侠义行为之中,我们却听到不绝于耳的戏谑之声。“闹剧”是老舍所喜爱的形式之一,他采用这种方式给我们创作了《马裤先生》《牺牲》《抱孙》等优秀作品,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种用滑稽写崇高的方式,给文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张力,荒诞感就是这一手法所引发的效果之一。
“小丑化”是老舍运用的手段之一。如老张(《老张的哲学》)、柳屯的(《柳屯的》)、老张一家、小赵以及丁二(《离婚》)、王二铁(《八太爷》)等形象,充分显示了老舍“犬儒的大玩笑家”[7]126的特点。侠客的义举与对象之间的不平衡性造成滑稽可笑的效果,既折损了侠客的高大形象,又解构了侠义行为的神圣和崇高。
《柳屯的》极力刻画悍妇的嘴脸,这个悍妇全村无人敢惹,只有“我”忍无可忍,最终向她宣了战,可是作为“打抱不平的侠者”,“我”未免底气不足,而且从一开始就抱着一种“玩玩票”的想法,带着看一出好戏的恶作剧心理,想看看这个悍妇的表演。所以,“我”并不着急想对策,也不着急采取行动,而是像个捣蛋鬼一样,故意下达战书,看看“柳屯的”到底如何反应。在“柳屯的”大张旗鼓地行动之时,“我”始终不肯与她正面接触,表面的虚张声势难掩内心的焦灼和慌乱,颇有骑虎难下之势。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柳屯的”被县里拿了去,“我”简直不知道要怎样收场:是好男不跟女斗,还是要打她一顿,或是到县里打官司?
《离婚》中的“侠客”丁二,是“机器神”(即解决情节危机的方便设计)[7]146一样的人物,如果没有他,老李的侠义行为也不知如何收场。丁二实在没有“侠客”的侠风傲骨,他是一个“废物”,不但形象猥琐,而且性格软弱,老婆就是因为他的无能才带着孩子跑掉了。于是,他便整天买醉,人不人,鬼不鬼,后来寄居在老张家里,地位仅比动物高一点,只是“活着”而已。他将恶棍小赵杀了之后,也并没有扬眉吐气,树立起自己的英雄形象,反而吓得躲在老李家里,再也不敢面对老张,害怕自己会说出去,害怕自己因为杀了人而坐监或偿命——“侠客”都如丁二一般,气数尽矣!而且,他杀死小赵的过程简单如同儿戏,与其说是理智的抉择,不如说是酒后的冲动。这种游戏般的戏谑和玩笑般的轻松不仅使他的侠客形象大打折扣,而且形成了有力的反讽,对老李的瞻前顾后和畏首畏尾的犬儒主义也是当头一击——杀死小赵太容易了,似乎不应该如此大费周章。
老李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他所要救助的对象几乎都是小丑式的人物,如张天真本身不知天高地厚,张秀真则浅薄无知,老张只知道混世而非老李的知己,而且他们竟然都不知道是老李在救助他们,这使得老李哭笑不得。而老李的另一个救助对象马太太在关键时刻与半吊子丈夫言归于好,宁愿在泥潭里生活也不愿意得到老李的拯救……老李的满腔热情突然沉入水底,只冒上几个可笑的气泡,使他成为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有着“侠客”狂想症的傻瓜,也显示出他与世界的隔膜——这世界虽然多有不公,但是已经没有侠客的立足之地,也有众多的苦难,但被救助者根本不承认或拒绝被救助。这种黑色幽默从根本上质疑了侠客救助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彻底颠覆了侠客的价值和救助的价值,使侠客们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荒谬之感:他们“在一个意义过于泛滥,或根本付之阙如的世界里追寻意义”[7]152时,却发现了自身存在的虚妄和危机,至此,我们以往对侠客的期待与崇拜全部化为侠客自身的反讽和讪笑。这正如老舍所说:“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8]349
《八太爷》中的乡民王二铁的遭遇则更为诡异。他倾慕晚清时期的好汉康小八(一般乡民称之为“贼”),在老母亲去世之后,卖地卖房倾其所有买了一支枪,到北京城准备“行侠仗义”,可是他所处的已经不是凭借一支枪就可以横行天下的康小八时代,他还没有施展武艺就遭遇了侠客最为窝囊的下场——死在鼠辈手里。他甚至不能够完成死前慷慨激昂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壮举,如阿Q那样将自己的生命在众人的喝彩声中落幕,便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了。他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英雄,但实际上什么也不是。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闹剧将侠义的价值戏剧化地逆转,才使得这一让人景仰和倾慕的行为转变为被嘲笑的对象。这种逆转与“侠客”所处的世界密切相关,这是一个魑魅魍魉的世界,是一个“以理想为笑话,以扭曲为常道”[7]144的非理性世界,这里存在凶险、麻痹、骗术、闲混,以及各路神魔的蝇营狗苟,而侠客们却依然奉行“义气”的江湖规则,就不免使自己的言行具有异于常人的种种乖谬之处。失去了江湖之根的侠客们成为了一群流浪儿,在不合时宜的世界里处处碰壁、举步维艰,种种侠义行为皆变为堂吉诃德式的笑料,供老张们茶余饭后咀嚼调笑,它所内含的崇高和神圣也在这种调笑中土崩瓦解,成为人生的一个“笑话”。在这种戏谑的笑声中,我们看到的是侠客们踽踽独行、渐渐远去的无奈及哀伤的身影,社会拒绝认同他们,而他们也拒绝认同社会,无论是极端的暗杀,还是被动的逃遁,或者主动的拒绝,都暗示他们“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结局。
老舍以闹剧的形式写出了侠客的困境以及不可避免的消亡结局,在轻松的背后却难掩痛苦和焦虑,闹剧之后一种悲壮感油然而生。他笔下的侠客不仅寄托着他对传统文化的凭吊,也承载着他关于人生和命运的思考,人生仿佛就是侠客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到头来尘归尘、路归路,既没有什么改变,也没有什么裨益,只是满足了看客。他们的复仇行为只剩下了最后的杀手锏——拒绝演出,并消亡在历史之中。这是他们在遭遇了生存的荒诞性和非理性的蹂躏之后,所作出的最后抉择。而老舍在侠客的困境和消亡的无言结局中,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对人生和命运的悲剧性言说。
三、英雄末路
在老舍为侠客们黯然神伤地写作哀悼的挽歌之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侠客在历史中消亡的必然性,这是老舍的现代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识的体现,由此造成的理智和情感的矛盾纠缠和痛苦体验,正是老舍文本的独具魅力之处。
侠客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困境,预示着他所代表的文化的逐渐陨落。中国的侠文化源远流长,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逐渐形成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时,侠文化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成为了必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产物,侠文化奉行的是“重义轻利”的价值准则,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历史氛围里产生和发展。到了近现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以“利”为价值导向的商业文化无疑会侵占“义”的空间——农业文明的原野、高山和森林逐渐被工业文明的高楼、工厂、烟雾所侵占;侠文化所代表的冷兵器时代被热兵器时代所取代,飞机、大炮、手枪使得身怀绝技的侠客们不堪一击。当老李由都市逃遁到乡间和沙子龙的“不传”回荡在黑夜中时,就隐喻了侠义精神领地逐渐消失的命运。
将沙子龙与侠客划等号似乎有些勉为其难。作为要养家糊口的镖师,他的行为并不是行侠仗义、快意恩仇,但沙子龙所行走的江湖也是侠客们的江湖,而他作为江湖中人也带有仗义、急人危难等品质,他对于“武”的虔诚、对于“义”的遵守以及“侠”的理解,与真正的侠客并无二致。因为在一个侠义精神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他们所受到的内心冲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把沙子龙也纳入侠客的范围,通过讨论侠客的困境来看看“侠”文化在现代社会里所遭遇的尴尬。
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于时代的变迁,沙子龙有强烈的意识:“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8]349。炮、枪和火车等现代产物使得刀、盾、长矛以及祖先的神明全都成了历史的遗物,皇帝也保不住了,在时代发生巨变的同时,沙子龙也改行开了客栈。他决心从“江湖”退出,绝不是和“侠”一刀两断,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精神坚守,也是为了避免“侠义”精髓在现实社会中遭受侮辱。沙子龙是带有贵族气息的人物,有着一腔的傲气,他宁愿带着自己的绝技进入棺材,也不愿意看到它在世间遭到践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变迁的残酷性和悲剧性。当侠客遭遇现代,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是个人,念念不忘的也不再是那些江湖的恩仇。历史的变迁,商业的发展,热兵器时代的到来,都对他们的生存空间造成了致命的冲击。他们最大的敌人来自于时代,作为侠客的个人是无法跟整个时代相抗衡的,这是他们必然消亡的悲剧所在。新时代的到来使得他们无条件地缴械投降,剩下的只是聊以自慰的深夜孤独的坚守,而伴随着昨日之梦逝去的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追求,还是一种高贵的精神和悠久的文化。
与沙子龙形成对照的是孙老者和王三胜,他们在对“侠”的理解上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制和时序性。如果说沙子龙是对“侠”的精神性坚守,那么孙老者代表的是“侠”的物质性痴迷,而王三胜则是注重“侠”的功利性投机。从沙子龙那里我们看到了“侠”的现在,孙老者活在过去,王三胜则代表着“侠”的未来。王三胜江湖卖艺继承的是武功表演化和商业化的末流小技,这是“侠”真正沦落的先兆。他不仅技不如人,武功缺乏造诣,而且对“侠”的精神境界领悟极低,在他那里武功只是混饭吃的工具,借此来装点门面以便追求到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之所以吹捧沙子龙,是因为要借沙子龙的名气上位,提升自己的行情,当有利可图时,便使劲吹捧,当无利可图时,便落井下石,极尽污蔑之能事。他不管在技艺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已经失去了武侠承传的资格,从这个市侩和钻营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武侠后继无人的真正衰落。
老舍对侠文化的衰落深感痛心,以至于他一改多数作品中的闹剧形式和玩笑口吻,而赋予《断魂枪》以严肃和庄重的悲剧意味,表达出他对于过去时代的眷恋和隐痛,“风萧萧兮易水寒,侠客一去兮不复还”。侠客们主动终结的不但是个人的生命,而且是一种文化的生命。沙子龙以自己的孤独坚守为这种文化献上了最后的祭礼,保留了最后一份尊严,“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8]357这种在黑夜里的孤独坚守,形成一种慷慨激昂的悲壮之感和风流俱往的悲怆慨叹!
在发现侠客与时代的矛盾之时,老舍也发现了侠客与国族之间的裂痕,完成他这一反思的是《茶馆》里的常四爷。作为旗人,作为中国人,常四爷看不惯那些为虎作伥的社会渣滓,也敢于仗义执言,是《茶馆》里正义的代表。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他到战场上去杀敌人,但是侥幸从战场上归来的常四爷并没有过上好日子,相反却在经历了辛亥革命、民国军阀混战和国民政府黑暗统治之后看不到生活的未来和希望,在他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之后,却无人为他的悲惨命运买单,他不但没有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而且无人在乎他的付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9]64常四爷的天问式困惑揭示出国族、社会与个人之间巨大的裂痕,这和巴金的《寒夜》暗通款曲,共同表现了大时代中个人的悲剧。常四爷和两个朋友最后撒着纸钱为自己送了葬,此时我们看到老舍似乎又回到他前期所具有的那种对于生命的荒谬感和虚无感的悲剧认识:一切都是个笑话,任何的抗争和付出最后都归于“无”。
四、结语
自古美女爱英雄。就老舍笔下的侠客来说,却是美女逐渐远离的过程,落入尘俗的侠客不得不遭受到“虎入平阳遭犬欺,鱼在浅滩遭虾戏”的悲惨命运。没有女性的依附和衬托,侠客们不但英雄意味尽失,而且男性身份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蔑视,变得岌岌可危。侠客们要么文弱无比,阳刚之气尽失,要么粗俗不堪,失去了英雄风流倜傥的铮铮铁骨和侠骨柔情,一方面趋向女性化使得自己的男性魅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又趋向野蛮和无知,有趋向无性的危险。侠客们不但从社会意义上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从生理和心理上对本体存在的意义提出了质疑。通过老舍小说中的这些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侠义精神在现代社会的遭遇和变迁,老舍敏锐地感觉到传统文化逐渐没落和消亡的悲剧性命运,侠义精神到此似乎可以终结。至于到了20世纪70~80年代金庸、古龙、梁羽生辈的叱咤风云,以及当今新武侠的颠覆与解构,则是商业消费时代的“嘉华年式想象”的狂欢,已与老舍无关了。
[1]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2.
[2]陈继儒.陈眉公小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3]董诰.《全唐文》卷七○九[G]//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1998.
[7]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8]老舍小说全集:第10卷[G].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9]老舍.茶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编辑:文汝)
I206.6
A
1673-1999(2016)12-0053-05
史玉丰(1977-),女,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焦作454000)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6-08-22
河南省教育厅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寻根意识研究”(2014-QN-64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