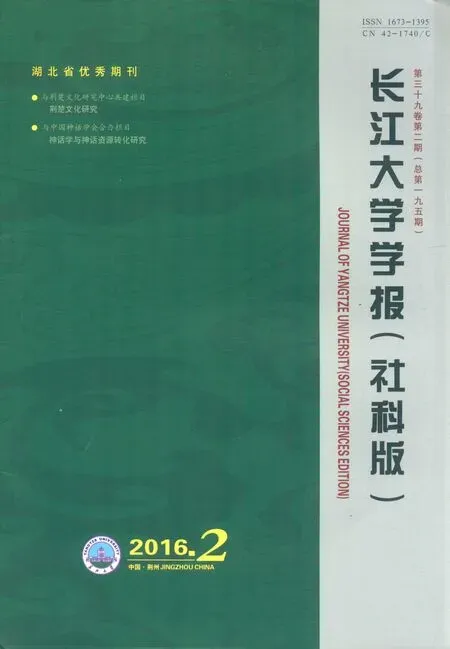程度副词“哏(很)”的共时分布与历时考察
2016-03-23刘金勤
刘金勤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程度副词“哏(很)”的共时分布与历时考察
刘金勤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程度副词“很”,又作“哏,狠”。“哏”产生于元代,明清常用“狠”。“狠”、“很”在汉代之前就已经产生,由于本义比较接近而经常混用,后虚化为程度副词。从“哏、很、狠”经常混用的情况可以推想,其程度义当由“狠、很”的“狠戾”之义虚化而来,为记录虚化后的程度义而新造词语“哏”。“哏”在元代语料中的分布状况,反映了蒙汉语言的接触和感染。
关键词:程度副词;哏;很;语言接触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很”源于元代新生的程度副词“哏”。“哏”主要用在元代的直译体文献以及会话课本中,在直讲体和纯汉语杂剧和南戏中极少见[1],现均录于下:
(1)那几个守户闲官老秀才,他每都很利害,把老夫监押的去游街。(《元刊·散家财·二》 )
(2)你不须提起蔡伯喈,说他每哏歹!(《琵琶记·三十七》)
(3)唐太宗是唐家很好底皇帝。(《经筵讲义·帝范君德》)
(4)行的好勾当呵,天下百姓心里很快乐有。(《经筵讲义·通鉴》)
(5)在上的人大模样的勾当不行,哏和顺。(《孝经直解》)
(6)先帝也哏理会得朋党不好,然而终不能勾去这朋党。(《直说通略》)
(7)贾后说哏道得是。(《直说通略》)
以上“(很)哏”以修饰形容词为主,如“好、歹、利害、快乐、和顺”等,也修饰动宾短语“理会得朋党不好”和动补短语“道得是”。
一、“哏(很)”在元代语料中的分布
“哏”多出现在直译体文献中,本文以直译体语料和会话课本为重点,考察“哏”的句法和语义特点。
(一)直译体中的分布
1.哏+形容词:
(8)如今地广民众,事物哏多有。(《朝纲一·典章四》)
(9)岀办的钱物入官的哏少有。(《户部八· 典章二十三》)
(10)省家的选法哏坏了有。(《吏部四·典章十》)
(11)田地相邻直至蛮子田地哏宽有。(《通制条格》二十八)
(12)奏呵,那里无得较少也者,哏是有。(《通制条格》十四)
(13)为那上头,他每哏生受有。(《户部十·典章二十五》)
(14)这般额定呵,哏明白有。(《通制条格》十三)
(15)如今吃饭的人多,种田的人少,日久以后哏不便当。(《工部三·典章六十》)
以上“哏”修饰单音节“多、少、坏、是、宽”和双音节“生受、明白”等形容词,此外还可以修饰否定形式“不便当”。
2.哏+动宾短语
(16)哏欺负百姓每有。(《户部九·典章二十三》)
(17)哏骚扰百姓有。(《礼部六·三十三》)
(18)江南田禾不收的上头,百姓每哏忍饥有。(《圣政一·典章二》)
(19)如今外前的猎户们哏打捕猎物有。(《兵部五·典章三十七》)
(20)俺省官人每各衙门官吏每接送呵,哏误了勾当有。(《通制条格》第八)
(21)指拘收不阑奚为名,那其间里哏做贼说谎有。(《通制条格》二十八)
(22)城子里勾当哏迟误有。(《通制条格》第八)
(23)为那上头,军人的气力哏消乏了有。(《兵部一·典章三十四》)
(24)那般交行呵,他每的气力哏费耗了有。(《通制条格》二十九)
(25)从这里马匹弓箭每、箭簳竹子等别军器也哏将去。(《兵部二·典章三十五》)
以上“哏”修饰动宾短语“欺负百姓、骚扰百姓、忍饥、打捕猎物、迟误了勾当”等,或动宾短语组成的并列短语“做贼说谎”。有时,如宾语前置于动词,“哏”则修饰动词。其中,“哏是+宾语、“哏有+宾语”比较常见:
(26)市舶司的勾当哏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有。(《户部八·典章二十三》)
(27)哏有歹言语。(《刑部十四·典章五十二》)
(28)军匠民战等户哏有窒碍。(《礼部六·三十三》)
3.哏+动补短语:
(29)圣旨哏道的是也。(《台纲一·典章五》)
(30)那般者,哏道的是有,好生禁治者。(《户部十三·典章二十七》)
以上“哏”修饰动补结构“道的是”,语义上指向补语“是”,即“道的哏是”。试比较:
(31)先皇帝根底哏道不是来。(《台纲二·典章六》)
该例为“哏”修饰动宾短语“道不是”,语义指向言说动词“道”,表明频率之高,程度之深。
4.哏+动词+宾语+补语:
(32)哏损着课程多有。(《通制条格》二十九)
(33)市舶司的勾当宋亡时分哏大得济来。(《户部八·典章二十三》)
“哏”与补语“多、大”配合使用,语法手段的重叠是语义强化的需要。
5.哏+交|教+名词+动词|形容词:
(34)哏交做买卖的人生受有。(《户部八·典章二十三》)
(35)係籍的医戶每哏交生受有。(《礼部五·典章三十二》)
(36)乐人每根底管民官每的勾当迟误说,哏教生受有。(《刑部十五·典章三十九》)
“哏”在使役句中,用于使役动词“交|教”之前,语义指向名词后面的动词或形容词。这种状语移位现象在现代汉语中依然很普遍。“哏”位于句首,比句中具有更广的辖域,其强调作用更强。
(二)会话课本中的分布
在《老乞大》中,“哏”具有与直译体中相同的语法功能,如修饰形容词及其否定式、动宾短语以及“哏是”结构等:
(37)汉儿小厮每哏顽,高廲小厮每较争些个。
(38)俺年时也在那里下来,哏便当。
(39)似这一等经纬不等,织的又松,哏不好有。
(40)既这般时,价钱哏亏着俺。
(41)这牙家说的价钱哏是本分的言语。
在《老乞大》中,与直译体相比,“哏”的功能有了一定的发展,可以用于比较句,还可以与形容词组合后直接修饰名词,而不借助助词“的”。这些用法,不仅直译体中不见,现代汉语也不具备。如:
(42)这桥便是我夜来说的桥,比在前哏好有。
(43)这桥梁,桥柱比在前哏牢壮。
(44)人蔘正关著,哏好价钱。
(45)今春新骟了的,哏壮馬。
前两例“哏+形”用于比较句中,现代汉语必须在被修饰成分后添加补语方可成立;后两例“哏+形+名”结构,现代汉语必须借助结构助词“的”。这种看似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用法,说明“哏”具有浓厚的蒙汉混合语特色。[2]“哏”很可能是源于元代并流行于北方的方言词。此外,直译体中“哏道的是”,在《老乞大》中作“说的哏是”,“说”对“道”的更替,表明后者的口语化程度;同时,“哏”由修饰述补结构逐渐转为修饰补语,句法关系与语义关系日趋一致。在直译体中,“哏”一般位于复杂短语前。其在《老乞大》中的结构已经十分简单,与现代汉语日趋接近。
从语义上看,在直译体中,“哏”除了修饰形容词和心理动词外,还可以自由地修饰一般动词、动宾结构、述补结构,如“哏将去”、“哏道不是”、“哏打捕猎物”等。这些核心动词本身不具有量级的语义特征,能受程度副词“哏”修饰,主要是为了强调动作本身蕴含的时间量,表示频率之高。频率从一定意义上看就是程度。这种现象在《老乞大》中已经大大减少,“哏”有16见,其中修饰形容词有15见,仅1例修饰动宾短语“亏著俺”,其中“亏”也是属于感受动词。可以说,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很”的基本功能,在元代《老乞大》中已经基本具备。
二、“哏(很)”虚化历程考察
程度副词“很”元代常作“哏”,明清时常作“狠”。其实三者本义迥异,仅仅是同音借词。《说文·犬部》:“狠,吠斗声。从犬,艮声。”《说文》段注:“今俗用狠作很,许书很、狠义别。”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狠,今用为很戾字。”《说文·彳部》:“很,不听从也。一曰行难也,一曰煞也。从彳,艮声。”桂馥义证:“很,借作狠。”由此可见,在清代,“很”、“狠”作形容词和副词时均经常混用。“哏”不见于字书,清代翟灝《通俗编·语辞》:“《元典章》有‘哏不便当’语。按:哏字未见于诸字书,而其辞则至今承之,如哏好、哏是之类。度其义,当犹云甚耳。”由此可见,“狠”、“很”在汉代之前就已经产生,且由于本义比较接近而经常混用,“哏”虽不见于字书,但在元代口语中却经常使用并流传至今。可以推想,“哏”是元代新生词语,其意义应当产生得比较早,并且从“哏、很、狠”经常混用的情况可以推想,其程度义当由“狠、很”的“狠戾”之义虚化而来,为了记录虚化后的程度义而新造词语“哏”。此类似于古今字中为分化的词义造今字。此外,汉语程度副词一般来源于具有量级的形容词,如“好、酷、殊、死”等。方言词语“蛮”与“狠”是同义词,也可表示程度义,表明二者具有相同的认知心理和虚化机制。
从“哏”的分布状况可以看出,该词主要分布在直译体语料和会话课本中。这些语料带有蒙汉混合语以及北方方言特色,因此可以断定,由形容词“狠戾”之义虚化而来并主要用于元代北方的“哏”是新生词语,并逐渐向南扩散。在明代《金瓶梅词话》中尚未发现用例,表明其扩散速度比较缓慢。或许因为“哏”是北方俗语词,纯汉语语料的作者一般弃之不用。此外,近代汉语程度副词系统比较庞杂,其他成员对新生词语“哏”也有一定的排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哏”在书面语中的分布。“哏”不仅可以作状语,还可以作补语,用于补语始见于明代[2],其在清代已经大量使用并延续至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作状语是一般功能,作补语是扩展功能。由于句末是语义的焦点,作补语时强调的语气更为强烈,所以程度补语“甚、很、透、极、死”等均表达极性量[3],其主观化程度均强于作状语的同类的程度副词。
程度副词“哏”由“狠毒”之义的形容词虚化而来,是元代北方的新生词语,带有较强的方言特色,主要在北方直译体和会话课本中使用,在杂剧和南戏中极少使用。在明代,“哏”的使用频率日益增多并可作补语,在清代,其逐渐取代其他副词而成为主导词。
参考文献:
[1]李泰洙.《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
[2]李崇兴,祖生利.《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3]唐贤清,陈丽.“死”作程度补语的历时发展及跨语言考察[J].语言研究,2011(3).
责任编辑 韩玺吾E-mail:shekeban@163.com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Degree Adverb “Hen”
Liu Jinqin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YangtzeUniversity,Jingzhou434023)
Abstract:The degree adverb “Hen”,also can be used as “哏,狠”,which produced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used as“狠”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In the Han Dynasty “哏”and “狠”have been produced,because the original meaning is close and often mixed,after became the degree adverbs.From the “哏、很、狠” often mix can be inferred the degree of meaning from ruthless and cruel,to record the virtualized degree and produce a new word "哏".The distribution of "哏" in the corpus of the Yuan Dynasty,reflecting the contact and infection of Mongolian and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the degree adverb;哏;Hen;language contact
收稿日期:2015-11-27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2014Z06010)
作者简介:刘金勤(1975-),女,湖北枣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近代汉语研究。
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6)02-007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