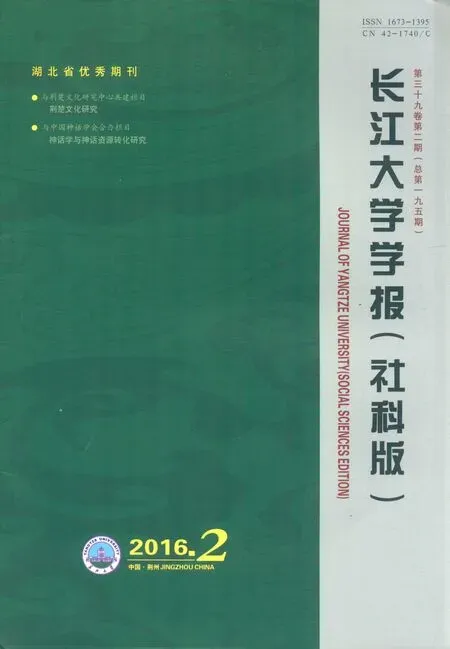《乌古斯汗传》与蒙古族感光受孕神话
2016-03-23陈岗龙
陈岗龙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编者按:
《乌古斯汗传》与蒙古族感光受孕神话
陈岗龙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通过古代回鹘文记录的史诗《乌古斯汗传》与伊斯兰教史学著作和蒙古文史书中记录的神话文本的比较,讨论了古代蒙古族建国神话。《元朝秘史》开篇的有关“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渡腾汲思而来”的记录并不具备神话叙事的要素,也不能构成一般意义上的建国神话。而相比之下,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神话在不同宗教语境的历史叙事中一直都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并在成吉思汗王统谱系中起着核心的关键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古代蒙古的建国神话或者王权神话是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神话,并且与早期的蒙古—突厥先民的长生天信仰有直接关系。本文的结论从建国神话的角度更加学理性地回答了蒙古族有没有狼图腾的问题。
关键词:乌古斯汗传;孛儿帖赤那;阿阑豁阿;建国神话;感光受孕神话
《元朝秘史》开篇第一句“成吉思合罕讷 忽扎兀儿 迭额列 腾格里额扯 扎牙阿秃脱列克先 孛儿帖赤那 阿主兀。格儿该亦讷 豁埃马阑勒 阿只埃。腾汲思 客秃勒周亦列罢”,是一个迄今为止未能彻底解决的学术悬案。这主要是因为《元朝秘史》原有的明代汉译文引起的,汉译原文如下:“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1](P1)从古代蒙古人离开额尔古涅-昆向大草原的西迁历程来看,《元朝秘史》开头这段记述反映的正是蒙古先民离开山林,进入草原的重要关头。因此,《元朝秘史》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当作全篇的开始。尽管明代汉译文的意思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更好的处理应是看作人名。今天我们认为,《元朝秘史》蒙古文原文的忠实翻译应该是,“成吉思汗的源流是上天有命的孛儿帖赤那,妻子豁埃马阑勒,渡腾汲思而来。”从朴素的记述来看,蒙古人并没有把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当作神话人物来记录。对比《元朝秘史》中对阿阑豁阿故事的重彩一笔,两者的差别悬殊。不过,对蒙古存有敌意的其他族群,倒是愿意选择“狼鹿”层面的意义阐释。明代朱有燉《诚斋乐府》中的《桃源景》一剧中,酒店女子骂抢食物的蒙古牧马人:“〔旦唱〕耸着肩似野狸,睁着眼似饿鬼,正是那渗[惨]白鹿青狼苗裔,恼的我一会家似醉如痴。”*方龄贵著:《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元朝秘史》汉译文的这种说法已经渗透到明代戏剧唱词中,也说明了“苍狼白鹿”的提法是早就有人知道的。由此可见,《元朝秘史》的明代汉译文就是“苍狼白鹿传说”的文献源头。于是就有了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是一对人名还是苍狼白鹿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而且近几年因为小说《狼图腾》和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蒙古族有没有狼图腾的争论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为了回应狼是不是蒙古族的图腾、蒙古族有没有图腾崇拜等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启动了“蒙古族图腾遗迹调研”,于2015年4~7月间分7个组分赴内蒙古自治区的6个盟市18个旗进行实际调研,完成10万字以上的调研报告,发现“蒙古族没有统一的民族图腾,更没有狼图腾”。该项调研虽然得出“蒙古族没有统一的民族图腾,更没有狼图腾”这样的明确结论,但是这种以今律古的做法实际上重新演绎了人类学进化论学派的“文化遗留物”学说。笔者认为,与其在当代民间寻找“文化遗留物”的痕迹,还不如重新认真考察和辨别相关古代文献中的神话文本,在学理层面上辨析有关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的记载是不是蒙古族的真正的神话。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重新考察相关神话文本的历史语境和性质,而且不能仅仅局限于《元朝秘史》和蒙古文史籍本身的记载,还应该拓展到相关民族甚至异文化的文献。本文主要以古代回鹘文史诗《乌古斯汗传》为重要参照点,再次考察蒙古族建国神话的记录语境。
一、《乌古斯汗传》与相关历史著作中记载的共通神话
《乌古斯汗传》是用回鹘文记录的古代乌古斯英雄史诗,其唯一写本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各国学者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耿世民先生的汉译本问世后,国内学界对该史诗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研究,涌现出了丰富的成果。不过,对《乌古斯汗传》的研究似乎主要局限在古代维吾尔族神话、史诗的研究和突厥语族民族神话、史诗的研究,迄今还没有学者将《乌古斯汗传》和蒙古族神话联系起来做系统考察。
从神话学的角度看,《乌古斯汗传》最突出的两个神话内容是狼的神话和天女的神话,而且都与光有关系。
一个是:有一天,乌古斯可汗正在祈祷上天,这时,夜幕降临了。忽然,从天上降下一道蓝光,这光比太阳还光灿,比月亮还明亮。乌古斯可汗走近一看,蓝光中有一位少女,独自坐着。她是位非常漂亮的姑娘,额上有颗亮晶晶的痣,像北极星一样。这少女如此的美丽,倘若她要是笑的话,蓝天也要笑,倘若她要是哭的话,蓝天也要哭。乌古斯可汗看到她时,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于是娶了她,一起生活,如愿以偿。少女怀了孕,一日日、一夜夜过去了,她临盆分娩,一胎生下三个男孩。大孩子起名叫太阳,二孩子起名叫月亮,最小的孩子起名叫星星。[2](P17)
一个是:翌日黎明时候,乌古斯可汗的营帐里,射进来像日光一样的—道亮光,亮光里出现一只苍毛苍鬃的大公狼。苍狼对乌古斯可汗说:“喂,喂,乌古斯,你要去征伐乌鲁木,喂,喂,乌古斯。让我在前面来带路!”乌古斯可汗起营上路了。只见队伍前头,走着一只苍毛苍鬃的大公狼,于是队伍紧跟在苍狼的后面行进。[2](P20)
《乌古斯汗传》是一部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古代萨满教信仰的乌古斯英雄史诗,而且,史诗中的内容作为乌古斯的生平事迹,在拉施特《史集》和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突厥世系》中都有记载。而拉施特和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都是伊斯兰教史学家,他们完全从伊斯兰教的立场上记录了相关的内容,与《乌古斯汗传》大相径庭。
乌古斯的诞生,在《乌古斯汗传》中是完全的神话和史诗的英雄特异诞生。“一天,阿依汗眼放异彩,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的脸是青的,嘴是火红的,眼睛是鲜红的,头发和眉毛是黑的,他长得比天神还漂亮。这孩子只吮吸了母亲的初乳,就不要再吃奶了。他要吃生肉、饭和喝麦酒,并开始会说话了。四十天后,他长大了,走路了,玩耍了。他的腿像公牛的腿,腰像狼的腰,肩像黑豹的肩,胸像熊的胸,全身长满了密密的厚毛。”[2](P14)
而《史集》中则记载道:“合剌汗作了父亲的嗣承者;他生了一个儿子,三昼夜不抓母亲的乳房,不吃奶;他的母亲为此哭泣祈祷。每夜她在梦中都仿佛看见孩子对她说:‘我的母亲!如果你信奉[真]主,爱戴他,我就吃你的奶。’由于她的丈夫[合剌汗]和他们全民都是异教徒,这个妇人害怕,要是她信奉真主被发觉,她就会和孩子一齐被杀死。她暗中皈依了真主,十分虔诚地作了[最高]真理——愿它普受赞颂——的挚友。于是婴儿抓着母亲的乳房,开始吮奶。”[3](P132~133)《突厥世系》中也是一样:“喀剌汗与其正妻生有一个俊美超过月亮与白昼的儿子。一连三个昼夜,这个孩子拒绝吸母亲的奶水。每个夜晚,他都好似陷入沉思,并屡屡恳求他的母亲皈依伊斯兰教,对他的母亲说:‘如果你不信仰真主的话,我将不再吃你的奶,就那样死去。’母亲出于对其新生儿的怜爱,在他的恳求下让了步,暗中回到了真主的怀抱,孩子也不再拒绝吃她的乳汁。”[4](P11)在《乌古斯汗传》中,乌古斯只吮吸母亲初乳就不再吃奶,是蒙古-突厥史诗中英雄主人公的普遍特征。而在《史集》《突厥世系》中,这种不吃母乳却变成了乌古斯要求他母亲信奉真主的条件,这是历史学家的有意改编。
而关于乌古斯的婚姻,两部历史著作的记载也和史诗不同。《史集》中记载的大意是:乌古斯的第一个妻子是阔思汗的女儿,乌古斯悄悄对她说:“你如果信奉真主,我就爱你,我就跟你好。”但是姑娘威胁乌古斯说:“我要告诉你父亲,让他干掉你。”因为乌古斯不喜欢第一个妻子,所以合剌汗又给她娶了古儿汗的女儿。也是因为妻子不信奉真主,所以乌古斯也不爱她。后来斡儿汗的女儿皈依了真主,乌古斯就娶了她并爱她。但是,因为前两个妻子嫉妒,向合剌汗状告了乌古斯信奉真主,于是合剌汗决意杀掉乌古斯,乌古斯和父亲对阵,打败了父亲。[3](P133~135)《突厥世系》也基本相同,只不过人名有出入。[4](P12~13)在史诗《乌古斯汗传》中,乌古斯的两个妻子分别是从光束中出现和在树洞里找到的,保留着古老神话的元素。而历史著作中的记载则是变成了乌古斯以皈依真主为标准娶妻的故事。
我们看见,史诗《乌古斯汗传》中的乌古斯的婚姻是保留着长生天信仰的乌古斯与天女之间的婚姻。而在《史集》和《突厥世系》中则变成了乌古斯以信奉真主为择偶标准。
我们还发现,《突厥世系》也记载了《乌古斯汗传》中的内容,但是已经篡改了其中萨满教的内容。在《乌古斯汗传》中的内容是:“乌古斯可汗坐在大帐里,在大帐右方立了四十尺长的一根木杆,杆顶上挂着一只金鸡,杆下拴着一只白羊。在左方也立了四十尺长的一根木杆,杆顶上挂着一只银鸡,杆下拴着一只黑羊。布祖克部人坐在右方,乌乔克部人坐在左方。宴席吃了四十昼夜,大家都很快活。”
而《突厥世系》的记载则是:“他(坤汗)又让人在左、右两边各树一根高40法寻的高杆。在右边高杆顶端上固定了一个金球,在左边高杆顶端上固定了一个银球。按照汗的命令,金球用作勃祖黑人及其仆从们的箭靶,银球用作兀出黑人及其仆从们的箭靶。他们应在纵马飞驰中发箭射击,射中箭靶者将获得价格昂贵的奖品。”[4](P24)《史集》中则没有这样的记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同一个人乌古斯汗的记载,在史诗和历史中是截然不同的。在史诗中,乌古斯汗是特异诞生的半人半神半兽型的史诗英雄,他的婚姻是天光中出现的美女为他生了三个儿子和树洞中出现的美女为他生了三个儿子,而且苍狼一直伴着他征战。而在《史集》和《突厥世系》中,乌古斯已经变成了引导乌古斯部落伊斯兰化的关键人物,乌古斯的诞生和婚姻完全取决于信奉真主的唯一标准。而且,在《史集》和《突厥世系》中为乌古斯带路的苍狼消失了,因为在历史记载中,乌古斯有了真主的引导,不再需要作为偶像崇拜的苍狼。
我们通过比较和考察,认为《乌古斯汗传》与蒙古族神话和史诗也有密切联系,甚至《乌古斯汗传》所具有的叙事模式与《元朝秘史》之间也有内在的联系。
首先,《乌古斯汗传》中有相当数量的蒙古语借词(或者与蒙古语相同的词汇),而且对长生天的崇拜和乌古斯与天光中出现的女人结婚的神话母题是相同的。《乌古斯汗传》中的“bengke kök tengri”(长生天)实际上就是蒙古语的“möngke kök tengri”(b和m在蒙古语和突厥语中相对应和置换)。可以说,早期乌古斯人所崇拜的“bengke kök tengri”和蒙古人的“möngke kök tengri”是完全一样的。《乌古斯汗传》中从天光中出现的美女就是与“bengke kök tengri”有关,乌古斯的婚姻就是和长生天有关。而苍狼也是从天光中出现的,是“bengke kök tengri”派来的。
有的学者也对《乌古斯汗传》与《吉尔伽美什》史诗做了比较研究,指出乌古斯与吉尔伽美什这两位史诗英雄之间有相似之处。实际上,《乌古斯汗传》具体受到《吉尔伽美什》史诗文本的影响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在吐鲁番曾经出土过与《乌古斯汗传》时代相近的蒙古文《索勒哈尔奈的传说》,也即蒙古文的亚历山大大帝传说,其中讲的就是吉尔伽美什寻找永恒之水的传说。如果我们把蒙古文《索勒哈尔奈的传说》、回鹘文《乌古斯汗传》和当时在中亚广泛流传的《吉尔伽美什》史诗译本放在一起讨论和比较,那么我们就会看到12~14世纪之间各种文化互相交流的一道风景。在这种文化大交流的语境中,很可能是《吉尔伽美什》直接影响了《乌古斯汗传》,而且《乌古斯汗传》与早期蒙古族神话和史诗具有源远流长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诸多共通性。
同时,我们还看到,《乌古斯汗传》和《元朝秘史》的叙事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性,那就是从祖先神话开始叙事,讲述主人公征服世界各地的英雄业绩。在这一点上,乌古斯征服世界各地和成吉思汗具有很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仅是主人公相似,而且还有可能就是因为作为史诗的《乌古斯汗传》,与作为史学著作的《蒙古秘史》,大约都有一个共通的“史诗-历史”叙事传统,这种“史诗-历史”叙事传统在蒙古-突厥民族以及波斯和阿拉伯世界有广泛影响。那就是史诗和历史著作是这些民族记忆历史的最重要的两个传统方式,民族神话保存在史诗传统或者历史传统中。我们从《乌古斯汗传》中乌古斯汗把征服的世界分给自己六个儿子的分配模式中也看到同时代的一些波斯史诗的影响。而且,从拉施特的《史集》看,当时的人们是相当熟悉《列王纪》这样的民族史诗的。[5](P133)
过去研究《乌古斯汗传》中的神话也好,研究《蒙古秘史》中的神话也好,都是把神话文本从整体著作中抽取出来,放到一起比较和分析,而很少关注记录这些神话内容的史诗或者历史著作的具体语境和记载性质,特别是宗教思想的背景。也就是说,不管是从史诗中抽取出来的神话文本,还是从历史著作中抽取出来的神话文本,放在一起就变成了“第一手资料”。而这种研究实际上犯的是弗雷泽的错误。普罗普批评道:“民族学者虽然经常引用民间故事资料,但是他们并不一定真正懂得民间故事。弗雷泽更是这样。他的《金枝》中虽然大量引用了民间故事资料,但是由于缺乏充分的分析,导致了对于民间故事的误读。”*参见(俄)普罗普著,(日)斋藤君子译:《魔法故事的历史起源》(日文),serika书房1983年版,第23页。中文译本见(俄)普罗普著,贾放译:《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页。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不同宗教背景下历史写作语境中的神话文本是不同的,历史学家运用神话文本和进行文化过滤也是不同的。我们分析这些神话文本,一定要把它们放在记录者的历史和宗教语境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不同历史著作中的阿阑豁阿神话与《乌古斯汗传》的关系
在《元朝秘史》中,除了对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的记载是不是神话有争论外,一个确定无疑的神话就是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的神话。而且,孛儿帖赤那和阿阑豁阿是成吉思汗祖先神话中的两个关键人物。不仅蒙古人自己的史学著作都有记录,而且《史集》《突厥世系》等伊斯兰教历史著作也都记录了这两个历史人物,但是记录的重点有所不同。我们先看看阿阑豁阿的神话。
在《史集》中,拉施特特别强调阿阑豁阿在蒙古族王权起源中的特殊地位。他说:“阿阑-豁阿属于迭儿列勤蒙古的一个分支豁罗剌思部落。按蒙古人的见解,[阿阑-豁阿]于[其]夫死后,曾感光而受孕,生下了三个儿子;属于这三个儿子氏族的,即称为尼伦。‘尼伦’意为‘腰’。此贞洁之腰表明他们[三子]起源于[灵]光。”[3](P249;P291)拉施特对该神话的详细记载是这样的:
按照这些前提,据说——讲述者[应对此]负责——阿阑-豁阿在丈夫死后过了一段时期,有一天,在家里睡觉。一线亮光从帐庐的[烟]孔上射进来,射入她的腰里。这个情况使她感到惊奇,她惊吓得不得了,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这件事。过了一些日子,她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当分娩的时日临近时,她的兄弟们和丈夫的族人们聚在一起说道:“一个没有了丈夫的妇人私下勾引男子怀了孕,这怎么行呢?”阿阑-豁阿回答道:“我没有了丈夫却有了孩子,不管[实际]情况怎样,你们猜测得对,你们的怀疑表面上看来也对。但是毫无疑问,‘有些怀疑真是罪过’。我怎么能作出应受责备的可耻的事呢?!的确,我每夜都梦见一个红发蓝眼的人慢慢地向我走近来,然后又悄悄地转了回去。我看得很真!你们对我的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我所生的这些儿子,都属于特殊种类。他们长大了要成为万民的君主和汗,到那时,你们和其他合剌出部落才会明瞭我这是怎么回事!”[5](P12~13)
在《史集》中,拉施特特别强调说阿阑豁阿是“万人的始祖”[5](P80),而相比之下,对孛儿帖赤那的记载并不突出。
我们再看看《突厥世系》中对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神话的记载:
一天清晨,当天快要亮时,她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道从帐房顶部天窗进来的白光惊醒。她清楚地看到一个长着一副白面庞、一双深蓝色眼睛的人从光束中出来,趴到她的身上。她想要喊叫以唤醒睡在旁边的女人们,但根本发不出声音。她想挣脱起来,但四肢如同瘫痪一样。但她的神志完全清醒,觉得这个男人轻柔地压在她身上,正在行使一个丈夫的权利。事情结束后,他就从来时的天窗出去,消失不见了。阿阑豁阿没有将这一奇遇讲给别人听,因为考虑到不会有人相信她的话。这个神秘的男人五六天后又来了,并且此后不时地前来造访。[4](P62~63)
《突厥世系》还强调深蓝色的眼睛,并且记载道,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巴阿秃儿生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蒙古人称这种眼睛为“孛儿只斤”。[4](P51)《史集》也记载了同样的说法。[3](P254)
《史集》和《突厥世系》中对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神话的记载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从天窗射进来的光束中走出来的人使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生下三个儿子;二是从光束中走出来的人是蓝眼睛或者深蓝眼睛的人。这与蒙古文史书中的记载不同,更像《乌古斯汗传》中的神话。
在《乌古斯汗传》中,乌古斯可汗祈祷上天时,从天上降下一道蓝光,这光比太阳还光灿,比月亮还明亮,蓝光中独自坐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少女,额上有颗亮晶晶的痣,像北极星一样。而乌古斯汗的第二个妻子,从树洞中发现的姑娘最突出的特点是,“她的眼睛比蓝天还蓝,头发好似流水,牙齿好比珍珠”[2](P18)。而《史集》和《突厥世系》中的神话文本则是把乌古斯的两位妻子的形象重叠在一起了,概括起来就是“从光中出现+蓝色眼睛”的模式。
而《元朝秘史》中的记载则是“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即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1](P7)
后世的蒙古文史书,包括藏传佛教思想的蒙古文史学著作的记载基本上和《元朝秘史》相同。最有代表性的《蒙古源流》中记载道:“脱奔·咩哩犍去世了。后来,阿兰·果火哈屯每天夜里都梦见一个漂亮的男孩子模样的人来与她共寝,第二天天一亮便出门而去。她把这梦常讲给妯娌们听。久而久之,寡居着生下了博寒·葛答黑、博合者·撒里直和孛端察儿·蒙合黑三个儿子。”两个儿子怀疑,阿阑豁阿把先前那梦的原由整个讲了一遍,又说:“由此看来,你们那三个弟弟很像是天神之子。”[6](P143)扎鲁特答里玛固实所著《金轮千辐》中记载道:“夜里有光进屋,黄色美貌之人从天窗而入,[亦说霍尔穆斯塔]服侍可敦,于是有了身孕生下长子天子孛端察儿博格达。”[7](P18)而官布扎布公的《恒河之流》和纳塔的《金鬘》中都记载为“光入阿阑豁阿身体”。[8](P43),[9](P20)
我们比较蒙古文史书、伊斯兰教史书和回鹘文史诗《乌古斯汗传》中的相同神话,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管是萨满教的史诗的说法,还是伊斯兰教史学家的记载,或是蒙古人自己的记录包括后来受藏传佛教思想影响的记录,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神话一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不变项*这里借用普罗普研究魔法故事结构和功能的术语“可变项”和“不变项”。。有一点是要特别引起注意的,那就是阿阑豁阿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生的三个儿子是天的儿子,而这个“天”的含义在三种不同宗教思想中是互相沟通的。在《乌古斯汗传》中,乌古斯的妻子是从天光中出现的美女,她与长生天(bengke kök tengri)有关;在《蒙古秘史》和《蒙古源流》以及所有蒙古文史书中,阿阑豁阿所生的三个儿子就是天神之子;而在伊斯兰教史学著作《史集》和《突厥世系》中,从光束中出现的男子有蓝色的眼睛,一方面与突厥有关系,一方面又是按照真主的意志。在这一点上,拉施特的解释正好反映了伊斯兰教史家对该神话的经典阐释:“阿阑-豁阿的丈夫朵奔伯颜早年去世。但无与伦比的造物主预先注定要让一个福星高照、威严雄武的君主出现在世上,让他征服世界一切国家,将驯服之轭驾到桀骜不驯的统治者们的颈上,这个君主的精神是那样坚强,他能统治世界,统帅所有的人,而在他之后,世界上所有的君主和地面上所有的统治者,都应当出自他的氏族——这就像那经过多年在壳内长成了一颗巨珠的蚌壳,但谁也不知道这是哪一个蚌壳,潜水者们经常潜入海中寻找这颗珍珠,他们找到许多蚌壳,获得了无数的珍珠,尽管这些珍珠全都各有一定用途,它们都属于珠宝,珠宝商将它们串成项链,而且其中每一颗都受到任何民族和任何人的珍视,[商人]将它们出售,买卖它们,进行交易——但众目所注的却是那颗名贵的珍珠,他[造物主]把阿阑-豁阿的纯洁之腰做成成吉思汗那颗宝珠降生所在的蚌壳,并在其中用纯洁之光创造了他的本体。”[5](P10~11)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不同语境中的史书记载的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神话,不管是伊斯兰教还是佛教,都稳定地保留了原来感光受孕的神话母题,而且这个核心情节链接着天和成吉思汗氏族的祖先。其中,从光束中出现的人使阿阑豁阿受孕和阿阑豁阿的身份,是固定不变的不变项。虽然阿阑豁阿在《史集》和《突厥世系》中属于豁罗剌思部落,与《蒙古秘史》和蒙古文史书有微妙出入,但是她的世俗来源是清楚的。这就是说,成吉思汗的母系是世俗的,父系是神圣的。世俗的母系不需刻意神化。下文关于孛儿帖赤那的记述说明了这一点。而使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的则是统一的从光中出现的人——这人代表着天神或者与天有联系,因此阿阑豁阿生下的三个儿子就是天子。在这一点上,阿阑豁阿与孛儿帖赤那有很大不同。
三、不同历史记载语境中的孛儿帖赤那
除了《元朝秘史》以孛儿帖赤那开篇以外,相关的中外历史著作也都记录了有关孛儿帖赤那的信息。
在《史集》中,对孛儿帖赤那的记载是比较客观而现实的,并没有神话色彩:“关于蒙古人最初生活的详情,诚实可靠的讲述历史的突厥讲述者说,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是从[某时]逃到额尔古涅-昆来的那两个人的氏族产生的.那两个人的后代中有一个名叫孛儿帖-赤那的受尊敬的异密,他是若干个部落的首领,朵奔伯颜与妻子阿阑-豁阿以及若干其他部落都出自他的氏族。他有许多妻子[哈屯]和孩子。名叫豁埃-马阑勒的长妻为他生了一个在诸子中最有出息、后来登临帝位的儿子,这个儿子名叫巴塔赤合罕。”[5](P6)在《史集》中也记载过尼伦部落的一个分支捏古思起源于察剌合-领昆的两个儿子坚都-赤那和兀鲁克臣-赤那*“兀鲁克臣-赤那”就是蒙古语“母狼”。,他们的后裔和氏族被称为赤那,又称为捏古思。[3](P255)而他们都是泰赤乌惕人的祖先。这就和成吉思汗的祖先孛儿帖赤那相差太远了。
在《突厥世系》中,对孛儿帖赤那的记载是这样的:“在走出额尔古涅-昆的时候,统治蒙古人的国王是孛儿帖赤那,他是乞颜和忽而拉思分支的后裔。他将使者派往各个部落,把自己从山中出来并抵达这里的消息告诉他们。其中有些部落对他友好相待,其他部落则视之为敌。鞑靼人向他们宣战。鞑靼人与蒙古人展开一场激战,蒙古人最终取得全胜。”[4](P31)《突厥世系》在其他场合提到孛儿帖赤那时记载也很简单:“当蒙古人从额尔古涅-昆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国王是忽而剌思奥鲁克的孛儿帖-赤那。”[4](P61)在《突厥世系》中,孛儿帖赤那只是作为蒙古部落首领的名字出现,而没有苍狼配白鹿的神话或传说的情节。
而《史集》和《突厥世系》中还体现出一种努力,那就是将孛儿帖赤那与乌古斯联系起来。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乌古斯是伊斯兰化的突厥人的祖先,因此把孛儿帖赤那的谱系上溯到乌古斯,就为伊斯兰教历史学家的写作找到了根据。《突厥世系》中记载道:“从孛儿帖赤那再上溯到乞颜,还有450年的时间。我们曾经尽力地想知道这两个国王之间互相继承的君主们的名称,但我们所有的探寻都没有结果,因为在任何史书上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段时间正是蒙古(蒙兀儿)人失败后躲进额尔古涅-昆之时,所以这些人的名称都失于记载。乞颜的父亲是伊勒汗。伊勒汗的父亲是腾吉思汗。腾吉思汗的父亲是明格里汗。明格里汗的父亲是余儿都思汗。余儿都思汗的父亲是爱汗。爱汗的父亲是乌古斯汗。”[4](P71)实际上,与《元朝秘史》从孛儿帖赤那开始叙述蒙古历史不同,《史集》和《突厥世系》用额尔古涅-昆传说把蒙古历史和乌古斯联系起来,将孛儿帖赤那上溯450年至乞颜再上溯到乌古斯汗。其结果就是,把孛儿帖赤那的谱系与乌古斯部落伊斯兰化的第一人乌古斯汗联系起来。这就是伊斯兰教史学的重要特征,相关历史学家也已经做过相当有说服力的研究*讨论伊斯兰教史学中相关问题的史学专业论文,可以参考日本学者宇野伸浩的《〈乌古斯汗传〉对〈史集〉构成的意义》等论文。,这里就不再重复讨论。
同样,在《蒙古秘史》以后的蒙古文佛教史学著作中,孛儿帖赤那逐渐与古代印度-西藏王统联系起来,为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找到了最有力的根据。如《蒙古源流》中记载道:“却说一个名叫隆南的大臣设计杀死海穴后侧金座王,自己即了王位,[金座]王三个儿子中的长子失宝出逃亡宁布地方,次子勃喇出逃亡保布地方,幼子孛儿帖·赤那逃亡工布地方。”[6](P75)几乎所有的蒙古文佛教史学著作都把孛儿帖赤那写成印度-西藏王统在蒙古地区的延续,从而孛儿帖赤那所渡来的“腾汲思”就变得更加复杂。[6](P171)
而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伊斯兰教的历史著作《史集》还是《突厥世系》,抑或是蒙古文佛教史学著作,孛儿帖赤那或者与乌古斯联系起来,或者与古代印度-西藏王统联系起来,其中孛儿帖赤那本身就成了一个任由伊斯兰教或者佛教按照自己的史学传统篡改身份的可变项。而且,在所有历史记载中都没有阿阑豁阿那样的神话元素成为孛儿帖赤那的标志,无论在什么样的宗教语境下都作为固定不变的不变项,支撑关于孛儿帖赤那历史记载的核心叙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蒙古族历史叙事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代表性人物,一位是孛儿帖赤那,一位是阿阑豁阿,他们分别代表了族源和王权。而记载有关他们的历史和神话的历史著作的性质也反映了他们本身的性质。从不同历史著作中记载的情况来看,有可变项和不变项的区别,也说明了阿阑豁阿的记载比孛儿帖赤那的记载更具备神话性,更能体现出蒙古族建国神话的特征和王权思想。而相比之下,孛儿帖赤那的记载已经没有了神话的光环,任由伊斯兰教历史学家和佛教史学家将其和乌古斯(伊斯兰化乌古斯部落先祖)或者印度-西藏王统(佛教王统)联系起来,就说明了这一点。
四、结语
在《乌古斯汗传》中,长生天是乌古斯人的最高信仰,与蒙古人的长生天信仰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其中,在乌古斯的婚姻和乌古斯征战中,从天光中出现的美女和苍狼,实际上都是长生天或者腾格里信仰的具体表现形式。《乌古斯汗传》的腾格里信仰是蒙古—突厥民族萨满教信仰的最集中的反映,在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和佛教化的蒙古人中,这种腾格里信仰也经过了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宗教过滤,具体表现在相关神话的历史记载中。因此,从历史记载语境,特别是从后来的不同宗教思想的过滤考察同一神话文本的记录策略,对我们正确理解相关的文献神话文本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
经过上面的考察,我们认为,《元朝秘史》开篇的有关“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渡腾汲思而来”的记录并不具备神话叙事的要素,也不能构成一般意义上的建国神话,因此只能看作客观的历史记载。而相比之下,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的神话在不同宗教语境的历史叙事中一直都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并在成吉思汗王统谱系中起着核心的关键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古代蒙古的建国神话或者王权神话是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的神话,并且与早期的蒙古—突厥先民的长生天信仰有直接关系。
参考文献:
[1]乌兰,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耿世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3](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M].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突厥世系[M].罗贤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5](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M].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
[7]答里玛,乔吉.金轮千辐(蒙古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8]乔吉.恒河之流(蒙古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9]纳塔,乔吉.金鬘(蒙古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琛E-mail:qiangchen42@163.com
Oghuznameand Photosensitive Pregnancy Myth of Mongolia Nationality
Chen Ganglong
(OrientalLiteratureResearchCenter,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Through the comparative text myth recorded by ancient Uighur epic Oghuzname and Islamic historiography and Mongolia history books,discussed the founding myth.The opening records of The secret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about Brte chonos and Aima Lang Le crossing Teng Kyrgyzstan Si-hai-come does not have myth narrative elements,it also can not constitute the founding myth in general sense.By contrast,Alan Huoa’s photosensitive pregnancy myth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high degree of stability in different religious context,and it plays a key role in Genghis Khan’s lineage.Therefore,we believe that the founding myth or the myth of kingship in ancient Mongolia is Alan Huoa’s photosensitive pregnancy myth,and has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arly Turkic ancestors of Mongolia’s immortal belief.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more rational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the Mongolia people have no wolf totem from the angle of the founding myth.
Key words:Oghuzname;Brte chonos;Alan Huoa;the founding myth;photosensitive pregnancy myth
收稿日期:2016-0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82)
作者简介:陈岗龙(1970-),男,内蒙古扎鲁特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蒙古学和东方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6)02-0001-07
中国神话学的百年学术史,从多个视角切入,可以发现丰富多样的方法论模型与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进入21世纪,神话学研究的多样性与转型特征十分显著。基于此,本刊与中国神话学会商议,自2015年1月起,计划用两年的时间,较为系统、深入地考察当代中国神话学的20位代表学者,每期刊发两篇论文:一篇是代表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一篇是对代表学者神话学研究的综述与批评。期望以代表学者的学术思想来构拟中国神话学的当代形态,思考中国神话学的当代问题与未来走向,建立起古典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本土文化逻辑,进而为中国文化转型的良性发展,贡献中国神话学的理论与智慧。本期特推出陈岗龙教授《〈乌古斯汗传〉与蒙古族感光受孕神话》及沈玉婵博士《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比较研究——陈岗龙神话学研究述评》,敬请学界关注并惠赐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