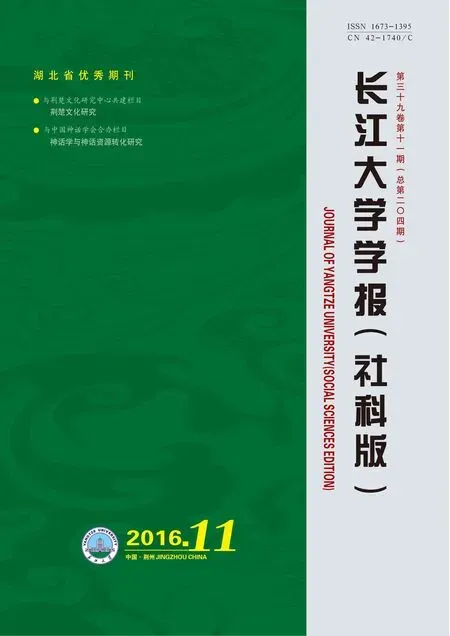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模式的经验主义矛盾
2016-03-23张举国戴巍巍
张举国 戴巍巍
(1.甘肃政法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模式的经验主义矛盾
张举国1戴巍巍2
(1.甘肃政法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社会制度建构理论不局限于社会学领域,也不单纯依靠经验主义的直接价值,更不能依靠经验主义的原理而否定系统理论架构的导向性作用。由于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在社会制度设计理论上,经验主义存在着排斥理性建构主义的思维倾向。在相关研究中,如以基础理论的经验主义矛盾为切入点,我们便能发现,经验主义容易陷入保守主义、个人主义、教条主义的泥淖之中。由此而言,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融合发展,是一必然趋势。
社会组织;社会救助;经验主义;矛盾
参与社会救助,是慈善组织的宗旨及基本职能。这是由其存在与活动的基本意义,以及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对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予以相关理论思考,不仅对推动慈善组织救助的制度化、专业化有着积极意义,而且也是社会转型中新型社会救助理念、体制、机制、方法创新之所必须。大多数社会学者将社会救助制度的研究重点,放在如何完善相关制度,以使其更具可操作性、适应性之上,这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与此同时,研究者也不应忽略社会科学的根本研究方法、方向性概念、系统性论证范式,以及对研究路径的必要反思。
一、经验主义的“幸福”
秉持经验主义的研究者通常是“幸福”的:他们可以忽略客观现实的实践特征,不加区别地套用经典理论,并以此解决几乎一切社会难题;同时,源自于经典理论的研究流派,通常又会固执地坚守自己的阵地,彼此之间互不干涉。例如,法学研究者们通常会将自己划入现有的某种经典理论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相关的理论探讨。这一路径,在欧洲人文主义思想革命中变得极为清晰,其影响留存至今。[1]我们可以说,格劳秀斯、卢梭属于人文主义时代的后自然法学派代表,但决不能说他们是前社会法学派的先驱,因为自然法学派重视朴素的社会规则,而社会法学者通常回避何为规则本原何为规则价值的问题,由此,二者之间无法达成模糊的融合。同样无法实现交流的典型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就是宗教学领域。研究者坚定地声称:宗教学有其特殊的规则本源,因此,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存在着天然障碍(当然,不同宗教流派之间的彼此挞伐,或许来源于其创设初期的自我保护,因此,其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对他们而言,只有排除本源差异的末端交流,才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佛教理论本土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此种交流非但不是天方夜谭,且更能促进宗教学说的发展与实践。因此,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方法论问题。如果经验主义者执着于负向型研究方式,即将目光着眼于过往事实的实践真实性,并将其视为指导未来制度设定的理论渊源,那么,他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过往即真理,存在即应然。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说,如果经验主义者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其制度创设本身就是错误的。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承认经验主义研究者所持的负向型研究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那么,这又将产生另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谁是第一个制度创设者?于是,我们就陷入了永久的哲学悖论之中:鸡生蛋,蛋生鸡……
结合社会保障的现有实践,经验主义者的以上理论,也可以转化为如下表述:社会保障制度的现有运行方式是不需要改变的,即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不需要引入不确定因素的非预见性干涉(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换言之,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并不存在改良的必要。[2]由此,这又将产生两个问题:其一,如此推导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制度存在合理性的质疑;[3]其二,第一个问题所产生的后果,必将引发学者们对更深层次问题的讨论,以使其避免得出由第一个问题所导致的可怕结论。显然,经验主义的理性派学者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在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他们站在了反对者一边。学者们共同讨论的问题是:在第一个问题中,经验主义教义派学者忽略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重要课题——存在的应然与实然,即教义派学者将社会关系或社会存在的应然性与实然性,做了绝对化的混同处理。当然,此种类似于涂尔干社会整体研究理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自有其哲学合理性,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反对派学者认为,社会实践的存在,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此种历史合理性,并不必然将社会实践导向社会的应然性价值,即不可以说,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必然应该永远存在下去。[4]由此,经验主义者与实证主义者的另一场论战即将展开:应然性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因篇幅所限,加之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讨论经验主义与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之关联,因此,对这样一场哲学讨论,本文不做具体阐释。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经验主义学者的所有研究方法都是错误的,在涉及社会演进过程的发展进路时,与激烈的教义派实证主义社会改良者相较,我们更赞同经验主义学说的某些理论,如保守主义的经验理论。我们之所以会支持经验主义者的某种社会研究取向,是考虑到社会演进并非一种理想型的设计过程,其必然会涉及到社会改良成本;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这种理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路径缺失:未能由单向的理论,导向实践并回归实践,借此促进理论的发展,并以此为新的起点,推动实践之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探讨的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恰是经验主义学者所忽略的。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中,这一经验主义研究路径的缺失,将带来如下两个后果:其一,在暂时不去讨论前文所述逻辑矛盾的基础上,我们将会看到社会保障制度稳健地存在着,并由此忽略社会个体因素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其二,在经验足以的惯性思维下,社会保障制度会保持或尽可能保持其现有存在及运行方式,并由此排斥非社会整体环境之外的因素的影响。
二、经验主义的“苦恼”
在有关社会制度存在与发展的研究中,经验主义者是“幸福”的;然而,其“幸福”的获得,却建立在对社会整体与个体差异性特征的忽略上。由于忽略了实践理性与构建理性之区别,因此,经验主义者无法解释行为意识与社会整体对象之间的关联性。
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理论: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整体性研究理论,以韦伯、布迪厄为代表的个体主义或多元综合主义研究理论。涂尔干的社会建构理论基于其对社会失序状态的判断。由此,涂尔干建立起了一套不同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国家构想的新的社会职业约束秩序观。此种理论模型的基础,是涂尔干对于19世纪晚期法国革命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涂尔干的研究方式及其所得出的结果,虽对当时乃至其后的西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仍旧没有摆脱经验主义的桎梏。涂尔干的实践理性,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指实践主体能以理性的方式从事实践活动,并达到此种实践所应然实现的状态。其包含两个部分:实践活动本身,设定目的的应然性。由此可见,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必然存在着思维创设因素;而涂尔干的经验理性,则更强调经验主义者推崇备至的实践部分,因此,在没有现实实践经验的前提下,其理性便无从谈起。涂尔干所谓的社会职业群体道德秩序,由于产生于此种经验主义范式之中,因此,其社会制度的构建理性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且其职业主义道德秩序是一个封闭的秩序系统,非相关职业者无法参与到其建构中来。如果用涂尔干理论指导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则会产生两种结果:其一,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承认相关从业群体或相关职业群体的自发性道德秩序,并将社会保障制度演进的希望,托付于此种实践的道德秩序;其二,反对非相关职业者参与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中来。但是,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在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所有社会制度都源于自发性建构的前提下,是否会产生综合性的社会管理制度?如果没有相关职业(群体)的互补与交叉,为何会出现整体性社会制度的概念,而不是单纯的个体职业制度的分别表述?显然,在社会制度建构过程中,这种实践为先的经验主义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社会保障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更多地指向实现自我的合理性。基于此,社会保障制度应关注全部社会成员,并在理想状态下,实现全部权利不完整状态的补充。这就需要做到两点:全部社会权利主体的制度参与,对全体社会成员权利状态的检视。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社会保障制度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完成其初始构建时期的既有封闭属性的职业化。假设我们承认,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某种建构与运行过程中的自洽形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就会是:这个被创设出来的社会职业群体,如何形成内部的秩序。在此,我们想先提一个前提性问题:自洽的职业群体如何与经验主义者的演进理论相融合?创设本身与经验主义渐进式的社会演化理论并不吻合,而社会保障制度显然并非产生于某种旧有制度的形态或名称的演进之中(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保障制度源于封建时代体恤制度的演化,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推论,这就意味着所有社会制度或社会存在都不具有创设性,也意味着经验主义演进理论的完全胜利);但同时我们要提醒经验主义者的是,这种假设如果能够成立,则意味着既消灭了实然与应然的差别,也消灭了经验主义者关于社会演进发展的必要性前提,最终消灭了经验主义存在的必要性。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自洽的职业群体如何实现社会职业的秩序化,一个可能的合理解释是:首先,应实现其准入的职业化,即针对职业者划定完整的职业群体界限范围,并由此实现职业者心理上的自我构建;其次,还应建立一种能够区分此种职业者与其他从业者之间界限的特定方式,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自身职业规则,但这样的职业构建首先会导向封闭化的结论,考虑到社会保障制度开放式服务的制度要求,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再者,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公益性社会满足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的唯一目的性就是利益再分配,并不是相对平等的利益交换,因此,受单向的利益制约,如果实现职业的特定化,则很难保证其运行的公正性,且其在构建过程中将要面对的控制社会成本的舆论压力,也是任何权力主体所无法承担的。[5]
由此可见,经验主义理论并不能完美地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当然,实证主义者也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唯一可能的做法就是:吸收二者之长,摒弃二者之短。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理论而言,经验主义的实践理论与理性主义的先验主义都有着同样的优势与弊端,二者均无法彻底解决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所存在的目的优先性与制度实然性之间的矛盾;而只有多种制度建设的综合理论即综合法学,似能达成制度设计过程中应然与实然的融合与协调。
[1]谢勇才,丁建定.从生存型救助到发展型救助: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困境与完善路径[J].社会与科学,2015(11).
[2]关信平.完善我国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5).
[3]彭华民.中国社会救助政策创新的制度分析:范式嵌入、理念转型与福利提供[J].学术月刊,2015(1).
[4]叶浩生.后经验主义时代的理论心理学[J].心理学报,2007(1).
[5]成素梅.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理论观及其影响[J].社会科学,2009(1).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Empirical Contradi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Assistance Mode
ZhangJuguo1DaiWeiwei2
(1.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GansuInstituteofPoliticalScienceandLaw,Lanzhou730070; 2.SchoolofLaw,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
The construction theory of social system is not limited to the field of sociology,also it does not rely on the direct value of Empiricism,and still can’t deny the guidance function of system theory framework on the basis of empirical pricinple.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there is tendency of rejecting theory construction in the design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system.This essay attempts to find the shortcomings of conservatism,individulism,dogmatism on the base of empirical contradiction which is the foundmental theory,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inevitable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between empiricism and positivism.
social organization;social assistance;empiricism;contradiction
2016-10-12
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13YD090);甘肃省民政厅2016年重大委托项目
张举国(1977-),男,甘肃景泰人,副教授,硕导,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究。
D632.9
A
1673-1395 (2016)11-00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