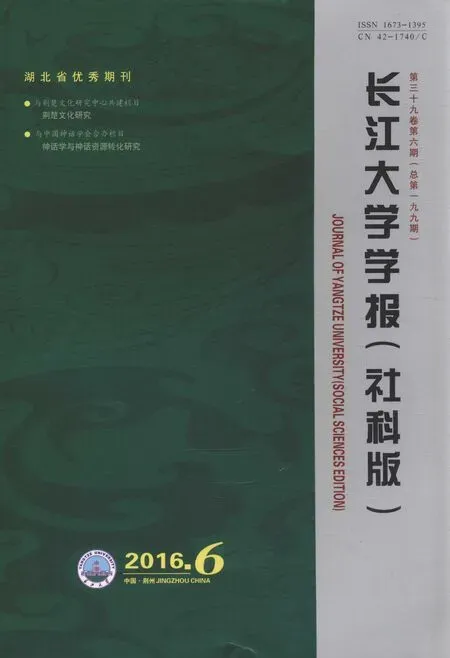论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在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案中的适用
2016-03-23徐孟华乐阳
徐孟 华乐阳
(1.华中师范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武汉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论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在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案中的适用
徐孟1华乐阳2
(1.华中师范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武汉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关联公司的兴起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关联公司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使资源的分配达到了比较合理的状态,有利于企业间的合作;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则利用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来逃避法律责任。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公报案例表明,虽然法院并不能直接适用《公司法》相关法条对关联公司人格混同行为进行规制,但是可以适用民法基本原则要求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这样的判决结果更符合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基本精神。
关键词:法人人格否认;关联公司;人格混同
股东有限责任和法人独立人格充分保障了公司股东的利益,但当股东滥用其权利时就需要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刺破公司面纱,直索股东责任,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平衡了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规定应该追究滥用权利的股东的责任,但对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的关联公司人格混同却并未进行规制。笔者拟通过刊登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10期的一则案例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在我国立法中的体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出台及实施,无疑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公司法》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也吸收、借鉴了外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一些在外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得到突出体现的法律理论和制度也逐渐出现在我国法律中,体现了我国对于人类文明成果的合理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是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并非对公司的全部债务负责,而仅仅承担相当于其出资额的责任。这样的规定减轻了股东在投资、设立以及经营公司时的顾虑,使得股东可以合理分配其投资,而不用担心要以自己的全部资产对某个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这大大激发了股东的投资欲望和市场活力。
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中两个重要的制度支柱是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这两个制度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股东和公司法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中股东滥用其有限责任和法人独立地位的情形时常发生。比如股东可能通过某种非法途径将公司在生产经营中获得的利润据为己有,一旦公司资不抵债发生破产时,股东仅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这样便可能侵害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了规范股东的行为,协调公司法人、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要求“视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为一体,对外承担连带责任”[1]。我国现行《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和第63条的规定均体现了这一理论。
否认法人人格制度的法律后果是直接追索公司背后的股东的责任,上述两个法条从不同侧面对适用条件做了规定。《公司法》第20条第3款适用于股东滥用其有限责任与法人独立地位,第63条适用于一人公司股东与公司人格发生混同的情形。但是在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另一种与此相似的情况:关联公司人格混同。关联公司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公司主体之间形成的一种组织联盟,它们之间存在控制与被控制或者是制约与协调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它们有统一安排或者共同进退的整体利益”。[2]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是指两个看似彼此独立的公司之间发生了组织机构混同、公司间财产混同和经营业务混同。对于因关联公司人格混同进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司法实践中多是通过否认有关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判令有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从而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法院的判例只具有参考价值而不能作为其他法院的裁判依据。《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和第63条仅仅规定了股东的责任,法院通过法人人格否认理论来裁判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案件,其理论依据何在?
二、案例回顾
2008年第10期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了一则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案例。当事人分别是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泰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来装饰”)、四川泰来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来房屋”)、四川泰来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来娱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以下简称“成都信达”)。
泰来房屋成立于1992年,为港商独资企业,其股东为沈氏兄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氏公司”)。沈氏公司以同样的方式在一年后投资成立了泰来装饰。1995年泰来娱乐成立,其股东为泰来房屋和泰来装饰,2004年泰来娱乐向泰来装饰投资,成为其股东。泰来装饰、泰来房屋和泰来娱乐虽然表面上是三家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但是三家公司的办公地址、电话号码和法定代表人都相同,财务管理人员在同一时期内存在相同的情况。泰来装饰将获得的借款大部分用于其他两个公司的经营,三公司的部分财务会计资料显示,它们的账目相互交叉、手续不清。
本案中,成都信达对泰来装饰享有到期债权,泰来装饰未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成都信达诉至法院,提出了若干诉讼请求,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泰来装饰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第二,泰来装饰、泰来房屋和泰来娱乐发生了人格混同,泰来房屋和泰来娱乐应该对泰来装饰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川省高院”)认为,“沈华源无视三公司的独立人格,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沈华源以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利用公司独立人格来逃避债务,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故泰来装饰的债务应由泰来娱乐和泰来房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审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是对被告行为定性的论述过程与四川省高院稍有不同。
三、案例评析
四川省高院在判决中多次使用了“滥用控制权”这样的表述,似乎想以《公司法》第20条第3款作为依据来否认泰来装饰的独立法人人格。但是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两个公司对另一个关联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未起诉股东;而且沈华源只是沈氏公司的股东,也并不是这三个公司的股东。因此,笔者认为《公司法》第20条第3款不能在此直接适用。一审法院通过引用《民法通则》第4条(即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合同法》第60条第1款(即严格履行义务原则)对本案进行了判决。
通过比较四川省高院的一审判决和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改变了对实际控制人沈华源行为的表述。
四川省高院认为泰来装饰、泰来房屋、泰来娱乐在同一地址办公,联系电话相同,财务管理人员在一段时期内相同,也是沈华源滥用控制权、公司人格混同的表现。最高法院则认为泰来装饰、泰来房屋、泰来娱乐还存在同一地址办公、联系电话相同、财务管理人员在一段时期内相同的情况。
四川省高院认为沈华源以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利用公司独立人格来逃避债务,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故泰来装饰的债务应由泰来娱乐和泰来房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法院认为泰来装饰、泰来房屋、泰来娱乐表面上是彼此独立的公司,但各公司之间已实际构成了人格混同。其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原审法院判令泰来装饰的债务应由泰来娱乐和泰来房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并没有试图依据《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法人人格滥用”来否认法人人格的独立性,而是直接从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等民法基本原则出发,注重主体行为的客观效果,落脚点在“人格混同”上。因为对于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问题,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无具体的条文予以规制,所以法院只能通过诚实信用原则作出裁判,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成文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局限性。
本案的二审审判长裴莹硕等在《人民司法》2009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详细分析了该案。她们对该案的评价是:“本文所述的案例……是对公司法所规定的法人人格否认规则的突破。对于关联企业的人格混同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正是本文案例的范本意义所在。”[3]
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当作用极其有限的实体法无法解决问题时,法官应该如何判决?最高法院原副院长李国光大法官和最高法院民三庭副庭长王闯在2005年发表于《人民法院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民法院只能根据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去判断某一具体案情,并依据诚实信用、善良风俗和权利滥用禁止等民法基本原则,在个案中实现这一制度规则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从而更好地体现出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的精髓。”[4]
四、结论
首先,在关联公司的人格混同案件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一般较为复杂,公司的行为当中究竟哪些是正常经营行为,哪些是混同行为,往往很难判断。作为债务人的关联公司发生人格混同,特别是财务混同之后,各个公司的会计账目往往就是一本糊涂账,想要理清各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状况也非常困难。法院在裁判几个关联公司之间发生人格混同并要求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时往往是以结果为导向。申言之,如果公司能够偿还所有债务,经营状况良好,债权人哪里会管几个债务人之间有没有发生人格混同?只有当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损害到债权人的权益时,债权人才会以人格混同为理由,要求相关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像本案一审法院四川省高院那样试图适用《公司法》第20条第3款,那么原告就必须要证明被告有“滥用”的恶意。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知道,由于证明对象本身具有模糊性,原告对此举证非常困难,所以,最高法院在二审中就放弃了适用《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转而以民法基本原则来裁判该案。
其次,我国《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和第63条均体现了法人人格否认理论,但是法条的规定仅限于直索公司背后的股东的责任,即依照我国目前的法律,只有当股东滥用其有限责任和公司独立人格时,才能刺破公司的面纱,“公司法人格之滥用者应限定在公司法律关系的特定群体之中,即必须是该公司之握有实际控制能力的股东”。[5]所以,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案件并不能直接适用上述两个法条,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时法院只能通过适用诚实信用等民法基本原则做出裁判。
最后,在民商事审判领域,法院在处理那些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案件时,可以依照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或者按照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国家的政策对案件作出处理。该制度在民商法中并不少见,比如我国《合同法》第124条的规定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公司法》第63条规定了当股东与一人公司发生财产混同且股东无法自证财产独立时,股东应该对他设立的这个一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文探讨的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与该法条所规制的一人公司股东与公司发生财产混同的情形非常相似,都是应该各自承担责任的两个民事主体之间责任划分不清。因此,司法机关在面对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案件时,可以尝试类推适用《公司法》第63条作为裁判依据。
参考文献:
[1]朱慈蕴.论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要件[J].中国法学,1998(10).
[2]王东敏.关联公司交易与债权人及股东利益的司法保护[J].人民司法,2014(19).
[3]裴莹硕,李晓云.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法人人格否认[J].人民司法,2009(2).
[4]李国光,王闯.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若干问题(中)——贯彻实施修订后的公司法的司法思考[N].人民法院报,2005-11-28(B01).
[5]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叶利荣E-mail:yelirong@126.com
收稿日期:2016-04-10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B2016454)
第一作者简介:徐孟(1988-),男,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
分类号:D922.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6)06-002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