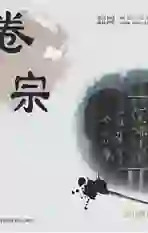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分析
2016-03-21李弈霖
李弈霖
摘 要:我们要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新的认识,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基于此,文章先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体系性构造缺陷进行了分析,然后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1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体系性构造缺陷
(一)《民法通则》第四章第一节明显名不副实、以偏概全
《民法通则》第四章第一节名曰“民事法律行为”,按通常立法技术看,该节之下所有法律条文(第54条至第62条)应该可以涵摄于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之中,换言之,该节所有内容应该是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具体规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民法通则》第四章第一节明显名实不符。如前所言,《民法通则》以合法性思维为标准对法律行为制度予以改造后,其第四章第一节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体系地看,实际上由三个关键词、三部分规范组成:一是民事法律行为及其相关规范,即第54条至第57条、第62条;二是无效民事行为及其相关规范,即第58条、第60条、第61条;三是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及其相关规范,即第59条、第60条、第61条。由此不难看出,民事法律行为及其相关规范仅仅涉及第四章第一节的一小部分规定,第四章第一节很大程度上着重规定了无效、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因为民事法律行为被界定为“合法行为”属于一种无法改变的前提条件,所以民事行为概念体系下的无效、可变更或可撤销的表意行为无论如何皆难以纳入民事法律行为的范畴予以解释。由于民事法律行为同样属于一种表意行为,《民法通则》第四章第一节以“民事行为”命名才能真正避免以偏概全的体系性缺陷。
(二)某些法律行为在法律效果上的特殊性被过滤掉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外在体系上的另一个显著弊端是,只以“无效”、“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等效力类型对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作出非常抽象的统一规定,既无法顾及某些法律行为在法律效果上可能存在的特殊性,又无法兼顾个别法律行为或意思表示在效力类型上的多样性或可转换性。前者如,对于欺诈、胁迫,不能对第三人欺诈、第三人胁迫的效力的特殊性作出明确规定;对于意思表示错误或误传,无法对非错误方因意思表示被撤销所遭受的信赖损失赔偿作出特别规定。后者如,像心里保留这种明显存在私法自治与信赖保护冲突,从而在效力类型上存在“无效”、“有效”两种规范可能的制度,在对“有效”、“无效”、“变更或者撤销”作出泾渭分明规定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妥当地作出安排。
2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改革
(一)我国现行法上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规范体系现状
概括地讲,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规范体系上主要由两部法律、三部司法解释构成。所谓两部法律,是指《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民事法律行为制度肇始于《民法通则》第四章,该章第一节通常被学界视为认识、理解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其实,体系地看,除其第四章外,《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一节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亦应纳入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范畴,其基本理由是:第一,在理论上,民事行为能力实质上指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第二,在立法上,《民法通则》第55条明确将“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规定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
《合同法》第三章关于“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实际上是对最重要、最典型民事法律行为———合同———的系统规定,“生效”、“失效”、“有效”、“无效”、“变更”、“撤销”等概念,充分揭示了该章的规范属性。对此,学界向来没异议。
所谓三部司法解释,具体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民通司法解释》第65条至第83条对“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性和补充性规定,“法释〔1999〕19号”第9条、第10条与“法释〔2009〕5号”第9条至第15条对《合同法》第三章的规定也作出了解释性与补充性规定。
(二)我国现行法上民事法律行为规范体系的总体特征
总的看来,我国现行法上民事法律行为规范体系至少可归纳出如下特点。第一,法律规定较为散乱。依法律规范的存在状况看,我国现行法上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明显较为散乱,这不仅表现为有关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分散于前述的两部法律及三部司法解释之中,而且表现为即使单独就《民法通则》或《合同法》来看其也有些散乱。例如,《合同法》第50条关于越权制度的规定,实质是为了解决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实施的法律行为的后果应否由法人承受的问题,不是关于合同本身是否有效的问题,将其规定在法人制度中较为妥当。
第二,法律规范前后有明显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民通司法解释》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对《民法通则》第四章有明显的超越和补充。例如,《民通司法解释》第67条所作“行为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应当认定无效”的规定,实质上承认了可依意思能力为标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作实质性判断,其完全超越了《民法通则》第12条第2款以年龄为标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形式性判断。再如,《民通司法解释》第76条关于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第77条关于意思表示转达的规定,皆属于超越立法的补充性规定。其二,《合同法》在立法观念与制度设计上对《民法通则》有重大修正:首先,不再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合法性行为,“合同无效”、“无效的合同”、“被撤销的合同”等表述是明显例证;其次,不再像《民法通则》那样规定(有效)合同应当具备的条件;再次,采纳一般规则与例外规定的立法技术,把“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定为一般规则,并对诸多例外情形作出了列举规定;最后,承认了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效力类型,并对其作出明确规定。
第三,法律规范残缺不全。虽然对《民法通则》有重大超越或革新,但在规范无效、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方面,《合同法》仍然因袭了《民法通则》的规定,未涉及一些法律行为,导致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规范体系上显得残缺不全。这突出表现为,立法乃至司法解释至今未对心意保留、虚伪表示、第三人欺诈、第三人胁迫等法律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另外,我国现行法亦未规定法律行为制度中涉及相对人信赖保护内容,如意思表示因错误或误传而被撤销时关于相对人信赖损失赔偿等。
第四,仍然采取“重效力、轻行为”规范模式。如前所述,在规范民事法律行为上,《民法通则》创造了以效力类型为纽带“组团式”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立法模式。《合同法》在规定合同的效力时,继承了这种模式。此种模式附带的规范缺陷实质上完全被保留下来。
3 结束语
在苏联民法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民法通则》以合法行为为根基、以民事法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严格区分为架构,创设了一种相当独特的法律行为立法例。以法律行为是践行私法自治原则的工具的法律思想看,我国现行法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规范逻辑上存在诸多不合理甚至是自相矛盾之处。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全面深化改革大势下,在自由被明确为一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文化观念下,应毫无疑义地以私法自治原则为基础、以信赖保护原则为辅助,深刻反思我国现行法上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并对此作出系统的完善。
参考文献
[1]赵桂华.浅议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重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9)。
[2]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