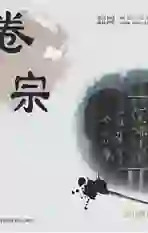刘再复的意义
2016-03-21刘效东
刘效东
摘 要:本文为一篇文学随笔,旨在从四个方面——理论体系的建构、理论体系的影响、理论体系的多元、理论体系的创新,来简单阐述刘再复的意义。
关键词:文学主体性;性格组合论;传统与中国人;大厦;丰碑;海洋;星空
某种意义上,假如没有刘再复,八十年代的文学理论是苍白的、文学理论界是沉寂的、文学理论体系是空洞的。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他是一幢大厦。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文人墨客不计其数,闪耀着智慧之光的高头文章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但大都对所阐述的思想做直观的、经验性的描述,鲜有人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建构了自己的理论大厦。古代、近代如此,现代亦然。太多的文化人倾一生之精力,竭终身之心血,青灯枯卷,皓首穷经,所做的工作无非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刘再复是个异数。一部《性格组合论》,煌煌三十六万字,对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的探究不是作者灵光一闪,更不是“微言大义”,其中既有对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实践的观照、省察,更有对文学现象所作的形而上的探索和归纳;既有丰厚的文学知识,更涉猎了哲学、美学、文艺学、心理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等学科的一些研究成果。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我在这部书中试图避免过去我国科学研究中常常存在的弱点,即缺乏自己所创造的范畴和概念系统。因此,我在本书的各章节中,都有自己论述的中心范畴和中心概念”。如此系统而又深蕴的原创性的文艺理论著作,客观地说,不仅在新时期是第一部,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刘再复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他是一座丰碑。粉碎“四人帮”,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大潮的到来,新时期的文学呈现出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新作家不断涌现、新作品层出不穷,但传统的、僵化的、极“左”的文艺理论仍禁锢着作家的心灵,束缚着作家的灵感。机械反映论大行其道,“文学的党性原则”、“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仍然是文艺工作者不敢碰触的禁区,一大批头脑顽固、思想僵化的“革命作家”仍然把持着文坛的话语权。在此背景下,刘再复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并捍卫了“文学主体性理论”和“性格组合论”,前者打破了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点的从苏联移植过来的旧的文学理论模式,为作家摆脱现实主体的角色羁绊而以艺术主体的身份进入写作状态提供了理论支持;后者通过“新方法论”的表述,使创作主体完成了从单向思维向双向思维的转换,“高大全”、“非好人即坏人”的一元论文学思维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刘再复的“两论”在写作实践中不仅为文学艺术家释放自己的创作激情扫清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障碍,纵然放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它惊醒了一代人,滋养了一代人,启蒙了一代人(马国川语)。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能涌现高行健、莫言这样世界级的大作家,刘再复功莫大焉——他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在新文学发展的道路上矗立起了一座高高的丰碑!
他是浩瀚的海洋。刘再复不单纯是一位卓越的文艺理论家,他还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散文家,一位有自己理论建构的大师级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开始在文学评论、散文创作、中国传统文化批评三条路径上快马加鞭、齐头并进,不仅有《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这样的大部头文艺论著,也有《读沧海》、《寻找的悲歌》等脍炙人口的散文,更有和青年学者林岗合作写出的《传统与中国人》——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大潮中,本书也是其中一朵耀眼的浪花。去国多年,刘再复没有停止自己的追寻(不像有些学者和艺术家离开了故国的土壤就江郎才尽),而是从大时代的拼搏回到了对生命存在的叩问,从家国情怀回到了终极关怀,就像他自己表述的:“在八十年代里,我的价值重心是‘学问和‘理念,现在的价值重心则是‘生命与‘灵魂。”他沉湎于思考、沉浸于读书,他近乎以癫狂的状态不知疲倦地写作:《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放逐诸神》、《罪与文学》(和林岗合著)、《红楼梦悟》、《共悟红楼》、《漂流手记》、《西寻故乡》、《独语天涯》、《双典批判》一部又一部闪耀着他思想光辉和精神气质的著作向我们“涌”来,使读者既目不暇接又欣喜若狂。他的创作量之大、之多,作品内容之广博、之阔大,犹如一片浩瀚的海洋。
他是深邃的星空。他是理论家,但他的理论不是知识和学问的简单堆砌,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架构和体系;他是思想家,但他的思想绝不人云亦云,更不拾人牙慧。从“文学主体性”到“性格组合论”,
从“告别革命”到“双典批判”,从“罪与文学”到“回归古典”,他的每一个新命题的提出都能在华人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和回应,每个命题的提出都渗透着他对“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独特思考。“告别革命”不是单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狭隘历史观的批判和质疑,不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简单消解和颠覆,而是提出了关于人类走向的大问题,他说:“可惜中国的未来,前途依然严峻,以‘革命为神圣中心概念的价值体系仍然覆盖一切,仅此一点,就让知识分子不敢过于天真。”《罪与文学》更是将中国文学放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来观照:中国文学无论是被视为“现实主义”还是被视为“浪漫主义”,也无论是被命名为“载道派”还是“言志派”,都没有越出关怀世道人心和感慨天地人生的范围,基本上都是现实生活的咏叹调,而咏叹之中或咏叹之外,我们都很难找到“旷野的呼叫”——对灵魂的叩问。《罪与文学》毫不掩饰的指出了中国文学的天然缺陷,它既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诞生海因里希·伯尔。因此,作者满腔热情地期待:我们希望自己和具有同感的作家,能够放下不必背负的“国家兴亡”的包袱,掉转身来审视自己的灵魂和他人的灵魂,把灵魂打开给读者看看,然后让灵魂发出“旷野呼告”,让灵魂发出不同声音的论辩。……读刘再复文章,每次都能得到审美的愉悦和心灵的满足,更能激发起自己探求新知的热情和兴趣——这大概就是思想家的魅力,也更是刘再复的魅力吧。他是那样深邃,他的思想和理论就像那神秘的星空,让你充满了好奇、充满了一探究竟的热望。
重读刘再复,我突然想起了尼采的一句名言:忧郁的心啊,是什么在激励着你不停地奔走,你究竟在期待着什么?